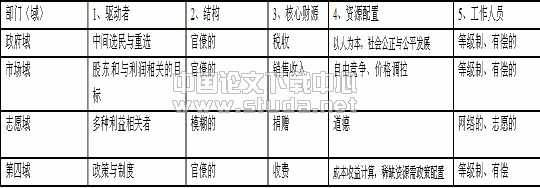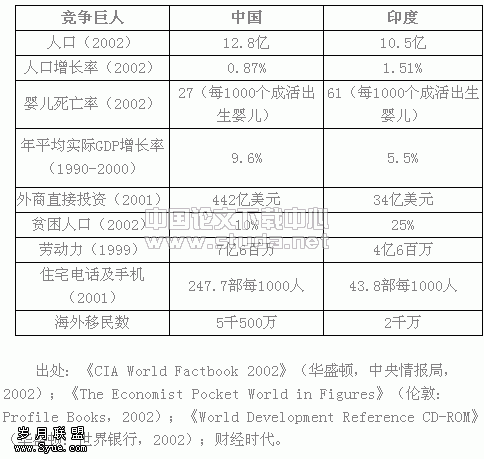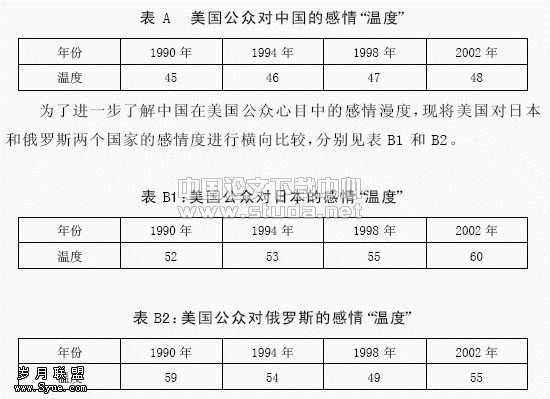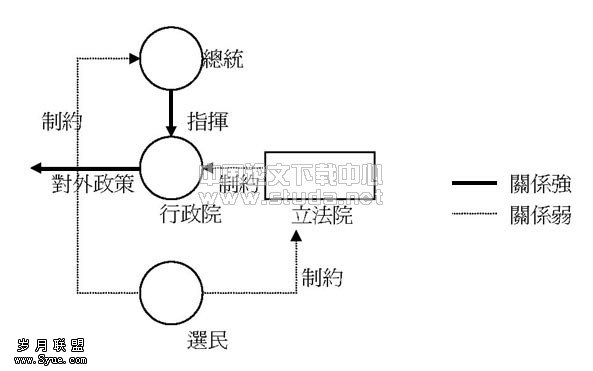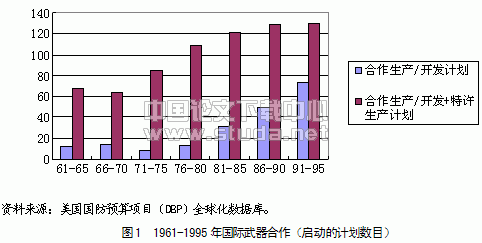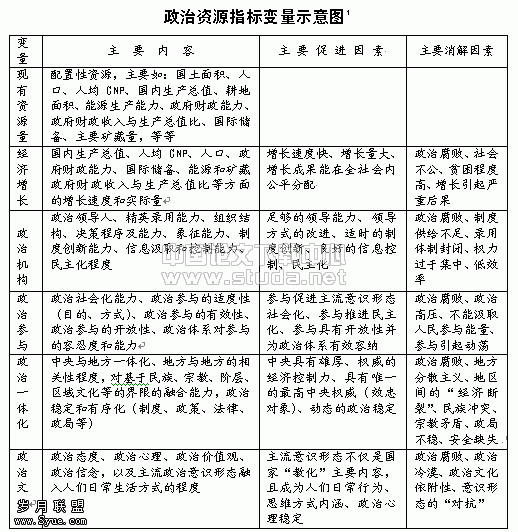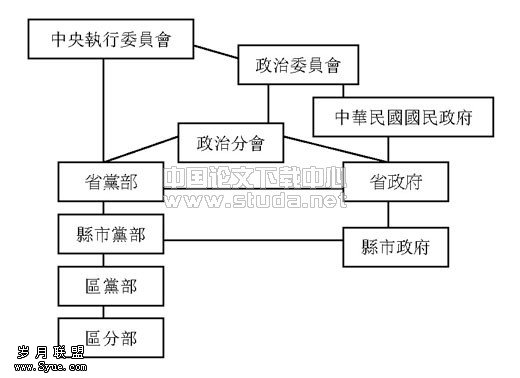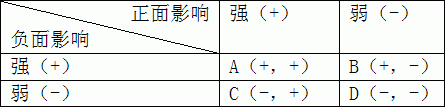理解政策失败中有选择的政治化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0
正如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不如意一样,公共政策也会遭遇失败,这种现象司空见惯。然而,有些公共政策的失败被人们视为“正常事件”:人们心安理得地接受它们,并认为在纷繁复杂的政府行为中这样的失败在所难免;而另外一些失败则会招致媒体的过分关注,甚至会引发政治动荡。政策失败会招来形形色色的反应:质疑、指责、调查以及来自媒体、议会和其他监督机构的批评意见。面对这些批评,决策者和决策机构则使出浑身解数予以应对,比如寻找借口、回击批评、推卸责任、进行人员调整乃至最后提出重大的改革动议。
本文试图对政治行为体在遇到紧急事件时的行为进行分析,并希冀本文的分析能够对相关的研究有所助益。我们在这里要深究的问题就是行为体是如何运用“界定”策略(framing strategies)对政治化事件的责任进行追究的。我们对既定政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进行了分析。界定(framing)和责任追究(blaming)的分析方法早已见于先前的政策分析之中,但是我们却找不到进行实证研究的例子。因而我们对行为体如何运用界定机制分配或推卸责任并不十分清楚。在本文中,我们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们将对两次军事行动进行剖析,这两次军事行动都出现了差错并最终都被政治化了。两个例子表明了在实践中界定和责任追究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分析,我们试图提出一般性的政治危机管理模式,并利用该模式对上述两个例子进行重新研究,进而提出一个初步的政治批评的界定模式(framing model)。 从瑞典海军的失败到政治动荡 1994年,瑞典海军笼罩在一片震惊和不安的气氛当中:人们对于外国潜艇入侵的理解和观念将要被彻底颠覆。瑞典经常发现外国侦察潜艇在其领海内活动,并时不时造成紧张的政治行动。1981年,一艘苏联潜艇在靠近瑞典海岸线的岛屿附近搁浅,这就为瑞典海军要求增强潜艇防卫的呼声提供了充分的理由。随后,瑞典海军得到了更多的财政预算并更新了武器装备。1992年,一种新的改进型的潜艇探测系统正式装备瑞典海军。事实证明,新技术是有效的。两年之内,海军探测到外国潜艇入侵的次数急剧上升,这些潜艇入侵事件都被记录在案并上报给政府。瑞典政府尤其是当时的瑞典首相对这些报告十分重视,并向莫斯科发出了正式抗议。首相本人长期参与防卫政策的制定,包括潜艇防卫政策的制定以及同苏联签订的若干双边条约的制定。他对苏军潜艇侵犯的事实深信不疑,认为政府不能试图压制民众的相关讨论,因为政府无法承受由此而来的政治风险。尽管抗议之声不绝于耳,这个事件还是迅速地被非政治化了。它成了仅供瑞典和苏联两国专家讨论的问题。在过去十年中,两国的专家致力于澄清记录、做出分析、得出结论,双方为此争吵不休。长期以来,瑞典海军专家和政治领袖一直指责俄国(前苏联)应对不断发生的潜艇入侵事件负责。 当瑞典的潜艇探测系统在1994年春被证明失效时,所有的指责都站不住脚了。在一次演习中,若干事件的发生促使瑞典海军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原先记录在案的潜艇声响或许来自于某种动物。当人们发现一种小型水生动物(水貂)同原先记录在案的特定声响存在直接的联系时,一切终于真相大白了。原先人们一直将这种特定声响作为敌人潜艇来犯的证据。 事情的真相被封锁于国防机构之内达数月之久。海军进行了更多的测试以检验结论的可靠与否。在国防机构内部,这种失误被视为一种“典型的情报问题和潜在的信誉问题”,当时的防卫情报部领导曾经如是说。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内部讨论之后,新上任的最高司令官排除阻挠,决定将事情的真相报告给政府并通报媒体。8月份,军队总部的新闻秘书向新闻界通报了海军所犯下的错误。 反对派领袖卡尔森(Carlsson)表示如果他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的话,他将对整个潜艇事件发起议会调查以澄清事实。反对派在随后的大选中大获全胜。在卡尔森的第一个首相任期内,他召集了一次咨询委员会会议,商讨国际问题。正是在这次高级会议上,卡尔森披露比尔德确实曾向叶利钦总统发出抗议信谴责俄国潜艇不断侵入瑞典海域。这封信并没有被解密,但是卡尔森对其前任的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为这种行为是不负责任的。人们就比尔德当时的行为是否合法以及他起草这样一封信时是否遵循了特定的国内程序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次会议结束之后,几位政党领袖就这些问题在媒体上发表了评论。大部分人对比尔德的策略表示质疑,认为他没有及时将这封信的内容及其意图通报给他们。在这一点上,所有的部长和议会成员都表示他们对是否存在这封信及其内容等问题一无所知。 这次事件对潜艇防卫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给与此事件有最直接联系的政治领导人的声誉涂上了一层灰色。潜艇防御的经费被削减,预算计划被重新修订。瑞典同俄国的关系也因此受到影响,因为现在整个世界都知道数年以来瑞典政府一直向莫斯科发去草率的信件,对所谓的侵入事件进行谴责,而事实上这样的侵入事件从来就没发生过。“水貂事件”导致瑞典政治结构中出现了长期的意见分歧。它引发了政治和军队领导人之间的对立,双方就潜艇政策最高审查委员会提交的审查报告争执不断。实际上,人们一直认为整个潜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防预算的重新调整,更多的预算投向了其他领域之中。 荷兰与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大屠杀 1993年,荷兰议会通过决议,批准了内阁作出的派兵到波斯尼亚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决定。荷兰的政策纯粹是出于道德的考虑,它希望自己能够在国际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为弱小民族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1992年,荷兰没能说服其他国家出兵,它自己也只是向冲突地点派出了增援部队而已。为了突出其维和色彩,荷兰对其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到了1993年,一支维和部队已日渐成形并整装待发了。尽管军事专家警告说荷兰军队对执行这样的任务尚没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且当时执行维和任务的条件相当不利,但是荷兰内阁和议会还是坚持派出了一个营的部队参加了“联合国保护部队”。1994年,荷兰军队被派往东波斯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在这个所谓的“安全地区”安营扎寨。 当斯雷布雷尼察失陷时,数以千计的难民潮水般涌向了荷兰军队的驻扎营地,这使得组织起有效军事防御变得更加不可能。食品短缺以及每况愈下的公共卫生状况使得斯雷布雷尼察地区很快就陷入了人道主义危机。立即撤退被认为是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必然选择。荷兰允许塞尔维亚军队将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俘虏运往Tuzla和俘虏营。然而,在接下来的数天内,血腥的大屠杀就降临斯雷布雷尼察地区了!大约7000多名波斯尼亚穆斯林士兵被杀害,其中很多人正是塞尔维亚人从“联合国保护部队”在Potocari的营地那边运来的! 当这次暴行开始为人所知时,Couzy将军——荷兰军队的司令官,起初仍向媒体吹风,说并没有证据表明真的发生了大屠杀。而荷兰的许多内阁部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描述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生的事情。由于怀疑军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情,媒体的批评因而变得辛辣而尖锐。一个电视台的节目无意中记录下了Couzy将军的一段话,后者提醒他的手下注意提防可能碰到的媒体关注。人们认为他发出这样命令的目的是故意不让媒体知情。在政治领域中,国防部长Voorhoeve则成了被攻击的靶子。逐渐地,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的过程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记者们抖搂出一大堆猛料,而国防部长对这些却一无所知……人们愈发怀疑军方隐藏了什么秘密;而政府则想尽办法维护荷兰军队的声誉。国防部长命令其手下为其提供一份详尽的报告,他试图以这份报告为依据对议会和媒体提出的问题做出回应。军方决定尽快对回国的荷兰士兵进行询问。整个询问过程缺乏深入的调查。结果却适得其反:媒体披露了军方内部存在的一些妥协,而这些内容却没有在报告当中得到丝毫的反映。到了1996年秋天,面对日益强烈的要求进行公开调查的呼声,内阁命令荷兰战争局(NIOD)对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的前前后后做彻底的调查。如此一来,就只能用时间来洗刷事情的真相了:等到荷兰战争文献局提交最终调查结论时已经是七年之后的事情了。 2002年4月10日,NIOD终于将调查报告递交给了内阁。报告主要对做出派遣维护部队的决策过程进行了质疑,尤其是对荷兰军队被派往斯雷布雷尼察地区的动机、使命和任务进行了调查。报告认为整个事件的根源就在于内阁决策的失败,而正是内阁在1993年做出了派遣军队的决定。当时的内阁已于1994年下台,其中很多关键人物自此在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报告认为,当时的几届内阁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们支持派军政策并在1995年7月的危机管理中出尽了洋相。然而,决定性的判断失误在这之前就已经发生了。报告也对联合国进行了指责,批评其发起的维和行动在军事上不具备可持续性、政治价值含糊不清;在危机升级时不能做出有效回应。荷兰媒体认为NIOD有意为荷兰士兵进行辩护,后者在当时眼睁睁地看着暴行的发生而无所作为,并因此受到了猛烈抨击。报告尤其对军队里的军事领袖进行了批评,特别是对其在1995年7月危机之后信息管理方面的失败进行了抨击。 NIOD的报告引发了公众和政治领域的激烈争论。首相Kok(他在1989-1994年的联合政府中任财政部长,在1994-2002年期间任荷兰首相)认为自己在当时已经倾尽全力,因而没有理由辞职。在同一个星期的晚些时候,Jan Pronk(他是1993年的内阁成员、原联合国副秘书长,时任Kok政府环境部长)在电视上发表评论,公开反对首相Kok的看法。他认为当时内阁(包括他本人)的所作所为是“极其”失败的。一些媒体的代表敦促De Grave(当时的国防部长)主动为军队的失败承担责任。由于De Grave只是在1998年才当上国防部长,因而他的辞职将会导致整个内阁的垮台,因为整个政府的集体责任(作出派兵决定)将大大超过De Grave本人应承担的责任。Pronk的公开言论“提高了反对者的声音”。正因如此,首相对其大加斥责;当听到Pronk公开的坦白时,首相本人“大为不悦”。当天在被邀请做电视评论时,Pronk猛烈抨击了媒体,宣称当涉及到政治中的道德立场时,“你从来都不可能拥有正确的答案”。首相形容Pronk的评论是“令人尴尬地脱离于(running ahead)内阁讨论和议会辩论之外”。NIOD报告提交的时机进一步导致讨论被政治化。接下来Kok决定采取主动。他在2002年4月16日提出辞呈,一同辞职的还有其内阁的所有部长。在五月份的选举中,这两个联合政党(coalition parties)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失败。 失败的界定与再界定(framing and re-framing failures):政治化的不同模式 在这些案例中,当涉及到责任政治或责任分担时,我们将从危机“管理”方面的三个视角对其进行分析,后者是我们从那些关于界定过程的研究文献(framing literature)中归纳出来的。这三个视角是:把事件描述为对核心公共价值的破坏;将事件描述为操作性失误或是特定问题的后果;确定谁应当为事件的发生(或应对危机不利)承担责任。 突出事件的严重性:核心价值被破坏了吗?唤起人们对价值的关注是政治化进程的核心。在这一点上,上述两个例子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我们将由此出发,深入分析政治化进程是如何一步步演进的。政治行为体界定的一系列事件对核心公共价值的破坏程度决定了这些事件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政治和社会争论的热点问题。当绝大多数人把情况界定为非政治性的、认为它们不会对核心价值造成威胁时,那么事件就会被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将事件界定为危机——而不仅仅是“事故”或“扰乱”——是任何批评政治(politics of blaming)的前提条件。各种对非正常事件的解读方式将会彼此展开竞争,争取在对事件的解读占据主导。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政治和组织的得失瞬间就会发生转换。 一些问题是如何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呢?它们又是如何保持或失去其“危机”地位的?事件发生的时机及其涉及到的实质内容是特定事件为何受到特别关注的重要原因。关于时机,Kingdon认为一个事件必须恰好发生在特定公众关注和时机刚刚产生之后。他写道:“如果事件并没导致任何形式的权威性决定的产生,那么行为体很快就会对它丧失兴趣。”如果事件没能获得被持续关注的动力,那么媒体及其他大多数政治行为体很可能对事件失去兴趣,转而将注意力投向其他热点事件。Nelkin认为,如果事件与实质性价值——这些实质性价值触动了诸如公正、民主和自由等广泛的社会主题——联系在了一起,那么人们对界定过程(framing process)的参与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争论就会变得高涨起来。在这方面,艾德尔曼(Edelman)强调了“国家安全”作为一种具有伸延性概念的极端重要性。与此相反,当大多数人将事件界定为“并非至关重要”——即认为事件是程序性或技术性问题时,对界定过程的参与浪潮就会大大减弱。Rochefort和Cobb认为,人们所意识到的事件的“严重”程度是吸引政府官员和媒体关注的关键之所在。事件被人们描述得越严重,参与争论的行为体可能会越多,政治争论的范围也就越广。这部分取决于那些唤起消极情绪的信息的可获得性。这些信息包括:令人震惊的图片、触目惊心的统计结果以及目击者令人惊骇的叙述。 因此,政治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必须存在一定数量的有影响力的行为体,后者能够在事件和政治体系的核心价值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一旦这些“危言耸听”的话语被用来确定事件的解释框架,那么对于事件的其他任何理解都会被排除在这个解释框架之外。因此,政治行为体被迫就事件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将自己纳入到特定的阵营当中。因为一旦发生政治危机,责任分担问题就会被摆到台面上。如果危及核心价值,那么人们不禁会发出“是谁负责保护这些核心价值”这样的疑问。既然在现今的风险社会中,“偶然”、“事故”或“不幸”这样的词汇早已不再被人们视为是出现社会问题和现实危险的理由,那么如果事件果真发生了,就必须有人为它承担责任。因而对“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谁应当为此承担责任”等问题的界定就会同公众和政界对重大事件的反应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些问题,利益相关者会做出不同的界定并彼此进行竞争。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发生,利益相关者就这些问题展开的话语斗争将会影响公众对它们信誉和地位的认知。 尽管在上述两个例子中,至关重要的价值——在瑞典是政府信誉,在荷兰则是军队的诚实——据说业已遭到破坏,但是只有一个事件被迅速提升到了高级政治的程度。在瑞典,事件被界定为基本的政治和外交政策问题,这就导致了两位高层政治领导人相互指责,后来又为国内外对瑞典政府信誉的公开辩论。在荷兰,从一开始政策失败就被隔绝于公众的视野之外。准确地讲,这是因为事件本身太过于棘手——这是一个最令政府感到难堪的争论话题——因而通过发起一个非政治的、费时的调查过程,荷兰政府果断地延迟了议会质询和媒体审查。在那段时间里,这个问题仅仅是专家们的事情;与此相反,瑞典的事件在开始时仅限于专家的小范围,但随着比尔德和卡尔森相互指责的升级,整个事件最终被公开了。 确定事件的责任人:追溯既往与顺藤摸瓜(Constructing agency: going back and going up) 当对“严重性”的争论烟消云散、事件业已被贴上“危机”标识时,政治行为体就会对事件界定过程的其他方面产生兴趣。在当今媒体和政界关于危机的语境下,人们在“发现”危机之后几乎立即会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对于这个问题,一般有两种典型的回答:危机或者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尤其被理解为体系或政策中出现的紊乱和失调,而这些问题本来是可以被避免的;危机或者被认为是一个“有深层原因”的事件,即危机只是更大的体系失败或政策失败的“征兆”而已。这两种理解究竟哪一种会被人们采纳取决于参与者当时在危机辩论中所持有的看法。人们越是强调危机的现时原因——比如将“飞行员的操作失误”作为飞机失事的原因,或者认为警察系统的腐败是由于存在“害群之马”的缘故——则技术的、操作性的、次要的原因就越有可能被当作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评论员和调查人员越是倾向于在更广的时间跨度下审视当前的危机,他们就越有可能放大深层次原因的巨大影响——他们会强调飞机的调度和飞机维护制度是飞机失事的重要原因,而警察系统的组织程序、文化和道德规范则会被他们认为是警察系统腐败的深层次原因。这些深层次原因植根于之中,它们往往会牵涉到决策者和重要的高层行为体。正如Boven和Hart所说的:追溯历史通常都意味着要将级别更高的官僚揪出来。 事实就是如此。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旦出现什么紧急事件,高层决策者总是急于将相关的调查和争论限定在有限范围之内,而反对派、记者和评论家们则正好相反。如果事件被认为是长期存在的问题,那么人们提出的问题就会更尖锐,事件可能牵扯到的行为体的数量和级别也会大大提升。当要求扩大调查范围的呼声日益高涨时,那么调查或许会质疑整个治理体系的组成结构并使后者的形象大大受损。那些支持进行彻底调查的人或许会和一些机构的工作人员或管理者结成联盟,而这些机构本身对危机的发生难逃干系。对于后者而言,这样做可以提醒人们: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在进行调查时,人们也应将先前事件的基本情况、思维定势、深层次的惯例以及外部资源的限制等因素考虑进去。对于工作人员和中层管理者而言,当他们感到他们的上司和领导人试图让他们去做替罪羊而故意限定调查的范围时,他们联合外部批评者以扩大危机调查的时间范围的倾向就愈强烈。另外,除了事件的直接责任人之外,其他社会行为体或许也同危机的发生难逃干系。比如在瑞典的例子中,卡尔森认定潜艇事件应被彻底调查,而这得到了那些呼吁政府更加开放的人士的积极支持,因为这是一个民主的原则问题:民众理应享有知情权。 在这两个例子中,两国处理责任人问题的方式迥然不同。在瑞典,几乎在比尔德首相的信被公之于众的同时,水貂事件就由一个操作性事件迅速升级为根本的政策和政治问题。人们很快就发现这并非仅仅是一个技术上的误判:比尔德不得不解释为什么要发这封信、这封信是如何起草的以及当时还有谁知晓信的内容。比尔德辩解道,他不过只是在继续他的前任们早已定下来的政策路线。这样一来,比尔德试图在事件和他的前任们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比尔德辩解道,如果他因为言词激烈而冒犯叶利钦总统是个错误的话,那么他的前任们也应受到谴责,因为他们一直所声称的苏联军事入侵现在看来根本就是杞人忧天。 在荷兰,调查涉及的时间范围的扩大更大程度上是一种“逐步上升过程”的结果,它并没有沿着瑞典例子中的逻辑模式。Srebrenica失陷后,媒体报道和公共辩论的焦点逐渐从“当事人”——荷兰士兵、尤其是他们饱受指责的司令官Colonel Karremans——向上转移。人们不禁要问:为何荷兰军队得到的命令是如此的死板?为何荷兰军队和联合国总部之间的沟通是如此不通畅?为什么荷兰军队的火力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为什么荷兰军队对任务的准备是如此的不充分?这些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人们不仅要关注1995年初荷兰军队被派往Srebrenica这件事本身,人们还应该关注在这之前的军事战略和联合国决策过程的各个方面。不久之后,人们批评的焦点集中在了荷兰的政治决策过程之上,正是后者赋予了荷兰军队一项不具备军事可行性的任务。因而,批评的矛头指向了那些支持荷兰军队参与此次维和行动的部长和议员们。面对民众要求进行调查的强大压力,荷兰首相采取了一项高明的策略:他任命一个倍受人们尊重的机构对整个事件进行调查,而整个调查的范围是如此之广,因此它一定会持续好多年的时间。荷兰首相并没有直接回应批评的浪潮,与此相反,他下令对事件进行调查的范围比民众要求的还要广泛,借此,他使整个事件拖延下去(on hold)。这种做法在策略上是成功的:在1998年大选期间,Srebrenica事件的阴影已经被逐渐冲淡了。但最终它还是导致Kok首相和他的内阁于2002年下台。 在这两个例子中,瑞荷两国处理责任人问题的方式截然不同,这似乎同行为体的策略及其表述方式没有什么关系。两起事件的性质和程度是根本不同的:水貂事件只不过是一起军事事故的曝光,它只不过引起了一些外交后果;而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却是一起针对数以千计的平民的大屠杀。后者的性质如此恶劣,因而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道德上几乎都不可能把它看作仅仅是由于操作人员失误而导致的令人遗憾的事件。诸如此类的重大灾难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某些“重大”原因,因而它一定会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 确定责任:批评的对象应该集中一些还是更分散一些呢?针对特定的有争议的政策,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倾向于通过界定谁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以及指责)的方式支持自己的观点,这就是第三个维度,即责任的分担。责任的分担并不遵循“追溯既往意味着追究上层”的逻辑,因为即使人们都认为悲剧的发生不只是实施部门的失职,高层官员最初的决策和行为也难辞其咎。但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是究竟是谁应该受到惩处。 被指责者可以辩解道,问题的发生源于体系的失败。在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时,他们会列举出一大堆复杂的因果关系链,后者涉及到行为体、决策和结构之间的互动。他们会尽力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众所周知的“多头管理”(many hands):责任被分散,这样他们就可以逃脱惩罚。而且,当重大事件的范围被扩大时,这很地会将原先的做法、邻近的政策领域以及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凸显出来,因而彰显了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政策问题的存在。这就导致居于政治议程之上的是政策问题而非责任追究问题(blaming issues)。如果问题的原因被认为是复杂的,那么一些简单易行的应对办法——比如将相关部门的部长或领导革职——就会失去它们原先的吸引力。相反,如果事件被认为是由于(单个)行为体的失误导致的,那么寻找替罪羊或“避雷针”(lightning rod)的做法就会应运而生。 Rochefort和Cobb指出,当政治领导人只用为数不多的几个因果因素界定某个重大事件时,这就表明他们准备采取措施处理问题。当事件被认为并非复杂问题时,那么它牵扯到的行为体和利益的范围就非常有限。这样一来,责任分配的问题就不那么棘手了,人们能够很容易地指出哪些行为体和事件的发生难逃干系。这种寻找替罪羊的做法将民众的注意力从其他决策者那里转移开来。这些替罪羊们为其领导承担了失职的责任:他们或者是被冤枉的或者是“甘愿为之”。Ellis用“避雷针”(lightning rod)来形容后一种情形,即真正的幕后黑手企图利用政治或官僚权力结构的为其开脱罪责。高层官员们通过寻找替罪羊、做出象征性牺牲的方式对公众的批评进行回应,这为他们增加了平息丑闻、渡过难关的又一筹码:他们在“危机管理”中表现出了果敢的勇气和决心!在这里,媒体操作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为了保证当权者的声誉不受负面报道的损害,这些人想方设法操纵媒体报道。但是当来自于媒体的批判浪潮日渐高涨时,他们总是由于过分殷勤而被其主子抛弃。事实上,在整个治理制度的设计中,对未来批评压力的预期或许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很显然,只有当重大事件被普遍认为并非深层次结构问题的表象时,“寻找替罪羊”的策略才会有效地“中止对责任的深究”。这时,“烂苹果”效应就能得以避免,批评的焦点就会集中在某一腐败机构之上,而这个腐败机构的大多数头头们都应该受到公众的质询。 体系失败既可以被界定为孤立性的,也可以被界定为结构性的。例如,当重大事件被界定为结构性问题和体系失败(根据第三个维度)时,随之而来的批评会在范围(会涉及到更大的网络)和时间上(会关注更长的时间)更为分散,整个事件也会被认为是一次深层次的体系失败。如果事件被认为是共同责任的结果,那么它就会在时间上被孤立出来,人们或许就会认为这只是一次偶然的体系失败。 在瑞典的例子中,卡尔森界定事件的策略十分成功。他迅速地将讨论的焦点限定在一个行为体(Bildt)身上,正如他所言,后者必须对由其本人造成的整个事件做出解释。Bildt在给叶利钦写信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一位首相不应该以这样草率的方式处理国家安全事务。这样一来,因水貂事件而曝光的政策失败的责任就落在了Bildt及其政府身上。Bildt试图扩大事件的时间范围,进而使原先的政府也承担一定的责任,但他的做法仅仅被视为是身陷困境之中的政客的一种防御性姿态。客观地讲,Bildt本来可以扩大应承担责任的行为体的范围,他也能够将事件界定为体系性失败。但是他们的疑虑以及测试的结果并没有通畅地、清晰地上报给军事部门。甚至当军方上层已经了解了相关情况,军事领袖们要将日渐凸显的疑虑通报给国防部也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 与此相反,在荷兰的例子中,争论的矛头迅速从个人转向了政策、结构和制度。人们普遍认为事件的发生是体系失败的结果而非某个个人的责任。失败的责任被分散了:先是军方和政治领袖们为自身开脱的言词,NIOD后来提交的综合性分析更使这种分散合法化了。在很早的时候国防部长Voorhoeve就指出,现在的困境正是由他的前任们造成的,这导致他一上任就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另外,荷兰军队在Srebrenica的行动是联合国多边维和行动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从直觉上告诉人们责任的分散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实上,后来提交的所有的调查报告都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体系失败,但是对于哪一部分的体系失败最应受到指责,它们的观点则大相径庭。根据联合国自己的评估报告,安全地带的失陷是由联合国总部、联合国保护部队司令官以及现场的荷兰军队的失职共同造成的。法国国民议会的调查报告将荷兰军队的行为描述成“疏忽”,并认为荷兰军队的不作为是“非常令人难堪的”。荷兰的调查报告突出了负责此次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法国将军的责任,后者拒绝了荷兰军队呼吁北约空军支援的请求;此外荷兰的调查报告还抨击了出动空军支援所必须履行的“双钥匙”程序以及联合国关于军备和维和行动的含糊不清而又死板的命令。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并没能阻止此次事件在荷兰国内政治舞台上的升级:它最终导致整个政府的集体辞职。 总之,在两个案例中,事件的界定过程以及责任的分配都带来了政治后果,但是两个案例政治后果的性质迥然各异。在荷兰,首相Kok静候NIOD的报告,但是环境部长的声明以及媒体和议会监察人员对事件原因的穷追不舍迫使他很快就“主动承担了整个责任,这就使得政治后果的出现不可避免”。NIOD报告的结论及其带来的政治反应迫使Kok首相及其内阁辞职,尽管他们在其辞职报告中仍旧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所作为是最应受到批评的。在水貂事件中,Bildt及其内阁成了替罪羊,但是由于当时卡尔森和新政府已经上台,因而内阁辞职事件并没有发生。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事件的责任人会相当明确以及为什么扩大事件的时间范围和责任人范围的努力没能成功。然而,水貂事件导致的最主要政治后果就是公众对前首相Bildt、他领导的政府及其安全政策失去了信任。 结论:理解批评的界定过程 对于精明的、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体而言,责任分配是一个理性的行为吗?我们的回答是:既是也不是。当行为体对问题或失败进行界定时,在界定过程的某个阶段——尤其是在它的起始阶段——行为体或许对事件只不过是一种条件反射和无意识的反应。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将清楚地分辨出哪些是对其地位或组织的威胁,哪些对他们而言则是机遇。因而,他们的行为更多的以预期推理和以往经验为准绳:他们解释事件并不仅仅是要表示他们心理上的妥协或向听众们表明他们行为的合法性。Pronk(当时荷兰的环境部长)试图作出解释,但他最终只是发出了“谁也不能够作出正确选择”的哀叹,而当时的其他内阁成员对他的公开言论都表示了强烈不满。行为体也常常卷入辩论之中以获得和规避特定的结果;在他们看来,这些特定的结果现在已经若隐若现,将来必定要发生。例如,卡尔森积极地了参与了对Bildt的指责,因为对于他而言,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方式: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集中到了一个特定的时期,而他本人的名声则丝毫不会受到影响。在荷兰的例子中,当首相Kok在悲剧发生七年之后选择辞职时,他试图在诚实和策略之间保持一种平衡。Kok及其政府之所以选择辞职似乎仅仅是由于不存在其他的选择。同时,通过这样做,他们强调了这一点,即主动去承担责任是一个必须的、诚实的、自律的选择,虽然他们自身并没有直接受到指责。即使行为体确实作出了关键性决策,他们也不得不向自己和他人说明这些决策具有合法性,尤其是在重大事件带来悲剧性后果的时候。 当责任分配的问题最终在民主或通常所说的“公意法庭”上得到解决并最终深嵌于集体记忆中时,政治界定和责任分配过程是否真的是紧密交织在一起?它们最终能否回溯到那些不同的辩论阵营之中?本文的主旨就在于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我们探讨了行为体会选择什么样的推理逻辑去影响公众对问题的认知(进而导致特定的责任分配结果)。显然,我们仍需进一步地比较研究以检验这些结果的说服力,同时对个人、制度、文化、情境等因素进行探询——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政治体系中会产生特定的责任分配模式。例如,当涉及传播和隐瞒信息时,某些行为体享有的制度上的优势很可能影响到责任分配博弈的进程和结果:与大众传媒的联系通道、制度合法性以及对个体个性的宽容等等。在这里,本文阐释了Edelman以及其他学者很早之前就信奉的观点:社会事件、甚至是棘手的社会事件——它们本身很少能够转变为政治斗争,除非一些行为体主动去推动这种转变过程(假如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的话)。对于他们而言,话语是其手中的一张王牌。上一篇:美国帝国体系中的中国与日本
下一篇:中国宪政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