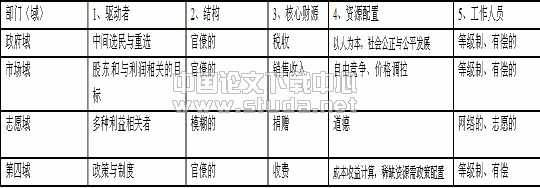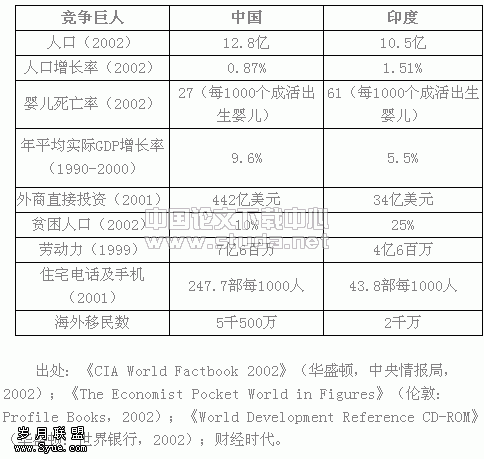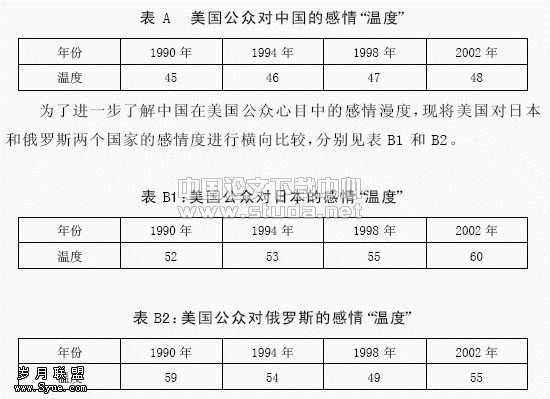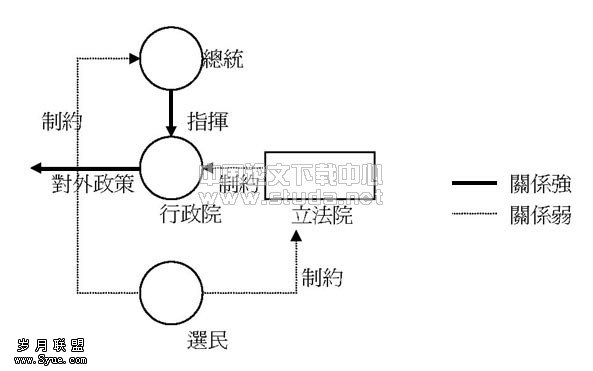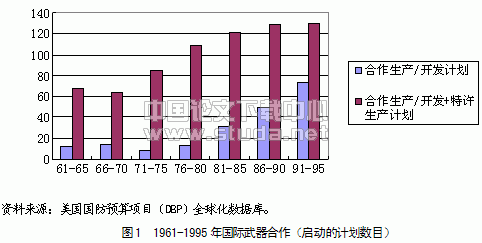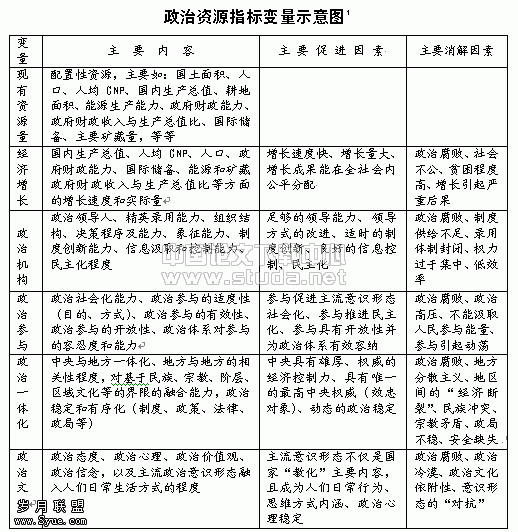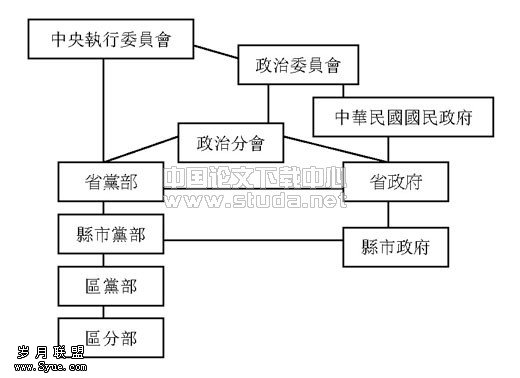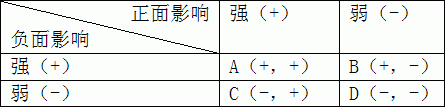忏悔与表现
蔑视公共礼法的坦率与自傲
卢梭在《忏悔录》中开宗明义地宣布:“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我。” [ 1]卢梭在这里由于摆脱传统伦理和世俗规范的羁约,执著于自我感受的赤裸裸表现,因而被贝尔等人看作是主义文化的开山鼻祖。[2]尽管卢梭本人很自信地认为,他的这份内心自白展示的是一幅“世界上绝无仅有、也许永远不会再有”的完全依照本来面目描绘出来的人像,但是在他之后,对自我经验的大胆探索不仅成为一种文化时尚,而且那些新时代的弄潮儿越发无所顾忌,以致完全抛弃了“忏悔”这一让人感觉沉重的心理负担。拜伦将激情和狂热视为沛然不息的生命本源,他对世俗流言蜚语的回答是“独自反抗你们全体 ”。[3]惠特曼追求一种无所羁绊的人生,他在《自我之歌》中高傲地宣称“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从而使“表现型个人主义”获得了更加淋漓尽致的发挥。[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尼采。这位“用锤子进行研究”的家,一方面对传统价值予以彻底的重估,另一方面又在“上帝死了”之后膨胀出了超人般的自我。当他将自己的自传命名为“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就是命运”、“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好书”等等的时候,可以说是唯我至上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在对新奇性的偏好成为时尚,或者借用尼采的说法,在“一切皆虚妄”因而“一切皆允许”的今天,人们在将自己心路历程展示给公众时,已经很少使用“忏悔”这样的字眼。因为就字面涵义,特别是就其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被赋予的特定的宗教和道德涵义而论,忏悔即悔过自新,也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堕落而期求上帝或道德法庭的宽恕、指点和援助,使自己从无意义的实存状态中超拔出来。这样一种基于罪感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否定,是与 “走自己的路”之类的自傲和自负不合拍的。现在要问:这种表现自我的无所顾忌甚或洋洋得意,能够从卢梭的《忏悔录》中找到它的思想原型吗?如果的确存在这样的渊源关系的话,它在卢梭那里又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呢?不妨看一看卢梭本人的表白:
不管末日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您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您把无数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面前,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好!”[5]
这是卢梭《忏悔录》中的一段纲领性文字。通常认为这段文字表达了卢梭勇于剖析自我的坦率。但是问题在于,一般意义的坦率并不足以显示卢梭的独特个性。因为在他之前,著名思想家蒙田,即曾出于对率真的生活的向往,试图剥离沉重的世俗装饰,撰写一部描绘自我的坦白之书。“我要人们在这里看见我的平凡、纯朴和天然的生活,无拘束亦无造作,因为我所描绘的就是我自己。”[6]但是卢梭觉得,蒙田由于不敢彻底摆脱“公共礼法”的约束,他在描绘自己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毫无保留、直截了当。他虽然也暴露缺点,但只是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结果仅仅将自己的一个侧面展现给了公众。“谁知道挡起来的那一边的脸上会不会有条刀疤或者有只瞎眼,把他的容貌完全改变了呢?”[ 7]在卢梭看来,这不是坦荡朴直,而是虚伪,是说谎,是用讲真话的形式来骗人。
卢梭声称自己不以可爱的缺点编造假面具。对他来说,彻底的坦率意味将这类面具打个粉碎,毫不掩饰地暴露出自己内心世界的丑陋与肮脏。假如这样做会招来世人的唾沫,他并不觉得有什么难堪。照他的说法,既然罪孽常常源出于保全名声,那么用名声的自我损毁来抵偿罪孽便合情合理。也只有如此,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忏悔。由于做了,或自以为做了这样的忏悔,一种自豪感便从卢梭心底油然而生。“是的,仅我一人,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有任何人敢于做我要做的事。”[8]尽管从严格的意义来说,任何回顾自己的追忆总要经过或多或少的过滤选择,因此卢梭的忏悔实际上也并不是坦率得不打折扣,但问题在于,卢梭力图在主观上刻意表现得不打折扣,方法就是大胆揭露普通人不愿自我公开的那类隐秘的“刀疤”和“瞎眼”。这种思想取向使卢梭的忏悔始终具有一种挑战意味。他在世人的蔑视中锤炼出一种逆流而上的气度,又因为这种气度而蔑视世人,甚至由此化解了忏悔罪孽时的负疚意识,于是,他不仅敢于像述说自己的忠厚善良一样暴露自己的卑鄙龌龊,而且在暴露自己的卑鄙龌龊时十分平静,平静得就像是在述说自己的忠厚善良。从其思想影响来看,后一方面蕴含着卢梭精神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品格特征,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解析,就是“唯我独尊”。
自我贬斥和皈依神圣
罗素曾讲:“审慎对热情的冲突是一场贯穿着全部历史的冲突。”[9]照他的看法,这场冲突在远古时代即已发生,而且从此将人类逼入了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人类文明中最伟大的创造似乎都包含着某种热情奔放的沉醉成分,倘缺乏这种成分,生活便没有趣味;可是另一方面,文明教化之不同于野蛮粗鄙,则又在于对自发的生命情感予以节制疏导,若没有这种节制疏导,生活就会变得极其危险。人类文明即是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曲折前进的。如果说,肇始于近代文艺复兴的个性解放运动,扫荡传统禁欲伦理对人的感性欲望的警惕和恐惧,使人的主体潜力或能力得到开掘,从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与,那么,当个人主义在今日生活中大行其道,以致对欲望边疆的自由开发超过了合理限度,造成了某种意义的“道德生态危机”的时候,究竟该怎样提出问题并设法谋求问题的解决?
从历史上看,这个问题并非今天才产生。古罗马时代就曾出现过,而且表现得十分尖锐。思想家海涅在论及这个问题时指出,随着古罗马的日趋没落,一种肆无忌惮的奢华、荒淫之风在全社会蔓延,这从某种意义上恰好反衬了基督教道德的合理价值。“唯物主义在罗马发展到惊人可怕的地步,大有摧毁人类精神的一切辉煌成果之势,基督教世界观作为克制这种唯物主义的一剂灵药,是必不可少的。”[10]虽然基督教后来演化为制度层面的行为控制,并不可取;但是,它在信仰层面表达的督导和约束个人的自然欲望与本能冲动的道德要求,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价值正当性。丹尼尔·贝尔将这种正当性表述为:如果缺乏必要的道德约束,纵然具有美学上和上的充分理由,人的那种要寻觅新奇、探索一切的自由冲动,也会导致可怕的肉欲、淫秽和堕落。因此,为了不致在无度的放纵中使整个文明被焚毁,“社会必须拥有一种羞耻感。”[11]
就基督教信仰体系来说,这种羞耻感来源于对超验神圣的虔诚敬畏,以及对上帝颁布的道德律令的优先接受。倘若一个人为世俗的名利和享乐所引诱,把持不住,触犯了道德戒律,则他就应该为自己的丑行感到羞耻,并向神圣天父由衷地表示悔过自新,这便是奥古斯丁式的忏悔。所以,与卢梭《忏悔录》中对“我”字的一再大写不同,在奥古斯丁式的《忏悔录》中我们一上来读到的是这样一段文辞:“主,你是伟大的,你应受一切赞美;你有无上的能力、无限的智慧。一个人,受造物中渺小的一分子,愿意称颂你。”[12] 可以作这样一个概括:卢梭的忏悔是一个目空一切的叛逆者的战斗呐喊,而奥古斯丁的忏悔则是一个倍感孱弱的流浪儿祈求救助的虔诚呼吁。
这种呼吁是向神圣天父发出的,它要求悔过自新者将自己毫无保留地裸露在主的面前。应当说,奥古斯丁在这方面做得很彻底,至少他的思想不允许他有什么谎骗行径。因为照他的看法,面对“至高、至能、至仁、至义”的神圣天父,渺小的个体生命本无任何秘密可言。对上帝坚守秘密,非但不能把自己隐藏起来,反而会把上帝在自己眼前隐藏起来,使自己看不见圣爱的永定之光。[13]为了领受这永定之光的照耀,奥古斯丁将自己和盘托出。他讲他过去如何偷盗,如何放纵情欲,如何蹈入自大狂的漩涡,如何羡慕别人的淫乱,以致于因为自己缺乏和那些败类相媲美的丑行而感到气馁……凡此种种,即使按卢梭式的标准来衡量,也应该说是相当地坦率了
但是,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里我们找不到后来卢梭在《忏悔录》以及在《新爱洛伊丝》和《爱弥儿》中对自己的隐秘心理感受所作的那种细致入微的刻划描述。这不是一个美学风格问题,而是一个更根本的精神品格问题。也就是说,奥古斯丁不是因为缺乏某种艺术训练而不会这样做,而是因为他出于一种道德恐惧而不敢这样做。他的信仰立场告诫他,仅当把追溯自己的险恶经历看作是向上帝悔罪的时候,忏悔才有意义。因此,忏悔不是别的,只是对自己的破碎处的省悟。这种省悟在奥古斯丁身上唤起一种自惭形秽的负疚感和羞耻感,从而给他的坦率划了一条不得逾越的道德边界。一方面,他不能隐瞒劣迹,为了让神灵之光驱散自己内心的阴霾;但是另一方面,正由于暴露的是丑陋和肮脏,他无法做到从容不迫。那不是喝一口凉开水,更不是品尝珍果佳肴,可以反复咀嚼,细细回味。那是揭脓疮。奥古斯丁因为看到自己的的溃烂而恐惧战栗。“我灵魂深处,我的思想把我的罪状全部罗列于我心目之前。巨大的风暴起来了,带着倾盆的泪雨。”[14]于是,忏悔在奥古斯丁就成了痛改前非的嚎啕大哭,成了基于罪感的自我贬斥,成了祈求天父赐予新生命的虔诚呼唤:
只有谦虚的虔诚能引导我们回到你身边,使你清除我们的恶习,使你赦免悔过自新者的罪业,使你俯听桎梏者的呻吟,解脱我们自做自受的锁链,只要我们不再以贪得无厌而结果丧失一切、更爱自身过于爱你万善之源的私心,向你竖起假自由的触角。[15]
奥古斯丁如此痛切的忏悔,用舍勒的话来说,所体现的是一种敛摄心神的谦卑、温良和恭顺。它不是玩味自我、张扬自我,而是走出自我、舍弃自我。然而也正由于走出了自我、舍弃了自我,奥古斯丁又使自己的灵魂长出眼睛,看到被人的愚妄自大遮蔽住的神性的本源世界,并在同这个本源世界的沟通中,自我复得,重新找回了自己生存的价值意义。因此,若作一简单比喻的话,奥古斯丁的忏悔乃是一种仰望,是对超乎自身之上的神圣声音的洗耳恭听。“我的天主,我真正的生命,我该做什么?我将超越我本身名为记忆的这股力量,我将超越它而飞向你、温柔的光明。”[16]这就是奥古斯丁的终极追求。
我感觉,故我在
毫无疑问,卢梭也向往光明。但是对他来说,光明既不是在远处,更不在上方,而就在自身内部,谓之“内心的光明”。“请教内心的光明,它使我走的歧路不致于像家使我走得那样多。”[17]但由于把内心的光明奉作至高无上的导师,奥古斯丁的恭顺便被卢梭彻底打翻了。现在,对光明的追求不再表现为仰望,而变成了自上而下的鸟瞰和俯视。
俯视世界,卢梭到处只看到阴暗、混浊、丑陋、肮脏以及装腔作势的虚伪、无聊、空虚和庸俗。当他反问:谁比我好?实际上已作出回答:没有人比我好!这良好的自我感觉,不仅使他不把揭露自己的缺点视为一种苦刑,倒深信这是一个大胆的创举。在他眼里,这实际上是一种向无聊世界的挑战,一种弃绝平庸的超拔,一种遗世独立、卓尔不凡的孤傲。他不需要面子,因为面子就是枷锁;他不需要谦卑,因为谦卑就是泯灭自我、向陈规陋习低头。他追求一种绝对的奇特性。倘若暴露自己性格经历中的诸般唐突乖戾可以显示这种奇特性,则他宁可舍弃别人对自己的好感而刻意暴露。他对此深以为豪:“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于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生来像我这样的人。…… 大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18]
丹尼尔·贝尔提醒说,切不可把卢梭的自我崇拜等同于单纯的顾影自恋,也不应用裸露癖来打发他那近乎处心积虑地制造轰动效应的坦率。问题的要害毋宁在于,卢梭在这里确立了一套影响深远的新的文化原则,按照这一原则,生存意义的阐释,与宗教信仰、与习俗成规、与传统的连续性巨链无关,而仅仅与自我的个性、与自我经验的奇特性有关。这便是卢梭式精神品格的最本质的构成要素。它的座右铭,用西方哲学的典型术语来表达,就是:“我感觉,故我在”。
对卢梭来讲,“我感觉故我在”决不是奥古斯丁所体现的那种“我信仰故我在”,尽管他在霍尔巴赫等人将启蒙运动推到战斗无神论方向的时候曾借萨瓦牧师之口发布过自己的信仰宣言。因为在奥古斯丁那里,“我信仰故我在”首先意味着对超绝的神性权威的优先接受,而反观卢梭,我们却看不到这样一种皈依神圣的谦逊和虔诚。《爱弥儿》中对“ 自然人”善良的本性肯定和《忏悔录》中一味追求独特表现的“我”,表明他像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一样,所推崇的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品格。原罪教义及与此相联系的自我贬斥和自我否定,在他眼里乃不堪忍受的重负,是必须予以摒弃的。
但是,与以“我思故我在”为基本信条的理性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不同,卢梭面对理性潮流,特别是理性化潮流与世俗化潮流汇合后形成的巨浪的冲击,又感到六神无主。他觉得人在摆脱传统羁绊的束缚之后,不应再度迷失,沦为逻辑符号、机器零件和既阴毒贪婪又卑贱下作的冷血动物。假如人已经异化为或正在异化为这样的冷血动物,在他看来,那就必须以反潮流的形式向沉沦的芸芸众生展示一种真正属人的生存理想。他从激昂炽热、圣洁单纯、自由奔放的生命情感那里,找到了支撑这一生存理想的原始基础。“我只有一个向导还忠实可靠,那就是情感之链。”[19]“我存在着,我有感官,我通过我的感官而有所感受,这就是打动我的心弦而使我不能不接受的第一真理。”[20]按照卢梭的看法,追随这一真理,人生将不再是异化沉沦、随波逐流,而成为无拘无束、无牵无挂的自由表演和自我实现。因此,跟着感觉走,跟着本能走,就是跟着良心走,跟着光明走:
良心呀!良心!你是圣洁的本能,永不消逝的天国的声音。是你安安当当地引导一个虽然是蒙昧无知然而是聪明和自由的人,是你在不差不错地判断善恶,使人形同上帝!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和行为合乎道德。没有你,我就只能按照我没有条理的见解和没有准绳的理智可悲地做了一桩错事又做一桩错事。[21]
大略说来,这就是卢梭在强烈感受近代理性化和世俗化过程导致人们精神生活的神意匮乏和价值饥渴后,所开出的疗救药方。药方的关键是褒激情,贬理智;扬直率,抑反思;重灵性,轻功利。卢梭试图以这种方式对人生意义重新加以解说,以延续和传递那颗形而上的人类精神火种。但是必须指出,由于坚持个人本位,放弃对超验神圣权威的优先接受,卢梭的思想努力从本质上讲不仅与本来意义的宗教信仰无关,而且可以说截然相反。丹尼尔· 贝尔认为,“凡是宗教失败的地方,崇拜就应运而生”。[22]卢梭的精神取向正是宗教失败后应运而生的崇拜。对他来说,忏悔仅仅是一种形式包装,其实质,则是借此确认坦率的正当性,然后再通过光明正大的坦率来达到对自我情感的狂纵不法的张扬玩味。他越是把自发的生命冲动界说为圣洁的良心,那么接受良心的指引也就越是演化为对道德禁忌,广而言之,对所有社会规范和文明准则的义无返顾的破坏与叛逆。因此,倘用一句话来概括,卢梭所走的道路,本质上乃是一条以代替宗教、以审美代替信仰、以英雄代替上帝的自我表现与自我崇拜之路。
但作为开路先锋,卢梭在这条道路上走得非常艰辛。其所以如此,倒不是因为他不渴望温情和友爱,而恰恰是因为他太渴望了,以致于他那艺术化的人生追求在现实生活中注定得不到满足。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只身漫步于人间的孤独者,没有兄弟,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真正的知音——除了自己。这既在他的内心,也在他与社会之间造成了高度的紧张。而当他拒绝与凡夫俗子同流合污,又拒绝听从上帝召唤,仅仅依靠坚定的自我崇拜来化解这种紧张的时候,生活中的失意便激起了他满腔的怒火。即使是忏悔也将这怒火压抑不住。休谟对卢梭作过这样的评价:“他在整个一生中只是有所感觉,在这方面他的敏感性达到了我从未见过的任何先例的高度。然而这种敏感性给予他的,是一种痛苦甚于快乐的感觉。他好像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不仅被剥掉了衣服,而且被剥掉了皮肤,在这种情况下被赶出去和猛烈的狂风暴雨进行搏斗。”[23]这搏斗使卢梭身心憔悴,几乎成了被害妄想狂:“我头上的房顶有眼睛,我周围的墙壁有耳朵。我被许多心怀恶意、目不转睛的密探和监视人包围着,心神不宁,精神恍惚。”[24]同奥古斯丁豁然开悟后的那种谦逊、温良、平和相比较,这也许不能说是一种健康的心态。
问题的症结,正如舍勒分析的那样,在于卢梭式的文化英雄在蔑视世俗的浅薄的时候,出了一种极有深度的骄傲。那是一种唯我独尊且不加收敛的骄傲。骄傲者只围绕自我不停地旋转,最终撕裂自己与社会、与传统相联结的一切纽带,成了和世界格格不入的 “尘寰逃兵”。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宗教衰微后的神意匮乏的世界,在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蔓延后确实显得有些刻板和平庸的世界,做“尘寰逃兵”无疑有它的文化魅力,因为它的神奇,因为它的不平凡。为了追求这种神奇和不平凡,卢梭把裸露自己的内心特别是内心深处的阴暗面当作一种向庸俗示威的特殊方式,孤傲得不要伪装,也无力伪装。可是,不管他有没有意识到,“不要伪装”一旦流行起,成为时尚,就会演变为一种新的虚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宫廷贵妇,常常打扮成牧羊女,连大革命时被斩于断头台的王后,竟也要刻意妆扮成哺育后代的母亲,据说都是响应卢梭的号召,做清水芙蓉,回归大自然。
事实上,卢梭引发的文化震荡,倒还不在于他身后有一群东施效颦的拙劣的模仿者。更厉害的是,卢梭那跟着感觉走的狂放的自我表现,在反理性、反功利、反制度化的过程中,彻底扫荡宗教信仰极力强调的那种对不加约束的自发本能与感性趣味的恐惧,以及对超绝的神性生命所加诸人类的道德戒律的虔诚敬畏,从而开辟了一条寻觅新奇、不断探索经验边疆的宽敞大道。沿着这条大道迅跑,很快涌现出一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他们跟卢梭学会了蔑视习俗束缚,“最初是服装和礼貌上的、小步舞和五步同韵对句上的习俗束缚,然后是艺术和恋爱上的习俗束缚,最后及于传统道德全部领域。”[25]他们一再膨胀帝王般的自我,不过已不像卢梭那样体验到痛苦,而是以极其得意的神态去接受刺激,拥抱魔鬼,从中取乐,堂而皇之地将自我经验的怪诞新奇当成了创造性的源泉。时至今日,风俗蛋糕已被打得稀烂,声言要叛逆传统好比奋力进攻敞开的大门。在这种背景下,丹尼尔·贝尔提出了一个耐人回味的问题:谁来约束自大狂呢?如果离开必要的约束,骄傲自大就是魔鬼般的堕落。舍勒入木三分地指出:
骄傲者是这么一种人:他通过连续的“俯视”而自我暗示,似乎他站在塔尖。他本人事实上的每一次下降之时,都盯一眼更深之处,以抵销他的实际下降,而且抵销得过头,从而反以为自己是在上升。他没有发觉,时时映入他眼帘的深渊恰恰在他展眼而望、幻想自己飘飘然于云端之际却在慢慢地把他拖将下去。[26]
这也许是在亵渎神圣、张扬自我成为时髦的今天,重新反思传统文化价值的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注释:
[1] 卢梭:《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2]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82页。
[3]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四分册,第329页。
[4] 贝拉:《心灵的习性》,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9页。
[5] 卢梭:《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6] 《蒙田随笔》,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7] 卢梭:《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8] 卢梭:《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页。
[9] 罗素:《西方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9页。
[10] 《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11]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39页。
[12] 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页。
[13] 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85页。
[14] 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57页。
[15] 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7页。
[16] 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01页。
[17] 卢梭:《爱弥儿》,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81页。
[18] 卢梭:《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19] 卢梭:《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
[20] 卢梭:《爱弥儿》,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38页。
[21] 卢梭:《爱弥儿》,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17页。
[22]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20页。
[23]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32页。
[24] 卢梭:《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页。
[25]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5页。
[26] 舍勒:“德行的复苏”,见刘小枫编《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三联1991年版,第1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