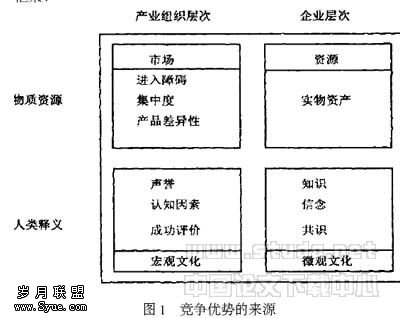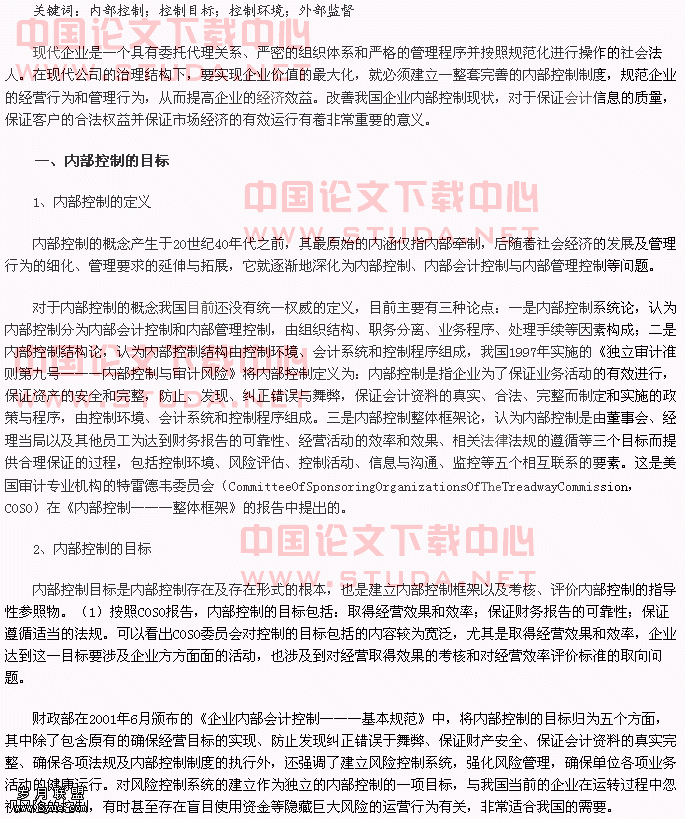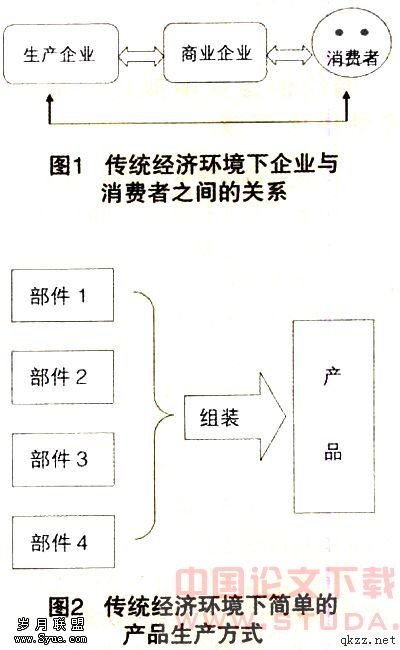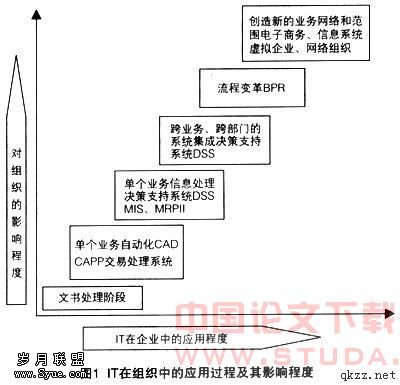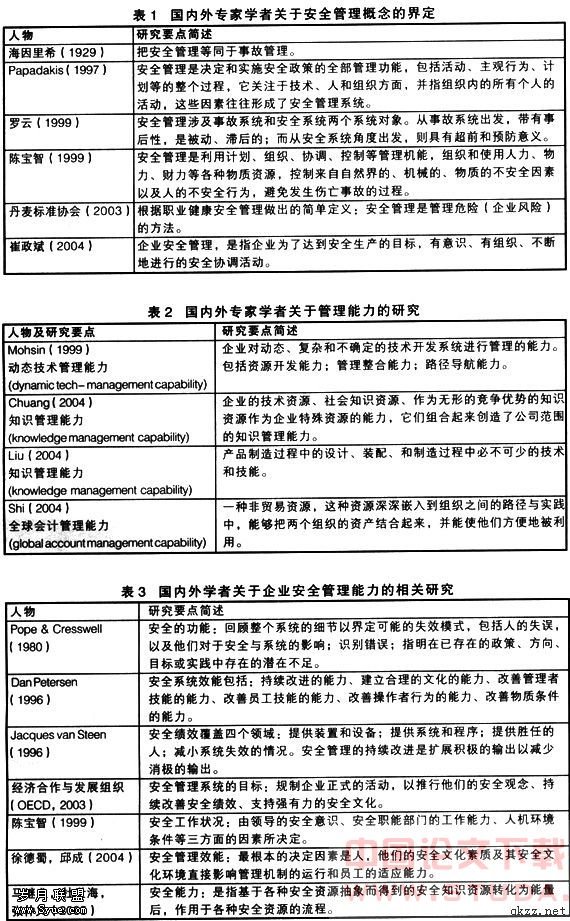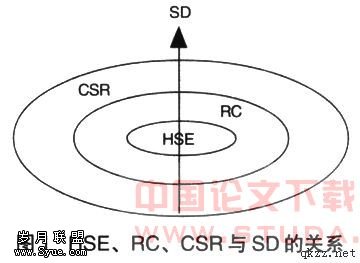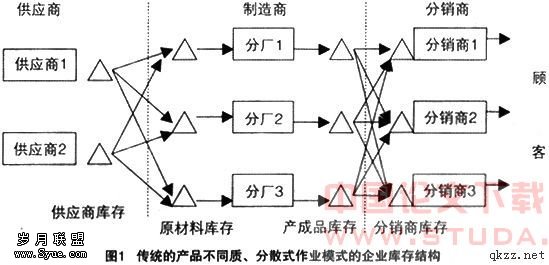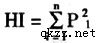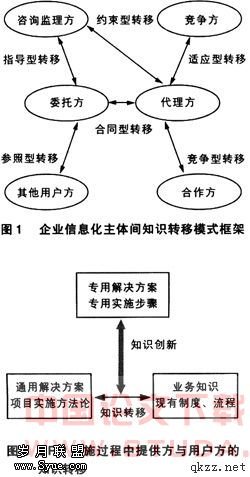试析中国国企高管人员的薪酬与激励:总结与思考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4-06-01
论文摘要:从制度成本的角度出发,关注中国国企高管人员薪酬制度的效率问题,并认为好的薪酬制度有助于实现国有企业剩余索取权的顺利复归。在这个基础上,着重探讨高管人员薪酬决定因素、过度投资与在职消费、年薪制及股权激励等重要题域,并对新的激励制度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在国企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博弈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所有者的分散状态,致使所有者处于局部劣势,难以实施有效约束。在约束边界的状态下,所有者欲在委托代理关系中获得利益最大化,只能设法将经营者吸引到合作关系之中。为此,所有者必须设计一种激励机制,使双方目标最大程度地趋于一致。然而,以激励作为合作的条件,这本身蕴含一个悖论,即这种以减少交易费用为目的之制度安排,又会增加多少交易费用(张五常,1999 )?在关于国企高管人员的薪酬与激励的课题中,这种担心不仅仅表现为薪酬的公平与效率问题①,更弥散至收人差距拉大、过度投资、在职消费、绩效薪酬、长期激励以及垄断福利等方面。
在国企财产权已渐次明晰、预算约束已渐次硬化②、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度已渐次完善的情形下,国企经营者自行或与职工共谋分光“剩余”的倾向似乎已有所淡化③。当下,政府与公众关注的焦点已转移至“如何激励”—既缩窄国企经营者与非国企经营者之间收人差距,而又不至于在国企内部出现过分不合理的薪酬差距④,同时设计出具有长效激励效用的新的薪酬制度。
有人认为只要产权界定了就可以解决国有资产的“公地悲剧”,这过片面。任何权利界定都会留下“公共领域”( public domain ),在此领域内的公共资源只要尚有经济价值,都会引起追租行为(rent一capturing)或福利攫取(welfare capture ),直至“租耗”( rent一dissipation)或“攫取损失”( apture loss );同时,所有者为权利界定所付出的监督成本等费用,亦构成了均衡的产权界定的条件(汪丁丁,1995;张五常,1999;周其仁,2000 )。故此,在评价国企高管薪酬的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的时候,首先要明确的是,这并非单纯局限于薪酬制度的激励效用,而是要兼顾薪酬制度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所带来的效用。就博弈均衡的角度而言,如果说“相机治理”机制(contingent governance)能有助于确保控制权的顺利让渡(杨瑞龙等,1998),那么好的薪酬与激励制度可望有助于实现索取权的顺利复归⑤。
一、高管人员薪酬决定因素的一般原理
一般认为,薪酬制度从简单到复杂主要可作以下类型化(姚先国等,2005 ):以工作为基础的薪酬体系;以能力为基础的薪酬体系;宽带工资;绩效工资;可变的薪酬体系(包括利润分享、经理期权计划与员工持股计划、收益分享计划、团队薪酬)⑥。可见,薪酬评价围绕的主要是工作、能力或业绩,其最终依据归结于组织业绩的提升。然而,从零散的文献中可以归纳,除了企业绩效之外,企业规模、相对绩效(通过企业与企业之间横向比较来判定)、职位晋升、职位解雇以及政治力量等诸因素均可左右高管人员报酬水平(周业安,2000 )。
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最优契约模式(optimal contracting pproach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首席执行官薪酬决定问题的路径,其核心是契约的“有效性”问题,即报酬—业绩敏感度,但事实上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魏刚,2000)。这样,管理权力模式(managerial power approach )逐渐被视为新的解释工具,该观点认为,首席执行官薪酬水平实际反映了其通过管理权力影响自身薪酬的能力。换言之,高管人员薪酬不是取决于经理人市场,而是“权力寻租”的结果(张炳申等,2005 )。众所周知,当下,国企经理人市场极不发达,为国企外聘首席执行官又会遇有政策障碍⑦,通过薪酬激励契约来缓和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利益冲突的,在实际操作上难度甚大。
二、过度投资及在职消费
对于国企而言,高管人员的与企业业绩无关且较低的薪酬,使得谋求控制权收益成为较强激励作用的因素(曹凤歧,2005)。其中,获取控制权收益的主要手段分别是过度投资与在职消费,此二者同属于一种扭曲的激励,并造成了盲目投资与利润转移等不正常现象。
一般而言,国企高管人员因担心决策失误而被追究行政责任,他们势必优先采取保守策略,形成职位固守( entrenchment ),即受到进行过度的专用性投资(specific investment)的激励(王艳等,2005 )。这种专用性投资往往不利于价值创造与风险分散,而与过度投资相伴的却往往是投资不足问题。深人而言,私有企业高管人员过度投资的倾向被视为源于外部替换的压力,但国企高管人员过度投资的倾向则源于政府监管的压力。在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约束机制而言,激励机制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
如果说过度投资构成了一项隐性的代理成本,那么在职消费则完全是一项显性的代理成本。从效用及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国企经营者的总收益包括薪酬、便利与事业成就,当事业成就难以成为主导需求时,其主要收益转化为薪酬与在职消费,而当薪酬小于其权力投人成本(包括教育成本、成长成本、公关成本)时,用在职消费补偿这种落差实在是在所难免的(赵文红等,1998 )。更富洞见的观点指出,在职消费问题与国企薪酬管制有莫大关联。内生于经营者业绩不可观察与所有者不可退出,制定整齐划一的薪酬体系几乎是作为出资人的政府的唯一选择。薪酬管制实际上剥夺了国企高管人员进行薪酬谈判的权利,随着情事之变迁,滞后而刚性的薪酬安排愈来愈脱离实际,从而引发一系列机会主义行为,并诱致一系列非货币的替代性报酬安排。这样,薪酬管制不仅降低了激励契约的效率,而且增加了高激励成本的在职消费,对国企价值创造产生了双重负面影响(陈冬华等,2005 )。
三、年薪制:绩效薪酬制度的适用问题
在公有及私有厂商相互竞争的“混合寡占”( mixed oligopoly)模型中,国企经理人有可能存在若干与政府目标不一致的动机,即他不但关心社会福利(可能影响其政治前途),也关心经营所得的货币补偿。薪酬结构与经营绩效严密挂钩,将导致国企经理人向利润倾斜(黄金树,2005 )。由于社会福利函数难以度量,为综合评价企业经营状况,财政部于1995年启用“资本保值增值率指标”,但该指标作用的发挥往往受制于国有资产评估市场的不完善。另一典型的考核指标“利润增长率指标”则会导致夸大利润的行为。尽管年薪制的各项业绩指标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⑧,年薪制还是在试点顺利推行开来了。顺着年薪制的思路,风险收入与风险抵押金等问题相继被提出:一是经营不善者风险收入应为负,即追加扣除一部分基本薪金;二是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者的收人只应相当于社会救济金水平;三是“风险抵押金”压抑人才,不宜提倡(李维宁,1995 )。此外,与年薪制匹配的经营者竞争机制也颇为重要,特别是到底由谁来选择优秀的经营者(郭元瞬,1995 ),这又会牵扯到所有者缺位的难题⑨。
除了题中应有之意,试行的年薪制还具有两个为学者所垢病的特色:一是经理报酬与职工平均工资挂钩;二是收入封顶(孙经纬,1997;林木西,1999)。
上一篇:关于我国企业薪酬管理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