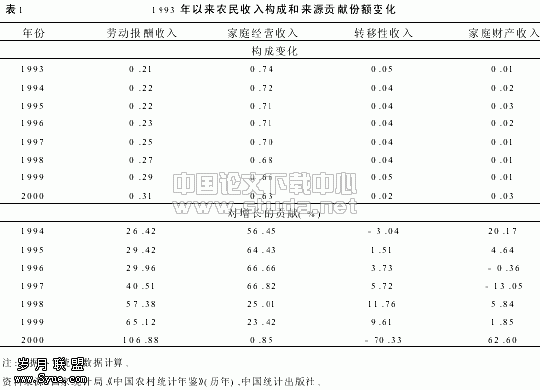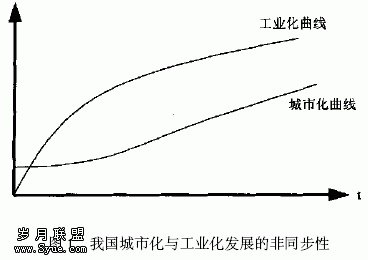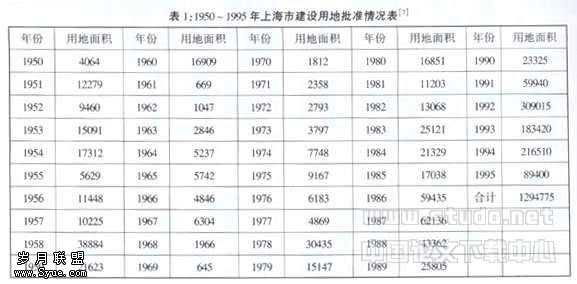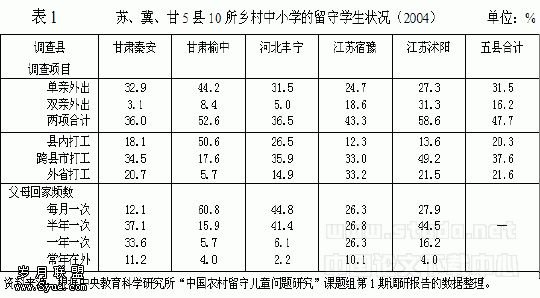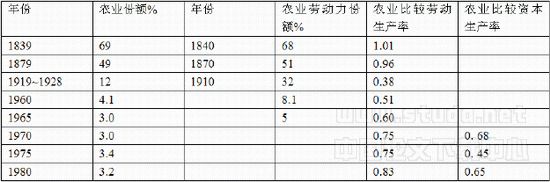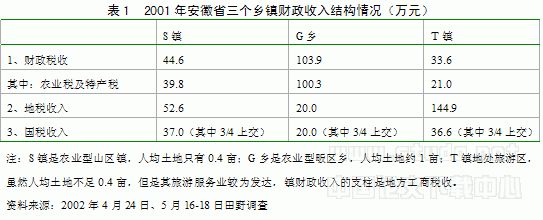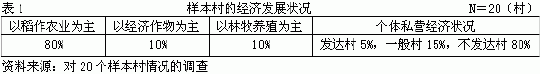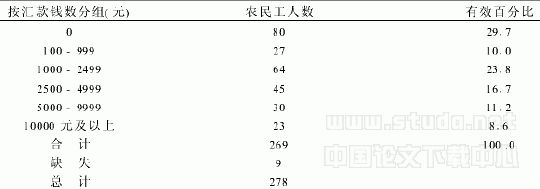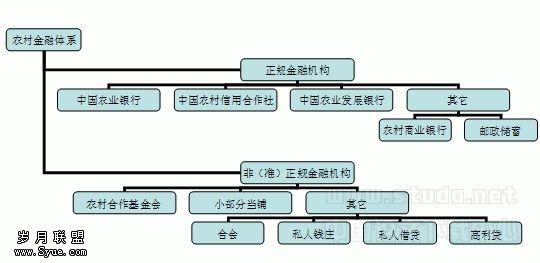中国农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3)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1
(一) 通过回顾对学科的思考
一个学科的对象、范围、理论、方法,往往为治史者所关注;但不是首先规定好了对象、范围、理论、方法,学科才得以,而是在学科的发展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对其对象、范围、理论、方法做出的。也就是说,关于学科的理论是对学科发展反思的结果。
建国以来的农史研究是从农书整理和农业技术史研究开始的,文革结束以后,农史研究走上全面发展的新阶段,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农史学科不能局限于农书整理和农业科学技术史研究,已成为农史界的共识。作为农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农业是再生产和再生产相互交织的过程,这过程的主导者--人组成为群体,不但与自然界交换其活动,而且在群体内部相互交换其活动。在化以前的漫长的时代里,农业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压倒优势的主要部门,极大地制约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因此,农史研究不能不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广泛方面。随着学科细分化和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农史学科中又可以划分出诸多分支学科或分支领域,如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书校释研究、农业生产史(又包括农林牧副渔、粮棉油菜果等各方面,每一方面都可以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或分支领域)、农业科技史、农业工具史、农田水利史、农业屯垦史、农业经济史、土地制度史、农业赋役史、农业政策史、农业思想史、农业文化史,地区农业史、民族农业史、农业环境史、农业灾害史、农民史、史、世界农业史等等。范围如此广泛的农史学无疑应该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农业生产史;因为农业就其最基本的意义来说是以人为主导的一种生产活动。上面列举的诸多研究领域,多是农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或共有的,而农业生产史则基本上是农史学科专有的,其他学科即使涉及,也是附带的。当年王毓瑚编写《农学书录》曾确定以下收录原则:"以讲述农业生产技术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知识的著作为限。其属于农业经济和农业政策性质的专书,如泛言重农以及以田制、荒政等等为对象者,一概不收。" 王先生的这一意见的前提,就是把中国传统农学视为一门以研究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为中心的学问。这也可以作为我们决定农史学科中心的。如果我们把上面提到的诸多的分支学科和分发领域归入广义农史学的范畴,那么,作为农史学中心的农业生产史,也可以称为狭义的农史学。
农史学作为学的一个分支,其理论与方法是共通的,都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用现代科学观照、解释古代的事物及其发展过程。但农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也有其特殊之处。作为历史研究和解释工具的现代科学,一般是指相关的社会科学;而农业生产由于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结合,所以作为农史研究和解释工具的,不但包括社会科学,而且包括自然科学。农史界的一些前辈学者,如石声汉、游修龄善于把现代自然科学运用于农史考证和研究中,解决了一些单纯用传统的历史考证和研究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形成了农史学科值得珍视的好传统。
农史学以农业生产史(包括农业科技史)为中心,但不能孤立地进行这些研究。农史研究、尤其是农业科技史研究最容易出现的毛病是脱离社会的和自然的现实条件,简单地罗列农书或中某种技术或工具最初出现的记载,构建出一幅直线发展、节节上升的图景。农业是以人为主导的生产活动,但我们的研究往往见物不见人,似乎农业史只是纯粹的物质或技术的发展过程。其实,即使是中国传统农书,也并非是单纯记载农业生产技术的。中国传统农学的指导思想"三才"理论,把"人"因素放在重要的地位。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组农学--《吕氏春秋·士容论》中的4篇论文,不但全部贯穿了人的主导作用的思想,而且其中的《上农》篇专门论述国家对农业劳动力和农业生产的管理,也就是专门谈"人"的问题。中国传统农书不但有国家如何管理农业的记载,而且有私人经济单位组织农业生产经验的记述,从《氾胜之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到陈旉《农书》,都有这方面的内容。[1] 总之,关于人对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是传统农学的重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于农业生产是以人为主导的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的过程,因此,我们的研究也应以人为中心展开,从农业生产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关系中研究它的发展。当前,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在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造成了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因此,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日益为人类所关注。凡此种种,使得综合性研究成为科学发展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交叉融合的趋向。在这种情况下,农史研究更应注意农业与社会、文化、自然诸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长期发展趋势的考察,而不能孤立进行。
近代考古学进入研究,是20世纪历史学的一大进步和一大特点。文革后农业考古的提倡,成为农史研究新的生长点,为农史学科的立下汗马功劳。但我们除了注意"考古" 以外,还应该注意"考现"。"考现"这个概念是已故农史学会副会长吕平提出的,他的农谚研究可以说就是"考现"的实践。由于历史是延续的,现实中总会存在历史的、传统的因素;我国这样一个历史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国家,近一二百年来又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社会急剧转变中,传统的东西更是与现代的东西交错杂陈、异彩纷呈。所谓"考现",就是考察近现代社会中的历史孑遗、传统因素,作为认识历史的一把钥匙。"考现"的另一个意思是把历史研究和现实社会调查结合起来;这样做,可以使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更加贴近。这方面,农史界也是有传统的,如文革前陈恒力把《补农书》的研究与杭嘉湖地区的社会调查相结合。文革以后,张波也曾经用这种方法研究耦耕和绿洲农业的起源。不过,总的说来,还做得不够,需要加强。
农史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农史学有两个源头:一是历史学、主要是史学,一是现代农业;农史学是由二者交汇而成的。中国农史学有两支队伍:一支是专业研究队伍,主要是从农学界或农经界派生出来的;另一支是非专业研究队伍,这是相对于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而言的,它包括其他学科(社会科学的和科学的)专业研究者而兼治农史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上述这两支队伍的人员可以相互流动或相互转化,而两支队伍本身及其职能却不能混同,它们只能相互参赞而不能相互替代。农史学科范围很广,它包括或涉及众多的研究领域,光靠专业研究队伍是不够的,需要依靠两支队伍的合作,需要两种积极性的发挥。事实证明,文革以后多种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给予农史学科的发展以无限的生机。而两支队伍的存在,又产生一个如何分工和协作的问题。从专业的农史研究专业队伍来说,应有自己的基地和中心;这个基地和中心,从队伍的基础和学科的结构看,我们认为应是农业生产史和农业科技史。专业研究队伍和专业研究者无疑不能自我封闭,要从友邻学科汲取营养,以至"借水行舟",完成本学科一些必要的建设,但不应该企图包打天下,四面出击,远离自己的基地,失掉自己的中心,以致丧失自己的优势。以上是就整个队伍来说的,至于研究者个人,应就各自知识结构的特点和实际需要进行研究,不可一概而论。农史研究者,包括专业研究者,一般来说,也有学历史出身的和学农学出身的区别,两者各有其优缺点。学历史出身的有较好的史学基本训练,但往往欠缺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学农学出身的有较丰富的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但往往缺乏史学的基本训练。应该取长补短,相互结合。
(二) 农史研究如何应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形势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面临如何适应农业现代化形需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而全球化浪潮又已汹涌而至。农史研究如何应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形势,成为摆在农史学科面前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农史学科应该从时代的需要中寻找自己的生长点。我们认为,新的形势向农史学科提出一些新的任务,例如:
1、在农业现代化中推进现代科学与精耕细作传统的结合。
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次大讨论以来,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要不要继承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优良传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农业现代化中如何具体实现现代科学和设施与精耕细作的传统的结合。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例如有些地方搞的"立体农业"或"生态农业"试验,实际上是传统农业中多层次综合利用农业资源经验的继承和发展;一些地方的"吨粮田",也是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与现代科技结合所创造的。但有些地方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好,仍然在机械搬用西方农业现代化的模式。精耕细作传统的精华之一是农业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用养结合,把生产生活中的废物作为肥料返回土壤,既培肥土壤、增加产量,又减少环境的污染,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精神。但现在不少地方已经很少使用农家肥料了。所谓"不捞
上一篇:中国农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
下一篇:中国农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