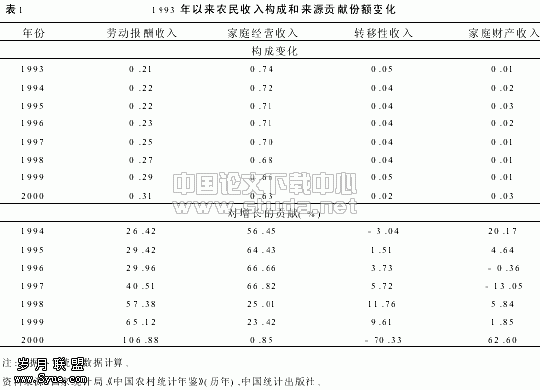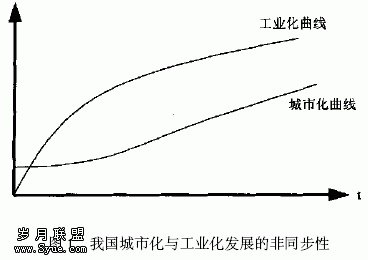我看“农村第三次革命”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1
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财政收入,税收
2002年4月,中央决定把原先在安徽、江苏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范围扩大到20个省、市、自治区,至此,“税费改革”的檄令传遍半壁江山。迄今为止,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这项被新一届政府确定为需要继续推进的农村改革,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学界也对其褒贬不一,乐观者把它奉为继“土改”、“大包干”之后的“农村第三次革命”,悲观者则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反革命”阵营。笔者虽在学界位卑人微,但值此“革命”紧要关头,既不敢不表明立场,又深感匹夫有责!
将革命进行到底
目前,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改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形势严峻,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正承受着巨大压力。据此,有些学者明确质疑“农村第三次革命”,也有人向政府建言,要“稳妥”、“谨慎”甚至“缓行”。而据笔者看来,只要政策和策略得当,农村“税费改革”不仅堪称“农村第三次革命”,而且很可能会由此引发“农村第四次革命”——农村社会、全面变革和进步,因此,当前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有些吃了欧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洋面包的人,总是羡慕西方上层建筑的“文明”而鄙视中国的民主,他们甚至怀着怜悯的心情把我国的村民自治叫做“草根民主”。我这个“土学者”愿意告诉那些“洋先生”们,华盛顿的“三权分立”并未能使美国一夜“文明”,100多年前的美国其腐败和“非秩序”较之今天的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否则你们今天也看不到“西部牛仔”电影了;可能出你们所料的是,当年美国“草根”们所发动的“建立新秩序”的“革命”恰恰是从规范税收、财政制度开始的,由财政改革推动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带动社会进步,这才有了你们今天看到的“文明”。美国当年的“革命”为什么要以财政改革为突破口呢?因为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也曾经是美国人的老师,马克思的《资本论》千头万绪,但归根结底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真理——社会关系的“内核”是经济关系、利益分配关系,因此任何上层建筑的变革都不能脱离经济基础,而财政具有政治和经济双重属性,它就是连接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纽带。美国人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找准了财政这个“革命”的切入点,把阳光雨露在“大树”和“草根”之间重新分配,并在分配过程中通过财政这个桥梁把改革基因悄无声息地由经济领域输送到政治领域,既促使了社会全面变革,又避免了“暴力革命”,从而兼顾了“改革、稳定、”。今天,学术届已经达成共识的是,农村改革应该是整体性的综合改革,改革的目标是要促使农村社会全面进步,而不仅以减轻农民负担为限。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农村革命”要有个切入点,如果能将农村“税费改革”这个革命进行到底,它就必然会演变为全面的财政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税费改革”就是我们今天“农村革命”的突破口,而且从财政这里切入不易引发社会动荡,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必须遵循的“改革、稳定、发展”相兼顾的既定方针。讲到这里,即使是白痴,恐怕也能领会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质,是要改革农村不适宜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这句话的深意了吧!难道现在你还不觉得中央所做的扩大试点范围、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决定,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吗?
什么是革命的首要任务
早在7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就告戒我们,要干革命,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什么是革命的首要任务,尤其要搞清楚,眼前急需解决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对于农村“税费改革”这场“农村第三次革命”,明确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无疑应该是决策者当前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现在,已经有许多学者提出,为了使农村“税费改革”顺利进行下去,就必须要进行多种配套改革,诸如政府机构改革、建立的财政预算体系、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等等,对此,我十分赞同。因为,既然农村改革是一个整体性的综合改革,那么进行多种配套改革就既是“农村革命”的题中之意,也是农村“税费改革”本身的需要。对于这些配套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已有许多学者做了比较深入、全面的分析,在此不再赘述。我想引导大家,从分析过去农村“税费改革”中已经暴露的主要问题入手,看一看对于农村“税费改革”来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
根据有关部门对试点地区“税费改革”情况调查研究的结果,综合起来看,目前农村“税费改革”已经暴露出的问题主要包括这样五个方面:一是“税费改革”导致县、乡、村三级收入大幅度减少,县、乡财政困难,威胁了基层政权组织的正常运转。二是“税费改革”堵死了基层政府收费、集资之门,乡、村两级遗留下来的巨额债务无法消化。三是“税费改革”在“减收”、“减人”的同时也减了“事”,由于基层没有钱,乡村社区本来少得可怜的公共产品就只能越来越少了。四是“税费改革”在技术手段上采用的是“摊丁入亩”的办法,造成了新的税负不公。五是“一事一议”制度在实践中难以落实,甚至走样。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两大类,前三个方面的问题是“钱”的问题——基层组织没有钱了、日子难过;后两个方面的问题是“技术”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可以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安徽省最近就针对“一事一议”制定了地方法规,“技术”问题对“税费改革”成功与否威胁不大;在“技术”问题上,可能还有人担心我们能否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但仔细研究后你会发现,黄宗羲是这样看问题的,他把历史上的历次“并税”式改革进行对比,而后得出结论——农民负担随着“并税”改革次数的增加而增加,实际上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因为,黄宗羲的对比,要么是把宋朝和唐朝对比,这个时间跨度是几百年;要么是把同一个朝代内的两个皇帝所做的改革进行对比,这个时间跨度是几十年;几百年、几十年前的社会结构与几百年、几十年后的社会结构还能对比吗?有可比性基础吗?换句话说,宋朝的农民负担就比唐朝的农民负担重吗?即使宋朝的农民负担就比唐朝的农民负担重,难道它就一定是“并税”改革造成的吗?如果这种对比也能成立的话,那这种“经济学研究”不成了简单的数学加减了吗?经济学家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再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即使“黄宗羲定律”是正确的,我想我们也不必担心,综观世界上的发达社会,还存在农民负担问题吗?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目前的良好发展势头,可以断言,二、三十年后的中国农民负担问题将会成为不必讨论的问题,“黄宗羲定律”不攻自破,难道我国政府还要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再搞几次“税费改革”不成?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国的改革事业恐怕也就接近于失败了,我们这些忝位“学者”之名的人还有什么脸面和闲心去和老祖宗黄宗羲对话?所以,我要诚恳地劝告秦晖先生一句,不要再做这种逻辑游戏了,如果我们能够以“少谈主义、多做实事”的态度去看问题,就会发现,“税费改革”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挺过眼前的困难,怎样解决支撑“税费改革”的“钱”的问题以及“钱”的合理分配问题。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下面”缺钱,只要“上面”能够给钱,增加“上面”对“下面”的转移支付,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事实上,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有人把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比作中央对地方的“输血”博弈,我以为并不为过。以最先试点的安徽省为例,2000年,全省农民总的税费负担是37.61亿元,比改革前同口径税费负担49.25亿元减少11.64亿元;与此同时,全省各级政府因税费改革而减收13.11亿元,平均每县减收1542万元。容易看出,农民的减负就是地方政府的减收,这个窟窿需要中央的“输血”来填平,而且“输血”的需求量还有逐年扩大的趋势,2000年,中央财政向安徽提供的“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是11亿元,2001年这个数字就飙升到17亿元,增加了54.5%。2002年,新增加的各试点省(市、区)向中央上报的“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数字之大远远超过了中央领导的想象,个别省份甚至开出了120亿元的“天价”。
再来就全国的总体情况算一笔帐,国务院“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结果表明,1998年农民负担的税费总额是1224亿元,其中农业税300亿元,乡统筹、村提留共约为600亿元,其余为其他费用。“税费改革”把农业税税率定为7%,农业税的附加上限定为20%,两项合计,就是要把农民负担水平调整到8.4%,经过调整后,全国农民负担总额——农业税及其附加大约为500亿元;原先向农民征收的600亿元乡统筹、村提留和其他乱收费一律减掉;这样就很容易推算出,基层政府将因“税费改革”而产生约700亿元的资金缺口;中央计划拿出200亿到300亿元作为“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其余的400亿元到500亿元缺口需要地方政府自我消化。另据农业部1999年对乡、村两级债务全面清查的结果,全国乡、村两级共负债3259亿元。所以,即使中央能够兑现计划“输血”量,面对如此骇人的数字,“税费改革”仍然前途未卜,一旦中央停止“输血”或“输血”量供不应求,则“税费改革”必将“崩盘”。虽然眼前各种媒体对“税费改革”的报道普遍“看好”,但这种“好”实际上和“一把手亲自抓”以及把“税费改革”当作“任务”来落实有很大关系,这种政治压力总不能永久持续下去,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更何况中央的日子也不好过,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我国当年社会保障基金收支缺口已由1998年的100多亿元扩大到2000年的近400亿元;庞大的国债规模更使中央政府如履薄冰;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仅社会保障和国债这两件事,就足以使中央财政疲于应付。
现在,有人把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减少吃财政饭的人数”上,就连温家宝总理也强调,税费改革“最重要的是要精简人员”。但从试点地区的实践来看,“减人”的幅度是有限的,水平较好的山东省也只不过减掉了20.3%,有的试点省份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为什么“减人”如此困难呢?因为,在农村吃财政饭的人中教师占大头,据安徽省政府的典型调查,农村教师工资占全部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的比重平均为75.2%,最高的地区达93.1%。农村义务还是要保的,农村师资本来就不足,如果以精简教师的办法来推动“税费改革”,无异于杀鸡取卵。因此,“减人”的幅度就不可能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即使以山东省的“减人”幅度作为全国平均水平,那也只能解决问题的20%,而且还不包括乡村两级的债务,相对于前面列举的那个惊世骇俗的“黑洞”,实在是杯水车薪!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认为,要确保“税费改革”最后成功,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要在财政收入上想想办法,而且是有办法可想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的变化,根据《统计年鉴》的资料,1986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为20.49%,1990年降至15.21%,1993年又降至12.29%,1996年竟然跌到了10.07%,到2000年这个比重也只缓慢回升到13.6%。从总体上看,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而趋减,这说明我国的应收税收收入正在大量流失。所以,只要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税收收入是可以增加的。虽然有些学者担心,加税会产生“挤出效应”,但该收未收也不对。
再来看我国税收收入结构,1998年,我国所得税占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为14.2%,其中所得税占10.8%,个人所得税只占3.4%;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得税占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一般都在50%以上,这说明我国在所得税方面是有潜力可挖的,尤其是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所得税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12%到15%之间,而我国的这个比重只有1.77%,仅相当于他们的十分之一。可以设想,只要将我国所得税占GDP的比重提高到发达国家下限12%的一半,即6%的水平,就可以使我国年财政收入增加3500亿元左右[10000亿美元×(6%-1.77%)×8.2=3468.6亿元人民币],填补“税费改革”的“黑洞”,足足有余了。
最后,还要看看我国财政收入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比例。根据财政部的统计,2000年,中央财政资金集中度从1994年的55.7%下降到52.2%,省级财政资金集中度则从1994年的16.8%提高到2000年的28.8%,县、乡两级仅占19%。比例严重失衡了,县、乡两级还怎能不困难。因此,财政收入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比例应当调整,至少要逐步“微调”!
站在政府的立场来考虑问题,面对当前“税费改革”的严峻形势,政策的制定和策略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也是“税费改革”的生命!
【】
[1]. 秦晖,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J], 改革,1997,(2).
[2]. 王绍光 王有强,公民权、所得税与预算监督[J],战略与管理,1996,(4).
[3]. 陈兆坤 ,税费改革:难点、对策及体系架构[J],辽宁大学学报(社会版),2002,(5).
[4]. 刘玉兰,农村费改税试点:成效、问题和思考[J],经济体制改革,2001,(5) .
[5]. 赵阳,农村税费改革:包干到户以来又一重大制度创新[J],中国农村经济,2001,(6) .
[6]. 赵阳,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启示录[N],中国经济时报,2002-12-20.
[7]. 秦晖,“农民减负”要防止“黄宗羲定律”陷阱[N],南方周末,2003-3-20 .
[8]. 张拥军,完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的初步设想[J],中国农村经济,2001,(9).
[9].罗纳德•C•费雪,州和地方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