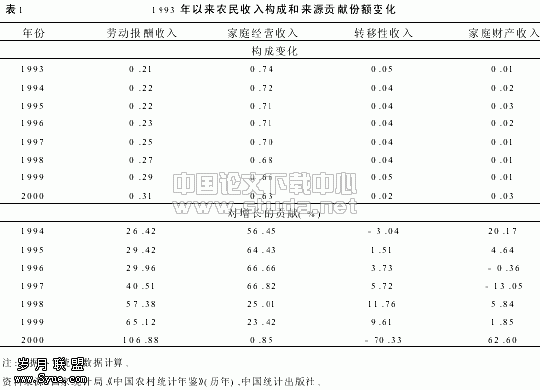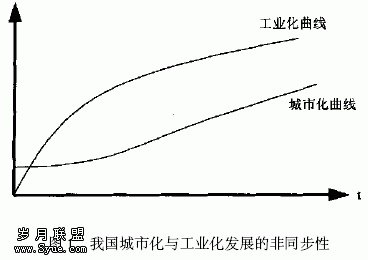村籍、地缘与业缘——一个中部中国村庄的社会分层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1
提要:南街村是豫中平原上一个村庄,1990年代迅速崛起,通过集体大办,完成了村庄化的性转变,并逐步形成自成体系的一套村籍制度,目前它已经演化成一种与工资、福利、就业、、医疗乃至婚丧嫁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制度综合体系,由此而形成的社区身份界限,成为村社区的社会分层的基础。在南街村,村籍制度的产生及其存在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它是这个村庄完全彻底的公有制和由此产生的福利制度的产物,其中既有对村民生老病死的“保障”,也有对村民思想行为的“规范”,对村民的约束力和管制力远远大于外来人。而且,村民对村庄的依附性愈大,这约束力和管制力也愈具威力。
一、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先后在豫西、豫东、豫北、豫南的若干社区作调查,近年来则集中专注于豫中平原的一个著名村庄南街村的个案研究,并由此推及南街村及其所处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观念、体制诸方面的深层问题,深感“精神制约”、“制度安排”
在社会经济变迁中的重要性。南街村是一个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迅猛崛起的中部村庄,以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著称于世。随着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南街村已完成了村庄企业化的历史性转变,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这里,传统村社的边界已被打破,并且随着新的社会成分的生成和新秩序的建立,已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村籍制度。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根据对南街村的田野调查,具体描述这一变迁过程,分析探讨这种村籍制度形成的条件背景,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对整个社区发展以及社区中人的发展的影响。
二、人口
南街村回汉两个民族多姓聚居,2000年,全村839户,户籍人口3187人。其中汉民761户,2869人,约占全村人口的90%,回民78户,318人,约占全村人口的10%.至今800多户原住居民共103种姓氏,其中王姓最多,约占全村人口的25%,分为5支,共一个祠堂。其次为李、赵、张、贾、耿,合起来共约占15%.长期以来比较分明地按民族姓氏门宗聚居。人民公社时期,南街村生产大队,共有13个生产队,按居住地划分。一——四队集中聚居着大部分王姓家族,其中一队和二队在城外“南关”,传统务农为主,大多是庄稼人。三——十三队在城内“南街”,传统上多为小买卖生意人,十二队和十三队是回民队,其中也有少数汉民。搬迁新的村民楼后,彻底打破了原有家族邻里和民族关系,按村民楼划分为22个村民组。
近十几年来,随着南街经济的迅速发展,进入南街企业的外地职工,最多时已逾万人,是本村总人口的3倍多,是本村就业人口的6倍多,大大超出本村原住人口,社会人口构成已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工种性质,女工多于男工。1999年1月,企业职工总数10207人,其中男4972人,女6075人;村民1048人,非村民9159人。外工流动性较大,有进有出,总数差额在100-200人之间。春、秋季招工时调入的较多。从1991年起,南街村先后吸收一批“有突出贡献的”外工为“南街村荣誉村民”,高薪聘请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长住村内,这些人享受南街村的大部分福利待遇,成为南街村的常住人口。由于招工有一定的条件规定,外工的年龄大多在18-25岁之间,文化程度初中以上,身高女1.60以上,男1.70以上,因此,外来人口的平均素质优于本村村民。此外还有工商法司税务银行等常驻南街单位的工作人员,合资企业外方人员以及村学校、幼儿园教师,南街村希望学校师生等等,数百人。
三、身份概念之界定
要说明这个村庄里的人和社会分层,须事先界定几个有关的概念。
通常村里人的观念里,有本村人、外村人、本地人、外地人的概念,这些可看作是一种文化的界定,一种文化概念。这种概念通行于一般乡村民间。
而现在南街村各种文件中正式使用的,有严格界定的概念是:村民、职工、荣誉村民。这些概念不单单是具有文化意义的符号,还表示界定着利益分配的权利,是一种具有实质权利意义的经济概念。这是南街村特有的概念。
村民,指一切有南街村户籍的人口。职工,指一切在南街村企业工作的人,其中有南街本村人,更多的是外来打工者。人们曾经将企业里的本村人称为“内工”,外来打工者称为“外工”。为了加强团结,共同奋斗,村领导集团经研究宣布,不准再使用“内工”、“外工”的称呼,而一律称“职工”。荣誉村民是一个新的身份概念,分为两类,一是户口已不在村里,回村参加企业的本村人;二是从外来职工中提升而来的有特殊作用或技术专长的人,对此有专门的文件规定。本村人的荣誉村民与非本村人的荣誉村民最显在的区别标志是,前者住村民楼,后者住荣誉村民楼。南街村实行工资加供给的分配制度,荣誉村民享受村民的福利待遇。
“本村人”并不等于村民。村里人的“本村人”的概念里,除了村民,还包括户籍已迁出、在外地生活工作的原南街村居民,甚至包括户籍从未在南街村、但祖籍南街村的人。这些户籍不在南街村的“本村人”,与村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企业发展初期,他们如果回村参加企业,便成为荣誉村民;没有回村,也在南街村扩大与外界的联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南街村在发展经济开拓市场方面很注重利用这部分社会资源。
“外村人”指在南街村企业里打工的当地人,他们来自邻近的村庄或县城,与“本地人”基本属同一范畴。“外地人”指离村庄距离较远的外省市人,“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区别标志主要在口音,本地人与本村人说同一种口音,而外地人与本地人口音有较大不同。
南街村还有一些常住村里,受到特殊优待的外地人和日本人,他们是村企业高薪特聘的技术专家,合资企业的外方老板、资方代表和管理人员,国外设备的销售商及安装调试人员。
国内的技术专家们住在一个四合独院内,配有一个专职炊事员负责他们的伙食。一些日本合资方人员住在村里称为“合资楼”的日本式小洋楼里,也有专人负责伙食。
以上这些人都与村企业有关系,无论村民与非村民都有一种业缘的关系。
还有一种非业缘的外来人口,他们是村里各种工程的建筑队与来村里贩卖瓜果蔬菜和日用品的小商贩。1997年,村里开放了一处“自由贸易市场”辟有摊位店铺,可以卖服装、农具、电器、化妆品、肉蛋、水果、蔬菜等等。南街村不允许本村人搞个体经济,这些个体摊贩全是外来商户,南街村向他们收取一定的管理费。
对这些概念进行清理和界定对于研究社会分层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概念表明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其产生的本身就已具有广泛深远的社会意义。
四、地缘与村籍
南街村地处县城,1949年以前社会成员构成小市民成分居多,南街村的身份认同融合于整个县城,自认为“城里人”,而没有“村”的概念。1949年土改时,多数人分了土地成为农民,不分土地的仍是市民,“当时凭自愿,绝大多数人愿意要地,就都成了农业户口,不分地的就是城镇户口”(刘坤岭访谈录,注)。之后,从个体农民到集体农民,其间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作为农村社会最基层的社会组织,这里的行政区划是不断变动的,直到1959年成立南街生产大队,才算有了较为清晰的行政边界。但是地域的边界仍然难以划清。居住在县城内的公社社员,虽然各大队有一个大致的范围,但东、南、西、北四个街区的住房以及村民与市民的住房,都有“插花”(混杂),很难划出一个清晰的边界,同属一个大队的人,从亲缘关系上讲,未必比与另外一个大队的人更近。这种情况使得南街村不同于中国农村一般的村落,长期以来它与周边社区没有十分明确的地域边界,也没有一般自然村落里那么强烈的家族观念。
同时,长期以来,低下的经济、社会地位,使这里的人只想流出去,而并不排斥别人流进来,作为一个农村社区,从这一点上说它的边界是开放的。走出农村进城当工人是当时村里人十分向往的“跳龙门”。南街村以其位处县城的“地利”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历次征兵、招工时,都有不少人通过各种关系进入城市。或者彻底“农转非”,户口迁进城,身份不再是农民;或者“亦工亦农”,虽然户口仍然留在农村,但是所从事的已不再是农业。
那时候他们不仅不在乎自己的村籍,还要力图摆脱它。而从外面进入南街的人,大多是在历次运动中被划为各种“分子”的人。比如张先皋,据说解放前曾任武汉三镇都督,“原是北街人,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南街劳动改造,是全体坏分子的头儿,平反后又当上了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前两年死了,家属都在南街,算南街人了,现在老伴在南街敬老院”(王国彬访谈录)。这说明以往南街村的地缘边界并不严格,向外,是向上流动,向内,是向下流动。
村里人开始注重地缘关系和户籍身份,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80年代中期,南街村集体企业开始起步,急需人力物力的支持。而村里的青壮劳力大多分布在县城里的各个部门或工厂,政策放开以后,还有不少人搞个体经营。当时南街村党组织号召人们回村为发展南街村的事业做贡献,并实行集体福利政策凝聚人心。1990年代以后南街村经济迅猛发展,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农村。企业的大发展也将大批外来人口引入村内,许多外来人不仅在南街村企业打工,还有想在村里长期定居下来的趋势。于是矛盾产生了:一方面是经济发展需要引进大量外来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发展带来的利益,只想让“自己人”共享,而不愿与“外人”分享。于是他们开始重视并强调地缘关系和村籍,制定了《关于职工福利待遇的有关规定》等一系列政策,逐步形成自成体系的一套村籍制度。
五、社区身份与职业分化
在这里,村籍制度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种与工资、福利、就业、、医疗乃至婚丧嫁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制度综合体系,由此而形成的社区身份界限,也就成为村社区的社会分层的基础。
大体说来村里存在8种身份群体(加:各群体分别占村人口的比例):
1、本村人。这里是指实际生活工作在村里的南街村人,包括拥有村籍的村民和没有村籍的本村荣誉村民。他们在职业与福利分配上没有区别,在村里拥有最优越的职业位置和社会身份。全村这样的人口3000多人,其中职工1700多人,约占企业职工总数的15%.本村人在企业里大多从事管理类工作,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赖好是个人都是头儿”。
2、外来荣誉村民。至2002年已有300多人,约占职工总数的3%.他们大都是企业的业务骨干,少数是中层管理人员,但都是副职。虽然享受村民待遇,但究竟还是外来人,缺少本村人的主人姿态和心态,地位不那么稳定,随时有离去的可能。
3、一般打工者。最多时超过万人,1998年以后,企业内部改革“减员增效”,人数维持在8500人左右,占职工总数的80%以上,都是一线工人。他们流动性很大,是村社区中社会地位最低人数最多的群体。
4、外聘人员。主要是村企业聘请来的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村戏校聘请的专业老师,共30多人,约占职工总数的0.3%.他们的收入和职业位置较高,但在村里的社会地位说不上,对村庄的依附性低于一般外来工,较具独立性,一般无意在村里长期落户,村里为他们单独安排吃住。
5、外方人员。指合资企业中外来投资方人员,包括外方经营代表,外方聘用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不足10人。合资企业的外方人员在村里就像“外宾”,受到“外宾”的礼遇,也受到“外宾”的限制,他们除了直接参与企业管理,不参加村内其他事务,也不受村内行政领导,不参加村里的各项活动,工资由外方发放。
6、教师。南街村办有中学、小学、幼儿园,全部经教委正式批准,教师全是公办教师,共计250人左右。教师除了领取国家工资,同时享受村民福利,村里专门盖有教师楼,结构与村民楼一样。
7、顾问。是一些由县委县政府部门退休的老领导老同志,被南街村请来当顾问,共15人。他们除保留原退休待遇工资外,享受村民福利,村里每月发100-200元生活补贴。
8、驻村单位工作人员。包括派出所、检察室、律师办、法庭、农行支行等驻南街村的工作人员,共130多人。他们全是国家编制内人员,工资关系在各派出单位,村里对他们有适当补贴。
从职业划分的角度来看,这8种身份群体有明显的差异,可以说,从业以社区身份为先决条件,社区身份决定着职业的类型。从与村庄的关系来看,前4种身份群体:村民、荣誉村民、外来打工者、外聘人员,统称为企业“职工”,共计11000人左右,占总居住人口的96.5%,与村庄的关系直接而密切,职业类型由企业决定;后4类身份群体:外方人员、教师、顾问、驻村单位人员,共约400人,占总居住人口的3.5%,与村庄的关系较为间接而疏离,职业类型是在来南街村之前就已确定了的。
目前,南街村收入已占全村总收入的99%以上,农业收入不足1%,除了一个80多人组成的农机队负责农田耕种管理,余者都从事工业生产。
南街村企业管理机构可分为6层:
第一、三大班子,即村党委、村委、村企业集团领导班子。最初21人,2002年为16人;
第二、公司各处室,约40人;
第三、厂队长、经理,50—60人;
第四、厂队的科室主任,约200人;
第五、车间主任,约400人;
第六、班组长,不脱岗,约1000人。
车间主任以上管理人员700多人。其中第一、二、三级管理层领导全是本村人,第四、五级管理者中,正职多为本村人,副职不少由外来荣誉村民担任。第六级班组长,被称为“带班长”,不脱产,直接参加一线生产,绝大多数是外来人担任,这是工厂里最初级的生产管理者,负责一条生产线或一个机台的工作监督。
2002年1月统计,南街村企业职工总数10321人。其中本村人1752人(村民1304人,本村荣誉村民448人);外来职工8596人(荣誉村民360人,一般职工8209人)。本村人中,约40%是车间主任以上的管理人员,2-3%担任班组长。余者也绝少一线工人,最普通的也可以作、保管员、治安员、档案员等。村里的老人和妇女,做办公楼勤杂工、环保队清洁工、职工宿舍管理员、食堂送饭工等,不需要技术,时间机动灵活,方便照顾家务。虽然决策层、经营层的职位有很高的职业声望,但是村里最重要的领导岗位都已被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占居着,村里的年轻人,现在最热衷的工作是业务员,挂在嘴上的理由是这份工作锻炼人,而实际是收入高。企业业务员每人每天60-90元出差补贴,比起在企业里每月200-300元的工资收入显然要高得多。其次,司机,特别是小车司机也是村里年轻人十分向往的工作。
外来人绝大部分是在村里工厂做一线操作工。外来人中的荣誉村民,是从外来打工者群体中提升而来的,其中有些从事部门管理工作如车间主任、技术科长等,但一般是副职,约占外工人数的2-3%。或者是比较专门的职业,如报社编辑、文工团演员、医生等。外聘人员主要从事专业管理类和技术类工作,如生产部主任、技术科长、总工程师、戏校教师等。
外来荣誉村民、一般打工者、外聘人员这三种身份的外来人中,职业身份与本村人有交叉。
但即便他们与本村人的职业身份是相同的,社会地位也不相同,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受职业身份和社区身份两个方面的影响。
南街村的外方合作者主要有两家,一家日商,投资彩印厂和麦恩食品厂,日方代表是位东北女性周静华,开始时长住南街村,作为总经理参加企业管理。彩印厂投产安装时,来的日本专家技术人员有十多人,村里专为他们建一座日本别墅,村里人称“合资楼”。1994年起日方退出管理,只享受分红,合资楼基本空着,周静华偶尔来村里住一下。一位日本食品专家大内,自带一个翻译,高薪受聘于南街村,一两个月飞来一次作技术指导,一般问题通过联系处理。另一家港商,以技术参股胶印厂,港方代表也是大陆人,直接参与管理,带七八个技术管理人员,与这个厂的南街村一方聘用的技术人员同住在一所平房院里,有专职炊事员。外方人员与南街村保持一种很纯粹的业缘关系,除了工作很少与村民交往,业余时间有时与“班子”有关人员打打麻将作为消遣。两家外方投资者之间没有来往。南街村在企业管理上也可以说是“一村两制”,在南街人看来,“他们搞得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而南街奉行的是共产主义原则”(吴培谦访谈录)。这是一个矛盾撞击又相互影响磨合的过程,此为另题作另论。
教师、顾问、驻村单位人员,在职业圈之间互不跨越,特别是与村民没有交叉,更不存在竞争,这是因为在这里存在着个人资质条件,特别是身份制度——国家体制内“干部”身份——的限制。教师是很受尊重的职业,南街村学校、幼儿园的教师都是“国家干部”身份,享受财政工资和村民福利双重待遇,在村里学校、幼儿园归宣教办管理,受村党委直接领导,学校校长和幼儿园园长都是南街人,教职工也参加村里的各项政治活动,但是教师们很少与村民交往,对村里的事情不关心也不感兴趣。“顾问”并不能算是一个职业的概念,而是一种身份的概念,在南街主要是起“政治”的作用,他们被称作智囊、参谋,职责是协助村党委工作,利用过去的社会网络关系,帮助村里解决工商税务及债务问题。村里召开各种大会请顾问领导坐主席台上,会后请作指导报告,表面看来政治地位很高,但他们对村里各项决策不参加表决,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驻村各单位人员的职责也很明确:为南街事业“保驾护航”,在各自岗位上配合南街搞好服务。
六、讨论:福利制度与人身依附
村籍制度是经济先发达村庄,与其他村庄之间形成巨大差别后,用以守护自身利益和加强利益控制的一种制度,也是巩固地缘关系和强化内聚力的制度化形式。其核心是控制外来人口进入和防止村社区利益外流。在南街村,村籍制度的产生及其存在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它不单单受到封闭的村落文化的影响,也受制于现有的土地制度,特别是它还是这个村庄完全彻底的公有制和福利制度的产物。
南街村的村籍制度,使绝大多数外工享受不到本村人享受村福利。所以外界常有人批评南街村剥削外工。
但是问题的要害并不在此。抑外强内几乎是每一个有明确利益边界的社区或组织单位在资源分配中所通行的惯例,而并非南街村独有的“特色”。现行的土地制度,使人头一份的土地成为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资本和最终的社会保障,也是它抑外强内的物质基础与“法理”依据。这样,对于村庄社区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利用外来劳力的同时,又限制外来人口的移入。这与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对农民工在经济上的吸纳和社会上的拒入同一道理。
问题在于,因此而在本村人和外来人之间所造成的难以逾越的鸿沟,还会给村庄和个人的带来不利影响。南街村虽然做出种种姿态表示对外来人的欢迎和认可,如向外工倾斜的工资政策,吸收外来者为荣誉村民、对外工食宿免费等等,也暂时吸引了外工,但无法解决人才合理流动的问题。因为社区身份的隔阂,外来人无论怎样努力,都有可能永远处于“打工者”的地位而不能成为村庄的“主人”,村庄最终不会接纳他们,他们也不认同于村庄。这样,村庄不可能拥有稳定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队伍,也不可能保持稳定的人口聚集规模。因此,无论村里人还是外来人都说:南街村留不住人。
更应当注意的是这种村籍制度对南街本村人的限制似乎更大。社区身份强化了他们的权利,同时也规定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村集体赋予他们生老病死的保障,同时也限制了他们个人的更大发展。南街村人只有株守祖居之地,才能保住既得利益,对于他们,特别是年轻人,都必须以牺牲日益多元化的个人需求为代价,因眼下利益所累而失去了更大的个人发展的机会。
在这里,村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有力地进入和支配着社区家庭和成员个人的生活,导致个人对村庄共同体更大的人身依附。“讲政治”可以说是南街村最显著的特点,村庄在政治思想行为举止方面对村民更具约束力。《南街村村规民约》对村民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都有严格要求,与之配套的措施是“十星级”管理。比如“思想作风”第一条规定:不重视政治学习、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信念不坚定,参加各项活动不积极,有过激言行怎么办?处理办法:进学习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转变错误认识,提高思想觉悟。第四条:无事生非、挑拨离间、戳三捣四,讽刺挖苦先进怎么办?处理办法:写检查1500份,由本人送至各单位及每户村民,义务劳动三个月。第十一条:搞第二职业怎么办?停发一切福利,取消建设小区的资格。而且还搞株连:第十二条规定,不愿参与南街村小区建设怎么办?
取消全家(父母、爱人、孩子)在南街村享受的一切福利……第十五条规定,对触犯人员的家属,停发一切福利,加强法规教育,视其态度酌情处理……
总之村庄对村民的约束力和管制力远远大于外来人。而且,村民对村庄的依附性愈大,这约束力和管制力也愈具威力。外来人对村庄的不满达到一定限度可以一走了之,而村民却不能轻易“抛家舍口”,远走高飞。而过分限制收入差距的福利分配制度,缺少激励机制,以致一些年轻人不求上进,不愿当车间主任而宁愿当保管员,“不操心,也不少挣钱”(孙德甫访谈录),这是一些外来者不能理解的。
这种村籍制度还表明,南街村这种脱胎于人民公社体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公有制模式,相对于以往一元化“大一统”中央全权,是一种分权,增强了村社区自主自治功能。相对于南街社会自身,却是一种集权甚至极权,消灭了公有制之外的其它一切所有制形式,形成新的“大一统”,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却凌驾于社会有机体及每个个人之上,垄断一切从而推动一切也窒息一切,压抑个体个性滋生蒙昧主义。其“未经个体性充分过滤的集体主义”,是妨碍其挣脱传统束缚走向社会的阻力。
传统农业社会以个人依附于身份性共同体为特征,现代社会则要求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完善的民主政治。这意味着每个个人具有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与公民权利,从而成为“完成的个人”。“平等,是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基础,是最崇高、最道德的基础,意味着不受专制压迫不受干涉、不受强制的自由,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人人都有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权力,是实现基本人权的基石”(鲁思·本尼迪克特,1989:32)。显然,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的社区上升到这一境界,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如何消除人的依附性而代之以人的独立性,从传统农业社会迈进现代公民社会,是包括南街村在内的中国广大农村社会中所存在的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
埃弗里特·M.罗吉斯等,1988,《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
丹尼尔·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
杜赞奇,1994,《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江苏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1985,《乡土》,三联书店。
拉南·魏茨,1990,《从贫苦农民到化农民》,中国展望出版社。
刘岱总主编,1992,《吾土与吾民》,三联书店。
鲁凡之,1987,《中国社会主义论》,台北南方出版社。
鲁思·本尼迪克特,1989,《菊与刀》,商务印书馆。
曼海姆,1992,《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三联书店。
乔·奥·赫茨勒,1990,《乌托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斯东,1998,《苏格拉底的审判》,三联书店。
王沪宁,1991,《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铭铭,1997,《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
王晓毅,1993,《血缘与地缘》,浙江人民出版社。
许烺光,1990,《家族、种姓、俱乐部》,华夏出版社。
英格尔斯,1992,《从传统到现代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乐天,1998,《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
郑大华,2000,《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文献出版社。
上一篇:消除体制障碍,让农民“后”富起来
下一篇:建立农村养老保障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