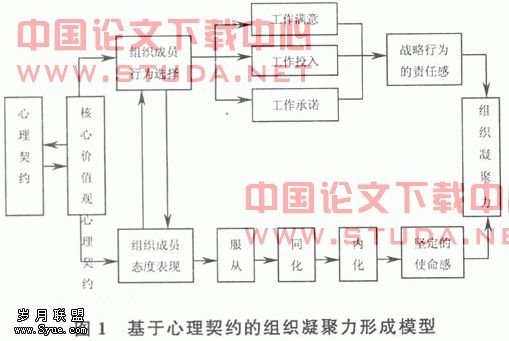尘埃未定时的反思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1
2001年9月11日,我几乎是在第一时间便知道了美国纽约发生的惨剧。惨剧使我震惊,更引起我久久的沉思。
20世纪是人类迈入文明之后最为惨烈的世纪。上半个世纪有德日法西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下半个世纪有文革反文明的悲剧加闹剧。进入21世纪,人们曾天真地认为,人类将告别惨痛迎来新的纪元。但随着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楼被两架挟持的波音客机所摧毁,新纪元的美好蓝图已被撕碎。双塔惨剧,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类21世纪的生活方式和游戏规则,现在尚难预料。但作为一个学者,我相信,它的冲击波,必将会对社会对人文学科对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21世纪永恒的反思主题。
眼下,尘埃尚在,惊魂甫定,绝不是做理性反思的恰当时刻。但看到中国各网站上汹涌喷出的狭隘民族主义言论,这里,只能请双塔之下的怨魂宽容,容我提前做这样的理性分析,以供各方人士或批判。是为“尘埃未定时的反思”,其重心将放在对狭隘民族主义和《东方学》的反思及批判上。
一、对双塔惨剧的反思
双塔惨剧,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残,也是对构成人类文明两大基石:科技与理性的挑战[1] 。惨剧的发生,以更直白的方式暴露出人类现代文明内在的深刻危机,包括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冲突与危机。
在对20世纪人类悲剧的反思中,现代学者早已提出了科学异化的概念。凡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武器,无一不是高科技的产物。高科技本身是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了福祉,也带来了生态灾难和生存恐惧--核按钮一旦掌握在战争狂人手中,人类将陷入灭顶之灾。但在那种异化分析中,武器的边界还是清晰的。只要将核武器的秘密守住,或只要能制造出相应的反导、反核武器,如此等等,根据矛与盾原理,高科技本身最终会制止高科技所带来的灾难。但双塔灾难却粉碎了这一理念。双塔是现代高科技的象征,摧毁双塔的两架波音飞机更是现代高科技的结晶。它们间没有矛、盾的概念。恐怖分子可能仅仅动用了最原始的刀具,便将巨型客机变成巨型武器,而巨无霸般的大厦本身,接下来又变为大屠杀的工场:大楼的每一块碎皮每一片玻璃都变成为锐利无比的凶器,大楼躯体变为巨大的坟墓。就这样,两个高科技的产物,瞬间都变成了能量巨大的杀人武器。这样的思路一旦被打开,那些人类文明视为骄傲的许多高科技成果,可能都将成为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斯之剑!这便意味着人类现代文明生活,就建筑随时可塌陷的万丈悬崖之上!想到此,真让人不寒而栗。尽管双塔惨剧后,有科学家说,现代科技会应对这样的挑战,可以避免类似的惨剧。但我相信,类似情况,是防不胜防的。只要世界上存在丧失人性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这样的风险便只能随着高科技的而越来越越大。因此,更重要的还是要建构起强大的理性的心理防线。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双塔惨剧最令人颤栗的,并不是惨剧本身葬送了多少人的生命,而在于这一惨剧制造者对人类理性底线的彻底否定和扬弃。人之为人,不在他能制造工具,更在他是理性的存在。而这一理性的底线,就是他对人的属类性即人性的价值认同。通常所谓的人权、自由、平等、正义或民族尊严、民族独立等等价值概念,都需要建立在对人性价值的理性认同上。不把自己的同类视为人,还有什么“人权、自由、平等、正义”可言!凡异族皆可杀,还有什么民族尊严和民族主权可言!人类几千年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就是建立起了被普遍认同的人性概念和把人当人对待的人道准则,以及相应的民族尊严与主权原则。无论人与人之间有存在怎样的权势差异,人也不能象对猪狗牛羊那样随意将人杀掉;无论民族与民族之间有怎样的文化差异,一个民族也不能随意侵略迫害另一个民族。
当然,由于人类生存资源的稀缺,由于各种不公平制度的存在,由于种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具有理性的人类或许更善于理性地对他人(或其它民族)进行抗争、报复或劫掠,各类革命、战争或暴乱便是不可避免的。但理性的人类在进行革命、战争或暴乱时,都会给出正当的理由,都不会承认自己是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而都要将相应的责任推给对方。这便表现出人类对共同游戏法则的认同:基本人性,是不能扼杀的;基本人道,是不能践踏的。只不过,在法西斯字典中,普遍人性,被优势和劣势人种所取代;在文革的语录中,共同人性,被对立的阶级性所替代。这便是人类大悲剧大惨剧的理性渊薮--既然对手已失去属人存在的价值合理性,那怎样从精神和肉体上消灭便只是个技术问题了。好在历史不是某个强势集团所书写的,最终的结论必将还原正义。正因如此,在20世纪末叶的局部战争中,尽量不滥杀无辜,便成为对战争本身正义性的衡量尺度--即便你是打着正义旗号的入侵,但只要造成了无辜平民的伤亡,那就也应承担战争罪责,并应接受正义的审判。美国也不例外。
但在双塔惨剧中,这一游戏法则却彻底地、史无前例地被践踏了。如果恐怖分子不是劫持客机,而只是引爆自己的肉体炸弹;再如果他们袭击的目标只是五角大楼而不是世贸中心;那么,这些恐怖行为尚可寻找某种正义性的理由。因为站在他们的民族或利益集团的立场上,这可解释为弱势群体对被美国政府所践踏或剥夺权利做出的绝望报复。美国政府,依仗其强势话语,将其国家和民族利益掩盖在捍卫普遍人权旗帜下,所做出的许多霸权主义行径,本身确是应受到谴责和批判的。但双塔惨剧的制造者,所攻击的首选目标却是国际性的商业设施,是数万名无辜的平民。这便使它必然激起全人类的公愤。因为这是一种大屠杀,是一种比希特勒更卑鄙的大谋杀。如果听任这样的谋杀行为发生,那么,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绥靖政策一样,最终只能将整个人类文明葬送掉。道理十分简单,当我们今天为美国的惨剧而幸灾乐祸时,明天,恐怖分子会用同样的手段在,在北京上海制造同样的惨剧!因为对恐怖分子来说,寻找某个正义理由实在太容易了。因此,谁为这种恐怖行动张目,那等于将自己的灵魂抵押给了魔鬼!
令人遗憾或震惊的是,国内许多网站上这种将灵魂抵押给魔鬼的舆论一时间竟甚嚣尘上!当然,经历过近年来中美之间种种磨擦事件,再加上诸多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左派”言论,一般民众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在此刻总爆发并不令人奇怪,甚至可以说非常正常。但这种情绪爆发的正常性,决不等于它的价值合理性。那些因仇恨美国霸权主义,因对王伟、对驻南烈士的悼念而对双塔惨剧幸灾乐祸狭隘民族主义舆论,毕竟已远远偏离了人类基本的理性价值立场。此刻,凡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社科人文学者,作为人类普遍理性和道德良知的体现者,作为人性价值尊严捍卫者,理应站出来,抵制、批判和彻底否定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而不是相反。在这一基本立场上,是不应有什么学术派别之分的。
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为这种幸灾乐祸做理性辩护的恰恰是一批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某些人文学者。双塔坍塌了,那惨案毕竟发生在大洋彼岸,其巨大的冲击波我们感受不到;但此刻,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旦理性堤岸被摧垮,我们的同胞宣泄出来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是何等地可怕!当然,这些人今天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对准美国的。但谁能保证,明天他们不会打着同样的崇高旗号,对准自己的同胞呢?文革的悲剧不正是这样开场的吗?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高喊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将昔日的老师或邻居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时,其理由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被指控为美国特务日本汉奸!一旦失去理性的价值立场,一旦越过做人的人道底线,人类必将被笼罩在恐怖之中。中国文革的证明了这一点,那些“革”别人“命”的红卫兵,很快被别人用同样手段“革”了“命”;今天的中东局势也证明了这一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屠杀对方无辜者的同时,也使自己同胞面临着随时被屠杀的命运。就世界范围而言,一旦某些国家公然拒绝遵守人类共同的游戏法则,那么,人类的文明也将面临灭顶之灾。因此,作为社科及人文学者,我们需要正视并深入研究双塔惨剧背后隐藏的人类文化的内部冲突及危机,但却绝不能承认恐怖主义的合理性。对这种恐怖主义行为的任何支持和赞赏,都是对人类文明准则的背叛,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二、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反思
必须看到,民族主义从来都是双刃剑。理性的民族主义,抵御外来入侵,捍卫民族尊严,促进民族进步,是捍卫人类基本价值规范的正义之剑。狭隘的民族主义,盲目自大、因循守旧、仇视异族,则往往是践踏人类基本价值规范的邪恶之剑。但我们长期来,并没注意划清这两者的界限。我对鲁迅尊崇有加,就是因为他是近代中国真正的理性主义爱国者。鲁迅深深爱着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但他却绝不狭隘,不夜郎自大,更不盲目排外,对于民族的劣根性,他深恶痛绝,绝不护短。最使我感佩的,是他对美国传教士明恩浦的态度。他生前多次希望能将明教士的《中国人的素质》翻译过来,让中国人照照镜子,认识自己。他甚至这样说:外国人“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2] 。
但在文化中,鲁迅似乎是另类。中国的民族主义几乎从没突破“狭隘”的囿限。“一代天娇成吉思汗”,几乎被我们视为民族英雄。在内蒙成陵成吉思汗坐像后面,挂着横跨欧亚的巨大元帝国版图。但这位英雄在中亚地区制造的屠城事件,却每每被忽略了。其实,这是如同德日法西斯一样的残暴行为,只是时代久远,无人提起吧了。我在日本福冈,见到过多处纪念挫败元入侵者的纪念标志。如果当初元帝国攻陷了日本,那我们更可自豪一番了。而同样是这个日本,在张扬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在不时地回避他们对亚洲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原因无它,就在日本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仍有市场。当初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胆敢发动侵华战争,正是由于得到狭隘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普遍支持的。儿子参军,母亲要送一把刀,不是用来护身,而是让他效忠天皇,关键时刻自裁。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人是很吃过狭隘民族主义苦头的。今天,当我们抗议日本篡改教课书、抗议日本首相参拜精国神社时,不就是在批判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么!与此同时,我们难道不该反思一下自身的狭隘民族主义么!
平心而论,由于民族主义是一种带有浓烈情感、渗透着群体无意识的社会意识,本身便带有浓厚的非理性特征,爱屋及乌,恨屋亦及乌。要对这种渗透集体情绪的爱憎做理性控制,是极不易的。特别是对爱面子的东方民族来说,更是如此。但这并不是说任何民族都难以跳出狭隘民族主义的桎梏。我想起了一位德国学者的表现。那是六年前,在与一位曾在欧盟任职的德国教授座谈改革问题时,有人不合时宜的地提起日本对侵华罪行的暧昧态度,询问教授的看法。就在大家感到有些难堪时,这位德国教授回答道:“对于日本的态度我无法评价,但对于德国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我们完全承认。尽管我是战后出生的,但如果在座诸位需要的话,我可以在这里代表德国表示忏悔。”会议室中的空气骤然凝固了。大家都被这位德国教授的坦诚态度所震撼。他赢得了入会者的尊重,正像德国人民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一样。深究下去,这是与德国知识分子坚持理性原则,并对青年进行理性主义的分不开的。有关法西斯的历史,是德国学生必学并反思的一段历史。我在一篇鲁迅的杂文中写到:“德国在普鲁士时代曾经是庸人气息弥漫的民族,连歌德都不例外。但经过包括马克思再内的一代代思想家家的批判,经过贝多芬这样伟大家的陶铸,百年过后的德意志民族已是世界上最有自信和自尊、最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民族之一。”这段话就是由此事感悟反思而来的。
令人遗憾的是,当代某些中国学者,不仅没继承鲁迅的理性民族主义思想,如同德国知识分子那样担当起高扬理性民族主义的责任,反而从鲁迅那里大大后退了,甚至将鲁迅视为批判的对象,以张扬他们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典型的例子就是刘禾及冯骥才借贩卖《东方学》的观点对鲁迅所作的批判。对此,我已有文章批判,此处不论。这里,我只想谈谈对《东方学》的看法。
三、对《东方学》的质疑
《东方学》被刘禾等人介绍到国内,引起学坛不小的振动;《东方学》的观点也被作为“后殖民”学说的经典论断被接受。于是,他们便纷纷寻找中国也被西方传教士等等妖魔化的例证。便找到了《中国人的素质》。对于《素质》是否歪曲丑化中国人,我认同鲁迅的观点,并拟另文专述。概而言之,如同阿Q对他头上癞疮疤的态度一样,在讨论别人是否凭借话语霸权丑化自己之前,先得照照镜子,了解自己头部的真实状况。否则,无论是讳亮忌光也罢还是封住别人的嘴巴也罢,自己的丑陋形象并不会因此改变,而只能使自己在外界眼中愈加丑陋。这似乎是常理,但碰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及其理论家,它便失效了。
实际上,刘禾们将《东方学》搬运到中国,本身就是一种基于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误读。严格说来,赛义德的所谓《东方学》,应是《东方-阿拉伯学》,是不能与西方的汉学划等号的。赛义德自己在《东方学》中便承认,“在汉学家和印度学家与伊斯兰和阿拉伯学家所取得的收获方面,也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实际上,欧洲和美国有许多专业的伊斯兰研究者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这一对象的研究,然而却仍然发现无法让自己喜欢它,更不必说仰慕这一宗教和文化。”[3] 赛义德说的对。确如西方汉学家自己所言,他们“把中国的古文化向外国介绍,使人对中国古文化发生一种崇敬的感情,由于这种崇敬的感情,对中国和中国人发生一种由衷的爱好。”[4] 西方汉学界尽管也有少数仇视中国的学者,但更多的人是因汉学而爱上了中国和中国文化。因此,将《东方学》的结论搬到汉学领域,硬要找出相似的和例证,只能是徒费心机。目前所见到的,除了刘禾借“语际书写”歪曲明教士原文生造的论断之外,后学们没拿出一件像样的例证,证明西方正宗的汉学家如何操作殖民话语丑化中国并为殖民者侵华提供舆论支持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方学》与阿拉伯文化的关系。尽管赛义德极力否定自己的理论是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提供理论支持,更不是“反西方”的。但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当赛义德教授坚决反对巴以和谈,并亲自向以色列占领区投掷石块时(此举因被曝光引起舆论哗然),他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已暴露无遗了。赛义德从理论上为自己辩护的根据是,他是在用一种“反本质主义”理论陈述事实。我搞不懂后学学者的所谓“反本质主义”是怎样一回事,只相信任何事实背后肯定有它存在的根据,并可进行价值评价。赛义德在《东方学》中记录了几段西方人对阿拉伯人的描述。其中便包括对阿拉伯人缺少清晰性;容易沦为“阿谀逢迎”、阴谋和狡诈的奴隶;对谎言有顽固的癖好、“浑浑噩噩、满腹狐疑”等等人格缺陷描述。[5] 这其中有些与明教士对人的描述大体相同。东方学者以此为据,得出西方人高于阿拉伯人的结论,那是一种价值评价。你可以否定这种评价,但同时,也得考证一下这些事实是否存在。可能对反本质主义者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否定西方人的价值评价。于是,翻遍全书我既没找到赛义德对这些事实存在的反证,也没有他对自己民族缺憾的反省或反思,而只是反复强调西方人眼中的阿拉伯世界是不真实的,是被歪曲的。这样一来,《东方学》客观上不是在为极端民族主义张目又是什么呢?
美国的人类学者乔治.E.马尔库斯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赛义德“在进行批评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以同样的修辞极权主义手法去反对他所选择的论敌”。“他没有认识到,东方学的对象,即他所要辩护的民族内部也存在、文化的分化”。[6] 事实确是这样,如果说巴以冲突尚折射出东西文化差异的话,那么,两伊冲突、伊科冲突以及各阿拉伯国家内部如阿富汗派别间的冲突,几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对此又该用怎样的西方文化霸权解释呢?这就间接地又回到了双塔惨剧。对处于美国话语中心的作为“特权知识分子”的赛义德来说,《东方学》问世20多年来,给他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声誉,但它给他的民族带来多少文化上的进步呢?笔者对阿拉伯世界素无研究,不敢妄断。但我想,如果赛义德有鲁迅般的理性,如果他在《东方学》中能对自己民族文化做出正确的价值评价,即便不如鲁迅那样对传统文化做彻底否定,只要能做出些许理性反思,那么,在《东方学》问世20年后,阿拉伯世界可能会增强团结,巴以和谈可能会取得成功,而双塔惨剧可能便不会发生。当然,这只是一些可能。但看到阿拉伯世界的现状,再读读赛义德极端之论,我真的很庆幸,我们民族拥有的是鲁迅,而不是赛义德;鲁迅塑造了一个阿Q让我们时时警策自己,而赛义德却恰恰相反。鲁迅,也应是东方民族不朽的精神支柱。
遗憾的是,从《东方学》到双塔惨剧所暴露出的许多知识分子身上的民族劣根性,使我深深感到,许多学人,包括著名学者,已经离鲁迅越来越远了。这值得我们警惕再警惕。否则,同样的惨剧会离我们越来越近。到那时,该其他人来幸灾乐祸我们了,当然,同样是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
[1] 注,这是沿用传统的说法,也是理性的产物。更科学的说法,应当是一块基石,两大分支: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
[2] 《全集(一)、坟》214页。
[3] 《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5月版,第442页。
[4] 桑兵著:《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56页
[5] 《东方学》,第48页。
[6] 乔治.E.马尔库斯 米开尔.M.J.费彻尔著:《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17—18页,三联书店,1998年3月版。
上一篇:从恐怖主义到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