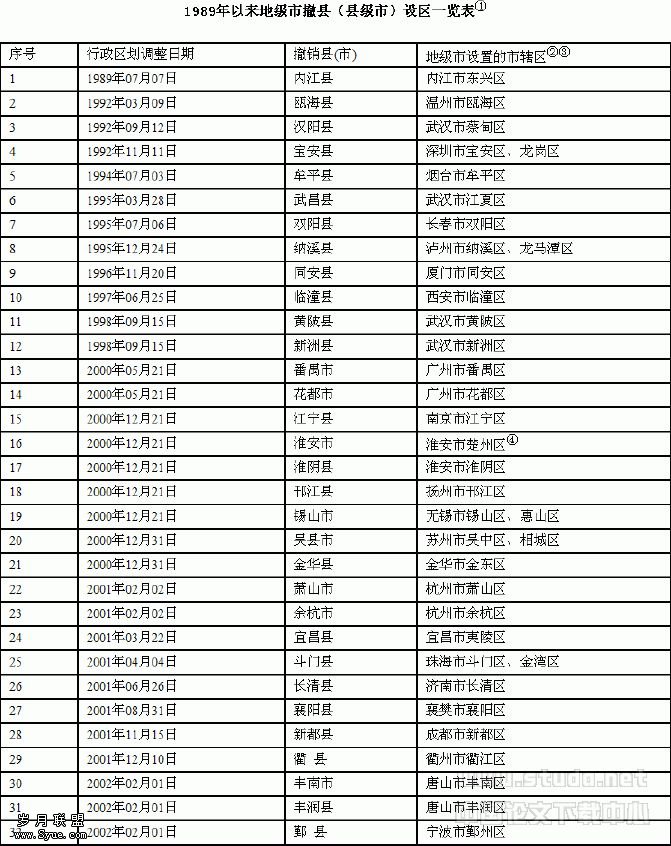“中间扩散”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0
体制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权力中心成为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能力和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方向、形式的主导因素。这样一种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在以较低的摩擦成本启动中国市场化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这种制度变迁方式的内在规定性,因此从理论上说,它在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方面存在着一系列难以逾越的障碍。然而,事实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不断深化。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是,当自上而下的改革面临障碍时,是哪些利益主体在市场取向改革中扮演着“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本文通过对江苏省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从自费开发区到省重点开发区,再到“国批”开发区的演变的案例分析,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认为放权让利改革战略与“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使经济利益独立化的地方政府不仅愈来愈成为沟通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中介环节,而且还直接从事能导致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活动。本文由此推导出的结论是,一个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国家有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选择一条激进式改革道路,而是走上了一条利用已有组织资源推进市场化进程的渐进改革道路。权力中心作为市场取向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制度供给能力和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形式的主导因素。这样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在以较低的摩擦成本启动中国市场化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 ,但由于这种制度变迁方式的内在规定性,因此从理论上说,它在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方面存在着一系列难以逾越的障碍(杨瑞龙,1994)。然而,事实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不断深化。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是,当自上而下的改革面临障碍时,是哪些利益主体在市场取向改革中扮演着 “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并不断推进市场化进程? 二、“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一种新的理论假说
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规则,其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诺思,中译本,1994)。随着市场规模、技术、行为人收益预期等因素的变化,很可能出现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打破原有的制度均衡。如果组织或操作一个新制度安排的成本小于其潜在制度收益,就可能发生实际的创新。至于一个社会通过何种制度变迁方式来获取这一潜在收益,则主要受制于这个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偏好结构。主流制度经济学一般认为,获取潜在制度收益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即个人或一群人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确定预期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实施的创新;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方式,即权力中心凭借行政命令、规范以及经济刺激来规划、组织和实施制度创新。
我国在改革之初选择的是典型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杨瑞龙,1993; 1994),其选择的目标是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产权并非纯粹是一种凭借私人信守来得到履行的私人之间的合约,因此在一个由权力中心的供给意愿和能力主导变迁方向的框架内,为完成向产权明晰化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不管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还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都会因陷入“诺思悖论”而面临一系列难以逾越的障碍(杨瑞龙,1994)。原因在于:为了解决搭便车行为和获得规模经济,一个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依赖于国家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但国家在界定和保护产权时,不仅具有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实现社会总产出最大化的动机,而且总是力图获得最大化的垄断租金。由于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垄断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从而当国家面临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时,会容忍低效率产权结构的长期存在(诺思,中译本,1991)。
突破“诺思悖论”的现实制度变迁方式可能介于纯粹个体的自愿牟利行为和完全由权力中心控制之间,即在私人之间的自愿契约与权力中心的供给行为之间存在一种既能满足个人在制度非均衡条件下寻求最大化收益的要求,又可通过在与权力中心的谈判与交易中形成的均势来实现国家的垄断租金最大化的集体行动。实施这一集体行动的主体便是组织。所谓组织,是指在既定制度规则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等团体。在现有约束所致的机会集合下有目的创立的组织是作为制度变迁的代理人角色出现的,当出现获利机会时,具有充分谈判力量的组织就会利用政治来实现最大化目标(诺思,中译本,1994)。组织在追求潜在收益(财富最大化)过程中会逐渐改变其结构,使国家在保护旧产权形式的成本递增的同时,增加从新产权形式中的获益,从而化解“诺思悖论”。
在以私人合约为基础的分散化决策中,市民社会之间制度化的协商和谈判既能协调各种私人权威,又能监督、约束、抵制和对抗国家的可能侵犯,从而这种超越个体水平的集体行动可同时增加国家守护旧产权形式的成本和保护产权创新的收益,直至重新建立国家获取租金的新的合约结构,使国家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新产权之间达成一致(周其仁,1994)。在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中,由于权力中心在制度安排的博弈中处于支配地位和产权关系的模糊性,以个人合约或组织为基础的集体行动因谈判力量的弱小或外部性问题而难以突破权力中心设置的制度创新的进入壁垒。然而,随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的选择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地方政府不仅拥有了较大的资源配置权,而且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地方政府经济实力的提高所引起的谈判力量的变化导致了重建新的政治、经济合约的努力,即地方政府不再纯粹地行使行政代理职能,被动地贯彻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而会为谋求可导致本地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与权力中心讨价还价。权威扩散化后,权力中心为保护旧的产权关系需支付更多的成本,同时可从由地方政府实施的制度创新中获得的收益增加(如财政上缴增多),于是,权力中心会修正制度供给意愿,或者追认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当经济利益相对独立化的地方政府成为沟通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中介环节、突破权力中心设置的制度创新的进入壁垒时,就可能使国家垄断租金最大化和保护有效率产权结构之间达成一致,化解“诺思悖论”。随着地方政府在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中逐渐扮演“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现实的制度变迁更多地表现为权力中心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我把它称之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它表明我国的市场取向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本文通过剖析江苏昆山自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案例,验证了上述理论假说,即在新旧体制因素处于相互对峙的格局下,现阶段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现实路径可能既不是从上(权力中心)做起,也难以从下(微观经济利益主体)做起,而是从中间(经济利益相对独立化的地方政府)做起。地方政府与企业合作扮演制度创新中的“第一行动集团”角色,追逐潜在制度收益;权力中心更多地从改革之初的倡导者转变为事后的追认者(即事后认可地方政府自发的制度创新行为),从而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三、地方政府利益独立化后的制度创新需求
在诺思的制度变迁模型中,国家理论与产权理论是两大核心。在国家理论中,诺思抽象掉了地方政府行为,即他假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具有相似的目标函数与面临相同的约束条件,集中考察国家与产权主体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博弈过程(诺思,中译本,1991)。显然,这样一种理论假说很难真实地描述我国的制度变迁过程。事实上,随着我国实行放权让利的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地方政府有了独立的目标函数,从而具有与中央政府不同的行为特征。昆山创办自费经济技术开发区便是一个例证。
位于上海与苏州之间的昆山市素有鱼米之乡之称,明末清初的爱国学者顾炎武诞生于此,著名的昆曲、阳澄湖大闸蟹等也出于此。在实行统收统支的传统体制下,昆山政府只拥有很小的资源配置权及不能分享剩余索取权,政府官员的权势、地位、声誉与预算规模有关。地方政府的寻利活动主要不是着眼于创造生产性利润,而是热衷于分割非生产性利润,如怎样就分享更高的预算规模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怎样获得更多的短缺投资品,怎样更容易地完成计划指标等等,既没有动机、也没有能力主动进行制度创新,以至于经济落后的状况一直未得到改善。60年代昆山全市年均工农业总产值仅为1.75亿元,70年代为2.73亿元。改革开放之初,随着普遍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及乡镇的崛起,昆山的经济有了较快的。83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为7.92亿元,人均收入403元。但作为农业县,昆山的基础还相当薄弱,综合经济实力在苏州地区八个县中仅排名第六位。然而从80年代初开始,由于体制因素的重要变化,昆山政府的目标函数、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一是“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使昆山政府具有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江苏省从1977年开始试行财政收支固定比例包干办法,1980年以后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划分收支就是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支范围;分级包干就是按照划分的收支范围,以1979年的收支预计数作为基数,地方收入大于支出的,多余部分按比例上交;支出大于收入的,不足部分由中央从工商税中确定一定比例进行调剂。分成比例和补贴数额确定后,五年不变,在包干期间,地方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后,昆山政府的预算规模就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财政收入规模;二是中央与地方分享财政收入的比例。由于分享比例已预先确定,且一旦确定五年不变,所以昆山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的规模直接与本地社会总产出水平正相关。当地方政府以一预先确定的比例与中央政府分享剩余索取权时,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纵向依赖的行政性组织,也逐渐成为一个追本本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组织。
二是行政性放权使昆山政府拥有了较大的资源配置权,从而具有实现地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我国在改革之初主要是通过行政性放权推进市场取向改革,即权力中心根据决策权的重要性不同,把一部分经过选择的决策权下放到地方或部门,或把一批原来隶属于中央的企业下放到地方(当时,一批在昆山举足轻重的国有企业下放到了地方)。昆山政府在拥有增大了的投资决策权的同时,还要为本地居民提供公共产品、社会福利以及为市场化改革提供必要的其它保障等。
三是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使地方政府有可能凭借经济实力争夺资源,加快本地的经济发展。如随着农村承包制的全面推行和企业扩权试点范围的扩大,国家指令性计划的范围不断缩小;国家调整了工业品的比价关系,实行浮动价格和双轨价格,相当一部分生产资料开始直接进入市场,从而生产性资源的横向流动有了可能等。
随着昆山政府经济利益的独立化,政府行为发生了以下具体变化:(1)由于预算规模与地方财政收入正相关,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发展本地经济的动机和响应获利机会的制度创新动机;(2)由于地方政府相对于个人具有更强的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它为使本地在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中居于有利地位,就力图通过讨价还价促使权力中心作出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或者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行使“退出权”,脱离权力中心的制度安排轨道,公开或隐蔽地从事能导致本地收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活动;(3)当地方政府获得部分剩余索取权后,不仅对下级代理人的监督动机增强了,而且常常利用行政力量增强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和控制或干预市场,如地方保护主义等。
昆山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财政收支基数低,因此在争夺资源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如何吸引资源、加快本地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支已成为昆山政府的当务之急。创立自费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是反映了经济利益独立化后昆山政府试图通过自发的制度创新吸引资源以获取潜在制度收益的强烈动机。 四、非平衡改革战略下的潜在制度收益与地方政府对制度创新进入权的竞争
经济利益独立化后的地方政府具有通过制度创新来营造有利于本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强烈动机,但这种创新需求并不是容易被满足的。因为,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下,权力中心通常依据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与垄断租金最大化双重目标接收和筛选逐级传递上来的制度创新需求信息,选择能平衡以上两大目标的制度创新方案,并通过纵向隶属的行政机构自上而下地实现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受竞争和交易费用的双重约束,权力中心一般偏好于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即就改革的空间来看,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策略;就改革的时间安排来看,从增量改革推进到存量改革。改革的先行者通常可以在承担较小改革成本的条件下获得双重收益,即一是由优惠政策带来的潜在收益;二是由改革先行一步的体制优势带来的潜在制度收益。由于存在进入壁垒,以上双重收益具有“租金”的特征。获得非平衡改革战略下的潜在制度净收益的必要条件是从权力中心那里获得制度创新的优先权或进入权。
显然,微观主体试图直接从权力中心那里争取制度创新权是很困难的,困为它并非是行政系列中纵向配置制度创新权的直接代理人,它只能通过其所从属的上级行政机构向权力中心间接显示其制度创新的需求。在当时的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作为权力中心的行政代理人,既有动机也有能力为谋求对当地经济发展有利的制度安排而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地方政府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争取可获取潜在制度收益的制度创新进入权:一是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渠道向上级传递反映本地利益的制度创新需求,并力图使这一需求转变为权力中心的正式制度供给方案,从而直接获得进入权;二是改革方案一旦形成后,地方政府为获得改革试点权而展开竞争。能否优先获得进入权,既取决于权力中心认同的改革方向,还取决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实力;三是没有获得进入权的地方政府将会通过变通的方式,以能否实现本地利益最大化的标准理解和实施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使实际的制度安排多少有些偏离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从而变相获得部分进入权;四是采取先斩后奏、暗中模仿试点改革等途径突破进入壁垒,争取潜在制度净收益,然后再凭借其经济实力与上级讨价还价,最终争取自发进行的制度创新得到正式的认可。昆山自费经济技术开发区案例显然属于后两种情形。
昆山政府创办自费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在我国非平衡改革战略下努力突破制度创新的进入壁垒,争夺潜在收益的一次成功尝试。1979年我国率先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由于享受了优惠政策与获得了制度创新的特许权,再加上独特的区位优势,这些特区在短期内吸引了国内外大量的资源与优秀人才,经济迅速腾飞。这种改革开放的先行优势诱使各地政府竞相争取这种试点权,以分享这种制度净收益。昆山政府一开始并没有条件争取到这种进入权,从而难以获得优越的投资条件。为了实现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昆山政府设法引入有利于吸引资源、激发微观主体创造出更多生产性利润的制度规则,通过在正式制度规则的边际上突破进入壁垒竞争垄断租金。昆山政府建立自费经济技术开发区。并非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权力中心从昆山政府自发进行的制度创新中获益的增加而逐渐竞争到进入权的。它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到创建自费经济技术开发区。80年代初,为加快本地经济的发展,昆山政府作出了“三个转移”的决策,即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农副工全面发展转移;从产品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移;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移等。当时实施这一战略所面临的障碍是,由于体制与政策没有优势,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很难像深圳那样吸引大量国内外资源。但昆山也有其特殊的区位优势,即它毗邻上海,水陆便利;同时,与上海相比,地价和劳动力价格比较便宜,劳动力的素质较高。特别是在当时,上海的一批设备较旧、污梁较重的工业急于想转移出市区,上海外迁内地的三线企业的一批经营与技术人员急于想回上海但户口又进不了上海。昆山政府利用当时中央鼓励横向联合的有利机遇,针对本地企业规模小、谈判能力弱的现实,由市政府出面,把与上海及上海外迁内地的三线企业横向联合作为突破口,以极富吸引力的投资条件(如让合作企业分享较高的利润,给来昆的上海师傅较高的报酬,解决支边上海籍技术与管理人员及家属的户口指标与住房问题等)来吸引资金与人才。1984年通过横向联合获得投资1.5亿元,建设了14个重点工业项目,工农业总产值首先突破了10亿大关,其中工业产值增幅达35.9%;上海金星电视机厂、金山石化、上海液压泵厂、工业部江西897厂先后落户昆山。
横向联合规模的扩大,使4.25平方公里的老城区难以容纳新的工业项目;另外,分散化的工业布局又不利于创造新的整体优势,所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昆山政府产生了模仿国家兴办沿海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做法,通过建立开发区进一步吸引资源的构想。当时,上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已被列为开放城市,1985年3月长江三角洲被列为沿海开放区,昆山是该开放区的一部分。这使昆山政府有可能突破进入壁垒,并于1985年初在老城区的东侧划出一块土地建立了一个工业区。由于没有国家正式授权,自费创办开发区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特殊的优惠政策,缺乏国家专项启动资金等。昆山政府突破制度创新进入壁垒的主要途径是:1989年昆山引进了江苏省第一家日商独资企业——苏旺你有限公司,随后又吸引了一批外商独资企业(因为外资企业可享受国家统一授予的优惠政策);1989年起在江苏省内率先试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依据国家、法规,向国内外客商有偿出让国家土地使用权,开辟了一条筹措资金、启动开发区运作的重要渠道。双管齐下,使得自费开发区初具规模。
第二阶段:从自费开发区到被列为省重点经济技术开发区。自费开发区创办后,不仅吸引了不少资源,而且带入了市场经济观念、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和技术人才,从而促进了昆山的经济增长。全市工业产值从1984年的7.7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36. 5亿元,取得了隔年翻番的好成绩。江苏省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各地政府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昆山自创立自费开发区后,一方面开发区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 1985年为507万元,到1988年达到了1096万元,上缴省财政收入也逐年增加,省政府具有保护所属政府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昆山政府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能力有了提高。但由于开发区没有得到上级政府的正式批准,从“地下”突破进入壁垒使得在开发区内形成的一套制度规则具有不稳定性,从而无论在招商引资、产权保护还是政策制定方面都遇到诸多不便。于是,为了更大规模地吸引国内外资源,昆山政府开始游说上级政府,力求使自费开发区从“地下” 转入“地上”,获得正式的进入权。为了获得国家的正式认可,首先要获得省政府的批准。经过多轮谈判,江苏省委与省政府于1990年6月把昆山开发区列为省重点经济技术开发区。
自“省批”以后,昆山开发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旨在吸引资源、放水养鱼、提高开发区档次的制度创新活动,突破新的进入壁垒。如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在开发区内兴办外商独资企业(至92年8月底已兴办了79家外资企业);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国有的三山集团、化工厂、制药总厂等先后试行股份制),优化企业治理结构;流通领域的经营、价格、用工和分配实现“四放开”;按“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力争在软环境上与国际惯例接轨等。
第三阶段:从省重点开发区到“国批”经济技术开发区。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全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尤其是上海浦东开发区的迅速崛起,为毗邻上海的昆山开发区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外从1985年到1991年昆山开发区完成工业产值32亿元,实现得税1.88亿元,出口创汇1.35亿美元。尤其是“省批” 后,一批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落户昆山开发区,如日本的丰田、伊藤忠,法国的阿尔卡特,的捷安特自行车、远东机械、正新橡胶等。1990年开发区的财政收入为1166万元,1991年达到2233万元,1992年上升到3101万元,大部分经济指标均超过了当时的许多“国批”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使昆山政府不再满足于“省批”,而希望获得国家的正式授权,开始向特区办申请进入国家级开发区行列。由于昆山开发区每年上缴国家的财政收入已超过了许多国批开发区,而国家并没有为此支付多少成本,同时国家当时希望形成以浦东为龙头的长江中下游经济开放区,所以国务院正式认可了昆山的自费开发行为,并于1992年8月批准昆山的开发区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入“国批”行列后,昆山政府为保持和加强其在与其他国批开发区的竞争中的有利地位,进一步加大了制度创新的力度。如加大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力度;加快内资企业的改革、改组与改造、提高其竞争力(其中三山集团成为江苏首家股票上市公司);完善产权保护的制度规则,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进一步吸引外资;实施外向带动战略,使全市的经济在开发区的带动下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等。
第四阶段:“国批”后对制度创新进入权的竞争。“国批”后,昆山开发区的总量迅速增长。至1995年,开发区累计创办近千家,三资企业总投资21.5 亿美元,累计完成产值194亿元,实现利税9.2亿元,出口创汇8.8亿美元,财政收入4亿元。然而,昆山开发区是从“自费”起家的,不仅开发过程家没有注入资金,而且国务院特区办下发的“批文”还专门注明昆山开发区“不援引其他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即昆山开发区“国批”后仍不能同等享受其他国家级开发区所享受的种种优惠政策。随着昆山开发区的经济实力超过了大部分国字号开发区,昆山政府为获得相应的优惠政策和制度创新进入权而与权力中心展开了新一轮的讨价还价。如要求获得更大的资源配置权;要求上级财政与银行在资金调配上向昆山开发区倾斜;在税收政策上要求适当提高昆山开发区在增值税中的留成比例;争取开发区的建设纳入国家的基础设施总体规划之中等。权力中心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还在继续之中。 五、地方政府自发制度创新的事后追认
变迁一般是指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诺思,中译本,1994)。在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安排中,由于权力中心设置了进入壁垒,获得进入权的试点单位得到的制度收益具有垄断租金的某些特征(杨瑞龙, 1993;1994),所以地方政府竞争进入权的实质就是试图分享这一垄断租金。由地方政府自主实施的制度创新能在多大程度上背离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还要视正式制度规则的变通余地而定。由于正式规则的执行是需要支付成本的,从而在边际上正式规则不起作用。巴塞尔认为,没有绝对的权利,规则总有变通的余地( Barzel,1992)。正是这种制度在边际上的连续的演变导致了制度中正式的也是可见的规则变迁(诺思,中译本,1994)。在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中,由权力中心正式颁布的制度规则的执行成本显然与权威扩散化程度成正比。所谓权威扩散化是指下级政府利用上级授予的权威去做并未授权于它去做的事情(林德布洛姆,中译本, 1992)。显然,行政代理层次越多,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越独立化、讨价还价的能力越强,执行正式规则的成本就越高,提供给地方政府在正式规则的边际上发挥作用的空间就越大。昆山政府正是在权力中心难以支付由以上因素所引起的过高的正式规则执行成本的情况下,通过变通正式规则突破进入壁垒,创办未有权力中心授权设立的自费开发区,追求本地区的经济。
本节感兴趣的问题是:既然昆山政府创立自费开发区并非吻合权力中心的最初制度供给意愿,那么昆山政府是采取什么方式突破进入壁垒的呢?上级政府及权力中心为什么最初会容忍昆山政府突破进入壁垒,乃至最终正式认可它们自发的制度创新活动?解开这一谜底,对于把握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路径不无益处。
1、“先做不说”。
横向经济联合是山自费开发区的“助产士”。在80年代初,昆山若想从上级政府那里正式获得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横向联合的特许权是不可能的。但昆山政府却四面出击,与上海、“三线”企业联合,建成了14个重点项目,为开发区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昆山政府为避开上级政府对进入权的管制,采取的战略是“先做不说”:第一,昆山搞横向联合基本上都不是通过上级政府审批获得合约订立权的,而是通过找“关系”来打通有关“关节”的。这些“关系人”大都是拥有一定实权的昆山籍“老乡”。例如,昆山第一个与上海二纺机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联合生产纺丝机的合作项目是通过当时的上海市经委顾问、昆山人龚兆源的牵线搭桥才办成的;把上海金星电视机厂引到昆山的“媒人”是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昆山人顾明;当重庆汽车厂党委书记、昆山人陈世生回昆探亲时,昆山政府领导拉他参观了几个工厂,最后谈成了合营生产红岩重型载重汽车的项目。由于“牵线人”的特殊身份,大大弱化了跨地区合营中的地方保护主义阻力及上级的“管制” ;第二,采用“文字游戏”,避开当时政策条文的限制。例如,第一个与上海联合生产纺丝机的项目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昆山的上级政府没有权力审批跨省合营项目,上海有关部门又不愿企业跑出上海市。为了获得进入权,1981年12月昆山人在“牵线人”家里秘密磋商、逐字推敲了一份叫做“关于协作建设纺丝机实验工场的协议” 。它用了“协作”,没用“合营”;用“实验”来表示该项目的非正式性或试验性;用“工场”没用“工厂”;用“协议”没用“合同”。在这一文字游戏的保护下,横向联合的审批手续大大简化了;第三,让投资者赚钱,提高联合的成功率。例如,让上海人当合营厂厂长;上海金星电视机厂落户昆山的代价是一次性给技术转让费 15万元,生产每台黑白电视机再给商标费15元;帮助红岩汽车打入上海市场,使得重庆汽车厂下决心来昆山办分厂。
横向经济联合达到一定规模后,昆山政府又“悄悄”地筹建国家不给一分钱的开发区。为了筹集资金,又率先尝试实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为了吸引外资,又“悄悄”地把江苏省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引入昆山开发区。自费开发区的创业阶段都是在“偷偷摸摸”状态下干的,没有引起国家的注意,因此干预较少。
2、“做了再说”。
昆山政府在没有获得国家授权的条件下,悄悄地进行了跨地区横向经济联合,然后又创办了自费开发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昆山政府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各种渠道来“说”自发制度创新所取得的成绩,希望通过制造声势和既成事实来获得上级政府的认同,争取正式的进入权。一是邀请名人来访,由名人之口来“说”成绩。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来昆山考察后,肯定了昆山搞横向联合的做法。他当时题词道: “以上海为依托,发展横向经济联系,促使经济高速度发展。”昆山人用薛暮桥的题词来抵御某些势力对横向经济联合的非议。费孝通于1990年考察了尚未列入正册的昆山开发区后,发表了“开发区的情况很好”的评价,并让新华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考察昆山开发区的消息,产生了较大影响;二是邀请来访,在媒体上宣传昆山自费开发所取得的成就。新华社受邀采访昆山自费开发区后,于1988年7月在《人民日报》刊发了对自费开发区的采访报导,并配发了《“昆山之路”三评》的评论,使得昆山开发区一时间名声大噪;四是在正式的会议上“说”成绩。由于外界的宣传,昆山自费开发区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并引起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注意。 1988年与1989年国务院分别在天津与烟台召开国务院批准的14个开发区会议,昆山作为唯一的“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昆山代表在会上报出的一串数字震惊了国务院主管开发区的领导,为以后被列入“国批”行列埋下了伏笔,这些数字是:昆山自费开发区的工业产值仅次于广州和上海,超过了其他12个国批开发区;两个国批开发区上交国家税金分别是200万元和300万元,昆山却上交了900万元。五是昆山人的自我宣传。昆山的报告文学家杨守松分别于1991年和1995年写了两部《昆山之路》,记述了昆山创立自费开发区的经过,在文学圈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通过别人“说”和“自己”说,为自费开发区列入国家“正册”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3、领导批示或题词,“地下”转入“地上”。
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尽管地方政府可采用“改头换面”、“变通” 等方式从事竞争制度创新进入权的活动,但这种“地下”活动要正式转入“地上” 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环是上级主要领导的赞同。昆山开发区从“省批”到“国批” 的几个重要转折关头都是与昆山政府努力获得上级主要领导的批示或题词有关。
昆山创办开发区尽管没有对外声张,但风声还是传到省里去了。1986年秋,当时的省委书记韩培信来昆山视察,听取了自费开发区的汇报并实地考察自费开发区,称赞开发区的总体构想不错。回南京后,韩培信书记在省委常委会上赞扬了昆山自费开发区所取得的成绩。随后,省委副书记、省长等都先后到昆山看了开发区。在当年的省人代会上,顾秀莲省长在省政府工作报告中还专门提到了昆山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省委书记的昆山之行是自费开发区从“地下”走向公开的转折点。昆山政府抓住这个好时机,不仅从省里获得了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特殊政策,还立即打征用土地的报告到省里,在原有开发区3.75平方公里的基础上扩大到6.18平方公里。1986年冬,当时的总理在上海市委书记的陪同下来到昆山考察,并把昆山工业小区改名为“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就在这一年,昆山开发区的名声开始传到北京,并为获得“省批”开了个好头。
从“省批”到“国批”也与领导批示有关。在昆山申请国家级开发区的关键时候,李鹏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沿江经济发展战略”会议上的讲话显著加重了申报成功的法码,他说,今后搞开发区,要像昆山那样,先行自费开发,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国家进行验收,然后再戴“帽”升级。随后不久,邹家华副总理到昆山为沪宁高速公路奠基剪彩时,昆山市委书记不失时机地请邹家华副总理写下了“加快开放步伐,搞好开发区建设”的题词;省长陈焕友还请副总理特地写上“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题”。这等于承认了昆山开发区的“合法”性,为获得“国批”创造了条件。
4、“先养儿子,再领结婚证”。
昆山自费开发区一开始是个“私生子”,开发区内的制度创新活动尽管受到了名人和领导的赞许,但并未受到正式制度规则保护,因而不利于更大规模的招商引资。自被批准为省级开发区后,昆山政府与江苏省政府在发展开发区上有更多的一致利益(因开发区上交省财政的数额逐年增加),于是在省政府的协助下,昆山政府努力使开发区由江苏省“地方粮票”变成全国“通用粮票”。首先,昆山政府于 1988年通过省财政厅做了财政部预算司的工作,在昆山每年上交国家财政中照顾 500万元作为国家对昆山开发区的支持;然后于1992年在陈焕友省长的支持下,由省政府正式发红头文件向国务院特区办申请国家级开发区的批文。昆山政府派一名副市长常驻北京,疏通关系,反馈信息,催办“结婚证”;最后有了李鹏总理的“ 戴帽升级”的讲话与邹家华的题词,李鹏总理在申报文件上批了“同意”两字。至此,“私生子”终于报上了户口,申办国家级开发区取得了成功。
昆山政府取得申办国家级开发区的成功并没有给昆山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因为批件上明确写明昆山开发区不享受其他14个国批开发区所享受的特殊政策(即自费开发的原则不变)。昆山政府之所以竭尽全力获得这张“结婚证书”,是因为它使自费开发由非法变为合法,由另册变为正册,从而使昆山悄悄地创立的开发区及在开发区内自主进行的制度创新行为正式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和保护。这种突破进入壁垒的自发制度创新的事后追认制,不仅有效地保护了新产权形式,增强昆山政府与上级讨价还价及继续突破制度创新的进入壁垒的能力。而且大大缓解了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诺思悖论”,加速了市场化进程。 六、制度安排的谈判协调与中间扩散
昆山不经权力中心的直接授权创办了开发区,且在开发区内引入的制度规则并不与权力中心当时的初始制度供给意愿相一致,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权力中心从最初容忍到最后正式追认地方政府的自发制度创新活动?为什么这种中间扩散的制度变迁方式有可能加速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这些正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
第一,在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方式因面临竞争和交易费用约束而难以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时,由地方政府扮演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角色,可大大弱化政府在保护有效率产权结构时所陷入的“诺思悖论”,从而能加快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当地方政府经济利益独立化后,由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分享比例一定,不仅地方政府追求可支配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依赖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而且政府的垄断租金最大化目标(主要表现为职位的升迁、权力的稳定性、对资源的支配力及灰色收入等)的实现也与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本地经济上不去就会丢官),这又依赖于企业的扩张和效率的提高。所以,这就大大弱化了可导致地方政府垄断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的冲突,即地方政府在界定和保护产权时更偏重于效率。从企业的角度来分析,由于单个企业谈判实力的弱小等原因,它没有能力通过突破进入壁垒来获得潜在制度收益,而必须借助本地政府的力量在不规范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因此,地方政府与企业在自发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合作多于冲突,它走的是一条政府与企业合作共同与权力中心讨价还价突破进入壁垒的道路。如在企业的跨地区横向联合中,昆山政府扮演了选对象、送聘礼、定婚约的角色;在自费开发的初创阶段(完成开发区内的“七通一平),当地企业提供了财力与人力的支持,政府给予出力企业以优惠的条件优先进入开发区的待遇;地方政府是开发区招商引资的主角,又是开发区的管理者,就连外商都与本地政府官员建立了密切的公务和私人联系。
第二,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效率导向。昆山政府为了在与其他地方政府的竞争中吸引更多的资源,这表现在它具有构建一个相对有效率产权结构的动机,期望通过明确微观主体的收益预期激励其创造更多的生产性利润,从而扩大地方政府的剩余分享额。昆山政府在筹建开发区之初,由于既不享有特区及国批开发区的特殊优惠政策,中央也没有专项的资金投入,本地的财政收入留成额又少,从而选择了通过在开发区营造有效率体制来吸引外商独资企业的战略。昆山政府当时算过一笔合资帐,如果每年引进4亿美元,本地投资额平均占25%的话,一年就要1亿美元,按 1992年汇率约需10亿元人民币配套资金。昆山1993年的全年财政收入仅3亿元,即使老城区不改造,财政不上交,全部投到开发区,投资比例也不足25%,而且即使占25%,在合资企业中也没有多少发言权。因此从效率角度考察,最合算的选择就是多建独资企业。为了吸引外商独资企业,开发区在制度创新上大做文章,如实现国有土地的有偿使用原则,筹集实现开发区内“七通一平”的资金;对产权实现有效的保护,明确外商的投资收益预期;开放市场;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体制,优化对外资企业的服务体系等。自昆山在1989年引进了江苏省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以来,至1995年底,开发区已引进了173家外商独资企业,总投资约12亿美元,占三资企业的55.6%。投资环境的优化使昆山的三资企业规模、出口量及技术含量在江苏省独占鳌头。
第三,权力中心在多大程度上能容忍乃至追认地方政府在正式规则之边际上的制度创新行为,一方面与权威扩散化程度有关。一般来说,权威扩散化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利益目标越独立、越有可能利用上级政府授予的权威去做并未授权于它去做的事情。正式制度规则的变通余地越大;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在地方政府为追求潜在制度收益而逐渐改变的制度结构中,权力中心从中获得的收益是否大于执行正式规则的成本。当权力中心为保护旧的产权结构的成本大于其从新产权关系中获得的收益时,就会容忍地方政府为追求更多的生产性利润所从事的制度创新活动,从而使权力中心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新产权之间达成一致。昆山开发区的创建并没有依赖国家的资金投入,但财政收入则从1985年的507万元上升到1995年的13000万元,上缴国家的财政收入逐年增长,仅1995年三资企业的上缴税金就达9000万元,从而为最终由自费开发区变为国批开发区提供了可能。这一案例验证了所谓的“无名氏”定理,即当统治者发现给予臣民们更多的自由可以分享由更多的自由所激励出的更多财富,并且分给统治者的增加了的财富可以抵销统治者放弃独裁所增加的不安全感时,臣民的自由便会经双方约定而增加(Barzel,1992;汪丁丁,1995)。
第四,当制度变迁由命令控制转变为谈判协调时,地方政府在我国向市场体制过渡过程中事实上起到了中间扩散新制度规则的功能,即一方面地方政府从本地经济的目标出发,通过从下接收信息、向上传递信息沟通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效率导向的制度创新活动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例如,昆山实施发展外商独资和合资的战略不仅吸引一大批国际著名财团和跨国公司前来投资,而且带动了开发区内外的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并对政府管理部门、服务行业按市场原则办事,对市场本系的培育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与外资企业的合作与竞争中,内资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步伐明显加快,产权明晰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内资企业在与外商合资合作及为外资名牌产品配套中提高了产品技术挡次和经济效益;通过转卖租赁等形式盘活了内资企业的存量资产等。 七、结论性评论
通过对昆山自费开发区案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简短的结论。
第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及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推行,使拥有相当大资源配置权力的地方政府可分享剩余索取权。由于分享比例已预先确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留成额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所以地方政府已不再是纯粹提供公共产品的行政性组织,它实际上已同时成为一个追求本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组织,其行为已经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倾向。即使实行了分税制,也没改变这一基本格局。因为“小型”集团的成员具有较强的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奥尔森,中译本,1993),从而越是处于下层的地方政府,其经济功能越强,行为越是市场化。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县、乡级政府已类似于一个集团公司总部的原因。
第二,具有以上特征的地方政府不仅成为沟通微观主体制度创新需求与权力中心制度供给意愿的桥梁,而且可凭借权力中心的行政代理人身份,从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的角度去理解与实施正式制度规则;或者通过讨价还价诱使权力中心作出有利于其分享垄断租金的制度安排,竞争制度创新的进入权;或者在正式规则的边际上进行自发的制度创新活动,突破“进入壁垒”。地方政府以行政手段实施的市场化行为既有助于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之迷,也有助于解释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为什么有可能实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
第三,解开制度变迁中“诺思悖论”的可能性主要不是依赖于单个行为人的自由选择,而在于超越个体水平的集体行动,实施这一集体行动的主体是组织。当地方政府扮演体制转换中的“第一行动集团”角色时,这种具有效率导向性质的制度创新既可能导致有效率的产权结构,又可能使权力中心从新产权结构中的获益超过保护旧产权关系的成本。于是,权力中心就会采取容忍乃至事后追认的态度,从而通过重组新合约使权力中心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新产权之间达成一致,逐步化解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诺思悖论”。
第四,地方政府的效率导向制度创新有助于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追求,企业在非平衡改革战略中追逐潜在制度收益又依赖于借助政府的一臂之力,因此,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多于冲突。可见自发的制度创新走的是一条地方政府与企业联合突破由权力中心设置的进入壁垒的道路。
第五,由地方政府扮演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角色也可能产生若干负效应。如地方政府在界定和保护产权时也不同程度地面临分利集团内的“诺思悖论”,从而使市场化改革具有不彻底性;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所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与国家利益的受损;容易滋生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等。因此,为了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客观上要求由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向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的转变。
第六,制度创新的“中间扩散”有可能实现这种制度变迁方式的转变。地方政府为刺激本地经济发展所从事的效率导向的制度创新活动有可能导致一个相对有效率的产权结构,有助于培育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而产权关系明晰化又会反过来限制政府的干预行为,使之主要提供公共产品。改革先行地区大多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管理体制正是这种趋势的反映。由此可见,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经济功能及制度创新功能呈现出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的“例U型”的变化态势。
总之,一个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国家有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渐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
(注)本课题的研究得到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资助;在调研中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宣炳龙先生及昆山市委政策研究室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张曙光教授、盛洪博士、张宇燕博士对本文的初稿提出了很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主要:
1、道格拉斯.C. 诺思,199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
2、道格拉斯.C. 诺思,1994,《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
3、Davis, Lance and North, Douglass. C. 1971, Institutional change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4、周其仁,1994,《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中国社会季刊》夏季号。
5、曼瑟尔.奥尔森,1995,《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6、曼瑟尔.奥尔森,1993,《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7、汪丁丁,1995,《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
8、林毅夫,蔡方,李周,1993,《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经济研究》,第9期。
9、杨瑞龙,1993,《论制度供给》,《经济研究》,第8期。
10、杨瑞龙,1994,《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济研究》,第5期。
11、Niskanen, W., 1978, "Non-market. Decision Making: the Reculiar Economics of Bureaucra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8, P.293.
12、Barzel, Y., 1992,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State",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127,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3、查尔斯.林德布洛姆,1992,《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 对杨瑞龙教授《“中间扩散”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江苏昆山自费经济技术开发区案例分析》一文的评论
上一篇:民主制度的言论限制
下一篇:从中国文化的认识到民主制度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