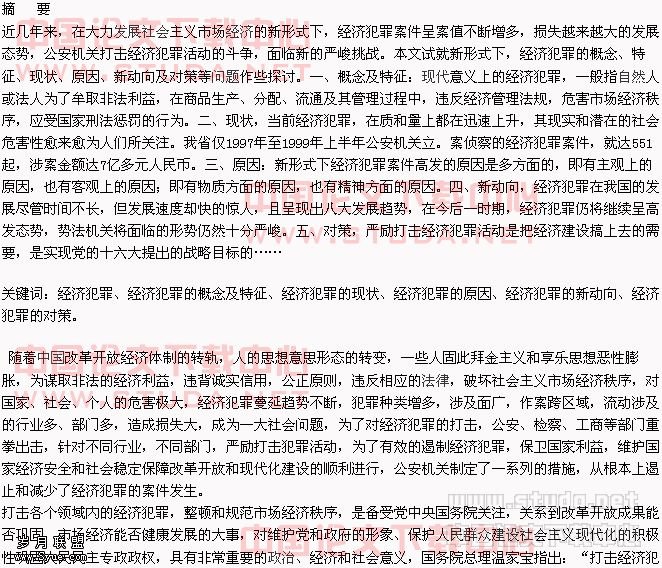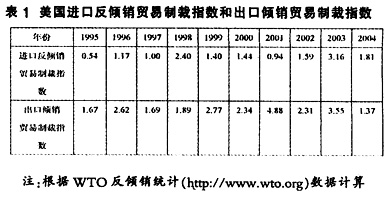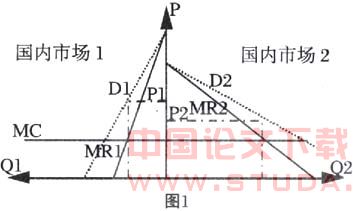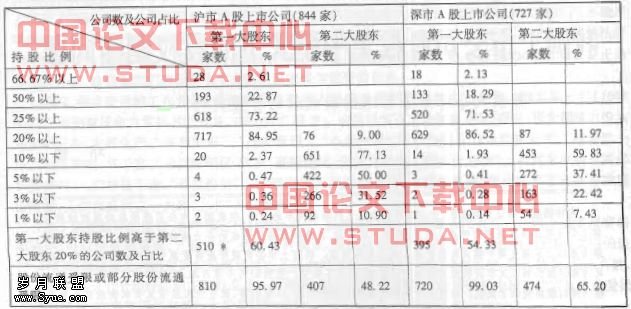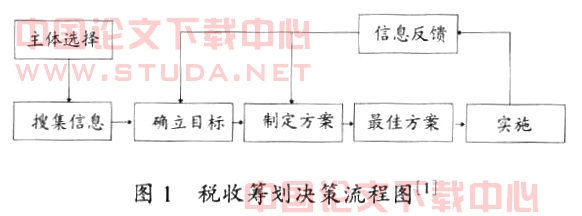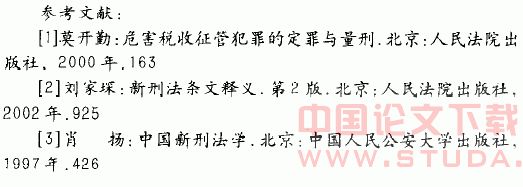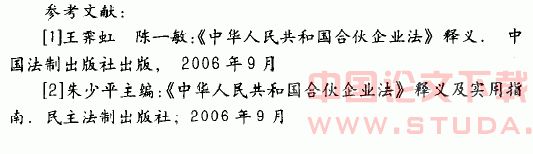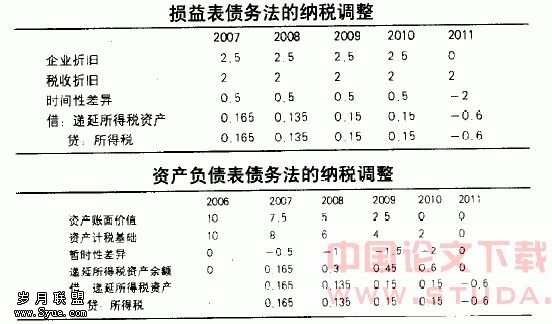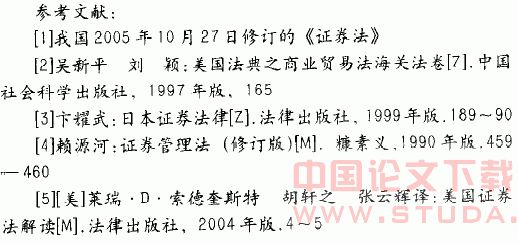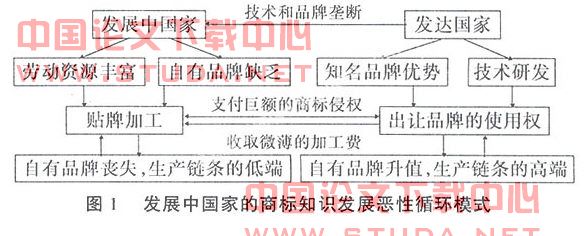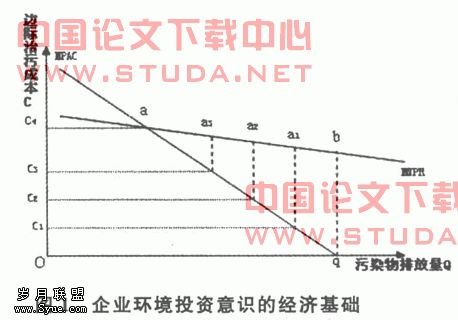论转租中对第三人的保护
摘要:世界各国关于转租有放任主义、限制主义和区别主义三种立法模式,在这三种模式下,当承租人违约时,一般赋予了次承租人的违约责任救济权,我国《合同法》第224条虽采限制主义立法模式,但在自行转租的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转租合同在承租人事后没取得处分权或没有得到出租人追认的应属无效,剥夺了次承租人的违约责任救济权。即使大多国家在承租人违约的情况下赋予了次承租人的违约责任救济权,但由于传统民法视租赁权本质上为一种债权,在承租人违约时次承租人不能以其租赁权对抗出租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因此对次承租人保护也为不力和公平。租赁权实质上是用益物权,这样承租人和次承租人合法取得的租赁权将获得物权法的保护。
关键词:转租、转租合同、类推适用、租赁权、用益物权
一、转租制度的立法模式及其对第三人的保护
转租为承租人不脱离租赁关关系,而将租赁物转租于次承租人之谓。转租中的次承租人即本文标题所指的第三人,一般而言,转租在房屋之租赁上最为常见,俗称所谓“二房东”,即指转租人而言。由于租赁物的使用收益关乎出租人的直接利益,近世民法就租赁物能否自由转租的问题上,形成了放任主义、限制主义和区别主义三种基本立法模式。作为转租关系中现实占有租赁物而为使用收益的次承租人往往是上的弱者,在其无过错的情形下,尤有保护的必要,因此,我们考察三种模式对于作为第三人的次承租人的保护,主要在承租人违约的情况下。
(一)三种模式下承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合同效力问题
法国、奥地利等国民法采放任主义立法模式,认为转租乃承租人的权利,如无相反约定,承租人可以转租。《法国民法典》第1717条第1款规定:“承租人有转租的权利,但租赁契约有禁止约定者,不在此限。”依《奥地利民法典》,如对于所有人无害或者契约上未明示地加以禁止的,承租人有转租权,因此,在放任主义模式下,如无相反约定,转租乃承租人的权利,因此承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的合同应为有效,当承租人违约时,次承租人可追究其违约责任而寻求救济。
德国、日本等国民法采限制主义立法模式,即规定非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不得转租。《德国民法典》第549条第1项规定:“承租人非经出租人允许,不得将租赁物转让于第三人使用,特别是不得将该物转租于他人。”《日本民法典》第612条第1项规定:“承租人非有出租人的承诺,不得将其权利转让,或将租赁物转租。”在此模式下,承租人在经出租人同意的转租行为就是合法行为,其后果与放任主义立法模式下,承租人在无禁止性约定下自行转租的法律后果相当,当承租人非经出租人同意而自行转租时,依此模式,次承租人将不能取得租赁权,但值得探讨的是承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的转租合同效力问题,德国及日本民法均无明文规定,但依德国民法法理而言,其把法律行为区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是当事人之间设定权利义务关系行为,通常表现为债权债务契约,一般情形,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即告成立,而处分行为是直接引起权利变动的行为,其成立须以有处分权为必要,按德国民法对租赁合同下的定义分析,租赁合同自属负担行为,转租合同自可类推适用,不论出租人是否同意,承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的转租合同应属有效。而日本实行的是同一原则,不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未经出租人同意的自行转租其转租合同效力又将何如呢?按《日本民法典》601条对租赁所下定义来看,其认为租赁合同的本质也是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一种债权债务契约,这与买卖契约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是契约所涉内容不同罢了,事实上,在未经出租人同意的自行转租,属于广义上的无权处分行为,可类推适用日本民法关于无权处分他人之物的合同效力问题,从《日本民法典》第561条和562条规定来看,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出卖人应负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显然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合同仍然是有效的,据此,笔者以为,自行转租的转租合同应属有效。因此,限制主义模式下,当承租人违约时,次承租人也可基于违约责任寻求救济。
意大利及我国地区“民法”采取区别主义立法模式,即区别不同情况或放任或限制转租。《意大利民法典》第1594条规定:“除有相反的约款,承租人有将承租物让渡他人的转租权,但未经出租人的同意不得转卖契约,涉及动产物时,转租应当由出租人授权或者与惯例相符。”我国台湾“民法”第443条第1项规定:“承租人非经出租人之承诺,不得将租赁物转租于他人,但租赁物为房屋者,除另有相反约定外,承租人得将其一部转租于他人。”区别主义立法模式下的不须要出租人承诺的转租合同与前述放任主义模式下的转租合同效力相同,次承租人的利害关系状态也相当。而未经出租人同意的自行转租其转租合同的效力问题,就我国台湾地区而言,其和德国一样,也把法律行为区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转租合同属于负担行为,应属有效。未经出租人承诺之转租契约,发生债权的效力。「1」而意大利也采同一原则,但其对租赁合同的本质把握与日本等国也是一致的,同时根据《意大利民法典》第1478条规定,关于无权处分他人之物的合同效力,其规定为有效的,类推适用,非经出租人同意的转租全同也应属有效,自不待言。因此,限制主义模式下,无论何种情形,转租合同应属有效,承租人违约时,次承租人可追究其违约责任。
我国《合同法》第224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让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由是观之,我国对转租采限制主义态度,经出租人同意的转租合同应属有效。未经出租人同意的自行转租,其转租合同效力何如呢?按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则产,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有学者认为我国法律上的无权处分制度中所说的处分主要指指广义的处分概念,即处分人在没有获得处分权情况下,作出各种法律上的处分行为,不包括事实上处分,这里的处分指各种处分财产,能够导致权利的设定和移转的行为。「2」民法不承认物权行为与物权合意,合同的立法者有意把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合成一个法律行为,故合同法上的合同概念仅指债权合同,「3」因此,无权处分合同中无权处分人事后没有取得处分权或没有得到权利人追认的,该债权合同无效。承租人未经出租人的同意而将租赁物非法转租给他人,也构成无权处分,因为,对于转租而言,虽然承租人擅自转让的只是占有权,使用权,不是转让他人的财产,但承租人擅自将其占有权、使用权转让他人,实际上是非法处分他人财产所有权能的行为,「4」故非法转租和无权处分相类似,且《合同法》第51条属于总则编的规定,而租赁合同属于分则规定,《合同法》第51条自应适用于租赁合同,照此理解的话,未经出租人同意的转租合同应属效力待定,当承租人事后没取得处分权或没有得到出租人追认的,自行转租合同应属无效,「5」次承租人不能追究承租人的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形下,次承租人可追究承租人的缔约过失责任,但该责任的救济内容主要是赔偿信赖利益的损失,其救济远不如违约责任救济有力。但《合同法》第228条又规定:“因第三人主张权利,致使承租人不能对租赁物使用,收益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从该条规定来看,因第三人主张权利,租赁合同仍然有效,出租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该规定自可类推适用于转租合同,在非法转租时,出租人终止租赁契约而向次承租人主张权利时,次承租人可追究承租人的违约责任,但违约责任以有效合同为前提,然根据《合同法》第51条,未经出租人同意的转租合同属效力待定,这样就出现了矛盾。因此,笔者也主张我国民法应采纳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即区分原则,并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这次由梁慧星先生负责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的第6条、第7条得到了反映。
综上,在采放任主义、限制主义及区别主义的国家及地区,无论出租人是否同意,转租合同都是有效的,当承租人违约时,次承租人可对承租人主张违约责任,得到债法上的保护。然我国虽采限制主义模式,但就合同法相关规定来看,当承租人非经出租人同意的转租合同在承租人事后没取得处分权或没有得到出租人追认的应属无效,此时,次承租人将遭受更大的损害,因其还不能向承租人主张违约损害赔偿,严重损害了交易安全。
(二)违约责任对次承租人保护是否公平、有力
一般情形下,无论采放任、限制或区别主义模式,转租合同都是有效的,次承租人可向承租人主张违约责任,而得以保护,但这种债法上的保护对次承租人有力、公平吗?特别是在次承租人善意而无过错的情况下。设出租人把租赁物出租给承租人,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再行转租给次承租人,这样在转租关系中存在两个合同,即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的出租合同,承租人和次承租人之间的转租合同。当承租人违约时,出租人终止其与承租人的合同关系时,那么承租人将丧失租赁权,此时,承租人和次承租人之间的转租合同关系作何处理呢?一般认为,次承租人的租赁权,成立于转租人租赁权之上,转租人之租赁权消灭,则次承租人之租赁权失其基础,不得对于出租人为主张,从而出租人与承租人之租赁关系,因租期之届满或因承租人债务不履行经出租人终止租赁契约而消灭时,则次承租人对出租人不得主张租赁权之存续,又出租人与承租人之租赁关系终止,而承租人和次承租之间转租关系,并不当然消灭。「6」然事实上,当租赁合同失效时,转租合同也会因承租人债务履行不能而为次承租人解除,从而转租合同也将失去效力(向将来失效,不溯及既往)。另外,当出租人违约时,承租人也可以解除租赁合同,但在转租中,承租人主张解除合同多半是因次承租人主张违约而引起的,无论哪种情形,当合同无效时,自然发生所有物返还之结果,传统民法认为,租赁权本质上是一种债权,故次承租人自不得以租赁权对抗出租人基于所有权的返还请求权。虽然,近世民法为保护承租人动辄因租赁物上物权之变更而影响承租人之地位特设有买卖不破租赁,以及出租人就租赁物设定限制物权时不得影响承租人租赁权之行使,但在转租中,是不适用这种情形的,「7」基于这样的认识,当承租人违约时,出租人解除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后,出租人得迳向次承租人请求返还其租赁物,而次承租人只能基于违约责任向承租人主张赔偿。「8」但这显然对次承租人是不公平的,物别是当转租合同还未到期的情况下(一般认为,转租合期限不能超出原租赁合同期限)。因为承租人是否违约,次承租人是无法预见和控制的,如此,次承租人的法律地位将与承租人是否违约而紧密相连,其法律地位将极不稳定。就一般法理而言,同一标的物上并存物权和债权时,债权是不能对抗物权的,出租人向次承租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于法有据,就法所追求的更高理念而言,在次承租人已经向承租人履行了合同义务后,因承租人的违约而导致租赁合同终止后,而毫无过错的次承租人将承担此不测之损害,有违法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要求。从事实层面来看,转租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目前许多写字楼、店铺、商场都是以转租的形式进行使用的,而诸如商场、店铺等往往涉及价格高昂的装修费用,广告费用等,尤其当承租人拖欠很小一部分租金额,而次承租人生意又正是兴隆之时,出租人解除合同,在这种情况下,片面保护出租人的利益有失公允,虽然次承租人也可基于违约责任向承租人追讨,但次承租人对租赁物已不能保有占有、使用、收益之权能,同时,既然承租人既拖欠租金,足见其支付能力有问题,这样次承租人的索赔风险也是极大的。另外,承租人有可能因其它原因收到次承租人的高额租金后即逃之夭夭,也未曾鲜有,这样次承租人将遭受更大的索赔风险。
近世民法所要保护的安全分为静的安全和动的安全,在转租关系中,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所有利益,属于静态的安全,次承租人作为现实占有租赁物而为使用收益之人,其为交易中的受让人,享有交易上的利益,属于动态的安全利益,民法的价值取向是从侧重保护静态安全走向侧重保护动态交易安全,因此基于利益衡量,笔者认为,当租赁合同失效后,而次承租人又为善意的情形下,法律应更注重保护次承租人的利益。然而世界大多国家规定,当承租人违约,出租人终止租赁契约时,一般赋予了次承租人对承租人的违约责任救济权,但由于租赁权本质上是一种债权,其不能对抗租赁物真正所有人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因此,对次承租人的保护也为不力。
二、对租赁权性质的再认识
1、债权说:认为租赁权无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与罗马法上“买卖不破租赁”的思想一致,这种学说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对承租人照顾不周全,现为大多国家立法所不采。
2、物权化说:认为租赁权的性质为债权,但是为保护承租人的利益,强化其效力,从而使其具有物权化趋势,表现在:①对抗力,近世民法采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即租赁关系存续中,承租人对于取得租赁物所有权或其他物权之人,亦得主张其租赁权,即所谓对抗力,②对侵害租赁权之第三人的效力,承租人基于其占有权当然可以对第三人的侵害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妨害排除请求权,但若单纯基于其租赁权,承租人能否行使这两项权利?租赁权作为一种权利,在受到侵害时,请求损害赔偿是可以的,同时学说及判例的态度也总体上承认了基于租赁权的妨害排除请求权,③租赁权处分可能性,即租赁权的让与和转租的可能性。对于租赁权之处分本不允许,然只要使出租人之租金收入,确有保障,则承租人为谁,无关重要,因而依其情形,对于租赁权之处分可能性渐予承认,④租赁权之永续性,一般言之,债权的存续时间较短,物权的存续时间较长,而租赁权多为长期存续。「9」租赁权的物权化说为许多国家立法所采。
晚近以来,不仅物权有债权化之趋势,债权亦有物权化之现象,租赁权之物权化即其著例。「10」由上观之,租赁权的物权化趋势大为扩张,几和物权相类似,其扩张性已非债权框框所能约束,租赁权的物权化在保护一般租赁关系中承租人的利益还能发挥其积极作用,但在转租中,其保护力度就相形见绌,为了强化对次承租人的保护,不如突破租赁权的物权化而直接承认租赁权为物权。上,日耳曼法就是将租赁权列入“物权”之范畴的,又普鲁士国民法规定租赁权为物权,奥地利民法典也认为租赁权于登记后为物权,参见该国民法典第1095条之规定。「11」德国法儒基尔克注重租赁关系之内面实质构造,意将租赁权从本质上变为物权的构成,接着1930年代雷宁(Lehning)分析租赁关系之性格,发表内部的论理构造上,具备完备物权性格之学说。「12」
物权为支配权,是绝对权,债权为请求权,是相对权,这是传统民法区分物权与债权的基本法则。租赁合同与租赁权的取得实际上是两个法律行为,各国关于租赁合同的本质认识是一致的,即是当事人一方约定以某物供相对人使用及收益,相对人约定支付租金的契约,租赁契约本质是在当事人之间设定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因双方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即告成立,这是一种典型的负担行为,其仅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承租人仅得向出租人要求移转其租赁物,并保证其使用及收益,但它并不直接引起租赁物权利之变动。事实上,承租人要取得租赁权,须以租赁物的交付为必要条件,而交付作为一种公示方法,是处分行为的标志,设定一个负提行为(债权债务契约)是不须要公示的。物权本质上是直接支配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之权利,物权的排他性,乃因对物直接支配所使然。「13」从租赁权内容来看,承租人得直接对于租赁物使用及收益,其性质,系直接管领租赁物之权利,并非仅对于出租人请求交由使用收益之权利,与债权显有不同,因请求他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之权利,始为债权,而租赁权乃占有租赁物而为使用收益,要达此目的,须以租赁物之支配为必要,而此支配权实为租赁权之本体。租赁权也具有排他效力,同一租赁物上,不得同时并存两个租赁权。
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人对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权利,用益物权和租赁权都体现了以“利用”为中心的物权观念。我们比较一下用益物权和租赁权:
①从内容来看,二者都是对他人之物的占有、使用及收益。
②用益物权之享有和行使以物之占有为前提,显然,租赁权的享有和行使也须以物之占有为前提。
③有益物权主要以不动产为标的物,但参各国立法例,也不否认动产上可成立用益物权,租赁权的标的也包括不动产和动产。
④就用益物权与租赁权的取得观之,其产生前提都须有一个债权契约,以永佃权为例,其通常基于与地主订立的永佃契约而取得,而租赁权产生的前提是租赁合同的签订,租赁权是租赁合同履行的结果。
⑤在采物权变动形式主义的国家例,动产用益物权的变动须以交付为要件,这和动产租赁权的取得应该没有什么不同,但在不动产上二者有区分,按《德国民法典》第1031条规定,不动产用益权的设立,必须有当事人关于设立该权利的合意,以及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的登记。按我国“民法”规定,地上权为物权,其得丧变更,由于法律行为者,非经登记不生效力,且应以书面为之。土地租赁权为债权,则无须登记,无须以书面为之。「14」但就不动产用益物权和不动产租赁权的核心来看,二者皆为对不动产进行使用、收益,这种支配性效力并没有不同。笔者以为,在采物权变动形式主义的立法例的国家,如若要强化对承租人的保护,须以不动产租赁权的取得以登记为要件,不动产租赁权的取得若不登记的话,承租人将遭受不测损害,因为根据登记簿的公信力,善意第三人将取得不存在租赁权的不动产标的物,即使未登记的不动产租赁权设定在先,这样就出现了“买卖打破租赁”的现象。如果不动产租赁权已登记,即推定买受人应当知道此负担的存在,其后设定的物权不得对抗在先的租赁权,已登记的不动产租赁权就产生了排他性和优先性,这显然不是债权所产生的结果。基于此,笔者认为,采物权变动形式主义的国家,不动产租赁权的取得也须登记,如不登记,将产生法理及实践上的冲突。而在采物权变动意思主义立法例的国家,以日本为例,其用益物权的标的物限于不动产,《日本民法典》第177条和第178条规定,物权变动,非经登记或交付,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同时该法典第605条规定,不动产租赁实行登记后,对以后就该不动产取得物权者,亦发生效力。即土地租赁经登记后,得对抗新所有人。其地上权与土地租赁权在成立要件和对抗效力是几无差别。在日本,基地租赁权与地上权二者合而为一,同视为借地权而予以物权化。「15」
由上观之,租赁权和用益物权几无差别,租赁权因它在理论上是基于租赁契约而产生,租赁权一直被认为是债权,然因契约产生的不一定只是债权,事实上他物权的产生大多依据契约,地上权、永佃权即是其例。自罗马法将租赁权列入债权以来,大陆法系多数国家立法从之,而将其规入债编,「16」虽然这些国家为保护承租人的利益,强化了租赁权的物权化,但视租赁权本质上是一种债权的观点并未改变。近世以来,“物权法定”原则有逐渐缓和趋势,德国民法学界近来已对“物权法定”这个原则有无维持必要展开热烈讨论。私法自治作为传统民法的指导原则,民法应为自治法,自治法追求的是对等的公平,物权法定确实是自治的重大例外,而它的合理性只能建立于交易成本和交易安全的考虑,「17」而通过立法承认租赁权是一种物权,完全利于交易效率及公平。
三、承认租赁权为一种用益物权及其在保护交易中的运用用益物权作为物权,权利人不仅可以依用益物权限定范围支配标的,而且有权对抗包括所有权人在内的任何人对其权利行使的干涉。用益物权的设定使物的利用关系物权化,巩固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得对抗第三人,此为用益物权在法律结构上异于债权的特色。「18」这就使得在非所有人对他人之物的利用方面,用益物权制度具有债权制度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而传统民法上,租赁权本质上因为采取债权的构成故并未能完全抑制出租人之解约权。如视租赁权为一种用益物权后,在承租人取得租赁权后,其理所当然的获得物权保护,而不必仰出租人之鼻息,受其左右,更不必用“买卖不破租赁”来予以保护。用益物权主要包括占有、使用、收益三种权能,其处分权能受到真正所有权人的限制,在转租中,如若经出租人同意的转租,那么,承租人对租赁物就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不完全,这里指转租权)四种权能,出租人同意补正了承租人的处分权能,因此,经出租人同意的转租行为非属无权处分,次承租人继而取得的租赁权在移转占有后也受物权保护,可以对抗所有人和不特定第三人,因此,即使承租人违约,出租人解除与承租人合同关系后,次承租人的租赁权在转租合同约定期限内基于合法占有权仍受保护,因为定限物权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对抗所有权人。在非法转租中,出租人未同意承租人的转租情形下,则承租人的处分权(转租权)将受到限制,其转租行为将是无权处分,当然转租合同仍属有效,次承租人能否获得租赁权,因其是善意或恶意面有别。在不动产转租中,善意要求次承租人不知即可,即不知承租人无转租权,当然前已述及不动产租赁需办理登记,因此,此时的次承租人需尽查阅登记备案的义务,而登记备案中往往涉及该租赁物能否自由转租的规定,如不尽此义务,不能称善意,将面临租赁物被出租人追夺的危险,从而不能取得不动产租赁权。而在动产租赁中,以交付为公示方法,因此占有动产租赁物的人推定是合法出租人,次承租人信赖此占有者,即为善意,将取得该动产的租赁权,在合同约定期内并能对抗出租人。如若次承租人知道承租人没有转租权而仍以之签订转租合同,将不能取得租赁权。
注 释:
[1][6] 史尚宽:《债法各论》,台湾荣泰印书馆,1981年版,第177页、176-177页。
[2][4] 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8页、609页。
[3][17] 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87页、93页。
[5] 王利明先生认为,这种情况下无权处分行为规定应为有效(根据《合同法》第228条),虽与《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存在着矛盾,但是按照“特别规定优先普通规定”的原则,应适用合同法分则的规定,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9页。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合同法》第51条属于总则的规定,依法理而言,总则自应统率分则。同时其所持的“特别规定优先普通规定”的解释,只是在适用法条上作出了价值选择,但其并不能消除《合同法》第51条和第228条的内在逻辑冲突。
[7] 若在转租中可类推适用买卖不破租赁规则,但似乎限于这种情形:当出租人将租赁物出卖给转租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时,租赁合同基于买卖不破租赁原理而效力不变,转租合同的效力因基础合同关系没有发生变化而不受影响,次承租人得依有效的转租合同抗辩租赁物所有权的继受人。
[8] 在未经出租人同意的非法转租中,若出租人已对承租人终止契约时,自得基于所有权,迳向次承租人请求返还其租赁物。参见,郑玉波:《民法债编各论》(上册),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250页。又依日本判例及德国学说,在未经出租人承诺之转租中,此时次承租人不得以其租赁权对抗出租人,出租人可不终止出租人与承租人之租赁契约关系,得以所有权为理由,对于次承租人为妨害除去之请求。参见,史尚宽:《债法各论》,台湾荣泰印书馆1981年版,第178页。
[9] 郑玉波:《民法债编各论》(上册),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201-202页。
[10] 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11] 戴修瓒:《民法债编各论》,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120页。
[12][15] 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144页。
[13][14]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5页、353页。
[16] 如德国民法典535条,日本民法典601条,意大利民法典1571条。
[18]王泽鉴:《民法物权(用益物权?占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