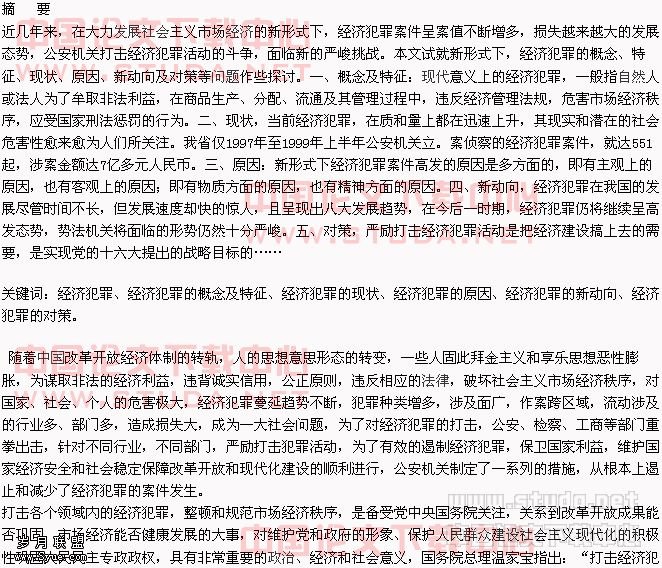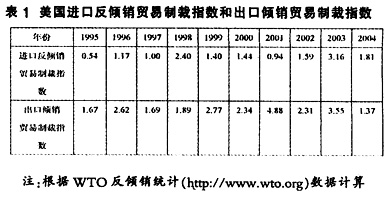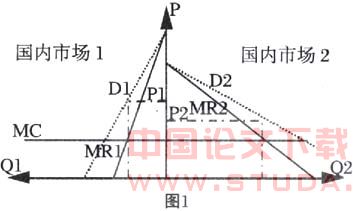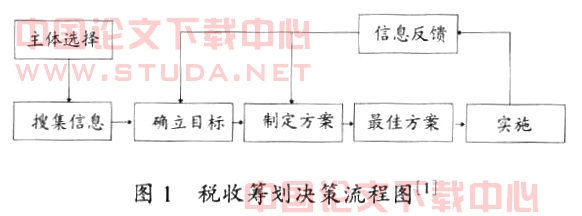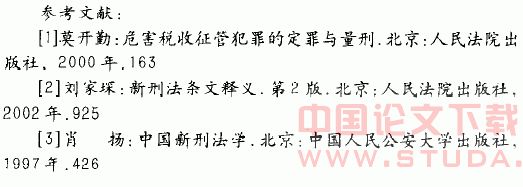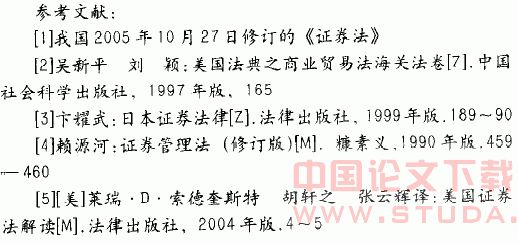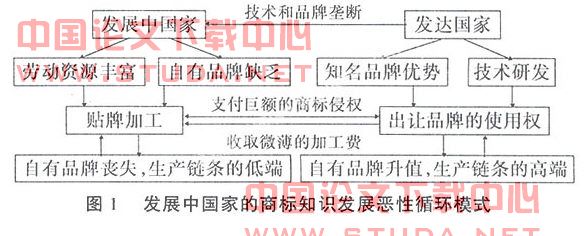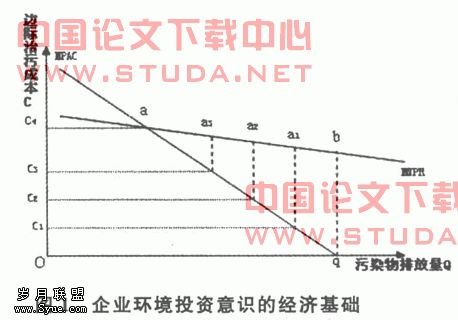威慑理念下的反垄断法刑事制裁制度——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改稿)》的相关规定
关键词: 反垄断法/威慑/刑事化/刑事制裁/立法建议
内容提要: 威慑是反垄断法中最优先,甚至可能是唯一的目标。反垄断法应强化刑事立法,但应有其限度,否则会形成过度的威慑。为此,我们必须设计合理的反垄断刑事制裁制度,以达到最优化的威慑效果。2005年9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改稿)》有关刑事制裁的规定有其局限性。在未来的修改中,我们应明确规定追究本身违法的核心卡特尔行为和行政垄断行为的刑事责任;规定两罚原则,追究个人和公司的双重刑事责任;同时,应像其他国家或地区一样在中规定告密者的刑事宽恕政策。至于刑事制裁措施的选择,我们应优先适用罚金,但罚金不能完全代替监禁。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性很大的严重垄断犯罪行为,动用监禁进行制裁是必须的。
对于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在何种程度上应确定为犯罪行为以及施加何种刑事制裁手段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我国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刚刚起步,有的学者主张我国反垄断法应当设置刑事制裁制度,另有学者则主张我国反垄断法应当非刑事化。[1]笔者认为,我国反垄断立法应采刑事化模式,但我们应对刑事化和非刑事化两种模式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准确把握趋势,充分认识刑事化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神化”反垄断的刑事规定,反垄断的刑事化应有其限度,其措施、手段的运用应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以达到最佳的威慑效果。
一、刑事化模式与非刑事化模式
(一)刑事化模式——以美国为代表
反垄断刑事化模式始于美国。早在1890年《谢尔曼法》制定时,就在其第1条和第2条中规定,违反《谢尔曼法》构成轻罪,可以处最高额为5000美元的罚金,1年以下的监禁,或二者并处。因此,我们可以说,从美国反托拉斯制度确立时起,个人和的刑事责任就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由于法律本身的模糊再加上政府执行反托拉斯的资源比较少,《谢尔曼法》的刑事执行花了几乎半个世纪才成为现实。[2]经过1955年的修订,最高罚金提高到5万美元;1974年的修订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公司的最高罚金被提高到100万美金,对个人的罚金从5万美元增加到10万美元,并且监禁期也从1年增加到3年。这个修正案还将违反《谢尔曼法》的犯罪行为视为一种重罪。1984年《刑事罚金执行法》引入了“两倍收益/损失”罚金条款,这是一种可替代的罚金,它基于犯罪行为人的收益或社会损失的两倍予以处罚。是否使用替代性的罚金条款,法庭有着自由裁量权。这种新的“两倍收益/损失”罚金条款适用于所有联邦刑事法律,包括《谢尔曼法》[3]。1990年的《反托拉斯修正案》将公司的刑事罚金提高到最高1000万美元,个人的刑事罚金提高到35万美元。根据最新的2004年《反托拉斯刑罚提高及改革法》的规定,对公司违法者的罚金增加到1亿美元,个人的刑事罚金提高到100万美元,而最高监禁期也从3年增加到10年。除了联邦立法外,美国一半以上的州也有反托拉斯刑事立法。[4]在美国,刑事诉讼是司法部反托拉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1980-1993年司法部提起的诉讼中,80%以上是刑事案件。[5]
(二)非刑事化模式——以欧盟为代表
欧盟的反垄断法制裁体系中没有规定刑事制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依赖行政罚款来制裁违法行为者。欧盟的基本竞争规则有3条,即《欧共体条约》第85、86、87条。其中,第85条第1款禁止限制竞争的协议、第86条禁止市场支配地位滥用、第87条授权理事会制定合适的条例或指令来实施第85和86条。第87条第2款特别指出,这些条例或指令应规定罚款和日罚款以保证执行第85条第1款和第86条的禁止性规定。[6]根据理事会1962年2月6日颁布的《第17号条例》第15条第2款的规定,委员会有权对故意或过失违反《欧共体条约》第85条第1款和第86条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处以1000至100万欧元的罚款。此外,还可以对违法企业征收上一营业年度销售总额10%以下的罚款。在确定罚款数量的时候,既要考虑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又要考虑违法行为的延续时间。然而,该条第4款明确指出,委员会作出的罚款决定“不带有刑法的性质”。[7]
(三)刑事化——一种趋势
反垄断刑事化模式与非刑事化模式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和文化背景。美国反托拉斯具有悠久的传统,反托拉斯的价值被广泛地认同,价格固定被看作是不道德的,与偷窃没有什么区别。与此正好相反,在欧洲的历史和文化中,反托拉斯法不具备这样的地位。[8]
20世纪90年代早期,反垄断法刑事化国家除了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以外,还有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为数不多的国家。世纪之交,美国的刑事化模式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效仿。在一些欧洲国家,反垄断法的刑事化甚至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法律项目。截至2003年,除美国外,还有8个国家和地区规定了对于个人和公司的双重刑事责任,它们分别是加拿大、日本、韩国、爱尔兰、奥地利、以色列、挪威和我国地区;另有4个国家规定了仅针对个人的刑事责任,它们分别是英国、法国、希腊和瑞士。其中,英国是新近引入反垄断法刑事化的一个国家。2002年11月7日,英国颁布了《2002年企业法》。该法规定,任何人,只要他不诚实地从事核心卡特尔行为,可能被判处最高5年的监禁和/或不受限制的罚金。[9]德国的《反限制竞争法》虽没有规定刑事责任,但1997年8月13日德国颁布了《反腐败法》,在该法第26章中规定了“反竞争的犯罪行为”,开创了对限制竞争行为予以刑罚惩戒的先河。[10]
另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积极推进本国或本地区反垄断法刑事化的立法进程。例如,2003年11月,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宣布,任命一个由财政部官员、司法部官员、竞争和消费委员会官员及公诉人协会联邦理事共同组成的委员会,来共同商讨引入卡特尔行为刑事犯罪的问题。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宣称,它原则上支持导入对核心卡特尔行为实施刑事制裁。[11]现在,一些欧盟学者认为,为了保证严格适用欧共体竞争法,欧共体有必要发展类似于美国反垄断法对人实施的刑事责任。[12]而且按照欧洲人权法庭的观点,如果存在由独立法院进行完全司法复审的可能性,那么,欧共体行政当局实施刑事制裁不会产生与《欧洲人权条约》相违背的问题。[13]
可以认为,在反垄断法中设置刑事责任是各国反垄断法的通行做法。[14]
二、刑事化的目的——有效威慑
在反垄断法中,威慑(deterrence)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无论是美国的刑事制裁、欧盟的行政罚款,还是其他国家的反垄断法制裁手段,其主要目的均在于构筑一个有效的威慑体系。正如波斯纳所言:“一个救济体系的基本目标是威慑人们不敢违反法律。”[15]同属芝加哥学派的Easterbrook法官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威慑是反托拉斯法最优先,甚至于可能是唯一的目标。”[16]美国反托拉斯法规定刑事责任的主要原因在于威慑其他类似的行为。美国司法部非常强调起诉个人并寻求监禁判决,其目的在于对违法者和潜在的违法者警告:他们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17]在欧盟,为什么对违反反托拉斯法的行为处以罚款?通常的答案是,既是为了对违法者予以惩罚,又是为了威慑违法者和其他人以避免相同的违法行为的再次发生,或是为了上述二者兼而有之的目的。[18]在英国,《2002年企业法》引入卡特尔刑事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对那些企图从事卡特尔行为的人将起到威慑作用。“我们并不期望人们停止卡特尔行为,但是如果他们从事了卡特尔行为,给他们发出如下的信息是重要的:他们的行为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都是不可接受的,这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19]在我国台湾地区,其所谓的“公平交易法”规定对违反公平交易行为人科处刑罚、行政罚或民事罚,目的也在于吓阻(威慑)、警惕、防止行为再发生,从而维持交易秩序。[20]
威慑原来是传统刑法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在传统刑罚理论中,威慑被认为是刑罚的主要目的。著名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早已指出,法律存在之主要目的在于威慑再犯。[21]传统或古典意义下的威慑是完全威慑(completedeterrence)。在此观念下,刑罚就在于剥夺犯罪人之利得,以达到完全威慑犯罪人再犯之目的。而威慑较的意义则是最适威慑(optimaldeterrence,也有人译为最优化威慑)。其含义是指,法律制裁的目的非在达到完全威慑,而是在求得威慑的效果维持在对社会之边际利益的贡献,等于其对社会所产生之额外的边际成本。[22]在宪政国家如美国和德国,威慑虽是刑法的主要功能,但具有威慑效果的并不仅仅限于刑法。行政法上的处罚如高额罚款、民法上的制裁如三倍损害赔偿同样也具有威慑效果。但是,要真正有效地把垄断控制在人们“可容忍”的限度内,不能没有刑罚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是由民事措施、行政措施的弱制裁性与行为人实施垄断能够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所决定的。尽管刑罚的威慑力也是有限的,但不可否认刑罚是所有法律制裁中威慑力量最大也是最能威慑违法者的措施。[23]
支持反垄断非刑事化观点的学者认为,监禁这种威慑方式完全可以通过对违法企业的高额罚款来达到。[24]反垄断非刑事化的典型代表欧盟就是试图通过罚款来形成有效的威慑。欧盟《第17号条例》规定,委员会可以对违法企业征收上一营业年度销售总额10%以下的罚款。就目前欧盟的罚款标准而言,许多人认为其罚款的威慑力是不够的。从1979年以来,委员会多次表达对威慑不足的关注。[25]为了威慑企业从事反托拉斯违法行为,从理论上说,应将罚款提高到超过违法者从事违法行为所获得的收益这一程度。如果按数字来量化,应是处以年营业额100%的罚款,即将现行的罚款标准提高10倍,这是形成有效威慑的底线。但是,从实践来说,这种高额的罚款是不可行的,主要理由如下:[26](1)公司没有能力支付这种高额罚款。处以公司年营业额100%的高额罚款会导致大多数公司破产。公司所获得的利润一般已经通过工资、税金、分红或其他形式加以分配,而从年营业额和资产总额的比率来看,绝大多数公司的年营业额高于其资产总额。这就意味着,即使公司被迫出售资产也不足以支付公司年营业额100%的高额罚款。(2)处以高额罚款会产生社会成本。在完善的市场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处以高额罚款会影响公司股东的利益,债券持有人和其他债权人的资产将缩水,雇员的薪水和国家的税收也将减少。最后,在不完全竞争状态下,罚款会导致更高的价格,从而导致消费者的利益也受到损害。(3)高额罚款不符合比例正义的要求。《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49条第3款规定,制裁应与违法行为的违法程度相当。由于反托拉斯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比较低,因而适当提高罚款的比例是需要的,但是,将罚款比例提高到年营业额的100%,任何一个法院都会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
也许有人认为,反托拉斯的私人执行会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反托拉斯的私人诉讼会产生有效的威慑。确实,通过反托拉斯的私人诉讼获得的三倍损害赔偿(美国)的威慑力是比较大的,但是过高的损害赔偿额同样会产生上述高额罚款的问题。基于这种考虑,现在除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实行了三倍损害赔偿制度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立法基本上都没有规定这种制度。而且,从美国现在的反托拉斯私人诉讼的实施情况来看,要求也越来越高,胜诉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其威慑力已经大不如前。
鉴于此,笔者认为,引入刑事制裁是构筑反垄断法有效威慑体系的关键要素。对于公司而言,刑事制裁只能是罚金,对于个人的刑事制裁则包括罚金和监禁两种。有学者认为:“对于罚金,其可替代性最为明显,完全可以用罚款来替代。”[27]笔者认为,在反垄断法中设置罚金刑是必要的。罚款是一种行政手段,不涉及道德判断,在社会伦理上是中性的。其对关系人之名誉及威信不发生影响,只是在陈述义务之警告。[28]而罚金具有耻辱效应,会引起社会对该企业或个人的评价降低。由此可见,行政罚款与刑事罚金即使数额相同,它们的威慑作用是不同的。从事垄断行为的经营者在主观上的恶意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必须通过罚金刑来进行道德谴责,行政罚款则不具备这种功能。刑事上的定罪通常会损害一家公司的名誉,这对被定罪者造成了额外的成本,因而构成了额外的威慑因素。[29]
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鼓励适用罚金而不是徒刑(监禁)。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为处罚经济性、非暴力的中产阶级犯罪——如固定价格、漏税、证券诈骗、贿赂等——已经越来越多地运用监禁。其主要原因是其中的大多数罪犯都能支付高额罚金,这样的罚金也就不足以构成威慑。[30]而针对个人的刑事罚金,在实践中公司会想办法由公司出面替个人支付从而减轻了罚金的威慑作用。但是,如果对个人处以监禁,那么公司无论如何都是不能代劳的。[31]正如一位公司的执行官所言:“在19世纪70年代末,只要是钱的问题,公司最后可以帮你解决,但是如果涉及剥夺我个人的自由,那么,公司没有任何解决办法。”[32]美国反垄断法专家也认为,对违法的领导人判处刑事监禁,比仅仅对企业征收罚款更有效和更有威慑力。特别当违法企业的领导人必须在监狱渡过感恩节而不能与家人团聚的时候,不管对企业的罚金有多高,都不会比制裁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更有效。[33]
三、刑事化的限度——防止过度威慑
美国许多学者认为,刑罚固然有威慑作用,但是威慑强度并不是无限的,它应当有一个限度。确定这种限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可变的。威慑强度超过了必要限度,为减少犯罪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就可能超过因减少犯罪所产生的收益。[34]我们在设计反垄断刑事规范时,应遵守一定的规则,以防滥用刑事化规则,造成过度威慑(over-deterrence),从而损害经济的。
(一)刑事化规则的限度——确定性
任何基于威慑和公平的制度必须有着明确的规则。如果被禁止行为在定义上具有不确定性,以及对具体行为适用该定义时也具有不确定性,那么,严厉的惩罚也许会阻止处于禁止边缘的合法行为。它们也许导致潜在的被告过于回避他意图进入的区域。[35]这就构成了过度威慑。在美国,在动用刑事制裁手段时,司法部和法院是非常慎重的。因为《谢尔曼法》第1条和第2条的规定很广泛也很模糊,在一个世纪以前,人们不知道哪些行为应该受到刑事追究,因而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美国法律规定了刑事制裁手段,但一直没有动用,以防止形成过度的威慑。后来,通过司法部、尤其是法院的努力,逐渐发展了应该受到刑事制裁的反竞争行为的类型,以及哪些应该受到民事制裁和私人索赔。一般认为,固定价格、串通投标和顾客、市场划分行为被认为是一个刑事犯罪行为,其他行为,如合营企业规则、固定标准商业惯例、垂直限制等被认为适于用民事制裁。当规则明确后,美国才开始大胆运用刑事制裁手段。
(二)适用范围的限度——本身违法的卡特尔
反垄断法在实施过程中,经常需要通过经济分析来判断行为的违法性,因此,其社会危害性并不一定非常清晰。在这种情况下,轻易动用刑罚的手段显然是不合适的,并且容易导致刑罚的滥用,从而造成过度威慑。
我们应该谨慎运用刑事制裁手段,只有严重的违法行为才适用刑事制裁。这些严重的违法行为,是指那些被称为本身违法的行为,被认为本身对贸易构成不合理限制的行为、经判例而被确认的本身违法行为,简言之,是那些被法院多次宣布为违反反托拉斯法的商业行为。[36]也就是说,刑事执行仅适用于本身违法案件或被告明知违法的案件。[37]
美国的刑事规范虽然比较多,但几乎所有由司法部提起的刑事诉讼都属于针对违反《谢尔曼法》第1条规定的横向限制竞争行为(卡特尔)。其刑事制裁的基本目标是本身违法的核心卡特尔,如固定价格、串通投标、市场分割计划等。实际上,98%的刑事案件涉及本身违法的横向限制竞争行为。[38]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美国的反托拉斯刑事制裁是有限度的,它针对的对象主要局限于本身违法的卡特尔行为。
英国、爱尔兰等国家的反垄断法仅对于核心卡特尔的犯罪问题作出规定;还有些国家如法国原来的反垄断法规定的刑事规范比较多,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但现在有慢慢缩小的趋势。因此,从目前各国所实际发生的反垄断法刑事制裁来看,有集中于本身违法的核心卡特尔行为的趋势。
(三)刑罚的限度——短期自由刑
刑事制裁应考虑违法行为和违法者的可谴责性,同时也应强调惩罚应与犯罪相适应。从重处罚可能会触犯道德准则和宪法赋予罪犯的权利。例如,对小打小闹的贪污行为处以死刑的法律显然是不合情理的。[39]也许长期监禁会避免大多数的反托拉斯违法行为,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反托拉斯违法行为者而言,这种长期监禁是不公正的。也许死刑判决会避免大多数的反托拉斯犯罪行为,但是,当我们看到CEO生活在恐惧之中时,那么,将会深深刺伤我们对于正义的感情。[40]这不仅违反了宪法的基本准则,也不符合比例正义的要求。反垄断法不宜设置长期自由刑和死刑,从目前各国的立法情况来看,主要限于短期自由刑,一般为5年以下。从实际执行情况来观察,判处1年以下监禁的案件占了绝大多数。
四、刑事化的应用——最适威慑
反垄断的刑事化可以对违法的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但这种威慑不可能起到完全威慑的效果。从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来分析,反垄断法的刑事制裁所追求的应是最适威慑。最适威慑的效应并不是铲除所有的犯罪,因为这样做的代价很高,而且社会效益不断降低。政策制定者应对有限的资源加以配置,争取以最少的成本实现威慑目标。也就是说,力求有效率地实现这一目标。[41]为了实现最适威慑效果,我们应在启动机制、追诉程序及刑事制裁方式方法等领域做出最优化的设计。
(一)最适启动机制
各国或地区有关启动反垄断刑事程序的做法不太一致,主要有如下三种模式:
1.美国模式:告发、起诉一体制在追究犯罪企业或犯罪个人的反垄断刑事责任方面,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享有单独主管权限。只有反托拉斯局有权对有关企业和个人提起刑事诉讼,其他机关、法人和个人均无此权。它既是反垄断犯罪行为的告发者,同时也是反垄断刑事案件的起诉者。在刑事诉讼中,反托拉斯局以检察官的身份出现。[42]
2.日本模式:专属告发制日本《反垄断法》规定,第89-91条规定的犯罪须待公正交易委员会告发后才可以论罪。告发要向检察厅总长进行。得到告发的检察厅总长须将案件移交东京高等检察厅,由东京高等检察厅的检察官提起公诉。[43]
3.我国地区模式:先行政后司法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公平交易法”第35条规定,违反第10条、第14条、第20条第1项规定,经“中央主管机关”依第41条规定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为或采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预期未停止、改正其行为或未采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后再为相同或类似违反行为者,处行为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1亿以下罚金。按照该规定,须先由“公平交易委员会”作成“命业者停止其行为”之命令,业者仍不停止,“政府”才能发动刑罚权,即“先规制后制裁”,或称“先行政后司法”。[44]
笔者认为,美国的刑事启动机制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机制。这种机制的确立是因为美国的司法部既行使公诉人的职责,同时又是反托拉斯案件的主管机关。尽管这种机制的运作效率比较高,但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反垄断主管机关都是一个独立的专门反垄断主管机关,它们并不行使公诉职能,因此,其他国家很难仿效。
我国台湾地区先行政后司法的模式存在诸多问题:第一,在行政处分权未发动前,司法机关无权加以处罚,这可能使事业较无顾忌滥用其市场独占地位;第二,如事业之行为已违反所谓“公平交易法”之禁止规定,经“主管机关”命其停止而即时停止其不正行为时,仍可免于处罚,如此反而有鼓励事业为不正行为之诱因存在;第三,以行政处分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于刑法理论上并不妥当。[45]
日本《反垄断法》之所以赋予公正交易委员会专属告发权,目的在于使在运作《反垄断法》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公正交易委员会能够根据案情的具体轻重来具体判断是科处排除措施命令等行政处分,还是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最终达到有效推进反垄断政策的目的。日本判例也认为,公正交易委员会作为日本唯一的《反垄断法》运作机构,有权综合考虑违反《反垄断法》行为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以及其他要素,最终作出不予追究、或采取行政性措施、或进行刑事告发的决定。[46]
笔者认为,反垄断法的实施是比较复杂的,它既涉及法律问题的判断,又涉及经济和事实问题的判断。执法机关在处理具体个案时,必须结合当时的经济情况,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等诸多要素进行综合判断,才能决定行为的违法程度及是否应追究刑事责任。在这方面,反垄断主管机关具有相当的优势。它有这方面的信息资料,也有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因此,由其告发不仅能提高威慑效果,还能最大限度地节约告发成本,从而达到最适威慑状态。司法机关应当尊重反垄断主管机关的专属告发权。目前,实行专属告发制的国家还有英国、法国、韩国等国,已成为一种主流的反垄断刑事启动机制。
(二)最适追诉程序
刑事指控要动用各种资源,而资源是稀缺的。我们有必要设计一套程序,确保优先指控对社会影响最坏且指控又能获得最大威慑效果的犯罪。对不是很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指控应尽量减少,否则,具有更大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可能会因此而得不到制裁。[47]在追究反垄断犯罪责任时,对于很多反垄断案件特别是违法程度比较轻的案件一般应通过快速简易程序进行处理,从而获得最适威慑效果。
1.美国模式
美国的反托拉斯刑事指控由司法部反托拉斯局负责。作为公诉人的反托拉斯局可能会提出令双方均比较满意的案件处理方案,即通过辩诉交易来处理反托拉斯违法犯罪案件。所谓辩诉交易,是指处于控告方的检察官和处于被告方的辩护律师进行会商和谈判,以撤销指控、降格控诉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等为条件,换取被告人作“认罪”答辩或满足控方其他要求。如果交易成功,达成协议,经法官审查被告人系出于自愿,协议内容合法,便加以采纳,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判刑,不再进行开庭审理。[48]
2.德国模式
在德国,如果一项反垄断行为构成犯罪,并且证据已经排除了合理的怀疑,那么,检察官必须提出公诉。除了正式的犯罪指控外,德国检察官还有如下两种程序可供选择:第一,附条件不起诉。《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a)条规定,在轻罪案中,检察官在公共利益不要求通过审判程序定罪时,可以在经过有管辖权的法院同意后决定“附条件不起诉”。这里的“附条件”一般是指被告人向被害人支付赔偿金或者向慈善机构或者国库捐款等。按照德国法的规定,大多数的反托拉斯犯罪是较轻的犯罪,因此,德国检察官经常适用这种程序来终止正式的刑事指控。[49]第二,刑事处罚令程序。该程序适用于证据确实且被告认罪的轻罪案件,罚金是唯一的制裁方式。由检察官向法官提出,用刑事处罚令来代替发动公开的审判程序。与此同时,检察官必须向法官提供对于案件事实的陈述和具体罚金数额的建议。如果法官批准了刑事处罚令,就发给该案的被告。被告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刑事处罚令;如果不接受,案件就进入公开审判程序。
美国和德国的快速简易程序的目的均在于节约诉讼资源,使诉讼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合理化,威慑效果最大化。但是,美国的辩诉交易模式的主动权掌握在检察官(司法部)手中,法官对于检察官的辩诉交易控制较少,其申请一般都会批准;而德国模式中法院的权力很大,它不受检察官建议的约束。笔者认为,德国模式更具合理性。检察官在本质上是一个行政官员,他会更多地考虑一些因素,而被告的行为一旦构成犯罪,其行为是否应该受到刑事制裁,则属于司法审判权的范畴。对于司法权,检察官无权处置。美国模式放大了检察官的权限,可能会导致两大弊端:无辜者在辩诉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有罪的被告从辩诉交易中获益。相对于检察官而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笔者认为更适合由法官来执行这种艰巨的任务。另外,美国的辩诉交易对于重罪和轻罪均可以适用,而对于那些严重的反垄断刑事案件,理应经过公开审判程序来加以处理,才能彰显其强大的威慑力。因为每个反垄断犯罪的罪犯均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公开审判将使他们感到非常窘迫,这种公开审判的威慑效果比法院实际判决的刑事制裁的威慑效果可能更好。
(三)最适刑事制裁
1.两罚原则
在反垄断刑事制裁中,有些国家或地区仅规定个人的刑事责任;而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则规定了个人和公司的双重刑事责任,即主张两罚原则。例如,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95条规定:“法人代表、法人或人的代理人、雇员及其他从业人员就该法人或自然人的业务或财产,实施……违法行为时,除处罚行为人外,对该法人也处以……罚金刑。”从最适制裁角度而言,需要确立两罚制度。这是因为:第一,如果缺乏对于公司的制裁,公司会鼓励其代理人从事违法行为,反之,它们会主动控制其代理人的行为;第二,对于家来说,如果不实行两罚原则,那么,他可能会安排相互之间的资产转移从而逃避罚金的处罚;第三,基于相同的事实起诉公司和个人,并且同时进行审判,其执行成本是的,但威慑力却大不相同;第四,实行两罚原则不会导致对于任何一方的过度惩罚,同时也会减少无辜当事人对于制裁的恐惧;第五,对于公司和个人刑事制裁的威胁会大大增加潜在的辩诉交易,所有的被告都希望通过辩诉交易来免除或减少制裁。[50]
2.告发免责——刑事宽恕政策
如上所述,反垄断的刑事制裁主要针对本身违法的核心卡特尔行为。然而,由于卡特尔行为的秘密本质,加之在实践中卡特尔往往使用合法的商业协会及会议活动作为掩护工具,导致取证工作相当困难。
有鉴于此,各国竞争主管机关近年来逐渐盛行对联合行为(卡特尔行为)之参与事业实行告密之“宽恕政策(leniencypolicy)”,即所谓“窝里反条款”,以有效遏止不法之联合行为。各国之宽恕政策一般均规定,在竞争法主管机关尚未知悉或完全掌握足够证据前,主动向其供述案情并提供具体证据,或于主管机关调查过程中,协助调查并提供具体违法证据,从而使竞争法主管机关或司法机关得以顺利完成调查任务者,依法可换取行政或刑事责任之减轻或免除。此制之引进,有助于司法效率之提升及行政资源之节省,对于吓阻(威慑)违法之联合行为(特别是恶性卡特尔行为)的发生以及及时发现违法联合行为并防止危害的继续扩大,帮助尤大。
美国从1978年开始推行刑事宽恕政策,但初期效果并不理想,每年只有一个案件申请宽恕。1993年,美国对该制度进行了修正,使申请公司如果系符合有关规定,则当然自动获得宽恕。修正后,申请宽恕的案件迅速增加到每月一件以上。该制度已经在很多案件中使公司与个人获得豁免,包括维他命卡特尔案。依照美国的经验,如果没有告密者,很多卡特尔案件将不可能被发现。[51]美国大多数成功控诉的国际卡特尔来源于宽恕计划,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他模仿美国做法的国家都不同程度获得了成功。[52]由此可见,刑事宽恕政策已经成为各国追究反垄断刑事责任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获得最适威慑效果的有效武器。
3.多用罚金,慎用监禁
一般而言,反垄断法中的刑事制裁主要包括罚金和监禁两种。从刑事制裁的趋势来分析,随着过失犯及行政犯的增加,罚金被广泛使用,且成为当今刑罚中最为常用的一种。从成本效益角度来分析,监禁的成本是比较高昂的。与此相反,罚金执行不需要太大的费用,也没有造成社会成本,反而有大笔的国库收入。因此,从各国反垄断法刑事制裁的实施情况来看,“多用罚金、慎用监禁”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
然而,我们不能用罚金来完全代替监禁。罚金仅仅是以剥夺财产上的利益来对受刑人的整个人格发生作用。一般来说,其痛苦的程度较轻。另外,对于得失之后实施犯罪的人来说,也不能对其一般预防效果抱有期望。在此,罚金便具有局限。[53]当考虑到违法者的财产状况、从事对社会不利的行为所获得的私人利益以及予以制裁的概率,如果对社会不利的行为造成的损害十分巨大,而金钱制裁并不能产生适当的威慑作用时,我们应选择监禁这种制裁方式。[54]实际上,任何监狱生活,尽管短暂,也有很高的威慑效果。当然,我们不能依赖监禁,监禁应当作为最后采取的一种刑事制裁方式,谨慎使用。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刑事化规定的局限性及重构
2005年9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改稿)》(以下简称《修改稿》)专门集中一个条文规定刑事责任问题。其第54条规定:“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试在对以上法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重构。
1.《修改稿》的局限性
从《修改稿》的规定来看,其在法律责任中分别规定了行政、民事、刑事责任。这种规定层次更为分明,表述也更为精练,同时也表明了我国将采取反垄断法刑事化模式。这种刑事化规定是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然而,《修改稿》也存在着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显现了立法上的局限性:
第一,犯罪构成规则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修改稿》虽然规定了反垄断法应追究垄断行为的刑事责任,但在何种情况下才构成犯罪,包括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犯罪行为等并没有明确的表述。这种模糊的规定,会导致实践中具体操作的不确定性:要么过于严厉造成过度威慑,要么过于宽松造成反垄断刑事责任的虚置。
第二,缺失反垄断犯罪的追诉机制和制裁措施。《修改稿》不仅没有规定反垄断刑事犯罪的追诉机关、追诉程序,而且没有规定相应的制裁对象和制裁措施。这会导致实践中无法有效地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实现威慑目标。
第三,反垄断犯罪适用范围不清。《修改稿》仅笼统规定“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这可能会导致反垄断法刑事制裁的扩大化,如将刑事制裁扩大到“经营者集中”。然而,对于“经营者集中”行为,各国一般不会追究其刑事责任。
2.对《修改稿》的修改建议
《修改稿》的上述局限性,极大地限制了反垄断刑事制裁制度的威慑价值。笔者认为,在下一步的立法草案修改中,应对反垄断法的刑事制裁制度作如下几个方面的修订:
(1)尊重刑事化立法的限度,防止过度威慑
我们一方面要强化刑事化立法,另一方面也应尊重刑事化立法的限度,防止形成过度威慑。有学者建议:“我们应当对行政垄断行为、卡特尔行为、纵向价格垄断行为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设置刑事责任。”[55]但笔者认为,从目前各国反垄断法所实施的情况来看,追究刑事责任的重心在于本身违法的核心卡特尔行为。虽然有些国家或地区规定了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为的刑事责任,但是在实践中几乎没有动用,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有的国家(如英国)鉴于这种实践,在本国的立法中仅对卡特尔的犯罪问题作出规定,从而将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为实现立法上的非犯罪化。从我国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大量的垄断行为是本身违法的核心卡特尔行为和行政垄断行为,而我国的行政垄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比本身违法的核心卡特尔行为而言,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笔者建议在未来的修改中,应明确规定追究本身违法的核心卡特尔行为和行政垄断行为的刑事责任。
(2)在最适威慑理念指导下,设计刑事化的应用体系
我们必须在反垄断法中设计更为合理可行的反垄断威慑执行制度,以达到最适威慑效果。第一,我们要设置独立的、强大的专门反垄断主管机关,授权其专属告发垄断刑事犯罪,利用其专业知识和技能,达到最适威慑效果;第二,对于那些不是很严重的反垄断违法犯罪行为,我们应借鉴美国和德国的简易程序进行快速处理,以确保优先指控对社会影响最坏且指控又能获得最大威慑效果的犯罪;第三,为了强化反垄断刑事制裁的威慑效果,我们应在立法中规定两罚原则,追究个人和公司的双重刑事责任。同时,应像其他国家或地区一样在中规定告密者的刑事宽恕政策。至于刑事制裁措施的选择,我们应优先适用罚金,但罚金不能完全代替监禁。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性很大的严重垄断犯罪行为,动用监禁进行制裁是必须的。为了达到最适威慑效果,反垄断法中罚金的最优数额应是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除以被处以罚金的概率;而监禁应是一种短期自由刑,最长以不超过5年为宜。
注释:
[1]赞成反垄断法刑事化的代表性学者是邵建东教授,参见邵建东:《我国反垄断法应当设置刑事制裁制度》,《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反对反垄断法刑事化的代表性学者是李国海博士,参见李国海:《反垄断法制裁手段研究》,载漆多俊主编:《法论从》第10卷,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200页。
[2][17][32]SeeDonaldI.Baker,TheUseofCriminalLawRemediestoDeterandPunishCartelsandBid-Rigging,GeorgeWashingtonLawReview,October/December,2001,p.695,p.698,p.706.
[3]SeeDonaldC.Klawiter,ThePowerfulEffectofSubstantialCriminalFines,Imprisonment,andOtherPenaltiesintheAgeofInter nationalCartelEnforcement,GeorgeWashingtonLawReview,October/December,2001,p.750.
[4][13][26][50]SeeClaus-DieterEhlermannandIsabelaAlanasiu,EffectivePrivateEnforcementofECAntitrustLaw,HartPublishing2003,p.414,p.398,pp.392-393,pp.435-436.
[5][30]参见[美]菲利普·阿瑞达、路易斯·卡普洛:《反垄断法精析:焦点与案例》(第5版),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6]1997年《阿姆斯特丹条约》对《欧共体条约》进行了修改,将竞争法的基石第85、86、87条改为第81、82、83条。
[7][8][18][25][29][54]参见[荷兰]伍特·威尔思:《欧洲共同体竞争法中的罚款处罚》,李国海译,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从》(第5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第281页,第252页,第276页,第278页,第256页。
[9]有关英国反垄断法刑事化内容的介绍,参见王健:《2002年法与英国竞争法的新》,《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2期。
[10][14][55]参见邵建东:《我国反垄断法应当设置刑事制裁制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11]SeeIt’sCriminal:TheDebateOverPenaltiesforCartelConduct
[12]参见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17页。
[15][35]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反托拉斯法》第2版,孙秋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页,第314页。
[16][21][22]参见陈志民:《吓阻概念下之反垄断法私人诉讼》,《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14卷第1期。
[19][51]SeeAngusMacCulloch,TheCartelOffenceandTheCriminalizationofUnitedKingdomCompetitionLaw,J.B.L.2003,Nov,p.619,p.625.
[20][44]参见赖源河编审:《公平交易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0页,第467页。
[23]参见郑牧民等:《垄断罪分析与立法建议》,《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5期。
[24][27]参见李国海:《反垄断法制裁手段研究》,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从》第10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第198页。
[28]参见洪家殷:《行政秩序罚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92页。
[30]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299页。
[31]参见王健:《英国卡特尔刑事化制度研究》,载志刚主编:《刑法问题与争鸣》第11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页。
[33]参见郑鹏程:《论垄断罪的依据、构成与刑事责任》,《河北法学》2003年第3期。
[34]参见储槐植:《美国刑法》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页。
[36]参见[美]马歇尔·C·霍华德:《美国反托拉斯法与贸易法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37][40][47][49]SeeFrankWamser,EnforcementofAntitrustLaw,PeterLangGmbh,1994,p.32,p.152,p.54-55,p.50.
[38][41]参见[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38-739页,第739页。
[42]参见戴奎生等:《竞争法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43][46]参见[日]芝原邦尔:《经济刑法》,金光旭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第77页。
[45]参见汪渡村:《公平交易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73-274页。
[48]参见卞建林:《刑事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168页。
[52]SeeJulianM.JoshuaandDonaldC.Klawiter,theUKCriminalizationInitiative,p.70.
[53][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