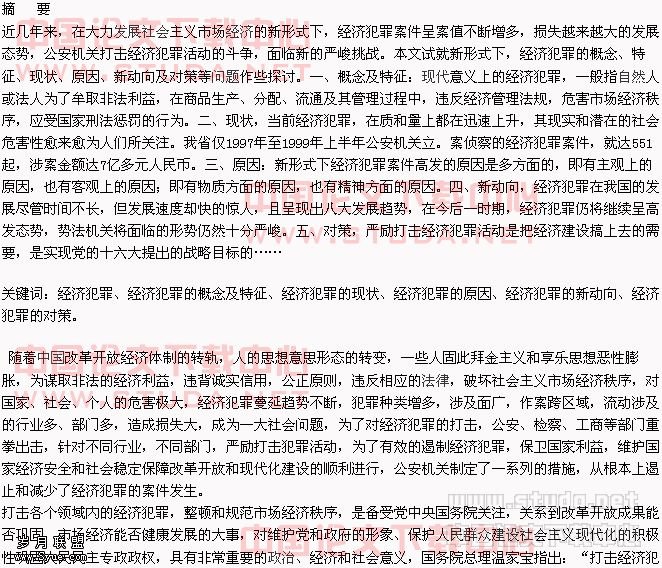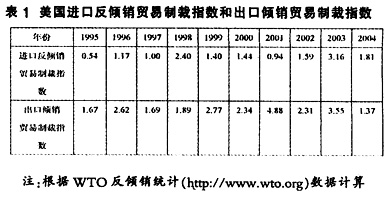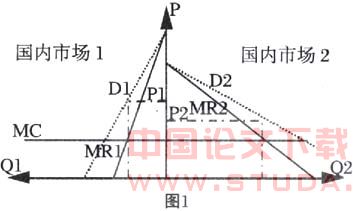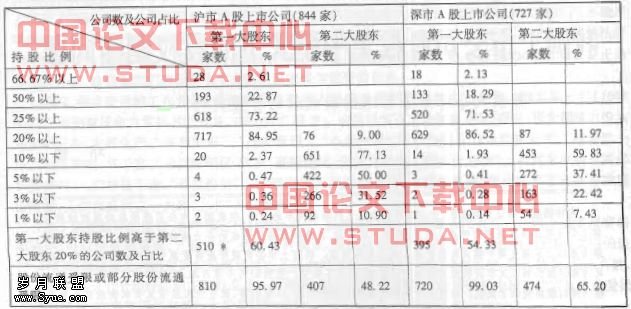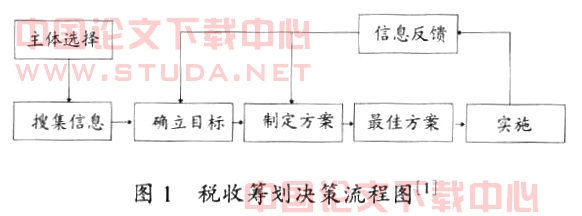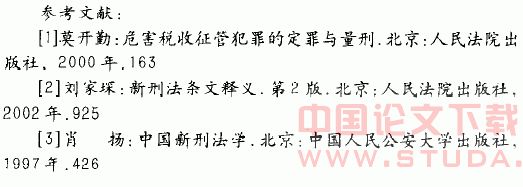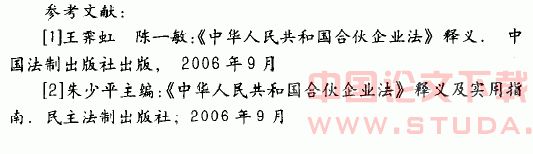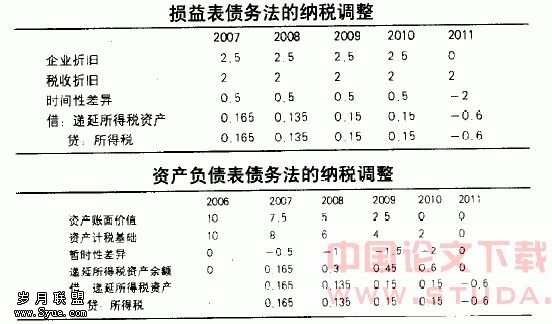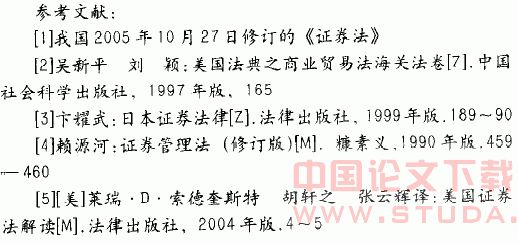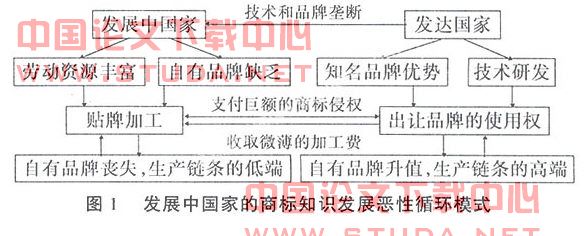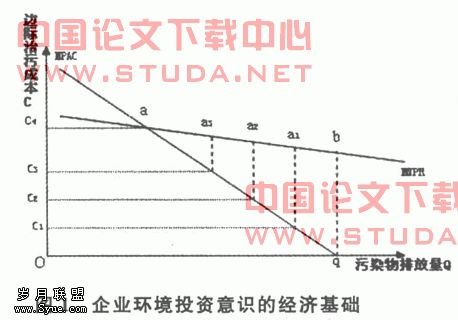“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之理论研究
关键词:无权处分 出卖 财产
论文摘要:关于“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之问题,我国学者王泽鉴先生于其专著《民法学与判例研究》中,曾不遗余力,再三检讨之,足见其于立法理论之澄清与司法实践之指导,意义之大。于我国大陆,对其之研究,理论成果可谓不少,然多因局于立法规定之限,难谓其研究成果具有实质之进展。故笔者特选本题为论,期能理清立法之规定,司法之实践,学说之理论三者关系,于学者研习此问题有所裨益。为达立论体系之起见,本文欲从无权处分,出买他人之物,二者相互之关系,以及二者于我国未来民事立法之体现,几方面研习之。
Key words: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betray, property
Abstract:About the issue of betraying others’ property and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Taiwan scholar, Wangzejian argues again and again in his "science of civil law and legal precedent study ",which brings forth that the issue’s significance to explanation of legislative theory and judicial practice. In our country continent, though the researches for the issue are abundant, achievements of the research are lacked of consequential progresses, for the limitation of legislative regulation. So I select the issue for my paper, for the purpose of distinguishing the relationship of legislative regulation, judicial practice and academic theory and offering some help to research. For the convenience of discussion, the paper will argue from four parts: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betraying others’ proper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other, and manifestation of each other on the civil legislation in future.
第一部分:无权处分之探讨
一、 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
欲探讨无权之处分,必先探讨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乃德国学者对行为之分类,现已为诸多国家继受之。所谓负担行为,系指以发生债法上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为目的之法律行为,买卖,赠与为其著例。所谓处分行为,系指直接以发生权利变更得丧为目的之法律行为。在此,处分有物权处分,债权处分之分,因债权处分以直接发生债法上的权利变动为目的,与物权处分类似,故台湾学者以准物权称之。[①]
关于二者区之效果,可简单区分为:负担行为侧重发生债权之效果,处分行为侧重发生物权之效果或者准物权之效果,因无权处分是针对权利处分行为而言,其并不当然涉及债法上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之给付,故无权处分与负担行为无关,负担之行为并不以负担义务者拥有处分权为其要件,然于另一方面,处分行为就以处分人具有处分权为必有。
二、无权处分行为于我国民事立法上之体现
无权处分之效力问题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并未规定,不知立法者之意图,是故意不规定留待以后学说与解释完善之,还是立法者在当时立法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毋庸置疑,应以前说为适。我国《民法通则》的主要起草者佟柔先生认为,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行为人必须适格,意识表示真实,内容不违背法律道德,符合法律形式。[②]在行为人适格中,包括了行为人对标的物的处分权,只是其为明确表示此法律行为应是处分行为,还是负担行为,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在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名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在第八十九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人共有物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分赔偿。针对此条规定可认定为,部分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擅自处分为无权处分,亦未明确规定无权之处分是适用于处分行为,还是负担行为,唯从后面的但书部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维护其权利”观察之,应认为此处第三人取得之权利应是财产之所有权,为物权,故为与后面部分相对比衔接,应承认该无权处分行为,应于处分行为为适,然其终为明确说明无权处分行为是否适用于负担行为。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处分他人的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实际上,此立法之规定极不严密,以致于学者之间引起热烈之讨论。按其反面之解释,如无权处分之人,于订立合同后,未取得权利人追认或者未取得处分权,其合同无效。合同乃债发生之最重要之原因,将合同之命运,系以债务人是否拥有处分权以及权利人是否追认之上,严重混淆法学之基本理论:负担行为不以负担债务人拥有处分权限为要件,处分权仅为处分行为为必要。我国立法采此规定,似与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与独立性有关,然这于一定程度上忽视对动态安全之保证,如出卖他人之物之情形,这将于下面讨论,这里暂不论述。
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是一条有关无权处分于物权上适用之规定,即物权善意取得制度。居于此,我国有学者认为由于有物权善意取得制度之存在,就无必要承认,于负担行为情形下,无权处分之负担行为有效性之理论。其认为,于物权善意取得制度下,善意之人已受必要之保护,无需承认其于负担行为义务人之间所谓之负担行为之有效性。[③]我认为其观点不妥,原因有二:其一,忽视了无权处分之负担行为与善意取得二者之关系问题,二者从法理上论,应是独立存在的,并不应承认善意取得制度,就应摈弃无权处分的负担行为之有效性, 如上所论,无权处分行为仅就处分行为而言,并不涉及负担行为的效力,实际上,可以把善意取得制度看成是对无权处分于处分行为结果上之校正,而不能简单看成是对无权处分行为 “无权”之本身属性之补充化。(此问题将于出卖他人之物部分检讨,此不赘)其二,在我国现阶段,善意取得制度有一定之局限,并不能充分保护善意之人之利益,维持物之动态安全。
根据以上部分论述,可知我国现行法律并不采纳无权处分之负担行为有效性之理论,于《合同法》中尤甚,部分学者亦以此出发去检讨学理。
三、无权处分于司法实践中之体现
我国司法之实践,皆依法而行,以现行之法律为其依据,不能引学理以断案,故依法而认定,无权处分之负担行为效力待定,又因我国采物权行为有因行,故处分行为于负担行为同其命运,此问题毋庸置疑,在此不赘。
第二部分 出卖他人之物
一、范围界定
出卖他人之物,有受他人委托而出卖之,亦有未经他人授权而擅自出卖之,前者属有处分权而出卖之列,后者属无处分权而出卖之列,于前者,其处理甚为显然,在此不论,为其争议最甚者,为后者,故本文仅限定于无处分权而处分他人之物之研习。
二、出卖他人之物于合同上之效力
为便于分析,试举一例,某人甲与某人乙订立一买卖之合同,约定甲将一奶牛出售于乙,于10天后交付之,乙向甲支付5000元人民币,唯此奶牛为丙所有,根据我国合同法之规定,如在奶牛约定交付日期之前,经丙追认或者甲已取得该处分权,该合同有效,如丙未追认且甲亦未取得该处分权,该合同便无效,该规定,极具争议,现做如下检讨:
第一,甲承诺10日后,将丙之奶牛交付于乙,无论乙是否知道该奶牛为丙所有,对其合同效力应不产生任何之影响。出卖人在与买受人达成买卖合同时,出卖人理应知其无处分之权限,而仍与买受人达成买卖之合同,足表明其愿受合同之约束,实际上,至于其是否能真正履行其合同之义务,于履行合同义务之前,其仍有一定期限,使其取得处分之权能,从而完成自己允诺之合同义务,至于其如不能取得处分之权能,不能完成对合同义务之履行,属于主观不能,不应影响该合同之效力,其理应对买受人承担违约责任,如此规定,既不会使买受人之利益与出卖人真正履行合同之义务相比,有任何之损失,亦使得真正权利人之权利,受到应有之保护,最终一切之不利结果,由无权出卖他人之物者承受,符合公平正义之价值,亦能促使无权出卖他人之物者慎重衡量其处分行为,对交易之动态安全保护颇为有利。
第二,再次分析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会发现一个饶有情趣之问题,无权处分之合同因权利人之追认,而有效,其有效究竟指何而言,买受人是否就能一定得到该合同实际履行带来之利益。首先,权利人之“承认”,并不使其成为该合同之当时人,买受人当然不能向其请求履行合同之义务,此乃合同相对性使然。[④]其次,合同只能于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产生约束之力,权利人之追认,补足了合同之效力,然而另一方面买受人其权利向谁主张,如权利人承认出卖人之处分,而不将该标的物给付于买受人(出卖人无权向其主张给付),故出卖人仍不一定真正得到该合同实际履行带来之利益,亦只得向出卖人请求违约责任。如此之追认又有何意义,还不如直接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为宜。
三、出卖他人之物在物权上之效力
为论述之便,试举一例研习,某人甲将一照相机出卖于乙,并交付之,唯此照相机为丙所有,乙能否取得该相机之所有权,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了物权之善意取得制度,买受人于一定条件下,可以直接取得该物权,故该制度亦被叫做物权即时取得制度。
我国物权法规定可谓简单,从中并不能完全解决出卖他人之物之问题。为此有必要从法解释学上,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之研究。
各国之善意取得制度皆以日耳曼法之“以手护手”制度原则为其伊始。该原则认为,任意将自己之动产交付给他人者,则只可以就该他人请求损害赔偿,而不得向第三人请求返还该动产之所有权,此制度乃对物权追及效力之限制。[⑤]至今之善意取得制度有二种基本立场:“极端法”立场与“中间法”立场。极端法立场又有极端否定法与极端肯定法之分:极端否定法认为“任何人不得把大于自己的权利让与第三人,”故此种立场除极少数情况下,承认善意取得,基本上不承认物权善意取得制度,采此立场者有挪威、丹麦;与此相反极端肯定立场,则无限地承认善意取得制度,采此立场者只有1942年之《意大利民法典》。而中间立场者,则是折中极端否定与极端肯定二种立场,采此立场者有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等国家,我国亦采此立场,为稍不同的是,各国根据不同之实际情况,对不同性质之财产,于“静之安全”与“动之安全”之间进行权衡。事实上不管那种立场,其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只能是直接取得该物权,而不是使无权处分行为本身,成为“有权处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要研究无权出卖他人之物权本身效力,需于比较法上进行进一步之探讨。《德国民法典》第185条规定:(1)无权利人就某一标的所为处分行为系经权利人允许而为之的,该项处分发生效力;(2)权利人追认无权利人就某一标的所为的处分,或处分人取得该标的,或处分人被权利人继承且权利人对遗产债务负无限责任的,该项处分发生效力。于后两种情形,对该标的做出两项以上相抵触的处分的,仅最初的发生效力。[⑥]德国学者一致认为,这里的效力仅是针对处分行为而言,故于德国学者看来无权处分而为之处分行为之效力待定。《台湾民法典》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1)无权利人就权利标的物所为之处分,经有权利人之承认始生效力;(2)无权利人就权利标的物为处分之后,取得其权利者,其处分自始有效,但原权利人或第三人已取得之利益,不因此而受影响;(3)前项情形,若数处分相抵触时,以其最初之处分为有效。台湾此条规定系继受《德国民法典》第185条,学者基本上采德国通说之观点:无权处分之处分行为效力待定。至于法国与日本,由于采物权变动之意思主义模式,其物权效力决定于债权之效力,故不存在无权处分在处分行为本身上之效力。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出卖他人之物于物权处分行为上之效力,我国现行法采物权处分行为与债务负担行为同其命运理论,以负担行为决定处分行为之效力。从其法理上分析,似承认二者独立为宜。当然我并不是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与独立性之理论,关于物权行为理论本身,于我国有诸多之研究,争议不少,在此,笔者不再检讨。至于在否定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同命运性”之后,出卖他人之物于物权上之效力,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性:无效与效力待定。基本上,效力待定为世界采物权形式主义国家所肯定。至于我国,采何种理论,笔者认为采出卖他人之物于物权处分行为上无效为宜,现论述如下:首先,如前面所研习那样,对于在承认出卖他人之物于负担行为上之有效性的前提下,则买受人无论于何种情况之下,其实际利益不受任何之损失,针对权利人而言,由于无处分权人出卖其物,其于处分行为上无效,则其并不丧失其权利;其次,在我国虽然有物权善意取得制度,一定情况下,买受人仍可以直接取得权利之标的,但是我国《物权法》之善意取得制度要求无权处分人对其权力标的之占有必为居于本权而占有,本权者,从何而来,其必要求无权处分人对权利标的之占有,必须根据权利人通过某种方式赋予而取得,于此种情况下,权利人对其赋权不谨慎而负责,实符合公平正义之原则,事实上,权利人仍可以向无权处分人提出侵权之诉,以维护其权利;最后,有不少学者,提倡采效力待定说为适,笔者认为不妥,在承认出卖他人之物于负担行为上之有效性以后,实际上采何种学说,于买受人与权利人影响不大,唯其需注意者,乃将此效力命运决于第三人之追认上,于确定物权权属,便于物之流通,发挥物之功效无益,当然如买受人仍有意买之,而且权利人有意卖之,其可直接通过买卖合同而为之。第三部分:“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之关系
“出卖他人之物”可谓是法学上之精灵,困扰实务界数十年,为彻底究明其“本性”,不克济事。[⑦]王泽鉴先生认为出卖他人之物非属无权处分之行为,笔者认为此观点有所不适,出卖他人之物,可从两方面观之:(1)出卖他人之物,于负担行为上之效力,即出卖他人之物之合同,此当然与无权处分无关,于符合合同有效要件之下,该合同有效。(2)出卖他人之物于物权上之效力,出卖他人之物,乃出卖人无出卖之权时而为之,当为无权处分。于我国,立法与实践严重混淆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之关系,实应进行检讨,对出卖他人之物,从不同行为性质进行分析检讨,理清其与无权处分之关系,唯有如此,才能制服“出卖他人之物”之精灵,恢复其本质,认识其原貌。
第四部分:“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于未来民事立法之体现
“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⑧]经验者,系指法律于社会之适应性与需要性而言。然而,实践中,部分学者以现行法律为逻辑起点,去屈就学说理论,以迎合法律之规定(此处严格区分对法律之解释)。学说理论如妥当且适于社会之需要,理应法律去主动适应理论,而非理论去迎合法律,唯有如此,法律才更具生命之力,司法才能进步,法制才能完善,学说理论方能完成其应有之使命。
故笔者,认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于未来民事立法中,特别是于未来民法典编撰之中,应有所体现与完善,可于未来民法典中作如下之规定:(1)于债编中,直接采纳处分权限并非负担行为之构成要件理论,即承认出卖他人之物合同有效;(2)于物权编中,直接规定无权处分他人之物不发生物权效力。如此,期能理清立法之规定,司法之实践,学说之理论三者关系,于学者研习此问题有所裨益。
[1] 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3] 王利明著:《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07年
[4] 梁慧星主编:《物权法》 法律出版社,2007年
[5] 周大伟编:《佟柔中国民法讲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①]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五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修订版,38—39页。
[②] 参见:《佟柔中国民法讲稿》 周大伟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197—200页。
[③] 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587—618页
[④]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修订版,134—135页。
[⑤] 参见梁慧星,陈华彬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6月第四版,208页。
[⑥] 参见陈卫佐 译注:《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6年2月第二版,60页。
[⑦]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修订版,136页。
[⑧]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修订版,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