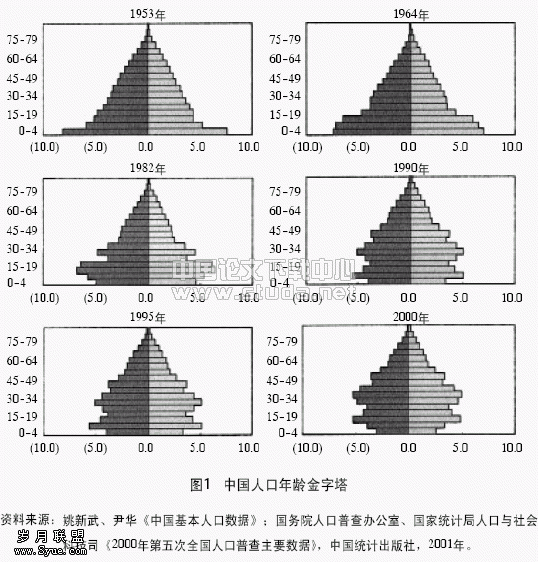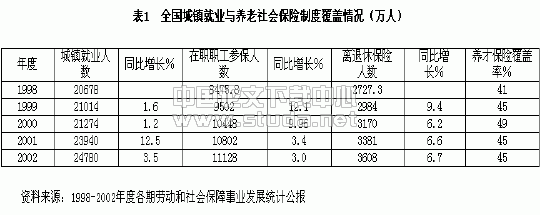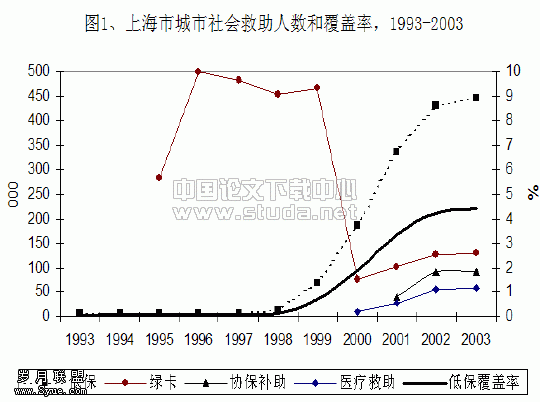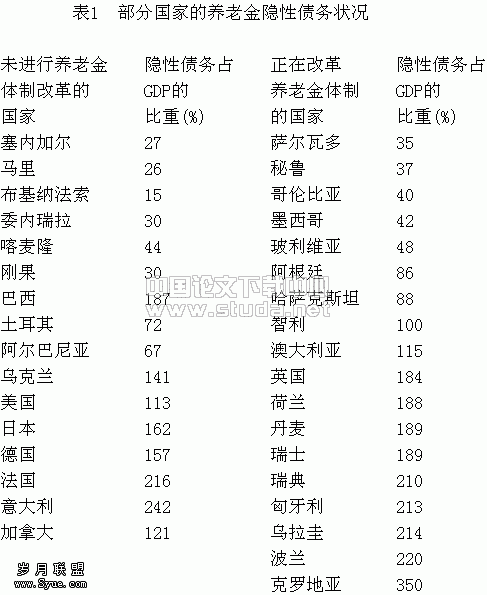家庭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作用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7
[关键词] 东西方文化比较 社会保障 家庭
对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比较分析,近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学界热情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中国学者从(宗教)、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学、心等学科,研究东西方社会文化的不同特点,社会演进的不同路径,并对其绩效进行评述,所得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中国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先生研究东西方社会结构,揭示出家庭这个社会单元在东西方社会结构中具有不同的特征。梁先生考察了社会结构中的三个基本元素:个人、家庭和团体,认为在东西方社会结构中,这三个要素的排列组合不同,所居于的地位不同,所起的社会作用不同 。从历史文化延续传承的常态看,西方社会结构的重心居于个人与团体之间,而家庭是很次要的。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林义先生认为,西方社会结构的这一特征构成社会保险首先产生于西欧的社会基础与条件 。
一、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家庭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和基础
(一)中国家庭的核心地位和结构特点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在社会结构与功能方式上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庭是社会生活的核心,是社会制度的基础;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或团体,构成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石、社会制度的原型、社会秩序的要素;是家庭伦理构成社会伦理和治国方略的基础,家庭结构构成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的基础,家庭功能构成社会功能和国家职能的基础;社会和国家就是以家庭为基础在结构上的放大、在功能上的加强、在伦理关系上的翻版与发展。
传统的中国家庭文化提倡多子多福,一对夫妇一般养育4~6个孩子。其中,长子是家族传种接代、家长权威传承、家庭财产继承、家庭关系维系的主要依靠和后继者。典型的中国家庭结构是多代同堂,少则三代多则四代、五代同堂而居。未婚子女与父母和祖父母同住,已婚子女或者分家或者不分,但崇尚的是不分。多代多子一锅吃饭,一门出入,同耕一块田地、同尊一个祖先,被尊为典范,受到四乡八里的尊重和敬佩。
居于家庭结构最上层的是家长。中国传统家庭的家长(一般为男性,偶见有以女性为家长者,但不具有必然性)不能完全等同于家庭的户主,他不仅对外代表整个家庭,而且对所有家庭成员来讲,他总是意味着权威、掌握着权力,他是“家规”的制订者、执行者和维护者,是家庭事务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是家庭生产生活的组织者和协调者。他在家庭处于核心地位,是家庭的统治者。在家长的统治下,家庭成员实行“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的内在制度规范,“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二)中国家庭的基本功能
中国传统家庭在传承历史文化传统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三大基本功能。
1、组织家庭成员参加农耕劳作或手工经营,并从中获得收入。中国不少传统名牌产品,如张小泉剪刀、全聚德烤鸭、内毕升布鞋、同仁堂药丸等都是在家庭作坊中孕育产生的。
2、维持全体家庭成员的衣食住行。传统上,住所对有钱的大家庭来可能是豪宅,相对讲究一些,但对于穷困家庭则可能只是一处窝棚。行主要靠双脚,有钱人家是靠轿子。而一日三餐对家庭而言最为重要和基本,它构成日常家务的主要内容。每逢喜庆节日,做一身新衣是重要标志,也是家庭成员期待的主要愿望,特别是过大年,有钱人家要给每个成员(包括佣人)做新衣,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也要想方设法完成做新衣的目标。
3、为全体家庭成员提供生活保障。这是中国传统家庭更为重要的功能,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传统中国家庭的保障范围十分宽泛,保障功能也比较强大,形成了特殊的保障机制。前述家庭提供的衣食住行功能,其实已具有了保障的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家庭为家庭成员提供了包括养老、医疗、生育、救济、福利等全方位的保障功能。举养老为例,我们知道,“养儿防老”是传统中国夫妇生育子女的基本理由,就是说传统家庭是通过生养子女来解决养老问题的。用现代社会保障的观点来看,生育和抚养子女的花费,可以被看成是正值劳动年龄的父母为将来养老而缴纳的保障基金。这笔基金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在逐年缴纳和积累,在子女的逐步成长中得以保值与增值。当父母老年丧生劳动能力时,当子女成年进入劳动年龄时,原先所缴纳的养老保障金就开始给付了,直至父母去世。从传统家庭的角度看,这种养老基金的缴纳、积累、增值以及给付,是一个十分自然的“天经地义”的过程,是一个衔接得十分平滑的过程,似乎找不到过渡的节点或环节。其他如医疗等保障的情形也大致如此。总之,在中国传统家庭中,老人的生老病死风险全由家庭提供保障;家庭保障的费用支出全部由家庭承担,保障基金的积累增值、代际之间的转移支付等等过程,一应在家庭中完成。家长统筹安排,其他成员各尽其责。
二、中国传统家庭保障功能的性质特征
中国家庭的保障机能经由儒家等传统文化精神的滋润得以强化和完善,呈现出如下特殊规定性。
(一)以家庭为载体,自然实现保障功能,自然完成保障过程
从相当意义上讲,家庭与家庭保障成为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凡家庭就具备保障功能;凡提供保障功能的家庭才成其为家庭,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家庭的生存与发展壮大的过程,就是家庭实现保障的过程。正是这种特殊的结构及其保障功能,使得传统中国家庭在社会结构中居于基础和基石的地位,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载体。可见,中国家庭的结构功能以及由此决定的家庭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与西方家庭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我们在考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创新,研究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时,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制度性基础和逻辑起点。
(二)处于中年阶段的家庭成员承受着 “双重缴费”的重负
在中国传统家庭保障模式中,中年家庭成员既要为赡养丧失劳动能力的父辈缴费,又要为抚育下辈缴费。“上有老下有小”,说的就是这种状况。因此他们成为家庭的基柱,一个家庭中中年家庭成员的多寡及强壮与否,往往成为决定家庭是否稳定与兴旺的主要因素。考察中国传统家庭演化史我们发现,“双重缴费”的重负之所以没有压塌家庭的基柱,是因为中国传统家庭建立了“生育多子”的内在制度,以此保持家庭人口年轻化结构,从而实现减轻“双重缴费”的家庭保障对每一个中年劳动成员造成双重重负的功能,由此使家庭保障机制不至于在一两代人的时间跨度中陷于崩溃。这就是中国“多子多福”历史文化传统的制度根源和经济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多子”确与“多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应当看到,一旦失去人口结构年轻化的条件,面对不断加强的人口老年化趋势挑战时,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中年人(可以等同于过渡方案中的“中人”)缴费负担过重的问题,为寻找新的解决办法而作出努力和抉择。
(三)保障机制具有一定的脆弱性
家庭保障虽然可以比较顺利地实现代际间转移的纵向调剂,但因囿于一个家庭(一般不会超出一个家族)的范围,其横向调剂则存在着许多制度性障碍,如财产所有制、家族血缘关系、家长制管理决策方式、地理条件等等限制。因此,家庭保障虽有“船小好调头”的优势,但也确实存在“难抗大风浪”的缺陷。历史上,一些原本颇有实力的家庭,只因家庭成员(尤其是中年家庭成员)的病重或病逝而日益破落衰败,此类实例也屡见不鲜。家庭保障的削弱成为家庭破落衰败的主要标志。但应当看到,家庭保障的脆弱性,为发展社会保障,为使社区在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安排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提出了需求。三、家庭的异化特性和超稳定性对其保障功能的保护作用
从形式上看,东方的家庭和西方的团体有某种相似之处。它们都由若干个人(个体)所组成。但从结构分析看,家庭的结构不同于团体的结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西方团体的架构是平面或平行的,成员之间关系是平等和互助的;东方的家庭则构建起立体或层级结构,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由上下贵贱以及命令与服从来规范的。中国传统家庭这种特殊结构,导致了中国家庭对家庭成员的异化,家长对家庭其他成员的异化,使由个人组成的家庭最后演化成家庭成员个人的异己力量。这种异化的力量,反过来又维持和强化了中国传统家庭的超稳定结构。这是中国传统家庭的显著特点之一。
中国传统家庭对家庭成员个人的异化特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家庭中个人权利与义务的失衡
西欧社会结构中,家庭功能的弱化或不足促使个人的感情归属转向团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的团体在相当程度上承接了类似于东方家庭的功能。但是西方团体中个人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团体中的成员要享受多少权利就必须履行多少义务,履行了什么义务就可以享有什么权利。但在中国传统家庭中,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等的。对家长而言,权利和权力是主要的,义务是次要的,家长本身就代表着权威,就是权力的化身。对家庭其他成员而言,其义务与其权利相比,要大得多、多得多、重得多,其权利是微不足道的。权利与义务的失衡,使家庭(以家长为代表)对家庭其他成员产生异化,使家庭成为异己的力量。一方面是家长行使权力、支配和命令其他成员的自由,另一方面则是其他成员履行义务、接受支配、服从命令的“自由”,他们不敢不如此“自由”。
2、强调个人对家庭的绝对服从与依附
中国传统家庭不仅强调义务多于权利,而且强调个人对家庭的绝对服从与依附。由于家长本身代表着权威,就是权力的化身,相比之下,其他家庭成员在家长面前就只有战栗、恐惧和绝对服从的份了。这种绝对服从与依附延续了千年,期间偶有抗争和反叛,但多半以屈服和就范而告终。绝对的服从与依附导致绝对的异化,在只允许家庭(以家长为代表)享有滥施淫威自由的同时,剥夺了其他成员略示些微不服的自由。
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是导致中国传统家庭中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强调绝对服从和依附的文化根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义务而忽略权利、强调内省而反对抗争、强调适应而忽略改造。这样的文化倾向反映在许多伦理教义之中,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它们在强调自上而下的控制、支配和命令权利的同时,更多地是教诲和强化自下而上的服从、接受和认可的义务。
3、彻底否认个人对家庭的退出机制
西方的团体是适应人们感情寄托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从本源上讲,团体就是一个自由的民主的社会单元。当需要时个人可以加入团体,并在其中履行义务和享受权利;当不再需要了,个人可以退出团体;或者当个人不需要这个团体而需要另一个团体时,就可以退出这个团体而加入另一个团体。退出机制的存在,限制了西方团体对个人的异化倾向。但在中国传统家庭中,个人一旦加入家庭,或出生于一个家庭而成为家庭的一员,家庭的制度安排本身就彻底地否认了个人对家庭的退出可能性。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家庭对家庭成员个人来讲,不存在任何有关退出机制的制度安排。
退出机制的缺失,构成中国传统家庭对个人的异化倾向获得强有力保护的制度基础。无论家庭(以家长为代表)多么专制、强权、残暴,其他成员绝无退出的可能性。不能退出,没有其他选择,就只能服从和就范,所以,家庭绝不会因为其专制、强权和残暴而遭受解体的打击。没有了解体的威胁,家庭就摆脱了根本性的反抗力量或制衡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基础上,中国传统家庭构建起了超稳定性结构。
自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家庭的超稳定结构,经受了文明的冲击,虽然其结构和功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也还会继续发生变化,但工业文明浪潮的冲击,并没有动摇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根基,中国绝大多数家庭(特别是家庭)依然维持了家庭的主要功能,包括保障功能。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在社会进步和新技术浪潮冲击下,家庭的功能并不一定具有日益衰减的必然趋势,相反家庭可能在新的条件下获得新的功能。由信息技术引导的后工业社会,具有使社会生产方式向分散化、小型化和家庭化的趋势,家庭生产方式可以在信息时代得以复活,从而使家庭的职能在新的时代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的浪潮中,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包容性和极强的生命力,一定会争取到更大的发展空间。有中华文化的依托,中国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不会遭到实质性的损害,其应有的地位一定会寻找到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发挥作用的方式。坚持这一发展观,是我们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创新的最深厚的基础、最可靠的根源和最不可缺少的参照维度。毕竟社会保障的基点是个人,保障的对象是个人。而在中国社会中的个人,其基调和底色则是家庭。
四、中国社会保障改革应当尊重和依托家庭保障的作用
家庭在未来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作用,可以表现在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失业保障等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养老保障方面。在农村,绝大多数家庭仍然是三代同堂,因此祖父母的养老可以由自身早先的积累——儿孙——来承担。在城市,家庭规模的小型化趋势比较明显,中年夫妇带未成年小孩的核心家庭所占比重比较大,空巢的老年家庭比较多。 虽然,多数城市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有所削弱,但对于主干家庭、联合家庭、隔代家庭来讲,家庭的养老保障作用还是很重要的。
——医疗保障方面。对医疗方面的支出,原本就是家庭总支出的一部分。在农村大家庭中,这仍然是普遍现象。大多数情况下,家庭遇有大病灾害,往往要通过对外举债才能度过危机,若无法借债则往往有倾家荡产甚或家破人亡的灭顶之灾。因此,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解决大病风险的问题,而一般的疾病则可以依靠家庭固有的保障功能加以解决。
——失业保障方面。失业风险与家庭的关系最为紧密。一方面失业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失业者又特别需要家庭这个温馨港湾的精神慰藉。家庭对失业者的精神慰藉,正是家庭在失业保障方面所能发挥的特殊作用,这种作用是其他保障方式所难以实现和难以替代的。此外,家庭的平时积蓄可以成为失业保障的来源之一,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是对失业者实现保障的最可靠、最直接的互济与调剂的来源。
上一篇:农民参加社保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下一篇:我国养老保险私营化可行性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