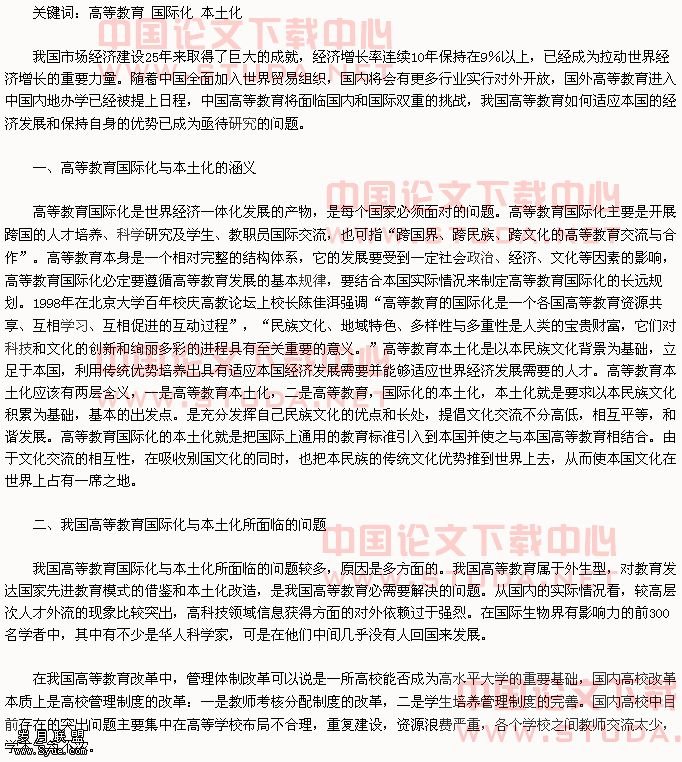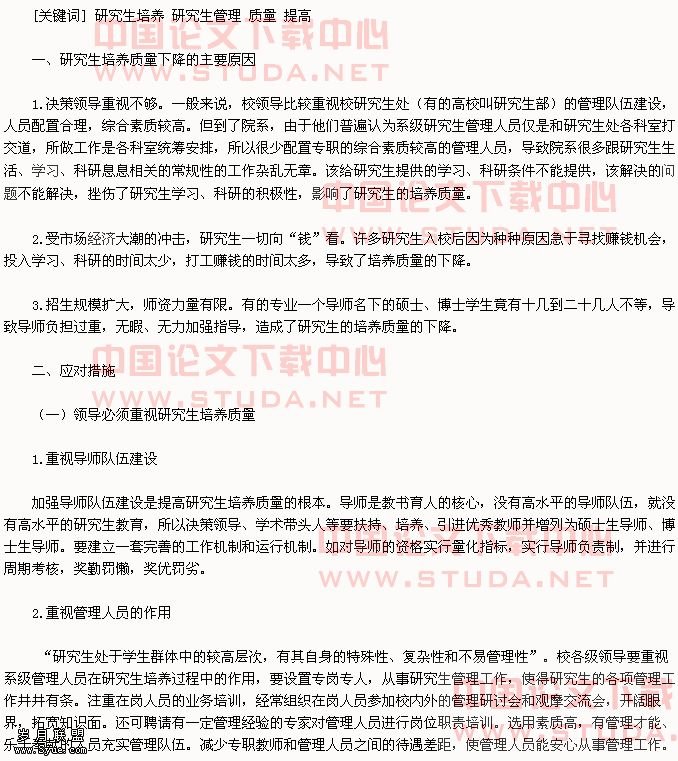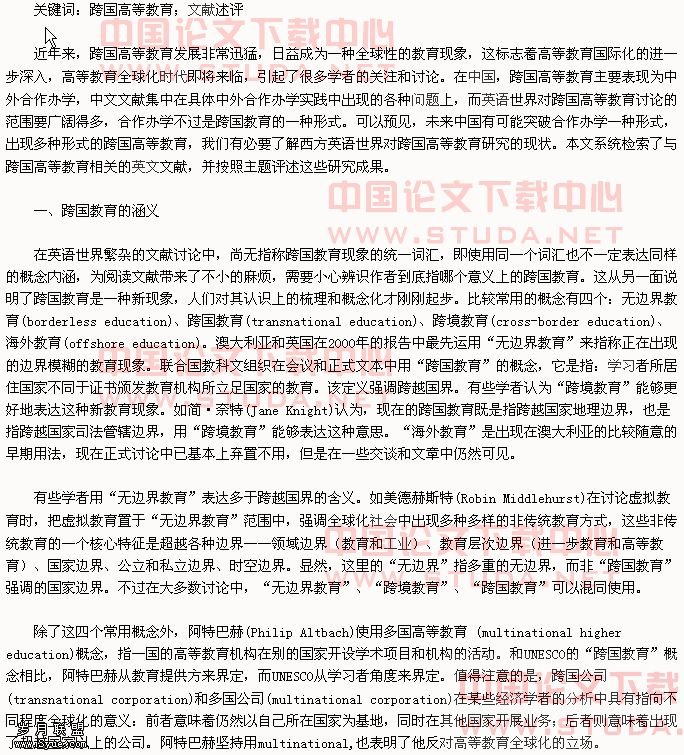大学的理念:形式与性质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6
进行这样一种简略回顾,是想讨论两个涉及到大学理念的问题:第一,大学作为一种社会团体的组织形式,到底是单个人的集合(类似于society),还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即所谓的unity),而这二者的区分,又与近代以来随着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而对社会、国家所作出的重新解释有关,它在根本上所涉及到的是个人与集体(大学里的所有人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学)之间的关系;第二,大学作为一类独特的社会团体,既然其在起源上与宗教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而宗教组织或宗教活动又要求着某种自觉自愿意义上的“虔敬”(reverence),这种“虔敬”无疑与对某种超验性存在的信仰有关,那么以此推想,进入大学或大学自身在性质(品行、德行、资质)上应该有着怎样的非一般性的要求或理想?
大学无疑是一个社会团体,而且首先是一个民间或民办的社会团体。问题在于:这个团体中的人是靠什么走到一起来的?或者说,维护这一团体存在的社会秩序是何以建立起来的?当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时,是从单个的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出发还是首先把学校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学校当然是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的,但学校同时又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这里的“整体”一点也不抽象,它就指的是“某个具体的或特殊的社会团体及其特殊的体制与表象”。比如我们并不认为就单个的人而言,同济大学的学生或老师与复旦大学的学生或老师有多大的差别,但同济大学与复旦大学作为两个不同的社会团体,却在具体的体制与表象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也正是这种不同,使得生活在同济与复旦校园里的人有了这样那样的差异。是从单个的人出发还是从整体出发,法国社会学家路易•迪蒙(Louis Dumont)在《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一开始就说,这几乎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学。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作者说,作为现代意识形态的个人主义,其实主要起源于犹太-基督教的遗产,起源于“人是与上帝相关的个体”这样一个观念。作者说,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希腊化的过渡中,有一个大大的“缺口”(中断),这就是个体主义的突然出现。“城邦曾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是自足的,而现在被视为自足的是个体。这个个体或被视作事实,或被伊壁鸠鲁、犬儒派和斯多葛派视为理想。”(见该书第24页)
也正因为出现了这样的自足个体,才有了以后的社会契约论,有了人与人的从属关系,有了出世与入世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有了与个人或人与人的关系有关的自由、平等、权利以及财产权、继承权之类的观念。当然,按照作者的说法,也才有了希特勒用“伪整体主义”伪装起来的个人主义,因为他所强调的“整体”只限于“种族”,也就是说,他用生物性的个体摧毁了国家这一实在性的整体,然后再把生物性个体缩减为同样具有生物性的阶级、党派、种族;这种缩减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它突出了生物性个体间的“人与人的弱肉强食”(由社会达尔文主义演变而来),而且认为这本身就是一切价值的尺度。
这里面更深层的含义在于,当社会成为单个人的组合(society)时,人们内心深处就会产生一种“革命的反弹”,这就是“unity”的复兴:人们开始重新渴望建立真正的宗教,渴望着人与人内心的相遇与相通,渴望回到古代希腊的城邦制度,因为在城邦里个人与共同体之间有着一种价值上的共享结构,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几乎也就可以理解为在现代性浪潮中出自我们现在内心深处的某种渴望。
问题在于,我们有过“真正的宗教”,有过“个人与共同体在价值上的共享结构”吗?如果有,恐怕就只能在孔子及其弟子,在汉代以后的太学以及晋代以后的国子学乃至朱熹、王阳明等人的书院中去寻找,当然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这种“大学”越为世俗的权力所控制,其脱离那种“真正的宗教”也就越远,这一点,在性质上与西方大学是否从一开始就被授予了某种脱离地方当局的“特权”有类似之处。
这一点也同时告诉我们,无论是从单个的人出发还是从整体出发,大学作为具有某种特殊性质(其实也就是与对某种超验的、理想的、非功利的存在的追求与探索有关)的社会团体,其实也就体现着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追求与探索上的品行、德行和资质。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有怎样的大学,大学里的人对自己的大学的“体制与表象”有着怎样的感情,是否认可其秩序以及在价值观念上是否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学有着某种共享结构,这几乎就能反映出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对自己的国家所具有的思想感情。
基督教除了为我们提供了个体主义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外,至少在中世纪还提供了一整套的教会制度、修身规则、管理办法以及强行灌输的思想原则。所有这一切,都披着“信仰”的外衣,而且似乎在管理制度上越严格也就越能体现出信仰的力量。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后来在启蒙思想家那里所表现出的对宗教的批判,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那种宗教制度的批判,他们的关切点在如何以人的“灵魂得救”取代外在的“赎罪形式”,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更新教会社会。于是“虔敬”才成为教会团体的基础,而教会生活也就成为有虔敬之心的人的自愿组织,并被理解为人的社会结合的最完美的组织形式。
上一篇:大学人文精神的信仰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