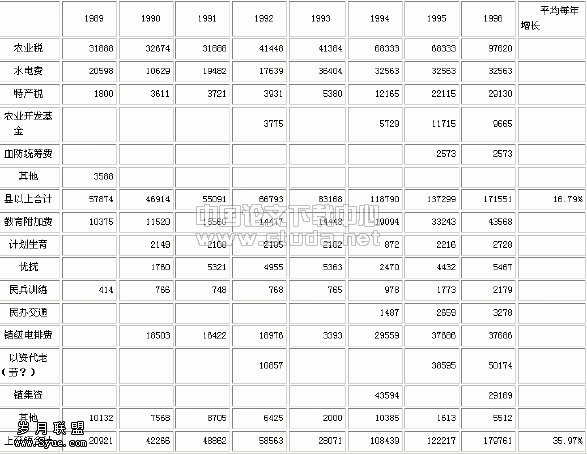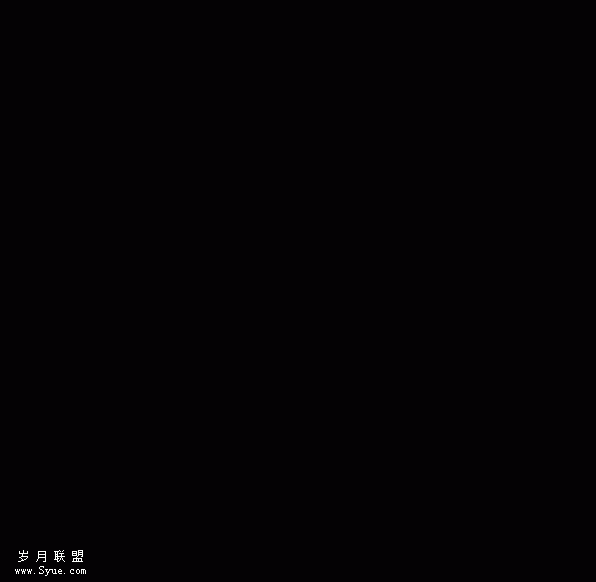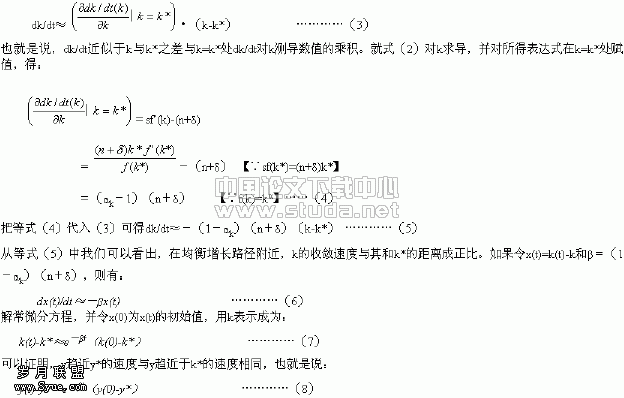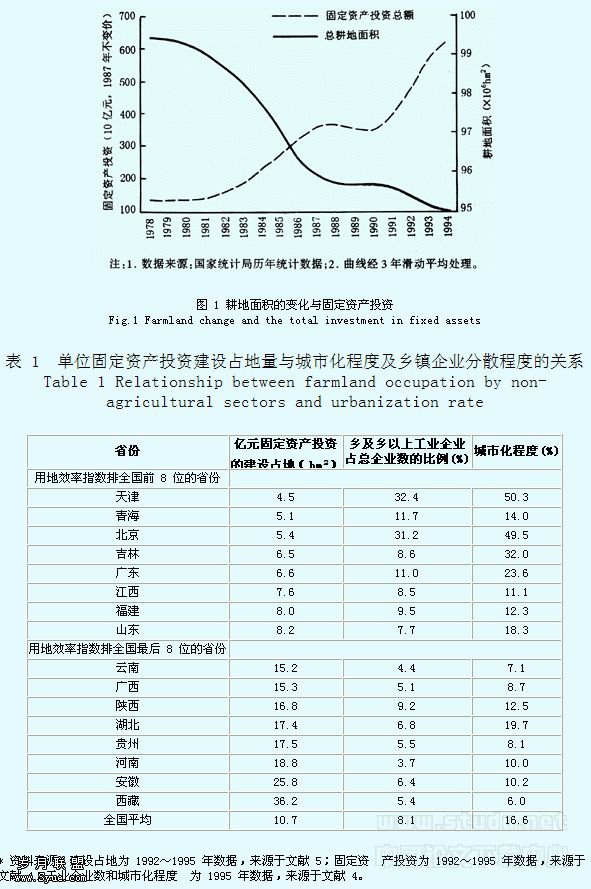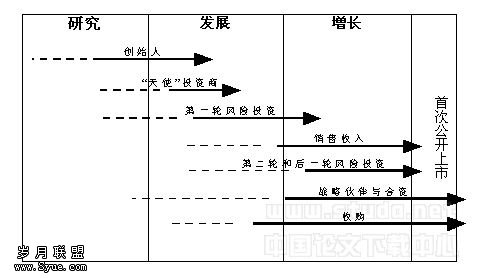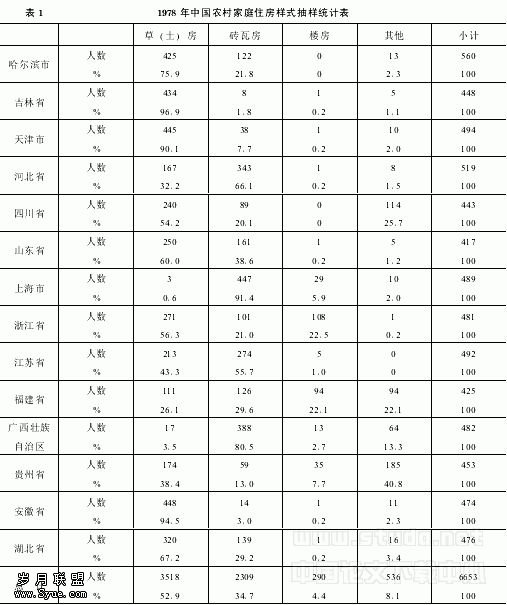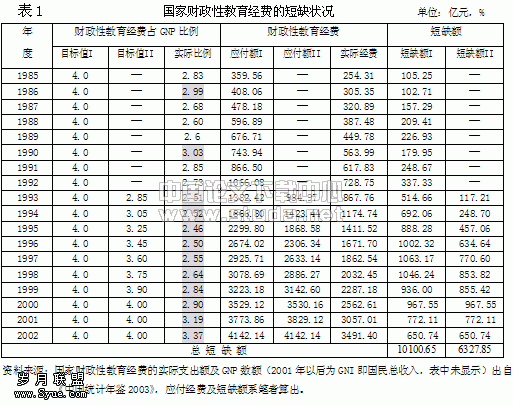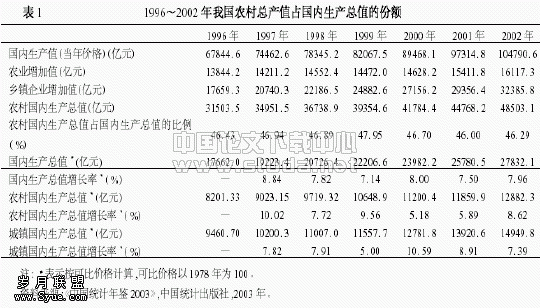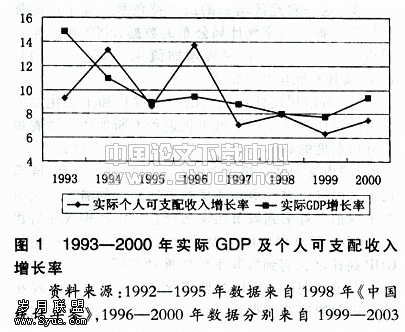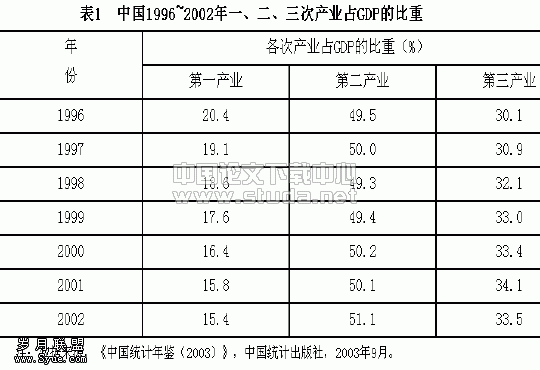县银行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新县制”建设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南京政府一向是采取削藩政策,致力于消灭地方的军事、政治势力,”②因此,南京国民政府自它建立的那天起便开始了与各省大小军阀进行连年的争斗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红色政权进行疯狂的军事进攻,到1934年才在表面上确立了自己在全国的统治地位。鉴于多年来同各地方军阀打交道和与红色政权斗争的经验教训,为了强化国民党中央的集权统治、防范各省地方异己势力的坐大、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政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国民政府便打着“完成总理地方自治理想”的旗号,决定在全国推行分县自治制度。
在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割据时期,地方的一切行政、财政和军政大权几乎都控制在各省大小军阀手中(这是军阀割据得以存在的前提和条件),作为基层行政组织的县级政权位卑势微,难以对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产生牵制作用,有的干脆就是割据势力的走狗。在国民政府看来,欲削弱地方势力、消除军阀割据,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提高县级政权的地位,扩大其权限,实行分县自治制度。
但要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搞县级地方自治没有相应的财力做后盾是很难成功的。这点国民政府心知肚明,因此,1934年当国民政府决定提高县(市)地方政府的职能权限时,财政部长孔祥熙随即提出了《财政收支系统法》,建议将国家的财政收支系统由过去的中央和地方(地方财政以省为主体,县附属于省)二级制改为中央、省、县(市)三级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省一级的财政,也有利于建立以县为本位的财政收支系统。这一建议很快被国民政府采纳,到1937年3月正式颁布《财政收支系统法施行条例》,并通令各地自1938年元旦起实行。但不久因全面抗战爆发,该《条例》未能按原计划付诸实施,国民政府的分县自治计划也就没能搞起来。
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政府提出了所谓“抗战建国同时并进”的口号。为适应这一需要,决定对县级基层组织机构加以彻底的调整和改进,一方面是便利政府各项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推行,筹粮筹款以应抗战之需;同时亦欲趁机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于是在1939年9月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正式在国统区实施“新县制”建设。
新县制实施的初期要做的工作很多,如清查户口、建立各种自治机关、评估地价、铺桥筑路、兴建学校、开垦荒地、举办各种合作事业,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有相应的资金支持。但资金从何而来?如果仍沿袭过去县财政附属于省财政的旧体制,不建立以县为本位的自治财政,新县制建设就会因无足够的资金保障而无法开展下去,于是国民政府在1940年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决议案》,1941年11月又公布《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与1937年3月颁布的《财政收支系统法实施条理》不同的是:《决议案》和《纲要》中,将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自治财政两大系统,原来的“省级财政”纳入“国家财政”系统,取消了省级财政的独立地位,确立了以县(市)为单位的自治财政体制。《纲要》中确立的县级自治财政自1942年元旦起执行。
上述关于财政收支系统的变更,表明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省级政权的控制,县级行政组织地位有所提高,权限也较过去扩大了。
建立县自治财政,势必设立县公库,而“县公库亦须有一机构为之代理。”那么,以什么样的机构来代理县公库最合适呢?在近代社会,能够代理县公库的莫过于各种新式机构。其次,新县制建设中所需之资金“若完全由县财政开支,自属不易,必须有金融机构为之相当之接济。”[2]也就是说,县财政只有得到各金融机构在资金上的有力支持,才能伸缩自如。第三,县财政既已独立,则各县的财政收支就主要靠自己在本县范围内自行解决了。而本县财源能否丰裕或有保障,同当地经济与否息息相关,这就要求各地在推行新县制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把发展社会经济放在极重要的位置,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更何况发展社会经济本身就是新县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发展经济的资金问题如何解决?这又是一大问题,特别是在新县制实施的初期,百废待兴,经济凋敝,资金极度缺乏。上述这些,都迫切需要有一健全的金融组织来“肩负新县制实施过程中各项自治设施之金融使命。”[3]可见,“实行新县制,如无适当的金融制度来辅助,则地方经济建设难免有脱节之处。”[4]
但由于当时的广大在战乱和封建剥削的重压下,已残破不堪。而农村本来就不多的一点资金又多通过地主之手流入城市,使得农村经济的复兴更加无望。虽然国民政府曾多次提出要复兴农村经济,并要求和鼓励国家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各省银行及其它商业银行到农村设立分支行,向农村提供资金援助,但因种种原因,他们多不愿将其分支行普设及于各县,而各县中原有的那些前资本主义的旧式钱庄、票号,或则其性质决定,或则已日渐衰落,也难以承担起复兴农村经济之使命。在此情况下,不少朝野人士认为能担当协助县地方财政、调剂县、自治经济等重大使命的惟有以县为本位的“县银行”。在新县制实施过程中,县银行可以担负起“各项自治设施之金融使命。”[5] “县银行在新县制下,将在养的方面尽其职责,扶助人民增加生产,发展地方经济”,最终达到协助政府完成新县制建设这一目的。因此,他们认为“县银行为新县制下唯一合理之金融机关。”[6]主张“为配合新县制起见”,“县银行必须设立。”[7]
县银行是民国时期出现的一种以县境为营业区域,以调剂地方金融、扶助地方经济建设为主要业务,且具实业银行性质的地方基层金融机构。最早出现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5年),广为推展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40年国民政府颁布《县银行法》),到全国解放的前一年,仅在财政部登记注册的县银行就达560余家,且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等大后方,其中以四川设立最多,几乎每县都有一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决定在其统治地区普遍设立县银行,虽然主要目的是为了复兴农村经济、增强经济实力以适应抗战需要,但也不排除最高当局的另一个重要用意,那就是配合新县制建设,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等。尽管《县银行法》中没有这方面的明文规定,但人们心知肚明。诚如当时人瞿仲捷所言:“中央公布《县银行法》约在《县各级组织纲要》颁行之后一年,然决定付诸普遍实施则均为时不久。一属于县地方与司法组织之改进;一属于县地方金融机构的确立,此种双管齐下之举,实寓有相依相存之用意”。“总括以言,吾国今日为抗战、为建国、为民生,均须建立县本位金融制度,而县银行实为此种制度之中心。”[8]可见,国民政府普设县银行,自有其政治动机和意图。
由上所述,我们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新县制建设虽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即通过实施新县制来满足当时民众普遍要求建立民主政治的心理,缓和社会矛盾,加强中央对地方基层政权组织的控制。但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实施新县制对于政府各项战时政策的推行、落实,向社会征集人力、物力、财力以支持抗战有一定进步意义。至于在这一过程中,县银行的设立对当时的新县制建设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本人持相当的保留态度,因为事实上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真正意义上的新县制建设始终未能搞起来。
[1] 《孙中山集·外集》第35—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② (民国)《财政年鉴》第3编第10篇。
[2] 童蒙正:我国县银行之过去与将来。载《各国银行制度》(民国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编印)。
[3] 邹宗伊:《中国战时金融管制》第47页。
[4] 刘如冰:县银行应有之使命。载(民国)《银行通讯》第2卷第9、10期合刊。
[5] 邹宗伊:《中国战时金融管制》第47页。
[6] 童蒙正:我国县银行之过去与将来。载《各国银行制度》(民国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编印)。
[7] 再论省县银行之合流。载(民国)《金融知识》第4卷第1、2期合刊。
[8] 瞿仲捷:对县(乡)银行的认识。(民国)《经济汇报》第3卷第9期。
下一篇: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