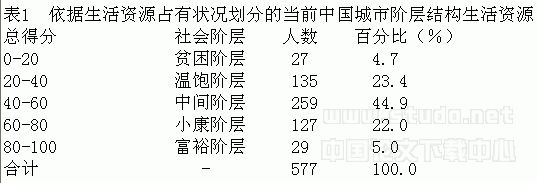捍卫科学——在理性范围内
让我们记住,从一个错误的极端到另一个错误的极端,这类愚蠢的事情是多么经常地发生。[托马斯·里德][1]
对的态度是各式各样的,一个极端是无批判的崇敬,中间经过不信任、怨恨、嫉妒,达到另一个极端,即诋毁和公开的敌视。我们在下述问题上常常被弄得混淆不清:科学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科学是如何做它所做的那些事情的,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社会在科学中的作用,科学与文学的关系,科学和宗教的关系,……
尽管很复杂,上述混淆还是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科学主义的和反科学主义的。前者是对科学的尊崇态度的夸张形式:例如,随时准备把科学所做出的任何断言当作权威的判断加以接受,随时准备把对科学或科学实践者的每一种批评当作反科学主义的偏见加以拒绝。后者是对于科学的怀疑态度的夸张形式:例如,随时准备看出对力量因素的兴趣在每一个科学断言中起作用,或者,随时准备接受对科学或科学实践者的任何这样的批评,它们削弱了科学所做出的夸耀,即告诉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
由于一种惊人的歧义性,使得清理上述混乱成为更加迫切的事情。有时候,“科学”一词被简单地用来指称一些学科:物,化学,生物学,如此等等,通常还指人类学和心理学,有时也包括社会学,学,诸如此类。但是,经常地——比不这样使用更为经常——“科学”及其同类词被赋予一种荣誉性用法:广告商要求我们使用新的、科学的洗涤剂,以便把我们的衣服洗得更干净;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教师要求我们科学地推理,使用科学的方法;专家证人得到信任,其理由是他们所提供的是科学的证据;通灵术,圣水,顺势疗法,或按摩脊柱法,或针刺疗法,则被贬斥为“伪科学”;在怀疑这个或那个断言时,我们抱怨说:它缺乏科学的解释,或者需要科学的证明。如此等等。“科学的”逐渐成为适用于所有目的、在认识论上起赞扬作用的一个词,意味着“强有力的,值得信赖的,好的”。这样一来,毫不奇怪,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有时是如此嫉妒,坚持认为他们有权获得“科学家”头衔。同样毫不奇怪的是,在其他领域如“管理科学”、“图书馆学”、“军事科学”、“殡葬科学”,其实践者是如此急迫地宣称他们所从事的是“科学”。
由于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荣誉性用法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用法又是不幸的。它模糊了另外一个明显的事实:在列为科学的那些学科中,并非所有的实践者,或者并非只有这些实践者,都(才)是好的、诚实的、彻底的、成功的探究者。这一事实已经诱使某些科学家毫无成效地关注在真正的科学和其他冒牌货之间如何划界的问题。这反过来又激起了对如此分类的学科的妒忌,鼓励了某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即其他领域的实践者不适当地模仿自然科学的风格、专门术语和数学化形式,等等。并且它也激起了对如此分类的那些学科的愤慨,鼓励了反科学主义的态度。有时候,你能觉察到妒忌和愤恨因素在同时起作用:例如,在那些自我标榜的人种方法学家那里,如他们经常自称的,他们在从事对科学的“实验室研究”,观察着生产铭文的事务中的部分复杂工艺;或者在“创造科学”那里,人们不得不勉强承认这种自我描述的修辞学夸张。并且(这正是我在本文中所主要关注的),这种荣誉性用法就等于直接承认:科学,也就是在其描述意义上的科学,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骗取信任的把戏。
科学不是神圣的:它是彻底可错的,不完善的,其成就是参差不齐的,经常是笨拙的,有时是污秽的,理所当然是不完美的。不过,它也不是骗取信任的把戏:在人类认知事业中,无论如何,自然科学确实是其中最为成功的。
承认这一点,根本不是要否认其他类型的探究——例如,,或哲学,或法学,或学——的合法性,贬低它们的成就;也不是要否认文学或的合法性,贬低其成就。不过,这给我们提出了下面一些严重的问题,即列为科学的那些学科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差别,如果有差别,其差别何在?其他类型的探究与那些列为科学的学科之间是否存在差别,如果有差别,其差别何在?如果文学或艺术都不是某种类型的探究,那么我们是如何从它们那里学到东西的?想象、隐喻和语言创新在科学中的地位如何?需要加以清理的核心之点是认识论方面的,即是说,它与科学知识、证据和探究的本性和条件有关。我们需要一种实在论的说明:各门科学知道些什么,并且它们是如何知道的。这里,“实在论”指其普通的、非专门的涵义,即不高估也不低估各门科学所能够做的事情。这一任务是困难的,同时又是紧迫的。因为主流科学哲学有时错误地沿着过高估计科学的方向,这使得它不能有效地回击下述刺耳声音的大合唱:这些声音是错误地、戏剧性地从另一个方向发出的,近来已经威胁到科学的认识论断言。
曾经一度——预先提醒一下,下面所要叙述的将是卡通画般的历史——面对圣经或先验形而上学的相反断言,不得不为好的经验科学在认识论上的正当性辩护。经过了很长时间,下面一点逐渐得到确认:科学享有特殊的认识论上的权威性,因为它独自具有客观的、理性的探究方法。随之而来的努力就是明确表达那种独有的客观而理性的方法可能是什么样子,这些努力导致了我所谓的“旧尊崇主义立场”的许多相互竞争的版本:科学进步是归纳地进行的,即累积被经验证据或观察事实所确证的真实或可能真实的理论;或者,科学进步是演绎地进行的,即通过检验其基本陈述来检验理论,用证实了的假说来替换已被证伪的猜测,从而来提高它的各个理论的似真度;或者,科学是作为工具而进步的,即发展这样的理论,尽管不能说它们本身就是真理,却可以说它们是预测的有效工具;如此等等。当然,也存在许多障碍:休谟的归纳怀疑论;确证悖论;由古德曼的“grue”(绿蓝)谓词所引出的“新归纳之谜”;R·汉森的观察依赖理论的论题;蒯因关于理论甚至不被所有可能的观察所充分决定的论题。但是,尽管承认所有这些障碍都是严峻的,但却认为它们都是可以超越的,或可以避免的。[2]
下述做法是充满诱惑力的,即用库恩的术语,去把这些问题描述为:在一个竞争范式开始起作用时,旧尊崇主义范式所面临的反常。库恩告诉我们,他本人并不打算从根本上摧毁科学宣称自己是理性的事业这类断言。但是,《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大多数读者,忽略了其中的许多微妙区分和许多的模棱两可,只听到一个声音:科学不是通过积累得到很好确证的真理,甚至不是通过抛弃得到很好证伪的谬误,而是通过在一次灾变过程中的革命性巨变而进步或“进步”的。科学史此后就由获胜的一方来书写;不存在关于证据的中性标准,只有属于不同范式的不可比较的标准;科学革命的成功,与革命的成功一样,靠的是宣传和对资源的控制;科学家转而忠实于一个新的范式,这种转变与一次宗教皈依相比,更不像是一次理性的心灵改变。在皈依之后,事物在他看来是如此不同,以致于我们几乎可以说,他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
即使如此,在25年前,当费耶阿本德做出下述断言时:根本不存在科学的方法;诉诸“理性”和“证据”只不过是修辞上的欺行霸市;科学并不比占星术或巫术优越,只是比后者有更好的根基而已;他被广泛地看作是——如他本人自称的——科学哲学的“宫廷弄臣”。占据主流地位的科学哲学家,把“不可比较性”和“意义变化”加进他们待要克服的障碍表中,承认在细节上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有时候他们从其关于科学目标的观点上稍微后退一点,只要求解决问题或经验适当性,而不是要求真理,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过去确信、并且现在继续确信:旧尊崇主义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不过,近期以来,激进的社会学家,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和多元文化论者,在文学理论、修辞学、符号学等领域的巴黎时髦的激进追随者,以及处于严格的科学哲学圈子之外的哲学家,已经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科学。在关于科学合理性的适当说明中,被主流科学哲学视为仍待克服的障碍的那些难题,如不充分决定性、不可比较性及其他,却被他们视为从根本上摧毁了科学是一项理性事业的断言。
简而言之,我们达到了一种新的犬儒哲学。现在常听到的说法是: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或在整体上是社会利益、谈判协商的事情,或者是制造神话、生产记叙性铭文的事情;诉诸“事实”、“证据”或“合理性”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谎言,以掩盖对这个或那个被压迫群体的放逐。哈瑞·柯林斯写道:自然界“在构造科学知识时,有一种小的、非实在的作用”;[3] K·格尔根安抚我们说,科学中的理论命题的有效性,“丝毫不受事实证据的影响”。[4] 根据这种新的正统看法,科学不仅没有任何特殊的认识论上的权威性,也没有任何独特的理性方法,它像所有受目的驱使的“探究”一样,确实仅仅是一门政治学。鲁丝·休巴德写道,“女权主义的科学必须坚持科学工作的政治本质和政治内容。”[5] 斯蒂夫·福勒宣称,“在‘好学问’和‘政治关联’之间,我看不出有任何差别。两者都将随着你在你的工作中试图取悦谁而变化。”[6] 里查德·罗蒂告诉我们,“科学只在一种意义上成为例外,那就是:它是人类团结一致的榜样。”[7]
只发出下述抗议是不够的:这些说法是荒谬的;甚至无论以多么详细的方式,去证明下述一点也是不够的:新犬儒哲学家为他们的惊人言论所提供的用来代替证据或论证的东西,是不融贯的、没有推理关系的,是夸张、混乱说法的大杂烩。针对新犬儒哲学的夸大其辞,一个适当的辩护要求适当地说明科学的认识论——要求在先前解释过的意义上的一种实在论说明。
而旧尊崇主义不能提供这一点。这并不是如新犬儒哲学家所设想的那样,是因为科学在认识论上没有任何特殊性,而是因为科学在认识论上的特殊性要比旧尊崇主义所假定的更精致,更不直接,更不那么令人放心。
也许,令人并不感到惊奇的是,在旧尊崇主义范式那里,最严重的疏漏不是十分明显的,而是把着重点弄错了。旧尊崇主义倾向于把人们的注意力只引向科学,或者引向科学和作为陪衬的“伪科学”——隐含的假设是:好证据以及进行得很好的、有想象力的、彻底的、诚实的探究,都以某种方式是特别合乎科学的,是为各门科学所固有的。它倾向于使自身过于专注于狭隘的逻辑纬度,而忽视或低估想象、概念创新、交流的意义以及科学的社会特性——并且经常地,通过聚焦于观察陈述,似乎要把整个世界放逐到阴影中去。它太多地关注于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的区别——当它急于把非逻辑因素放逐到发现阶段时,在无意中鼓励了新犬儒哲学家去把理论的辩护也看作是科学家所从事的一种修辞活动,而不是关于它们的证据有多么好的问题。更有甚者,旧尊崇主义关于证据结构的看法,在过于狭隘的(也就是在过于形式的)意义上是逻辑的,不仅它们的演绎主义表述是如此,而且它们的归纳主义表述也是如此。
于是,下述现象也许不那么令人惊奇:对于一名外行来说,新近的科学哲学所提供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解释,听起来与其说令人放心,不如说更使人苦恼;究竟是下述那一点造成了如此状况,不得而知:例如在批判理性主义那里,它假定科学寻求有意义的真理,但它不能如此令人信服地解释科学是如何达到这个目标的;或者,例如在工具主义的新近变种和后嗣那里,它只能通过不合理地淡化科学旨在扮演的角色,才能证明科学是如何取得成功的。
也许,某些新犬儒哲学家模糊地感受到了旧尊崇主义探究的某些这种类型的缺陷,他们坚持科学方式之外的其他认知方式的合法性,或者强调下述事实,即无论科学还是什么,科学是一种大规模的、强有力的社会建制,或者强调语言创新在科学中和文学中的类似性,强调想象在两者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能证实他们诱使我们得出的那些夸大其辞的结论:在所谓科学的发现与我们所叙说的以使我们能够对付的其他故事之间,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差别;科学理论是否被接受,完全取决于社会的力量或政治的利益,如此等等。
为了断然谢绝上面那种诱惑,我将试图明确表达一种说明,权且称它为“批判的常识主义”,它能够纠正旧尊崇主义的过度乐观主义,而又不屈从于新犬儒哲学的矫揉造作的绝望。新犬儒哲学的主要论题是:不存在任何客观的认识论标准,科学在认识论上也没有任何特殊性。这些论题既鼓励了新犬儒哲学家的下述策略,并且又受到后者的鼓励: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评价性的根据(warrant)概念(相对于这个或那个科学断言,某证据是否足够好),转到了描述性的接受(acceptance)概念(这个或那个断言在相关的科学共同体眼中是什么样子)。但是,存在着客观的认识论标准,科学在认识论上也有某些特殊的东西。旧尊崇主义正确地承认了这一点,但其方式是错误的。科学在认识论上没有特权,但它却是出类拔萃的;要害在于:与特权不同,出类拔萃是必须通过努力去获取的东西。自然科学值得享有适度的尊敬,而不是无批判的尊崇。
人们几乎可以说,旧尊崇主义本身曾经是作为更旧的正统的造反者出现的,后来本身获得了正统地位;与此类似,由于自然科学艰苦赢得的出类拔萃地位慢慢凝结为不允许批判的特权,就只能预期它对新的造反者做出过分激烈的回应。但是,这种过分激烈的回应是不必要的,就像科学在认识论上所假定的特权是站不住脚的一样。我们关于好的、强有力的、支持性证据的标准,以及关于得体的、诚实的、彻底的、富于想象力的探究的标准,并不是为各门科学所固有的。在判断科学在何处取得成功、在何处失败,在哪些领域和什么时候做得较好,在哪些领域和什么时候做得较坏时,我们就是在诉诸这些标准,我们据此去判别经验信念的可靠性,或者一般地说,去判别经验探究的严格性和彻底性。但是,根据这些标准来判断,科学,至少是某些门类的科学,至少在某些时候,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关于好证据和适当探究的标准不是各门科学所固有的,这一说法并不等于说:一位外行,能够像相关科学专业领域里的某个人一样,同样好地判断某个证据是否适于某个科学断言,或者同样好地判断某次科学探究的品性。经常——通常——只有专家才能判别某个证据的份量,或者为防止实验错误而采取的预防措施是否周全,如此等等;因为做出这样的判断,一般需要关于背景理论的广泛而又详尽的知识,更别提要熟悉专门词汇,而这些事情对于一位外行来说不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尽管唯有专家才能够判别这个或那个证据的价值,不过,尊重证据,关注对证据的评价,坚持把证据找出来,这既不是只为科学所需要的,也不是科学的本质性要素,而是我们据以判断所有探究者——侦探,历史学家,爱寻根究底的新闻记者,等等——的标准。
在新犬儒哲学家中间,普遍持有一个令人惊骇的论证,它是与他们试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根据引向接受的意图密切相关的。下述假设在鼓励这个论证方面也隐含地发挥着作用:认识论标准(他们也许会说,假设有这样的标准的话)是为科学所固有的。该论证说,被科学家当作或接受为已知的事实或客观的证据或诚实的探究等等的东西,在有些时候却被证明并非如此,已知的事实、客观的证据、诚实的探究等观念被揭示为意识形态的谎言。(该论证的)前提是真实的,不过很明显,结论却是得不出来的。确实,这个令人惊骇的论证——我把它称作“认同谬误”[8]——不仅是错谬的,而且是自毁的;因为如果其结论是真的,该前提就不可能是已知的事实,对于此事实,诚实的探究已经发现了客观的证据。批判的常识主义对此可以做出明确的回应:科学探究并不总是能够达到那个认识论理想,但是,唯有通过真诚地审视证据,我们才能够发现它在何时、何处失败了——不过,对于那些假定该认识论理想是由各门科学所设定的人来说,做出这样的回应并不是很容易的。
对于我的目的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发现与辩护之间的区分,而是好证据的标准与适于探究行为的规则或指导方针之间的区分。这里相互区别的,与其说是在一个花卉展览中识别玫瑰的标准与培育玫瑰的规则或指导方针——后者,而不是前者,将不可避免地提到马粪;毋宁说是营养的标准与计划菜谱的规则或指导方针。科学探究的目标是有内容的、有意义的、起解释作用的真理。并且,如果一个人忽视计划菜谱这一目标的另一个方面即可口,那么做出一顿有营养的饭就更容易一些;同样,如果一个人不在乎他所得到的真理是不足道的或无意义的,那么他提供真理也会更容易一些。好证据的标准关注该目标的仅仅一个侧面,即提示真理;而探究行为的指导方针则必须关注内容、意义以及真理。这就是造成下述现象的原因:不可能有指导探究的规则,不可能有能够被机械地遵循的指令,而只有在应用时需仔细斟酌、审慎判断的指导线索。
使用一个长期以来我信赖的类比,证据的结构比纵横填字字谜更不像数学证明。[9] (如我近期刚发现的,爱因斯坦注意到,一位科学家就“像一个正投身于解决一个设计得很好的字谜的人”。[10]) 想一想关于在南极洲发现的陨星的争论吧,该陨星被认为是在大约40亿年之前来自火星,含有可能已成为细菌残留物化石的成分。有些科学家认为,这就是在火星上有早期细胞生命的证据;另外一些科学家赞同它们是细菌残留物的说法,但认为它们是在该陨星在南极洲期间形成的;另外一些科学家认为,它们不是细菌残留物,而是在火山口形成的;另外一些科学家还认为,那些看起来像细菌残留物的东西,也许只是仪器操作产生的假象。[11] 他们怎么能够知道,放出这些气体就表明:该陨星来自火星?该陨星是大约40亿年以前的?细菌残留物化石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像纵横填字字谜的各个格一样,可以沿所有方向展开理性的翅膀。
纵横字谜的一个格填得是否合理,取决于:这种填法是否得到该格的暗示以及先已填完的相交格的多大程度的支持,另外那些格填得是否合理(这不依赖于所讨论的这个格),以及该纵横字谜已经完成了多少。类似地,一个经验断言是否有根据,取决于它得到经验和背景信念多大程度的支持,这些背景信念有多少根据(这一点不依赖于所讨论的那个断言),以及该证据所包含的相关证据有多少。
并非所有的科学理论都得到好证据的充分支持。被好证据否决的大多数理论结果证明是不应被否决的;几乎所有的科学理论,在其生涯的某个阶段,都只是得到很少支持的思辨;无疑地,某些理论得到接纳,甚至是基于不足信的证据。不过,至少各门自然科学已经提出了深入的、广泛的、有解释力的理论,它们深深地扎根于经验之中,并且令人吃惊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并且,如同在一个填字游戏中,合理地填写很长的有很多交叉点的格,就极大地增加了一个人填完该游戏的更多格的机会一样,这些成功已经导致了更多的成功。
要记住,目标是实在论;这要求坦率地承认:就社会科学而言,并不那么容易想出发现的例子,与合理填写长的、有很多交叉点的纵横字谜的各个格相类似。确实,这就是有些人不愿承认社会科学是科学的部分原因。这给我们提出了某些更为严重的问题:社会科学很少取得使人印象深刻的成功,对此的解释简单地就在于它们是相对年轻的,或者更深入地说,也许像某些人所认为的,必不可免地要归因于它们的题材。
还有,自然科学,至少根据我们的经验证据的标准,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它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并不是因为它们占有独特的理性的和客观的探究方法,这些方法是历史学家、侦探和我们其他人得不到的,它们确保产生真实的、或可能真实的、或越来越接近真实的、或越来越在经验上是适当的,如此等等的——结果。P·W·布里奇曼写道:“科学方法,就其作为方法而言,只不过是打定主意拼命死干,一往无前。”[12] 并且我要补充说,就其作为方法而言,它也是历史学家、侦探、爱寻根究底的新闻记者或我们其他人,在我们确实要把某些事情弄清楚时所做的事情——也是当我试图搞明白为什么我这次做的这道菜显得要比上次做的要好一些时所做的事情:提出一个有内容的猜想,作为一个令人迷惑现象的可能解释,看它能否经受住你能够获得的最好证据的检验,然后作出你的判断:是接受它,多少带有一些尝试性;还是修改它,使它更为精确,或者替换它。
不过,关于自然科学中的探究,存在某些特殊的东西;或者毋宁说,存在大量的东西:各式各样的实验设计,统计评估和数学模型化的特殊技巧;对于批判和检验,对于找出方法在某个时候隔离开某个变量等等的系统承诺;在一代或数代人中间,许多人的投入,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和相互竞争。
E·O·威尔逊描述了他在红收获蚁激素警示系统方面的工作:搜集这样的蚁;把它们安置在人工蚁巢内;解剖新杀死的红收获蚁,把白色的肌肉弄成小块状,把这些小块置于传导杆的尖端,递给余下的红收获蚁:它们“争先恐后地钻进了线团里”。招募一位化学家,他使用色相层析和物质光谱仪去识别那种活跃的东西,然后提供在实验室里合成的具有同样成份的纯样品。再把这些纯样品供给那群收获蚁:出现与先前完全一样的反应。然后招募一位数学家,他构造一个有关该激素挥发的物理模型。然后设计试验,去测试该分子传播的速度以及红收获蚁感知它们的能力。[13]
借助于解决其他问题的方法去解决某个问题[14], 借助于一个理论的设计技术和工具去检验另一个理论,自然科学已经把小的成功累积成为大的成功,这又使得更多小的成功成为可能,后者又累积成为更大的成功,……如此循环往复。假如自然科学探究不在上面解释的意义上成为一桩社会的事业,情况就不可能是如此。
科学探究的社会特性,既不是如某些旧尊崇主义者所急于去假定的,在认识论上是无意义的;也不是如某些新犬儒哲学家所急于去断定的,在认识论上是破坏性的。它只是下述众多途径中的一条途径:科学据此扩充和深化了经验和推理的方法——当我们严肃地尝试着解决某些经验问题时,我们所有人都使用这套方法。不,远不止如此:承认科学探究的社会特性,对于理解它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本质性的——并且,对于理解对它的继续成功所构成的潜在威胁也是本质性的。[15]
对科学知识和科学探究的一个适当说明,必须承认逻辑、个人、社会诸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当然,这种相互作用开始于这样一个开端:有才能的个体提出有想象力的猜想,其他的猜想以此为基础,该猜想本身接受整个相关共同体的审查;并且,这种相互作用在每个阶段都在发生。任何经验命题的根据都部分地取决于经验证据,也就是说,取决于某个(或某些)个别观察者所看见或听见(诸如此类)的东西,于是,也取决于其他人在认为该观察者可信时是否合理。
我现在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接受是如何与根据适当关联的。科学断言都是有根据的,只是程度不同;并且存在很大的灰色地带,关于下述问题可以合理地发生意见分歧:一个断言,是否有充分的根据把它放进教科书里,或者应该首先使它通过更一步的检验,或者相对于另一种选择或无论什么,要更仔细地对它作出评价。什么时候要接受一个理论,什么时候要拒绝一个理论,在这方面所存在的规则,并不比在下述方面的规则更多:在一个纵横字谜游戏的某一格中,什么时候应填进某个字母,什么时候要擦掉它?“最好的”程序相对于不同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同的,有些人更大胆一些,有些人更谨慎一些。
我已经明确表达的科学探究概念是实在论的,不仅在“实在论”一词普通的、非专门的意义上是如此,而且在新近科学哲学所使用的某些专门意义上也是如此:[16] 科学探究的目标是实质性的、有意义的真理;科学理论通常或者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在真实的科学理论中所设定的实体、类别和是实在的。也许我需要补充的是:当我把一个科学断言或理论描述为真的时候,我的全部意思是:事物正如它所说的那样;举例来说,如果它说:DNA是由一对多核苷酸链组成的双螺旋,只有在DNA确实是由一对多核苷酸链组成的双螺旋时,它的说法才是真的。
我不怎么同情旧式的工具主义,因为我不相信在能够为真或为假的观察陈述与不能有真值的理论“陈述”之间能够划出鲜明的界限。我也不怎么同情新式的构造经验论。不过,我乐于承认,科学家在表述他们的理论时所做出的真实断言,很少有无条件的和独断式的自负,通常是谨慎的和尝试性的。
并且,按有时与“实在论”一词相连的强进步主义解释,我的探究不是“实在论的”。确实,随着自然科学的进展,已经积累了数量巨大的有充分根据的断言。但是,没有任何保证可以说:在每一个步骤上,科学都积累了更多的真理,或者用真的理论替换了假的理论,或者与真理更为接近;也没有任何保证去说,现在接受的理论,即使是“成熟”科学中的理论,都是真的或近乎是真的。在任何时候,科学的某些部分可能跑在前面,某些部分落在后面,另外一些部分则完全可能在倒退。在有进步的地方,进步可能是积累了新的真理,或者是用较好的理论替换了不值得信任的理论;在这些情形下,新理论可能隐含着旧理论在有限的范围内是正确的,或者它部分地与旧理论重叠,并且/或者它引入了新概念,通过累赘的迂回说法,可以把这些新概念翻译到旧理论中去。或者,进步可能不是理论层次上的,相反,却属于有关新工具、或新试验、或新技术、或更好的词汇方面。
有关客观性的问题需要类似的细致梳理。一个科学断言是真的或者是假的:是客观地为真或者为假,也就是说不依赖于是否有任何人相信它。科学断言的证据是强的或弱的:是客观地为强或者为弱,也就是说,不依赖于任何人认为它是多么强或多么弱。但是,却没有任何保证去说,每一个科学家都是完全客观的,也就是说,是完全无偏见的、无偏好的真理追求者。科学家是可能犯错误的人;他们并非没有先入之见和宗派情绪。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归根结底而言,自然科学已经设法克服了个体的偏见,其手段是:制度化地允许相互揭短和相互审查,从事竞争研究的团体之间相互竞赛,——以及内部的组织化。换句话说,自然科学已经设法在整体上使大多数科学家,在大多数时间里,保持了合情合理的诚实。
这些复杂的问题被下述事实弄得混淆了:公众眼中的“科学家”形象在下述意义上是客观的,他或她不仅没有偏见或先入之见,而且是无情感的,无想象力的,呆头呆脑的,是典型的收敛型思想家。也许某些科学家是这样,但是感谢上帝,并非所有科学家都是如此。之所以“感谢上帝”,是因为对于成功的科学探究来说,想象力,构想关于令人迷惑现象的可能解释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还因为:痴迷于这个或那个问题,甚至并非很少见的,满怀激情地承认某个雅致的但并未得到很好支持的猜想的真理性,或者热切地期望赢得某次竞赛,对科学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这里所显示的,当我说到“偏见和宗派情绪”时,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可以说是职业性的偏见和宗派情绪:一位科学家太易于接受一种探究或一个理论,因为它是他的导师所构想出来的,或者是因为他把自己多年的时间用来发展它;或者说,他太易于拒绝一种探究或一种理论,因为它是由在职业领域内他的竞争者构想出来的,或者是因为他把自己多年的时间用来发展另一种理论,如此等等。比较而言,在新犬儒哲学家阵营中,关注的焦点是政治方面的先入之见和宗派情绪,例如性别歧视,种族主义,阶级主义等等,新犬儒哲学家认为,科学中充斥着这些东西。就物理科学而言,假设性、种族、阶级与物理理论的内容没有明显的关联,这种观念看起来是糊涂观念。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假设性、种族、阶级与某些理论的内容明显关联,政治和职业方面的先入之见共同在起作用,情况看起来只是有些夸大。
确实,这提示了对先前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的答案的开头部分:在一方面是人文社会科学、另一方面是物理科学之间,一个有意义的差别也许恰好在于:给定前者的题材,急于挤进诚实的探究中的某些先入之见是政治和职业方面的。几页之前的一段文字表明:另一个有意义的差别也许是,数学技术以及在探究方面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已经帮助自然科学建立起先前的成功,而在社会科学的目前发展阶段,对这些东西的采用相反却在鼓励某种做作的、数学化的晦涩难解,以及早熟的群体性(或者学说方面的宗派性)思维。
“科学家”的另一种形象也使这幅图景模糊不清。这一次与其说是公众眼中的形象,不如说是哲学中的形象,即他们作为本质上的批判性思想家,拒绝把任何东西当作权威。系统地允许检验、核对、相互揭短和相互审查,是导致自然科学探究获得成功的那些因素之一;但是,这种允许是而且必定是与有充分根据的结果的制度化权威结合在一起的。要害并不在于:纵横字谜的各栏一旦填入就绝不可能再更改,而是在于:只有把某些东西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才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把某个变量抽离出来,或者才有可能借助于其他人对更老问题的解决方案去处理一个新问题。这又把更多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次是有关科学中权威的本性、基础和限度的问题。
至此为止,我已经强调了对自然科学探究的成功起了作用的途径或方式:当然是凭借分工协作;凭借使创造性和细致性、想象力和严格、有规则的批评和有充分证据的结果的制度化权威相结合成为可能,这些要素对于成功的探究来说是本质性的;凭借着克服甚至是积极地利用个别科学家在人性上的不完善。但是必须承认,科学的内部组织和外在环境可能或多或少也有助于好的、富有成效的探究。
苏联和纳粹科学的灾难提醒我们注意:如果科学家着手为了政治上需要的结论而制作案例、而不是为了弄清楚事物本身的真相时,探究能够遭受到多么严重的扭曲和损害。直接提醒我们注意的其他潜在损害因素,也许不那么惊心动魄,但也是扰人心智的,其中有: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获得基金,去以适当的过程用自己的成功去给可能提供基金的无论什么人留下印象;在资源方面依赖于某些部门,他们对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产生的结果感兴趣,或者对接近他们的某些竞争者被否定感兴趣;承受压力去解决被认为是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去解决在该领域的目前状况下最有可能解决的问题;出版物的数量是如此之大,以致妨碍了交流而不是使交流成为可能;诸如此类。
以上列举的因素并不鼓励对科学的目前状况感到满足,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够坦率的。重要的科学进展一度借助于很少的设备——例如一支蜡烛和一团绳子——就可以完成,但科学家们似乎已经作出了绝大多数此类发现。随着科学的进展,需要有越来越贵重的设备去获得越来越精细的观察结果。并且,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多的学科在资源方面依赖于政府和大型——这些部门能够提供某种支持——这比上一段中所描述的那些损害科学的因素造成的危险更坏。科学的技术和工具变得越来越精致复杂;但是,迄今为止已经证明是或多或少足以维持理智整体性的那些机制,却受到了约束。
科学证据通常是整个科学家共同体享有的资源;科学中的探究,无论是合作的还是竞争的,都把一代或数代中的许多人卷入其中;科学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一个较大的社会背景中进行的,这个背景对什么样的研究能够得到基金支持,什么样的结果能够得到广泛传播,有时候对得到什么样的结论,都会产生有意义的影响。不过,旧尊崇主义者经常假定,科学的社会因素,尽管可能对在认识论上无关紧要的发现语境有某种关系,最好能够对在认识论上至关重要的辩护语境发生否定性关联。并非很少的科学社会学家,至少是部分地意识到旧尊崇主义者的狭隘逻辑模型是不适当的人,似乎已经被新犬儒哲学所吸引——也许部分的原因在于:与旧尊崇主义不同,新犬儒哲学给像他们这样的人提供了一个讨人喜欢的大而重要的角色。而这又反过来强化了主流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家本身在下述一点上的分歧,即在理解科学事业这一任务中,严肃地把科学社会学当作潜在的同盟军。
“认识论和社会学之间的这一争论”,已经模糊了要不然会很明显的下述事实:科学内部的组织方式或者它的外部环境,可以促进或妨碍(科学的)进步。与近来已经变得时髦的犬儒主义的科学社会学不同,明智的科学社会学能够揭示出科学的内部组织和外部环境的哪些方面,在鼓励着好的、彻底的、诚实的探究,结果的有效交流,以及有效的检验和批评。
正像我们需要区分明智的科学社会学与犬儒主义的科学社会学一样,我们也需要在下述两者之间做出区分:一方面是,在何种意义上下述命题是真的并且在认识论上是重要的,即科学是社会的,即是说,科学探究是需要很多人的投入、合作和竞争的事业;另一方面是,由健忘症或怀疑论所提倡的关于根据问题、证据作用的一种时髦但虚假的解释:科学的目标是成就社会所希望达到的目标;科学理论的接受要通过某种类型的“社会谈判”来进行;科学要通过某种更“民主”的认识论来改进;科学知识,甚至是实在本身,都只不过是某种“社会建构”;自然科学从属于社会科学,如此等等。
既然科学主义和反科学态度都根源于误解了科学探究和科学知识的特性和限度,迄今为止所关注的焦点一直是认识论方面的。但是,这既没有否认下述困难问题的合法性,也没有贬低其重要性,它们是有关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的伦理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应该由谁来决定、并且如何决定政府应该给什么样的研究计划提供基金?由谁来控制、并且如何控制由科学发现所释放出来的用于善和恶的力量?……,如此等等。
如这里所表明的,有关科学和价值的那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之所以令人烦恼,部分地是因为它的众多的歧义性。科学探究是探究的一种类型;于是,认知价值,其中主要是对于证据的尊重,必然是相关联的(这并不是说,科学探究总是或必然满足认知的考虑或体现认知价值)。但是,正如前一段提醒我们的,也存在着道德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既与科学程序有关(例如,获取证据的某些方式在道德上是否可接受),并且也与科学的结果有关(例如,对于具有潜在爆炸性的科学结果的获得和应用,是否应该加以控制以及如何控制?)。顺便说一下,那种歧义性是意向性的!
在新犬儒哲学家中,有些人似乎设想:科学发现能够具有坏的用途,这一事实就是质疑那些发现的善意的一个理由;有些人似乎理所当然地假定:持有下述看法的人以某种方式显示出他们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即科学已经做出了许多真实的发现,甚至存在着像客观真理这样的东西。但是,简单地指出那个明显的混淆是不够的,简单地抗议那种炫耀性的道德上的胜人一筹也是不够的。还有必要精确表述关于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的那些困难问题的明智答案:特别是要指出,只有通过诚实的、彻底的探究,我们才能够弄清楚造成所要的社会变化的有效手段是什么。并且,总是有必要去避免科学共同体的夸大以及反科学群体的夸大:特别是要指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付关于世界的科学知识所赋予我们的力量,这方面的决定是否聪明或正当,本身并不是可以负责任地只留给科学家去回答的技术问题。
在本文开头,我从里德的一段话开始,我认为他的观察是敏锐的;我也在意有关下面这个学生的谨慎的故事——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传说还是史实——据说他在哲学导论课时写道:“有些哲学家相信上帝存在,有些哲学家相信上帝不存在;但如经常所发生的那样,真理存在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处。”在目前的情形下,真理确实存在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处:一方面是旧尊崇主义的有缺陷的极端,另一方面是作为它的对立面的新犬儒哲学。当然,这只是关于真理恰好存在于何处的一个概略描述。我正在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注 释
[1] Thomas Reid,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Powers(《理智力集》)(1875), VI, 4; in Beanblossom, R. E. and Lehrer, K., eds, Thomas Reid: Inquiry and Essays (《托马斯·里德:探究和论文集》)Hackett, Indianapolis, IN, 1983.
[2] 在这一段和以下几段中,我利用了我的论文“ Puzzling Out Science ”, Academic Questions(《学术问题》)Spring 1995, 25-31; 该文重印于我的著作 Manifesto of a Passionate Moderate: Unfashionable Essays(《一位热情的稳健派的宣言:不可能变得时髦的论文集》)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98, 90-103.
[3] Harry Collins, “Stages in the Empirical Programme of Relativism”,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的社会研究》)11, 1981, p.3.
[4] Kenneth Gergen, “Feminist Critique of Science and the Challenge of Social Epistemology”, in Feminist Thought and the Structure of Knowledge(《女性主义思想和知识的结构》) ed. Mary M. Gerge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8, 27-48, p.37.
[5] Ruth Hubbard, “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Masculinity of the Natural Science”, in Gergen, Feminist Thought and the Structure of Knowledge(《女性主义思想和知识的结构》)1-15, p.13.
[6] Steve Fuller, e-mail posting, 5. 4. 94.
[7] Richard Rorty, “ Science as Solidarity ”, in John S. Nelson, Allan Megill, and Donald M. McCloskey, eds.,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人文科学的修辞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 WI, 1987, 38-52, p.46.
[8] 我最先在下文中引入了这个短语:“Knowledge and Propaganda: Reflections of an Old Feminist”, Partisan Review, LX.4,1993; 重印于Manifesto of a Passionate Moderate(《一位热情的稳健派的宣言》)123-36. “Staying for an answer”,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泰晤士报文学增刊》)July 9th, 1999, 12-14.
[9] 参看我的论文:“Theories of Knowledge: An Analytic Framework”,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83, 1982-3, 143-57; “Rebuilding the Ship While Sailing on the Water”, in Perspectives on Quine(《蒯因概观》)eds. Robert Barrett and Roger Gibson, Blackwell, Oxford, 1990, 111-27; 以及我的著作:Evidence and Inquiry: Towards Reconstruction in Epistemology(《证据和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Blackwell, Oxford, 1993.
[10] Albert Einstein, “ Physics and Reality ”, The Journal of the Franklin Institute(《弗朗克林研究所杂志》)March 1936; 重印于Ideas and Opinions of Albert Einstein(《爱因斯坦的观念和意见》)trans. Sonja Bargmann, 1954, p.295; John Norton 在1996年引导我注意到这一点。
[11] Adam Rogers, “ Come in, Mars ”, Newsweek(《新闻周刊》)20th October, 1996, 56-7; Sharon Begley and Adam Rogers, “ War of the Worlds”, Newsweek, February 10th, 1997, 56-8.
[12] Percy R. Bridgman, Reflections of a Physicist(一位物家的反思)Philosophical Library, New York, 1955, p.535.
[13] E. O. Wilson, 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一致:知识的统一》)Knopf, New York, 1999, 69-70.
[14] 我从下面这本书中借用了这个方便的短语:Quine, From Stimulus to Science(《从刺激到科学》)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1995, p.16.
[15] 还可参看我的论文:“Science as Social—Yes and No”, in Feminism, Science,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女性主义,科学,和科学》)eds. Jack Nelson and Lynn Hankinson Nelson, Kluwer,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1996, 79-93; 重印于Manifesto of a Passionate Moderate(《一位热情的稳健派的宣言》)104-122.
[16] 关于“实在论”一词的多种含义的精确表述, 参看Haack, “ Realism ”, 即将发表在 Handbook of Epistemology(《认识论手册》)中,eds. Ilkka Niiniluoto, Matti Sintonen, and Jan Wolenski, Kluwer,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