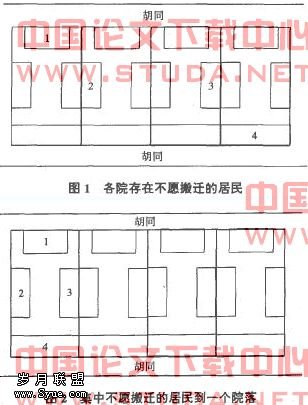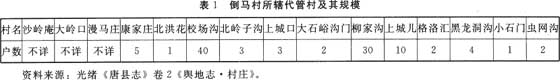明代云南人口、土地问题及封建经济的发展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2
各民族的经济发展,都有其悠久的。我们研究明代云南各族的经济发展及其特点,除现实情况外,还要上溯其历史发展。此外,田野的实地调查,文物的比较研究,兄弟民族的传闻和民歌故事,都可以作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线索。现仅根据身边能读到的史籍、史料,对明代云南地区的人口,土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明代人口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云南
自元世祖率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大理城,到明初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军平定云南以后,内地居民向云南移迁达到了一个高潮时期。据地方志载楚雄的情况是:“自洪武二十六年傅沐二公平定后,留兵戍守,太祖又遣江南闾右之民以居之,复有宦游商贾入籍,大部南人较多,故俗亦类江南。”其实,不仅楚雄是这种情况,整个云南也都是这种情况。从明至清数百年中,从外地迁移到云南的,就其性质来看,有以下几种情况。
1.留戍
元代和明代,对云南用兵以后,必留兵力戍守。因此,戍军成为云南移民的主力。元世祖平大理后,蒙古人移住滇中的甚多,今大理,永昌等地,尚能寻见蒙古坟和蒙文碑志。河西县境内的打鱼村,全村数百户,和内地人的风俗语言有所别异,自称系随元世祖征滇时留守在此地的。世祖平滇后,以瞻思丁抚滇,从此云南更有阿拉伯人的移入。《新元史》本传载:“赛典赤瞻思丁,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别庵伯尔者,西域诸国尊回回救主之名也。世祖征西蜮,瞻思丁率千骑迎降,至元十年,奉上命抚滇,在滇六年,建树极伟。”从这一记载中,可以推定在此期间阿拉伯人到云南来的必然很多。据《大理县志》载:“境内之有回教,其来久矣。元时,赛典赤瞻思丁以平章使云南,至元十六年,其子纳速刺丁迁大理路宣慰使都元帅,是为回教人至大理之始。今境内回教约一千余家,凡姓沙与马者,皆赛部子孙。”(《大理县志稿》)反映了元代云南戍军落籍于狙中的情况。
明初平定云南后,留戍滇地的士兵,多为长江黄河一带人。《明史》称:“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此留戍。”(《明史•兵志》)
明代,军队戍守的地方,叫做卫所。明代云南都司所属卫所,计有左卫、右卫、前卫、大理卫、楚雄卫、临安卫、景东卫、曲靖卫、金齿卫、洱河卫、蒙化卫、平夷卫、越州卫、六凉卫诸处。所谓“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明史•兵志》)依此类推,仅就设卫的地点来,云南各卫所留戍的士兵,将近十万人左右,这还没有计算后来随时补充增戍的人数。此外,在正统时王骥的三征麓川,万历时刘犍,邓子龙的深入缅地,顺治四年李定国的率大军入滇,顺治十五年铎尼、赵布泰、吴三桂的进取云南,他们所统率的军队,多有一部或全部留戍或流亡在云南,以后大都落籍在滇地。有些士卒的妻子也被迁往云南。
2.仕宦的落籍
云南人中,还有一部分是外省仕宦落籍于滇的。他们是仕宦的后裔。
根据《云南机务钞黄》所载,洪武十五年平滇后上谕,“各处仕宦人员,流寓在彼,及本处人民,如有怀才抱艺愿仕者,有司礼送赴京,以凭擢用”。可见元末及明初,在云南做官而流寓在那里的,巳为数很多。明代三百年间, 滇中的官吏,有很多是外地人,如知名的文人杨慎 (升菴)、李贽(卓吾)等都在云南流寓过.清初吴三桂治滇,当其声势显赫之时,就有所谓“西选”之官,遍布东南,为仕宦而入滇的外地人,至此盛极一时。吴三桂失败后,终清一代,滇中官吏,仍多队外地派入。据昆明县志载:自顺治迄道光间,昆明历任知县,计四十二人,其中二人为满籍,三十九人皆闽粤江南或北方来者;凡此外来仕宦之人,他们的子孙固然未必完全落籍滇中,但任满后不再返回故乡的,也大有人在。特别是李定国在云南时,其兵士多为外省人。起义军失败后,其土卒多流亡滇地。如部将贺九仪,欲出降,定国杖杀之,其卒多溃还云南。” (《南疆逸史》)
3.移民
明初,一方面从山西洪洞县移民以充实河南山东等地,另一方面“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永昌府志》载:“明初,迁江南入居此地,故其习尚与江宁相仿佛,是以俗号小南京。永昌即今之保山。明代到保山做官的多是些江苏一带的人。:《徐霞客游记》称:“景泰中,设镇守。弘治二年,设金腾道。嘉靖元年,巡抚何孟春(彬州籍,江阴人),巡按御吏陈察(常熟人),疏革镇守,设永昌府,立保山县,改金齿指挥使司为水昌卫府,领州一,(腾越)二县,(保山,永平)仍统潞江安抚司,凤溪、施甸二长官司。”
不独保山如此,楚雄,大理也有类似的情况。西地居民,也大都由江南移来。《楚雄县志》载:“县邑自前明洪武十六年傅,沐平定后,留兵戍守,太祖又徙江南闾右之民以居之。”至今保山仍多江南人。《大理县志》说:“明成化十二年,设兵备进驻洱海,以后移民实边,”“阅百年,而生齿日繁,流寓日众。”
我们对于明代从内地移民到云南的资料,掌握得极少。详细事实,史无专记,在地方志中可窥见一些零星史实。滇人藏有族谱的家庭不多,所以,当时的移殖详情,和移来的人口确数,都缺乏详尽的统计。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明代三百年间,通过移民的方式,流入云南的户口,为数不会太少。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洪武实录》卷186,页3)
4.官吏的谪戍
明代云南的移民中,有一部分是因罪革职的官吏,或者叫做谪戍。《永昌府志》载:“考流寓者自当明始,而谪戍居多焉。或以文章寄兴,或以忠介全身,或以暂离而仍归,或久居而不返。”除保山外,其它各地也有这种情况。明代为谪戍而流寓云南省的,各府县地方志上不乏此种记载,如明初的傅友德家属,当傅友德殁后,被分戍云南,辽东。在云南的一支,子孙旺盛,明代末年的傅宗龙就是他的后人。宋濂的儿子宋慎,也在洪武时坐胡惟庸党徙临安卫,又徙石屏,滇人称其子孙为学士后人。南京富户枕万山,洪武时举家被充军云南,今滇中尚有其后人。其他为御史施武,参知政事姬思忠,进士刘寅,翰林周志宏,都是因罪谪戍云南而落籍滇中的。今保山金鸡村有大户蔺,自言为蓝玉后人,因玉获罪,怕株连,乃改蓝为蔺。以上都是避徙谪戍的移民。 当然,也有谪戍得还的,如诸城知县陈元恭,便是一例。
5.朝代更替和流亡
这种情况以明末清初为最多。顺治14年,永历帝入滇,宗室遗民髓着他由曲靖到昆明的很多。据《滇南杂志》中的《永明外纪》记载:帝于顺治十六年西走永昌时,随行之众,不下四千,自永昌入缅时,官员随行者四百余,侍从遗民则有三千以上.失败时,尚且如此,初入滇时,来的为数当更多了。吴三桂在云南,以“复明”为号召,许多人都看不清楚他的狼子野心。由于当时“人心思汉”,受其蒙蔽,中原人士响应入滇的很多。
6.工商业者,文人的流寓
由于经营工商业,流寓在云南的也不占少数;大多为四川,江西、两湖,闽,广诸地的人。《昆明县志》载,“县城凡大商贾,多江西湖广客,其领当帖设质库者,山右人居其大半。”可见当时在昆明经营当铺业的多是山西人。不仅昆明一地如此,其他各县也是如此。
云南多流寓的内地文人。如浪弯(即洱海)的何巢阿,昆明的唐泰,永昌的闪人望等。这些流寓在云南的文人,当徐霞客游滇时,都和徐氏有来往。至于流寓于石钟山的李元阳,西华山的杨升菴,那更是鼎鼎大名,人所共知的了。
从以上材料中,我们可以知道今天的云南人,实际上多为江南,中原,燕北,闽广,山西,湘,赣的移民。当其最初入滇时,境内原有不少当地居民(包括一些少数兄弟民族)。在当地居民人数远胜于新来的移民之时,流寓此地移民的生活习惯,往往不足以左右或影响当地居民。在这种情况下,新来的移民,往往易其旧习而迁就当地的土俗.这就是常说的移民的土著化。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元代以前。自明平定云南以后,中原居民移居于云南的日渐增多,对当地的原有居民,就发生两种作用:一种情况是外来居民与内地移民融合,正如丘浚所说的:“久之固巳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皇明经世之编》)这虽指明代“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而言,在其它地方的各族杂处,情况也是如此。此种融合或同化遗迹,在现时云南境内各族居民间,都可以找到。昆明四乡的子君,散民, 子,夷人等,就是同化尚未完全彻底的原有居民的残迹。大理一带的民家,实质上是内地移居民户与南诏大理居民的混合体。在抗战时期,永昌鹤庆有蒋家,人们称他们为“阿莽蒋”,其族约数千户,据说原为南诏蒙氏的后代,初姓阿,后改姓莽,以后又改姓为蒋,通过各种关系,其生活习惯语言,和内地迁徙于此地的居民巳完全没有分别了。此为中原居民移居边地后融化原有居民的情况。一为原有居民聚居边区或山谷一带,而中部平原沃壤,则多为新来的移居的客户。这种情况在宾川西部山区更为明显。从云南全境来说,腹部多中,原移来的人,四境边地则多为原有居民。就一县区而言,城关及附近的平原地带,多有内地移民居住,而四周山区地方,则为原有居民散居之区。但是,无论是那一个兄弟民族,他们对于开发祖国的边疆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7.宗室藩封
洪武时,封其宗室子弟于云南。如岷王封于云南后,大兴土木,营建宫室。洪武二十七年冬十月,始“罢建岷王宫殿。”再如周王,原封于河南,今开封龙亭即其王府旧址。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崩,……未几,果有言周王不法者”,“驱迫王及世子阖宫皆至京师,削王爵为庶人,迁之云南。”(《太宗永乐实录》卷1,页3—4)这样,周王朱梗和他的后代也都落籍在云南昆明了。此外朱埔次子朱有勋(汝南王)也居住在大理。至今大理,尚有朱氏后裔。
二 明代的屯田
明代继承和了历代特别是金,元的屯田制度,在全国各地普遍开设屯田,云南也不例外。封建统治阶级企图通过屯田,建立一支庞大的,在兵士军粮和武器来源方面不受任何影响的,维护封建统治政权的国家机器——军队。可是,他们无法克制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所固有的腐朽性。因此.在开设屯田的高潮(洪武,永乐间)过后不久,屯田制随即遭到破坏(宣德,正统间),紧接着来的是,王公勋戚贵族和卫所军官对屯田的霸占和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化,致使大量屯田走向民田化。正统中,凤阳等处的军官占田有多至“千余亩者”(《明英宗正统实录》卷106,正统八年七月)。嘉靖,隆庆到万历以后,屯田巳成为档册上的记录了。下面谈谈明代在云南屯田的沿革,及其对当时社会发展的作用。
1.军屯
明洪武十四年,当朱元璋调集军队进入云南之际,曾自岳州至贵州设置了二十五驿,每驿贮粮三千石,以供军食,明军进入云南后,采取的是向元军借粮的办法,所谓“前恐蛮地无粮,符抿将军令分军回卫,今知资粮于敌,军可不必回也。”
(《太祖洪武实录》卷140,页8)但是,终因蒙古贵族煽动云南农奴主和奴隶主进行叛乱,局势未能及时稳定。当时,云南行省从元朝接收下来的贮粮只有十八万二千多石,仅够四个月的军需。军队“好生无粮”的现象比较严重,甚至发生了“逃军”现象。明廷当时采取了“打粮”的措施,即命令明军分别结集,把该地有粮的民族头人都“打了取粮用。”这种办法,一方面,虽可打击一部分奴隶主和农奴主,暂时解决一部分军粮问题,但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明军在这一军事行动中不可避免地要伤害一部分群众,对稳定云南局势起了不利的作用。于是在洪武十五年议置云南都指挥使司,以谢熊戈,冯诚署司事;修道路,置邮驿。“谕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沾益诸酋长曰:‘今道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士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同上,卷142页1下)除发展外,还推行开中之法(注:“开中”是明政府利用食盐运销权使商人输送粮米到边疆成京都的制度.明太祖洪武8年,为筹备边储,仿宋代折中法,出榜召商运粮到边塞或边远缺粮地区 (成在边境设立商屯产粮),政府登记缴纳种类和数量,以及应支盐敷,发给领盐凭证——盐引,商人持此盐引赶户地支盐,并在指定地区贩销.最初行于山西大同,后普及全国。)。在明军初步平定乌撒叛乱后,洪武十六年,随即班师,只留沐英镇守云南。与此同时,少数地区为了解决军粮问题,开始了戍兵屯田。
洪武十九年,沐英建议:《(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同上,卷179,页6上)这一奏章,获得了朱元璋的批准和奖励。谕户部臣说:“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赵充国始屯金城,而储蓄充实,汶享其利,后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废,英之是谋,可谓尽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然边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实难,宜缓其岁输之粟,使彼乐于耕作,数年之后,征之可也。”(同上)在明廷的提倡与鼓励和在沐莱的与推广下,屯田成为云南驻军的一项制度,并以此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准则,所谓“岁较屯田增损以为赏罚。”如,曲靖卫播种800石(约合三千多亩)。该年,傅友德遣人至京奏事时,称:“督布政司窍实云南,临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乌撒等卫,及沾益,盘江等千户所,现储粮数一十八万二干有奇。”这些粮食,拿来供给军食,犹感不足,“宜以今年府州县所征,并故宫寺院入官田,及士官供输,盐商中纳戍兵屯田之入以给之。”(同上,卷143,页10)可见当时已“戍兵屯田”了。据载,当时云南后卫 (治昆明)的屯田,到洪武十八年已做到“军不乏食”了。洪武二十年,命孙茂“以钞二万二千锭往四川市购牛万头”以备云南屯田之用。“将征百夷,欲令军士先往云南屯田预备粮储故也。”(同上,卷184,页4上)同年八月,命令四川都指挥司“选精兵二万五千人给军器农具,即云南晶甸之地屯种。”同时,“复命云南楚雄府开中盐粮”,这是由于早些时候,“商人输米云南楚雄,曲靖诸府,给以淮浙盐,末久而罢,令戍卒屯田以自给,至是仍啬于用,户部请复行中盐法”。 (同上,页6上)同年九月;并命沐英,在楚雄、景东一带大力扩展屯田。“自楚雄自景东,每一百里置一营屯种。”(同上,卷185,页1下)又在同年九月,命令湖广,“以靖州、五开、及辰、源等卫新军,选精锐四万五千人于云南听征,”又令“市牛二万往彼屯种。”(同上,页6上),并“分屯曲靖,越州。”(同上,卷187,页4上)同时,“以白金二十万两给各府县籴粮备用。”“复诏耿炳文下率陕西士军三万三.千人往云南屯种。”又于该年10月“于定边(今称南涧),姚安等处立营屯种,以俟食隙往进,既而又命桓等领兵屯田于毕等卫。(同上,1—3页)同年十二月,复命沐英等,“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置军屯田。兼令往来递送,以代邮传。于是:自曲靖大忽都至云南前卫易龙设堡五,自易龙至云南右卫黑林子设堡三,自黑林子至楚雄,禄丰设堡四,自禄丰至洱海卫普朋设堡七,自普朋至大理赵州设堡--j自赵州至德胜关设堡二。”(同上,页6至6)以上共计设堡二十三个,既发展了生产,也便利了交通,所以“人称便焉”.
从洪武二十一年开始,云南各地普遍开始屯田,命马烨“率西安等卫兵三万三千屯戍云南。”并在“禄肇立堡”(同上,卷188,页6上)。洪武二十二年九月,为了便于屯田粮储,而减低速价以致商人,解决盐重米轻问题。到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命常升往湖南辰阳“集民间丁壮凡五千人”,于平夷卫(今富源)屯田。这是通过“垛集”(征兵的一种制度)以达到屯田的目的。此外,又于洪武二十三年夏四月在寻甸屯田(在甸头的易龙驿和甸头的果马里)。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又在宜良置屯垦田。又在二十三年六月,接受唐胜宗的请求,“以源州及思州宣慰司镇远,平越等卫官牛六千七百七十余头分给屯田诸军。”(同上,卷202,页6下)当时麓川傣族农奴主叛乱,进行军事活动,必须屯田生产以解决军粮问题。到洪武二十五年,云南各卫“垦田至百余万亩”,基本上已全面实行屯田了。
2.商屯和民屯
商屯是明代盐商代替政府运送粮草前往边境的屯垦。太祖洪武三年,为利用盐商输送粮草供应边地军需,实行开中法。盐商为避免收购,运送粮草的费时和其他种种困难,于是在边境召募农民开垦荒地耕种,就地取得粮食,草料换取盐引,支盐远销各地。《明史•食货志》对商屯的解释是:“募盐商于各边开中”。根据《明实录》及《明史》的记载,明代不独在今云南的昭通、曲靖、昆明、建水、沾益,普安等地实行“开中”,也还在玉溪、红河、楚雄、大理、保山、德宏等地区,先后实行过商屯。为了加强盐业专卖的管理,在洪武十七年,新置盐课提举司三。即白盐井、安宁、黑盐井。”在这些盐商中,除了本地的地主兼商人外,更多的是“客商”。这些“客商”,必然和在全国其它地区一样,也在云南各地开设了许多“商屯”。《云龙记往•段保传》中有关于当时五井盐区“客商”集中土地的记载,应是与“商屯”有密切关联的真实情况的记录。自明宪宗成化以后,“开中”由缴纳粮食改折货币(银纳化),也就是地租的形态逐渐由实物地租过渡到货币地租,盐商就不再需要进行“商屯”了。这种情况,在云南也毫无例外。如洪武十七年,在云南就有用金银海贝(货币)来代替粮谷(实物)来缴纳地租的。该年十二月,云南左币政使上奏“今后秋租,请以金银海贝布匹朱砂水银之属折纳,诏许之。”(《洪武实录》卷169,页3)直到洪武十九年,还有“不许输谷”现象,造成“商人少至”,“军饷费给”现象。“商屯”既巳进入黄昏境地,那么,这些“商屯”的土地,必然为当地豪强地主所包买集中,而成为他们的庄田了。
至于有关明代开设“民屯”的具体情况,也间有一些记载。考民屯始于三国,献帝时,曹操在许下屯田,后来推广到司、豫、冀三州,招募农民来耕种,叫屯田客,官给牛种,收获果实;厂官取六分,民取四分。如自备耕牛,官民对分。明制,“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 (《明史》卷77,《食货志》)这是相对减轻了。洪武六年,“太仆丞梁野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同上)所谓“流亡”,实即穷苦无依的贫民。根据记载,在洪武十七年,明政府“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洪武二十年十月,“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出一丁,往屯云南。” (《洪武实录》卷186,页3上)现在云南地名中凡称“卫、所、营、屯,堡”的居民点,大都是明代“军屯”的遗迹;“民屯”则多称,“村、镇、街”等。至于“坝子”,则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对平地或平原的称呼。
一般说来,民屯、组织性强,耕地面积大,能利用先进耕作法,产量较高。但是,如果管理不善,官吏营私舞弊,渔利剥削,那就会走到反面。所谓“屯粮之轻,至弘、正而极,嘉靖中渐增,隆庆间复亩收一斗。然屯丁逃亡者益多。管粮郎中不问屯田有无,月粮止半给;”(《明史》卷77,《食货志》)这虽指“军屯”而言,“民屯”也未能例外。
总上所述,当时各种屯田,几乎遍及各省,屯种面积估计约在一百五十万亩以上,占当时登记在册的全省总耕地面积将近一半。这些土地来源,除部分是接管元代的屯田和“没官田”外,绝大部分都是些原属于农奴主或奴隶主的领地。从上来追溯,这些土地,在唐代时,也都是南诏均田制下,属于官吏的分田。(《蛮书》卷5,)明廷实行中央集权制,确立了封建国家对各土司领地的最高土地所有权,这就使明代有可能大规模地在原属各土司的领地内开设屯田,为促进这些地区封建地主的创造了前提,因而,屯田的开设,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三封建地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有好几十个。其中主要或部分居住在云南境内的有二十一个,约有一千万人,占全省总人口三分之一。明代住在云南地区的有白族,彝族、纳西族,哈尼族,傣族,壮族等族人民,在明代,云南地区因为长期受到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社会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许多地区已经由封建领主经济进入封建地主经济阶段,甚至有些地区如昆明,大理等,地主经济巳占统治地位,农业已有显著发展,并且普遍使用犁耕.当然,住在高寒山区的一些部落,生产力还比较低下,但也有了阶级分化,开始从原始公社制末期进入奴隶制,有的直接进入了封建制。
明代到云南从事农生产的(包括屯田等)汉族劳动人民,估计有四,五十万人之多,其中仅军屯就有二十九万人。再加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一些外地移民,留戍家属、仕宦落籍、谪迁后裔、工商流寓,宗室藩封等等,这一大批从内地来到云南的各族人民,必然会给云南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带来极深远的影垧。由于大量土地的开垦,许多在云南历史上有名的水利灌溉工程都在这时得到兴建和整修。宜良坝子的汤池渠水利工程长达三十六里,是一万五千名屯军凿的,昆明南坝闸工程的兴建,做到了“田不病于旱防。”再就是滇池海口的疏浚工程也一再整修,使整个滇池平原摆脱了“每岁秋夏,雨集水溢,田庐且没”的灾患。此外,如石屏异龙湖引水工程、保山九龙池的灌溉系统,邓川的弥苴怯江堤工程等,都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素以干旱著称的云南县(今祥云)坝子,人民群众还创造了“地龙”灌溉网(地下蓄水池和渠道),减少了水的蒸发量,使大片荒田受到灌溉而成为绿野。特别是清华洞一带,风物更加美丽了,出现了人们常说的“土地挂在悬崖上,庄稼长在石窝里,片片梯田耸云霄,条条清泉绕山岗”的壮丽图景。当时就有“云南(县)熟,大理 (府)足”的光荣谚语。这些工程的修建,绝大多数都是汉族屯户和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血汗共同凝聚而成的。例如昆明县(拓东城)横山水洞,“引泉以灌入村之田”,《滇记》称:“隆庆六年左布政陈善始成是役,溉田四万五千六百余亩’。再如漠池地志称:“明初傅友德,沐英驻守云南,皆事屯田,而滇池之水,皆首为灌溉之利。”又如邓川的弥苴怯江堤,就是“东堤军屯修筑,西堤里民修筑.”当正统十三年时,邓川的“湖尾沟渠淤塞,以致水不能泄,禾苗淹没”,幸得“州、卫军民相兼疏浚”。宾川鸡足山南的上仓湖,最为幽胜,居民有灌溉之利。当时,汉族屯户与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田地是“畛畔相入,盈亏相察”。这些水利事业的典修,不仅灌溉着屯田,也促进了广大云南地区生产的发展,所谓“军民俱利”、“夷汉利之”。这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事实。
除灌溉系统的发展以外,驿路也取得了重大成绩。如洪武二十九年, “修峨嵋至越 道途毕工”.(《洪武实录》卷 246)洪武二十七年修《寰宇通衢》书成,“其方隅之且有八,……西南距云南金齿,陆行为里六千四百四十四,马驿一百。水陆兼行为里八干三百七十五,驿一百一十三。广西云南之各二,……云南水马驿九十六,为里七千二百, 马驿八十三,为里五千二百七十五。”(同上,卷 234,页6至7)交通的发展,为工农业产品的生产及分配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如洪武二十六年,赖镇在景东就“置廨舍邮驿仓库,又立屯堡”达到“军民相安”。
(同上,卷225,页4至5)同时,也扩大了边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如云南的白药(三七)传入中原并得到了。
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在内的各族人民,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进了云南边疆,并且在少数民族中得到广泛传播,这就大大提高了云南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凡是有水利的地方,水车,水碾,水磨等工具都普遍得到使用,“舂碓用泉,不劳人力”,这就大大地改变了云南上“二牛三夫”的落后耕作方法,如樊绰所描写的:“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一佃人秉耒。”(《蛮书校注》卷七)进入云南的军匠,就地铸造和内地规格相同的先进生产工具,内地农作物的优良品种也得到推广和。
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和矿业也有了进步。大理西郊点苍山生产的玉石,作为各色各样工艺品行销全国各地。此外如矿产;虽在云南已早被采掘,但是,大规模的开采还是从明代开始。如铁,钢,银等开采的主要技术力量却是来自军匠。根据云南地方志和宋应星《天工开物》上的记载;两相比较,云南腹地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已基本上达到了全国的水平。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也有了进步。定期集市在各地普遍建立,“四方之货一入滇,虑无不售。”少数民族在坝子上的各种交易活动也更加频繁了。云南史上,向以“贝”为货币,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云南购物也以白银为主币了。如洪武十九年二月,命许英“赍白金二万二千五百两往乌撤等处市马。得马七百五十五匹。”(《洪武实录》卷177,页2下)“贝”终退居于次要地位了。货币的统一更加进一步紧固了云南和祖国内地经济联系的纽带。
但是,在这里必须指出,尽管明代云南商品经济已有了显著的发展,可是局限性还是非常大的。它不象沿海咆带,手工业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云南,有明一代,自始至终,经济的发展,还未能为资本主义萌芽准备好更多的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