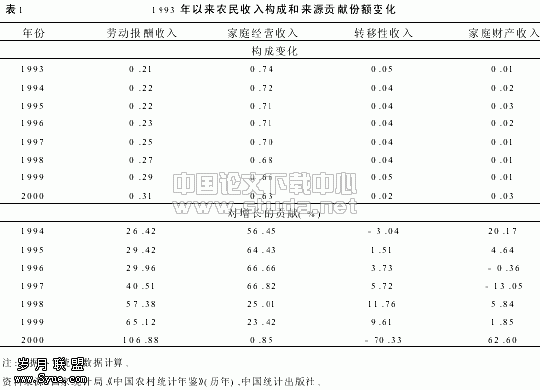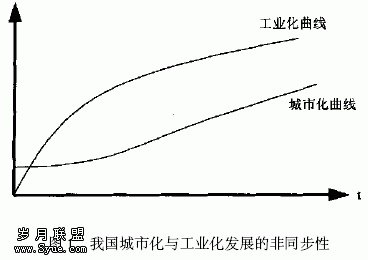论农村法治的基本框架(一)
我赞成以法律方式保障农民权益。但是,以什么样的法律方式保障农民权益,却值得研究。制定和颁行《农民权益保障法》是不是种好的方式,也值得研究。我认为,《农民权益保障法》的立法设想,在理论上并没有抓住农村法治问题的要害,在法律技术上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即便它真的出台了也难有多大的实用价值,社会效果不会显著。与其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推动这一立法,不如直奔主题地去研究和推动涉农的关键性法律问题,为农村法治框架的建立奠定基础。
在此需要声明的是,我对《农民权益保障法》立法设想的具体内容一无所知,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资料。我所指的这一立法设想,是凭我的经验和想象来界定其内容的,也许和发起者所说的立法设想不同。
另外,我要谈的这个题目,也许要用一篇博士的篇幅和架构才能表达清楚。但是,由于忙于生计,没有时间和机会坐下来写篇规范的论文,我只能谈谈我认为重要的观点,用粗略的方式来表述观点。
一、《农民权益保障法》立法的必要性及技术和制度障碍
在这个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被大规模侵权的时代,说立法保障农民权益没有必要,是不是需要点勇气?作为一个有十年从业经历的律师,我说制定《农民权益保障法》没有必要,是出于一种理性的怀疑,而不是出于价值判断。耳闻目睹农村失落的现实,看到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一贫如洗,缺乏生活出路,流落城市,流落风尘,我痛心但无奈。我办理过一个青年农民杀人的案件,起因是他的未婚妻进城后卖淫,最后在各种纠纷引发的冲突中他杀了人。当他面临法律的制裁时,我能感受他内心的痛苦。曾经有一个被政府执法队员打伤的农民找我咨询,问了一个让我难以回答的问题:镇政府在抓计划生育的过程中为了乱收罚款,抓人、打人、抢走财产并毁损财物;既然镇政府执法队打我是非法的,我能不能还手,正当防卫?要在法律上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并不容易。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只有针对正在发生的犯罪行为,才能实施正当防卫。镇政府执法队乱抓人、乱打人、抢东西不是执法队员的个人行为,而是职务行为,如果说其行为是犯罪,犯罪主体是镇政府。虽然法人可以作为犯罪主体,但政府能成为犯罪主体吗?这种情况在法律上应当怎样解决和处理?为此,我思考研究了很长的时间,并完成了《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及其救济》的硕士论文。这篇论文被武大的老师称为当年武大宪法行政法专业最好的一篇硕士论文。说这些,是想说明我对农民是有感情的,但感情不能代替法律,法律应当合乎法理和逻辑,推敲法理时应当有平静的心态和严谨的论证。
我怀疑《农民权益保障法》的立法必要性,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弱者权益保障立法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变异
我国现有的弱者权益保障的特别立法有:《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1990),《未成年人保护法》(1992),《残疾人权益保障法》(1991),《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6),《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4)。这些立法的理论根据是对社会弱者权利加以特别保护的立法理论。这种立法理论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特别是政府主导的立法体制下,上述社会弱者权利保护立法之成为现实,是有其现实原因的。与其说这些立法出台是出于立法理论和道德热情,不如说是部门利益推动的产物。我们且看:先有侨办和侨联,后有《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先有共青团和少先队,后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先有民政部门和残疾人联合会,后有《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先有妇联,后有《妇女权益保障法》;先有老龄委和老干局,后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先有工商局,后有《消费者权益保障法》。
上述已有的社会弱者权益保障立法,从出台至今,已有十多的。经过了实践检验,其效果如何,现在可以作研究、下评价了。我国的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老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做得怎样?对此,我不想加以评论,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评价。对其作整体的评价超出了我的能力。我想知道的是,这些社会弱者权利保护工作做得好还是不好,与这些立法的实施有多大的关系?与其说这些立法保护了社会弱者,不如说这些立法为相关部门的存在和获取社会资源(如财政拨款等)提供了法律依据。侨联、共青团和少先队、残联、妇联、老龄委、消协等,这些所谓的群团组织是不是部门?我认为是。这些组织的管理者都是国家干部嘛。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中国的立法与部门利益之间的关系相当明显,这是很多法律出台的真正原因,那些立法理论是美丽的包装而已。
《农民权益保障法》有没有可能派生出中国的农民协会或者农会?我认为,如果这部法律真出台了,应该能够派生出农会。我想,这可能是推动者真正想实现的一个具体目标。如果《农民权益保障法》能够派生出农会的话,我是会赞成的,农民确实需要自己的组织;否则,《农民权益保障法》只会成为词语抽象动听的一篇政治宣言或者道德宣言而已,不可能有多大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但是,话说过来,有了农会又怎样?我们不是已经有工会了吗?中国工人的权益保障工作做得如何呢?大家可以看看珠三角、长三角数以千万计的打工仔、打工妹,看看大江南北永远留在大地深处的矿工们,看看成群结队讨要工资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们,看看那遍布城市的下岗工人,看看被拖欠工资的乡村教师。看看他们的状况,数数他们的数量,答案就有了。我所在的城市,工会以及团委都是好单位,不仅政治待遇好,效益也好。投资巨大的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都是他们掌管的资产,都对外出租成了餐馆、商场和营业性的娱乐场所。这些庞大资产都是财政拨款和市民捐款建成的啊。为建青少年宫,我是捐了款的。但是,我的女儿从来没有机会免费享用一下名义上是他们的宫殿。说工会成了众多利益部门中的一个利益主体,应该不过分。工会的利益,并不代表工人的利益。如果有一天《农民权益保障法》出台了,农会成立了,那会是怎样一个农会?我不敢把话说绝了,但是,我认为在现有体制下,农会象工会一样成为准政府部门的可能性太大了。如果农会象工会等组织一样,成为官僚机构和准政府部门,我认为有不如无。首先,要养许多农会干部,每年要花费多少亿的财政收入啊,这难道不会加重农民负担吗?第二,这些行政化的群体组织的存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产生的阻力和障碍。试想,如果中国有了真正的工会,工人自己的组织,现有工会的这帮人的饭碗都成问题了,他们能不反对吗?
2、《农民权益保障法》在法理上有逻辑悖论
公民权利生而平等,要为某一群体特别立法以保障其权利,须有特别的理由。目前看,从立法理论上的理由就是该群体乃弱势群体。我前面在列举我国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特别立法时,没有列举《工会法》。工人是不是弱势群体?相对于资方而言,工人就弱势群体。但也不尽然。在法治社会,在工人可以组织工会的情况下,工人的数量远远多于资本家,只要工人组织起来了,工人就并非弱势群体。但在我国,劳动力的供给过剩、资本短缺的状况下,又没有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工人是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应无疑义。农民是不是弱势群体,也不尽然。但在我国社会现状下,农民是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也应无疑义。
但是,按照我的理解,立法理论所称的弱势群体,并非一般意义上所称的弱势群体,盖有法律上特殊的意义也。强弱乃相对而言,没有绝对的强弱,因时因事因地而异也。立法理论上所称之弱势群体,应为因客观原因形成的强势群体,有不能克服的缺陷和弱点而弱势,而且能识别的群体。如老人、小孩、病人、残疾人和妇女。归侨及侨眷中有很多人属强势群体,但是20世纪70—80年代从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返国的侨民确为弱势群体,强势群体中的华侨归国者寡。所以,把归侨、侨眷作为弱势群体有一定的理由,其弱势乃他国政治及战争等不可抗力所造成。但是,农民是弱势群体吗?农民的客观弱势却不是客观原因所造成,而是制度歧视所造成,这并非是不可抗拒的。法律就是制度。制度就是法律规定本身。换言之,农民的弱势是法律规定及实施的不当所造成;现在,又以农民是弱势群体为由,要特别立法保护其利益。这二者之间难道不存在法理上的冲突和悖论吗?好比在一个奴隶制社会中,在法律规定是一部分人是奴隶的同时,又颁行一部法律叫做奴隶权益保障法。岂不黑色幽默?如果农民的弱势地位是由法律规定(制度)本身所造成,废除这些造成农民弱势的法律规定不就行了吗?不废除旧的法律,而是制定一部新的法律,新旧两种理念冲突的法律如何实施?治治的要义之一是法律统一、和谐的理念。法律之间相互打架,适用何种法律就成了问题。这是法律体系自身的神经分裂症,将导致疯狂。逻辑是法律的生命,相互冲突的法律,在逻辑上足以使法律本身灭亡。如果出台的《农民权益保障法》不与现行法律和制度相冲突,可以说这部法不会有多大的价值,不过是法律的花架上又多了一个点缀;如果出台的《农民权益保障法》不与现行法律和制度相冲突,又将毁坏法律自身。岂不两难?
如果把法律上的弱势群体定义为因客观的、难以克服、不可抗拒的因素所造成的事实上弱势的群体,那么,农民就不是弱势群体,中国农民的弱势更多地是法律及制度本身所造成;以保护弱者的立法理论为依据制定《农民权益保障法》,就不足为凭,没有理论依据。贫穷不意味着法律上的弱势,文化水平低也不意味着法律上的弱势。只要给农民身份上的自由、财产上的自由和结社的自由,他们就会富裕起来,文明起来,强大起来。
谁是农民?这是个问题。这是上十分重要的问题:身份识别问题。一个人有没有资格享受《农民权益保障法》的保护,一个人有没有资格依据《农民权益保障法》向法院提起诉讼,都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有农民的身份。如何识别农民的身份,有以下几个识别标准,但都有致命的缺陷。
(1)以户籍为标准识别农民身份:户口的人就是农民,城镇户口的人不是农民。户籍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我们暂且不论(应该是违宪的)。现实的问题是有很大一个群体,他们虽然是农村户口,但从事工商业等非农行业,居住在城市。他们中出现了许多农民家、农民工人、农民教师(民办教师)、农民律师等。如果有一天《农民权益保障法》出台了,一个腰缠万贯的农民企业家手持该法,说我是农民,是弱势群体,请给予特别保护,岂不风趣。
(2)以职业为标准识别农民身份:以农、林、牧、副、渔的生产劳动为职业的人是农民。问题有二:①农村人口中有人数众多实际上失业、半失业不从事农业劳动的群体,有从事非农职业甚至亦工亦农、半工半农的群体,还有许多没有劳动能力的未成年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他们并无农民这种职业身份。②大农业的外延很宽泛,使以农业劳动为职业的界限也模糊起来。如果城市户口的人到农村做农业工人或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或科研,这些城里人岂不也成了农民了吗?甚至农业企业家、农业家(育种、生物、农艺、林业专家)等是不是农民?③依此标准进城打工的农民是工人而非农民。④在化、集约化、商品化的农业经营生产中,工业和农业的界限难以区分。作为职业的农民身份,本身也是模糊的。
(3)以地域为标准识别农民身份:凡生活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都是农民。问题是:①农村地区这一概念本身就十分模糊。在城市化的大潮中,在城乡结合部。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你很难区分农村地区和城镇的边界;②城镇户口的人生活居住在农村地区,是否认定其农民身份?③农村地区生活居住的非农业人口如教师、医生、商人和政府工作人员等,身份如何界定?
(4)以户籍、职业的双重标准识别农民:有农村户口并且以从事农业产业劳动生产为职业的人是农民。上述许多问题仍然存在,把太多的人(农民工、农民商人、农民企业家、失业人口、无劳动能力的、老幼病残等)排除在外。
(5)以户籍、职业的兼容标准识别农民:有农村户口或者以从事农业产业生产劳动为职业,二者居其一便是农民。
… … …
我不想继续探讨农民身份的识别标准了。如果识别一个农民的身份都这么难,那么,司法操作和法律实施的成本会相当高。更重要的问题是,农民作为一种身份,应当是可以流动的,不论是户籍意义上的农民流动,职业意义上的农民流动,还是地域意义上的农民流动,都应当是大力推动的事情。如果农民身份在频繁流动,农民身份如何识别?《农民权益保障法》的有效实施是否要以农民身份的不流动为前提?这种前提是否违反了潮流?各种身份应当可以交互流动。如果哪天我厌倦了都市的繁华,向往乡村里田园诗画的生活,制度安排也应当满足我的这种愿望。如果市民和农民身份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农民身份的识别就更困难了。
4、《农民权益保障法》的制度障碍:谁来执法和司法以保障农民权益?
“谁是农民”的问题之后,紧接着的就是“谁来保障”的问题。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应该讨论一下我国当前的执法和司法主体存在的问题了。
我国的许多立法,都规定某某部门或者机关为该法的实施主体,即规定某行政部门或机关为该法的主管机关或者执行主体。我认为这是我国立法理论和执法实践中的一大误区。因为,一部法律的有效实施,往往涉及众多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利益主体、社会群体,涉及、行政、、文化等多个领域。将一部涉及众多主体和领域的法律由一个部门去实施,一方面往往超出了其职权和能力范围,另一方面又赋予了该部门一定程度的执法垄断权力,强化了部门利益。我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之严重,与这种执法体制有莫大的关系。在一个法治国家,由法律来统治国家和社会,而不是由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来统治社会。一旦法律颁行实施了,所有与这部法律有关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社会群体、公民和法人都必须遵守并实施该法律,而不应将实施法律的权力归定为单一部门专有。这才是真正的法治。但是,在我国现有体制下,这种法律的直接统治往往行不通。如果不规定某一部门为该法律的实施机关,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有利可图的事情,多个机关或部门争着管、抢着管,争权夺利;无利可图或者棘手的事情,互相推委,没人去管。这时,国家机关不再是中立的、超然的社会公正提供者,而成为社会生态中趋利避害的动物。
目前关于信访立法的争论,就与我国当前的利益化了的执法、司法体制直接有关。我在2001年的一篇中就指出,我国专门的信访机关,只有程序上的价值,而没有实体上的价值。信访机关受理信访案件,却没有权力和能力进行实体性的处理,而是批转给有关部门进行处理。而信访、上访的老百姓,期待的是公正的实体处理结果。这种实体与程序的背离是如此严重。无法有效地解决实体问题,怎么能化解社会矛盾呢?我完全赞成于建嵘先生对此的观点:取消专门的信访机构。取消信访机构后,问题怎样解决?解决之道很简单: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各级立法、行政、司法、党群部门都应当从自己职责和分工的角度,承担起信访的职能,履行各自化解社会矛盾的职责,按照各自的职责和分工,不仅在程序上受理信访、上访案件,而且必须依法进行实体性的处理。也就是说,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职责和分工将全部党政、立法、司法机关都变成信访机构,承担起目前专门信访机构所承担的职能。这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若将现有的专门信访机构变成准司法机关,违反了依法行政、职责法定的基本原则,注定要破坏法治。这已有先例。我国已经把纪委变成了准司法机关,而且比一般司法机关享有更大的权力。纪委的双规限制人身自由,但缺乏法律依据。纪委司法化后,权力极速膨胀却缺乏制约。据说一家地级市的纪委,每年的“暂扣款”(暂扣款应予退还,或移送司法机关,实际纪委不退还或移送)近千万元,正在以培训中心的名义建:“双规楼”。这种偏离法治规道的做法,类似武侠小说中的邪门功夫,虽有急功近利之效,却是舍本逐末,最终会走火入魔、自废武功。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不断出台许多改革措施,但是改革效应递减,以至于越改越乱,改革加速了王朝的灭亡。这种教训应当为前车之鉴。我认为根本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我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在民主和法治的规道上进行系统的制度创新,才能闯条出路。
再谈谈我国的司法主体存在问题。我国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已经颁行好几年了。这两部法律的执行情况如何?如果中国的法院和检察院对规范自己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都不能遵守和实施,难道我们还能指望它们能很好地实施其它法律吗?事实是,我国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律师法》规定:只有取得司法资格的人,才能从事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职业。中国的律师早在1990年就开始实行的方式授予律师资格。律师资格考试历经十余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现在的司法资格考试就是从律师资格考试延续而来。但是,长期以来,对法官和检察官的从业资格却没有限制。司法资格开考以来,有多少法官和检察官通过了司法资格考试?我手中没有数据,但我知道极少有现职法官和检察官司通过司法资格考试的。我所在的城市,在司法资格考试开考的第一年,法院、检察院和司法局系统参加考试的数互公职人员中,竟无一人通过考试。我估计,在全国范围内,现职的法官、检察官司中有80左右的人没有司法资格。这些没有司法资格的人,按照《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规定,是不能做法官和检察官的,更谈不上行使司法权。可是,事实是,我国80%左右的法院判决和检察院起诉决定,是由这些没有司法资格的人作出的。这就是我国司法主体的现状。
在目前这种执法、司法体制和现状下,如果《农民权益保障法》出台了,由谁来执法、司法?是否也象许多法律一样,指定某个行政部门作为该法的实施机关?这部法律能被很好地执行和遵守吗?其实,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更损害法律的权威,更打击人们对法治的信心。有不一定比无更好。
我国的工会法是由工会作为主管和实施机关的。这在法理上非常荒唐可笑。工会应当是工会法调整、临管的对象,怎么能由工会自己做执法者呢?我国不仅有立法者就是执法者的问题,自己给自己立法的问题;而且还存在执法者就是被执法者的问题,自己给自己执法的问题。工会法就是一例。
我还未见过以工会法为依据提起的诉讼案件。如果工会会员与工会发生了纠纷,能不能向法院起诉?是以民事案件起诉,还是以行政案由起诉?我不知道。如果一部法律不能在司法程序中适用,这部法律的价值不值得怀疑。
如果《农民权益保障法》出台后派生出了农会;农会与该法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农会会不会成为该法的执法者?该法由谁来实施和执行,是农业部,还是农会,以及其它?这都是应予考虑和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