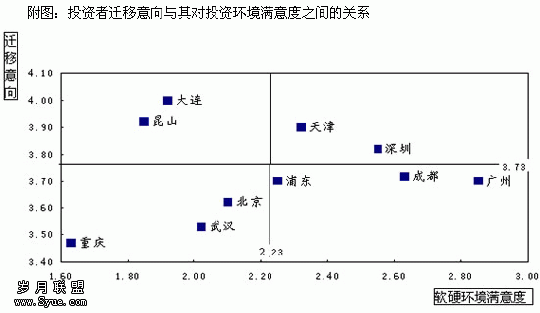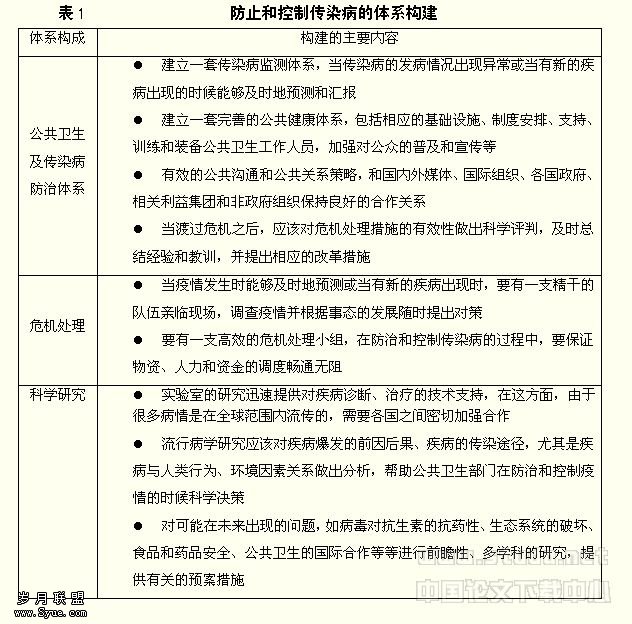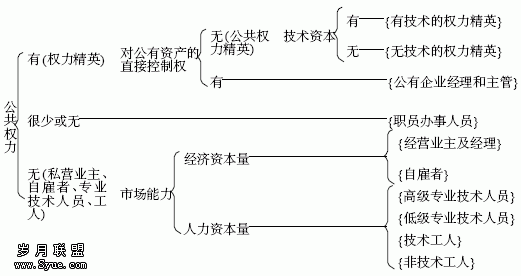从陈村计划生育中的博弈看基层社会运作
Abstract:Based on the field work in Chen Village in the east plain of HenanProvince,this paper present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game in the process offamily planning in rural China.It attempts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and society or state and villagers,the evolution of local social order and patternof local social operation through the macro and micro2analyses of the game in familyplanning in Chen Village.In micro-game analysis,the authers analyze the main meansand strategies of game used by players.Based on the micro-analyses ,the authersanalyze the macro-game and try to clarify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family planningin the game and formalization of outcomes of games in past over 20years.Four changestook place in the game of family planning in Chen Village (and neighboring areas)。In the conclusion part,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two-line-operatingsociety"and finds the model of evolution of order.
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Bourdieu )认为:"社会学家和学家的职责在于对社会的运作进行分析。法国一位科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Bachelard)说过:'科学必须发掘隐秘',这就是说,既然有一个研究社会的科学,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发掘隐秘??"(转引自孙立平,2000:5)。本文所要发掘的隐秘就是基层社会的运作。它通过对中部一个村计划生育中博弈的实地考察,力图更好地发现当今中国国家与社会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基层秩序的演变,以及基层社会运作的模式。
一、分析框架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有三个核心概念:博弈、事件和制度。
博弈即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和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博弈参与者都想从博弈中获得利益,这种利益是各博弈方追求的根本目标,也是他们行为和判断的主要依据。①「这里是以有限理性人为前提预设的(参阅西蒙,1989:45-101),各博弈方并非充分理性的,他们各自的决策也不是在寻求他们的最大得益,而只是在有限理性限度内力求获取较满意的收益。」
孔飞力(1999:288)认为:"虽然'事件'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并无确切的定义,但在中国的官僚实践中,它却是一个很能够说明问题的用词。'事件'有一个开端(当有人首先引起事端)和一个结尾(当某人因处理事端的方法而受到赏罚)。一个官员的仕途取决于他的表现,而他的表现则取决于他处理具体事件的优劣。"按照孔氏的概念分析,计划生育也是事件。孔氏还说",'事件'作为一种机会,不仅可以为一个人带来幸运,也可以同时服务于上司和下属的需要,并编织起使一个人得以在公共生活中立足的人际关系。"(孔飞力,1999:288)当然这是为了说明"叫魂案"事件中国家作为工具和制度对于对方的意义,从而分析出了君主权力和官僚权力的(结构性)紧张关系。同孔氏一样,我们关注的也正是事件所反映的人际关系、人与制度的关系等方面。但不是所有的事件都是利益冲突性的博弈事件,因此本文把"事件"限定在利益冲突情况下发生的各方进行博弈的事件。
制度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在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模式,以及与此关系相联系的规范体系。这里制度取两层含义,一是政策等条文规定,二是人们在行动中所实际遵从的关系模式。本文称前者为"文本制度",后者为"实践制度".这两层含义反映着表达和实践之间既存在一致又有分歧矛盾的关系。本文中制度的核心思想是关系模式,尤其是行动者在互动中体现出的关系模式。博弈、事件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博弈是在事件中进行的,制度的形成或演变是在诸方反复博弈的事件过程中发生的;第二,博弈事件过程既是当时制度——尤其是实践制度——的具体展现,又是制度演变的动力。
这种概括是综合"结构/制度"和"过程/事件"两种分析方法①「关于这两种分析方法的关系的梳理主要了张静(2000)在《基层政权》中"方法原则"的讨论。只是张的"制度"概念是指"对社会各种行为正当性的确定体系".与本文所用的制度概念有差异。我以为这并不妨害采用她的讨论。」包涵的思想与博弈论思想的产物。结构P 制度分析重视行为的社会规则;分析社会行为时,分析者往往会特别重视具体"事件"或"过程"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关系,因为不同的制度,会刺激出不同的行为(发生不同的事件)。而"过程P 事件"分析重视丰富的、具体的、过程的描述。实际上,发生在事件中的博弈过程在反映制度和结构的同时,也对之产生影响作用并改变制度和结构。
(一)陈村概况
陈村位于豫东平原,该村95户,人口约350人②「其中包括经常居住在村的非农户口者12人,户口分得耕地但不经常在村的3人。未包括(案例8)逃跑在外的一户至少5人,户口已迁走耕地还未退的3人,2个有耕地但在县以外的地方求学且户口已经农转非的大学生。」,分两个生产组,东组人均耕地8分,西组人均111亩。陈村人谋生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冬小麦和玉米,其他有大豆、红薯、绿豆等,作物以棉花为主,一般由于条件所限种的也少。基本上每家都养些猪羊牛作为一项主要收入源。10多年前,村民主要在农闲时干些离土不离乡或离土又离乡的零工,挣个零花钱;近些年,有些人或有些户一家人都整年或几年一直在外打工,打工成了另一个主要收入来源,有的户靠打工已存款十来万元。目前来看,若没有外出打工这一项,这个村的村民很可能饭也吃不饱。
(二)陈村人的生育观
生育观是人们对生男育女的基本看法和观点。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人们长期受同一文化传统影响,他们有着大体一致的生育观。从地理位置看,陈村是典型的连接东部和中西部的平原农村。诸如多子多福、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观念在陈村人头脑里基本上没太大变化。能感觉出来的一点变化是多子多福的观念有所减弱。陈村人的生育观以及使之形成的相关观念可以概括为:首先,陈村人的幸福(的条件)观是"有日子有人"."日子"就是指物质生活水平至少不怎么紧张,手头较宽松。"有人",就是子孙满堂有老有少。在他们看来,当有了日子又有了人时,就会成为幸福的人、享福的人。第二,陈村人有一种信念:过的是小孩子的日子。在陈村会经常听到"过的不就是小孩子的日子吗"这样一句话。这反映了一种以"子女为生活中心"的观念。如费孝通所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两个自我,一个是理想的自我,一个是现实的自我(费孝通,1998),以生孩子来获取再一次的重生机会对缓解人们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给人以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具有重要作用。第三",不孝有三,无后(指男孩)为大".习俗所安排的是男系继承制,儿子天生具有继承父母财产的合法权利。最后,生理因素和社会文化造成了男女有别,从而重男轻女本身也是一个现实的生活策略,比如养儿防老和人多不受气等都很现实(参阅李银河,1994;郭正林,1996;费孝通,1998;等)。
(三)关于陈村生育人口的统计结果和提出的问题
笔者是从材料中发现问题,然后为回答问题继续搜集材料的。在陈村做的统计结果③「对统计的详细内容感兴趣的读者,请参阅同题目硕士原文(人民大学图书馆)。」显示,近年来陈村人口的超生越来越少。从对陈村不同年龄阶段的夫妇生育子女数的统计,可以看出生育数量基本上保持在两个子女和三个子女,以两个的居多,且多是一男一女(两户双女户于2000年迁走一户)。我把这种状况称为"弹性动态平衡".弹性两端是村民强烈的生育意愿和控制人口的国策。那么,弹性动态平衡是怎样产生的?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弹性动态平衡在陈村有可能继续吗?为什么?
上述问题是基于跨度达20年之久的不断博弈的结果提出的。下面拟从行动者采取的博弈方式与手段和博弈过程两个视角对它们做出回答。虽然博弈方式和手段是在博弈过程中应用的,两者本为一体,但为了分析的深入和方便,则先对选择和运用具体策略,即博弈方式和手段进行分析,而后在此基础上对跨的博弈过程作宏观分析。
三、博弈方式与手段:微观分析
博弈的方式和手段是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反复过招中运用的,而且通常不是孤立地使用,而是根据具体情景几种手段综合运用。但为了分析的需要,把它们归纳为以下八种博弈方式和手段。
由于采用何种方式和手段与具体博弈情景密切相关,所以没有区别它们的重要性,分析的先后并不表示重要性和使用频率的高低。
(一)利用规则
文件与法规政策是计划生育工作中各博弈方的游戏规则,主要是指乡镇级及其以上政府机关所发送和传达的文件和讲话精神等。文件相对于下级土政策(翟学伟,1997)是普遍主义的。在基层社会运作中这个因素一直起着宏观支配作用,在具体操作中有各种变通,特殊主义几乎无处不在。不同的博弈方都在利用规则。比如",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作为政策的力量,就是(计划生育)"小分队"等强大的合法性后盾。
村民也在利用文件政策。对生二胎游戏规则的规定和解释中的缝子的利用,是村民和干部同时利用同一规则进行互利式合作的一个例子。办二胎准生证的理由之一是,符合"经县级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织鉴定,报市(地)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织确诊第一个子女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条款。上级(或国家)的人口生育计划中有这方面的指标,各地都有。于是,村民可以此作为突破口来寻求生第二胎;而乡村等有关干部也可利用这一点从中牟利。如村民C2,花了近3000元办个二胎准生证。在这种合作中村民获得了生育第二胎的权利,干部们获得了被请客和得到现金等礼物的好处。
村民利用政策的另一个例子是,利用上级禁止"连四邻"、扒房子等规定,保护自己的财产。这一规定和计划生育一样具有对政府政绩一票否决的作用。有了这一政策,村民可以对抗地方政府破坏性和扰民性的行为。最明显的是,1998年以来,小分队不敢轻易地像以前一样到村民家里牵猪牵羊,抱电视机,弄粮食,扒房子等。实际上,博弈各方诉诸的案子很少。无讼(费孝通,1998)依然是乡土社会的突出特点。①「甘琦说:"我替上访告状的清朝百姓算过几笔帐??结论竟是骇人听闻的两句话:当冤大头是老百姓最合算的选择,而当贪官污吏则是官吏最合算的选择。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利害格局决定的。"(甘琦、吴思,2000)今天大概也是依然如故。」
(二)关系
关系可以概括为看似合法实际上又非法,或看似非法实际上又合情合理的交往,是特殊主义的交往。干部和村民都在利用关系来参与这场博弈。"离开关系办事难!"这是人们常发的感慨。这里的"办事"包括上级要求下级(也可以指村民)的、下级请求上级的以及同级人之间互动的事情。上级对下级的要求如果只以正式渠道下文件讲精神,一般效果不好。他们需要以"哥俩好"的交情让主要依靠的下属卖力工作,否则,别说做好工作,位子也坐不牢。
利用关系在村民的计划生育博弈策略中同样占据要津。关系是保护伞,能遮风挡雨。送礼请客等行为是非法的,但从村民自身利益和时下社会环境来看,几乎成了被锁定的事实。
两个办事渠道——通过官方法定程序的正式渠道和通过社会关系的非正式渠道——同时存在,我称之为"双线运作".基层社会中真正发挥了效力的往往是非正式渠道,正式渠道有时甚至退居到了仪式和形式的地位。双线常常交织在一起共同运作。
在日常生活中,村民需要请求上级时大多尽量动用社会关系网络资源解决问题,不会轻易动用法律。更何况村民本身也多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因此更不愿去触动法律。"民告官"的上访是需要勇气的,上访成功与否都要付出很大代价。总之,动用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往往是最有效和的。用一位村民的话说",当官的得有老百姓撑腰,老百姓也要有当官的保护"",撑腰"和"保护"的对象是同一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这是一种社会资源交换。
(三)暴力
暴力即强制的力量、武力,是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诸博弈方都采用的一种手段。使用暴力手段是小分队名声不好的原因之一;相应地,村民以暴制暴的反抗也时有发生。虽然实际上真正动手的不多,往往不过是一种策略。而且这种反抗多是村民个体或一家一户的行为,几乎没有集体暴力反抗。因为集体反抗需要组织者,而组织者要冒很大的风险。另一方面,与人口流动有关,陈村近1P3的人口经常在外打工,而且外出的多是年轻力壮的好事之人,留在村里的则多为老弱者,所以很难产生集体抗暴,只有各自采用不同方式对付计划生育执行人员。
(四)金钱
经济因素在计划生育工作中非常重要。超生罚款就是用经济手段对村民加以制约。近乎残酷的罚款对村民形成巨大的压力,但村民们应对的策略也是以钱铺路。要想超生,即使是逃跑"打游击"了,家里人也要花些钱把有关人员稳稳台。尽管在计生之列的村民多是不富裕的,还是要小恩小惠地送些礼。
多送比少送好,少送也比不送好。至少让一些干部和有关人员觉得被重视了,否则就"依法办事".但上级的检查越来越严,干部们也只得把活动余地一再压缩,所以这种对策的效果也是有限的。从近几年看,1994年以来几乎没有超生的,表明这种手段的效果下降很多(其他因素,比如人的生育观,生育期的妇女数等,和以前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可是,我调查的人中都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多生孩子。
以钱铺路仍然是村民们常用的策略。
(五)逃跑
躲藏与外流,这种打游击式的方式是村民的另一个策略。村民中流传这么一句话",有钱的钱生,有人的人生,没钱没人的就跑着生",说的是有钱人家拿钱拉关系走门子超生,也不怕罚;有权力和关系的人靠权力和关系超生;两者都没有的就靠藏藏躲躲超生。到亲戚家,尤其是远方的亲戚,不容易被发现和找到,或者出外流浪打工。打游击的超生方式在是最普遍的,在台帐和孕检建立之前更是超生游击队强大的时候。在我访谈的对象中除了一例,几乎都牵涉到躲藏或外流的打游击方式。就是有钱有关系的,比如C5,也说,只要听说风紧,其妻马上转移。只要抓不到(怀孕的)人,就不怕,抓住了,就比较麻烦。为逃避超生费而逃跑在外流浪的典型是村民C8,陈村里已没有他的房子和耕地,他也不用回来了。在外打工过活,代价是多年生活飘忽不定,担惊受怕,难能富裕。一般是较穷的超生又多的人家容易以逃跑来逃避被罚款。
现在,为堵塞以打工名义外出躲避计划生育这一漏洞,外流人员的管理也逐渐规范化,已婚育龄妇女外出必须办外流证,办证要向村和乡各交押金500元。并且每隔三个月要寄一张当地开的孕检证明交给村里,村里再上交。到期不交,视为计划外怀孕,就要到家里罚款。城市里也相继出台了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和办法。但还是有机可乘。比如在北京这样的都市,有些打工仔在老板的庇护下躲避城市管理者。而且,在外地超生对当地政府没有什么影响,不上当地户口,不算当地管辖区的超生人口,当地人也不愿自找麻烦。结果实际上查起来成本高,技术操作也难。
(六)作假
反映在陈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隐性结婚。由于一结婚就成了计划生育户,就要经历办证件、入台帐、月检查等麻烦不完的事,受计划生育人员管束太紧,于是就出现了隐性结婚对策,不办结婚手续,也不举行结婚仪式,而成为事实上的夫妇关系,然后两人一起去外地,一般是投靠亲戚打工,生了孩子再办结婚或办个不太正式的场子。陈村的女孩也有2例隐性结婚的。上级的对策是,15岁-49岁的外流女性必须办外出证。
第二个是假离婚。一对年轻夫妇为了生个儿子,或多生个孩子,就表演一场假离婚。一般是大吵大闹或大打出手一阵子做样子给人看,接着就到乡里办离婚手续,女方回到娘家去。
村民们也是心照不宣。乡里虽然也知道这样的事,但没有政策依据,技术性操作也难。后来据说想出的对策是,让离婚的双方各缴500元押金,如果复婚不再归还。
再一种是隐瞒"黑孩"和藏匿财物。在超生范围内没有户口的小孩被称作小黑孩。小黑孩没有户口也没有田地。因为超生会被罚款,瞒起来至少现在不会被罚。而且,就是不瞒也不会马上得到户口和耕地之类。所以,一般小黑孩在外婆家生活。再就是把家具、粮食藏在邻居家,以免被抄走,风声紧时,猪羊也藏到别人家喂。
作假也是干部的博弈手段。基层干部有两套记录体系,既应付了上级而不使利益受损,又一定程度上给村民以弹性空间,他们从中收利。因为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各博弈方存在着对信息控制的争夺,谁控制的信息多一些,谁就在行政过程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所以一个要"了解下情",一个要"欺骗上级".产生了作假。
(七)技术手段
现代科技为计划生育博弈提供了技术和工具等物质性条件。从陈村计划生育博弈中我们发现,在政府一方,引入了高科技机械仪器,像B 超机、波姆光等设备操作孕检、体检等。建立台帐时利用电脑建立数据库。技术上有了保证,避孕成功率也提高了。
与此同时,村民和合作作弊的干部也可以通过高科技作假。比如,开假证明。钞票、身份证之类都可以以假乱真,更何况弄张假扎证之类。尤其在外流动的育龄妇女,三个月寄来一张孕检证。人不在当地,当地计生办只能相信这张证明。
再者,利用现代通讯即信息联络工具。例如,现在电话基本上各村都有,乡村干部和有些村民还配上了手机。这样,在干部一方来说,相互可以很快地取得联系,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执行。如果遇到了问题,可以马上与乡派出所和指导站总部取得联系。而在村民一方,同样也容易获得信息帮助应对。比如检查队来了,村这端的人家可以通过电话告知村那端的人或其他村的亲友躲避。
(八)互利的合作
先说村民的合作。村民们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世世代代一起生活的熟人,他们是一个群体。在计划生育中村民之间自然达成联盟,可以让别人的东西暂时放在自己家里,打一下掩护,当外人打探某某的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事时,不向外人提供信息,等。相互提供方便,至少不坏别人的事。村民们明白,合作比背叛好。
再看基层干部一方。他们之间的差别也造成内部的不同博弈方。我们可以把他们粗略地分成乡级在编干部(指那些在县里的人事报表上有名字的干部)、乡级不在编干部(只是乡里聘任的干部,比如一些小分队成员)和村干部三个博弈方。在编干部要对上级负责,所以要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结果,比如,低超生,但又要保持工作尽量不太出格,出了问题就是麻烦,影响可获得提拔资格的政绩。而具体工作通常是由那些不在编干部做的。所以在编干部必须保持与不在编干部的合作,以求他们工作细致谨慎,干出成绩又少惹是非。
现在来看干部和村民的合作。生二胎就是干部和村民默契的互利合作的一个很好例子。
此外,基层干部不完成一定的任务就要受罚,又要照顾到村民实际,所以他们集执行小鬼与庇护神于一身,平时是以村民为对手打游击,上级来检查时又与村民结成同盟,通风报信,出谋划策。村民面对上级调查者,衡量利弊的结果,就是对他们说假话。这样相互隐瞒对双方都有利。
四、博弈与制度演变:宏观分析
真正的制度建立"主要不是一个学习、宣传和贯彻既定政策的问题,而是一个所有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受益者或受损者为了他们的利益——用学家的话来说——反复博弈和公共选择的过程"(苏力,1997)。本节引入纵深的时间维度,分析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变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以及这些决定又是如何改变现实的。调查发现陈村(及其一带)计划生育博弈中发生过四个转变。下面具体探讨这四个转变及其实践结果和逻辑,从中认识计划生育博弈过程中的主脉络。
(一)从村级执行到乡级执行:小分队取代村干部
从一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到20世纪80年代末,陈村的计划生育中的通知、催逼和罚款等工作都是由村干部去执行,或一人或几人,或整个行政村所有干部加上乡里派来的一个坐队人员。这个坐队人员监督村干部的工作,同时也为了拔高村干部的行为,使之更具有国家(或上级)意志的合法性,壮村干部的胆以威摄村民。在计划生育方面,那时的村干部较现在有更多的权力。这样做的后果有:(1)村干部容易从中得利。因为村干部具有决定性实权,村民巴结他们就可以受到一定的庇护,减少利益损失。(2)
瞒报计划生育实情的事较多。因为村干部得到了某个村民的好处,就要回报,这是很现实的交易,所以就要瞒上。同时我们知道,基层干部工作很棘手,村干部必须照顾到他们依靠的力量。碍于老邻居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人情面子,逼得他们一般也是能瞒上时就瞒上。
即便如此,村干部还是容易得罪村民,为了计划生育工作而与村民吵架甚至打架的事时有发生。国家是他们当然的后盾,国家在这里的具体体现是乡政府、派出所、计划生育指导站及计划生育小分队。但"国家"只是在一定时间和方面能作后盾力量。他们一旦不当干部,还是要和这些邻里乡亲天长地久地厮磨在一起。
后来,计划生育的执行机构改革,乡政府成立了"计划生育小分队".小分队在乡计划生育指导站直接领导下工作。比如现在,每村由一人来承包,该乡有37个行政村,所以小分队总人数37人,男性女性都有,其中约四五个是在编干部,其余都是临时聘请的。除了在编人员由乡里发工资外,①「基层干部的工资通常不高于中小学教师,所以一般不会超过四百元,而临时聘请的人员规定的工资数更低,没有隐性收入生活是成问题的。」其余人的工资都是从计划生育罚款中提取,每月二三百元——当然也有远超出这个数目的隐性收入情况。他们的年龄大都在20到30岁之间,最大的也不超过40岁,而且一般体格威猛,因为这是"强制性"工作所需。
为了避免任用当地干部所带来的弊端,其中占一半多的人员来自外乡。一般来说他们的文化水平较低,初中毕业就不错了,高学历者通常不会到这小地方来,即便来了也不干这一行。但这些学历低的人社会适应能力很强,软的硬的灵活使用,当然有时也难免"软的欺硬的怕".农村计划生育要决心有效地进行,地方"小分队"的建立是可以理解的。②「因为"事实上,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上级各条线均把无限责任下达给基层政府,而基层政府原本非常有限的职权却逐步上调归口。
权与责的严重分离使乡镇政府极难承担日益加重的管理责任。基层政权已面临责任极度膨胀和职能急剧萎缩的矛盾之中"(施振强,2000)。」小分队取代了村干部的执行功能。
工作程序是:先由村干部通知计生户是做手术还是超生罚多少款等事情,如果按通知做了,没问题。否则,小分队随时可能出现,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甚至凌晨时分。抓该引、流产或该结扎的孕妇,抓不着本人就抓她们的父母等亲人,家人就得拿钱去把人赎回。抓不着人就拿东西,牵猪牵羊挖粮食抱电视,只要能卖钱的都拿。如果家里没有人,他们就砸开门。
扒房子的也有。小分队成立之初的几年,孕妇们几乎不敢赶会上街、抛头露面,因为随时有可能被抓,抓住了麻烦就大了。即使怀的是头胎,小分队并不知道,被抓住了也不大好。小分队是群体出动,人多力量大,也分散了责任,干起来放得开。当然,常规时候要跟个村干部,一般是支部书记。计划生育执行功能从村转到乡,是实践中摸索的结果,也是村民、村干部和乡政府之间博弈的结果。但其中一个后果是村政逐渐在功能弱化中衰退。
(二)从株连到违规者自负其责:走向秩序化
连坐制古已有之,在陈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再次出现。它没有形成书面文件和政策,但出现在实际的技术性操作中。株连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慢慢盛行起来,大约1996年时为最烈。1995年,陈村所在的XH乡在地区级计划生育检查时挂了黄牌,到1996年乡领导班子换届,县委派W 任乡党委书记,最大的任务就是摘去这面黄牌。其实,1993年时的连坐已很厉害了,因CDS 生第二胎被罚,小分队把半个庄子村民的牛都给牵走了。但是为什么要弄邻居家的东西呢,人家又没有在受罚范围内?理由是他们不协助计划生育执行者的工作而是帮助那些超生户。确实",传宗接代"是每户的头等大事,一点马虎不得。村民形成统一战线,对付共同的对手。
因为以上原因,从执行人员角度来看,自然村民都是"对头"了。同时也主要是为了给超生户造成压力,并不是要树敌太多。但从宪法和的角度来说,株连邻居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所以就有村民不断上访。当然村民在执行的过程中也有抵抗,但在小分队面前往往显得力量单薄。株连亲邻的方式造成人心惶惶,既严重影响了经济,也使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强,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社会是一张网,纵横相连,一些官员的亲人也难免受到冲击。
所以,这种方式是注定要收敛的。到了1998年,陈村一带就开始扭转这种执行方式了。1999年和2000年,按上级的精神,不准搞株连,不准牵牛牵羊弄东西,更不准扒房子等,责任由违规者自己承担;如果真流动在外找不到,就找男方的父母,不再扩及他人。并且逐步实行由乡成立的法律事务所对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当然这种规定是根据上级文件政策和地方特色制定的)者惩罚,由事务所向县法院起诉,由县法院依法执行。这是一个大的转变。然而对所谓"不合法"的暴力强制执行方式村民认为也是"合理的",他们说,在这种乡村里不这样做又怎么做呢?近两年情况好转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一方面执行人员受上级规定的几不准的约束;另一方面实际上很少有超生的新户,超生的老户一般都有了清单卡,即使没交清的也因为吓破了胆,来要就尽力地给,不必要暴力强制了。但有些时候还是会发生的,所以"暴力强制"近期还不会完全消失。
(三)从规定"指标"到建立"台帐":数字管理的引入
原来的规定是按各村人数来分配指标。比如,陈村有300多人,一年要完成3个妇女结扎任务。上世纪80年代常是这样给各村分派任务。因为乡级政府了解下情是通过村干部,往往情况不实,所以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下指标。但这中间就有问题产生了:如果该村当年没有这么多符合结扎条件的呢?于是为了完成任务,就让村民中沾计划生育边的都掏点名义上是罚款的钱,村干部拿这个钱到县里买指标,买张结扎证书交到乡里就算完成了任务。
如果够结扎的人数多,当然先哄着他们去结扎,不去再罚钱,总之要想办法完成指标。如果某个村民有本事,有路子,可以假结扎,弄张结扎证明交上去就可以了,只要没有人告。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告的。罚款也有指标,某村某年要上缴计划生育罚款费多少多少元。总之,那时候的针对性较差,求实性较低,马马虎虎就混过去了。所以到80年代中后期超生的人数很多。
小分队建立后,开始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小分队开始到村里逐家搜查,掌握情况。现在这种查底方式依然在用着,只是突击性的检查少了。但是,在上级检查团到来之前,村干部会安排村民,该藏的藏,不该说的别多嘴。为少有麻烦起见,人们尽量做的周全些。
1996年到1997年间,逐步引入了"数字管理"——建立起了台帐。台帐是指由计划生育管理和执行人员建立的详细的人口统计簿,为此,他们逐家逐户进行登记,把已婚到49周岁的育龄妇女情况、生育孩子数、是否手术,超生的是否缴清罚款,每月人口的增减、结婚几对等逐一登记在册。每村都有一本台帐,而后就按照台帐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由于每月都可能有新婚、新生、死亡、外流人口,所以由村计划生育专干协同包村的乡计划生育指导所(即原来的小分队)派来的计生管理员,每月统计出来签上两者的名字并加盖村公章于当月的25号交上去,一式三份,一份上交县计生委,一份交给乡计生办,村里自留一份。台帐的建立使监督和管理更加严格、方便。正如吉登斯(1998a )所认为的,民族-国家是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其动因之一就是"以信息储存和行政为手段的人身监视力(surveillance)"的发展。乡村干部按照台帐的材料,通知计划生育户该做什么,比如单月孕检、双月学习、换准生证等;而且罚款也有了数目依据;省级和乡级的有关条例,每个计划生育户都有;同时,村民也有了开收据的意识,缴多少钱,得有个字据,以后遇到麻烦可以有个证明。可是,尽管有了台帐,说不定何时上级检查团还是会来寻找漏洞的。
从规定指标到建立台帐,乡级管理人员试图绕开村干部把触角直接伸向最基层的农村,在技术上是一大进步。台帐的建立使单月孕检等活动开始迈向有序化,制度化。
(四)从紧收到轻放:弹性动态的产生和持续的原因
现在来看由前几个转变带来的后果之一:小分队由向外抽款到向内拨款,由富变穷及可能的继续博弈。抓计划生育工作的人以前被认为是很富的,有人送礼,有的罚款可以据为己有,在登峰造极的几年里,小分队所到之处一车一车地拉走东西。小分队人员的工资收入就从这些罚款中来,明面上的工资很低,据说每月200来元,但实际的"收入"不少,还会对外说发不起工资。当时的计划生育是乡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
罚款数目是很不稳定的,省里和县里都有文件,但实际上很难严格按这些文件执行,不论是村干部还是小分队,用各种方法,能罚到手多少是多少。每次逢计划生育运动,有超生小孩的家庭都习惯了被罚,小孩十几岁了也是让你拿你就得拿,村里干部会哄村民说",先拿一点过去这个关,实在不行,就给你开个村里的清单".但是,下次又到罚款运动了,还会罚,理由是",咱的清单是村里开的,乡里的要求高,咱也没办法".同样,乡里的清单也管不住县里的,依次类推,所以,村民一度在这方面很不信任政府。
1999年,陈村所有12岁以下的超生孩都要再次被罚款。几年甚至十几年超生户也别想安宁。所以抓计划生育的小分队是可以发财的,而且每年为乡财政作出了大贡献。
但是近两年,小分队变穷了。2000年县里开三级会议,要求各乡为计划生育拨出专款,保证计生工作顺利进行。小分队由向外抽钱变成需要向内拨钱。从下面的事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2000年11月份到2001年元月份,计生办向各村发出通知,春节前全乡育龄妇女都要带10元钱到计生办进行检查。
而实际上,村民交了钱什么也没检查就回来了。她们说,就是去一个人把钱带去都可以,计生办主要想要钱罢了。村民们说:"小分队穷了,人家都不超生了,罚不了钱了,又生个要钱办法。"
这一转变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小分队里除了个别的领导完成任务能提级升官,其他成员一般是没有这个奢望的,多吃点和多捞点钱物对他们来说是最现实的。
所以现在出现了不让超生与找人超生这样的现象。譬如,搞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找村民办二胎准生证。要是按文件规定,陈村几乎没有一户是完全符合生二胎条件再办二胎准生证的。
办证过程是中间人员和负责办证人员谋利的好机会。继续博弈下去,就将产生一种动态的平衡,二胎还是可以生的,只要没有环境的大变化,甚至只要有关负责人在表面上可以摆脱责任(一般他们会睁只眼闭只眼),以打游击的方式生第三胎都有可能,邻村就在2000年打游击超生一个。超生了就要被罚钱,罚的钱多了搞计划生育的人员才有更多的利可图。但目前来看,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使生三胎很困难。因此,村民生二胎为主的弹性动态平衡是可能继续下去的,除非某些力量有什么大的变动。实际上,没明文规定,私下里每个小分队员每年都有规定的上缴罚款数,坐队计划生育管理员每年要上缴乡里1万元,完不成任务辞职,并且不发工资和奖金。如果没有超生户了,他们怎么办?这样的状况使弹性平衡更容易形成。
以上是陈村计划生育博弈过程中产生的四个转变。这四个转变有力地显示出在博弈过程中,各方争取各自利益的策略和后果。它们之间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这一系列后果并不都是决策者最初的意愿,有些就属于"控制辩证法"带来的"意外后果"(吉登斯,1998b )。在这一过程中,小分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他们的使命似乎已告一个段落,当我调查的时候,有人(比如村支部书记)认为小分队解散了;但大部分人(包括另一个村的支部书记)认为没有解散;在计划生育办公室这个小分队的老家",小分队"的一个成员告诉我,现在的指导站(所)就是小分队,但已不用小分队的名称,只是实际上执行着当年小分队的某些功能,比如,突击检查,下乡罚款等。
五、结论与讨论
(一)双线运作与游戏规则:一个秩序化的障碍及其克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基层社会运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双线运作。不管是上级让下级办的事还是下级有求于上级的事情,都是双线运作的。"双线运作社会"是对基层社会的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分析性概念。这是乡土社会里法与实施法的环境脱节的事实造成的,虽然不合法但从执行实践效果的某些方面看又是合情合理的。这就成了非正式运作路线。而且,如前面所讲,利用社会关系(做的事有非法的也有合法的)与利用如上访①「我们的信息(比如上访)是逐级进行的,也有越级,但都在一个系统之内,各级官员的信息过滤和扣压是惊人的。
通过上访(包括走访和信访)解决问题之难,可参见应星、晋军《集体上访的"问题化"过程》(2000)。」之类的合法途径比较,走前一条路更好。所以人们从日常社会实践中了这样一条经验",学会拉关系,学会靠关系".总之,这是个双线运作的社会:一条是明线,即官方的,合法的,公开的,但往往官僚化,多障碍,低效率,甚至根本就走不通;一条是暗线,即民间的,非法的,私下的,却往往效率极高。它有时是在法治渠道代价高甚至根本走不通情况下作出的选择;有时是某些人或部门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作为。两条线在基层常常相互纠缠在一起。
孔飞力说:"伴随规则而来的是可预期性和标准化"(孔飞力,1999:250),也即是秩序化。但是,双线运作社会,而且非正式程序的(并非完全都违法)暗线尤为起作用的事实降低了"可预期性和标准化".从此种意义上看,双线运作正是社会秩序化的一个障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暗线运作的不稳定并且较低的可预测性。所以,我们还是要靠制度建设,这恐怕没有异议。制定并共同遵守具有较长期稳定性的游戏规则是制约专制权力和克服"可预见性与标准化程度较低"的暗线运作的一剂良方。就稳定性方面看,丁学良(2000)曾画出了一个关于"稳定性、可预期性的程度"的示意图表。图表显示,从宪法、、行政、政策条例到指示、意见,其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依次减低。而目前大部分的社会管理都是在意见和政策的跨度内展开的,随意性强。所以,要依法而治,通过法治控制随意性。但这又要求必须保证上下沟通渠道畅通,这是信息通道的保证,否则等于白谈。②「我想引用"晏氏转型"的故事来说明信息渠道的重要性。晏子奉命治理东阿,百姓安居乐业时晏子却受到齐景公的指责,晏子遂转变政策,闹得民不聊生反而受到表扬。问题就出在信息渠道上,即便百姓利益受损,只要利益分配方式有利于控制信息渠道的权贵集团,传上去的就是好话,反之则是坏话。因此,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筛选者的偏好(见甘琦、吴思,2000)。」
人们容易明白上面这些道理,但实际上如何达到法定规则的有效性,如何使法规得到有效的执行仍然是个令人头疼的大问题。
(二)秩序演变的形态
由于法定规则的有效性和实际执行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暗线运作的规则几乎无孔不入地破坏或取代明线运作的法定规则。秩序③「"我们人对'秩序'的理解是比较简单的,通常是指社会治安、街道上的状况之类。中的'秩序'(order )的含义则深厚得多,强调的是结构化的和社会关系(structural relations in politics and society)"(丁学良,2000)。本文对"秩序"的使用是基于后者意义上的。」是通过一种看似非理性的纷乱无序,而微观上又是各种力量争取自身利益的博弈而产生的。就陈村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所经过的无序到有序的规范化过程来看,这些在宏观环境中的微观利益博弈现象体现了利益在让步和妥协中得到制衡的过程。在陈村计划生育执行过程中实际遵从的运作模式是与国家(或说上级)抓的松紧直接相关的。从其史可以看出,在基本政策不变的情况下,村民和乡村两级干部三个阶层之间及各阶层内部的博弈造成了计划生育的现状。
他们之间的冲突以及对这种冲突的容忍也是秩序化的一个必然过程,因为"冲突在一个团体经常发生有助于现存的规范获得新生;或者推动新规范的产生。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冲突是一个调整规范适合新环境的机制"(科塞,1989:137)。"地方政府与农民各自的行动边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完全由各种法规条文所决定的,而是在双方的互动中不断伸缩回旋着的,就好像两个正在推手的武师的手掌那样"(应星、晋军,2000)。因此,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秩序演变的形态:计划生育游戏规则在利益博弈中达成并在实施中形成制度;同时,基本政策等外部刺激因素相对稳定,则秩序逐步形成,但依然是动态的。
:
边燕杰,2000《城市家庭的社会资本》",问题与方法: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稿。
丁学良,2000《转型社会的法与秩序:俄罗斯现象》,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甘琦、吴思,2000《潜规则:中国中的真实游戏——〈万历十五年〉没有点透》,载《南方周末》12月7日。
郭正林,1996《公共政策的文化分析——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为例》《中国社会季刊》(香港)春季卷,总第14期。
黄仁宇,1997《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
——,2001《关系千万重》,三联书店。
赫伯特·西蒙,1989《决策理论的基石》,杨砾、徐立译,北京学院出版社。
吉登斯,1998a 《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
——,1998b 《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
科塞,L.,1989《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社。
孔飞力,1999《叫魂》,上海三联书店。
李强,2000《,"心理二重区域"与中国的问卷调查》,载《社会学研究》第2期。
李银河,1994《生育与村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林耀华,1989《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三联书店。
林毅夫,1991《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
罗伯特·艾克斯罗德,1996《对策中的制胜之道》,吴坚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彭希哲主编,1992《传统变革与挑战——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人口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
施坚雅,1998《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施振强,2000《乡镇政权运行有四难》,载《改革内参》第24期。
苏力,1997《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1997学术年会论文。
孙立平,2000《,"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
孙立平、郭于华,2000《,"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
谢识予,1997《经济博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应星、晋军,2000《集体上访中的"问题化"过程——西南一个水电站的移民的故事》《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
翟学伟,1997《"土政策"的功能分析》《社会学研究》第3期。
张静,2000《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
郑也夫,1995《代价论》,三联书店。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2《当代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编辑部,1997《党和国家领导人论人口与计划生育》(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版社。
《河南省计划生育条例》,1990年4月12日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2000年3月30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修订。
《计划生育工作手册》,北京市计划生育办公室,1979年。
《计划生育政策明白书》,XH镇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