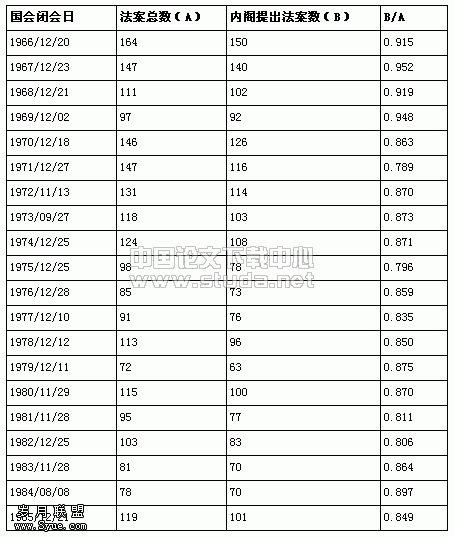现代科技与证据制度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7-07
一部人类文明史伴随着的是一部厚重的科技史,作为人类尊为万物之灵长之权杖的科技,决定了任何人类理性活动中深深的科技印迹。自从司法裁断这一纠纷处理的理性活动在文明史中神龙见首之后,证据体系就是其不可或缺的当然共生形态。因此,证据史无可避免地折射着理性的熠熠之光,无论是从“神证”到“人证”飞跃中所展示的从科学的蛮荒状态到人类对自身认识理性的信任与尊重乃至崇拜,还是从“人证”到“物证”的调整中所显现的客观科学派生出的物质证明力量对于主观认识的补充与制衡的互动, 我们看到科学演进中人类司法史从“非理性到理性,由愚昧到文明”①的伟大进化之路,我们看到的是由科技引导的人类认知的真实的凸显。
二、科技真实――一个视角下的证据真实
首先我们辨析一下科技真实的实质。几乎所有法学家都承认了完美的客观真实状态不能事实,因为我们无法逆转时间的经过,也很难绝对地还原已经过的空间与状态,科技同样不能(至少在现在)完成上述的客观真实的“不可能承受之重”的证明任务。这是一种科学的逻辑的结论因而我们很难反驳。因此从第一个证明论的层面来看,承认并服从证明的客观真实不能本身就是科技认识带来的科技认知的重大进步,这是科学从其实质上排除了客观真实的可能;当然我们马上要面对这样的一个诘问,如果科技证明不是证明一种客观真实,那么它存在的证明价值又从何而来呢?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但是提问前提错误的问题,因为提问忽略了一个前提即客观真实的不能态,其决定了所有类型的证明活动都只能是一种趋进式的证明,一种不断向客观真实接近的过程,借助科技的手段,我们所唯一有把握的只是我们离绝对的客观真实会更接近了。建立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当然要认同这种科技证明来提升我们的证据证明认知能力,进而实现认识深度的深入,所以我们抛弃唯心的神证,转向客观的科学认知证明方式,这就是科技排除客观真实却得以融进客观真实的神妙之处。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仍然老套却又执着地将科技的真实归入法律真实的范畴,事实上人类目前所产生的全部司法证明均可纳入这个法律真实标准:最早的神证,可以说是一种法律真实对于客观真实的最大背弃,但因为这种神证的证明依然是源于法律的规定,在法定程序中生成的法律真实,其是采用证罪方式通过唯心的神化或宗教化的证明模式实现的,所以即使是在这种唯心证明的巨大愚昧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神证方法可能的对客观真实的揭示作用(请注意:这是一种揭示而非证明),因为神证对于当时崇尚神灵的广大民众而言,具有极大的威慑作用,这可以从心理层面促使其发生异常行为而自暴其罪,此如早期欧洲盛行的“面包奶酪法”①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因此神证依然有其证明真实的价值存系;至于的科学更为有证明价值的如DNA鉴定,微量检定等,从其检测的发动到具体实施、提交经由质证,最后被认证,无一不是在法定程序与标准的流程下经过,否则就成“毒树之果”而不被采信,既然客观真实态不能,推定其为法律真实也就理所应该了。
三、科学错误--证据领域永远的悖论
也许上述的关于科技真实推论,在敏感的读者眼中会产生一点不快,因为我们只是在一个完全说服不能态的前提之下,折衷并且机巧地选择了一种可行的妥协论证方法而已,但是这也同时发出一种警示信号,我们一向引以为人类自豪的科技同样是不完美有缺陷的。这在一贯追求最佳证据的诉讼证明理念中,潜藏着一个危机,一个我们在个案中无法具体说明的危机形态--科技错误引发的证明错误。我们应当承认科学的局限性,而局限性意味着科学的条件性,因此只有在条件范围之内我们才有把握科学的正确性与可重复性乃至可以推导性,就如同对上述科学局限性的命题的承认也是有条件的一样,所以我们才可以在后续的同等状态(或者更优状态)下将科学可以由此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又重新作为一个可以被肯定的认识起点,这一过程的循环就是一个科技证据证明的逻辑。科技证据证明能力要求的相关性就是扣紧了这样的递推思维,并信任由此引入科技手段的证明过程。然而同样适用这一科学逻辑得到的前提性结论是人类认知的能力与水平范围的有限性这一命题,换言之,我们可以沾沾自喜并被实际运用到证据证明理论中的“附条件科技证明”的这些条件同样是在一个有限范围的环境下被认知上,相对于我们并不强大的认知能力和“知”不能及的未知范围而言,这些条件在证据程序中的提出并被最终纳入证明内容的前程将会是一个地道的“挂一漏十”,由此所要引导出的关于涉及科技内容的法官心证又怎会是可靠的呢?
这种相同的证明推演逻辑产生的证明“不能”,是直接否定了科技证明实践上的可行性,还是依旧演绎出我们上面阐述的科技真实的理论哪?先不论可行与否,看一下结果:采用科技方法获取的证据信息才在更广的程度上披露了未知(相较于其他的证明方法),因而也更接近了案件的绝对真实,或者说这种科技对于证明事态的还原更能体现事理发生的真实程度,作为一种反映法官的内心确信的人造裁断纠纷的制度设计而言,这种借助科技证明的作法当然互为优越的一种理性选择,不难我们就无法在以公正为根本的法庭上奢谈证明真实了,因此至少在工具层的科技证明价值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是一个人造诉讼体系对相对人为的科技证明的天然亲和的表现。
我们应该正视的是,这种亲和绝不仅仅意味着因工具的优异产生的妥协性的选择。以一个证误的角度来看“,假设永远不能得到肯定真实,他们只能被证明错误”①。既然在程序中证明成立肯定是不能,则反之证明一系列前提或条件的错误,不就可以在证明的反面确定假设的成立了吗?我们可以用如下几个原因完成我们的说明:
首先,与已确立的学识相冲突的观察(即证错)所带来的信息量会超过不冲突的观察。因此这将有助于在法庭质证过程与认证过程中为所有涉案人员提供更为丰富的证明信息,“与某一理论的预言相冲突的结果......比其他结果更能照亮人们的视野”②,显然强调证明错误将帮助克服了证“实”中的偏见。所谓证实中的偏见是指在科学证明中倾向于预先确定一种理论,随后寻找数据来证实其成立而不是反驳其成立①,该偏见与证据证明模式是格格不入的,尤其要被听审的法官所排斥,否则作为法律审判代言人的法官,将使居中的内心心证先天地偏向事实成立与否的一态,这不但有违神圣司法裁判的公平性公正性,也是法官恣意的一种放肆,进而可能背离了诸如“疑罪从无”(如果法官先偏向罪行成立的心态),或者是证人自由陈述等等的法律原则(特别是在大陆法系法官主导询问,其先存的心理偏好会不自觉地在询问时,干预了这种本应毫不受影响的证人陈述空间的要求)。
而证明错误可以更有效地在民事庭审过程中展开,一则便于当事人双方的交锋形态的构架,从而在彼此的交互中形成对各自证“实”中的纠偏,使证明在对方证错的制衡下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二则证明错误所借助双方各自立场的出发点,可以有效地纠正法官不自觉(因为自觉是不被法律允许的)形成的先决的内心偏向:无论法官先行倾向任何一方,对方的证错行为都会有利于减低法官上述的对于居中公正立场的立场的背离,从而实现整个诉讼状态的动态均衡。
不过仅仅证明证据中证明错误模式应用的成立,只不过解决了一个方法层面的问题,我们还得解决科学精度与证明错误的兼容性问题。因为证据所反映的科技真实始终是存有缺陷的,这不就意味着证明错误永远的存在:例如,在法庭上DNA检测结果的展示中,专家们的陈述一般是会强调从一犯罪现场或其他情境下提取的DNA与从人群中随机抽取的这个人的DNA相吻合的概率非常小(几十亿分之一)②,亦即目前最为精确的DNA检定,同样有着误差或者重叠性的可能,但法律并不因此就视之为法庭采信的否定证据而认同该检测信息的不成立,因为这种证明几率太小而不足以被采信,由此我们引入了概然性居上或者是优势证明标准(ON APERPONDERANCE OF PROBABILITY),这是科学性与证明错误在证据学兼容的纽结所在了。在民事诉讼中,当法律仅仅要求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证明其主张事实的真实性大于不真实性”时①,我们可以发现科技真实先天不足的致命伤——误差错误,是可以被证据系统所吸收认可的。诚如上述我们所讲到的亲和性,科学证明被民事诉讼宽容到了极宽的精度范围,美国学者摩根认为的“证据优势就在于一种使人信服的力量”(Covinecing Force)②,就真实而言,只要这个虽有瑕疵的信服力量足以校正其自身的因瑕疵带来的对于真相揭示的反力量,即使有误差不足以同样地被接受而认可。而且事实上,科技同样是存有弹性而完成上述理论自洽的,这种弹性反映在误差上就是一种对系统性和随意性误差③的认识与调整,从而使得科学的推断或结论具有现实的实用价值,这种弹性反映在科技证据认知推理上就是法官或陪审团心证形成的自由裁量权,亦即每个裁断者的科技水平下所能够接受的借助科学手段之后产生的证明信息,当然诉讼类型决定的证明标准要求将是这种接受过程中心证衡量的标尺了,比如刑事证明标准就要高于民事证明标准同样是适用于科技证明过程的。
四、证据法的被动配置——科技异化
正义法则告诉我们,权力与义务相对等是不容质疑的,证据法对此的反映就是举证责任——证明优势——诉讼利益这一链条的推递。由此也才能建立当事人举证的激励从而推动双方证据证明模式的运作。然而科技的迅猛在带给我们以舒适便利的人类生活时,同样附加了科技这一双刃剑的异化作用,我们勿需赘述种种科技引发的公害及危险,从证据法对上述链条推递的变化之中,我们亦可一见端倪:
1.科技潜在的危胁引发的证明主体的模糊
我们先来看一个著名的案例,1980年美国加州高院的Sindell v. Abbott Laboratories④案件。在1937年到1971年间美国妇女为防止流产而使用一种“Diethylstil- bestrol”简称DES的人造雄性激素安胎药。原告母亲由于怀孕时服用DES,导致原告成年后患有癌症,由于当时有190家公司生产DES,原告无法举证其母向哪一家公司购买,于是原告以当时在市场上占有95%销售率的5家公司为共同被告,法院认为95%的市场占有率已属于“重要市场占有”(Substantial Share),如该5家公司无法提供反证证明自己的免责,则必须分担原告的损害。在1991年的Enright v. Eli Lilly & Co. 案中①,这种理论再次被认可。这些案例突破了以往证明责任主体与诉讼条件的直接紧密联系性,在民事侵权领域中引入崭新的市场份额证明责任标准,然而确认这种“份额——证明”联系的深层意义,却体现了该案例所要指引出的一种担忧的倾向:由于科技潜在的危险性以及长期潜伏性,我们没有理由在法律层面放纵科技冰冷的不良技术特性的泛滥,相反,在司法层面进行有力控制,借助公力救济手段中证明要素的调整,将严格的直接联系放宽至宽松的份额联系,以期强化特定科技运用主体范围,进而将证明重心聚焦于科技运用源头,从而更有利于技术利益回馈社会民众群体,这是科技社会化的要求,更是法治手段对其的一种有效的社会化矫正,以此来促成科技的安全化发展。当然这里明显存在着一种社会利益的合力作用,其一方面反映着一种社会化科技人本的最终价值理念的普遍作用与意义,同时也暗合着对上述证据设计中矫正功能的一种平衡,因为如果过度放任了这种矫正力量,那么科技的发展创新无异于同时戴上沉重的证明责任与被诉风险的脚铐而可能裹足不前了,因此在考量科技异化在这一层制约时,应有一个宏观视角下社会综合利益的修正与补充,毕竟因噎废食并不是理性的证据制度所要实现的。
2.危险领域——特殊证明分配标准的新延伸
伴随科技进步而来的是新产品的应运而生,科技巨大威力同时带来的就是使用上的危险程度的上升,因此在证明责任分配标准的规范修正说②中延伸出危险领域说(GEFAHRENKREIS THEARIE),认为当以危险领域作为标准,当损害原因处于债务人或加害方控制的危险领域时,证明责任应当发生转换,即作为请求人相对方的债务人或加害人应当对故意、过失以及因果关系的不存在承担证明责任。落实在具体的案件之中,科技适用主体往往就成为了上述证明责任分配倒置之后的承受者。这是一种实质性分配理念的必然结果:因为较之于一般消费者,上述的高科技产品侵权的专业性特点,天然屏闭了一般人员的实际证据参与能力,同时科技适用主体与科技证据的相对的近距离更有可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信息,并因此使得科技适用主体有了预防损害发生的激励(可参见本书中“证据法的学分析”的相关论述)。借助危险发生领域特殊证明责任的分配有助于还原上述证明主体的科技水平不对称造成的巨大不平衡,实现诉讼两造间的能力不平等的衡平。
3.专家证言——人证对科技证明的软化
证据系统在完成上述举证责任置换之后, 虽然已在程序上被转化为义务负担,但为了减少单方作证在专业性极强①的科技证明信息上的披露不完整或作不真实的反映的可能,两大法系均推出了旨在化解单纯因技术造成的认知不足的证明困难的专家证言体系,以补充法官的知识②,因为借助现代的鉴定工具与方法,诸如证据的关联性甚至法律性均可能更为有效地为涉审主体所认知和把握,并更好地显现证据的完整证明能力与证明内容。
探究专家证言制度的设计,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种人证对科技事实最有效的还原——将间接的与认知主体相距较远的科技事实,借助其他有权威认知能力的主体来披露,既可防止当事一方因与证据的近距离(由一方的科技优势而来,比如高科技致害产品方)的披露片面性证明倾向,更可以使得专业说明以一种更为居中公正的视角来评述,这就隔绝了法官认证可能的被专业门槛带来的认知信息受污染风险.并且上述专家证言只是就法庭据此查明的案件事实中涉及到的某些专门性问题作出鉴别和判断,而不能直接对问题作出结论性意见③,进一步减低这种信息传递中可能的对法官公正听审与裁断(涉科技专业方面)的越俎代庖的风险。
笔者认为专家证言的作用进一步地扩大表现在一种“专业”诉讼代理人的延伸上,随着诉讼种类的细分,专业律师或者有明显行业特征的律师代理人的出现,使得这种由于科技造成的对证明认知的影响,转向了更具诉讼主导权与参与能力的代理人身上.这种变迁将本来高高在上的科技真实从其背后颇为常人敬畏的神坛复归到平等的诉讼对抗空间下,借助双方代理人的专业性优势,让科技真实在交锋之中去伪存真,凸现其更为理性与正确的证明信息。笔者认为,这是科技平民化的一种应有之义:在带来科技物化形态的使用和广泛触及同时,社会系统经由细化分工之后的反应.不但是当事人所依托的代理证明(诉讼)体系的细分, 也包括了法院系统内部的细分(典型的如知识产权庭之类的专业性法庭的分设以及审判人力资源使用的对口①),于是我们在诉讼证据这一的平台上看到了这种自然科技下社会自身的演进,这不也就是科技对于证据仍至宏观诉讼形态影响的最为显性的表现吗?
五、结语:科技的偏执与法律的理性
在科技与商界所谓的“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应该有一种审慎地认识,在科技越来越具备人性化的友好界面的外表之下,科技主体天生的对于未知的揭示与探幽品质,也不时更为激烈地冲撞着人类自身神圣的隐私空间,不但是个人主动的:我们无法否认克隆技术专家孜孜以求的对于人类自身复制的执着;我们也无法否认黑客红客们在旧产权制度主导的互联世界激进演出的振振有辞,我们更无法否认科技所具备的迅速切换的时空的能力,将生人社会形态更急剧地推向我们每一个人;还有群体自觉的:美国“9·11”恐怖事件之后,个人权利至上的美国人自动妥协了对个人电话和邮件和信件的绝对权利,使美国司法部可以借助间谍卫星等高科技手段对上述通讯进行监视审查。②而2001年10月26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签署了参众两院日前通过的反恐怖法案,更是使之固定化,该法律的主要内容包括:允许执法机构窃听恐怖嫌疑分子的电话并跟踪其互联网和电子邮件的使用①;人类的法律因此有理由反思,反思自身法律制度设计应有的理性品格定位:我们不想将法律背后的立法主体的人性元素张扬在法律之外,而只是将法律的应固有理性凸显,因为我们希望,法律品格如同证据一样,一进入司法阶段就被固化而不容变更。这种理性的定位,不只是一次厚重的人与法的合法性的转变,更是一份微妙的规范与行为的合理性契合。
我们更应该将法律视为人类社会的推动,而绝非只是人类的思维产物。
通讯地址: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刘志骅(邮编:362000),
电子信箱:cwxing@sina.com.
联系电话:0595-2781017, 013625006094
* 作者系厦门大学法律系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 作者系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
① 张翀著:《司法证明与科学》,何家弘主编《证据学》(第二卷),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页。
① 即在法庭上,法官要求被告人快速吃下一盎司的大面包与同样的一块奶酪,如果吃时没有困难,则可证其元罪,反之有罪。在那种情况下,被告人由于害怕“神灵”报应,会心理产生压力,唾液分泌减少,于是口干舌燥,难以下咽。参见自张翀著:《司法证明与科学发展》,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二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466页
①这是以卡尔·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的一种证明思维流派,参见[英]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美]肯尼斯·R·福斯特、彼得·N·休伯普著:《对科学证据的认定--科学知识与联邦法院》,王增森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②[美]肯尼斯·R·福斯特、彼得·N·休伯普著:《对科学证据的认定--科学知识与联邦法院》,王增森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0-55页。
①参见[美]马哈尼:《作为研究课程的科学家:心理必须因素》,(Baillinger,1976), 第155页;[美]马哈尼、戴盟布伦:《科学家的心;分析解决问题的偏见》,《证知疗法与研究》,美国(1977)229-238页。
② 参见[美]吉彻:《即将到来的生命》,CSIMON AND SCHNSTER,1996,第170-172页。
① Peter Murphy,“A PRACTICAL APPROACH TO EVIDENCE”,BLACKSTONE PRESS LIMITED 1992,P105
② [美]摩根著:《证据法之基本问题》,李学灯译,世界书局发行1982年版,第48页
③ [美]Little E.B.Wilson:《科学研究学者论》,DOVER,1990,第232页
④ 26 Cal.3d 588 , 163 Cal.Rptr.132 , 607 P. 2D924 . (1980)
① 77 N.Y.2d 377, 570 N.E. 2d 198, 588 N. Y. S. 2d 550 . (1991)
② 德国法学界将谢瓦本和汉斯.普雅庭等的观点称为“规范修正说" 详见Musielak-Stanler,G RUNDFRAGEN DES BEWEISRECHTS,S.121ff. 转引自陈刚著:《证明责任法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194页
① 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技术的垄断或者拥有诸如技术秘密的合法的法律保护壁垒。
② 参见陈朴生著:《刑事证据法》,台湾三民书局1983版,第418-419页
③ 刘善春等著:《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48页。
① 比如拥有其他专业背景的法律审判人员对涉及此专业的案件的优先审判制度的设立。
② 参见张梦颖:《27天,美国怎样准备战争》,《观察报》,2001年10月15日A2版。
① 胡晓明:《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签署反恐怖法案》 http://news.sina.com.cn/w/2001-10-27/387149.html,2001年10月27日。
上一篇:陪审制度纵横论
下一篇:论行政司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