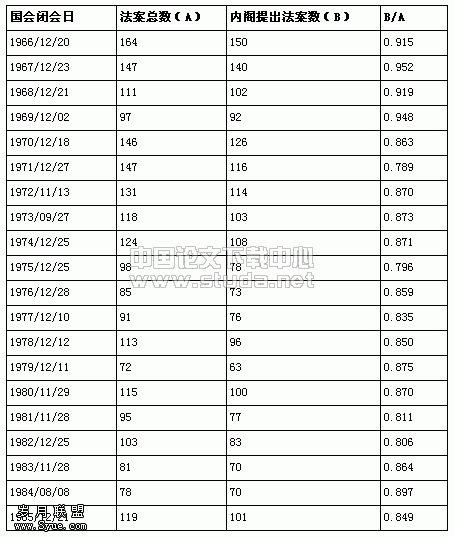配偶权初探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7-07
一、配偶权的概念和特征
我国曾先后颁布了两部婚姻法,最高法院也多次作过贯彻婚姻法的意见和批复,但均未对配偶权作出规定。故法学界对配偶权下的定义也有所不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身份说,“配偶权是夫对妻及妻对夫的身份权”;1二是陪伴说,“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2三是利益说,“配偶权是指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基本身份权,表明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支配,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3四是法定说,“配偶权是赋予的合法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享有的配偶身份权利,其他人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4五是性权利说,“配偶权是项民事权利,夫妻互为配偶,就有配偶权,配偶权的核心特色是性权利”。5
笔者认为,配偶权是指法律赋予的夫妻互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身份权,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它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必须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我国前两部婚姻法均未作规定;二是夫妻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具有双重性;三是这种身份权是互为条件和因果的,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利;四是夫妻以外的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
配偶权具有以下特征:(1)主体的对偶性。夫妻互为配偶,共同享有配偶权,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这是婚姻关系的属性所决定的。(2)客体的利益性。配偶权的客体是夫妻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不包括财产利益,且这种利益具有独占性,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共享,这是我国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所决定的。(3)内容的双重性,即权利义务的不可分割性。配偶权的核心是性权利。一是这种权利义务的实现需要双方同时履行和协调配合;二是配偶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缺一不可。(4)权利的排他性,权利的独占性必须就具有排他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配偶权也是对世权,即夫妻以外的人都是义务主体,都具有不作为的义务,不得实施干扰、妨害、侵犯配偶权的行为。如与配偶一方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姘居、重婚等都是对配偶权身份利益的侵害。
二、关于确立配偶权的争议
我国前两部婚姻法在家庭关系一章中对夫妻间的权利义务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但并未规定夫妻享有配偶权。配偶权的概念最早来自西方。如法国民法典第212条规定“夫妻相互负忠实、帮助、救助的义务”。瑞士民法典第159条第3项规定“配偶双方互负诚实及扶助义务”。英国、美国的一些法律都规定夫妻有忠实义务。澳门地区夫妻关系的法律规范根据《葡萄牙民法典》,家庭关系第9章中明确规定“夫妻有忠诚义务和同居义务”。日本民法典第752条规定“夫妻应同居,相互协力,相互扶助”。我国民法第1001条也规定“夫妻互负同居之义务。但有不同居之正当理由者,不在此限”。可见,配偶权制度已有较长的,实行配偶权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少,那么,它是否也适合我国国情呢,在修订婚姻法(婚姻家庭法)时是否也应照搬,目前在法学界争论较大,主要有两种意见:
1?持肯定意见的认为,“夫妻应负忠实义务,这是基于个体婚姻的本质要求,是一夫一妻制度的具体体现。一夫一妻制的实质,在于规范男女两性关系”。6目前“由于中国现行《婚姻法》没有规定忠实义务,没有规定同居义务,因此对于拒绝承担忠实义务和同居义务的配偶,就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7如果“规定夫妻有相互忠诚义务,对不忠于婚姻的当事人及介入他人婚姻的违法行为人,具有警示和威慑作用,同时为追究侵犯合法婚姻的违法行为提供法律依据”8特别对“有些通奸姘居行为性质比较恶劣,对公民配偶权或夫妻生育权直接构成了严重侵害,……婚姻法再不管,让当事人私了,是国家极不负责任的做法。且处罚这部分通奸者,在当今西方国家大部分的法律中都有明确规定”。9所以,“改革开放已经20年的今天,立法者应当理直气壮地为配偶权正名,在新的《婚姻家庭法》中,规定配偶权和配偶权的具体内容”。10
2?持否定意见的认为,夫妻间的忠实义务是道德问题,不能用手段来强制。“配偶权意味着夫妇双方拥有对方的性权利,这是十分荒诞的!如果结婚就意味着自己的性权利一次性地承诺给了配偶,那么还有没有婚内强奸呢?”?“如果配偶权被立法肯定下来,很多人可以拿配偶权为自己的粗暴行为作挡箭牌,其结果更不利于保护妇女的权益”。?我们在制订和修订法律时,“如果立足于防范可能发生侵权(例如第三者侵权),而不顾及事实上会在更大范围内造成对公民侵犯并伤及无辜的后果,这种颇似于‘宁错抓一个而不漏一个’思路的法律规定是落后而不合时宜的”。?笔者赞同这一观点,也投否定意见一票。
三、配偶权不合我国国情,不应在婚姻法中规定
配偶权制度在西方国家已有一百多年,在理论上也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它并不适合我国国情,一旦在婚姻法(婚姻家庭法)中确立,不仅不能达预期的社会效果,反而会有损法律的尊严,其理由:
1?婚姻的契约已默认了同居和忠实的义务,无需再用法律强制。我国现行的婚姻法第7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一张结婚证如同一份契约,双方约定(默认)了同居的义务和忠实的义务。因为:一是婚姻是两性的结合,同居是夫妻双方生理上的必然要求;二是婚姻关系又是社会的细胞,任何一对夫妻均应对社会负责,这是婚姻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夫妻间的忠实,不仅是性自私的必然结果,也是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德的必要约束。对这众所周知的常识和常理,法律无需再作强制性的规定。诚然,社会上也确有少数男女在结婚时出于各种动机和目的,甚至有欺诈,“放飞鸽”等行为,致使结婚契约不能、不愿履行。对这种现象应用道德规范和行政规范来调整,确已构成犯罪的,可用刑法调整,但不应用婚姻法来强制当事人的同居和忠实行为。
2?确立配偶权未必能解决“婚外恋”问题。主张在婚姻法(婚姻家庭法)中确立配偶权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婚外恋”,巩固“一夫一妻”制,一旦发生侵害配偶权,就可及时予以惩治。因为配偶权的重要内容是夫妻双方的贞操义务,其核心是性的独占性。夫妻一方与任何第三人发生性行为都是违背了贞操义务,侵犯了对方的贞操权,依法应受到制裁。这里显然把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二为一,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首先,夫妻在结婚登记时虽然都已承诺(默许)或应当承诺(默许)除配偶外不与任何人发生性行为。但性行为是以感情为基础的,这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而感情并非一成不变的。任何一对夫妻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已婚男女与未婚男女依法享有同等的自由。“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完整的人权,为什么一旦结婚,自己的一部分人权将属于配偶?一个健康的独立人为什么要拥有另一个同样是健康的独立人的部分人权?”?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体而存在。而精神生活、性生活、物质生活在任何一对夫妻的存续期间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永恒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加之“异性相吸”的生理特征不可能因结婚而消失,人的情感和激情丰富易变,需要理智来调节和控制。但一旦出现激情状态下非理智的性行为,就可能使一些当年曾“海誓山盟”的夫妻,在感情上发生异化和关系上的裂变。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法院每年受理的离婚案件约占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其中不少当事人均有不同程度的侵犯配偶权,对他们难道都进行惩处?显然不妥。夫妻间的忠诚属于情感领域,不应用法律来强制,情感纠葛应当让当事人自己解决。婚姻关系包含应受社会尊重的个人隐私内容,不宜增加法律干预程度。惩罚第三人者的立法将导致危及个人隐私权,这是不可取的。笔者不赞同有的学者既主张确立配偶权,又主张有例外的观点:“‘婚外恋’如果纯粹是感情上的事,双方并未发生通奸姘居行为,或极其秘密地偶尔发生的通奸行为,实际上并未破坏公民配偶权的,没有必要处罚,是个人隐私问题”。?与其这样随心所欲,自相矛盾的处理,不如不对配偶权作出规定。其次,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男女的结婚动机不纯,目的不一,甚至出于被迫无奈,结婚后“同床异梦”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他们之间发生“婚外恋”就更为常见。尤其在社会上还存在着“三陪女”、有夫之妇卖淫、有妻之夫嫖娼等现象,且将会较长时间存在,这些不正常现象绝不可能因配偶权的确立而根治。一旦婚姻法确立了配偶权,上述侵犯配偶权的“婚外恋”及“三陪”、卖淫、嫖娼等行为,必然会“法不责众”,反而影响了法律的尊严。再次,看看早已确立配偶权的一些国家对配偶权的保护又怎样呢?大量的“婚外恋”管了吗?“瞒着老大,供着老二,骗着老三,又搂着老四”的现象比比皆是。据“1995年美国对包括各种婚姻状态的人们的性生活状况所作的抽样调查表明:一年中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为76%,5年中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为40%,一生中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为21%。其中男性有婚外性伴侣的大大多于女性。”?这数字可以说是对他们国家确立配偶权的一个讽刺。当然笔者并不是默许,更不是赞同上述不道德的甚至丑恶的现象,对这种不轨及丑恶的现象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和鞭鞑。如果因此而造成婚姻关系破裂的,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可对有“婚外恋”一方给予一定的民事制裁,并在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一方。然而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总有其自身的,婚姻作为两性结合的形式,本来就因其与人最难把握的情感和激情因素相联系而使婚姻的巩固面临着许多难题。对于“婚外恋”要遏制它、解决它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应运用多种手段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方式,绝不能一罚了之,否则只能事与愿违。
3?确立配偶权不利于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既然配偶权的核心内容是夫妻互相享有与配偶进行性行为的权利,反之夫妻也互负有与配偶发生性关系的义务。那么夫妻之间是否又互享有拒绝与配偶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呢?根据宪法和有关的规定,每个公民均享有人身自由权,回答也应是肯定的。当夫妻这两个权利主体行使各自权利发生矛盾时,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妇女的权益,在修订婚姻法(婚姻家庭法)时是首先应该考虑的。任何一对夫妻在漫长的婚姻存续期间的同居生活不可能不发生冲突,因为每个人的性能力、性观念、性需求、性技巧都存在差异,冲突、碰撞是绝对的,只是大部分夫妻都能在人道主义、理性精神和宽容精神的道德文化和法律文化的影响下自我调节,从而达到和谐和谅解。但也不能排除确有一些素质低下,道德败坏,践踏妇女性权利的人存在。如最近上海青浦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一起婚内强奸案(见《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5日三版)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事例绝非鲜见。如果法律一旦确立了配偶权,类似婚姻内的强暴行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而这时法律又无可奈何,其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苛求每一对夫妻对同居的诺言一成不变。“如果同居是一种永久不变的承诺,势必造成对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限制,性便最终成了脱离灵魂的毫无情感、只能满足另一方欲望的工具,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同居之名肆意侵害对方尤其是妇女合法人身权利的手段,同居也就成了婚姻的枷锁。”?当然笔者并不认为夫妻之间性生活的不协调,甚至稍有一定强制行为,都用刑法来调整,这显然也是不当的。因为夫妻之间毕竟有一个契约行为,守约是前提,有了矛盾还是应该通过自我调节,达到解决和谅解。但是这种“守约”和“谅解”也是有度的,超过一定的度,就会产生质变,尤其是那些婚姻关系恶化,夫妻感情破裂,夫妻已长期分居,或已进入离婚诉讼阶段,丈夫违背妻子意愿,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应该以强奸罪论处。这是符合刑法理论的,因为刑法关于强奸罪的规定,并未对“丈夫”这一特殊主体作例外规定。对此,即使承认配偶权的国家对夫妻之间的性行为也有例外的规定,以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如德国民法典第1353条二项规定“在建立共同的婚姻生活之后,一方如果滥用其权利而提出要求或者婚姻已经破裂,则婚姻另一方无义务满足其要求”。反之,也不能因配偶权的确立,而将那些出于一时冲动,一时激情,一时失去理智的“两厢情愿”的婚外性行为,作为违法犯罪进行打击,这显然也不合情理,不符合刑法的立法原意的。记得在修改刑法时曾有人提出要打击通奸行为,设立通奸或妨害婚姻家庭罪,最后也未被立法机关所采纳。
4?确立配偶权将使公安机关难以招架。在修改婚姻法(婚姻家庭法)过程中,有人建议增加侵犯配偶权的处罚规定,如“夫妻有互相忠贞的义务,一方对另一方不忠时,另一方得请求公安机关排除妨害”。笔者认为这种建议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首先,在理论上它违背了婚姻的基础是爱情,“捆绑不成夫妻”。如果一对夫妻关系要用警察来排除妨害,这对夫妻关系能持久吗?相反,会使一些本来可以挽救的婚姻加剧破裂。因为夫妻之间的纠葛事出多因,大量的还属隐私范畴,或者说有的还处于隐私阶段,即使一方出于一时的冲动暴露了部分矛盾,在外界未介入之前往往容易调和。特别是因一时激情状态下的非理智行为,只要对一方幡然悔悟就能使其理解和谅解的。而一旦外界介入特别警察进行干预,就可能使缝隙难以弥合,甚至矛盾激化。其次,公安机关一旦介入大量的这类婆婆妈妈、妻妻妾妾的家庭纠纷,就会顾此失彼,大量的案件和复杂的调查取证、说服工作,靠目前本来已紧张的警力是无法招架的,况且,公安机关总不能常常介入“床上捉奸”的行列,这势必影响公安机关的形象。
5?侵犯配偶权的争议法院较难决断,影响诉讼效果。既然配偶受到侵害时,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排除妨害”,公安机关查证属实,要作出排除妨害、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具体行政行为,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一旦受理必然遇到三难:一是取证、认证难。侵犯配偶权的行为往往是因一方的“婚外恋”引起,这类案件不但原、被告举证较难,证人一般也不愿作证,更不愿出庭作证。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调取某些证据,法院无从下手,必然影响案件的准确处理。二是定性难。由于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举证困难,无疑使法院对案件当事人是否构成侵权的认定带来困难。无论是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还是支持原告的请求,都感事出有因,又缺乏证据,难以下判,因此不能达到预期的诉讼效果。三是分清责任难。婚姻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它受社会、、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婚外恋”也有多种情况,有的因一方放荡行为引起,有的可因对方过错激起,有的因第三人的诱惑引起,审理这类案件确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感,要分清责任,有其特殊性和难点,尤其当妻子被他人强暴,不通情理的丈夫得知后反以妻子侵犯其配偶权而请求保护,更会使我们处于两难境地,不受理不行,受理嘛本来已被害的妻子,却成了配偶权的侵权人,显然不合情理,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不能取得好社会效果。
综上,笔者认为在制定或修订时,既要广泛吸收外国的先进立法经验,共享人类文化遗产,又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既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超前意识,又必须适合现存的社会状况。对于一些“可看不可用”的规定,与其说有不如没有,我们不能试图用法律去管它管不了或不该管的事,否则,倒头来“法不责众”,反而有损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注释:
1、2、3转引自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260页。
46578910?同上,第277页。第291页。第262页。第274页。第287页。第259页。第290页。
?吴晓芳《配偶权的是是非非》,载于《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5日三版。
?转引自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02页。
???同上,第289页。第287页。第299页。
?肖劲松、段文生《论分居权》,载于《人民司法》江西专刊1999年6月期第25页。
(作者单位: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一篇:论赔偿损失
下一篇: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