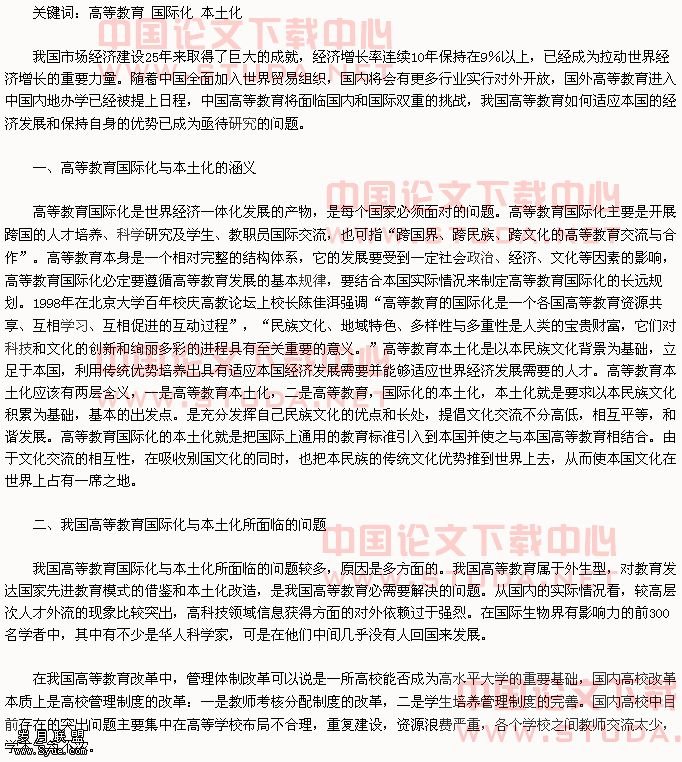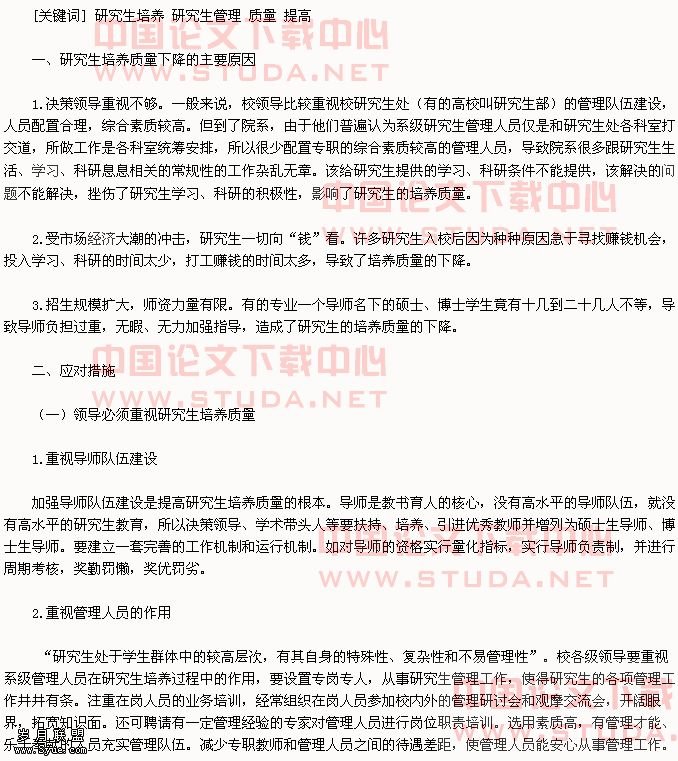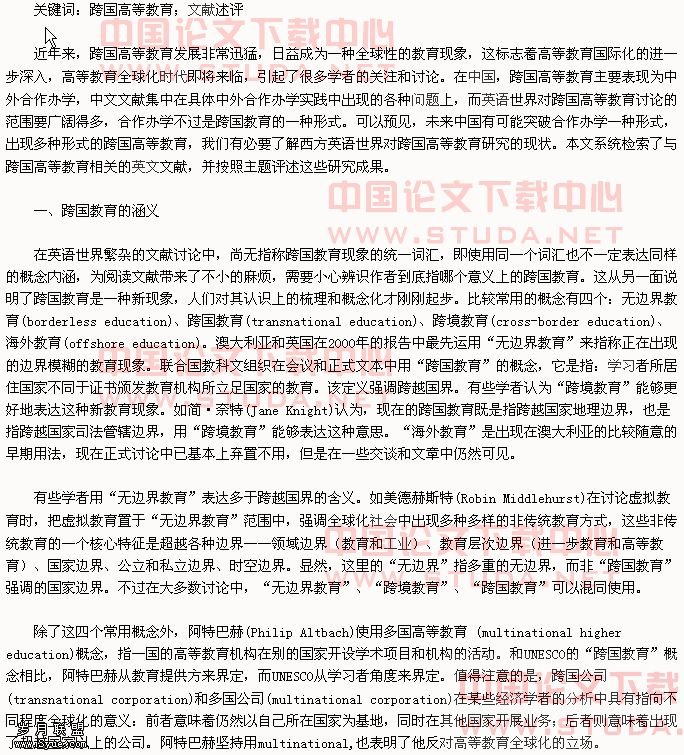大学体制与文学教育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6
照韦伯的看法,性的过程乃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进步。所谓分化,在韦伯的社会学意义上说,主要指"去魅化"和合理化,前者是指把宗教的东西与世俗的东西区分开来,后者是指强调人的行为、手段和目标都应符合理性原则。这就导致了两个最重要的分化:世俗的东西和宗教的东西的分化,文化的东西与社会的东西的分离。于是,文学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领域便应运而生。中国虽然是一个世俗的国家,没有强大的宗教传统和势力,但近代以降,文学的也依循相似的路线演变。文学从传统社会中的道德重负中摆脱出来,逐渐形成了自律的文化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大学堂和书局等现代体制的涌现,为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奠定了基础。讲授文学不但是一种职业,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关怀。新文化运动中许多作家、批评家和学者,他们既是文学家,又是教育家;他们既在大学讲台上讲授文学的一般知识和理论,同时也在通过文学来关注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关注中国的种种问题,从国民性到启蒙和救亡等。现代文学及其教育在摆脱道德说教的同时,又被附加上许多它有时难以完成的重任,诸如"小说界革命","文学救国","以美育代宗教"等等。文学在去掉一些功能的同时,又被赋予另一些技能。但从总体上说,不同于传统的文学教育,近代以来的文学及其教育在创作与社会实践、学术知识和社会关注等方面,似乎保持了较为合理的张力。
倘使我们以这样的格局来透视当代中国大学的文学教育,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大学作为一个制度的产物,作为一个话语生产和传播的场所,作为一种权力的运作,与文学自身内在的激情和灵性,与文学不可或缺的社会现实关怀,与文学作为一种质疑陈规旧习和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手段,似乎存在这相当紧张的关系。我以为,这种紧张至少表现以下几个突出的方面。
第一,大学的制度化正在或已经改变了文学教育的宗旨。从传统意义上说,文学作为道德教化和人格培养,自有其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忽略文学教育的此种功能,很容易导致文学和社会关联的断裂,进而否定一切文学对人格与精神的塑造有积极作用的观念。高度制度化的当代大学文学教育,相当程度上把重点放在一种可替代的知识的传授,而非思想与人生体验。它更加偏重于讲授"什么是文学?",而非"如何作文进而如何作人并认识社会"。所以,文学教育正在把学生作为一个单纯的知识受体,而将教师简单地功能化为学术传授的载体。尽管在正规的大学文学教育中可以使学生知晓许多知识,从某个文学运动,到某种文学体裁,甚至某些作家作品,但是,文学教育与人格修炼完全脱节,与社会关注和人道使命及责任的培育无关。非文学的东西,而然地被当作有碍于文学教育的东西排除在外。文学的知识化丧失了它自身的社会有机性和社会实践性,这一方面是大学教育制度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和当前的文学有意淡化与社会关联的倾向有关。诚然,传统的文学教育亦有道德说教的弊端,但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却不容忽视。文学的独立自足的确使文学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它也因此而失去了与社会的深刻广泛的关联。文学教育在其中可以起到什么矫往过正的功能呢?
第二,大学的文学教育在制度化条件下,不可避免地趋向于专门化和职业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中国的大学文学教育,完全是职业化的细密分工的产物。职业化和专门化的结果之一,是学术或知识的分化,文学教育作为一个总体范畴,实际上并不存在,实际存在的是文学史、语言学、文艺学等专门领域,甚至更加具体专门,文学史领域的实际领域乃是古代文学,更有甚者是断代文学史,甚至更加专门的某一时期某一作家或文类的研究。随着学历教育层次的提升,专业便越发具体、细致和局限。一个文学博士很可能只是研究一个比较具体特定领域里的专门问题,博士最好称之为专门家,因为他的学识并不广博。细密琐碎的专业分化使得文学成为"拆碎七宝楼台"。诚然,具体的专业分化使得文学教育的深度和专门性大大加强了,但在有所得的同时亦有所失。教授在专门研究可以达到相当精深的地步,却有可能失去对文学现象的生动活泼的体悟;学生也许会在某些艰深难题上有所突破,却有可能被训练成工具性的存在,丧失具有新鲜活泼的对文学的灵性和敏感。于是,文学教育中充满了后现代式的"微小叙事"。越深专门精深的知识,听众和知音便越是稀少。专门的话语和概念不经严格训练无从领会。更严峻的问题在于,既使在文学教育领域内,不同专业的人之间操不同的术语,谈论不同的话题,彼此之间无法获得一种"通约性"。研究文学理论的人读不懂专门的文学史研究,现代文学研究者可能缺少丰富古代文学的常识,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的现实的。"微小叙事"的盛行标志着"宏大叙事"的衰落,于是,教师和学生皆自满于在狭小的专业领域里穷经皓首,但文学教育与普遍的社会关怀关系疏远了。难怪有人不断地呼吁"人文精神"。难怪有人极力主张人文知识分子真正的角色在于他的"业余性"。
第三,大学文学在制度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强调学术规范、教育规范和运作程序,这是制度的权力和权威之表征,也是高等教育本身合理化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大学作为一种体制的必然目标。在现实的文学教育中,在不同的学术和学历教育层次上,规范化都是一个重要的游戏规则。课程如何设计,教材如何规范,考核如何客观,作业或如何符合写作要求,成绩如何评价,学生素质如何评判,学生如何学,教师怎么教……,一系列的规范意味着合理化已经渗透在大学文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之中。当然, 规范化是大学文科教育中极其重要一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问题在于,种种繁琐规矩是有力还是有碍文学及其教育的特殊性。比如说,在论文写作中,技术性的因素往往被突出强调,材料的取舍,的运用,方法的选择,表述的规则,观点的提炼,结构与篇章的统筹,都有种种规则来控制。这很容易使得许多技术性的环节压倒了思想的自由及其阐释。一言以蔽之,当代文学教育中实际上存在着重视"技"而轻视"道"的倾向。其结果必然是学生的论文越写越规范,技术上越发完善和符合标准,但思想的锋芒和创造性的灵见却日渐率微。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好论文",但有创造性观念的论文却寥寥无几。如此一来,便带来两种潜在的后果:其一,文学教育的规范化和思想火花的激发相去甚远。我们的教育制度培养的和要求的是一些对规范和规则驾轻就熟的工具性人材,而带有创造性和思想家气质的人材却少得可怜。其二,标准总是客观的和公正的,它不会对任何人有任何特殊性,而文学教育和人材培养的特殊性,特殊的素质所需要的特殊的教育,便被同一的规范化所抹杀。如今的大学文学教育成批地生产出同一标准的毕业生,但有独特才能和思想的人难以寻觅。至此,一个问题也许无法绕过:大学文学教育是否隐含着这样的潜在危险?亦即文学教育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培育的重要场所,将越来越趋向于技术官僚性知识分子的塑造。照此,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社会角色和职业敏感便会逐步丧失,工具理性便大行其道。
最后我想说,制度化的大学文学教育,以各种方式威胁着文学本身,也威胁着人文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危及他们的话语文化。或许我们有理由认为,人文知识分子在制度化的文化和教育面前,最最重要就是捍卫其"批判性的话语文化"(古德纳),其公共角色也就是"展示真理并揭露谎言"(乔姆斯基),他的本性乃是"自由飘浮的非依赖性的"(曼海姆),其基本任务在于"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萨义德)。假使我们承认这些说法切中了人文知识分子的要害,那么,反观当前的大学文学教育,一种制度化努力与这种角色意识塑造之间的紧张便赫然眼前。然而,真正的困境还在于,大学体制的完备制度化,从本性上说是遏制和压抑这样的人文知识分子塑造的,但在体制外实现文学教育在当代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实的选择和问题便是:我们如何在制度化中开拓非制度化的可能空间?
这显然是一个严峻而又难解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