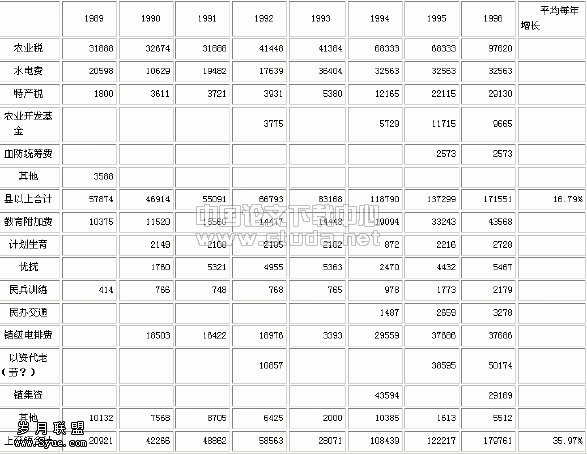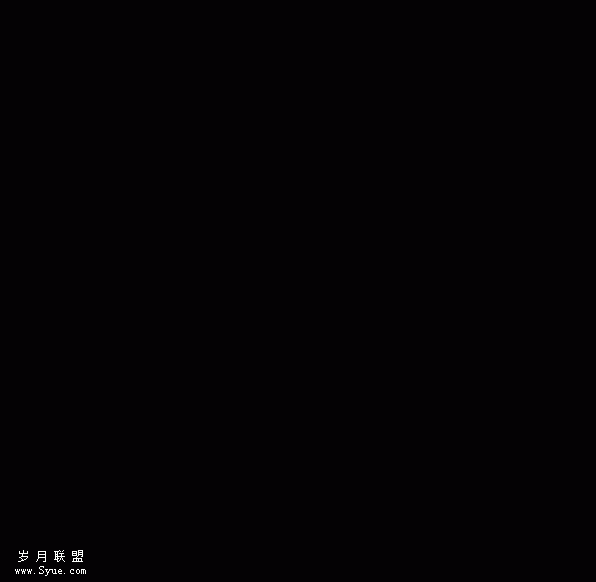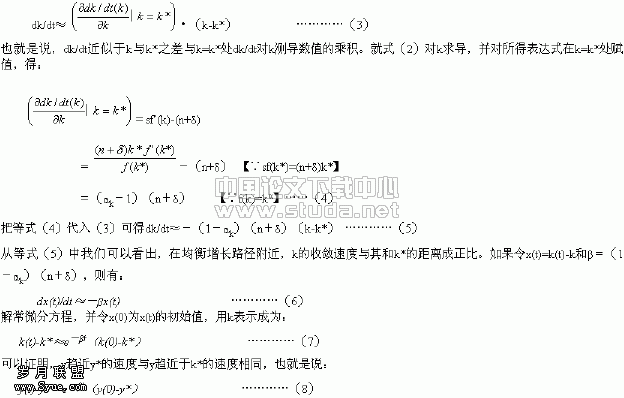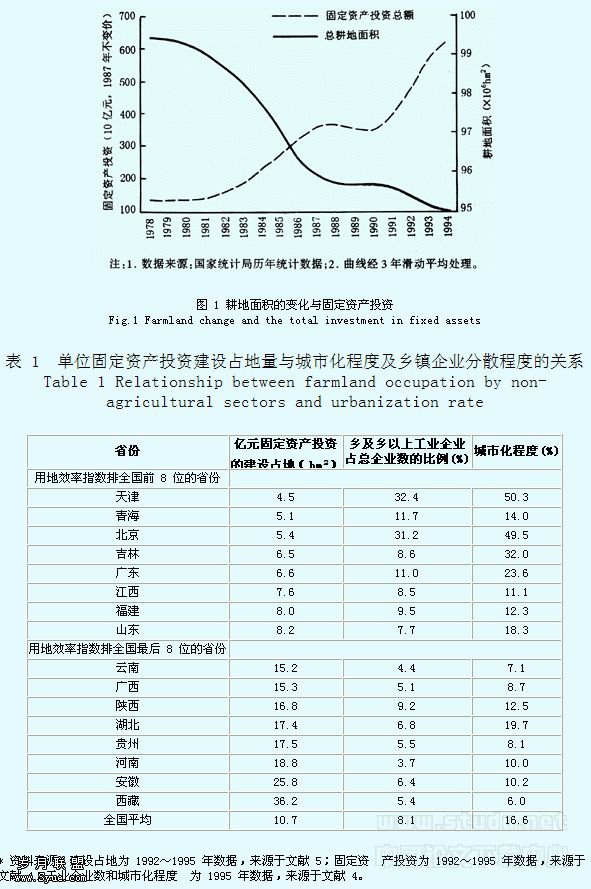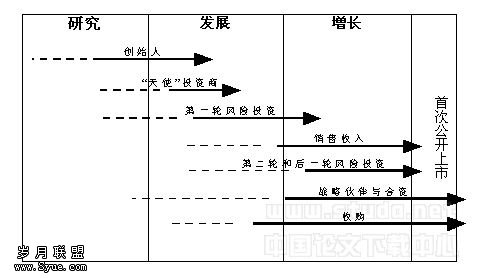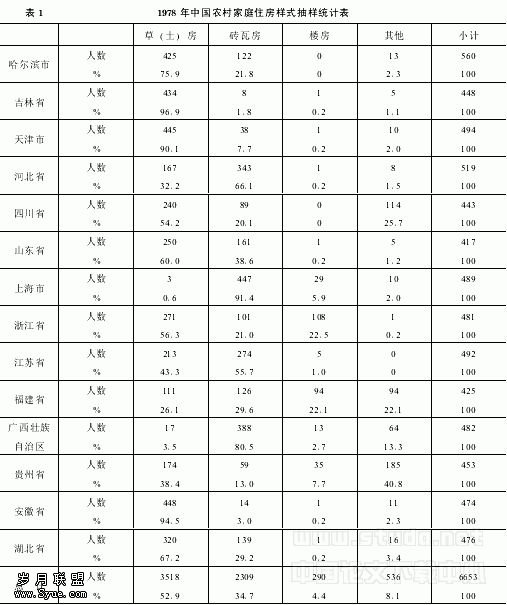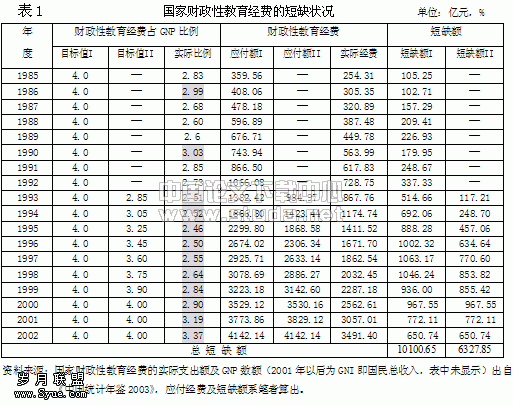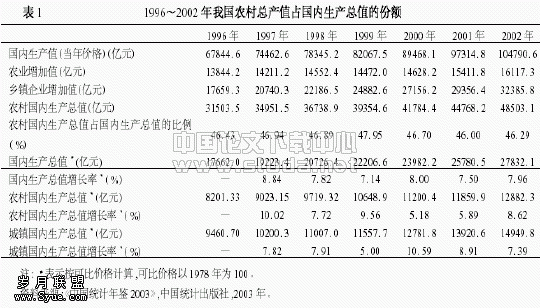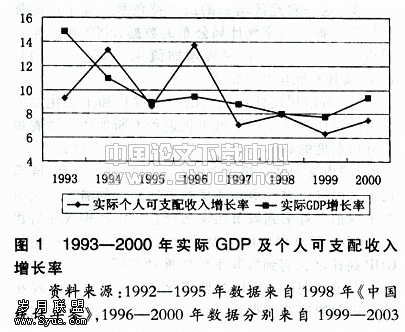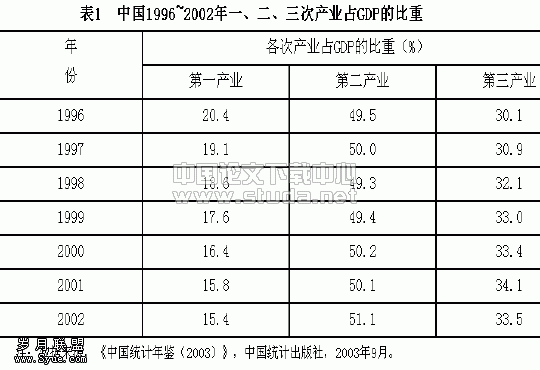试论金元时期北方经济(4)
二、各行业状况
1.畜牧业
北方地区有着辽阔的草原即天然牧场,历来是畜牧业的主要基地。金元时期,大批游牧民族拥入中原并成为统治阶级,畜牧业的专业地域扩大,呈现出新形势。
金初沿袭辽代旧制,在水草丰美且无蚊蚋之地设置5群牧所,金世宗时扩展为7所,所牧牲畜有马、牛、羊、骆驼。马作军用,“牛或以借民耕”。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官营牧场拥有马47万匹,牛13万头,羊87万只,骆驼4千峰。[i]此后仍有发展。虽无总数传世,但金末仅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就有监马近百万匹,[ii]可知其时马匹超过百万是没有疑问的。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又将骟过的马分散于中都路、西京路、河北东、西路民间牧养,[iii]仍属官营牧马业的一部分。当时在内地也设置了牧场,明昌三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南京路有牧地63520余顷,陕西路有牧地35680余顷。[iv]两地合计99200余顷,仅此就已超过了北宋时官营牧地98900余顷。[v]陕西地处边防,原本即有牧地,但南京路地处中原腹地,原为人口密集的农区,此时牧地多出陕西3万余顷,就农业而言是倒退,就牧业而言则是发展。金世宗时唯有河南、陕西两地“人稀地广,藁菜满野”,与大面积的牧地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由此也可知,两地的“藁菜满野”并非全是荒地,只是利用方式、产品结构改变了。
民间畜牧业也有相当规模。如养马业:相州(今河南安阳)“家家有马”。[vi]海陵王正隆年间,为南侵攻宋,大括民间马匹:“凡调马五十六万余匹,仍令户自养饲以俟。”[vii]民间总数大约也超过百万匹。养牛业: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曾派官到东京、西京、北京、中都、河北等路买牛5万头。[viii]民间实有牛数远多于此。金朝末期,蔡州新蔡(今河南新蔡)征收赋税以牛数多少为差,[ix]说明牛是主要产业。养羊业:大定年间,诏以羊10万只拨付乌古里石垒部畜牧,“其滋息以予贫民”。[x]养猪业史料很少,但从地处东北的会宁府金朝前期曾每年贡猪2万头来看,[xi]民间养饲是极为普遍的。
以游牧民族而建国的蒙元,“以兵得天下,不藉粮餽,惟资羊马”,[xii]将其擅长的畜牧业推行大一统的全国,一度将境内都变成牧场:“周迴万里,无非牧地”;养马业尤为兴盛:“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有之,盖其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亦一代之盛哉!”[xiii]由于元代畜牧业太广泛太兴盛,以至于没有具体数字传世。可以肯定的是会超越以往,达到鼎盛期。而畜牧业尤其是养马业、养羊业的重心无疑在北方地区。畜牧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大,是这一时期的特色。
2.桑蚕棉麻业
发祥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虽仅产麻,“土产无桑蚕”,[xiv]但那是当地条件造成的,并不影响其建国南下后对桑蚕业的高度重视。在大力发展各地原有桑蚕业的同时,尤其注意培养督促猛安谋克户从事桑蚕生产。金朝规定:“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缺。”金章宗明昌初,针时猛安谋克户再次下令:“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并以事怠慢轻重罪科之。”[xv]照此,金朝的桑树种植面积,大约占垦田数的十分之一二。
金代桑蚕业以河南、河北、山东最为发达。金朝末年,宋军北上,从洛阳向钧州、许州、蔡州、息州(今河南洛阳、禹州、许昌、汝南、息县)行军途中,因粮饷不继,有两天全靠采食桑叶活命。[xvi]足见这一带到处都有桑林。唐州泌阳县(今河南唐河)金末新种桑树30万株,“县以之致富”,[xvii]经济效益明显。又如相州(今河南安阳)也是“桑枣相望。”[xviii]金哀宗正大五年(1228年)郑州(今河南郑州)发生雹灾,“桑柘皆枯”。[xix]河北献州(今河北献县)“桑荫障目”,[xx]燕京更是“桑、柘、麻……不问可知。”[xxi]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有扫帚桑,望都县(今河北望都)有大龙桑、小龙桑,[xxii]种类丰富,也是桑蚕业发达的表现。此地还很多人工放养的柞蚕,如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邢、洺、深、冀及河北西路十六谋克之地,野蚕成茧。”[xxiii]山东济南府的济阳(今山东济阳)“有桑蚕之饶”。[xxiv]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大面积的桑柘之林令人惊奇: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夏,宋将岳飞率兵10万攻东平,金军仅5千,“时桑柘方茂”,金帅使人在林间广布旗帜以为疑兵,竟使10万宋军不敢进攻,相恃数日而退。[xxv]则这片桑林之广,至少能容纳数万人才能吓退宋军。金朝境内桑蚕业兴盛,还有一例可以证明:金末发生大饥荒,饿死许多人,到夏初青黄不接时,“其桑椹已熟,民皆食椹,获活者不可胜计。”[xxvi]桑树之多之旺盛,可以想见。
尽管经过战火的摧残,元代初年北方的桑蚕业仍兴旺不减当年。文天祥被押解北上时,有感而发的几首诗中对此予以称赞。如《新济州》言济州(今山东济宁)“时时见桑树,青青杂阡陌”;《发东阿》言东阿(今山东东阿南)“秋雨桑麻地”;《发陵州》言陵州(今山东德州)“远树乱如点,桑麻郁苍烟”;《献州道中》言献州(今河北献县)“乃今来中州,万里如一概。四望登原隰,桑麻蔚斾斾。”[xxvii]马可波罗所看到的更多是桑蚕业的结果――蚕丝:北京附近“丝之多且贱”,每日入城的丝“计有千车”;河间“饶有丝”;山东东平“产丝之饶竟至不可思议”;河南开封“有丝甚饶”;山西沿黄地区产“丝不少”;山西太原“亦种桑养蚕,产丝甚多”,山西临汾“亦产丝甚饶”;关中地区“田野桑树遍布”,西安“产丝多”;西安以南至汉中“有丝甚饶”。[xxviii]此后持续发展,仅从桑蚕灾害就可以看出。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清州、莫州、沧州、献州(今河北清县、雄县南、沧州、献县)4地桑遭霜害,毁桑2417000余棵,坏蚕12700余箔。[xxix]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真定路(今河北正定)、汴梁路(今河南开封)、晋州、冀州、深州、蠡州、景州、献州、恩州、冠州(今河北晋县、冀县、深县南、蠡县、景县、献县、山东武城东、冠县)发生桑树虫灾,其中冠州受灾桑树就多达40余万棵![xxx]冠州仅领1县,桑树至少有40余万棵,则上述各地桑林之广,是不言而喻的。山东桑蚕业仍是当地主要产业,“山东农家因之致富者,皆自丝蚕旬月之劳。”[xxxi]又如大宁路(今辽宁朝阳西)也有4州、3县“皆土产桑”。[xxxii]一直至元朝末年,不少地方还在进一步发展桑蚕。如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保定路庆都县(今河北望都)通过劝课,“四郊之桑皆郁然成列矣。”[xxxiii]元末陕西宜君县一石姓农民养蚕30箔,据传说其蚕发生变异,化为一巨蚕,吐丝15斤。[xxxiv]如果不去理会其传奇色彩,我们得到的是当地养蚕业兴盛的信息。
关于元代北方蚕事,农学家王桢有不少论述载于《农书》。王桢著《农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南北各地经验教训,以利取长补短,所以多进行南北比较:“北方养蚕者多,农家宅院后或园圃间,多种萑苇以为箔材……南方萑苇甚多,农家尤宜用之,以广蚕事。”[xxxv]“北方蚕小时,用刀切(桑)叶碪上,或用几,或用夹。南方蚕无大小,切桑俱用碪也”;所言“夹”即桑夹,为挟桑叶的工具,以便于铡刀切桑,此为北方特有的工具,一般高二三尺,“若蚕多之家”所用的大桑夹,“实纳桑叶高可及丈,人则蹑梯上之……南方切桑唯用刀碪,不识此等桑具,故特历说之,以广其利。”[xxxvi]又言:“南方例皆屋簇,北方例皆外簇。然南簇在屋,以其蚕少易办,多则不任;北方蚕多露簇,率多损压雍阏。南北簇法俱未得中……南方夏蚕不中缲丝,惟堪线纩而已。”[xxxvii]缫丝时,南方用冷盆,所出丝“细缴何轻匀”;北方用热釜,所出“丝圆尽多缕”。质量各有千秋,但若论数量、速度,则以热釜为佳:“凡茧多者,宜用此釜,以趋速效。”[xxxviii]以上不同情况归结起来,有三点可以明确:一,北方桑蚕多,养蚕业规模大;二,北方蚕事工艺先进;三,北方由于养蚕多,只好屋外露簇,相比南方蚕少可以屋簇显得粗放。由此可知,元代北方桑蚕业并未衰退,不但是发展的,而且发达于南方,至少不比南方落后。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天下户一百五十七万九千一百一十。赋丝七十万六千四百一斤,钞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七锭”。[xxxix]户均丝4.47斤。元代科差专有丝料一项,户口专有“止纳丝户”、“丝银全科户”和“五户丝户”等;其时蒙古统治区主要是北方地区,丝是主要赋税品种,充分证明北方桑蚕业的发达和在当时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统一南方近50年后的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全国科差丝总共为1098843斤[xl],仅增加39万余斤而已。当然,其中主要恐怕是赋税结构变化造成的,但至少可以说明,就丝而言,朝廷并不依赖于南方。非但如此,元朝以五户丝为王公贵族食采邑的主要方式之一,一般每位数百数千斤,多者上万斤,全部出自北方。[xli]
桑蚕业之外,麻的生产也很普遍,女真人的发祥地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田宜麻谷”,[xlii]麻是最主要的种植作物。金代陕西“种艺不过麻、粟、荞麦”,[xliii]麻也被放在首位。元代北方麻业进一步发展。王桢言:“北方种麻颇多,或至连顷。”收割时,使用专用工具刈刀,优于南方用手工拔麻“颇费工力”。并专作诗云:“森森麻幹覆荫浓,顷亩方期一捲空。谈似吴侬初未信,中原随地有刀工。”在沤麻方面,北方作法优于南方:“大凡北方治麻,刈倒即束之卧池内,水要寒暖得宜,麻亦生熟有节。须人体测得法,则麻皮洁白,柔韧可绩细布。南方但连根拔麻,遇用则旋浸旋剥,其麻片黄皮粗厚不任细绩。虽南北习尚不同,然北方随刈即沤于池,可为上法。”纺麻技术以中原地区最先进,使用大纺车,“昼夜纺绩百斤……中原麻布之乡皆用之。今特图其制度,欲使他方之民视此机栝关键,仿效成造,可为普利。”[xliv]元代北方麻业发展的另一标志是从南方传入苧麻:“近岁以来,苧麻艺于河南……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并取得显著效益:“目今陈、蔡间,(苧麻)每斤价钱三百文,已过常麻数倍。”[xlv]丰富了麻业品种和人民生活。
元代北方纺织原料生产大发展还有一划时代的标志,即棉花种植推广到内地。南北朝时新疆已植棉,至蒙元时已很兴盛。如喀什“出产棉花甚饶”,和田“产棉甚富”。[xlvi]大约在金末元初,传向陕西:“近岁以来……木棉种于陕西,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当地人民“深荷其利”。[xlvii]并很快推广到关东地区。从此,种植业结构有了较大调整,并为北方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i] 《金史》卷44《兵志》。
[ii] 《元史》卷122《槊直腯鲁华传》。
[iii] 《金史》卷44《兵志》。
[iv] 《金史》卷47《食货志》。
[v] 《宋史》卷198《兵志》12。
[vi] 《攻媿集》卷112《北行日录》下。
[vii] 《金史》卷5《海陵纪》。
[viii] 《金史》卷10《章宗纪》。
[ix] 《元史》卷160《刘肃传》。
[x] 《金史》卷7《世宗纪》中。
[xi] 《金史》卷24《地理志》上。
[xii] 《元史》卷205《卢世荣传》。
[xiii] 《元史》卷100《兵志》3。
[xiv] 《大金国志校证》卷39《男女冠服》。
[xv] 《金史》卷47《食货志》2。
[xvi] 周密《齐东野语》卷5《端平入洛》,中华书局1983年版。
[xvii] 《秋涧集》卷52《金故朝请大夫泌阳县令赵公神道碑》。
[xviii] 《攻媿集》卷111《北行日录》上。
[xix] 《金史》卷23《五行志》。
[xx] 《金文最》卷42,初昌绍《成趣园诗文序》。
[xxi] 《大金国志校注》卷40,许亢宗《奉使行程录》。
[xxii] 《攻媿集》卷111《北行日录》上,卷112《北行日录》下。
[xxiii] 《金史》卷23《五行志》。
[xxiv] 《金文最》卷78,陈大举《济阳县创建先圣庙碑》。
[xxv] 《金史》卷84《昂传》。
[xxvi] 《农书》卷9《桑椹》。
[xxvii] 文天祥《文山全集》卷14,北京市书店1985年版。
[xxviii] 《马可波罗行纪》第96、134、137、148、113、110、114、115章。
[xxix] 《元史》卷50《五行志》1。
[xxx] 《元史》卷35《文宗纪》4。
[xxxi] 《秋涧集》卷62《劝农文》。
[xxxii] 《元一统志》卷2《大宁路• 土产》。
[xxxiii] 《滋溪文稿》卷18《从仕郎保定路庆都县尹尚侯惠政碑铭》。
[xxxiv]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3。
[xxxv] 《农书》卷20《蚕椽蚕箔》。
[xxxvi] 《农书》卷21《桑碪》、《桑夹》。
[xxxvii] 《农书》卷6《蚕缫篇》。
[xxxviii] 《农书》卷20《缫车》、《热釜》。
[xxxix] 《元史》卷5《世祖纪》2。《元史》卷93《食货志》1作“丝七十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一斤”,与此数稍异。
[xl] 《元史》卷93《食货志》1。
[xli] 《元史》卷95《食货志》3。
[xlii] 《三朝北盟会编》卷3。
[xliii] 《金史》卷92《毛硕传》。
[xliv] 《农书》卷22《麻苧门》。
[xlv] 司农司《农桑辑要》卷2《论苧麻木棉》、《苧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实际上陈州在先秦时已产苧麻,《诗•陈风•东门之池》:“东门之池,可以沤纻”即是。
[xlvi] 《马可波罗行纪》第50、53章。
[xlvii] 《农桑辑要》卷2《论苧麻木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