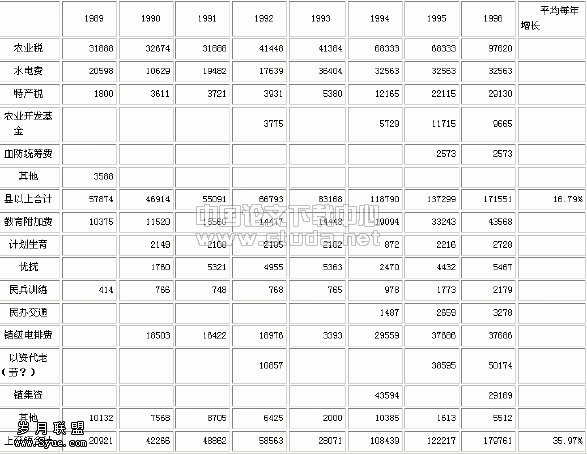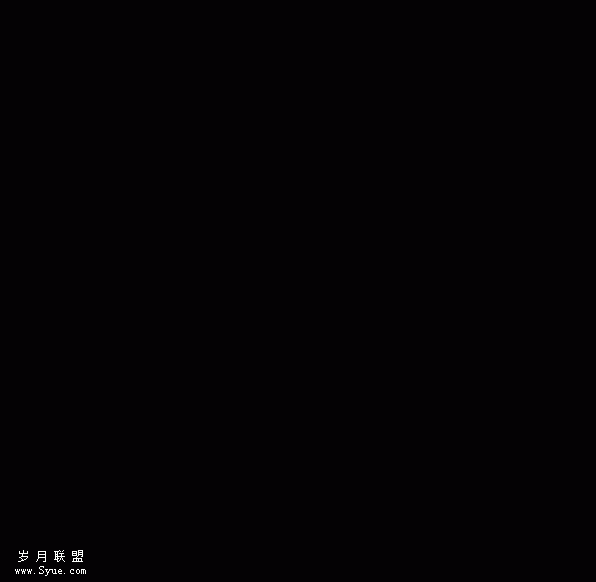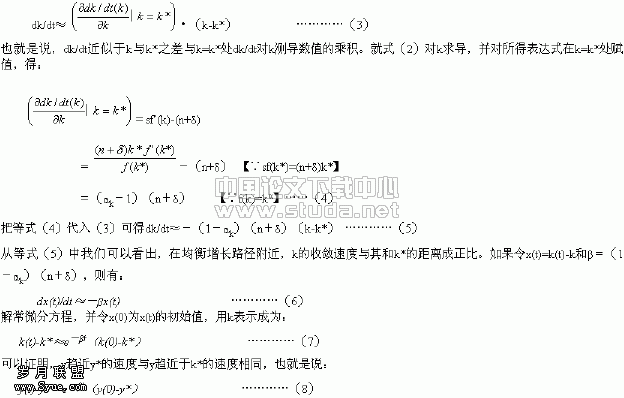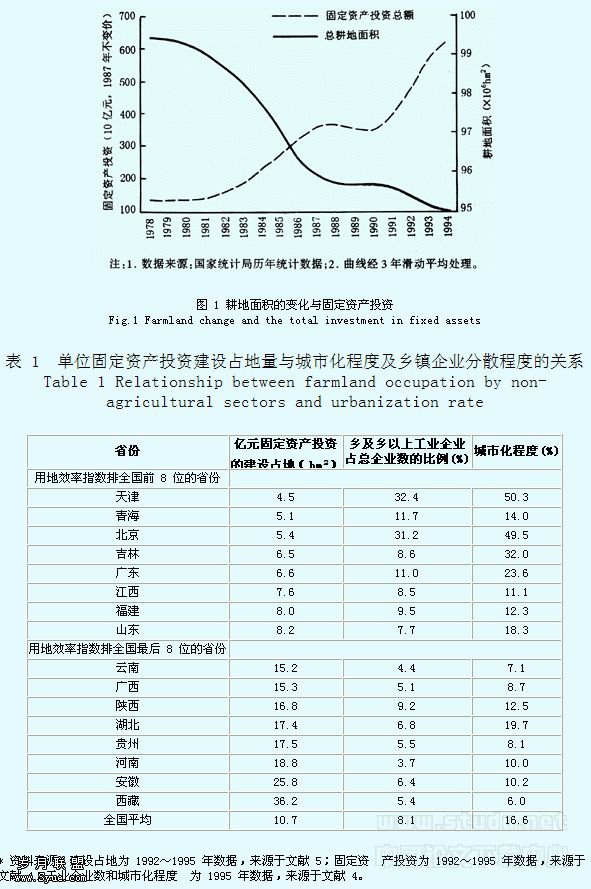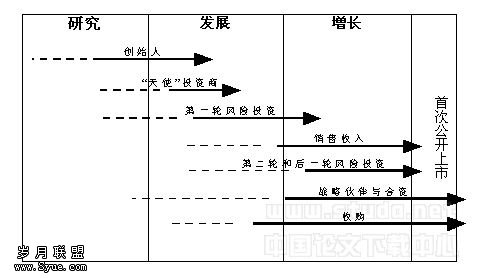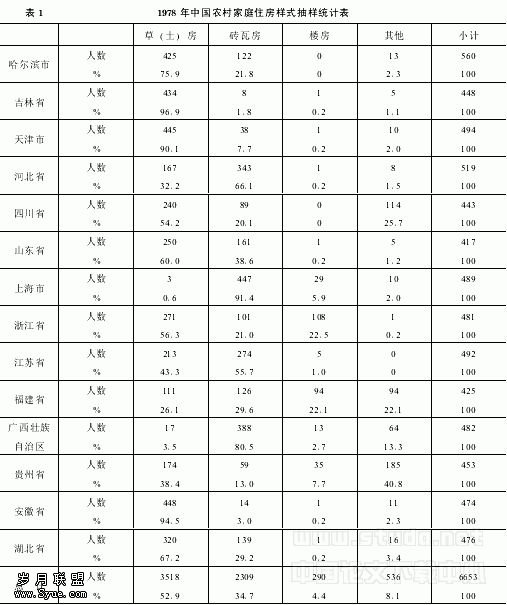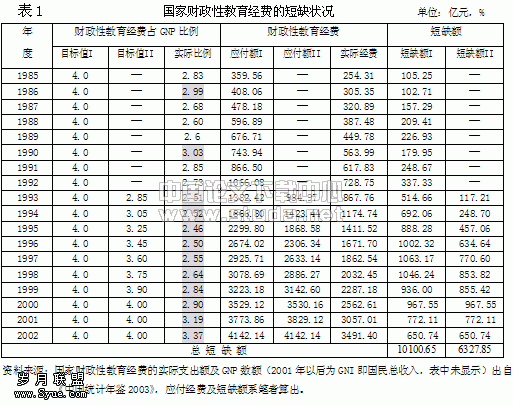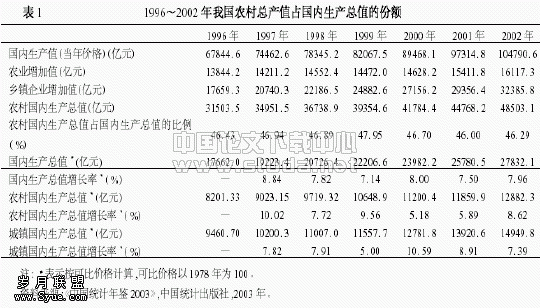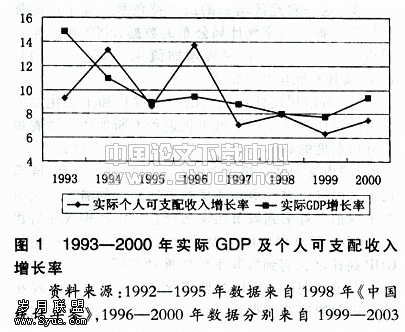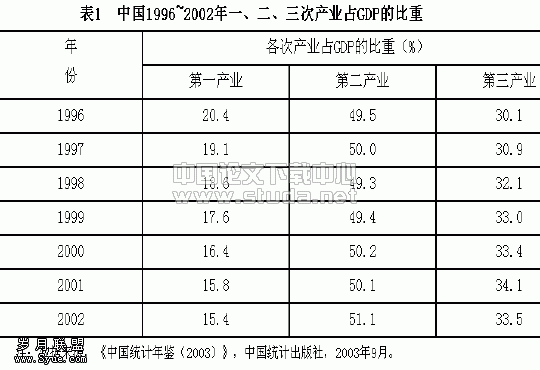产业革命的梦寐(下)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首航川江的这条小轮船,是属于一家由四川士绅和商人组成的川江轮船公司的。这是一家在四川收回路矿权利的运动中诞生的华商公司。它打着官商合办的招牌,但在经营的过程中,却受到官府的阻碍。它虽然得到四川总督赵尔丰在草创时期的赞成,但却遭到湖广总督陈夔龙在营运过程中的反对,以至后来竟一度闹到“蜀通”轮船不准进入湖北的境地。[4] 创业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蜀通”号还是出了川江。不仅如此,通过“蜀通”的影响,此后数年,川江之上陆续出现了众多的小轮船公司。当然它们的寿命,大都是短暂的。但川江轮船公司却顶住困难,存在了一个相当长的岁月。1919年4月我国著名的家任鸿隽从海外回到故乡,坐的就是“蜀通”号轮船。他在船上还对这条陌生的小轮作过一番描写,抒发了自己对这条船的感情。在4月16日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这船是航川江商船的始祖。他的造法甚为稀奇。全船分为两只,一只单装汽机,一只单装客货。两只合并起来用绳缚住成一个‘狼狈’形势。但是若在河中遇着大风,风水鼓荡,两只船一上一下,所生的剪力(Shearing force)可了不得,就有一寸来粗的麻绳,也可以振断。“因为蜀通轮船是四川人办的,坐船的也大半是四川人,所以我一上蜀通船,就有身入川境的感想。”[5] 这位科学家的见闻和感情都是真实的。“蜀通”号在订购之时,就附有一只拖船,它的载重,甚至超过了轮船本身。其所以如此,显然是为了减轻轮船的吃水,以适应峡江的航行。[6] 这说明当年川江航行的原始状态,反映了航行条件的极端困难。就在任鸿隽乘坐的这趟船上,根据他的亲身体会:“那船的簸动,比在海船上遇风还要利害。”[7] 尽管这样,它却引发了这位爱国科学家的怀乡情感。任鸿隽把“蜀通”号说成是航行川江商船的始祖,从一个角度看是事实,即它是中国自办商轮航行川江之始。从另一个角度看,则并非事实,因为在它第一次航行川江之前10年,英国的“利川”号轮船已经到过重庆[6] 而德国的轮船“瑞生”号,则在其后二年准备继“利川”而进入川江之时,沉没在宜昌上游之崆岭[9] 。“利川”号航行的成功,在英国人的眼中,是“以文明的方式进入川江之始”[10] ,可以提到“名垂史册”的高度[11] 。而“瑞生”号的沉没,在德国人的眼中,则是“一个挺有希望的事业的可悲结局”[12] ,是“一场明白无误”然而又是“极其伟大”的悲剧[13] 。事情是实际存在的,看法却颠倒着。任鸿隽的提法,有把颠倒过去的看法再颠倒过来之效。人们从这里所感受到的,是弘扬中国的情结,也就是弘扬中国的产业革命精神。
在航运业中,还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华侨对祖国远洋航运的开辟。1915年旅美华侨创立的中国邮船公司,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向袁世凯提出21条无理要求后,旅美华侨纷纷奋起,以抵制日货表示反对。为了打破日本对太平洋航运的垄断,在同年10月集资创立了一家航行太平洋的远洋航运公司,先后购置万吨级轮船三艘,并以金煌的名字“中国”命名第一艘轮船。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了显著的业绩。虽然战后因剧烈的竞争和日本的破坏而被迫停业,但它的短暂存在,在中国航运史上,仍不失为可歌可泣的辉煌一页。[14]
在讯息传递的电报业中,中国人所表现的进取精神也异常突出。早在中国电报局正式成立之前的1872年,据说一个在法国研究电报技术多年的华侨,就从那里带回自制的汉字电报机器,准备在上海开办。[15] 这个计划虽然没有下文,但是在后来的中国电报局中,中国的留学生在电报技术的更新和标准化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留美学生周万鹏就是其中比较出色的一位。1907年邮传部成立之际,周万鹏被派出席在葡萄牙举行的万国电约公会。会议期间他了解到西方各国的电报政策和技术规范,深感我国治理电政未谙约章,动辄为外人所牵制,于是在回国以后,着手编纂《万国电报通例》,使我国电政“底于统一”。1909年,周万鹏任职电报总局兼上海分局总办时,发现各局仍用旧莫尔斯机收发电报,易于阻滞,乃全部改换成新创的韦斯敦机,从而使上海电报局趋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推动了电报业的全面革新。[16]
电话业中,传出了同样的讯息。20世纪之初,据说声筒,“以玻璃为盖,有钥司启闭,向管发声,闭之以钥,传诸千里,开筒侧耳,宛如晤对一堂”。还有人造德律风,“较西人所制,可远三倍”。[17] 这些虽属传闻,缺乏具体依据,但从中可以察觉到:社会风尚,已不同于往昔。
资本主义中焕发出来的产业革命精神,尤其引人注目。作为例证,我们选取人们所熟知的三个企业——张謇的大生纱厂、简照南与简玉阶兄弟的南洋烟草公司和范旭东的久大与永利盐碱工业系统,它们都有艰难的创业历程,都有高度发挥生产力的业绩。久大开辟了中国制碱工业的新时代,获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这是人所共知的。南洋、大生的早期奋斗业绩,也为人所知晓。它们的,共同表现了中国近代产业革命的精神。没有必要描述它们的全部历史。表现他们之间的共同精神,只需各举一例。
创办久大、永利的范旭东,被人们公认有“一颗炎黄子孙的心”。如今保留在天津碱厂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22年,当永利正在建厂的过程中,英国卜内门洋碱公司的经理李特立[18] 曾当着范旭东的面说:“碱对贵国确是重要,只可惜办早了一点,就条件来说,再候30年不晚。”面对这种奚落,范旭东的回答是:“恨不早办30年,好在事在人为,今日急起直追,还不算晚。”[19] 三年以后,当永利建成并成功出碱之时,卜内门的首脑又反过来要求“合作”,这时的范旭东则坚持公司章程:“股东以享有中国国籍者为限”,将卜内门拒之于永利大门之外。[20] 最终打破卜内门独霸中国市场的企图。
这种精神,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玉阶身上,同样可以找到。
南洋烟草公司成立于1905年。它的成立,本身就有着抵制洋货、收回利权的历史烙印。[21] 成立以后,中经多次挫折,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才慢慢立定脚跟。正当南洋蒸蒸日上之时,曾经多方遏制南洋于襁褓之中的英美烟公司,此时却变换手法,企图以“合办”的方式,兼并南洋。面对这一外来压力,在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之间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哥哥简照南认为英美烟公司“势力之大,若与为敌,则我日日要左顾右盼,无异与恶虎争斗,稍一疏忽,即为吞噬。若与合并,则变为通家,如孩童之得有保姆护卫,时时可处于安乐地位也”[22] 。弟弟简玉阶则坚决表示拒绝,一再表示:“纵有若何好条件,亦不甘同外人合伙。倘大兄不以为然,弟唯退隐,无面目见人而已。”[23] 简玉阶的意见占了上风,南洋免遭兼并,获得了一段空前的营业鼎盛时期。
这种精神,同样也见之于张謇在大生纱厂的创业阶段。张謇在封建文士耻于言商的清王朝治下,以“文章魁首”的状元之尊,为创办通州的第一个资本主义企业而全力奔走,这本身就具有明显的为振兴实业而献身的精神。“马关条约”开外国在中国内地设厂之禁,使他的这种精神受到极大的推动。他大声呼号:“向来洋商不准于内地开机器厂,制造土货,设立行栈,此小民一线生机,历年总署及各省疆臣所力争勿予者。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沾。”[24] 日本“今更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25] 。张謇之全力创办大生纱厂,即使还有其他种种原因也不能抹煞这个基本的因素。
如所周知,张謇的实业活动,初期遇上了严重的困难,从大生筹办(1895)到开工(1899)的五年中,多次陷入筹措资金的困境,几乎到了“百计俱穷”、“一筹莫展”的境地。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也曾用招洋股的办法,来威胁曾经支持他的两江总督刘坤一。然而他究竟没有这样做,终于挺了过来,作困兽之斗。这还是难能可贵的。把它归结为产业革命的精神,应该说:“当之无愧”。
“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的气氛,也弥漫到相对沉寂的手工业中。
中国封建社会中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来得及为中国的机器大工业提供产生的条件,但是在大工业已经产生的土地上,却不妨出现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化。这种情形,在辛亥革命前后的20世纪初,尤其明显。这里只选取中国的传统两大著名手工业——以四川为中心的井盐和以苏南为主体的丝织,让它们来印证这种气氛的弥漫景象。
四川井盐采用蒸汽动力和机械开采的酝酿,在19世纪的90年代,就已经开始萌动于一批有进取心的人中间。[26] 实际着手,是在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的10年间。而正式启动推广,则在辛亥革命之后,大约又经历了10年的光阴。
作为四川井盐重镇的自贡盐场,是蒸汽采卤机车诞生之地。走第一步的,却是一个经营花纱生意的商人。他的名字叫欧阳显荣,从1884年起,就在内江经营花纱生意,并在重庆设有庄号。[27] 大约与此同时,他又曾在自流井办过盐井,深感“纯用牛力”吸卤的笨拙。1894年,据说他曾经去过一趟武汉,在汉阳看见长江码头的货轮用起重机装卸货物,便产生了起重机升降货物的原理,用于盐井汲卤的设想。随后通过同他人的合作,设计出一张汲卤机的草图,由汉阳周恒顺五金厂工厂试制。经过一年的时间,终于制成第一部汲卤机车。随后运到自流井试行运作,这时已是1902年前后。此后两年,对机器不断进行改进。据他自己说:“此井推水较前用牛力推水者加强10倍。”但因机件易于损坏,经常发生故障,“终难获永久之利用”。[28] 一直到1904年以后,才基本上解决了汲卤中的各种问题,机器应用于井盐生产才逐渐得到推广。到1919年止,整个自贡地区盐场中,使用蒸汽机车的盐井,共达到37眼之多。[29]
手工丝织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化,在时间上比井盐业要晚一些。而且既有一个落后的手工工具——改良的手工工具——机器的完整过程,又有未经手工生产而直接进入机器生产的例证。
改良手工工具的引用,最先是日本式的手拉提花丝织机的引进。大约从1912年开始,这种织机先后出现在苏州、杭州、湖州、盛泽。而电机的引用,则首先见之于1915年的上海。[30] 至于苏杭等地手工丝织业中由改良工具向机器的过渡,则迟至20世纪的20年代以后。苏州手工丝织业在正式引用改良手工工具之后七年,就进而引进电力织机。[31] 杭州的手工丝织业,在1919-1926年之间,也“由旧式木机,一变而为手拉铁木合制机,再变为电机”。[32] 稍后更扩大到湖州、宁波等处。[33]
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手工业,在20世纪之初,再现了18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产生时期手工与机器的对抗。四川井盐中第一部汲卤机车的出现,多数井户持反对的态度。最先试办机车推卤的欧阳显荣,甚至碰到“没有井户把盐井出租给他推汲”的尴尬处境。[34] 苏州第一家引用电力织机的苏经绸厂,也引起了传统手工业者的恐惧和反对,经常受到他们的“来厂滋扰”,以至厂主不得不请求地方当局的“保护”。[35]
正由于此,由手工向机器的转变,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进程。欧阳显荣为了向手工井户证明机器生产的优势,不惜将他长期从事的花纱生意停下来,把营业权和房产加以变卖,三赴汉阳,聘请翻砂工,制造车盘、车床、车钻、车挂和双牙轮等部件,反复试验,通过同各种阻力和困难的斗争,终于成功地安装起第一部汲卤机车,为以后的推广打下了基础。[36] 而苏州丝织业中采用机器生产的厂家,在变木机为拉机、电机,变土丝为厂丝、人造丝,变分散织造为集中生产三个方面,也作出了艰巨和富有成效的努力。“进行之神速,出品之精良,实有一日千里之势”[37] 。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产业革命的精神。
在变化最小、最少的农业中,人们也能察觉到这种精神的存在。
应该承认,在近代中国,农业中的“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并没有“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所代替,农业和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没有“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38] 但是在资本主义企业向国民各个部门扩散的影响下,这个内里保持不变的最大经济部门的表层上,也出现了若干新的斑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新式垦殖企业。从190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从东北到西南,掀起了一个设立垦殖公司的小高潮。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止,全国各地设立的各种类型的农垦企业,在170家以上,申报的资本达600多万元。[39] 这些农垦企业,绝大部分是徒具形式,既少自营,更少更新生产工具和技术。同资本主义农场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这些农场的出现,究竟是前所未有的,其中不能说没有一点资本主义的影响,这些企业的创办者,不少是接触过西方资本主义的人物。如1906年在海南岛创办中国第一家橡胶垦殖公司的何麟书,是一个曾经在英国殖民地马来西亚橡胶园里做过工人、对橡胶树的培植管理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华侨。[40] 1907年在黑龙江成立的兴东公司,它的创办者也是一名久居海外的华侨。[41] 1916年在江苏宝山创设一家万只养鸡场的何拯华,则是一位曾经“留学毕业返国”的洋学生。[42] 有的农场的经营管理,也能吸收一点资本主义的经验。如1905年成立的浙江严州垦牧公司,其种植技术“悉仿日本新法”[43] 。1906年在广东嘉应成立的自西公司,也声称“参用西法试种橙、橘、松、杉、梅、竹各种木植”[44] 。而上述的兴东公司和张謇在1901年首创的通海垦牧公司,一个声称引进外国火犁,进行开垦[45] ;一个更具体提出怎样“采用美国大农法”于棉麦的种植[46] 。这些事实,客观上可能都有夸大之处,但它至少表现出创办者进取的主观意图,这是无可置疑的。
同在手工业中一样,在农垦业中,也存在着新旧势力的冲突。同何麟书齐名的另一华侨梁炳农,1911年在南京后湖创立了一个江宁富饶垦牧场,还没有正式开办,就受到了“湖民全体”的“聚集”反对,原因是农场成立以后,他们会“陡失生机”。[47]
这种先进同落后的冲突,甚至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福建华侨之投资农垦企业,集中在30年代的后期。然而蓬勃一时,又迅速衰落。其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遭受反动统治机构和地方封建势力的摧残”[48] 。在遗留下来的旧时代官府档案中,如今还保留着大量的华侨为举办农场而请求地方官府给予保护的文件。这些只是“层层转呈”而往往没有下文的文件,就是这些农垦企业的命运的最好证明。
同在其它行业中一样,新式农垦业的兴起,也包含着创业者的艰苦努力和革新精神。被称为海南橡胶鼻祖的何麟书,在森林莽苍、蔓藤纠葛、荆棘丛生、山岚瘴气的海南岛上,开发这块沉睡的土地,的确包含了无限辛酸。他胼手胝足,身体力行,不顾不服水土,吃住在山林,不顾身患重病,仍然坚持工作。艰苦备尝,终于垦出了200多亩胶园,为农场奠定了基础。[49]
他又是一个勇于探索、百折不回的革新者。他在海南岛引进橡胶,最初的方法是播种橡胶种子,但是一连三年,九次播种,全未成功。集来的股本,付诸东流。在股东纷纷要求退股的严峻时刻,何麟书毫不动摇。他变卖自己的产业,清偿旧债,重招新股。继续进行试验,精心培育,终于探索出一条从播种树种到移植树苗的成功办法。[50] 不到10年功夫,乳白色的胶汁,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从橡胶树上流了下来。[51] 应该说,这种努力,也体现了一种产业革命的精神。
中国的资产阶级对产业革命寄托了浓厚的希望。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初,民国政府成立之日,中国的资产阶级团体就发出了产业革命的呼声。一个名叫工业建设会的团体在南京民国政府成立不久的1912年初,就曾经发出“建设我新社会以竟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的欢呼。[52] 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从那时起,满怀产业革命之梦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又奋斗了近40年,中经国外强邻的凌虐,国内军阀的蹂躏,其后又经历了八年抗战工厂内迁的流离与颠簸,大后方创业的困厄和艰辛。他们梦寐以求的产业革命,终究却成为泡影,不得一见。当八年抗战胜利来临之日,光明即在眼前之时,他们从当局者口中得到的讯息,都是“现存工厂无论在资金、设备、技术各方面,都根本不算工业,不如任其倒闭”的评价。[53] 这一可悲的结局,彻底结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长达将近一个世纪对产业革命的憧憬。
近代中国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产业革命。近代中国产生了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中国没有经历过产业革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它仍是一个向下沉沦,看不到前景的社会。
中国的沉沦,并不等于中国不再奋起。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沉沦,所以才有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力量在艰难中的奋起;正是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一个沉沦的社会中诞生,所以新兴的资产阶级才面临着奋起的艰难。产业革命之不能出现于近代中国,正说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是多么艰辛而难以实现,正是要人们记取几代人为资本主义前途进行艰苦奋斗而又不能如愿以偿,必须另觅途径的历史必然。
中国的无产阶级接受了这个时代的挑战。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接过了革命的火炬,领导全国人民将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取得了成功。完成了民主革命的新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实现中国资产阶级所不能实现的产业革命,是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成功地实现中国的产业革命。但是,它的众多代表人物是中国资本主义历史的创造者。无论是漠河金矿的李金镛、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大生纱厂的张謇、南洋烟草公司的简玉阶以及航运、电讯、农垦、盐场等行业中的先进人物,都是在这段历史进程中起过作用的带头人。历史是不会磨灭的。当人们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它的发展和不发展,它的创业者的业绩——包括成功和失败,都不应该也不可能被遗忘和忽视。
注释
[1] 《支那报告书》, 第 47期,第24-25页,转见樊百川:《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 410页。
[2] “蜀通”号载重,一说为80吨,一说为30吨,均不超过百吨。参阅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410页,聂宝璋:《川江航权是怎样丧失的》,参阅《研究》,1962年,第5期,第144页。
[3] 《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 第 1卷,宜昌, 第 261页,参阅聂宝璋:《川江航权是怎样丧失的》,见《历史研究》,1962年, 第 5期。 ,第 144页。
[4] 《史航政编》,第3册,第1253页,转见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410页。
[5] 民国八年四月十六日,任鸿隽致胡适函,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1979年版, 第 37-38页。
[6]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 第 410页。
[7] 民国八年四月十六日任鸿隽致胡适函,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第 37-38页。
[8] Herald ,1898年4月11日, 第 612-614页。
[9] Herald,1901年1月2日, 第 3-4页。
[10] Herald,1898年4月11日, 第 613页。
[11] Herald,1898年4月11日, 第 613页。
[12] Herald,1901年1月9日, 第 63页。
[13] Herald,1901年1月9日, 第 63页。
[14] 张心徵:《中国交通史》,1931年版, 第 289页。
[15] 《海防档》,1957年版:丁,电线(一),第100、105页;(二),第306-307页。
[16] 《宝山县再续志》,卷14,人物事略。转见沈其新《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实业》,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0),上海社会院出版社1990年版。
[17] 张通煜辑译:《世界进化史》,下卷,1903年版, 第 68页。
[18] 卜内门公司(Brunner ,Mond and Co·Ld)为E·S·Little所创办。李特立亦作李德立。
[19] 《永利厂史资料》,(1)48/53,第110-126页,转见《工商经济史料丛刊》, 第 2辑,1983年版,第3-4页。
[20] 《工商经济史料丛刊》, 第 2辑, 第 4页。
[21] 清原:《简玉阶先生和他的事业》,转见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史资料》, 第 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 第 489页。
[22] 1917年3月16日简照南致简玉阶,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 113页。
[23] 简玉阶致简孔昭,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第 111页。
[24] 《条陈立国自强疏》,见《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参见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1986年版, 第 48页。
[25] 《张謇致沈散夫函札》,(稿本),转见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 第 60页。
[26] 《关册》,重庆口,1891年, 第 68页。
[27] 张学君:《四川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初步》,。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 4期, 第 97页。
[28] 自贡市档案馆475号案卷:《欧阳显荣呈文》,转见《四川井盐史论丛》,1985年版,335-336页。
[29] 钟长永据林振翰:《川盐纪要》,订正。见《四川井盐史论丛》, 第 340页。
[30] 王翔:《中国传统丝织业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过程》,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 3期,86-87页。
[31] 苏州档案馆藏档案资料,见王翔:《中国传统丝织业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过程》,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 3期, 第 88页。
[32]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第 3卷,1957年中华书局版,第 73页。
[33] 王翔:《中国传统丝织业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过程》,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 3期, 第 88页。
[34] 《四川井盐史论丛》, 第 337页,
[35] 《苏经绸厂请求保护电机案卷》,见王翔:《中国传统丝织业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过程》,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 3期, 第 88页。
[36] 《四川井盐史论丛》,第336-337页。
[37] 《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呈请立案》,见王翔:《中国传统丝织业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过程》,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 3期, 第 92页。
[38] 参阅《资本论》, 第 1卷,第551-552页。
[39] 《农商部,第一次农商统计表》,转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57年版, 第 698页。
[40]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概论》, 第 178页。
[41]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 696页。
[42] 《宝山县续志》,实业志,卷6,转见毛德鸣:《中国近代新式农垦企业初探》,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 2期, 第 94页。
[43] 《东方杂志》,2年7期,转见毛德鸣:《中国近代新式农垦企业初探》,参阅《中国经[史研究],1989年,第 2期, 第 94页。
[44] 《东方杂志》,3年3期,转见李文治:《中国近代新式农垦企业初探》,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 2期, 第 878页。
[45]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 696页。
[46]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二, 第 29-30页,参见毛德鸣:《中国近代新式农垦企业初探》,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 2期, 第 94页。
[47] 《时报》,宣统三年三月三十日,转见小岛淑男《清朝末期南洋华侨在祖国的企业经营》,(油印稿)。
[48] 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1985年版, 第 199页。
[49] 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 第 314页。
[60] 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 第 314页。
[51]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 第 180页。
[52] 1912年工业建设会发起趣者,见《民声日报》,1912年2月28日。
[53] 齐植璐:《抗战时期工矿内迁与官僚资本的掠夺》,参阅,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工商经济史料从刊》, 第 2辑,1983年, 第 96页。
上一篇:中国国情与早期现代化(上)
下一篇:产业革命的梦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