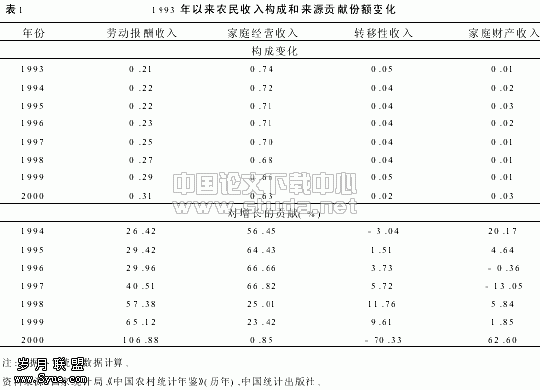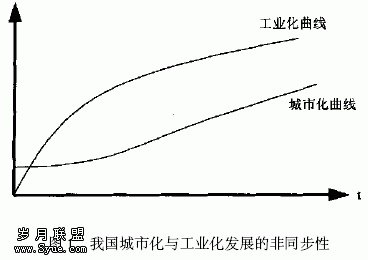非正式制度与社会冲突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1
The moral, religion, rite, bible record, and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are regarded as informal institutes in this essay. It is important to analyze these institutes for explanation of social stability or confliction. (1) The offspring of religion is the trepidation for the uncertainty, and so religion has a function of diminishing the degree of uncertainty. There are no hard lines between religion and cult and that of between religion and superstition, in human mentality. It is positive for social stability to limiting the extension of religion, but it is no necessary and even dangerous to seek eliminating the religions. (2) Rite is a type of human behavior, which can communicate some important information among people, and can make the surroundings in order. Proper rite is propitious to social stability. (3) Moral is a set of rules of behavior with the function of shame feelings.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moral c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social integration, and in the periods of transi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the moral function seem unimportant. (4) In the closed rural society,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supports a stable social structure. Only in terms of destruction onto traditional rural order taking place, and the old benefit equilibrium is tipped, fierce confliction among different clan will take place.
关注乡村社会冲突,不能不关注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相对而言,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在乡村要大于城市,因此,本文论列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在乡村社会。本文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学的方法。通常,非正式制度也被学者们看作一个社会的文化状态(樊纲,1994)。但一谈到文化,便触及到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泥坑,因为文化研究领域几乎没有统一的学术研究语言,导致以不同学术语言武装起来的学者经常胡乱战在一起,见不到分晓。到未来,要看哪一个人文学科取得学术霸权,它的语言也就会一统人文学科的天下。但许多问题的讨论显然不需要等到这一天。为避开这一麻烦,本文把道德、宗教、礼仪、典籍文化和宗法制度看作非正式制度,分析这些制度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如果把是否通过国家进行规范作为一种制度是否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的依据,那么,本文是涉及的一些因素在某些国家的某些时候也可能是正式的制度,但这种个例并不妨碍本文的分析。
一 . 宗教影响
(一) 宗教的本质
宗教产生的根源是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因此,宗教具有降低不确定性的作用。伟大的费尔巴哈曾说:“宗教的整个本质表现并集中在献祭之中。献祭的根源便是依赖感----恐惧、怀疑,对后果、对未来的无把握……而献祭的后果……则是对后果的有把握,自由和幸福”(费尔巴哈,1845 )。在人与的关系当中,宗教的存在反映了人们试图规范这种关系的愿望,尤其反映了人们关心彼岸世界、试图与彼岸世界对话的愿望。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宗教具有加强人们之间相互认知的作用。共同的崇拜对象、普遍接受的教义规则,可以成为人们之间相互认知的符号,从而可以降低人们之间的交易成本。
(二)宗教与社会稳定
强烈的宗教感情对于同一宗教共同体能起到稳定内部关系的作用。但是,在不同的宗教共同体之间,宗教分野会强化人们的对立,造成大范围的社会不稳定。在落后社会,宗教对人的行为有较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不确定性在一定范围里是知识积累程度的函数,知识的进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不确定性,从而弱化人们的宗教感情。在文明产生之前,宗教分野曾经是社会对立的一个重要因素,更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根源。
在社会,宗教仍然对人们的行为有重要影响。有人把宗教的这一作用当作文化独立性的表现,是没有根据的。也有人对现代文明社会的宗教感情表示不可理解。实际上,现代文明并没有消除宗教存在的根据----人们对彼岸世界的恐惧。在死人与活人之间因差异而存在信息的绝对不对称,不能回答彼岸世界究竟存在与否;此岸之人对彼岸之人完全无知。我们看到,即使相信灵与肉不可分离的无神论者也少不了那份面对死亡时的虔诚与恐惧。总之,科学不可能消除人们的宗教感情,现代社会的人们仍有可能从宗教中寻求“终极关怀”。这一论点所包含的启示是:如果某种宗教引起了社会不稳定,政府不要试图去消灭宗教本身,而应该去设法改变宗教的内容或形式。
很难一般性地概括说哪一种宗教更有利于或不利于社会稳定,也很难说哪一种宗教更成熟或更不成熟,对大的宗教来说尤其如此。对这方面作出评论,只能从实施出发。可以把宗教分为正统一神教、多神教和异教三个大的类别。被某些国家官方认可或尊奉的正统一神教中,基督教在现代社会有较强的稳定作用,但它也曾有过引起民族纷争、社会动乱的历史记录。欧洲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大多有宗教背景。
(三)科学与宗教的斗争
敬畏科学并不意味着消灭宗教,甚至从目前来看不可能消灭宗教。尽管宗教没有证明“彼岸世界”的存在性,但科学也没有证明“彼岸世界”的虚假性,而总有一些人在心理上对“彼岸世界”的存在性寄予希望,于是,科学的局限性便给宗教活动留下了空间。在死人与活人之间因自然差异而存在信息的绝对不对称,科学不能回答彼岸世界究竟存在与否;此岸之人对“彼岸之人”完全无知。于是,现代科学把宗教驱赶出世俗生活之外时,便不得不与宗教和平共处了。宗教批判家可以雄辩地批判一切关于上帝的故事,但对上帝本身的批判却只能停留在的意义上。现代世界主要宗教的活动边界,很符合休谟和伏尔泰的“自然神论”所给出的宗教的意义:“神一旦创造出世界,就不再干预世界的事务。”离开世俗事务,宗教只去照顾那些对“彼岸世界”的不确定性在心灵上发生恐惧的人们,使他们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宗教通过一系列程式化的礼仪,使信徒的恐惧心理得以安抚,并产生了某种稳定社会的功利价值。但是,现代宗教已经十分知趣,除过某种“劝说”,而决不再替代和道德对人的世俗行为进行裁判,更不去与科学技术争论长短。科学与宗教在欧美国家最终确立各自的边界,是人类文明的杰出成就,并对于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具有重大的功利意义。伏尔泰有这样一句充满理性光辉的话:“即使没有上帝,也要捏出一个上帝来”( C. 阿尔塔莫诺夫,1954)。
科学与宗教的斗争,也使宗教自身得以被改造,并使一些宗教上升为区别于邪教、迷信的主流宗教。宗教与邪教之间、宗教与迷信之间,并没有人类理性意义上所能够确定的界限。在历史上,那种与世俗的王权相互承认的宗教可能是正统的宗教,而处于二者之间并且不被世俗王权承认的宗教,则可能被看作异教、邪教。与那种有严密组织的宗教相比,另一些散见与传统乡村社会的、通过传说和习惯保留下来的有神论观念及其祭祀活动,则会被主流社会视为迷信。与邪教、迷信相比,现代世界的大多数主流宗教的领袖行为较为节制,教徒对另类宗教的态度相对宽容,教会机构不追求更不行使对教徒的世俗行为(乃至信仰选择行为)的裁判权。这是科学以及世俗权威与宗教斗争的结果。
并不是一切国家都确立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稳定的活动边界。宗教一旦越过自己应该立足的边界,几乎毫无例外地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并表现出种种邪教恶行。在这种国家,主导宗教的旁边会经常滋生某种形式的邪教,并裹挟着某种社会情绪,使被蒙蔽的广大信徒成为邪教领袖实现野心的赌注和牺牲品。近年来一轮又一轮的“气功热”的确让人们深思。表面上看,中国人对肉体关照的需求似乎超过了对心灵关照的需求,并把关照肉体的希望寄予某种神秘的力量,其实这是中国医疗事业不发达所产生的结果。欧洲国家也曾有过那么一个时期,人们把身体交给“上帝”去关照,后来在科学力量和政府权威的压力之下,宗教才逐步放弃了照顾人的肉体的责任。如果这个边界守不住,主导宗教就无异于邪教,各种小的邪教也会不断兴风作浪。在世俗生活领域,现代科学本来具有足够的力量战胜宗教,如果出现了相反的情形,一定是这个社会现代文明的发展存在严重障碍。
从洋务运动开始化的历程,但期间没有认真出现过启蒙运动。某些时期的世俗政府甚至与邪教建立联盟,以图自保。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搞统一战线,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民间也鲜有对宗教的批判,使无神论思想的传播极为有限,老百姓事实上不能区别宗教和迷信究竟有什么区别,更不懂得从合法性上判断宗教活动应该遵守的边界。本来,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与民间对宗教的批评应该并行不悖,但我们民间对宗教的批评几乎是万马齐喑。看看近一些年的图书市场吧,少有宣传无神论的书籍来与宣传“怪力乱神”的书籍叫板(似有一位可敬的记者批判柯云路)。无庸讳言,充满“怪力乱神”的书籍能在市场上找到极好的“卖点”,追求金钱而粪土理性的一些国有出版的老板们便为了金钱拥抱乱神去了。说实话,要不是“法轮功”领袖的利令智昏使他们的信徒围堵中南海,这种局面不知何时才会结束。这种状况就是奉行出版自由原则的欧美国家也很难发生,这不令人深思么?
企图通过在普通民众中普及彻底的无神论,是极为困难的。有人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与宗教信仰之间并没有关联。1916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勒巴的研究人员的调查结果发现,只有40%的科学家相信上帝。他预言,科学家中不敬神的比例将随着教育的普及而增多。为了检验勒巴的预言,佐治亚大学学家爱德华·拉森和马里兰州的拉里·威瑟姆在1997年采用勒巴当年使用的方法又对科学家的信仰作了调查,结果与前一次有惊人的相似:大约有40%的科学家仍相信存在有血有肉的上帝和灵魂。两次调查中都有45%的科学家不相信上帝,15%的则抱怀疑态度。这项研究表明,教育的提高和普及并没有消除一部分人的信仰需要。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在邪教或异教的信徒中,鲜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这个事实说明,良好的教育尽管不能消除宗教信仰,但却可以约束宗教活动于某种确定的、非世俗的范围之中。为了使科学与宗教之间有一个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边界,现代政府必须注意两点:第一,在世俗生活领域,应该通过立法,不仅不能允许宗教及其变种干预,也不能允许它们“关照”人的肉体。耍鬼弄神致人死命的,以谋杀罪论处。第二,即使退出世俗生活领域,进入所谓信仰领域,固然不可用立法来限制人的信仰,但应保护民间人士对宗教的批评态度。通常,宗教界有强大的财力宣传有神论,而民间个人却没有财力来宣传无神论,因此,政府应通过资助科学的途径来帮助宗教批判家。
当前,批评邪教、迷信,宣传无神论,决不能殃及社会进步力量(至少是潜在的进步力量)。从历史经验看,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是最有可能欢迎无神论的阶级,至少他们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宗教。中国改革正在造就一个中产阶级,他们在本质上反对宗教力量的世俗化。我们切不可说什么唯心主义、有神论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再把资产阶级拉出来批判一通,更不可以要人民大众去“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如果要这样做,那无异于以迷信批判迷信,注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守卫好科学的边界,把一切世俗事务交由科学技术去控制,有着广大的内涵。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技术也包括社会技术。政府的组织形式作为世俗事务,应该遵循社会科学;政府的施政行为也应该被规范为一种社会工程技术。以往我们把太多的东西看成了意识形态的东西,现在应该把它们还原为中性的社会工程技术。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使科学的光辉照耀人类生活的一切世俗领域,而把各种宗教约束在一个有限的、确定的范围里,使我们的社会稳定地实现现代化。
二. 礼仪影响
(一)礼仪的性质
礼仪是人们通过程式化言行交流某种信息,以求得生存环境的秩序化、消除对环境的陌生感、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的行为类型。礼仪还可以看作社会交易中实施基本行为规则的技术性模式,看作行为文化必要的外包装。所谓“仁义道德,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等(《礼记》,曲礼上),也说明了礼仪的这种功能。一个人施礼时,必希望回报,即所谓礼尚往来,否则施礼会变得没有意义。在人际地位不平等时,礼尚往来仍是通行规则(假借礼仪而行贿属例外)。宗教中人对神施礼更是一套严格的行为规则,更反映了人们要求回报的虔诚心愿。从这个意义上说,礼仪是利己主义的文化包装。这种包装实在必要,它使社会关系有了温馨、和谐的外观。 我们可以进一步对礼仪作学分析。施礼包含有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恐惧。礼仪的程式化本身预示了人际交往(或人神交往)秩序化过程的开端,有助于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减轻恐惧感。所以,礼仪约束一般是自律性行为 。环境信息越不充分,人们越希望通过礼仪交流信息,礼仪对于降低不确定性的意义就越重要。礼仪能够过滤那些不确定性较强的信息,而加强确定性较强的信息。王权政治之下,百姓难以得到关于国王的信息,于是,百姓与国王通过礼仪进行交流,借此求得相互之间的认知。传统社会中人们关于某些规律的信息更为难得,如彼岸世界、自然灾变等,相关的礼仪便更加程式化,甚至转变为宗教。总之,礼仪的程式化程度或严格程度与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成正比。
人们的礼仪行为背后有严格的成本-效益分析,虽然这种分析可能不是自觉的。施礼需要付出成本,这种成本是人们为了降低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投资,其收益的现值会因人们的信息的完备程度的差异而受到不同评价,因此人们遵守礼仪的自律程度是不同的。施礼的成本一旦超过施礼的收益,礼仪便无法存在。如果一个人对“死后进入天堂”的预期收益评价为零,那么他无论如何不会去购买天主教会发售的“赎罪券”。从上看,使人们负担过重的礼仪很难有生命力,除非这种礼仪以人们对于相关信息的掌握极主完备为前提。所以愚昧常与复杂的;礼仪相联系。但一种礼仪一旦转变为节日,包含了娱乐或其它社会功能,其复杂形式就与愚昧无关了。
(二)礼仪对于社会稳定的意义
鉴于礼仪的上述性质,决定了礼仪有可能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如果抛开具有神秘性的宗教礼仪不说,一般的社会礼仪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正面的。这是因为功能良好的礼仪能够提高设置的认知程度,起到消除或减缓社会隔阂的作用,从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功能良好的社会礼仪必须有下述这样一些特点:一是礼仪的普遍性。礼仪在一个社会的普遍化,会产生全社会的合作性收益,即礼仪越是普遍化,才越能有效发挥降低不确定性的社会功能。礼仪的普遍化包含礼仪语言(符号)的统一化,否则人们无法借助礼仪达到相互认知的目的。二是礼仪的简单性。一般来说,礼仪越是简单,越有可能被人们普遍尊奉,其促进社会认知的功能也就越强,稳定社会的作用也就越大。礼仪的简单化降低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能够提高全社会的运行效率。除非有强烈的宗教感情支撑或某种外在压力存在,否则复杂的礼仪不可能长久流行于世。三是礼仪的非歧视性。一个社会应该有一些通行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礼仪,以便弱化社会成员相互认知的壁垒。反映社会阶层特征的礼仪不可能取消,但如果过分标志化,会成为导致社会分裂的条件。标志社会身份的礼仪会使其它社会阶层产生陌生感,造成相互之间的敌意。文化大革命曾经了一套崇拜毛泽东的复杂礼仪,如诵读语录、悬挂肖像,早请示、晚汇报等,这套礼仪不仅过于复杂,而且具有歧视性(阶级敌人不被允许施行某些礼仪),不仅没有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反而社会的分裂 。
通行于一个社会的礼仪能否具有上述三个特征,当然与社会的文化传统有关,但最终还是与社会的发展程度有关。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便揭示了社会基础条件与礼仪的关系。处于赤贫状态的人们不会尊奉礼仪。但在一般情况下,破坏传统礼仪常常是制度因素或意识形态因素的变化。在商品交易量低、条件落后的社会,通常缺乏礼仪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如果硬性推广某个阶层的礼仪或某种外来的礼仪,用以替代其它阶层的礼仪,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社会的分裂。如果一种被人们长久认可的礼仪具有宗教色彩,那么试图替代这种礼仪的社会风险就更大。本世纪60年代伊朗国王巴列维改革的失败,原因之一便是人们对礼仪改革的不认同。对传统礼仪的破坏意味着对既定秩序的瓦解,通常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三)礼仪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稳定的意义
既然礼仪与人与人以及人与的关系中的不确定性有关,那么社会礼仪是不可能消失的,因为不确定性不可能消除。但是,礼仪并非一成不变。礼仪的形式及其变迁有大致的可循,人为地干扰这种规律,往往会瓦解社会秩序,造成社会不稳定。从历史发展的总体看,礼仪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趋于简单,某些礼仪完全消失,某些礼仪约束被功利主义原则代替。 1. 传统社会通常是一个礼仪纷繁复杂的社会。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生存能力低下,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如战争、自然灾变、龙颜大怒等)对人们的现实利益影响很大,因此人们对避免不确定性所进行的风险投资的预期收益也很大,在其它投资手段不具备的情况下,礼仪便成为合适的手段,并且与较大的预期收益相对称,礼仪的成本也可以很高昂。这样,礼仪的纷繁复杂就不难理解了。复杂的礼仪对维持传统社会的稳定是有好处的。在社会基础结构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瓦解传统社会的礼仪,新的礼仪并不能形成,社会可能出现礼仪的空白,对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举例来说,在传统社会中,由于自由恋爱受到很大限制,使婚姻生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于是,关于婚姻的礼仪也十分复杂;复杂的婚姻礼仪起到一种广而告之的作用,借以向社区宣告不可侵犯的性权利关系,达到稳定婚后生活的目的;婚姻礼仪起到了一种界定性权利的作用。否定这种婚姻礼仪可能导致传统社会性道德的紊乱,导致社会不稳定。
2. 某些礼仪会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而消失。传统社会中,某些代价高昂的礼仪与人们对某些或社会现象的极端无知有关。无知产生恐惧幻觉;恐惧越大,实施礼仪的代价就会越大。“在非洲和近东,割阴常与这样的信念有关,即妇女的自然性欲过于旺盛以致若要保持男性统治和家庭的稳定,就必须对妇女进行文化上的阻抑。因此,这种手术就是对妇女性欲和潜能基本恐惧的一部分”(墨菲,1986年,231页 )。随着人们的进步人们会完全否定这类礼仪的社会功利作用,这类礼仪便随之消失。如果一个社会的极不平衡,过时的礼仪在有些地区存在,在另一些地区则可能消失,由此产生的礼仪规则的差异,也可能导致社会冲突。 3. 随着社会的进步,功利主义的原则会替代某些礼仪。礼仪作为避免未来不确定性的长期投入行为,其存在的根据有些可能曾经是真实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有些根据会消失。此时礼仪约束便会向纯粹功利约束转变,使功利主义失去传统的文化包装。例如人际交往中真实的礼让行为(不是已经符号化的礼貌行为,如人“你吃了没有”的问候)一般与物质匮乏联系在一起;随着物质产品的丰富,个人不再有基本生活必需品匮乏之虞,以礼让行为进行长期投入以换得对方回报不再有意义,礼让行为便会消失。此时这方面的交易便会由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原则支配。发达国家已经较为普遍的夫妻分立帐户、家庭成员间相互雇佣等现象,可以由此得到解释。这种变化提高了人们的福利水平,因为人们不再为这种礼仪承担风险成本,即不再为礼让是否得到回报而担忧。只要传统社会转入社会,在新的功利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礼仪替代,从总体上看对社会稳定是有好处的,因为功利主义下的契约是靠来保障的,不象礼仪那样是靠道德来保障的,前者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更加可靠。
三. 道德影响
(一)道德的本质
一般来说,道德是依靠羞耻感来维持的人们的自律性行为规则;在传统社会,宗法关系也是维持道德的基本力量。道德和法律在社会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一些现代国家通过法律把传统道德固定下来,借以更有效地约束人们的行为,例如新加坡的法律对随地吐痰、男子留长发给予惩罚,便是用法律约束替代了道德约束。但一般来说,一种行为如果可以用道德来制约,引入法律就没有必要,否则会增大社会秩序化的成本。道德的社会功能在于降低人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节约社会交易成本。
道德发挥行为约束作用的重要条件是人们社会价值观的一致。价值观有差别,人们就不会有统一的羞耻心,统一的道德规则也就难以形成。例如,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有的人认可家庭雇佣关系,而有的人不认可,不存在统一的羞耻心,那么相关道德的约束力也就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一般来说,一个停滞的传统社会会有固定的价值观,因而有较统一的羞耻心,道德对人们的行为有较强的约束力。
(二)道德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
道德对于一个传统社会能够较好地发挥稳定作用。传统社会通常是由许多血亲共同体构成的。在血亲共同体内部,血亲关系是人们相互认知的重要条件;生产技能靠口授亲传来实现,个体之间的生产技能差别很小,所以人际关系中的信息交流充分,不确定性程度低,个人实施机会主义的风险收益较小,具有流氓性格的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与共同体的传统道德规则反差较大,容易识别;违规行为会使当事人名誉扫地,承受羞愧的惩罚(贝克尔,1981,277页 )。在传统社会,人们离开共同体出走的障碍非常巨大羞愧的惩罚无异于死刑宣判。因此,传统社会道德自律压力必然很大;道德成为稳定社会的主要力量。这种社会对强制性的正式的行为规则没有需求强度,而且正式规则的供应成本较高,非正式的道德自律的实施成本较低,所以道德是传统社会中最有效、最合理的行为规则。
在现代社会,道德所能发挥的稳定社会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传统社会的瓦解伴随血亲共同体解体,社会的不确定性程度增大,机会主义的潜在收益随之增大。因为人们可以较容易地通过“逃亡”的办法来避开羞愧的惩罚,道德自律的作用必然降低。此种过程的反复,也削弱了羞愧在共同体内部的作用,甚至修改了道德的标准。例如,是否有婚外情曾经是西方一个家能否当选的重要条件,但近几年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的选民已开始容忍有婚外情的竞选者(性骚扰行为仍属例外)。社会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人们的道德自律性就越低,道德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就越弱。但是,机会主义行为会加剧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大交易成本,人们在反复交易中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必然要寻找新的交易规则,以填补道德自律失去后留下的行为约束机制的空缺。于是产生了对法律的需求。充当法律供应者的是现代国家;交易技术的进步使现代国家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制定和实施法律,法律遂得以成为现代社会主要的行为约束力量。上述观点并不否定道德约束在现代社会仍具有一定的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现代社会中所消失的是血亲共同体,并非任何共同体;因职业、兴趣等结成的共同体还会存在,家庭还存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难以用法律来约束,或者说法律监督和实施的成本很高,这样便给道德调节留下了发挥作用的余地。
在社会转变时期,特别是由自给自足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传统道德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会显得力不从心。血亲共同体瓦解,人口流动性增大,羞耻心在社会控制方面的功能大大减弱,人们违反道德后受惩罚的可能性降低,全社会人们的行为规则便会发生紊乱。社会对新的行为规则的需要与新的行为规则的建立通常有一个时间差。这是因为新规则的建立不仅要付出直接成本,人们适应新的规则还是一个长时间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主要不是靠政府灌输,而是靠反复进行的社会交易过程所产生的利益得失的估价给人们记忆的刺激;也就是说,反复的违规行为会造成反复的利益损失,才会教会人们遵守新的规则。观察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化过程,可以看到这一时间差无一例外地都会存在。社会转变时期人们常发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慨叹,原由大抵如此。
在乡村地区,应该看到传统道德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局限性。乡村社会的传统道德一般只适用于村社共同体内部,较少推及与其它共同体的关系,更少推及与政府的关系。俄国社会学家米罗诺夫这样描述俄国村社的道德状况:“农民认为,蒙骗邻居或家长是不道德的,但为了农民的利益而蒙骗政府官员或地主(俄国地主与地主不同,前者往往不是村社共同体的成员----笔者注)是应该受到奖励的有道德的行为。偷窃邻居的东西,破坏邻里之间划分份地的田界,未经允许而在村社的树林中砍柴等,均是不道德的;但在地主田园中采摘水果,在地主的树林中砍柴,或多耕了地主的土地则不是不道德的行为,不应受到指责”(米罗诺夫,1988,52页)。米罗诺夫认为农民对待外人使用了另一种道德标准,其实,这种情形不能说明传统农民有双重的道德标准,只说明他们没有认同共同体以外的社会;他们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是偶然的、不确定的,道德损害对他们眼前或长远的利益没有足够的影响。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道德对人的约束力就越低。这种情形还说明,道德损害对于集体行动是没有制约力的,因为在集体的共同行动中,羞耻感的惩罚作用已不复存在。村社之间的械斗乃至相互凌辱对方的长者、妇女,民族之间的惨绝人寰的屠杀等,道德的制约无影无踪,其道理就在这里。米罗诺夫描述的情形在中国今天的社会也存在。铁路沿线的农民可以集体抢掠铁路财物,偏僻乡村的农民可以从人贩子手里买妇女为妻,而政府予以干涉时,村民们往往采取一致对抗的态度。在社会转变时期,出现这种情形不应奇怪,因为道德的约束作用在确定性程度高的环境下才能充分发挥。
四. 经典文化与符号文化
(一)经典文化的内涵
经典文化或典籍文化是指在过去大多数时代由官方提倡并反映在历史典籍中的文化,这里特别指古代“圣人”所勉力传播的行为文化。世界主要文明国家在历史上遗留下了大量文化典籍,其中的一部分典籍由于官方或其它重要社会势力(如宗教)的推崇,对民族历史发生了较大影响。这些典籍的作者被尊为“圣人”,他们倡导的人类行为规则被当作(只是被当作,不一定实际上是)民族行为文化的代表。
笔者认为,我国学者在文化研究方面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关于民族的经典文化与实际的民族行为文化的关系问题。对这一关系不讨论清楚,关于文化问题的一切研究都可能走入歧途。多数文化问题的研究专家常把一个民族的经典文化看作民族的行为文化,把民族间经典文化的差异看作民族行为文化的差异,然而这一等式决没有普遍性。行为文化与经典文化之间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历史上的学者不一定将本民族的行为规则研究清楚,并将其真实地记录下来;历史上的家的艺术创造也不一定反映民族的真实情感和社会的本来面貌。学者们的作品难免渗透自己和自己所在阶层的价值观,甚至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其价值观的诠释。学者们不是圣人,他只愿意说出那些在他看来对他生前死后最有利的话;虽然某些学者对“真实”有特殊的偏好,但这仍不能保证他没有思想上的片面性,因为人的生活范围和知识积累的状况总是要限制人的眼界,学者们也不例外。所以,一个民族的经典文化,首先是一个符号文化系统,它是否反映民族的行为文化传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这个传统,是极不确定的。但是,学者们很难这样看问题,他们倾向于把民族的经典文化看作实际的民族的行为文化。这一认识误区产生的原因,除了相沿的历史研究不得不依靠文化典籍之外,还由于与人力资本积累相关的“学者行为”在起作用。学问是学者的看家本领;为抬高学者的地位,必要抬高学问的地位,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学者们一生为自己的学问而投资,日子越长,越有理由希望得到高额回报;同时靠新知识获得回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由于这种基本的学者行为,使学者们极易夸大自己所掌握的文化典籍的意义。例如,梁漱溟先生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别,并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便犯了以民族经典文化替代民族行为文化的错误。实际上,儒家经典的伦理本位,并不等于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任何一个民族在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时期都不可能是以伦理为本位的;而一切现代社会恐怕都是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在较稳定的传统农业社会的血亲共同体内部,才会有伦理本位的文化类型。对人类社会的实际文化类型作出简单概括,在理论研究上是危险的。
(二)经典文化对社会稳定的作用
尽管经典文化与民族的实际行为文化存在差异,但一种经典文化的存在仍会对民族发生影响,包括对民族社会的稳定发生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会改变民族历史的基本进程。
经典文化有教化统治者的作用。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许多文化典籍本来是作者为统治者而撰写的。孔子在《论语》中要求人们“正心、诚意、修身”,是为了更好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史记》、《资治通鉴》等典籍的作者也直言不讳为统治者服务的目的。欧洲历史也一样。公元一世纪欧洲大地家斯特拉波(前64-20)的巨著《地理》就是“为了有教养的家和军事家们写的。他的目的是为罗马行政长官和军事首领们提供情报文本而他的作品就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行政人员手册”(当然没有《论语》早。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1981年,49页)。经典文化对统治者的教化肯定会统治者的行为发生影响。以欧洲历史为例,欧洲历史上的统治者比较重视实证,这除了本第二章分析的原因之外,也与从古希腊哲人到培根的实证科学传统有关。这种传统注重对的研究,进而注重寻求社会的自然秩序,有利于建立一个结构稳定的法制社会。 经典文化也有教化人民的作用。这种教化作用与人民受的程度有关。人民受教育的程度高,经典文化的教化作用就强;反之,则弱。但是,宗教因素可以弱化这种相关性。与历史不同,欧洲中世纪人民几乎没有阅读能力,但宗教经典可以由传教士向人民传播,从而对人民的行为发生影响。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到基督教《圣经》包含有一种等级制思想,使欧洲人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也使欧洲社会在长时期内保持了一个较为稳固的等级社会。欧洲也有过农民起义,但其结果与中国不同;欧洲农民即使推翻了旧国王,也不会自己去作国王,他们要在贵族中寻找一个新国王。农民的这种行为不容易使社会结构因起义而发生重大变化,民族历史遗产的链条也不会轻易被打破。 由于历史的变迁,一种经典文化所包含的思想可能会变得与社会现实相冲突,这时,经典文化与新文化的冲突可能造成社会意识形态的分裂,从而对社会进步发生有害影响。若对这方面的历史作一番考察,可以发现,解决这方面的冲突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断然抛弃经典文化,一是使经典文化符号化。中国“五四”运动曾试图抛弃儒家经典文化,结果并不成功。更常见的是后一种办法。这种办法是继续沿用经典文化的语言符号,但改变其思想内容。例如,继续沿用儒家经典的“仁、义、礼、智、信”这样的语言符号,但抛弃它本来具有的宗法思想,而赋予其内容。实际历史过程大体上也正是如此。无疑,采用这种方式的社会交易成本较低。文化冲突反映社会利益冲突,从经典文化的内容上而不是从语言符号上瓦解旧的经典文化,可以使代表旧文化的社会阶层在精神上保持某种尊严,以减弱其反抗的冲动。如果一个国家政权想要抛弃一种旧的经典文化,采用这种釜底抽薪之举,也会降低社会分裂的可能性。在笔者看来,中国现在正进行着这样一个过程。 (三)符号文化及其对社会稳定影响 符号文化是具有某种历史继承性的、表征人类对自身与环境认知水平的特殊信息系统,具体表现为文字、有声语言、形体语言和各种形式等。符号文化不同于知识,它只是知识的形式外观;人类社会的制度、价值准则和道德信仰等行为文化通过符号文化来表达。符号文化的功能在于给人们提供社会交流的工具,起到降低社会交易费用,从而降低社会生活不确定性的作用。一个团体,一个社会群落,乃至一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有自己的统一的符号文化,人们借此达成相互之间的认知,减轻陌生感和恐惧感,增强信任感,从而达到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的目的。符号文化越具有稳定性和统一性,其降低社会交易费用的功能就越强。 符号文化的上述特征,使其必然成为社会集团特别是暴力集团的领袖们的运作对象,以达到他们动员社会民众的目的。在人类争夺生存空间中,那些符号化的标志易于成为人们相互沟通的手段,这种沟通手段远较其他手段更为低廉,同意符号文化可能成为区别敌友的简单标准。所谓“人以群分”的界标,常常会是某种同一的符号文化形式。从历史上看,若有一定的条件,人群间在符号文化上的差异,常常引起相互间的敌意,甚至引起相互仇杀。一些暴力集团的领袖为了动员民众追随自己,也常常突出强调某一社会群体的某些符号文化特征,没有例外,这些符号文化特征在识别上必然具有简单性,其获取成本必然具有低廉性,否则会大大增加动员民众的成本。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有不少暴力集团用某种“主义”来动员或“武装”民众,似乎很有效果,但这只是一种假象。民众所能接受的只是“主义”的符号化特征,真正对“主义”的内容是很难理解的,更谈不上去接受它。这一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样一种现象:真正的理论家常常当不了暴力集团的领袖;领袖只能是那些深谙民情的人;因为在动员民众中起作用的是一些已经符号化了的学说内容,而不是学说内容本身。 一般来说,符号文化的统一程度与稳定程度是由行为文化的相应特征决定的,但二者之间也可以发生背离;符号文化一旦形成,便不容易发生改变;如果发生改变,通常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渗透有关。从符号文化变迁的历史看,为了使行为文化与符号文化保持一致,当行为文化发生变化后,那些聪明的社会控制者常常不是去改变符号系统本身,而是去改变对符号的诠释。从节省社会交易费用的角度看,这种作法具有性和合理性,因为从历史的经验看,改变符号系统的代价要大得多;改变对符号的诠释就不同了,因为民众对符号的历史内容本来不大关心,也关心不了。历史上不乏这种偷梁换柱的例证。例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天主教罗马教会就不断改变对教义的解释,而不去改变教义的文字符号。分析到这里,细心的人会想到,类似的进程正在今天的中国出现。顺便指出,符号文化变迁的这种特征,会产生符号文化的独立性外观,进而产生文化变迁的迷雾,这着实使那些不谙熟经济性方法的文化研究者困惑不已,并会引导他们的研究走入歧途。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理:一个社会的官方,也可以通过符号文化的运作来影响社会的稳定;或者说,好的运作会有助于社会稳定,而坏的运作则会不利于社会稳定。例如,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淡化民族差异会有助于社会稳定;而突出民族差异则不利于社会稳定。在一个事实上不平等的社会,强调平等观念会不利于社会稳定,而强调竞争则有利于社会稳定。在我国过去官方宣传的符号系统中,“主人”这一符号得到突出强调,其结果对我国的权威结构影响很大;有效率的企业权威结构要求厂长经理对工人的不可动摇的支配地位,但我国工人对“主人”这一符号有广泛认知,并影响着工人与厂长经理之间的博弈关系,使企业无法形成那种应有的稳固的权威结构。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企业的低效率,还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例如,据报道,在我国一些合资企业中,工人与国外老板对抗时,使用了诸如“做主人”、“反剥削”一类口号。在适当条件下,“主人”这一类符号如果能在政治关系中发挥社会团体的认知作用,才有利于社会稳定。
五. 宗法组织
(一)宗法关系的本质
宗族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由同一祖先繁衍下来的人群,通常由共同财产和婚丧庆吊联系在一起,并且居住在同一村庄。宗法关系便是基于宗族血统而产生的地域性极强的社会关系。在宗法关系中,男性长辈容易成为核心,也往往是宗族内部纠纷的裁决者和对外抗争的领袖人物。宗法关系下的行为规则,完全是儒家经典提倡的“仁、义、忠、孝、悌”这一套道德伦理。宗法关系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关系,也就是说,宗法关系所包容的人的行为规则是传统社会所具有的普遍的行为规则。传统社会的这种结构具有明显的合理性。本第二章已经指出,人的社会活动实质上是交易行为,人们在交易中总是在寻求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安排;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就是最合理的制度安排。在传统乡村社会,虽然交易内容简单,交易范围狭小,但交易双方仍然要建立信任关系,取得相互之间的认同。建立认同关系时最廉价、最确定的信息莫过于血缘关系方面的信息;正常情况下,乡村中的任何一个人总是靠汲取家庭、家族的各种营养成长,家族方面的信息要比乡村社会的其它信息对他有更高的刺激强度,所以家族成员之间更容易取得认同。家族社会还了一些制度,来巩固宗法关系,这些制度包括续修族谱,建立宗祠,定期祭拜祖宗,表彰优秀宗族成员,宗族内部互助等等。
在乡村社会封闭程度很高的情况下,宗族关系会成为乡村社会最重要的关系,成为支撑乡村伦理道德的基础社会结构;乡村宗教力量也通常依附于宗法关系,甚至国家政权对乡村的统治也要与宗法关系相结合。无疑,一切能够打破乡村社会封闭性的因素,将改变乡村社会的交易成本函数,从而引发乡村社会制度结构的改变,导致宗法力量地位的下降,甚至使其瓦解。从社会学家对农村研究的资料看,本世纪初,中国农村中的宗法统治已经开始瓦解;在一些乡村地区,宗法关系虽然还存在,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杜赞奇对40年代前华北乡村社会的研究,把华北村庄的权威结构分为两种类型,分别为宗族型和宗教型;在宗教型村庄中,宗法力量统治乡村已大大减弱(杜赞奇,102-103页)。概言之,宗法关系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关系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
(二)宗法关系与农村社会的稳定
在限定条件下,即在较为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本身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封闭性越强,乡村社会中的族长、中人和道德化身相统一的可能性越大。宗法关系能为活动提供一个稳定机制。家族成员在生活告急时,往往求助于同族成员;在承租土地及钱财借贷中,往往是同族成员充当中人;一无所有的同族成员也可以从宗族中获得帮助以求生存。从传统乡村社会的研究资料中还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外界因素干扰,尤其是没有官府力量的介入,宗族之间的冲突通常也可以通过家族领袖之间的谈判确定妥协的条件。在乡村阶级冲突中,宗族力量也可以协调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产生出相对有利于佃农的结果。“如果一个地主(不论其属于哪一个宗族)向佃农提出高于常规的地租,则佃农所在的一族会联合起来拒绝租种该地主的土地。例如,在1939年,当物价下跌时,(寺北柴村)宗族联合其成员,成功地迫使地主降低货币地租”(《华北惯行调查》,第三卷,97-98页)。
在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关系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的基础。封建国家一般是为了取得税赋而对乡村进行控制,为此要从调查、确定纳税人口的目的出发,把乡村人口编为不同层次的组织单位;官府为了方便,通常以十进制和居住范围编制单位,但贯彻下去却不得不适应宗族的户口状况。例如,清朝实行的保甲制的“牌”是以十户为单位,但到了乡村却可能是同一宗族的十几户人家,且不一定居住在一起。在较为封闭的乡村社会,官府任命或认可的保甲长,也一般是宗族领袖。根据片山冈的研究,在珠江三角洲,相当于里甲的图甲制划分与宗族中的宗、门划分完全重合,国家通过宗族组织征收赋税(片山冈,1982年,《清时珠江三角洲的图甲制:田赋、户籍与宗族》,《东洋学报》,第63卷,第3-4期27页)。这种制度安排利用了既有的信息传播渠道和社会认同关系,显然可以降低政治活动的交易成本。在宗法力量尚强大的时候,国家政权要完全替代宗法统治,可能是愚蠢之行。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推行5家为邻、5邻为闾的“闾邻制”,然而,“由于横征暴敛和强行专制,国民政府建立以户为统治基础的努力收效甚微,而且,由于切断宗族与乡村政体的纽带,使新的村政权失去旧有的文化中的合法性,同时,国家政权也堵塞了一条传达其旨意予乡村社会的渠道”(杜赞奇,101页)。
乡村社会的宗族械斗常为人们所关注。宗族械斗肯定会破坏乡村社会的安定,导致社会的局部不稳定,但是,宗族械斗本身一般不会导致全社会的混乱;械斗到极端时的调停常常要借助官府的力量。宗族械斗不可能是传统乡村社会经常性的现象,否则,传统社会不可能延续几千年。只有在乡村宗法关系受到干扰,旧的利益均衡被打破时,宗族械斗才可能发生。社会的利益关系不断发生被动,利益冲突并不常以械斗方式来解决,而宗族冲突为什么会导致械斗?这是一个有趣且应当回答的问题。 在封闭的乡村社会中,交易内容简单,利益关系也简单;道德认同可以调整利益关系,但道德认同缺乏强制力量;而根据本第二章的分析,一个社会的强制力或暴力的不可缺少的。暴力的实施是需要成本的,实施秩序化的暴力的成本更大。在前现代化社会时期,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实施秩序化暴力的成本大到足以让国家政权放弃这种努力。国家政权的暴力主要是对付大的社会动乱和抵御外国侵略。这样,替代国家暴力的是宗族的暴力。在一般情况下,宗族暴力只是一种潜在压力,可谓之暴力潜力。在宗族均衡关系的背后,便存在暴力潜力这个变量。所谓利益均衡关系的破坏,意味着乡村社会的某一宗族提出了重新界定宗族间财产权利边界的要求,也意味着向对方的暴力潜力挑战。如果这种挑战导致用谈判方式建立新的均衡,械斗便可避免,否则就会产生械斗。如果没有官府力量的介入,或介入不力,宗族械斗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尤其在械斗宗族双方人数接近的情况下更会如此。 宗族间利益关系发生变化,并引起宗族械斗的原因,一是宗族人口数量发生变化,直接导致宗族暴力潜力的均衡受到破坏;二是商品关系的扩大,新的获利机会出现,使宗族间的实力的对比发生变化;三是官府力量的介入,造成乡村社会生活的新的不确定性,使宗族成员的行为预期发生变化。在漫长的传统社会,这三种变化常常周期性出现,导致乡村社会的周期性不稳定。近代中国社会的宗法关系逐步瓦解,这三方面的因素持续存在,更使中国乡村社会进入长久的不稳定时期。
费尔巴哈,1845 《宗教的本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初德国》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Yang,C.K.1967:《中国社会之宗教》,伯克利,加州,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年,北京,
《中华民国法规大全》,1936年,第一卷,上海,1166页)。
《资治通鉴》,卷五十八
《中国惯行调查》,1981年,东京,
《礼记》,《四书五经》,中国书店版。
罗伯特.F.墨菲1986年《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论语》,《诸子集成》,上海书店版。
加里.S.贝克尔1981年《家庭经济分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米罗诺夫,1984年,《学家和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8年。
杨懋春,1945年,《中国的一个村庄:山东省台头村》,纽约。
杜赞奇,1988年,《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版,1995年。
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1981年《地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梁漱溟,1949,《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樊纲,1994年,《中华文化、理性化与经济发展》,《经济文论》,三联书店,1995年版。
C. 阿尔塔莫诺夫,1954,《伏尔泰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
上一篇:当前农业进一步发展面临的制度瓶颈
下一篇:新世纪中国农村改革:反思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