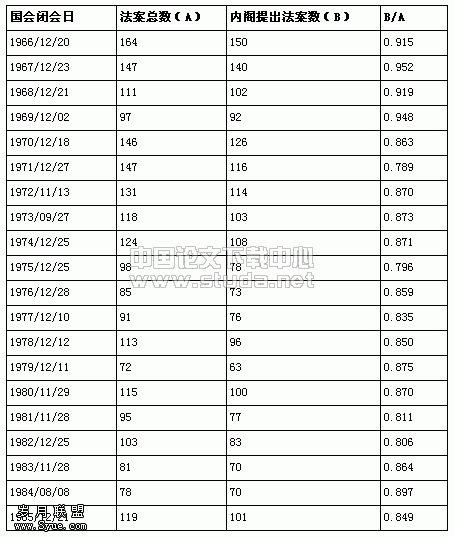谦抑、民主、责任与法治的关系探讨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4-09-22
美国民主理论家萨托利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观混乱的时代,虽然我们都声称喜欢民主,但并不知道什么是民主。[14]P7萨托利的这一论断也适用于立法民主问题。尽管民主已成为立法领域一个牢不可破的信条,但何谓立法民主仍缺乏一种清晰而有说服力的阐释。借鉴萨托利关于参与式民主的分类,[14]P119我们可把立法民主分为直接民主立法、全民公决式立法和代议制民主立法三种类型。
所谓直接民主立法,是指所有公民组成公民大会直接讨论、表决和通过法案。这种直接民主立法模式仅仅存在于古希腊雅典城邦那样的微型国家。这种微型国家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人民很容易集会,每个公民都能很容易认识所有其他的公民;[15]P84-85二是每个公民与他们的国家休戚相关,甚至可以说是生死与共。[14]P283-284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所有公民才既有积极性也有可能性,定期或不定期地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和制定法律。所以,这种直接民主立法模式无法为地域更广、人口更多的现代国家所复制。更何况,即使在古代的雅典城邦,直接民主立法也并非是真正的全民参与立法,因为享有立法权的公民不过城邦人口中的少数,广大妇女、奴隶和外来移民都不享有立法权。
全民公决式立法是指所有公民直接投票表决和通过法案。学者们一般把全民公决式立法视作是直接民主立法,但全民公决式立法其实与古代的直接民主立法有明显的区别。从实际操作形式来看,全民公决一般是各个地方的公民分别在当地设立的投票点对法案进行投票。因此,它失去了古代直接民主立法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即所有公民聚集在一起面对面地就法案直接进行讨论和辩论,然后基于深思熟虑的决定对法案进行投票表决。用萨托利的话来说,它是孤立的、无关联的个人的直接民主,而不是相互作用的参与者的直接民主。[14]P120当然,和代议制民主立法相比,全民公决式立法在现代国家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直接民主立法的理想。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立法模式称为现代版的直接民主立法。
尽管全民公决式立法能够更直接地表达了全体公民的立法选择,但并没有因此而成为现代民主国家的主要立法模式,只有少数国家对宪法或某些重要的法律采用这种立法制度。究其原因,乃在于全民公决式立法在现实操作和运行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和困境。其中,最突出的两个障碍性因素是立法过程的经济成本和普通公民的立法能力。全民公决式立法的经济成本包括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两方面。前者是国家组织公民投票和监督投票过程的人力物力成本,如设立投票点、监票、计票等方面的成本。后者是公民到投票点参加投票的时间和经济成本。立法过程的经济成本是随着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的增加而不断增长的,因此大国很少采用全民公决的立法形式。普通公民的立法能力是制约全民公决式立法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很多民主理论家都强调,民主的实际效果受到普通公民的知识和能力的制约。萨托利认为,随着政治事务的越来越复杂化和专业化,公民表决式民主会可悲地迅速撞在无认知能力的暗礁上沉没。[14]P129戴维·沃克认为,民主最主要的缺陷在于绝大多数公民没有能力理解包含在现代管理中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中的许多十分困难和复杂的问题。[16]P252立法民主对公民素质和能力的要求比其他方面的民主的要求高得多。如果相当多的公民不能理解法律草案的内容,甚至都不识字,对立法进行全民公决只会流于形式,不能说这种公决会真实地反映出全体公民的意志。相比较而言,全民投票选总统相对简单得多。一个人即使不识字,也可以根据传媒所提供的某些信息,大致了解总统候选人的高下优劣,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和选择。但是,如果你连法律的内容都不理解,就很难对法律的好坏做出独立的判断。而且,随着法律越来越专业化,不要说不识字的公民,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可能也很难充分理解法律的内容,实质性地行使立法表决权。
正是出于对上述因素的考虑,现代各国一般都采取代议制或代表制这种间接民主立法模式。所谓代议制民主立法,是指由民选的议员组成立法机构,代表全体国民行使立法权。代议制民主立法能够消除全民直接立法的诸多问题。例如,议员作为专职立法人员,在法律专家和其他专家的辅佐与协助下,一般都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处理专业性很强的立法事务。但是,代议制民主立法本身也有其明显的弊端。首先,选民虽然有选举议员的权利,但无法直接控制议员的立法行为,无法确保议员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立法。按照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和哈蒙·齐格勒的说法:“选举使民众有权选择公职人员,但不能左右公共决策。”[17]P213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现代议会政治是政党政治。议员分属于不同的政党,议员的当选往往取决于所属的政党及相应的利益集团的支持。议员当选后必须听命于议会内党团和议会外利益集团,因此议会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党立法或利益集团立法,政党或利益集团的利益往往凌驾于公众的利益之上。[18]P218-219为了克服这些弊端,现代各国在代议制民主立法之外都采取了某些直接民主立法的因素,如立法听证会、立法座谈会。
中国的立法者发明了一个很好的词汇,即“开门立法”,来概括这种意义上的直接民主立法。由于各国间接民主立法的模式大体上相同,因而各国立法的民主程度主要取决于开门立法的程度和效果。对于我国的立法来说,立法的民主化程度也体现为开门立法的程度和效果。因此,推进立法的民主化实际上就是深入推进开门立法工作,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参与立法,让人民群众的意见更多地反映到立法中。我们已在立法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开门立法的形式和途径很多:(1)问卷调查制度,即就是否进行某项立法、立法中的某些重要条款设计出若干问题,以问卷的形式在网络或报纸上公布出来或直接发给一定范围的公众,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2)意见征集制度,即通过网络或报纸等传媒将法律法规草案全文向社会公布,广泛征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3)立法听证会制度,即举行立法听证会,就有关立法问题直接听取公众和有关方面意见;(4)立法调研会制度,即立法者到有关地方、单位和部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听取有关人员的意见;(5)专家论证会制度,即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就立法中的专业性问题进行研究论证。
不过,开门立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难的原因有的时候并不在于立法机关主观上不想进行开门立法,而是开门立法像前面所提到的全民公决式立法一样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一是开门立法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基础的。在许多国家的议会,不仅整个议会有一支庞大的立法工作队伍,而且议员个人也有自己的立法助理。这既保证议员个人能够搜集和处理社会各方面对立法的意见和建议,也保证议会有足够的人手组织各种立法听证会、论证会。而我国立法机关、特别是地方立法机关都普遍面临着立法工作人员太少的问题。如果每部法律法规都要组织多次民意征集、调研会、论证会、听证会,现有的人手肯定不够。所以,有的学者建议人大、特别是地方人大要建立立法助理制度。②二是,开门立法是以公民具有较强的立法参与能力和较高的立法参与热情为基础的。立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法律法规草案公开了,但没有征集到几条真正有价值的意见,听证会和调研会召开了,但没有听到几句有见地的话。这样,即使立法机关有行民主立法之心,也难以产生民主立法之效。更为普遍的情况是,普通公民缺乏立法参与的热情,他们或者是认为立法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或者是认为自己发表意见不会真正影响立法。在西方国家,各种利益集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动机在参与议会立法方面十分积极,而且它们都雇佣一大批律师专门研究立法,因此也具有很强的立法参与能力,这样就解决立法参与能力与热情的问题,但这种民主立法的模式容易产生前述的利益集团操控立法的问题。我们不能学习这种模式,必须培养中国公民的立法参与能力,调动中国公民的立法参与热情。
四、责任理念
有权力必有责任,权力与责任相统一,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行政权和司法权是这样,立法权更应当是这样。从影响的范围来看,立法权的行使往往会影响到不特定的成千上万人的利益,而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行使一般只影响几个特定的当事人的利益。从影响的时间来看,一次不公正的立法行为会产生持久的恶劣效果,引发出千百次不公正的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因此,如果行政主体和司法主体要对其错误的、违法的行为承担责任,立法主体更应当对其错误的、不公正的立法行为承担责任。这里所说的责任是指法律责任,而非政治责任或道义责任。立法主体承担道义责任是一个自然事实。特别是在英国、美国等国家,许多法案通过后以提案人的名字命名,这就使得提案人对其法案要永远承担道义责任。法案的声誉将直接影响提案人的声誉。一部声名狼藉的法案,如美国的麦卡锡法,可能会使提案人遗臭万年。麦卡锡法是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共法案,因由美国联邦参议员麦卡锡提出而得此名。而一部功效卓著的法案,如美国的谢尔曼法,则使提案人名垂千古。谢尔曼法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的反垄断法案,因由美国联邦参议员谢尔曼提出而得此名。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立法主体也不得不对其立法承担政治责任。这种政治责任主要表现为各种政治力量对立法主体所做出的负面评价和不利反应。最典型的政治责任是选民的选票制裁,即选民不再投票支持那些提出了糟糕法案的议会党团或议员。
立法主体是否应对其立法行为应负法律责任,一直是一个引发激烈争论的问题。传统的政治法律理论一般都否定立法责任的存在。③以传统的主权理论为例,无论是按照博丹的君主主权理论,还是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都认为主权者不存在承担立法责任的问题。博丹把主权定义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19]P82按照这个定义,作为主权者的君主不存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包括立法责任)的问题。在卢梭看来,法律就是人民(主权者)的公意的体现。这种公意既不存在错误的问题,也不存在不公正的问题。“无须问法律是否会不公正,因为没有人会对自己本人不公正”。[20]P47这样,卢梭就排除了因立法不公正或错误而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不过,近代思想家所说的那种不受法律约束、而且永远不可能犯错误的主权者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假定,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退一步说,即使把各个国家的民意代表机关勉强视作是主权者,豁免其立法责任,也仍然存在着其他立法主体是否承担立法责任的问题。事实上,立法权从民意代表机关向行政机关的大规模转移,行政立法在空间上与数量上大肆扩张和膨胀,已成为现代立法场域的一道有目共睹的景象。由于行政立法——特别是地方行政立法一般都缺乏严格的程序和有效的监督,容易发生违反上位法、怠于行使立法职权、乃至侵犯人民权利等立法乱象。④在中国的立法实践中,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各种乱象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密切关注。立法责任制度的缺失被认为是这些乱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也被认为是立法法的重大缺陷。周旺生先生把立法责任不清视为中国立法的一大弊病:“无论立法主体或立法人员在立法方面如何不尽职守,应当立的法不能及时立,应当修改或应当废止的法不能及时修改或废止,都无人承担责任,也无人追究责任。”[21]P10他认为缺乏立法责任制度是立法法的一大缺陷:“立法法拒绝设置法律责任,使中国的立法工作成为随便怎么做、做好做坏都无所谓的一项不存在责任、不需要责任的工作。”[21]P18基于相同的考虑,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立法主体应对立法行为负法律责任,特别是行政立法主体应对行政立法行为负法律责任。
当然,我们应当承认,与行政、民事、刑事等法律责任相比,立法责任在制度设计和操作上确实面临着更多棘手的难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有四个:
一是立法责任的承担主体问题,即哪些立法主体应承担立法责任。由于各个国家的议员或代表一般都被赋予职务行为免责的权利,这使追究议员或代表个人的立法责任已成为不可能。很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都规定,议员在议会上的发言、辩论、投票等活动不受法律追究。我国《代表法》第31条明确规定,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这一规定实际上排除了人大代表的立法责任。因此,对于议会或权力机关的立法而言,立法责任的承担主体只可能是议会或权力机关以及向它提出法案的其他国家机关;对于行政立法主体的立法而言,行政立法机构和个人均有可能成为立法责任的承担主体。
二是立法责任的承担范围问题,即哪些立法行为应承担法律责任。对立法责任承担范围的设定,既不能过于广泛和随意,以至于立法主体在立法上畏首畏尾,甚至不敢立法;也不能过于狭窄和严格,导致法律责任形同虚设,事实上很难追究立法主体的责任。借鉴国外的规定和判例,我国立法责任的设定应主要限于四种情形:违反宪法规定的立法行为;明显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立法行为;有受贿、徇私舞弊等立法腐败行为;严重损害公民正当权益的立法行为。其中,第四种情形中的“立法行为”,既包括立法作为,也包括立法不作为。立法不作为又包括未及时制定新法律和未及时修改或废除旧法律这两种情形。2001年日本政府因未及时废除强制隔离麻风病人的“隔离法案”而向所有麻风病人支付赔偿金的案件,就属于立法不作为的立法责任。
三是立法责任的承担形式问题,即立法主体应承担什么形式的法律责任。与上述承担立法责任的情形相适应,立法主体主要承担三类法律责任:第一,宪法责任。当立法行为违反宪法或宪法性法律的规定时,应依宪法或宪法性法律规定承担宪法责任。立法的宪法责任的具体形式包括:罢免行政立法机构的负责人;立法人员引咎辞职;撤销同宪法或上位法抵触的立法或宣布其无效。第二,刑事责任。当国家工作人员在参与立法过程中有受贿、徇私舞弊等立法腐败行为时,应当承担刑事法律责任。当然,目前我国刑法并没有把立法腐败行为纳入犯罪的范畴。如何界定立法腐败行为,哪些立法腐败行为应确定为犯罪,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⑤第三,赔偿责任。当立法行为严重损害公民正当权益时,立法机构应当向受害者进行赔偿。立法赔偿责任属于国家赔偿的一种形式,可纳入到国家赔偿体系中。有不少学者指出,我国目前的国家赔偿只限于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尚未承认立法赔偿,因此建议国家赔偿法确立立法赔偿制度。[22]
四是立法责任的认定程序问题。显然,不同的立法责任适用不同的认定和追究程序。在我国,立法的违宪责任主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认定和追究,但目前我国尚有待建立认定和追究违宪责任的法律程序。参与立法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法律责任的认定和追究应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由人民检察院侦查和起诉,由人民法院审理和做出判决。立法赔偿的程序应由国家赔偿法加以明确规定。立法赔偿的请求既可以向赔偿义务机关直接提出,也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提出。
五、法治理念
尽管许多学者都提到过立法的法治理念或原则,但很少有人充分地意识到在立法领域实现法治有多么地困难。毫不夸张地说,立法的法治是所有的政治和社会领域里最难实现的法治。这是因为,在现代政治体制下,特别是在制定法的体制下,法治之法大都来源于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如果说在其他领域中制定法律的机关与执行法律的机关是分开的话,那么在立法领域中制定法律的机关与执行法律的机关就是同一个机关。⑥因此,在其他领域,法治意味着立法者给他人立法,立法者立法约束他人。而在立法领域,法治却变成了立法者自己给自己立法,自己立法束缚自己。毫无疑问,前一种法治实现更容易,而后一种法治实现则更难。立法法治的实现首先要看立法者有没有勇气给自己立法束缚自己。从世界各国来看,除了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有一部专门的《立法法》之外,国外境外几乎找不到直接称为“立法法”的法律。[23]如果要对这种现象作一种非善意的解读的话,哪个立法者愿意给自己的行为套上一副沉重的法律枷锁呢?不过,即使有一部称作“立法法”的法律,也不能说立法者的行为就一定有了法律的约束。关键是看立法法是否是对立法权力和立法活动进行了系统化的严格约束。从这方面看,我国立法法仍然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除了前述的缺少立法权限制和立法责任的规定之外,我国立法法在公民参与立法、立法监督等方面还有不令人满意之处。例如,在立法的违宪审查对象上,《立法法》第90条仅规定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而未把法律、军事法规、部门规章、军事规章等纳入违宪审查的范围。[24]作为立法法的制定者,全国人大不把它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纳入违宪审查范围,似有自己为自己解脱责任之嫌疑。
立法法治的实现更取决于立法者是否能够严格地服从立法规则。尽管约束和规范立法活动的规则很多,但是立法法治的最根本要求是“三不”原则,即不越权、不违反程序、不抵触。
不越权,是指立法主体必须在法定的立法权限范围立法,不得超越法定的立法权限。判断立法主体是否超越立法权限的标准有三个方面:一是根据宪法和法律所明文规定的立法权限判断立法主体是否越权。各个国家一般都由宪法和法律事先对各类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以保证立法权限的法定化。在我国,各类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目前大体上是比较明确的。除了宪法以外,规定各类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的法律主要有《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二是根据是否有上位立法主体的授权来判断立法主体是否越权。根据立法主体的立法权的来源,立法一般可以分为职权立法和授权立法。所谓职权立法,是指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所进行的立法,而授权立法是指依据上位立法主体的授权所进行的立法。如果有上位立法主体的明确授权,下位立法主体的立法行为就不能认定为越权。三是根据法的一般原理(法理)来判断立法主体是否越权。在某些情况下,立法主体虽然没有明显违背国家法律有关立法权限的规定,但依照法理也构成了越权立法。例如,法的一条基本原理是,下位法不得规定上位法的效力或适用的问题,只有上位法才可以规定下位法或同位法的适用问题。
不违反程序,是指立法主体不得违反法定的立法程序。在立法活动中,合理的立法程序是立法民主化、科学化、理性化的重要保障。我国目前在立法程序上主要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立法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有关立法程序的规定不完备,很难对立法主体的立法活动进行有效的约束。其次,即使就不完备的立法程序而言,违反立法程序的现象常有发生。特别在地方立法中,由于对违反程序的行为缺乏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嫌事先规定的立法程序繁琐,违反事先规定的立法程序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该提交专家咨询论证的,没有提交专家咨询论证的;该开听证会的,没有开听证会。违反事先规定的立法程序,虽不会直接造成重大的社会危害或损失,但无疑会影响最后的立法质量。因此,我国一方面应完善各种立法主体的立法程序,同时应设定违反立法程序的相应责任。
不抵触,是指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所有法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这一原则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全国法制的统一。不抵触原则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很复杂,也很有争议。立法抵触的情形多种多样。按照立法抵触发生的时间,可以把立法抵触分为自始发生的抵触和后来发生的抵触。自始发生的抵触是指下位法在制定之时就与上位法发生抵触;而后来发生的抵触是指因上位法的修改或上位法虽未修改、但对上位法的理解或解释发生变化而导致下位法与上位法发生冲突。后发生的抵触在地方立法中比较常见,这要求地方立法要随着中央立法的修改而修改。另外,按照立法抵触发生的形式,可以把立法抵触分为直接抵触和非直接抵触两种。所谓直接抵触,是指下位法直接与上位法的明文规定相抵触,例如,上位法明文规定禁止的行为,下位法却改为允许;上位法明文规定允许的行为,下位法却改为禁止。所谓非直接抵触,是指下位法虽未直接与上位法的明文规定相抵触,但与上位法的基本精神、原则和原理相抵触。从目前的立法情况看,直接抵触的情形越来越少,非直接抵触的情形更为常见。
注释:
①例如,周旺生先生从《立法法》的文本出发把立法原则概括为宪法、法治、民主、科学四项原则;高其才先生从现代立法的普遍规律出发提出了人本立法、客观立法、平衡立法、合法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全球视野等立法理念;刘武俊先生通过对主流立法观念的批判性检讨提出了质量至上、效益至上、以民为本、程序正义、人权保障等立法理念和意识;刘军平先生也在批判传统立法理念的诸多误区后提出了以人为本、立法有限、立法平衡、立法效益、立法透明、程序立法等六大新的立法理念。参见周旺生:《论中国立法原则的法律化、制度化》,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3期;高其才:《现代立法理念论》,载《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刘武俊:《中国立法主流观念检讨》,载《学术界》2001年第2期;刘军平:《中国法治进程中的立法理念刍论》,载《政法论丛》2005年第3期。
②参见秦前红、李元:《关于建立我国立法助理制度的探讨》,载《法学论坛》2004年第6期;毕可志:《论建立地方立法的立法助理制度》,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10期。
③关于立法责任的否定说,参见杨福忠:《立法责任引入我国宪政制度建设之思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6期;张勇:《论立法责任》,载《福建法学》2007年第3期。
④关于行政立法的违法表现,参见温晋峰:《行政立法责任略论》,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
⑤2008年发生的郭京毅案曾被媒体称为“中国立法腐败第一案”。郭京毅长期在商务部条法司工作。郭京毅因受贿被双规后,媒体曾报道,其受贿行为涉及有关外交并购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司法解释。但是,后来检方的指控和法院的判决并未提到他的立法腐败行为。
⑥尽管很多国家都把立法的违宪审查权赋予了普通法院、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等独立于立法机关的机构,但是这种做法只是把一部分立法监督权转移到了其他机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立法机关既制定立法规则又执行立法规则的局面。
上一篇:论我国法的名称设置的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