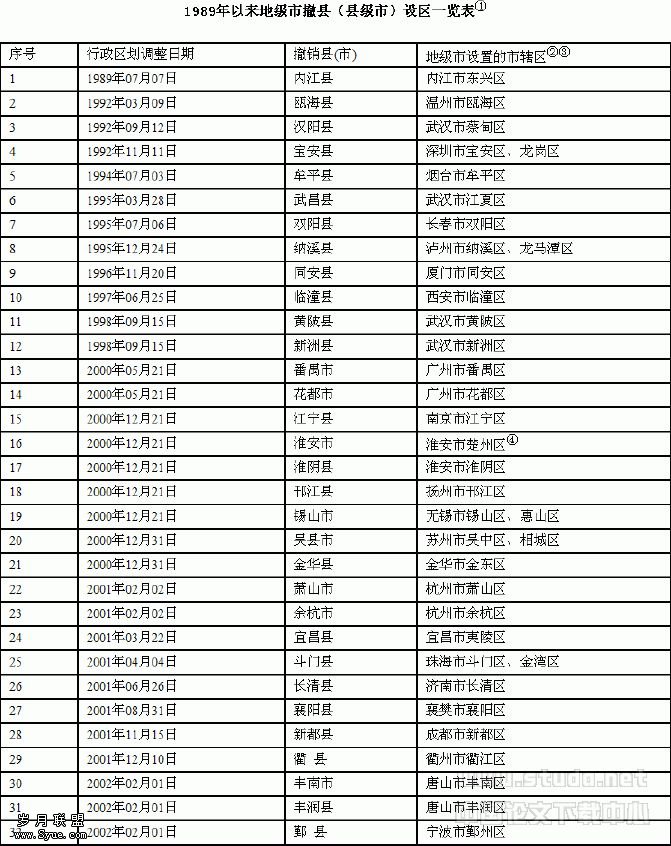让法治和自由在中国生根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0
19世纪中国的最后一年是以两件事为标志的:一是义和团事件;另一是北方大旱,“货卖人肉”,有几十万人活活饿死。两者既是19世纪中国的,又是20世纪中国之命运的隐喻。而这些都与有没有真正的法治和自由息息相关。
愚昧怎样成为灾难
义和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迷信、民族自大、排外、残忍、邪教等等的集中体现。这些文化垃圾过去有,现在也有,将来还会有。如果这只是少数公民的个人信念或信仰,它无碍大局,不会成灾。它所以成为震惊世界、祸国殃民的奇耻大辱,离不开两个重要条件:
1.、文化在国内外不能自由交流,在有形、无形的思想控制和思想蛊惑下,出现大面积的群体愚昧。
在义和团席卷华北之际,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符咒可令“刀枪不入”,屎尿等秽物可以破解和抵挡洋人的枪炮?为什么居然有那么多人把残杀“洋鬼子”、“二毛子”,拆毁铁路、电线、学堂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正义行动?国际法传入近60年后,北京又为什么会出现军民联手攻打使馆的事件?在一个号称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礼义之邦,以此等蠢行迎接20世纪,无疑是令中国人蒙羞的国耻。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又以新的形式重演了。以革命的名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知识越多越反动”,“破四旧”,“消灭帝修反”, 火烧英国代办处,使难以数计的知识阶层备受折磨乃至家破人亡……亵渎文明,无以复加。中国又一次蒙羞。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不应再揭的旧疮疤,请再看看两年前的景象:几个少不更事的文人炒作狭隘民族主义,狂呼“中国可以说不”!有多少人如醉如痴,让炒作者名利双收?!
窃以为这类现象所以在20世纪中国不绝如缕,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公民独立自主的自觉还没有成为多数国民的习惯。他们相信“大师兄”,相信“最高指示”,愿意盲从,而没有依靠自己的理性观察一切的自信。
二是盲目的民族自大。一个饱受欺凌的古老民族,急于恢复汉唐盛世,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却又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对世界现状缺乏基本的认识。于是,神仙和超人指点的各种捷径和发泄渠道,往往一夜之间掀动全国,趋之若骛。
2.民主制度尚未建立,独裁专制的权威犹在。
与鸦片战争年代不同,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有一大批朝野人士对中国和世界的现状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可是,他们无法左右局势。例如,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八个总督中只有一个摇摆观望,其他都反对依靠这些愚民的骗术“扶清灭洋”;还有一大批巡抚持同样的态度。在决定和还是战的关键时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徐用仪、袁昶、许景澄,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在京大臣也一再上疏或在慈禧和光绪皇帝面前直言,坚决反对向各国宣战。他们义正辞严地指出:“围攻使馆,实背公法。”“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国乎?”[1]可是,在专制制度下,独栽者不但听不进去这些常识,还把他们的脑袋砍掉!这样的专横,在一些有法治传统的西方国家,即使在中世纪也是不容许的。例如,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的第39条就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2]而在中国,时至19、20世纪之交,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为基础的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在慈禧一类宗法专制者的头脑中仍没有任何位置。这当然不是某些人的认识问题。认可专制权威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加上民间社会力量尚不足牵制这些专制统治者,使他们无法为所欲为;合理的民主制度结构也就难以建立了。
翻检20世纪中国史,义和团以降的各次大灾大难,几乎无一不与这个状况息息相关。如果有民主和法治,21条能通过吗?如果建立了以自由、法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全国公民可以在这样的制度下正常活动,从九一八到八年抗战的肯定会重写;后来的什么“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恐怕也不会发生。
贫困和天灾实质是人祸
改革开发20年,温饱尚未解决的人从两亿五千万降至两千六百万。这当然是一项重大成就。不过,如果用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50%以上为贫困)来衡量,中国的贫困人口肯定要大大超过这个官方数字,也许要超过十倍以上。[3]不能忽视平均达到“小康”背后,还有几亿贫困的中国人。从地区看,则三分之二以上江山总体上仍然十分贫困。假如加上日益受到重视的环境等因素去,问题就更加突出了。贫困是20世纪中国最严重而且尚未解决的问题之一。
请从亲身的见闻说起。小时候我很怕死尸,但偏偏耳闻目睹很多死尸和死尸的故事。只讲一件印象最深的事。1943年,我在兴宁一中念初中一年级。有个周末,从学校回到家,看见对门良友照相馆的橱窗中挂着两幅很大的照片。一幅是枪毙吃人犯,在跪着即将枪毙的犯人身旁,是吃剩的一个小孩的头和两个手臂。另一幅照的是一个善堂的工人一手拿着一条竹杠,另一个手提着一具饿死的婴儿正往用薄薄的白木版钉成的棺材中放。棺中已经有两三具,而地上还有五六具,有一个婴儿则坐在旁边哭。我不敢多看,含着眼泪,赶快离开。这些照片记录了潮汕地区的惨剧。那一年广东大旱,加上日寇入侵,“1943年全省死于饥饿的达三百万人,约占当时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十。各地饿死的人数,有可查的计台山县十五万人,潮汕地区五十多万人,电白县沿海地区三万人,新会县城十二万人中饿死了四万人,澄海县饿死的农民占三分之一。”[4]“旱灾前,惠来全县人口有40余万人,1943年就死了11万多人。”达濠“饿死者也达万余人,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5]人吃人,当时在全省许多地方屡见不鲜。而据现有资料,自从清顺治五年(1648)那次灾荒后,将近三百年间,广东已经没有人吃人的记载。[6]
广东这次灾荒不过是20世纪中国数不胜数的众多灾荒之一。就在1942年,“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300万人之多。”也占当时人口十分之一。“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7]人吃人,狗吃人,报章的记载连篇累牍。
要是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灾荒通常是地区性的,下半叶则出现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大灾:1959~1961年的三年饥荒。“累计增加的死亡人数——除开预期的正常死亡数——估计有1600万到2700万。”[8]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最近公布的数字更高达4000万。[9]这个“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中国灾荒史上是空前的;无论绝对数还是占人口的比重,都已超过苏联集体化造成的大饥荒。[10]
天灾年年有;由此变为饥荒,甚至登峰造极,饿死人,人吃人,这可怪不得天老爷。这是人祸。贫困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人祸。说到底,还是缺乏自由和法治。
时至18世纪末,乾隆爷时代,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的中国人,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的三分之一。那时的中国不是穷国;但穷根早已深深埋下,进入19、20世纪的一百多年间便每况愈下了。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工商业必不可少的自由,阻碍着中国社会由中世纪向现代转型,从而无法告别贫困。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财。”[11]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和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例如,19世纪国际贸易的主导商品是纺织品。它和鸦片是19世纪外贸入超的主要因素。为与外商争利,70年代开始,朝野有关人士就着手筹办纺织厂。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车生产,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从1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起算,几经折腾,整整历时14年。1880年,为办这么一个厂,李鸿章特地上奏,并经皇帝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12]1888年张之洞在广东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致电李鸿章协商:“阅《申报》载,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消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给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望速电复。”[13]李鸿章的答复是:“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14]照“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双方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李鸿章和张之洞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在人治社会官场文化的氛围中,矛盾顺利化解了。
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其他人办,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黯然回国退休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出面筹办的,已筹集资本两万余,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15]
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自由。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于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社会转型步履维艰,没有新的经济领域和企业可以大量吸收过剩劳动力;亿万农民守着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开发已近极限的小块土地,一遇天灾,怎能不饿死?
1942年河南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蒋委员长不承认有那么大的天灾!他不但没有认真救灾,还“严令河南的征收不能缓免。”当时“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税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因此,收成越坏,从农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在少数地方,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缴纳军马饲料。”[16]与此同时,国民党和蒋介石把言论自由视为洪水猛兽。《大公报》的记者把河南大灾人吃人的惨状公诸于众,蒋委员长竟下令该报停刊三天!已定好机票应邀赴美的该报总编辑王芸生,在出发前两天接到中宣部长的电话:“委员长叫我通知你,请你不要到美国去了。”[17]一个敌视新闻自由、拒绝独立的大众传媒监督的专制政府驱赶农民走向死亡!
1943年的广东,则一是日寇横行,他们当然不管中国人的死活;二是国民党官员虽然也做了一些救灾工作,挪用救灾物资投机倒把的也大有人在。人祸的气味也是很浓的。
自由和法治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20世纪中国下半叶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1959~1961年的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语),早有定论。后二十年解散人民公社,使农民获得经济自由而使农业蓬勃的事实,强有力证明了前二十多年农业问题的症结所在。举世公认,内外私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最强大的推动器;国有经济只有摆脱行政羁绊走向市场,才能起死回生;又从另一侧面奏响了经济自由颂。当前经济发展的隐忧和障碍何在?经济自由不充分,不准进入的禁令太多,私人经济仍然是二等公民,不少方面还处在不平等状态。国有经济仍受意识形态束缚,即使挂上公司的招牌,仍然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神憎鬼厌的贪污腐败黑潮所以无法根治,说到底,也是由于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而公民应有的自由权被侵蚀,反而要向官员乞讨。
希望在勇敢地与国际接轨
毕竟在前进。要是说上一世纪之交“灭洋”的叫嚣还能愚弄千百万农民,还能在权贵和最高决策层中占上风,改革开放却是人迎接新世纪的主旋律。
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每个公民都有自己应尽的责任。
中国人应该拥抱世界,令人类文明的所有先进成果为我所用。
自由是舶来品;又是国家和现代公民的必需品。没有自由,就没有现代经济。没有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也不可能有学术、文化的繁荣和清明。
法治也是舶来品。如果它不能在中国生根,神州必然沦为可怕的黑金世界。
有识之士早已指出,竞争是制度环境之争。一国、一省、一市乃至一个,制度环境优良,资金、人才就会汇聚;反之,则逃之夭夭。
在新世纪,让狭隘民族主义远离我们!中国的希望在勇敢地与国际接轨,让法治和自由牢牢生根。
2001年元旦试笔
原载《合生月刊》第15、16期合刊(2001年1月)
[1] 《清史稿》卷466。
[2] 周一良等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第183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北京。
[3] 2000年全国平均的恩格尔系数为51%;其中三亿多城市人口为40%;而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为2.5倍。九亿多农民状况如何,不难估计。
[4] <1943年广东旱灾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第3页,广州市政协1963年。
[5] 吴华胥:<1943年潮汕旱灾见闻>,《广东文史资料》第11辑第91、93页,广东省政协1963年。
[6] <1943年广东旱灾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第12~13页。
[7] 钱钢、耿国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第375、3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8]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90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0年北京。
[9] 廖盖隆:〈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
[10]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91页。
[11] 沈之奇:《大清律辑注》第215页,出版社2000年北京。
[12] 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
[13] 张之洞:<致天津李中堂>(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张文襄公全集》卷131。
[14]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同上。
[15] 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40~241页,岳麓书社1984年长沙。
[16] 《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第384~386页。
[17] 同上第398页。
上一篇: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败
下一篇:政府的规模与范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