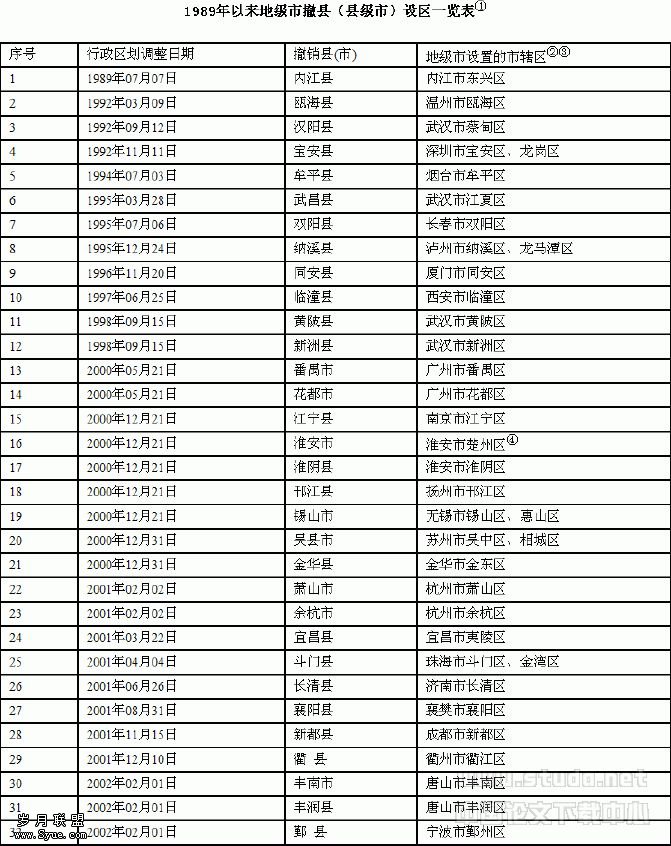当代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前提的再思考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0
发展家能否实现民主?或者说,民主的政治形式是否能够成功地移植到非西方国家?许多政治学家曾对此持怀疑态度。在60~70年代,世界上的一些权威主义政权显得稳定和强有力,而大批建立民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却充满危机和混乱,纷纷倒向军人独裁政体,从而形成一股强劲的全球性非民主化浪潮。这种情况带来政治学界对民主在发展中国家适用性的非常广泛的悲观主义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我国一些政治学者在80年代提出的“新权威主义”也是这种思潮的一种反映。
然而的发展却使这种悲观主义理论不攻自破。自70年代中期起,一股巨大的民主化潮流从欧洲南部悄然兴起,导致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军人独裁政权垮台,西欧最后这三个权威主义政体完成了向民主的过渡。接着,民主化潮流漫卷拉丁美洲,军人独裁者纷纷交出政权,让位给民选的文人政府。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的潮流涌入东亚和南亚,菲律宾、韩国等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到80年代末,民主化潮流迅猛席卷“斯拉夫-东正教”地区,前苏联和东欧集团各国一个接一个转向西方式的民主道路。80年代末和90年代,民主化潮流也回荡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冲击着“中东-伊斯兰教”地区。美国著名政治学家S.亨廷顿把这次民主化运动称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根据他的说法,从1974年到1990年,世界上有约30个国家由权威主义政治过渡到民主,另有20多个国家出现了强大的民主运动,或开始了朝向民主化的改革。⑴进入90年代,又有数以十计的国家完成或开始了向民主的转变。正如L ·达尔蒙德和M ·波莱特耐尔所说:“当未来历史学家回首20世纪时,他们可能把这个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视为现代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民主躁动时期。”有的学者乐观地指出,“民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唯一受到尊重的政治制度。”“20世纪是民主的世纪。”⑵这场民主化潮流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特别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问题形成更明确更有根据的认识。在70年代以前,虽然有部分发展中国家走上了民主道路,但大多是受到西方政治文化冲击而产生的暂时效应,或属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这种没有深厚根基的民主或者很快就垮掉,或者难以健康地运作。而在当前这场民主化浪潮中,有如此众多的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转变,其中多数国家向民主的转变都是自身民主化条件发育成熟的结果。它表现为:这些国家向民主的过渡多都是以较为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很少暴力和流血;民主制度建立后,很少遇到强大的反抗,基本没有反复;民主制度的运作较为顺利,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为多数国民所认同。⑶这样,它就为我们认识发展中国家民主化问提提供了可靠的材料。本文拟根据近20来来各国民主化的实践,国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对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诸种前提作一个初步的分析。
2.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定量联系
经济因素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历来为人们所强调。但是,关于两者之间具体的联系方式人们却有着不同的认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根据数十个国家的经验,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当代发展中国家向民主过渡的经济阀值。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对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正相关的联系作出过精彩的论述。他引用一些数字证明:“民主较多国家的财富、化、城市化程度和水平的平均数要高得多。”依次而降,是“民主较少”的国家和“独裁较少”的国家,而在“独裁较多”的国家这些指标处于最低水平。⑷李普塞特以后,许多研究者沿着这个思路探寻民主化的原因,把民主化视为经济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国民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的一个必然产物,而把一个国家的GNP 视为解释民主的“关键的变量”。
但也有许多学者对这种解释模式提出了挑战。特别是60~7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权威主义统治下获得了较高的发展水平。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并行不悖,这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使人们把经济发展与权威主义政治联系在一起。G.奥唐奈就曾向李普塞特的“社会经济越发展=政治民主的可能性越大”这一“乐观的等式”挑战。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开始的前一年发表的著作中,他通过对南美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现代化对民主不利。至少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超出一点就与民主制度发生冲突,民主只与中等水平的经济发展相联系。“最可能与现代化最高水平相伴随的是政治权威主义而非政治民主”⑸G.奥唐奈的观点不是孤立的。一位学者在1979年悲哀地得出结论说:“西方大多数发展理论家似乎都已接受并带有几分懊丧地承认:发展必须与权威主义政府相伴随。”⑹然而第三次民主浪潮迫使人们重新为经济因素定位。为什么60~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看起来如无根浮萍的民主到80年代却开始生根开花?M.塞利克森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中就这样问道:“为什么在这个地区(中美洲)长期以来像孤儿一样的民主,却突然开始找到了一个家?”⑺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突出变化就是经济的发展。经济因素比政治因素更稳定,比文化因素更活跃。我们看到,在经济低度增长和停滞的国家,往往是民主化的“盲区”,或仅表现出微弱的民主化冲动;而在经济失败的国家,尽管会发生激烈的政治动乱,但难以启动健康的民主化进程。第三次民主浪潮主要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或中度增长的国家。在50年代,这些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实现民主的最基本的经济前提,经过20多年的发展,许多国家开始跨过了作为民主必要经济前提的阈限,结果导致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经济因素虽不是绝对的,但却能够解释多数国家的情况。1989年被世界银行划为高收入的24个国家(人均收入6010—21330美元)中,除3个石油输出国外都是民主制度,其中新加坡是半民主制度。而在另一端,被世界银行列为贫穷的42个国家(人均收入130—450美元)中,只有两个国家(印度、斯里兰卡)建立和维持着民主制度。在其余53个中等收入国家中,有23个民主国家,25个非民主国家,5个在向民主制度转变。⑻由此可见,向民主的转变应主要发生在中等或中上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穷国,民主化不可能,而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完成。两者间有一个政治“转变带”,在这个特殊发展水平上的国家最容易转向民主。多数转向民主的国家都应在这个经济水平上。当国家经济发展进入这个阶段,它就有了民主化的希望。它也告诉我们,经济变量在民主化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其它变量只有在解释例外的情形时才可能超过经济因素的作用。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也使我们可以大体上确定“转变带”的GNP 水平,从而在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建立起定量的联系。虽然第三次浪潮民主化国家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上,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却有着大致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到80年代末实现民主的31个国家中,有27个属中间收入水平。它们中的一半在197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3000美元间。而1976年在这个发展水平上的国家中,有四分之三在1974年由非民主的政府统治,到1989年实现了民主化。进入90年代,又有一些处在这个发展水平上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根据亨廷顿的说法,在战前,转变带的中心是300-500美元(1960年币值),到70年代提高到500-1000美元。进入80年代又有所提高。⑼在90年代的今天我们大体上可以说,一个国家的GNP 在1000-3000美元间是开始向民主转变的阈值;当它达到3000-6000美元时,则是完成转变的阈值。这个阈值上下,是其它因素起作用的领域。如在这个水平以下实现了民主或超出这个水平仍未实现民主的情况,应考虑是其它因素超过了经济因素在发挥作用。
不过,对这种说法必须作出一定的限制。所谓GNP 水平必须是标志着一个国家经济正常发展的综合指标,即必须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大众传媒以及识字率等指标的同步发展。仅仅财富的片面增长则不在此例。
3.重估文化变量
古典和当代的民主理论都认为,民主不仅是一套制度建构,也是一整套独特的政治信仰、态度和情感的体系。国民关于政体合法性的信念和感觉是政体维持和变更的关键因素之一。当代家的民主化也证明了这一点。它既是政治体制的变更,同时也伴随着政治文化的嬗变。如果说以往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多停留在制度变革层面上的话,当代民主化浪潮却以民主政治文化的发育成熟为特征。它为我们考察政治文化变量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实际作用以及各种政治文化与民主的关系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材料。
在以往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中,有人将政治文化作为独立起作用的因素予以高度评价,甚至将其视为导致民主化的最重要的因素。R.戈斯泰尔就认为,适宜的条件对民主制度的成功是有帮助的,但对民主扩散的更长过程来说它是第二位的因素。他的结论是,在特定国家民主的存在或缺失,“首先是民主及其支持概念传播的相对效果的产物。”⑽J.皮诺克把民主需求的各种因素分为三类:、社会经济秩序、政治文化。他认为,政治文化因素可能包括了民主的最好解释。⑾也有人把政治文化作为受其它因素特别是经济发展制约的因素,作为一个起中介作用的变量引进民主问题的研究。在这些学者那里,政治文化是作为随时代变化和现代政治经济发展而不断改变的因素来考虑的。根据这种观点,“政治文化也许是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关键的联系环节。”⑿但政治文化还有相对稳定的部分。它们具有民族特征,由该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形成。虽然政治经济现代化过程对它的表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影响,但它深层结构的变化仍然是有限的。政治文化研究要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当代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驱动下,民主能够在迥然不同的文化区域建立起来吗?
以往政治文化的研究倾向于强调民主的文化特殊性、不可移植性,强调发展中国家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性、其嬗变的缓慢和长期性。但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表明,各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是民主化的基本驱动力,它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发展,也以不可阻遏的力量在摧毁权威主义政治,推动着民主化进程。一个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可以构成民主化的动因或障碍,推进或延缓民主化进程,但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力量面前,它的作用是有限的。经济发展能够突破文化的界限,或推动文化发生较快的变革。文化的特殊性可以使一个民族走上一条特殊的民主化道路,也可以使一个国家初建的民主制度及其运作着上民族的颜色,但没有一种文化构成实现民主的绝对障碍。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基本上是全球性的,在非西方文化的各个地区和国家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在经济条件成熟的条件下仅因为文化条件特殊而未能实现民主化的事例是少见的。它昭示了现代民主在全世界普适性的光明前景。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也使我们能够确定各种文化与民主的具体联系。亨廷顿根据与民主的积极关系,给各种文化排出一个序列。它们依次是:新教、天教、东正教、孔教、伊斯兰教和黑非洲文化。⒀新教文化最适合民主,这已经为历史发展所证实。最早实现民主化的西欧、北欧、北美、大洋洲各国几乎都是新教国家。战后的一项研究表明,“在99个国家中,人口中新教徒的比例越高,民主的程度越高”。⒁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使人们对天主教和东正教与民主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直到本世纪70年代,天主教和东正教文化还被认为是不利于民主的。但第三次浪潮几乎是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浪潮。“大约在1974—1989年转向民主的国家中有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国家。”⒂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督教的另一分支东正教国家也基本上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
基督教对民主政治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在韩国表现得十分突出。在战后初期,韩国基本上是以孔教为外表的佛教国家,只有1%的基督教徒。到80年代,基督教徒猛增到25%,即4千万人口中有1千万是基督徒。改宗基督教的主要是政治上最活跃的部分:青年人、市民和中产阶级。它使韩国社会孔教的权威主义和佛教的消极让位于基督教的好斗精神。民主运动的两位著名领袖金大中和金泳三都是基督徒,70年代在《民主救国宣言》上签名的都是基督徒,有的是教会神职人员。金大中就曾极力推祟基督教在韩国民主化中的作用,认为基督教是民主运动的精神源泉,教会是民主运动的保垒。⒃伊斯兰教文化和黑非洲文化与民主的积极联系最弱,这一点已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事实所证明。如今,权威主义政权和少量传统的君主政治主要集中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和中东伊斯兰教地区。但是,从90年代的情况看,黑非洲文化与民主的积极联系也许超过伊斯兰教文化。这与亨廷顿的排序有出入。在黑非洲,文化因素同时导致政治发展的低水平和经济发展的低速度。但是,直接阻碍民主化进程的主要是经济因素。另外,我们还需看到,黑非洲文化对民主化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其惰性力量,是其传统政治文化的低水平对现代民主文化的不适应。这个差距需要随着社会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而得到弥补。也就是说,黑非洲的主要问题是发展问题。而在“中东-伊斯兰教”地区,本土文化则表现为一种对现代民主的好斗的对抗性。政治文化的变革在文化领域本身就遇到强劲的挑战。特别是在一些国家里,比较开化的政治精英必须以权威主义的方式控制政权,而权威主义统治的松动和民主化的改革往往会带来反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抬头。“中东-伊斯兰教”国家民主化改革面临着这种二难困境,其民主化进程也许更为困难。
4.外部因素:民主化的助力
一个国家的民主化主要依赖于内部诸条件的发育成熟,但外部因素也是影响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变量之一。它可以加速或延缓民主化的进程。对一些国家来说,外部影响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根据前面的分析,一个国家发展达到一定社会经济水平,即进入民主化的“转变带”。但外部影响会使其在进入“转变带”前就实现民主化,或在其进入“转变带”后推迟实现民主化。
根据亨廷顿的说法,世界上有几个主要的权力中心对第三次民主浪潮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即梵蒂冈、欧共体、美国和苏联。它们的影响都是世界性的,但又各有侧重。天主教会的影响主要是实行权威政体的天主教国家;欧共体的影响集中在南欧和东欧;美国的影响面要广些,但其影响较大的是拉美和部分亚洲国家;前苏联的变革清除了东欧民主化的主要障碍。这几个权力中心每一个都有过政策上的变化,没有这些变化,第三次浪潮的情形会大不相同。⒄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间,美国虽然口头上也高唱民主原则,但事实上,它常为了战略需要和实际经济利益而牺牲民主原则。世界上许多独裁国家都是仰美国鼻息而生存的。在冷战的年代,为与左翼势力对抗,发展中国家的右派军人独裁政权和传统的君主政体常得到美国的偏爱。但是从1974年起,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开始把促进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标。这恰与第三次民主浪潮的兴起相吻合。到1981年底,里根政府确定了不仅在共产主义国家,而且在非共产义国家促进民主的目标。美国那些权威主义的盟友开始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这些国家的民主反对派则开始受到来自美国的鼓励和支持。
西欧各国在战后主要是收缩而不是扩张其权力。在推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方面,主要是英国在其非殖民化过程中做过一些努力。应该说,英国殖民地比其它国家的殖民地更容易走上民主道路。除此之外,战后西欧政府已习惯于同任何非民主的政体合作,默认其国内事务的安排。无力施加巨大的影响。不仅在拉美,而且在欧共体的直接边缘国家也如此。⒅但欧洲议会和欧洲共同体却是一贯支持民主的。在各国际组织中,只有它们“明确地和始终一贯地在其所有成员国中维持民主”。⒆欧共体的扩大以民主为条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从经济发展角度都迫切需要加入欧共体。欧共体对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60年代中期以前,天主教会是保守的反民主势力。自60年代中期起,它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官方层面,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确立了支持社会政治变革和促进人权的方针。在拉丁美洲和其它地区的主教会议上,这一方针都得到重申。在基层,普通信众、基层教士和年青一代的教会知识分子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开始与权威主义发生冲突。从此,天主教会在各地都站在了权威主义政权的对立面。在巴西、智利、菲律宾、波兰和中美洲国家,天主教会在反权威主义运动中承担着中心的角色。教会有大量可资利用的资源,有严密的组织,有教堂、电台、报刊等工具,有谙熟政治的领导人,能够利用其国际性的联系和影响,这都使它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
除政府之外,各种非政府组织,政党、工会、教会等,以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如世界基督教民主同盟、社会党国际等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外部影响的另一种来源是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影响。亨廷顿称其为“示范效应”和“滚雪球效应”。
所谓“民主化浪潮”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它表现为向民主的过渡和民主化改革在若干国家同时发生或相继出现。率先民主化的国家产生一种示范效应,为其它国家所摹仿。若干国家相似的进程产生连锁反应,它们交叉影响,相互呼应,从而创造出一种国际性的气氛和时代精神。对于民主条件成熟的国家,这种气氛减少了民主化进程的阻力,对于民主条件尚不够成熟的国家,外部影响往往是启动民主进程的最初动力。
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国际交往的扩大和深化,已经使当代世界已经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特别以覆盖全球的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不分国界的“空间”,使世界真正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这使率先民主化的国家对其它国家产生更强烈更直接更迅捷的冲击。
民主的示范效应在地理上相近和文化上相似的国家产生最强的反响。如葡萄牙对南欧的影响,葡萄牙西班牙对其前殖民地拉美地区的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转变令人信服地说明,伊比利亚文化并非天生不变地是反民主的。”⒇在拉美国家内部,示范效应表现为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府还政于民。在亚洲,1986年2月马克斯的垮台,引起了亚洲其它国家权威主义领导人和民主反对派的焦虑和希望。特别对韩国产生了直接的积极影响。在黑非洲,示范效应使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滚雪球效应在东欧最具戏剧性。当波兰于1989年8月将铁板一块的斯大林模式冲开第一道缺口后,权威主义的堤坝开始迅速坍塌,各国的民主化接踵而至。匈牙利是9月,东德是10月,捷克和保加利亚在11月,罗马尼亚在12月。甚至在阿尔巴尼亚那样根本不具备实现民主条件的国家,民主化浪峰所至,权威主义政权也被摧毁。
滚雪球效应还产生加速度的变化,先行者艰难曲折的历程在后来效法者那里会以压缩的形式和以较顺利的方式重演。因为一旦雪球滚起来,其滚雪球本身的过程就开始起作用。我们看到,在波兰,其民主化过程花了十年,匈牙利是十个月,东德是十周,捷克是十天,罗马尼亚则是十个小时。
如此众多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使当今世界已经形成了一种有利于民主的政治气氛。这种气氛对于未来各国的民主化进程是非常适宜的,而权威主义政权的维持将日益困难,违背时代潮流的非民主行为将面临前所未所的压力。非洲国家塞拉利昂两年前发生了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但是,国际社会施加了强大压力迫使军政府交出政权,西非国家甚至联合起来直接进行干预,强行推翻军人政权,将民选总统迎接回国。比较一下60-70年代国际社会通常会承认军事政变的既成事实的做法,我们看到时代潮流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注释:⑴⑶⑻⑼⒀⒁⒂⒄⒇Samule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pp.3—5.164.194-196.263-264.60.(9?)315.75.76.86-87.103.⑵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Edited by Geraint Parry and Michael Moran ,London,Routledge,1994.P.2.264.⑷S.M.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e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1):pp.69-105.李普塞特:《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3—34页。
⑸⑺⑽⑾Tatu Vanhanen,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147states ,1980-88,Taylor &Francis,1990,P.43.46.44.42.45.⑹引自塞缪尔·亨廷顿:《的目标》,载《化——理论与经验的再探讨》(译文集),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33—334页。
⑿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Edited by Larry Diamond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3.pp.1—2.⒃金大中:《建设和平与民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68—169、192—197页。
⒅⒆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edited by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G.Schimitter ,Lanrence Whitehea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Ⅲ。pp.3—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