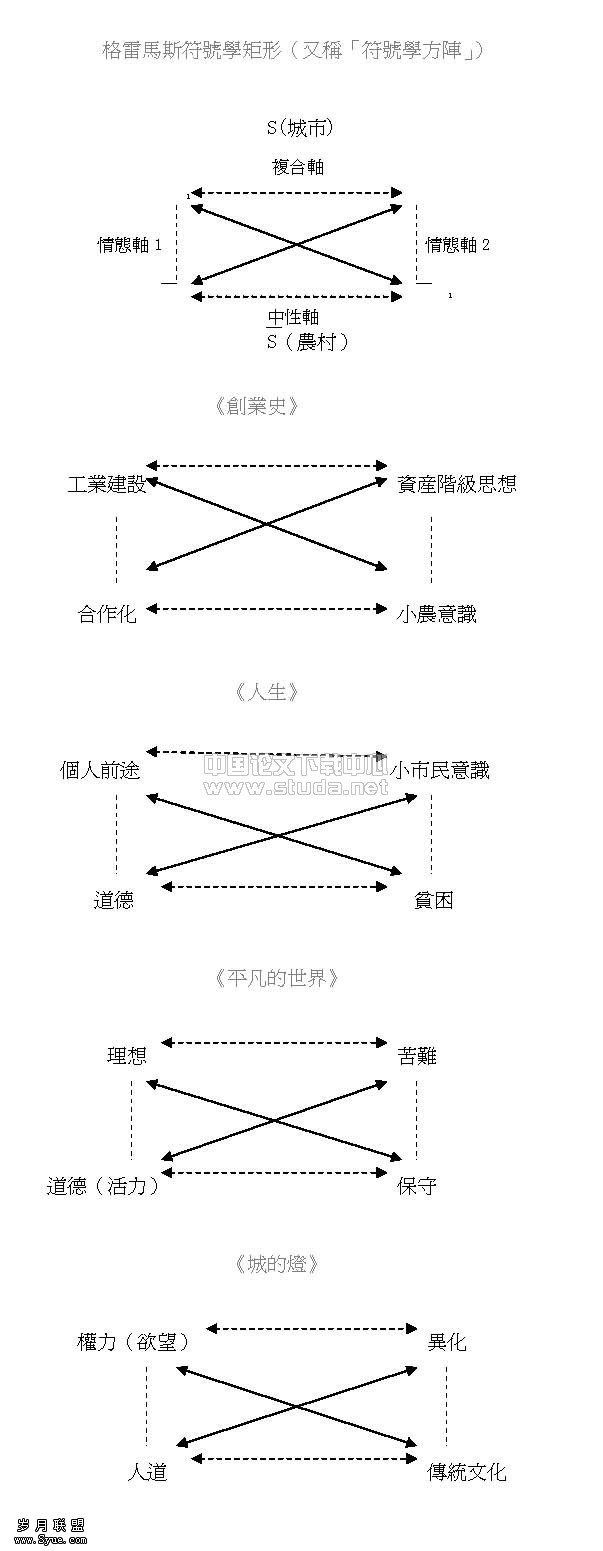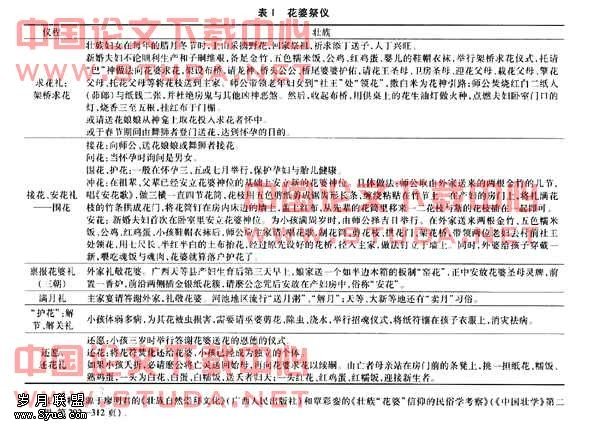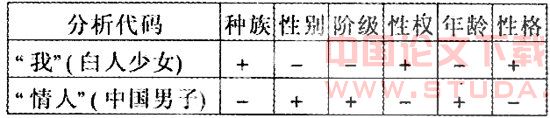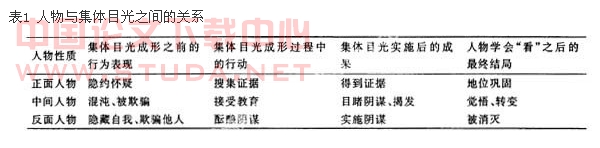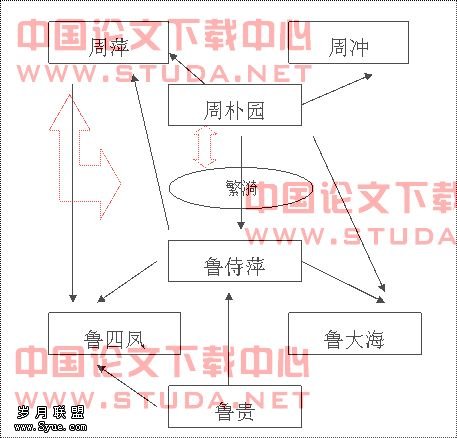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范妮·伯尼小说创作
[摘 要]英国18世纪小说家范妮·伯尼被女性主义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尊称为“英国小说之母”,虽然她在英国文学史上历来享有一席之地,但她创作中的女性视角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范妮·伯尼的作品才被重新发掘和重新阐释。以女性主义视角聚焦其小说创作的主题、动机和影响,她对父权社会的鞭挞、嘲讽和暗中颠覆便彻底显露出来。作为研讨妇女内心隐秘的一位早期女性小说家,她为使小说成为妇女喜爱的文学样式做出了努力。
[关键词]范妮·伯尼;女性主义;父权社会
Abstract:Fanny Burney,an English novelist in 18th century,was regarded as “the mother of English Fiction” by the feminist pioneer Virginia Woolf. Although she made a name in the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the female point of view in her works had long been neglected. Her works were rediscovered and reinterpreted only after the rise of 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feministic perspective,her criticism,irony and subversion of the patriarchal social system are quite obvious in the theme,motivation and effect of her fiction writing. As an early woman writer who explored the women’s innermost being,she helped to make fiction a favorite literary genre for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women.
Key words:Fanny Burney;feminism;patriarchal society
范妮·伯尼(Fanny Burney,1752~1840年),也称达布莱夫人,被英国20世纪著名女作家和女性主义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尊称为“英国小说之母”。虽然她在英国文学史中历来享有一席之地,但她所表达的对妇女命运的关怀及其严肃的社会主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重视,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英国第一位值得尊敬的女小说家从未因为对其性别的艰辛和挣扎的渲染而得到恰当的认可”[1]。直到女性主义批评兴起后,人们才开始关注伯尼小说创作的女性主义主题和动机。
一、范妮·伯尼的小说创作主题
范妮·伯尼一生共创作了4部长篇小说,记叙的都是年轻女性的坎坷经历。第一部小说《伊夫莱娜——一个年轻女子涉世的》讲述了一个无依无靠的灰姑娘伊夫莱娜如何赢得一门美满婚姻的浪漫传奇。看似一部传统童话,而实际却是一个被剥夺了权力、金钱、头衔、家庭和姓氏的女子,如何设法以不公开打破规范的方式最终获取所有这一切的故事。女主人公伊芙莱娜自幼丧母,并被父亲贝尔蒙特爵士遗弃,没有真正的父姓,从而没有合法的身份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权利和地位,因为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必须根据其与男性的关系来定义。于是,她只有嫁一个有钱有势的丈夫,以求得夫姓的保护,使将来的生活得到保障。而这都得取决于她是否具备淑女风范,即必须在男性面前表现得幼稚无知,恭顺谦卑,自我克制。纯真的伊夫莱娜在父权社会习俗的逼迫下,最终学会了伪装。“虽然她从没有丧失自己的洞察力,却学会了抑制自己的观点,不致引起遭人谴责的影响,学会获得了奥维尔先生特别崇敬的那种良好教养的构成要素,即沉默、严肃和镇静。”[2]57伊夫莱娜对男性的屈从终于使她如愿以偿,她的成长历程明显地折射出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及对她们人格的扭曲。
范妮·伯尼的第二部小说《塞西莉亚——一个女继承人的传略》对女性在父权社会的地位做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故事的女主人公塞西莉亚年轻貌美,自幼父母双亡,叔叔死后留给她一大笔可继承的财产。她没有父母长辈的约束,没有拮据的烦恼,婚姻对她来说也不是很迫切的事情。她决心好好把握自己的命运,按照自己的意愿交友、读书、弹琴、与需要帮助的朋友分享财富。但是,他叔叔的遗嘱规定:在她21岁以前,她的财产必须由3个男性监护人掌管,她必须与其中一位监护人共同生活,婚后必须让她的丈夫改随她姓,否则她就没有继承权。为此,塞西莉亚先是落入3个男人手中,他们一个挥霍无度,一个爱财如命,一个愚蠢傲慢;接着被一群觊觎其继承财产的求婚者包围,他们对她的意愿置若罔闻;当她有了意中人后,对方家却坚决不同意婚后改姓,使她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乃至疯狂而流落街头。最后她虽然被丈夫一家接纳,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姓氏、财产和独立的能力。她和伊夫莱娜一样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财富只赋予男人自由和权力,而她作为一个女人,什么也得不到。小说让读者看到:年轻女人的独立个性和社会经济总是不断受到威胁并难以维持。
与前两部作品不同,范妮·伯尼的第三部小说《卡米拉——一幅青年画像》的女主人公卡米拉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中,拥有父母之爱,手足之情,还有一个十分疼爱其兄弟姐妹的伯父。但父姓在给予她社会庇护的同时,也严格限制着她的独立和自由,使她必须和伊夫莱娜一样屈从于男性。她父亲总要求她淳朴、温顺和迁就他人,在他看来,“女子的适当,无论为了实用还是为了幸福,仍要探索,仍是人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它的改进,或它的疏忽,对女子是好是坏,只有根据该女子最终落入其手的丈夫的脾性而定”[3]。 也就是说,女子教育没有确定的价值,与女子本人无关,让人不禁想起英国女权主义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女权辩护》一书中对这类观点的驳斥。在父权社会既定秩序的束缚下,卡米拉既不敢大胆表露自己的爱情,又对经济事务一窍不通,乃至受尽恋爱挫折的痛苦,并误使父兄卷入债务纠葛中。虽然故事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却在传统故事结构下暗藏了小说作者对女性不能自主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对父权社会把妇女排斥于、经济和文化生活之外的批判。
在其最后一部小说《流浪者——女人的艰辛》中,范妮·伯尼对女性的普遍困境进行了更大胆而深刻的探讨。小说女主人公朱丽叶本是一位英国伯爵的秘密婚生女,一直生长在法国。法国革命爆发后,她为了使其监护人免遭绞刑,被迫成婚。婚礼过后,她随即逃往英国,隐姓埋名,打算靠自己的才能独立生活,因为法国革命已唤醒了女性的人权意识。然而,作为一个流落异乡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年轻女子,自立又谈何容易。朱丽叶历尽艰辛,靠给人缝补衣服、做家庭女教师和陪护、卖艺等方式来维持生计。直到她的监护人找到她,才使她可能恢复财产继承权,有个安身立命之所。伯尼由此强调了父权体制下受压迫女性的社会弱势地位,希望妇女能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从而使女性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小说中范妮·伯尼笔下的女权主义者爱里诺说道:“我知道,你们认为我被那些革命思想玷污了,而我却认为自己因此而高尚。因为那些革命思想,我敢作为平等的社会成员,而不是可怜的屈辱的必要的社会附属物,保有自己的智力和态度;因为那些革命思想,我要求从附和不经检查的意见和受我所藐视的偏见控制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因为那些革命思想,我有了人类早该有的珍贵的敢于独立思考的基本公民权。”[4]她直接以革命的激进话语表达了女性政治的理想。
毋庸置疑,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伯尼聚焦于未婚妇女的生活,揭示了她们在婚姻、财产继承、家庭关系和就业等方面的困境。因此,范妮·伯尼最新的传记作者克莱尔·哈曼(Claire Harman)形容伯尼具有“而强大的女性主义”[5]。
二、范妮·伯尼的小说创作动机
美国教授克里斯蒂娜·斯特洛伯(Kristina Straub)曾评论道:“伊芙莱娜的虚构情形实际反映了伯尼自己作为一个女人,试图在传统父权社会中寻求女性问题解决方案所面临的困境。”[6]152作为一名生活于18~19世纪的妇女,范妮·伯尼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传统观念的束缚。那时,妇女没有任何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她们只是男人的附属物。对妇女来说,婚姻是她们人生的最高目标,相夫教子是她们的职责,除了做贤妻良母,她们不应该有任何其他追求。根据约翰·乔治博士的说法,“如果你偶然有些学问的话,最好把它作为一个完全的秘密,特别不能让男人知道”[2]2。写作对妇女而言简直就意味着对父权社会传统的挑战。
虽然,因为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查尔斯·伯尼博士是研究史的学者,与当时各界的社会精英交往甚密,家中的座上客包括字典编撰家约翰逊博士、戏剧家谢里丹和政治思想家伯克等名流,范妮·伯尼“大有机会观察到丰富多彩的人间景象,而丰富的人间万象为她提供了充足的推动因素”[7]1390。但是,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却不允许她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妇女从事文学创作。下面这段描述极为真实地再现了范妮·伯尼当年的窘困处境:“女孩子写东西被认为有点荒唐可笑;而成年女人写作就是很不相宜的事了。……范妮的继母也不赞成舞文弄墨。……有一次,她被迫在后花园里把所有的文字付之一炬。最后,似乎是达成了某种妥协。早晨是神圣不可侵犯地,用于缝纫之类的正经工作;她只有在下午可以在那间临河的瞭望房里涂涂写写……”[7]324
显然,范妮·伯尼深切体会到了英国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因此,她力图在自己的创作中真实再现妇女受压迫的事实,与父权社会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抗争。所以克里斯蒂娜·斯特洛伯认为,伯尼的创作动机在于:“写作使她能在父权社会的女性选择中,做出与她的社会和个人权力不相称的美学和想象选择。换言之,伯尼可以轻易赋予其小说女主人公高于男性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她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的”[6]152 。
伯尼不仅目睹了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女权意识的萌发,还目睹了19世纪上半叶英国女权运动的兴起,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女性意识,并通过其作品和创作实践触动了那个时代的许多妇女。除了小说,范妮还留下了《才女》、《爱情与时尚》、《繁忙一日》和《厌恨女人者》等剧作,这些作品都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和女性意识,因而近年来引起了女性主义学者的重视。
三、范妮·伯尼的小说创作影响
范妮·伯尼对男性文学领地的侵入,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使她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男性批评家的猛烈抨击。虽然《塞西莉亚》出版时曾受到舆论的好评,第二年又两次重印,但一些读者,包括爱德蒙·伯克,却抱怨小说结尾太阴郁,不像当时绝大多数小说那样,以婚姻、和解、巨额财产的意外获得告终。而伯尼却坚持保留她的现实性结尾,即塞西莉亚虽与丈夫一家和解,却失去了财产继承权。她在1789年4月6日写给自己尊敬的导师塞缪尔·克瑞斯普(Samuel Crisp)的信中辩解道:“我已经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了,如果我被迫放弃这个结尾,我的整个计划就会失败。”[9]伯尼希望表现的是造成女主人公自身境遇的固有矛盾和无可救药的现实。
在《流浪者——女人的艰辛》一书出版后,伯尼受到了当时评论家的一致贬损。他们指责伯尼笔下的人物和情节不真实,语言啰索晦涩。其中,威廉·赫斯利特(William Hazlitt)在1815年《爱丁堡评论》上撰文批评道,小说女主人公经历的所谓女人的艰辛都是无中生有,范妮·伯尼的著作因而一文不值。1843年,麦考莱再次在《爱丁堡评论》上批评该小说语言支离破碎,十分糟糕。结果该书出版后只卖出3 500册,原先的再版计划不得不被迫取消。但范妮·伯尼却在1815年7月10~12日写给兄弟的信中说:“若干年后,一些优秀读者在不或了解首版的情况下,即排除任何偏见和偏爱后读这本书,将会宣布‘这是一本由先前或真或假地得到公众嘉许的年轻女人写的同类作品。’”[10]
今天,由于女权主义斗争已经成功地使妇女获得了和文学表达的权利,伯尼的作品终于得到了读者更多的理解和认同。朱莉娅·爱泼斯坦评价道:“在我看来,伯尼在欧洲小说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于她表现了各种层次微妙而复杂的父女关系、家庭和婚姻关系、革命性政治变化、对妇女的身体侵害、妇女的独立和财产问题,以及妇女参加工作的观念。”[11]
作为第一个研讨妇女内心隐秘的女性小说家,范妮·伯尼让妇女们看到小说可以给予妇女交流和表达自己思想的空间,她为有抱负的女性作者树立了成功的先例,为使小说成为妇女喜爱的文学样式开创了先河。所以,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写道:“简·奥斯汀应该在范妮·伯尼的坟墓上放置一个花圈。”[7]548马吉·莱恩(Maggie Lane)也称范妮·伯尼为“简·奥斯汀的文学教母”[12],她研究发现,简·奥斯汀的名字首次,也是其生前唯一一次出现在印刷品中,是在范妮·伯尼1796年出版的小说《卡米拉》所列的订阅者名单上,而简·奥斯汀发表小说一般都不具姓名。奥斯汀从小就喜欢读《伊夫莱娜》和《塞西莉亚》,20岁时听说她最喜爱的作家事隔多年后要出版另一部书,激动得立刻亲自用自己有限的零花钱去订阅。后来,奥斯汀的小说不仅情节与伯尼小说的情节十分相似,就连小说《傲慢与偏见》的标题也是受伯尼小说《塞西莉亚》结尾处一句话的启发:“这桩不幸事的所有一切都是傲慢与偏见的结果”。“毫无疑问,简·奥斯汀在她的成长岁月里,深受范妮·伯尼小说的影响。”[12]
总之,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范妮·伯尼的确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女性文学先驱。
[参考]
[1]Rose Marie Cutting.Defiant Women:The Growth of Feminism in Fanny Burney’s Novels[J].?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500-1900?,1977,17(3):519.
[2]Judy Simons.?Fanny Burney?[M].Houn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 :Macmillan,1987.
[3]Fanny Burney. ?Camilla,or,A Picture of Youth?[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359.
[4]Fanny Burney. ?The Wanderer or Female Difficultie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172.
[5]Susan Ostrov Weisser.the Novelist in Spite of Herself[N/OL].[2001-11-04]. http:∥www.nytimes.com.
[6]Kristina Straub.?Divided Fictions:Fanny Burney and Feminine Strategy?[M].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7.
[7]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M].北京:社会出版社,2001.
[8]Margaret Anne Doody.?Frances Burney:The Life in the Work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39.
[9]Barbara Benedict. Reading by the Book in Northanger Abbey[N/OL].[2006-05-11]. http:∥www.jasna.org/persuasions/on line/vol20no1/benedict.html#11.
[10]Justine Crump.The Wanderer,or,Female Difficulties[EB/OL].[2004-02-29].http:∥www.litencyc.com/php/sworks.php?rec=true&UID=8085.
[11]Julia Epstein.Burney Criticism:Family Romance,Psychobiography,and Social History[J].?Eighteenth century Fiction?,1991,3(4):280.
[12]Maggie Lane. Fanny Burney:Jane Austen’s Literary Godmother[J].?Jane Austen’s Regency World?,2005(17):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