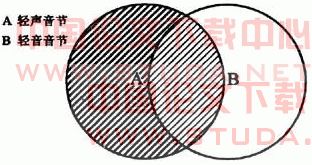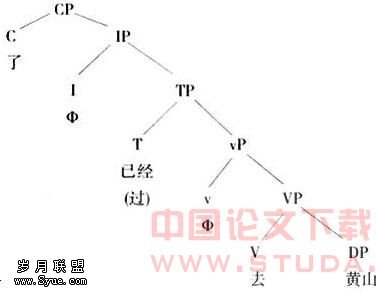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
章太炎曾自言:“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1],他对小学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在讲学中,他也“以音韵训诂为基”[2],首先讲授的便是小学。而正是在他的教导下,章门弟子也大多擅长小学研究。其中,钱玄同就是著名的一位。尤值得注意的是,钱玄同并不仅限于学术研究,而是运用其深厚的学养,积极投入到语言文字改革的实践中去,从而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
一 “主张用万国新语”
地看来,中国近代语言文字改革早在清末便已发端。如吴稚晖即曾在《新世纪》撰文激烈鼓吹废除汉文,“谓中国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3]。而与吴稚晖夙有积怨、且以“保全中国语言文字”[4]为职志的章太炎,则对这一观点痛加针砭。他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严厉批驳此说是“好尚奇觚,震慑于白人侈大之言”,并指出:“大地富媪薄厚矣,殊色异居,非白人所独有。……若夫象形、合音之别,优劣所在,未可质言。”因此,“今以中国字母施之欧洲,则病其续短矣。乃以欧洲字母施之中国,则病其断长矣。……世之君子,当以实事求是为期,毋沾沾殉名是务。”[5]对于章太炎的这一批评,吴稚晖反驳说:“语言文字之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既为人与人相互之具,即不当……一任天然之吹万而不同,而不加以人工齐一之改良。”他并且讥讽章太炎“横好古之成见”、“满肚子之不合时宜”[6]。对此,章太炎一再撰文指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7],“至若病汉字难识欲尽废之,而以罗马字拼音,则年来浮薄少年,歆羡岛中蛮夷,多倡此议,……甚无谓也”[8]。
今天看来,在这场论争中,双方虽不免带有一些意气用事的情绪,但仍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问题,如吴稚晖对文字改革必然趋势的论述,以及章太炎将语言文字与民族存亡相联系起来的观点。而从学理上看,无疑是章氏之说较为正确,由是也被其弟子广为接受。钱玄同便认为:“中西文之难易实相等,未必西文较易于中文”[9],并尖锐讽刺《新世纪》用“万国新语代汉语”的主张是“想入非非”,是“可笑之事,太炎谓其发疯,诚然”[10]。他还一再强调:“愚谓立国之本,要在,果使学术修明,必赖文字正确,……文字一灭,国必灭致亡,……故今日急务实在复保氏之教为最要”[11],“我国文字发生最早,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夫文字者,国民之表旗,此而拨弃,是自亡其国也”[12],持论明显与章太炎相同。
但是随着历史的,特别是受到袁世凯复辟事件的刺激,钱玄同逐渐改变了对汉字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国民之所以思想愚昧,屡屡被封建统治者蒙蔽利用,就是因为汉字难以掌握、妨碍了文化普及。由此出发,他开始倾向废除汉字的主张。1916年9月29日,他便在日记中写道:“经典之精义全不系乎文字。纵令今日中国之书焚毁净尽,但有精译本之西文五经则经典即可谓之不亡”[13]。从他后来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发出了废除汉字的先声。不过客观说来,钱玄同当时公开发表的主张仍然较为平和。1917年6月1日,他曾指出:“昔年吴稚晖先生著论,谓中国文字艰深,当舍弃之,而用世界语。章太炎师曾著论驳之。弟则以为世界未至大同,则各国皆未肯牺牲其国语,中国人自亦有同情。故今日遽欲废弃汉文而用世界语,未免嫌早一点。然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可。”[14]这一方面发出了提倡世界语的号召,另一方面也明确肯定废弃汉文的时机不成熟,“未免嫌早一点”。
然而就在此时,张勋复辟丑剧上演了,这更是给钱玄同以强烈刺激。以此为转折点,他终于提出了废除汉字的激烈主张。1918年3月4日,他在日记中批评汉字“论其本质,为象形字之末流,为单音字之记号。其难易巧拙已不可与欧洲文字同年而语。……此等文字亦实在不可以记载新文明之事物。”[15]在此基础上,他于3月14日专门致信陈独秀指出:“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在;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因此,“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16]。至此,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已跃然纸上。
至于废除汉字后应代之以何种文字,钱玄同也明确提出:“中国的语言文字总是博物馆里的货色,与其用了全力去改良它,还不如用了全力来提倡一种外国语为第二国语,或简直为将来的新国语,那便更好”[17]。而在各种外语中,他认为“Esperanto语根精良,文法简赅,发音平正,是人类文字而非民族文字。……所以我的意思,以为我们既认定人类文字胜于民族文字,……则当竭力提倡Eperanto,以为将来正当之文字”[18]。与此同时,他还一再援引吴稚晖当年有关观点作为佐证。显而易见,他这时已经转而赞同《新世纪》派用万国新语取代汉文的主张。
1923年1月,他在《汉字革命》中更揭櫫了“汉字革命”的口号。他断言:“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于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因此,“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19]
今天看来,钱玄同的这种主张显然失之过当。语言文字是维系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要素,不能单纯凭某些人的主观意志而取消。尤其是汉字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字,浓缩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和血脉亲情,是不可能完全废除的。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便提出:“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20]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则更是早在1923年就说:“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基础之时。”[21]
此外,钱玄同认为世界语作为人工改良的文字,比民族遗传的文字更优良,正所谓“人类文字胜于民族文字”,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错误的。陶孟和当时即指出:“各民族之言语,乃天然之语言,各有其嬗变之历史,故言语乃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质也”,相比之下,“世界语既无永久之历史,又乏民族之精神,惟攘取欧洲大国之单语,律以人造之文法”,其生命力必不长久[22]。朱我农也批评说:“私造了一种文字,要世界的人拿他当作日常应用的语言,是万万做不到的,所以Esperanto断不能当作世界通用的语言”[23]。时至今日,世界语诚然仍有特定的交流价值,但由于它毕竟缺乏民族历史的传承与积淀,所以始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的推广,这无疑从实践上充分证明了用世界语废除汉字的主张是行不通的。
不过平心而论,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首先是因为汉字难识难写,妨碍了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播。客观看来,这种针砭固然不免尖锐,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揭示了汉字的某些弊端;而更为关键的是,钱玄同深感以往用汉字记载的思想观念过于陈腐,“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24],因此应废除。这说明他这一主张虽然偏激,却是出于思想革命的动机。对此,陈独秀一方面指出这种偏激的主张是“石条压驼背”,另一方面则为之申辩说:“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叶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25]而任鸿隽在批评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有点Sentimental(指情绪化——引者按)”的同时,也十分公允地为他澄清说:“我想钱先生要废汉文的意思,不是仅为汉文不好,是因汉文所载的东西不好,所以要把他拉杂摧烧了,廓而清之。”[26]
至于钱玄同之所以提倡世界语,其实也是基于对世界大同的追求。他认为:“夫世界进化,已至二十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异日欧战告终,世界主义大昌,则此语必有长足之进步无疑”[27],并解释:“我自己是信人类该有公共语言的。这公共语言,是已有许多人制造过许多种的。这许多种之中,在今日比较上最优良者是Esperanto,所以我现在便承认Esperanto为人类的公共语言。”[28]这显然是一种渴望大同的美好愿望,“是抱有世界大同之理想而改革文字之一种急进派的主张”[29],应当是可以理解的。
二 从“世界语”到“国语罗马字”
如前所述,钱玄同在五四时期曾主张用世界语废除汉字,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这一目标短期内难以实现。他曾公开声明:“我固然是主张中国当废汉文而用Esperanto之一人,但我以为这是将来圆满之解决。若讲现在,则Esperanto尚在提倡时代,未至实行时代;……我虽极力主张Esperanto,然事实如此,不能讳言”[30],并且表示:“我以为中国废汉文而用Esperanto,这是将来圆满之解决。当此过渡时代,汉文尚未废灭,便不可不想改良的办法”[31]。具体说来,他所谓“改良的办法”即是推行国语罗马字。
所谓“国语罗马字”,原本是作为一种注音符号提出来的,也就是用罗马字母来为汉字注音,类似此前所述的注音字母。对此,钱玄同最初并不抱有多大的兴趣。他虽然承认“中国现在应该兼用罗马字母和注音字母两种来标音”,这是“因为罗马字母,已经变成现世界公用的音标;凡其国有特别形式之文字者,若把他的语言和名词行于国外,都要改用罗马字母去拼他的音,……我们中国向来没有纯粹的音标,现在急须新制,当然应该采用罗马字母,这是无庸致疑的”;但他同时也客观指出,“因为中国字是直行的,罗马字母只能横写”,二者存在形式上的矛盾,而且“罗马字母记音的方法,……长短不大相同”,记在汉字旁边往往会参差不齐,于是“这就不能不用注音字母的了”[32]。此外,钱玄同还认为罗马字母“单音之词太多,一义有数字”,不如“旁注‘注音字母’”。[33]
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人则开始主张罗马字母不仅是一种注音符号,而且还应当在此基础上演变成为一种取代汉字的文字。对于这种主张,当时竭力倡导世界语的钱玄同也不赞同,他表示:“至于汉字之代兴物,我以为与其制造罗马字母的新汉字,远不若采用将来人类公用的Esperanto。……我以为采用Esperanto与采用外国语,比制造什么罗马字母的新汉字,上算得多,有用得多”[34]。他还具体解释说:“我的意思,以为中国方音之庞杂,同音字之多,文法之不精密,新学名词之缺乏,都是难以改用拼音的理由。所以中国要造拼音文字,断非旦夕之间就能完全告成的。……假如我这句话还有几分道理,则与其改华文为拼音,不如老实提倡一种外国文为第二国语,……似乎也不必定要改用罗马字来的拼音。”[35]
概言之,钱玄同此时在记音符号上倾向于注音字母,在新文字上则大力提倡世界语,对罗马字母并不抱多大兴趣。而随着实践经验的丰富,他的这一看法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开始认识到注音字母的缺陷以及推行世界语的困难。如注音字母虽是建立在章太炎创制的基础上,具有较为充分的学理依据,然而由于它仍采用汉字的基本形式,难以与国际接轨,尤其是在译介外来术语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鉴于此,钱玄同提出:“若承认中国应该和世界文化不隔膜,应该设法补救国语贫乏的缺陷,而主张无限制的采纳外国的词儿并且直写原字到国语中来,则非将国语改用罗马字母式的字母拼音不可。……简单一句话,就是注音字母虽然是改革过了的汉字,虽然是拼音的字母,但和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还是隔了一层。”[36]相比之下,“中国拼音字用了罗马字母,采用西文原词,真如天衣无缝,自然熨贴”。与此同时,钱玄同还觉得注音字母“形式不甚方便,也不大美观,印刷和书写都不如罗马字母”。由是,他最终概括说:“因为要图形式美观,书写便利,表音精确,所以要提倡国语罗马字。因为要与现世界的文化学术融合,有尽量采用西文原词之必要,所以要提倡国语罗马字。”[37]总之,“汉语一日未废,即一日不可无表汉语之记号。此记号,自然以采用罗马字拼音为最便于写识”[38]。这无疑意味着在记音符号上,他已经更倾向于罗马字母。
在新文字的选择问题上,这一时期的钱玄同尽管仍然坚信未来大同世界的语言必定是世界语,但也意识到短期内用世界语取代汉字的困难,因此他虽在《汉字革命》一文中将废除汉字的时间定为十年,但也深知这一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在日记中就写道:“汉字在将来总是废除成的,不过究竟是在若干年后,则此次没有把握,我那篇文章以十年为期,不过是聊作快语,以鼓励同志罢了,实际上恐未必能够这样称心如意。”[39]这说明他对这一问题有了较切合实际的认识。黎锦熙便说:“民九以后,他就觉得这种理想(指用世界语取代汉字——引者按)太高,的中国,只能提倡国语,而改革传达国语的文字工具使之‘世界化’,故专心致力于‘国语罗马字’了。”[40]
具体说来,钱玄同在1923年1月发表的《汉字革命》一文中就正式“把的新文字定名为‘国语罗马字’”[41]。同年,在国语研究会第五次常年大会上,钱玄同又提出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的议案,获得通过并出任委员。从此,他更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国语罗马字”研究和设计工作中去。1925年夏,他还与刘半农等人发起组织了“数人会”,专议“国语罗马字”问题。在他的积极推动之下,“国语罗马字”委员会终于在1926年9月14日制成通过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并于同年11月9日首先由国语统一筹备会公诸于世,1928年9月26日又由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将之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在全国范围内正式颁行。
对这份倾注了许多心血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钱玄同十分满意,他曾说明:“查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标音的分别,既不厌精详,拼切的形式,尤务求平易。信可谓斟酌尽善,毫发无憾之法式。”[42]客观地说来,这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建国后制定的、沿用至今的《汉语拼音方案》也正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1958年,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这篇报告中就肯定地指出: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一个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43]
地看来,钱玄同提倡国语罗马字的主张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转移了反对派的视线,从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1927年,鲁迅在回顾白话文运动时就说:“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除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44]
当然,钱玄同等人创制国语罗马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要取代汉字,他们批评汉字“为象形字之末流”,“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主张代之以西方的拼音文字,这事实上是一种“汉字落后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状况来看,汉字都具有自己的特色,拥有独特的优势,并非一种落后的文字。而随着文字改革深入开展,钱玄同也逐渐意识到短期内用国语罗马字取代汉字是不可能的,于是“对于汉文汉字的意见随后也有转变,不复坚持彻底的反对的意见了”[45],这尤其体现在他晚年将主要精力转向提倡“简体字”上。
三 提倡“简体字”
事实上,早在1920年,钱玄同便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中表示:“我以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间就能够制造成功的;更不是粗心浮气、乱七八糟把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所以这几年之内,只是拼音文字的制造时代,不是拼音文字的施行时代。……这拼音新文字的施行,总还在十年之后。如此,则最近十年之内,还是用汉字的时代。……既然暂时还不得不沿用汉字,则对于汉字难识难写的补救,是刻不容缓的了。”与此同时,他还表示:“我是很高兴做这件事的。”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出了“补救汉字难写”的办法,即提倡“简体字”,并将之归纳为八类:采取古字、采取俗字、采取草书、采取古书上的同音假借字、采取流俗的同音假借字、新拟的同音假借字、新拟的借义字、新拟和减省笔画字。“总而言之,抱定唯一的主张曰‘减省笔画’”[46]。
在此基础上,钱玄同在1922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常年大会上,正式提交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开篇即申明:“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这种根本改革,关系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目的的。……但现行汉字在学术上、上的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图补救的办法!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47]该议案很快顺利获得通过,并成立了以钱玄同为首席委员的“汉字省体委员会”,组织进行该项工作。
由此可见,在文字改革实践中,钱玄同已经认识到国语罗马字虽然是中国文字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就是所谓“治本”;但在汉字仍然存在时,则必须首先“治标”,即减省汉字的笔画,使之简单易写。关于这一点,黎锦熙曾深刻分析说:“钱先生邃于《春秋》公羊之学,有时也把‘三世’来推断当前的一切事理。”钱玄同自己也说:“世界化的‘国语罗马字’应该是‘太平世’的初步;现在中国社会还离不了汉字的环境,总须就汉字加以形体的改良和声音的帮助,所以选定‘简体字’……普遍通行,才可了结这‘升平世’之局。”[48]
钱玄同之所以提倡写“简体字”,除了深受“三世说”的影响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章太炎的启发。如前所述,1908年,章太炎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一方面驳斥用世界语废除汉字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承认汉字过于“深秘”,应逐步改良,使之“易能、易知”。他还提出具体方案:“欲使速于疏写,则人人当兼知章草。”[49]这对钱玄同显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曾公开说明:“一九〇八年,我在东京从余杭章太炎先生治声音训诂之学。那时有人主张中国当废汉字而用万国新语(即Esperanto,今译世界语)。余杭先生不以为然,著论驳斥。论中对于汉字的难识和难写,都想了补救的办法。……补救难写之法,则余杭先生主张采用章草。……我读了余杭先生这段文章,认定他这个主张是最切于实用的,是写汉字唯一的简便方法。……我二十年前读余杭先生之论而认定章草必应采用,此意至今信之益笃”[50],他后来所拟订的汉字简化方案也主要是采用草书,“所采之材料,草书最多”,“许多草体可以放胆增加,笔势从章草”[51]。
历史地看来,钱玄同尽管早在20年代初便已开始提倡“简体字”,并且拟订了有关方案,但由于简体字的编制需要收集大量的历史资料,以求“字字有来历”;而且当时钱玄同最关心的还是国语罗马字,所以并未立即展开简体字的实践工作。直到30年代中期,随着积累的不断丰富以及认识的逐渐深化,简体字才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34年,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钱玄同开始筹划编制《简体字谱》,经过一年抱病努力,终于在1935年5月编成了《常用简体字表》,并呈送教育部审定。8月21日,教育部根据这份《常用简体字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这是解放前由政府正式颁布的第一批规范简体字,为建国后制定《汉字简化方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近代语言文字的改革实践中,钱玄同虽曾提出过废除汉字的偏激主张,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但他很快就纠正了这一错误,并在罗马字拼音与简体字两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后人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他的学生徐世荣曾评价说:“试看现在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哪一项不是钱师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早着‘先鞭’了。说他是‘滥觞’也好,说他是‘草创’也好,说他是‘前驱’也好,反正现在如果上溯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的历史渊源,总不能遗忘这位树起‘汉语规范化’和‘汉字拼音化’的里程丰碑的闯将!”[52]今天看来,这一评价应是客观公允的。
注释:
[1]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2]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
[3][5][49]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338、351、344页。
[4]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6]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209、210、212页。
[7]章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
[8]章太炎:《诛政党》,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6页。
[9]《钱玄同日记》第1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10][11]《钱玄同日记》第2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72、844-845页。
[12]钱玄同:《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13]《钱玄同日记》第3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9页。
[14][16][18][22][23][24][26][27][28][30][31][32][33][34][35][38][46]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1、166-167、276-277、101-102、234-235、163、203、202、20、336、276、333、68、212、220、284-285、212、400-404页。
[15][17]《钱玄同日记》第4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2、1707页。
[19][36][37][47][51][42]《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80、388-391、85、496-498、294-295页。
[20][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53页。
[21][英]帕默尔著、李荣等译《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1页。
[25]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3页。
[29][40][41][45] [48]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0、48、15、53页。
[39]《钱玄同日记》第5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5页。
[43]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页。
[44]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50]钱玄同:《<章草考>序》,《钱玄同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49页。
[52]徐世荣:《序》,曹述敬编《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