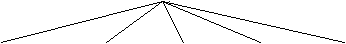楚简“ ”字及相关诸字考释评议
包山楚简和郭店楚简中有个从“言”从“菐”的字,还有许多形体相近或相关的字,现在我们把有关形体按构件的分布和辞例的用法整理如下:
相关的未确释字
1、辛——![]()
![]() 五行
五行
2、水+[辛+水]——![]()
![]() 五行
五行![]() (合文上部)性自命出
(合文上部)性自命出
3、業+攴——![]() 、
、![]() 语丛四
语丛四
4、[業+攴]+米——![]()
![]() 包山(原释“米+敖”)
包山(原释“米+敖”)
5、言+菐——![]()
![]()
![]()
![]() 包山
包山![]()
![]() 五行
五行![]() 穷达以时
穷达以时![]() 语丛一
语丛一
6、菐+戈——![]() 性自命出
性自命出
7、菐+刀——![]()
![]() 包山(原释“
包山(原释“![]() ”)
”)
8、口+[菐+戈]——![]() 成之闻之
成之闻之![]()
![]() 尊德义
尊德义
9、心+[菐+戈]——![]() 性自命出
性自命出
相关的已确释字
10、菐(僕)+臣——![]()
![]()
![]() 包山
包山![]()
![]()
![]() 老甲
老甲![]() 语丛二
语丛二
11、[菐+臣]+木——![]()
![]() 老甲
老甲
12、邑+菐(僕)——![]()
![]()
![]()
![]()
![]()
![]()
![]() 包山(第七形原释“業”)
包山(第七形原释“業”)
13、糸+菐——![]() 包山
包山
14、金+菐——![]() 包山
包山
上述各字中都包含着一个上部作三点竖或四点竖的近似形体,为了指称方便,我们统一用“D”来表示这个形体。跟这个“D”形相近相关的字,古文字中有“菐(pu)”、“業”、“丵(zhuo)”、“对”、“辛(qian)”等,因而关于从“D”诸字的释读,围绕这些相关的字先后提出了十多种考释意见[i]。我们在《包山楚简“言+菐”义解诂》[ii]一文中初步认为从“言”从“D”之字的“D”相当于“菐”,并考定这个“言+D”字所记录的词的意义是对已知事情或证据的检查、勘验、核实、确认,但没有指明这个字的用法是本用还是借用,也没有说明它跟有关字词的关系,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言+D”字的本音本义。我们认为,对文本中疑难字词的考释,应该做到形、音、义(本义)、用(文本中记录的词义)四个方面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能够涵盖所有的变体和全部的辞例,才能算是完全的和成功的考释,否则就是一种不完全考释或有疑问的考释。下面我们从“言+D”的释读出发,联系相关字形,分析时贤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看看其中有哪些合理的因素,又可能存在哪些问题。
(一)不少人认为“D”是“對”字的左边,所以把从“言”从“D”的原形楷定为“![]() ”、“
”、“![]() ”或“對”,各家都读为“對”,但释义有“应对”、“招供”、“作证”、“证实”、“查问”等不同说法[iii]。刘信芳先生认为“言+D”就是“對”字的异体,解为对簿、对状、对证、查对之义[iv]。这种释读只适合部分字形和部分辞例。就字形说,既然“言+D”读“對”音,那实际上应该是“D”与整个“對”字相当,严格来说当楷定为“譵”,或分析为从“對”省。因为“
”或“對”,各家都读为“對”,但释义有“应对”、“招供”、“作证”、“证实”、“查问”等不同说法[iii]。刘信芳先生认为“言+D”就是“對”字的异体,解为对簿、对状、对证、查对之义[iv]。这种释读只适合部分字形和部分辞例。就字形说,既然“言+D”读“對”音,那实际上应该是“D”与整个“對”字相当,严格来说当楷定为“譵”,或分析为从“對”省。因为“![]() ”不独用,在“對”字中不是音符,因而不能代表“對”的读音。“對”字原本从丵从土从又(或廾或丮),《金文编》157、158页所收“對”字有少数不从“土”的形体,可能是“對”的简写,也可能是“對”的声旁借用。这种不从“土”的“對”可以跟楚简中从“又”或从“廾”的“D”沟通;但无法解释来自“對”的“D”何以会从“人”(刀)从“大”(矢),有时还“人”(刀)“又”并出,因为“人”(刀)、“大”(矢)的形体是“對”字无由演化的。忽视同功能字形的总体而仅仅根据其中个别形体的相似就把“D”跟“對”完全等同起来,是不符合构形系统性原则的。就用法来说,先秦中的“對”一般作“对扬”(见于金文)、“对答”、“对比”讲,罕见用于司法语义的例子。汉代以后“對”确实有了对簿、对状、对证、查对之类的意义,用来解释包山简的用例勉强可行,但读为“對”或者看作“對”的异体,根本无法讲通郭店楚简的相关用例。
”不独用,在“對”字中不是音符,因而不能代表“對”的读音。“對”字原本从丵从土从又(或廾或丮),《金文编》157、158页所收“對”字有少数不从“土”的形体,可能是“對”的简写,也可能是“對”的声旁借用。这种不从“土”的“對”可以跟楚简中从“又”或从“廾”的“D”沟通;但无法解释来自“對”的“D”何以会从“人”(刀)从“大”(矢),有时还“人”(刀)“又”并出,因为“人”(刀)、“大”(矢)的形体是“對”字无由演化的。忽视同功能字形的总体而仅仅根据其中个别形体的相似就把“D”跟“對”完全等同起来,是不符合构形系统性原则的。就用法来说,先秦中的“對”一般作“对扬”(见于金文)、“对答”、“对比”讲,罕见用于司法语义的例子。汉代以后“對”确实有了对簿、对状、对证、查对之类的意义,用来解释包山简的用例勉强可行,但读为“對”或者看作“對”的异体,根本无法讲通郭店楚简的相关用例。
(二)葛英会先生认为“D”是“菐”字,所以把原形楷定为“言+菐”,当做见于《集韵》的“言+僕”,训“以言蔽也”。但他认为此义难通,故读作《尚书·康诰》“丕蔽要囚”的“蔽”,引《论语》“一言以蔽之”何晏注“蔽”犹“当”,而“当”《小尔雅》有“断”之训,所以确定“言+菐”用为“断”义[v]。但“菐”声字借用为“蔽”字,古音屋部月部远隔,恐怕难以相通。而且把“言+菐”读作“蔽”而训“断”,只能勉强讲通包山简15反的“新俈迅尹不为其![]() ”一句,包山简其它的用例都明显属于查核,不宜直接讲成断决。至于郭店楚简的用例就更不能讲成“断”了。所以葛先生释字为“言+菐”,虽然没有从形体上详加论证,却是很有见地的(理由见《考辨》[vi]一文),但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义训上的问题。
”一句,包山简其它的用例都明显属于查核,不宜直接讲成断决。至于郭店楚简的用例就更不能讲成“断”了。所以葛先生释字为“言+菐”,虽然没有从形体上详加论证,却是很有见地的(理由见《考辨》[vi]一文),但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义训上的问题。
(三)认为“D”是“業”,所以把原形楷定为“言+業”,而以“業”声字阴阳对转而读作“验”。此说先由胡平生先生提出[vii],最近许学仁先生也赞成这一说法,并作了补充论述[viii]。先秦文献中的“验”确有检验、验证的义项,且多与有关,而“验”字从“马”,《说文解字》训其本义为“马名”,可见这种用法属于借用。如果把包山楚简的“言+業”当作“验”的本字倒是很合适的,但要解通郭店楚简中的全部用例就会很为难。而且更重要的是形体上讲不过去。“業”字的形体现在能见到的有“![]()
![]()
![]()
![]() ”(古文字字形表98页)、“
”(古文字字形表98页)、“![]() ”(金文编724页)、“
”(金文编724页)、“![]() ”(金文编1186页)、“
”(金文编1186页)、“![]() ”(上博楚简《诗论》第5简)等,其基本构形是下部从木或从大,大、木在古文字中常互讹(如“樂”字下部既有从木的写法也有从大的写法),大又可以讹成交、火、矢,所以这些形体都是可以贯通的。第3、4组字所从的“D”是可以跟“業”字认同的,但在“言+D”字的各种写法中只有一个下部从“矢(大)”的写法跟“業”字相关,而其它各种写法与“業”字是没有关系的,如果都是从“業”,怎么解释这些无关形体的变异呢?也许有人会说“D”下的“廾”可以看作是“業”下“大”的变化,其实不然,我们知道“廾”变异为“大”是隶变的结果,隶变之前“廾”与“大”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即使是隶变,也只能“廾”变为“大”,没有“大”变为“廾”的现象,这是不能逆推的。“人”可以变从“大”,而“大”通常不换从“人”,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在做字形认同的时候,应该从相关字的总体着眼,并且要注意演变的方向和时代。
”(上博楚简《诗论》第5简)等,其基本构形是下部从木或从大,大、木在古文字中常互讹(如“樂”字下部既有从木的写法也有从大的写法),大又可以讹成交、火、矢,所以这些形体都是可以贯通的。第3、4组字所从的“D”是可以跟“業”字认同的,但在“言+D”字的各种写法中只有一个下部从“矢(大)”的写法跟“業”字相关,而其它各种写法与“業”字是没有关系的,如果都是从“業”,怎么解释这些无关形体的变异呢?也许有人会说“D”下的“廾”可以看作是“業”下“大”的变化,其实不然,我们知道“廾”变异为“大”是隶变的结果,隶变之前“廾”与“大”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即使是隶变,也只能“廾”变为“大”,没有“大”变为“廾”的现象,这是不能逆推的。“人”可以变从“大”,而“大”通常不换从“人”,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在做字形认同的时候,应该从相关字的总体着眼,并且要注意演变的方向和时代。
(四)董莲池先生根据《古文四声韵》所收“辩”字有省与不省二体,且所从“辛”旁下作“人”形,因而认定楚简的“言+D”和《五行》中独用的“D”是“辩”字省形,这些“D”都应分析为上从“辛”下从“人”,如“![]() ”字的右边是由“辛”下的两斜笔和“人”字的两斜笔合笔交叉连写而成。他认为《说文》小篆从“言”“辡”声的“辩”原本是两个带“辛”的罪人相与讼,所以“辡”下实省掉了两个“人”字,因其讼争,故又从“言”。至于意义,郭店简都读作“辨”,训明察;包山简则或训明察,或训判决,或训审理,或训辩解,或读为“徧”而训周遍[ix]。董说是经过了认真考论的,初看好象形音义用都有着落。但仔细追究,也有难以信从的地方。第一,古文字中未见有从两“辛”两“人”的“辩”字,甲骨金文中倒是有上从两辛而下从两人或两大或两兄的字(见《古文字字形表》97页,《金文编》152页,《甲骨金文字典》199页),但那个字公认为“競”,音义都跟“辩”字无关。另有跟“辩”同从“辡”声的“辨”字,所从“辡”字却没有两个人(见《金文编》289页,《汉语古文字字形表》163页,《甲骨金文字典》328页),而且“宰”字所从的“辛”表示罪人却也不从“人”。因此说“辩”所从之“辡”原本有两“人”而小篆省略了,缺乏实证。《古文四声韵》这种后代字书所收的字形可以作为线索和,如作为唯一的证据就显得薄弱。实际上古人写“辛”字有时在下面的竖画旁加一斜笔作装饰,后来讹变使得“辛”的下部有时候既像“刀”又像“人”,《古文四声韵》《汗简》等所收“辛”和从“辛”之字的这类形体就是这么来的,其实并非从“人”或从“刀”。第二,董文认为“辩”是从“辛”从“人”从“言”会意,则其中上“辛”下“人”的构件不能表音。可是郭店简还有个“
”字的右边是由“辛”下的两斜笔和“人”字的两斜笔合笔交叉连写而成。他认为《说文》小篆从“言”“辡”声的“辩”原本是两个带“辛”的罪人相与讼,所以“辡”下实省掉了两个“人”字,因其讼争,故又从“言”。至于意义,郭店简都读作“辨”,训明察;包山简则或训明察,或训判决,或训审理,或训辩解,或读为“徧”而训周遍[ix]。董说是经过了认真考论的,初看好象形音义用都有着落。但仔细追究,也有难以信从的地方。第一,古文字中未见有从两“辛”两“人”的“辩”字,甲骨金文中倒是有上从两辛而下从两人或两大或两兄的字(见《古文字字形表》97页,《金文编》152页,《甲骨金文字典》199页),但那个字公认为“競”,音义都跟“辩”字无关。另有跟“辩”同从“辡”声的“辨”字,所从“辡”字却没有两个人(见《金文编》289页,《汉语古文字字形表》163页,《甲骨金文字典》328页),而且“宰”字所从的“辛”表示罪人却也不从“人”。因此说“辩”所从之“辡”原本有两“人”而小篆省略了,缺乏实证。《古文四声韵》这种后代字书所收的字形可以作为线索和,如作为唯一的证据就显得薄弱。实际上古人写“辛”字有时在下面的竖画旁加一斜笔作装饰,后来讹变使得“辛”的下部有时候既像“刀”又像“人”,《古文四声韵》《汗简》等所收“辛”和从“辛”之字的这类形体就是这么来的,其实并非从“人”或从“刀”。第二,董文认为“辩”是从“辛”从“人”从“言”会意,则其中上“辛”下“人”的构件不能表音。可是郭店简还有个“![]() ”字,其左边正好是上辛下人,那这里是会意还是表音呢,怎么跟“辩”字的构形分析沟通呢?而且如果把“辩”看成会意字,那要把《五行》中独用的“D”直接释为“辩”就不可能是借音而只能是省写了,说“言+D”是“辩”省去了一个重复的构件还有可能,而把“D”也看作“辩”字之省,那恐怕省得有点过份了。第三,按照上“辛”下“人”的分析,即使同意董先生把“辛”下的两斜笔“V”和“人”形的两斜笔共四笔一径变作两个交叉斜笔连写的说法,也只能解释部分形体,像《五行》的
”字,其左边正好是上辛下人,那这里是会意还是表音呢,怎么跟“辩”字的构形分析沟通呢?而且如果把“辩”看成会意字,那要把《五行》中独用的“D”直接释为“辩”就不可能是借音而只能是省写了,说“言+D”是“辩”省去了一个重复的构件还有可能,而把“D”也看作“辩”字之省,那恐怕省得有点过份了。第三,按照上“辛”下“人”的分析,即使同意董先生把“辛”下的两斜笔“V”和“人”形的两斜笔共四笔一径变作两个交叉斜笔连写的说法,也只能解释部分形体,像《五行》的![]() 下部根本不是交叉的两个斜笔,而是“又”字的一种常见写法,《包山》的
下部根本不是交叉的两个斜笔,而是“又”字的一种常见写法,《包山》的![]() 在交叉的两斜笔之下却另有“人(刀)”形,这些都是无法迁就合笔连写说的。至于说
在交叉的两斜笔之下却另有“人(刀)”形,这些都是无法迁就合笔连写说的。至于说![]() 、
、![]() 等只能认定为从“又”从“廾”的形体“当是受菐形影响而讹写造成的”,则更有武断之嫌。再说意义,包山简“言+D”的用例语境其实比较统一,除137号简有点特殊之外,都是指对已知事情或证据的查验、核实,先秦的“辩”字虽有“明察”“分辨”“争辩”等义,却没有“调查、检验、查证、核实”的用法,所以并不完全适合包山简的辞例。
等只能认定为从“又”从“廾”的形体“当是受菐形影响而讹写造成的”,则更有武断之嫌。再说意义,包山简“言+D”的用例语境其实比较统一,除137号简有点特殊之外,都是指对已知事情或证据的查验、核实,先秦的“辩”字虽有“明察”“分辨”“争辩”等义,却没有“调查、检验、查证、核实”的用法,所以并不完全适合包山简的辞例。
(五)刘信芳先生原来是把“言+D”释作“![]() ”而看成“對”的异体字的,后来改释为“
”而看成“對”的异体字的,后来改释为“![]() ”,即把“D”看成《说文解字》训为“丛生草”而“读若浞”的“丵”(zhuo)字。认为这个字从言丵声,借用为“督”字[x]。根据人归纳的古音音系,“丵”从纽药部,“督”端纽觉部,语音虽然隔了一层,总还可以算是相近。“督”字也确实有“查验、核实、考察”之类的用法,可以跟“察”同义,后代的“督察”即是同义复合语。所以用“督”来解读楚简的“言+D”大部分辞例是勉强能说得过去的。但是,“丵”(zhuo)的音义仅见于字书,文献中从无单用的例子,古文字中也只有《说文》所分析的小篆“叢”跟这个“丵”(zhuo)的所谓“丛生草”的意义相关,其它的“丵”形都被认为是“辛”的变体,表示“凿”具[xi]。然则字书中“丵”(zhuo)的读音并没有语言实证,本身都成问题,怎么能拿来证明“
”,即把“D”看成《说文解字》训为“丛生草”而“读若浞”的“丵”(zhuo)字。认为这个字从言丵声,借用为“督”字[x]。根据人归纳的古音音系,“丵”从纽药部,“督”端纽觉部,语音虽然隔了一层,总还可以算是相近。“督”字也确实有“查验、核实、考察”之类的用法,可以跟“察”同义,后代的“督察”即是同义复合语。所以用“督”来解读楚简的“言+D”大部分辞例是勉强能说得过去的。但是,“丵”(zhuo)的音义仅见于字书,文献中从无单用的例子,古文字中也只有《说文》所分析的小篆“叢”跟这个“丵”(zhuo)的所谓“丛生草”的意义相关,其它的“丵”形都被认为是“辛”的变体,表示“凿”具[xi]。然则字书中“丵”(zhuo)的读音并没有语言实证,本身都成问题,怎么能拿来证明“![]() ”的读音而推知它是“督”的借字呢?另一方面,字形上被《说文解字》分析为“象丵嶽相并出”的“丛生草”的“丵”,怎么会变出从又、从廾、从人(刀)、从大(矢)的各种写法来了呢,其演变过程同样难以证实。
”的读音而推知它是“督”的借字呢?另一方面,字形上被《说文解字》分析为“象丵嶽相并出”的“丛生草”的“丵”,怎么会变出从又、从廾、从人(刀)、从大(矢)的各种写法来了呢,其演变过程同样难以证实。
(六)黄锡全先生把“D”的形体分析为“上面四短竖,中间一横,下面一个叉”,认为这一形体来源于甲骨文中的“带”(见《甲骨文编》附录789页或《甲骨文合集》20502、13945、26879等号),只是省去了字形的下部,还举了子犯编钟和古玺做例子,因而把原形楷定为“言+带”,训“审查”义[xii]。《集韵·霁韵》:“谛,《说文》:‘审也。’或从带。”原来“言+带”是“谛”的异体字,所以有“审”义。“谛”与“审”“察”“督”皆有相同的义项,用来讲解楚简辞例不是不可以,但字形上难以说通。因为作“上面四短竖,中间一横,下面一个叉”的只是部分形体,还有下面并不是“叉”而是从“人(刀)”、从“大(矢)”、从“廾”或既有“叉”(实际上是“又”)又有“人(刀)”的种种写法,怎么说明它们跟“带”字的关系?而且黄先生所举用来类比的字形其实尚存争议,目前战国以前的文字里还没有发现已经确释而得到大家公认的“带”字。楚简中倒是真有“带”和从“带”的字,但其“带”字大都下从“巾”,偶尔也有跟“![]() ”字所从“D”形相近的写法,但右下四点之间不是一笔,而是有点象“丩”的两笔,区别仍然很明显。所以要把“D”字跟“带”字认同是很困难的。
”字所从“D”形相近的写法,但右下四点之间不是一笔,而是有点象“丩”的两笔,区别仍然很明显。所以要把“D”字跟“带”字认同是很困难的。
(七)裘锡圭先生读作“察”,刘钊先生等依从并加补证。郭店楚简《五行》篇“思不清不![]() (下文用A代表这个字形),……清则A,A则安”,马王堆帛书《五行》中相应的句子作“思不睛不察,……睛则察,察则安”,郭店简《五行释文注释》注释[七]说:“裘按:帛书本与此字相当之字为‘察’,简文此字似亦当读为‘察’。此字在包山简中屡见,读为‘察’,义皆可通。”又郭店简《语丛四》:“
(下文用A代表这个字形),……清则A,A则安”,马王堆帛书《五行》中相应的句子作“思不睛不察,……睛则察,察则安”,郭店简《五行释文注释》注释[七]说:“裘按:帛书本与此字相当之字为‘察’,简文此字似亦当读为‘察’。此字在包山简中屡见,读为‘察’,义皆可通。”又郭店简《语丛四》:“![]() (下文用B代表这个字形)钩者诛,B邦者为者(诸)侯。者(诸)侯之门,义士之所廌(存)。”该篇注释[七]:“裘按:此段内容与见于《庄子·胠箧》的下引文字基本相同:‘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简文第一、五二字左旁,与本书《五行》中应读为‘察’的从‘言’之字的右旁相近。包山楚简中应读为‘察’的从‘言’之字,其右旁并有与此字左旁极相似者,可知此字之音与‘察’相近。‘窃’‘察’古通,故此字可读为‘窃’。”又郭店简《五行》:“心曰唯,莫敢不唯;如(诺),莫敢不如(诺)。进,莫敢不进;后,莫敢不后。深,莫敢不深;
(下文用B代表这个字形)钩者诛,B邦者为者(诸)侯。者(诸)侯之门,义士之所廌(存)。”该篇注释[七]:“裘按:此段内容与见于《庄子·胠箧》的下引文字基本相同:‘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简文第一、五二字左旁,与本书《五行》中应读为‘察’的从‘言’之字的右旁相近。包山楚简中应读为‘察’的从‘言’之字,其右旁并有与此字左旁极相似者,可知此字之音与‘察’相近。‘窃’‘察’古通,故此字可读为‘窃’。”又郭店简《五行》:“心曰唯,莫敢不唯;如(诺),莫敢不如(诺)。进,莫敢不进;后,莫敢不后。深,莫敢不深;![]() (下文用C代表这个字形),莫敢不C。”注释[六三]:“裘按:此句(指最后一句)首尾各有一从‘水’的相同之字,似当读为‘浅’。它们的右旁据帛书本当读为‘察’。‘察’、‘窃’古通。‘窃’、‘浅’音近义通。《尔雅·释兽》‘虎窃毛谓之戋+虎猫’郭注:‘窃,浅也。’”“某读为某”实际上是“某借为某”的换一种说法,可见注者是把“言+D”当作“察”的借字的。广濑熏雄先生就直接说“言+D”是“察”的假借字[xiii],反映的正是裘注的观点。这种释读由于有“言+D”字跟“察”字的异文为证,而且还发现了跟“察”读音相近形体也相关的“窃”和“浅”,所以得到广泛赞同。如刘钊先生就认为裘说“有内容相同的帛书或传世典籍的对照,可以肯定是确切无疑的”[xiv]。
(下文用C代表这个字形),莫敢不C。”注释[六三]:“裘按:此句(指最后一句)首尾各有一从‘水’的相同之字,似当读为‘浅’。它们的右旁据帛书本当读为‘察’。‘察’、‘窃’古通。‘窃’、‘浅’音近义通。《尔雅·释兽》‘虎窃毛谓之戋+虎猫’郭注:‘窃,浅也。’”“某读为某”实际上是“某借为某”的换一种说法,可见注者是把“言+D”当作“察”的借字的。广濑熏雄先生就直接说“言+D”是“察”的假借字[xiii],反映的正是裘注的观点。这种释读由于有“言+D”字跟“察”字的异文为证,而且还发现了跟“察”读音相近形体也相关的“窃”和“浅”,所以得到广泛赞同。如刘钊先生就认为裘说“有内容相同的帛书或传世典籍的对照,可以肯定是确切无疑的”[xiv]。
裘先生的说法对讲通有关辞例确实很管用,但还留下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证实。第一,如果“A”是“察”的借字,那“A”究竟是个什么字,它的本义是什么,文献中有这个词的用例吗?第二,如果“A”“B”“C”中的“D”是同一个构件,表示相同或相近的读音,那这个“D”究竟是什么字,本来应该读什么音,这个读音跟“察”相同或相近吗?第三,“A”“B”“C”中的“D”的各种不同形体(见第2组至第5组)是怎么变化来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大而整齐的差异?它们跟楚简中已经确释的读“pu”音的“D”(见第10至第14组)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言+D”中的“D”总体上会跟已知读“pu”音的“D”写法那么一致?这三个问题分别反映了义(构形本义)、音、形三个方面,总起来说就是一个字源问题。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裘说也只能算是假说。如果仅仅因为帛书本的异文就断定“A”当读为“察”,仅仅因为《庄子》的异文就断定“B”可读为“竊”,亦即“A”为“察”的借字、“B”为“竊”的借字,其实是难以让人信服的。顺便就可以举出个反证:上引《语丛四》“B邦者为者侯”《庄子·胠箧》作“窃国者为诸侯”,“邦”与“国”也是异文,我们能说“邦”是“国”的借字吗?显然不能[xv]。而且这段话还见于《庄子·盗跖》篇,作“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然则“B”又与“盗”为异文,是否又该说“B”应读为“盗”呢?其实刘钊先生自己也明白异文不能证明同音或同字的道理,他曾否定有人根据帛书异文把郭店《五行》篇“不D于道”的“D”释为“辩”,理由就是“郭店楚简的‘察’字在马王堆帛书中作‘辩’是同义换用,并不能证明郭店简的‘察’也应释‘辩’”[xvi],为什么到了“A”要读“察”、“B”要读“竊”时,就因为“有内容相同的帛书或传世典籍的对照,可以肯定是确切无疑的”了呢?作为异文,“甲”字可能是“乙”字的异体字或同义字,即使“甲”是借字,也不一定就是异文“乙”的借字,还有可能是借用为“乙”的某个同义字“丙”,“乙”也可能是借用为“甲”的某个同义字“丁”。例如《包山楚简》用来纪年的句子“东周之客许呈至胙于戚郢之岁”,其中的“至”字同书又作“归”字,这是一组很典型的异文材料,但我们不能据此认定“至”就是“归”的借字或者“归”是“至”的通假字。其实这里的“至”和“归”用的都是借字,“至”借为“致”,“归”借为“馈”,然则“至”和“归”本身并没有形音义上的关联,而是因为它们各自的本字“致”和“馈”具有同义关系才构成异文的。可见仅用异文来证明“A”是“察”的借字(通假字)是靠不住的。
那么,“A”“B”“C”三个字的偏旁“D”形体相近,是否就一定是同一个声符,它们的读音就一定得相同或相近、因而“A”就一定得读为“察”呢?恐怕也未必。首先,这三个字中被看作同一构件的“D”其实形体并不完全相同:左边从“水”的两个字样(第2组)右下也都明显从“水”;右边从“攴”的四个字样(第3和第4组)左下都明显从“大(矢)”;左边从“言”的字样较多(第5组),除包山简有个“![]() ”的写法其右下跟从“攴”的“B”的左下偶然相同即都从“大”(矢)外,还有右下从“又”(“又”的左向斜笔跟上部的横画相连)从“廾”和同时从“又”从“人(刀)”的写法。就构形的系统性看,这三组字形中的“D”特别是下部从“水”的“D”形体上是很难沟通的。这样一来,要用“B”“C”跟“A”所从“D”的同形关系证明“A”当读为“察”也就失去了依据。其次,即使这三个字中的“D”形体上可以认同,也不能证明它们的读音就一定相同或相近,因为汉字中存在大量的同形字和同形构件,即形体相同而读音和意义并不相同。且不说隶变以后的偏旁混同现象,战国以前同形字和同形构件就已经普遍存在了。如古文字中的“舟”是既可以表示船(读zhou)也可以表示盘(读pan)的,“幺”是既可以读“you”(幼小)也可以读“si”(丝线)的。楚文字“丑”“升”不分,“贝”“目”相混,“人”“刀”难别,“夕”“月”任作。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D”形,如果“A”中的“D”因为跟“B”和“C”的“D”形近就应该读音相同的话,那楚简中还有一系列后来读作“pu”的从“菐”的字,如“僕”、“樸”、“菐+阝”、“镤”、“糸+菐”(第10至14组)等,就更应该读音相同了,因为它们所从的“菐”从总体上来说跟“言+D”中的“D”形体几乎完全相同,那是不是这些公认读“pu”的字也应该读“察”?既然“僕”等可以跟“B”“C”读音不同,为什么“A”就一定要跟“B”“C”读音相同或相近呢?第三,即使“A”“B”“C”三字中的“D”确实读音相同,而且确实“‘察’‘窃’古通,‘窃’‘浅’音近义通”,那也只能证明“A”有可能读为“察”,而不能证明“A”必然要读为“察”。因为如果“A”是“察”的本字或异体字,那也符合这几个字读音相同相近的条件;如果“A”是“察”的同源同义字(就像“命”跟“令”的关系),那同样符合这几个字读音相同相近的条件;甚至可以反过来,“察”是借字而“A”是本字,那仍然符合这几个字读音相同相近的条件。
”的写法其右下跟从“攴”的“B”的左下偶然相同即都从“大”(矢)外,还有右下从“又”(“又”的左向斜笔跟上部的横画相连)从“廾”和同时从“又”从“人(刀)”的写法。就构形的系统性看,这三组字形中的“D”特别是下部从“水”的“D”形体上是很难沟通的。这样一来,要用“B”“C”跟“A”所从“D”的同形关系证明“A”当读为“察”也就失去了依据。其次,即使这三个字中的“D”形体上可以认同,也不能证明它们的读音就一定相同或相近,因为汉字中存在大量的同形字和同形构件,即形体相同而读音和意义并不相同。且不说隶变以后的偏旁混同现象,战国以前同形字和同形构件就已经普遍存在了。如古文字中的“舟”是既可以表示船(读zhou)也可以表示盘(读pan)的,“幺”是既可以读“you”(幼小)也可以读“si”(丝线)的。楚文字“丑”“升”不分,“贝”“目”相混,“人”“刀”难别,“夕”“月”任作。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D”形,如果“A”中的“D”因为跟“B”和“C”的“D”形近就应该读音相同的话,那楚简中还有一系列后来读作“pu”的从“菐”的字,如“僕”、“樸”、“菐+阝”、“镤”、“糸+菐”(第10至14组)等,就更应该读音相同了,因为它们所从的“菐”从总体上来说跟“言+D”中的“D”形体几乎完全相同,那是不是这些公认读“pu”的字也应该读“察”?既然“僕”等可以跟“B”“C”读音不同,为什么“A”就一定要跟“B”“C”读音相同或相近呢?第三,即使“A”“B”“C”三字中的“D”确实读音相同,而且确实“‘察’‘窃’古通,‘窃’‘浅’音近义通”,那也只能证明“A”有可能读为“察”,而不能证明“A”必然要读为“察”。因为如果“A”是“察”的本字或异体字,那也符合这几个字读音相同相近的条件;如果“A”是“察”的同源同义字(就像“命”跟“令”的关系),那同样符合这几个字读音相同相近的条件;甚至可以反过来,“察”是借字而“A”是本字,那仍然符合这几个字读音相同相近的条件。
《郭店楚墓竹简·五行》篇“不D于道也”的“D”,马王堆帛书有异文作“辩”,因而关于这个“D”字的释读就存在两难选择:若强调这个“D”跟“言+D”等字的形体联系而读为“察”,就不得不舍弃异文,若强调异文而读为“辩”,又不得不放弃跟“言+D”等字的形体联系。刘钊先生认为这个“D”就是“A”等合体字的偏旁,故“不D于道”即“不察于道”,“但是这个字在马王堆帛书中写作‘辩’,于是有人认为郭店简的这个字也应释为‘辩’。其实古代‘察’、‘辩’二字可以互训,皆有‘分辩’之义。……郭店楚简的‘察’字在马王堆帛书中作‘辩’是同义换用,并不能证明郭店简的‘察’也应释‘辩’”[xvii]。上文已经提到,刘先生对“D”字异文的态度跟他强调“A”等字的释读“有内容相同的帛书或传世典籍的对照,可以肯定是确切无疑的”的态度是矛盾的。裘锡圭先生针对原注释[五十]“简文此字当读作察”加按语说:“此字之形与当读为‘察’的从‘言’之字的右旁有别。帛书本与之相当之字为‘辩’。待考。”虽说是“待考”,但从裘先生强调“此字之形与当读为‘察’的从‘言’之字的右旁有别”来看,他其实是不同意“D”读作“察”而倾向于“D”读为“辩”的。但从前文的原形对照可以看出,这个“D”跟“当读为‘察’的从‘言’之字的右旁”的差别其实并不比“当读为‘察’的从‘言’之字的右旁”相互之间,以及被认为跟“当读为‘察’的从‘言’之字”具有同一声符因而当读为“浅”和“竊”的几个字形之间的差别大。如果“![]() ”“
”“![]() ”“
”“![]() ”跟“
”跟“![]() ”“
”“![]() ”这些显然差别很大的形体都能统一起来而“读作察”,那《五行》的“
”这些显然差别很大的形体都能统一起来而“读作察”,那《五行》的“![]() ”看起来不是跟“
”看起来不是跟“![]() ”“
”“![]() ”等字的“D”更为接近吗,为什么反而说它们“有别”而不能读作“察”呢?这种对形近字时而求同时而求异的态度也是模棱的。既然刘先生认为异文不能证明“D”必读“辩”,形近才决定“D”应读“察”,而裘先生又倾向形近不能证明“D”必读“察”,异文才决定“D”当读“辩”,那就说明异文和形近字对于判定文字的释读作用都是很有限的。
”等字的“D”更为接近吗,为什么反而说它们“有别”而不能读作“察”呢?这种对形近字时而求同时而求异的态度也是模棱的。既然刘先生认为异文不能证明“D”必读“辩”,形近才决定“D”应读“察”,而裘先生又倾向形近不能证明“D”必读“察”,异文才决定“D”当读“辩”,那就说明异文和形近字对于判定文字的释读作用都是很有限的。
因此,尽管“A”有“察”作为异文,尽管还有“B”“C”等形近字或同形构件可作旁证,“A”是否就读作“察”仍然难以定论,关键还得从该字符本身说明其形音义的来源,也就是得回答前面提出的那三个问题。
刘钊先生从读“察”出发,已经考证过从“D”诸字的字源,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但似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刘先生说:“这个可用为‘察’、‘浅’、‘窃’三个字声旁的‘D’究竟是什么字呢?因为其形体与‘察’、‘浅’、‘窃’三个字都无关系,所以显然只是一个用作声符的借音字。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推测这个字有可能就是‘![]() ’字的变体。‘
’字的变体。‘![]() ’本为‘辛’的分化字。古文字中从‘辛’或从与‘辛’类似的形体的字,其上部在演变中都变为‘
’本为‘辛’的分化字。古文字中从‘辛’或从与‘辛’类似的形体的字,其上部在演变中都变为‘![]() ’或‘
’或‘![]() ’,这一点与上引‘D’字的特征正相符。‘
’,这一点与上引‘D’字的特征正相符。‘![]() ’字古音在溪纽元部,与精纽元部的‘浅’和清纽月部的‘察’音都不远,而‘窃’字在典籍中又分别可与‘察’和‘浅’相通。正因为‘
’字古音在溪纽元部,与精纽元部的‘浅’和清纽月部的‘察’音都不远,而‘窃’字在典籍中又分别可与‘察’和‘浅’相通。正因为‘![]() ’与‘察’、‘浅’、‘窃’三字音都可通,所以‘
’与‘察’、‘浅’、‘窃’三字音都可通,所以‘![]() ’字的变体也就可以分别用为‘察’、‘浅’、‘窃’的声旁。”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前文已经论述“A”是否读“察”、“A”“B”“C”三组字所从的“D”是否为同一构件都还未定,假定未知为已知并以此为前提推论“D”的形音,方法上值得考虑。第二,如果这种以假定为前提推出的读音在形体上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也还可备一说,但事实上很难证明“D”就是“
’字的变体也就可以分别用为‘察’、‘浅’、‘窃’的声旁。”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前文已经论述“A”是否读“察”、“A”“B”“C”三组字所从的“D”是否为同一构件都还未定,假定未知为已知并以此为前提推论“D”的形音,方法上值得考虑。第二,如果这种以假定为前提推出的读音在形体上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也还可备一说,但事实上很难证明“D”就是“![]() ”(下文用“辛”代替或包含)。刘先生说“古文字中从‘辛’或从与‘辛’类似的形体的字,其上部在发展演变中都变为‘
”(下文用“辛”代替或包含)。刘先生说“古文字中从‘辛’或从与‘辛’类似的形体的字,其上部在发展演变中都变为‘![]() ’或‘
’或‘![]() ’”,尽管用“都”有点以偏概全,但毕竟是能找到例字的(如“宰”下的“辛”就有这种写法),可是这只能证明“D”的上部是由“辛”或类似的形体变来的,却无从证明整个“D”等于“辛”,因为“D”的下部还有“又”“廾”“大(矢)”“人(刀)”“水”等其它构件。刘先生在上引文章中没有解释这些构件的来源,但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一句“其下部的各种变体应是在发展演变中产生的类化或讹变”[xviii],可是没有具体论述。我们认为文字的形体演变是有可寻的,是要受到系统约束的,如果这些多出了许多构件的“D”都是“辛”的变体,那怎么能说明它的具体演变过程,如何能解释那么多已经认识的从“辛”的字为什么没有“D”这样的变体,而偏偏这几个未释字中的“辛”就统统变成了“D”。因此我们认为“D”的上部可能与“辛”或类似的形体有关,而“D”的下部大都是与“辛”无关的另外的形体(《五形》中独用的“D”可能为“辛”的变体,参下文)。如果说楚文字中的“D”因上部的“辛”都省掉竖画而容易跟下部误会为一体的话,刘先生文中所举的几个金文字例,其中的“辛”可是完整无缺的,显然跟“廾”是各自独立的构件,没有任何理由能把“廾”看作“辛”字变体的一部分。因此,即使“D”字的上部是由“辛”变来的,我们也只能承认“D”中包含有“辛”,但并不等于“辛”。形体上不相等,读音上能否等同呢?这也很难证明,因为“D”中的“辛”未必就是声符。“D”的基本形体是从“辛”从“又”或“廾”,以“又”“廾”持“辛”,“辛”作为义符或形符的可能性比作声符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由此看来,刘钊先生的字源考证,还无法说明“A”组字何以能够读作“察”。
’”,尽管用“都”有点以偏概全,但毕竟是能找到例字的(如“宰”下的“辛”就有这种写法),可是这只能证明“D”的上部是由“辛”或类似的形体变来的,却无从证明整个“D”等于“辛”,因为“D”的下部还有“又”“廾”“大(矢)”“人(刀)”“水”等其它构件。刘先生在上引文章中没有解释这些构件的来源,但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一句“其下部的各种变体应是在发展演变中产生的类化或讹变”[xviii],可是没有具体论述。我们认为文字的形体演变是有可寻的,是要受到系统约束的,如果这些多出了许多构件的“D”都是“辛”的变体,那怎么能说明它的具体演变过程,如何能解释那么多已经认识的从“辛”的字为什么没有“D”这样的变体,而偏偏这几个未释字中的“辛”就统统变成了“D”。因此我们认为“D”的上部可能与“辛”或类似的形体有关,而“D”的下部大都是与“辛”无关的另外的形体(《五形》中独用的“D”可能为“辛”的变体,参下文)。如果说楚文字中的“D”因上部的“辛”都省掉竖画而容易跟下部误会为一体的话,刘先生文中所举的几个金文字例,其中的“辛”可是完整无缺的,显然跟“廾”是各自独立的构件,没有任何理由能把“廾”看作“辛”字变体的一部分。因此,即使“D”字的上部是由“辛”变来的,我们也只能承认“D”中包含有“辛”,但并不等于“辛”。形体上不相等,读音上能否等同呢?这也很难证明,因为“D”中的“辛”未必就是声符。“D”的基本形体是从“辛”从“又”或“廾”,以“又”“廾”持“辛”,“辛”作为义符或形符的可能性比作声符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由此看来,刘钊先生的字源考证,还无法说明“A”组字何以能够读作“察”。
赵彤先生也试图从字源上解释“A”读“察”的理据。他认为ABC几组字中的“D”就是“祭”字,因为甲骨文的“祭”有“1![]() 2
2![]() 3
3![]() 4
4![]() 5
5![]() ”等写法,本象以手持肉之形,后加义符“示”。所从“肉”字往往横置(如2、3),与“口”相混同。战国文字的“口”形往往将上面的一横两端写出头作“廿”形,下面再加一横划即讹变成“D”的字形。4、5在“示”字两横之间加饰笔亦可讹变为“D”的字形。“C”所从的“D”下部显然是从“示”讹变来的。“B”所从的“D”下部则是由“廾”讹变来的。[xix]如果“D”确为“祭”字,那“A”当然能读作“察”了,“察”也从“祭”得声嘛。可是恕我孤陋寡闻,好象没有见过“示”能变成“水”的,也没有见过“廾”能变成“矢”的(“廾”可以变为“大”是隶变的结果),那么多已知的“祭”字和从“祭”的字,似乎也没有曾经讹变为“D”的。前面说过,汉字演变是有规律有系统的,不能根据个别形体和局部笔画的相近相似就随便系联。即使形体上有可能发生讹变,也一定要有同字或同类字讹变的事实才能承认,例如“‘口’形往往将上面的一横两端写出头作‘廿’形”,这是事实,可以举出许多例证,但“廿”的“下面再加一横画即讹变成‘D’的字形”就没有见过,“在‘示’字两横之间加饰笔”也无实例。因而这样推测得来的字源恐怕是难以成立的。
”等写法,本象以手持肉之形,后加义符“示”。所从“肉”字往往横置(如2、3),与“口”相混同。战国文字的“口”形往往将上面的一横两端写出头作“廿”形,下面再加一横划即讹变成“D”的字形。4、5在“示”字两横之间加饰笔亦可讹变为“D”的字形。“C”所从的“D”下部显然是从“示”讹变来的。“B”所从的“D”下部则是由“廾”讹变来的。[xix]如果“D”确为“祭”字,那“A”当然能读作“察”了,“察”也从“祭”得声嘛。可是恕我孤陋寡闻,好象没有见过“示”能变成“水”的,也没有见过“廾”能变成“矢”的(“廾”可以变为“大”是隶变的结果),那么多已知的“祭”字和从“祭”的字,似乎也没有曾经讹变为“D”的。前面说过,汉字演变是有规律有系统的,不能根据个别形体和局部笔画的相近相似就随便系联。即使形体上有可能发生讹变,也一定要有同字或同类字讹变的事实才能承认,例如“‘口’形往往将上面的一横两端写出头作‘廿’形”,这是事实,可以举出许多例证,但“廿”的“下面再加一横画即讹变成‘D’的字形”就没有见过,“在‘示’字两横之间加饰笔”也无实例。因而这样推测得来的字源恐怕是难以成立的。
(八)认为“言+D”是“讣”的异体,是“覆”的借字,与“察”同义。前面提到,我曾经把《包山楚简》的“言+D”楷定为“言+菐”,并论述其基本含义是“检查、勘验、核实、确认”,相当于“检察”之“检”、“察”,但没有肯定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蒙王宁先生(这位先生跟我的业师同名)同意我的楷定和义训,并进一步申说“言+菐”字何以会有这样的意义。他说:“这个字确是从‘菐’声,则不当读为‘察’。由古文‘撲’又作‘扑’、‘墣’又作‘圤’、‘樸’又作‘朴’推之,此字当是‘讣’之或体,在楚简中其义确实与‘察’相同,但‘讣’之本意是‘告’或‘告丧’,《集韵》‘讣,告也。通作赴’,《玉篇》、《广韵》训‘告丧也。通作赴’,‘赴’《说文》训‘趋也’,是‘讣’、‘赴’皆无‘察’义,故此楚简中的‘讣’是个假借字可无疑义。《说文》:‘察,覆审也’(《广韵》引《说文》作‘察,覆也。’),由此笔者认为,楚简中的‘讣’当读为‘覆’,二字古音同滂母双声、屋觉旁转叠韵,音近而假。《尔雅·释诂》:‘覆、察,审也。’是‘覆’与‘察’古义训相同,古‘覆’亦训‘察’,如《管子·五符》‘下愈覆鸷而不听从’尹注‘覆,察也’是其证,则‘覆’、‘察’二字古可互训也。又《广雅·释言》‘覆,索也’,即检索、调查之意。是‘覆’字古确有‘检验、核实、确认’等含义,与‘察’义相同。”[xx]
今按,王宁先生虽然没有详论字形,但他同意我的楷定,认为“这个字确是从‘菐’声,则不当读为‘察’”,从形体系统来看是比较客观的;他说“言+菐”的“察”义来源于“覆”词也很值得重视。对这两点我们将在前面提到的《考辨》一文作补充论证。但我们不同意“言+菐”是“讣”的异体字的说法,也不信从“讣”是“覆”的假借字的说法。因为,第一,“覆”的本用指倾覆、覆盖,表示检验、核实义也属于借用,所以它不可能是“讣”的本字,不能说“讣”假借为“覆”。第二,根据《说文解字》,在古代的文字中除了表示土块的“圤”可以说是“墣”的异体外,其余“仆”(顿首)与“僕”(执事者)、“扑”(“攴”的异体,小击)与“撲”(手相搏)、“朴”(树皮和树名)与“樸”(未加工的木材)都是不同的字,表示不同的词,文献中偶尔通用,古人都注明属于假借,形成异体字关系实际上只限于“繁简字”层面,而这已经是后代的事,不能拿来类推战国文字。何况文献中的“讣”根本没有“覆”(察)的用法,怎么能够断定就是具有“覆”(察)义的“言+菐”的异体字呢!所以这样的字际关系表述值得商榷。
关于“言+D”字的释读除了上述八种主要的观点外,可能还有别的看法,真可谓众说纷纭,但似乎难求一家全是。它们或者把没有关系的“D”当作同一个字处理,或者只抓住个别或部分形体解释来源,而把无法解释却本来有关联的字形和变体撇开不管,或者把可能当事实,用未知证明未知,或者用后代的文字现象类推前代的文字演变,以致在字源的分析和辞例的解读上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疑问。因而这个字的释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的看法将在随后发表的《楚简“言+菐”字及相关诸字考辨》一文全面论述。
[i] 参广瀬熏雄《包山楚简に见ぇゐ证据制度につぃて》,《楚地出土资料と古代文化》,郭店楚简研究会编,汲古书院2002年3月;许学仁《战国楚简文字研究的几个问题——试读战国楚简〈语丛四〉所录〈庄子〉语暨汉墓出土〈庄子〉残简琐记》,《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三辑,中华书局2002年6月。
[ii] 初稿首发于《简帛研究》网(02/09/07),http://www.bamboosilk.org/Wssf/2002/liyunfu01.htm
修改稿正式发表于《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
[iii] 有关说法见许学仁《战国楚简文字研究的几个问题——试读战国楚简〈语丛四〉所录〈庄子〉语暨汉墓出土〈庄子〉残简琐记》一文注释8的介绍。
[iv] 刘信芳《包山楚简司法术语考释》,《简帛研究》第二辑,出版社1996年9月。
[v] 葛英会《包山楚简释词三则》,《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下文所引葛先生的观点皆见此文,不再一一注明。
[vi] 本来在评述各家之说后,下文专门论述我们的看法,但限于篇幅,不能一次发表,所以把我们的观点部分另作一文,题为《楚简“言+菐”字及相关诸字考辨》,随后发表。
[vii] 胡平生《说〈包山楚简〉的“言+業”》,《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集》,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
[viii] 许学仁《战国楚简文字研究的几个问题——试读战国楚简〈语丛四〉所录〈庄子〉语暨汉墓出土〈庄子〉残简琐记》,《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三辑,中华书局2002年6月。下文所引许学仁的观点皆见此文,不再一一注明。
[ix] 董莲池《释楚简中的“辩”字》,《古文字研究》第22辑,2000年7月。
[x] 分别见《包山楚简司法术语考释》,《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9月;《释“![]() ”》,《简帛五行解诂》附录九,艺文印书馆,2000年。
”》,《简帛五行解诂》附录九,艺文印书馆,2000年。
[xi] 参陈昭容《释古文字中的“丵”及从“丵”诸字》,《中国文字》新二十二期。转引自许学仁《战国楚简文字研究的几个问题——试读战国楚简〈语丛四〉所录〈庄子〉语暨汉墓出土〈庄子〉残简琐记》,《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三辑,中华书局2002年6月。
[xii] 黄锡全《楚简“言+带”字简释》,《简帛研究》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xiii] 参广瀬熏雄《包山楚简に见ぇゐ证据制度につぃて》,《楚地出土资料と中国古代文化》,郭店楚简研究会编,汲古书院2002年3月。
[xiv] 见刘钊《利用郭店楚简字形考释金文一例》,《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2002年初月。下文所引刘钊先生的意见除有另注者外皆见此文,不再一一出注。
[xv] “国”应是从“或(域)”词分化出的派生词,跟先秦的“邦”同义,汉代因避讳而用“国”字代换了先秦的“邦”字。参大西克也《“国”的诞生——出土资料中“或”系字的字义变迁》,《楚地出土资料と中国古代文化》,郭店楚简研究会编,汲古书院(日本),2002年3月。
[xvi] 刘钊《释“儥”及相关诸字》,见《简帛研究》网 (01/08/07)http://www.bamboosilk.org/Wssf/liuzhao.htm
[xvii] 同上。
[xviii] 同上。
[xix] 赵彤《楚简中用作声旁的“祭”》,见《简帛研究》网(02/09/12) , http://www.bamboosilk.org/Wssf/2002/zhaotong01.htm。
[xx] 王宁《申说楚简中的“讣”》,见《简帛研究》网(02/09/15),http://www.bamboosilk.org/Xszm/2002/wangning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