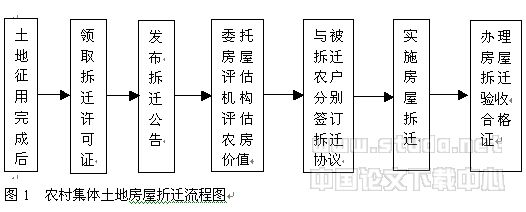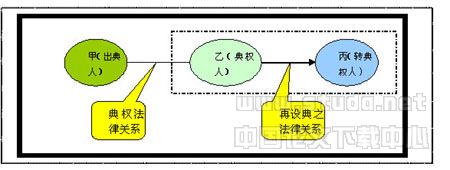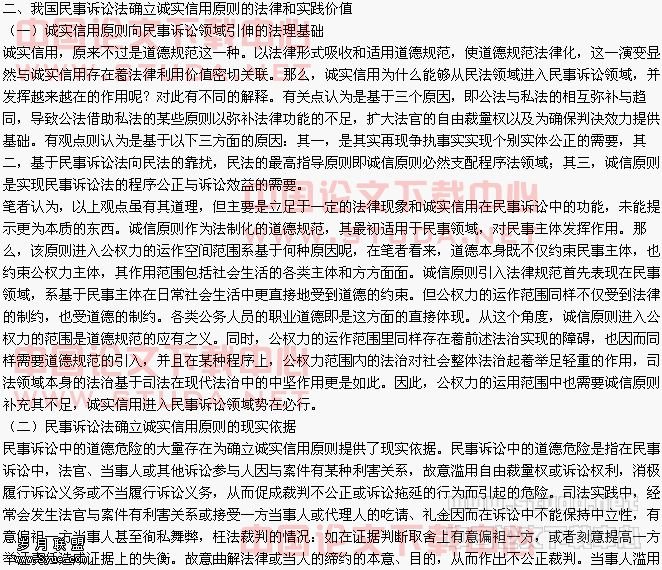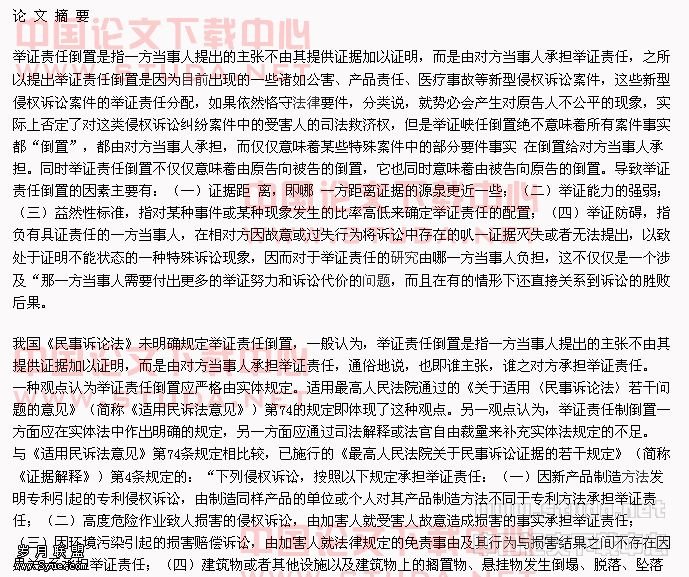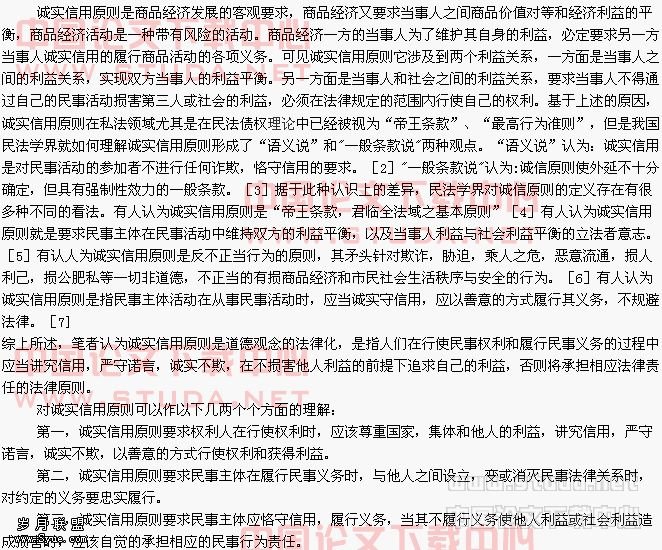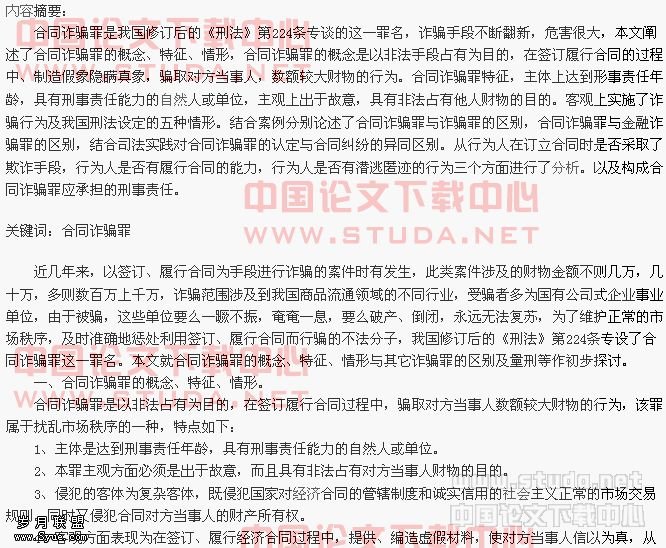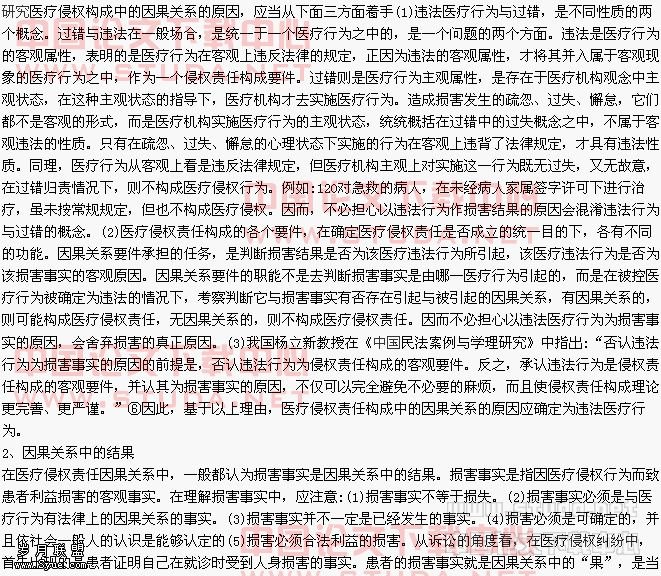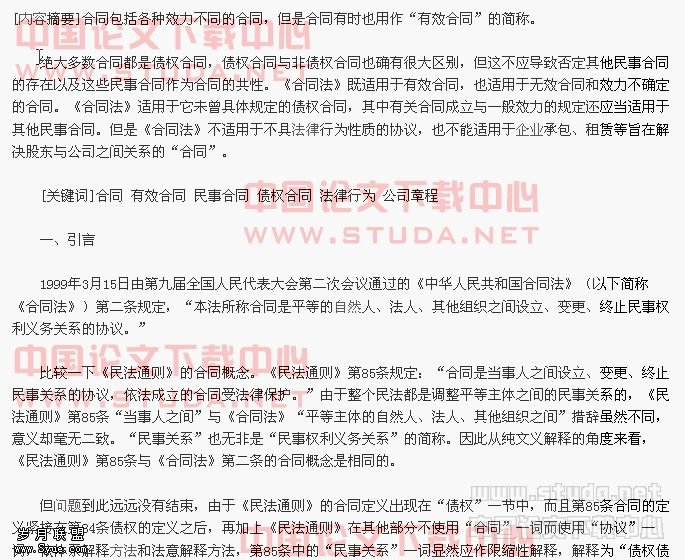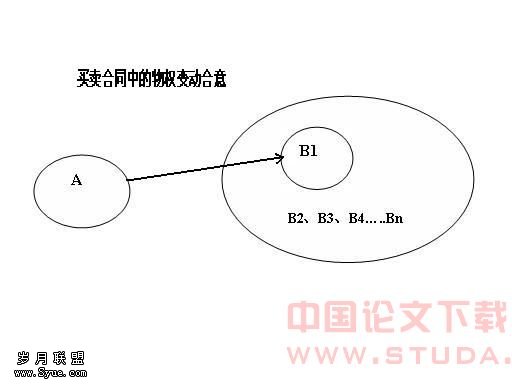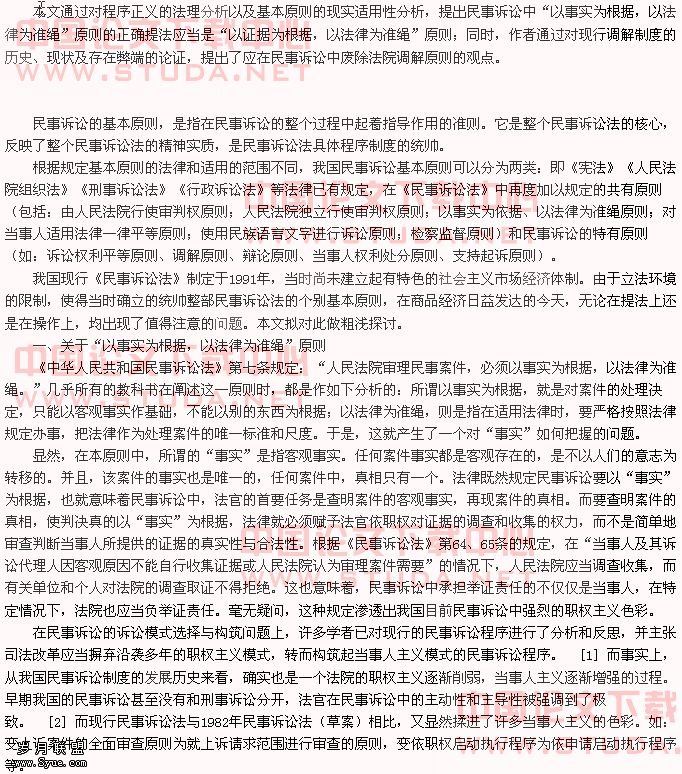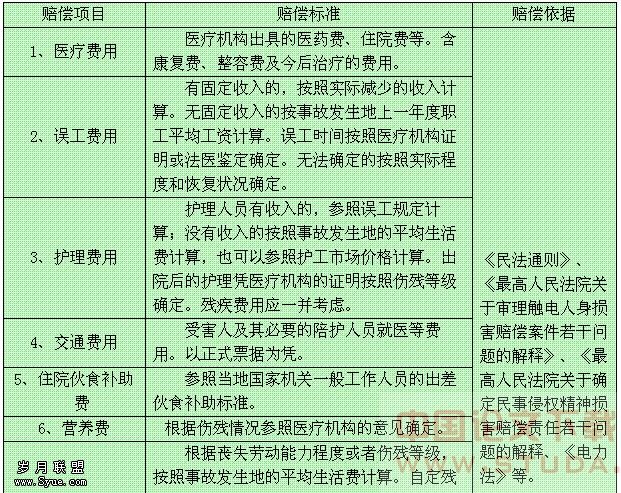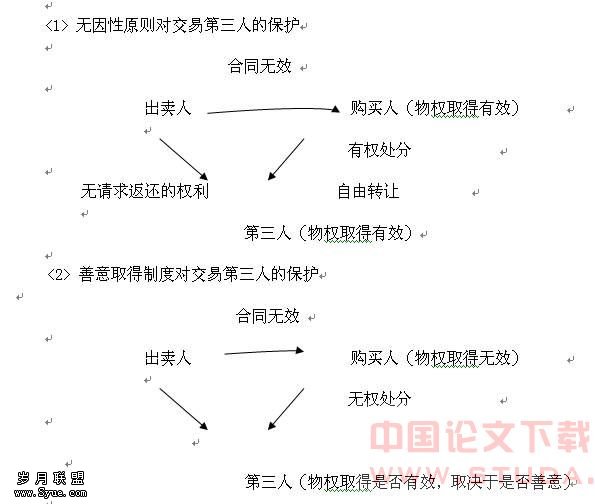环境法学权利研究方法论
摘 要:在环境法学权利研究中,方法论是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当前,环境法学权利研究中,过于注重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运用,从而将权利研究引入两个误区:其一是过于强调国家利益优于个人利益,形成了权力支配下的“义务本位”;其二是过于强调生态的整体性,将权利主体扩张到人之外的其他生命甚至是非生命体。而由权利的本质所决定,个体主义方法论应是权利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论之一。这两种方法论在环境法学权利研究中应紧密结合。
关键词: 权利;方法论;整体主义;个体主义
Abstract:While studying rights in environmental law, one should, first of all, have a full knowledge of relevant methodology. Regretfully, now the study seems to have been misled by over-emphasis of the collectivism methodology and two adverse effects are manifested: (1) over stress of priority of state interests over private interests has resulted in the “obligation orientation” dominated by power; and (2) over stressing the integr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led to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owner of rights to the life other than man, even including non-life objects. Determined by the essence of rights, individualism methodology should be deemed indispensable in the study of rights. Indeed, both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methodologie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 the study of rights in environment law.
Key Words:right; methodology; collectivism; individualism
一、方法论对环境法学研究的重要性
一切理论探讨,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其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一切理论变革又首先依赖于对其研究方法论的变革,只有方法论上的更新才能带来该学科的重大突破。正如巴甫洛夫所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1]。拉伦茨教授在其名著《法学方法论》中亦说:“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2]。可是,在我国法学研究中缺乏对方法论的重视,诚如民法学者王泽鉴先生所言:“我国法学一向疏于方法论之研究,……致使法学之发达甚受限制”[2]80。梁慧星先生曾说:“我国大陆法学忽视方法之倾向更为严重,此是不争之事实”[2]80。
朗内斯特在他1983年所编的《词典》中指出“对那些总是指导着科学探索的推理和实验原理及过程的一种系统分析和组织……,也称之为科学的方法,因而,方法论是作为每一门科学的特殊方法的一种总称”[3]。1977年出版的《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则将方法论定义为“一门学科所使用的主要方法、规则和基本原理;……对特定领域中关于探索的原则与程序的一种分析”[3]22-25。梁慧星先生在论及方法论时,认为“方法论的任务是说明这样一种方法,凭借这种方法,从我们想象和认识的某一给定对象出发,应用天然供我们使用的思维活动,就能够完全地即通过完全确定的概念和得到完善论证的判断,来达到人类思维为自己树立的目的”。“方法论与人的活动有关,它给人以某种行动的批示,说明人应该怎样树立自己的认识目的,应该使用哪些辅助手段,以便能够有效地获得科学认识”[2]81。
方法论与方法是不同的。“方法”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它由“遵循”和“道路”两部分组合而成,意为“遵循某一道路,即为实现一定的目的,必须按一定的顺序所采取的步骤”[4]。方法是“做任何事的方式、模式、程序、过程……有规则的、有条理的、明确的程序或方式”[3]22-25。环境法学的研究方法,是指在环境法学研究过程中所应遵循的一套原则、手段程序和技巧等。这些研究方法在环境法学的发展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职能,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环境法学发展的水平和风格。可见,没有成熟、科学的研究方法,就不会有成熟、完善的环境法学,也就不可能推动环境法的发展。环境法学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首先可以采用法学研究的所有方法进行其理论研究工作;其次,鉴于环境法学是介于法学和环境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这使得用生态学观点思考问题,研究现实事物的生态学分析法成为了环境法学有别于其他部门法学研究的独特方法。二战以后,随着自由主义法学、法学、法社会学、综合法学等形成,这些新兴的法学研究方法都成为环境法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罗尔斯《正义论》出版后,一些环境法学家在《正义论》和其他哲学、环境道德学观点的影响下,提出了环境正义、绿色正义、环境公平、环境权等主张,使得用自然法学派理论研究环境法成为环境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此外,由于环境法学是有关环境资源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最新成果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方法以及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方法在环境法学研究中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借鉴和运用。
“方法论”一词是指在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途径的研究。一般来说,它要涉及到研究主体思考问题的角度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比较选择,研究手段的筛选和运用,研究目的的限定等。而“方法”一词则指用于完成一个既定目标的具体技术、工具。这就决定了方法论的主要功能或目的“是要帮助科学发挥最好的效力,或者说是要引导如何从事科学研究,而不是指导平庸的科学如何工作”[5]。而“方法”的功能或目的,旨在提高研究效率,但不能给予人以指导。方法是根据,而方法论是包括一定的哲学认识论及逻辑推理过程的一套思考法现象的理论体系[6]。
法学方法论对环境法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方法论指导理论框架的确立。如前所述,方法论关注的不仅是研究的具体方法问题,更主要的是要有明确的合理的假定以及基本的研究立场,只有具备这些,才能构建研究活动的基本框架。例如,自然法学派以个人为本位,通过自然状态、自然人、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等范畴构筑一套完整的法学思想体系;而社会法学派则立足于社会的角度,将作为社会过程的一个内容。而方法论指导下的理论框架的确立,对于学科研究起着关键的作用。美国学者就曾指出:“一些在政治学方面被看做较有独到见解的和比较有用的著作,是由经济学家所撰写的,他们从自己学科的工具箱中取出的合理的概念和模式应用到政治学上……获得了成功。”[7]其次,方法论有助于环境法学研究的深化。“学科发展与深入的途径有两种:一是继承,即对前贤的研究成果进行清理,吸收其精华,作为学术绵延与发展的“薪火”;二是借鉴,即借鉴其他学科所取得的成果,特别是方法论因解释框架、论述格式上的共通性而更应加以重视,必须大胆借鉴,为我所用。”[8]“方法论对认识国家和法的重要性是无法估量的。方法论成为认识国家法律过程和现象复杂而矛盾的本质所必不可少的真正前提”;不仅如此,法学方法论的重要性还表现在,“研究国家活动某一领域法律调整规范和条件的专门部门法律学科也使用该方法论的”[9]。正如俄国著名生物学家巴甫洛夫所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法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注:巴甫洛夫.巴甫洛夫文集[M].转引自:卓泽渊.法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291.)
从方法论角度拓展法的研究领域,仍是法学工作者们目前及今后时期的艰巨任务[10]。而法学方法论涉及到两种范式的方法论,即一般科学方法论在法学研究中应用而产生的理论法学方法论及法解释学方法论。现今环境法学研究中过于注重法学方法论中法解释学的一元性,即注重应用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并对这种方法论———法解释学方法论过份强调,导致了法学方法论的畸形发展,特别不利于环境理论法学的发展,因而有必要重新把科学方法论导入环境法学研究之中,即法学方法论应由科学方法论与解释学方法论二元构成。这两种方法论当然并非并重,一般来看在理论法学中以一般科学方法论为重,当然解释学方法论亦有其作用。基于以上对法学方法论的认识,下文仅对理论法学方法论进行初步探讨。当然,不论述法解释学方法论,并不是这种方法论不重要,亦不是说此种方法论不能推进法理论的发展,而是由于这种方法论已成为法学界的共识,且在法学中得到较完善的论述。同时,因篇幅所限,加之作为初步探讨,因而也不可能涵盖理论法学方法论的所有方面和主要问题,只就在环境权利研究中冲突最为明显的法学方法论范畴——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进行讨论。
二、环境法学权利研究中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误区
整体主义方法论是指以整体作为研究的基点,通过群体行动的分析来说明该学科的基本立场与基本内容的方法体系。“在社会科学和学中,指一种主张可以或者应该通过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社会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法则、倾向和运动等等”[11]。柏拉图直接将个人视为为城邦服务的工具,脱离城邦的个人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在其《理想国》明显表达的就是整体主义思想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因为整体必然优先于部分……城邦作为自然的产物,并且先于个人”[12]。涂尔干认为:“社会并不是个人相加的简单总和,而是由个人的结合而形式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则是一种具有自身属性的独特的实在。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个人意识,任何集体生活都不可能产生,但仅有这个必要条件是不够的,还必须把个人意识结合或化合起来,而化合还要有一定的方式。社会生活就是这种化合的结果。因此,我们只能以这种化合来解释社会生活……因此,如果我们从孤立的个人出发去研究,我们就完全不能了解团体内部发生的一切”[13]。有学者认为“最恰当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14]。对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极力倡导者和使用者,当首推马克思,其阶级分析法就是整体主义的具体表现。在他看来不仅有超越个人利益的阶级利益(集团利益),而且更为关注阶级利益。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而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我们的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5]251两个阵营,他们各有其自身的、相互对立的阶级利益。正是这种阶级(集团)间的利益对立、斗争,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在环境法学研究中尤其应注重整体主义方法论,因为在生态学中,整体性是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特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生态系统的各种因素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使生态系统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2)生态系统层次结构的等级性、生态系统的组织性和有序性,表现为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性;(3)生态系统发展的动态性,表现为它的时空有序性和时空结构的整体性[17]。大地伦理学更是把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视为最高的善。认为“整体,即生态系统本身,完完全全地创造并模塑着它的组成部分”[18]。该学派代表人物利奥波德认为整个生物圈是一个有机整体。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从物种层次、生态系统层次到生物圈层次都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从而构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而个体并不拥有独立于它所依赖的各种关系的价值,个体的重要性是由它在生态系统中所发挥出来的功能来决定的。“大地伦理学并不公开地把同等的道德价值授予生物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个体(包括人类个体)的价值是相对的,要根据它与利奥波德所说的大地共同体的特殊关系来加以衡量”[19]。随着人们对生态系统整体性认识的深入,美国哲学家贝阿?德·卡利柯特等人进一步阐发了利奥波德的这一思想。卡利柯特指出,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的大地伦理是我们人类道德良心的扩展,这不是取消我们的道德义务,而是把道德义务置于更为广阔的生态系统之中。“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20]。
整体主义方法论在环境法学研究中固然重要,但过于注重这种方法论,势必将权利研究引入误区。误区之一就是:过于强调国家利益优于个人利益,形成了权力至上支配下的“义务本位”。这种社会整体观,一方面表达了人们对于社会和谐与社会整合的期望,也同时使个人无法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因为“礼治秩序对社会中的个体实现了精心巧妙的组织与确定,然而可惜的是它对个体的组织与确定,不是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生命的潜能,不是让个体自我负责地实现生活的过程。相反,却把个体‘长幼有序’地固定化,使其身在其中而不能动弹,没有个性的出路”[21]。在法律认识论的理论层面上,它表现为对有生命的现实的个人理性能力的怀疑,强调人作为类的群体存在,认为法律的产生、发展、作用和目的都是仅仅取决于人的群体意识及群体活动,否认人作为个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否认具体的个人的实践活动。在法律实践论的现实层面上,认为法律实践的直接对象是群体间的关系,法律实践的主体仅仅是作为整体的人或群体化了的人,不承认或者轻视个体特殊性,更回避个体创造性的实践意义,将个人作为一种手段,一种实现类的或整体的目标的工具[22]。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更是将社会整体利益绝对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他说:“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废法也”[23]。但是,如果我们完全采取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立场,强调“社会本位”,“社会利益优于个人利益”,就有可能使人本身成为一种社会的工具。正因为如此,许多伦理学家对大地伦理学的整体主义的批评主要是它赞成了整体的“好”而牺牲个体的“好”,“大地伦理学的整体主义削弱了对个体的内在价值的尊重”[24]。雷根明确地指出,大地伦理学“明显包含了这样一种前景:为了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个体得牺牲给更大的生物共同体的‘好’。在这样一种……可恰当地称之为环境法西斯主义的论点中,我们很难为个体权利的观念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整体主义给我们提供的是对环境的一种法西斯主义式的理解”[25]。克尔则直接称大地伦理学的整体主义是“专制主义”[26]。
环境法律制度有两条利益和意志主线,一是社会整体利益和国家意志,二是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和当事人意志。一个理性和健全的环境法律制度,应该是这两条主线的有机结合。而我国以往环境法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总是把个人的人格和权利附属于其所归属的社会团体,崇扬国家的权力而淡化个人权利。不适当地忽视甚至否认第二条主线,致使环境法律制度被定位于环境权力法,重环境管理权力的设置与实施,忽视公民环境权利的分配与保障。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改革后,公民环境权利的重要性日益彰显,环境法的权利体系构建更加迫切。“这种制度性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构建环境权利的法律体系,完善环境权利的法律规则,实现环境权利法和环境权力法的并存和配合,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具有特色的环境法律秩序。可以预见,环境权利将成为我国未来环境法律制度的基础”[27]。
误区之二:过于强调生态的整体性,将权利主体扩张到人之外的其他生命甚至是非生命体。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陈泉生教授认为,可持续发展法学突破了传统法学权利主体的范围,其不仅承认人类这一种群的权利,也承认其他生命物种种群的权利,并建立了相应的法律制度。近代法律观念是权利本位,现代法律观念是社会本位,而可持续发展法律观念是生态本位,其要求法律制度应围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精心设计,既要体现人的权利,也要反映生态自然的权利,从而与可持续发展法律的要求相吻合[28]。蔡守秋教授认为,“人与生态自然具有不可分割性,人有享有适宜自然环境的权利,意味着自然环境具有满足人需要的功能和价值;人有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意味着自然环境有受到人尊重的权利。”[29]美国学者Christopher Stone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树木应有诉讼资格:自然体的法律权利》。他指出既然法律可以赋予不能说话、没有意识的国家、公司、婴儿、无行为能力人、自治城市和大学等法律资格,那么也可以赋予自然物体以法律资格,并为它们设定保护人和代理人[30]。而在美国《野生动物案例、法律和政策》教科书中第7章《野生动物的权利》中有一节为“人类与海豚之间的交流:接受其他物种的可能性”。作者在该节中提出了彻底的“生态中心主义”的立法主张,即“在人类法律中,个体的鲸被赋予人类个体的法律权利”,由“人类个体和人类团体代表被人类置于危险境地的鲸类个体行使控告权或者出庭”,并在人与鲸类动物之间的沟通方式研究出来后,“人类与鲸类合作,研究出新的种际法、种际协议和种际条约”[31]。有学者以例为证,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就是保护珍稀濒危动物的生存权及其生态环境,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对动植物给予人道的待遇或人权,如前苏联《动物保护与利用法》(1980年)规定“控制某些动物数量的措施,必须采取人道的方法”,“培养公民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动物”[32]。法国环境法甚至强调环境本身为法律之主体,而并非仅为法律之客体。也就是说,对生态之损害,生态本身即为法律主体,则即使生态损害没有必然反射到对人之损害,加害人也应负法律上之责任。依我看来,即使不考虑其道德合理性,作为一种个体的道德追求或宗教信仰,这无可厚非,但如果将其转化为法定权利就恐怕是对现有法律制度的一种颠覆了。因为权利只是“对行使一定自然权力的一种允许”[33],权利体现在社会习惯、道德、宗教、法律等诸多方面,包括着习惯权利、道德权利、宗教权利、法的权利等大量内容,而法的权利与权利不同,它只是权利之一种,是一种被法律化了的社会权利。它是在法律社会中产生、存在,并以特定法的形式予以许可和保障的权利主体自主享有的权能或利益[34]。法律上的权利,不能等同于人类的道义,也不能与生态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划等号。如果我们将自然利益、动植物利益与人类利益等同视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如何才能衡量一个动物或植物的利益?应由谁来进行这种衡量并将它与人类利益作比较?那个特殊的衡量者是如何获得合法性的?目前在环境法上难以确立环境权,难以将环境权上升为基本权利或人权,原因之一或许正是在于环境权不仅涉及以人为主体,且涉及以动物、生态及生物生存空间为主体之权利,界限甚为辽阔。
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虽然也属于环境的创造物,但他却不可能与其环境合为一体:“真正的人不愿溶化到他的环境中去。他不可能向它投降或把自己消溶到其中去。如果他确实消溶到其中去了,甚或他只是希望这样,他也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了。人是这样一种造物,他不仅仅是完整的造物世界中另一个单纯的成分。他虽属于被造物,但他与其被造同伴却有着天壤之别”巴思·教会释义学[M].转引自: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454.。社会发展的实质在于“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和“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提升出来”[35]。人类之所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还在于关心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而不是为了生态自然本身。脱离了人、脱离了社会的自然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如马克思所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36]。比如我们保护动物,并非为了保护动物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和“享受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37],保护动物的目的在于维护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的平衡以及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包括观赏、科学研究和用于工农业、业、娱乐业目的。正如前民主德国学者霍尔茨所说的那样:“是否需要维持合理的生态平衡,对自然界来说确实是无所谓的,环境保护与自然无关,而只是涉及人类自身的利益,环境保护实际上是人类保护……它主张以对人类有利的形式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38]。同样,自然界也不会对人类提出任何权利要求。“人类对环境问题和生态破坏负有道德责任,主要根源于对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以及后代人利益的关心”,而“非人类的自然无所谓‘公共利益’,也无所谓可以辨识的责任和义务”[39]。“不管人们如何理解环境保护,是从人类的角度来理解,还是从一切造物主的尊严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理解最终总是涉及到政府机构、议会和法院中的人就其他人应当保护环境做出什么决策。”[40]因此权利始终是人的权利。
作为一种研究立场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是指以个人作为学科分析的基点或基本研究单位,从而通过对单个人的行为分析,展开该学科的一般原理及性问题。也就是说,个体主义方法论是一种立足于个人的视角研究学科问题的方法体系,它以个人为分析问题的基点,通过对个人行为、动机、目的、偏好等方面的分析,来展现社会的基本脉络[41]。其理论根据的核心内容在于,把个人看作是分析和规范化的基础,社会则被认为是各个追求自身利益的总合,相应地,国家或社会便成为个人得以通过它而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机构[42]。
“社会现象,包括集体,应按照个体及其活动与关系来加以分析”[43]。因为“社会世界的最终成分乃是各个人,这些各个人或多或少适当地依据其倾向及其对情境的理解而互动。每一复杂的社会情境、制度或事件,乃是诸个体以及诸个体的倾向、情境、信念、物理资源和环境的一个特定逻辑结果”[44]。个人并未因参与集体而失去了其独立的性质,相反,整体的行动、整体的制度,是由各个个人所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个体的加入,整体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自由、平等的个人,他们作为自己的禀赋及利用这些禀赋的所得之所有者,彼此联系在一起。社会是由这些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形成的”[45]。“那些属于日常的思维或的(或其他专业的)思维的集体机构,是现实的人(不仅法官和官员,而且包括‘公众’)的头脑里的观念,部分是现实存在的观念,部分是应当适用的观念……”[46],“我们应该从个人的行动出发,因为这是我们可以直接认识的惟一事物。离开了个人的行动而可以运行和表明自己的社会的观念是荒谬的。每一个社会的事物都必定是可以以某种方式在个人的行动中认识的”[47]。
在权利研究中,个体主义方法论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因为“任何团体或‘集体’,不管是大是小,仅仅是无数个体的组合。除了个体成员的权利之外,团体没有其他的权利。在自由社会中,任何团体的‘权利’是从其成员的权利中引伸出来的,是个体自愿选择和契约式的同意,也是个体在进行特殊活动时的权利运用。”[48]“法治所特别加以关注并将其置于首要重任的仍是对个人权利的充分而全面的有效保障。”[49]“如果你希望倡导一种自由社会,你必须意识到,它的必要基础是个体权利的原则。”[49]85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有创造性的、有理性的社会中,并且,彼此的交往有益于相互的利益,那么,他们必须接受社会的基本原则,否则,道德的和文明的社会是不可能的。这个基本原则就是个体的权利。承认个体的权利,意味着承认并接受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而由其本性所需要的条件”[49]108,而“一个人如果否认个体权利,那么,他也就不能要求、捍卫或坚持任何其他的权利。”[49]136因为从根本上说,“人类权利的源泉并非神的法律或议会的法律,而是自我的法律。A就是A——人就是人。权利是存在的条件,是人类本性的要求,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如果人要生活在地球上,运用理智是他的权利,根据他的自由判断而行动是他的权利,为他自己价值而行动是他的权利,拥有他劳作的成果也是他的权利。”[48]89在权利研究中,必须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以法律作为目的,这样才能就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固有张力进行消解。具体地说,并不存在与个人利益根本对立的社会利益,国家本身也没有干预人的个性发展的正当权力。
个人与个人主义是两码事,不可同日而语。人做为个人而存在是社会的进步,绝不能因为反对个人主义就否定人作为个人的社会价值。个人主义方法论是对分析单位的逻辑选择,不涉及价值判断问题;而个人主义是相对于国家主义或者社会本位等观念而言的,它表现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建构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还是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问题,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性质。
环境法学的兴盛恰恰需要从重建个体主体性开始,研究个体的环境权利。因为个体享有在适宜环境中生存、发展的权利,是个体依法利用环境要素或环境资源、享受适宜的生活环境条件的法律保障;是防止个体生活环境被污染、破坏而使其身心健康和财产遭受损害,或在受到损害时依法请求救济的法律武器;它赋予公民参加环境保护活动、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平等资格,是实行环境民主和环境公众参与的法律依据。承认个体对安全健康的环境的独立权利还具有其他重要意义,例如:个体环境权利加强、补充了受保障的其他人权,是实现其他基本人权的一个手段;个体环境权利是人类尊严的一种表达形式,它不仅完善了当代人的权利,也是实现后代人其他人权的前提条件。
当然,个体主体性并不否定整体,相反就是为了说明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进而说明法律的生命运动存在于个体绵延不绝的永恒的创造之中。庞德指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巨大的力量就是自发的个人主动性。因此,个人自由行为中包含的社会利益,是个人生活利益的一部分”。“它可以或者暗示一种社会现实应该得到完整描述,或者指出一个社会应该作为一种制度来加以研究,这种制度的各种成分是相互联系的。用来研究变迁的这个概念还可以指出,只有构成社会现实的全部成分才能理解变迁”。个体主体性所否定的只是虚幻的、空洞的、抽象的整体。观念中的整体在法律的实践中是没有任何操作层面的意义的。正如“法人”离开了组成法人单位中具体的个人行为,法人只不过是一个观念的空壳,并不具有任何法律上的意义。这意味着“整体”只有在结合“个人”的意义上才是有用的分析单位。“个别与整体都通过各种方法来发展整体。这些方法包括表示、维持、与促进或旨在促进文明的法律制度与制度,这种文明是他们在当时当地所理解的那种文明”[50]。超越以整体主体性为核心的传统环境法学,使法律与个体的环境权利紧密结合,才能更有利于整体环境权利的实现。因为环保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不仅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和引导,更重要的是需要在全社会自下而上培养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忧患意识和真正形成环境保护的广泛共识,并把这种意识与共识付诸到日常的行为中去。
四、两种方法论在环境法学权利研究中的结合
从表面看,个体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是处于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状态。其实两者的对立远不像想象的那样尖锐,亦即说,它们各有其合理性。不仅如此,辩证地来看,它们之间还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如黑格尔所说,“普遍性和特殊性两者都只是相互倚赖、各为他方而存在的,并且又是相互转化的。我在促进我的目的的同时,也促进了普遍物,而普遍物反过来又促进了我的目的”[51]。
在法学中把个人作为考察对象的出发点有其自然的一面。因为法律是通过规制人的行为实现其目的的。其目的能否实现主要建立在人能否按法规制的行为规范而行为。法是基于人是理性的,是趋乐避苦的生物这一假设上的,为此设置了对违法行为惩罚的规范,以警示、吓阻人的不法企图,否则法则无法达到诱导、指引人的行为的目的。因此,法必须考察作为行为源的“个人”。不仅如此,就考察者本人来说也是个人,而且其看到的、接触的也多是各种各样的现实中的个人。此外,社会研究结果也表明,保障个人的自由选择,尊重个人的价值与意义,本身可以给人以激励,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同样,方法论的整体主义也不象布坎南批判马克思时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忽略对个人的偏好分析而只考虑集体或阶级利益。只不过,马克思把当时流行的从人的个体认识人的本质,转向了从人的社会性上去认识人的本质,而且由于当时对人的社会性的忽视,使马克思更加强调从人的社会性认识人的本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人的个体本质的彻底否定,至少在对人性的看法上马克思是如此。
“个人”与“社会”只是从人们不同的生活场域而言的,因而这两种分析方法可以说都是就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区别只在于选择据以分析的基点不同,因而导致结论上可能存在的差异。但严格的说,两种研究方式又是可以互补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在宏观上对社会现象进行总体的把握,有利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也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法律的精神及建构原则,从而确立由一般到特殊的分析流程。“不难想见,有些人类行为不考察人的集体行动就无法透彻地理解,因为许多个人目标及行为只有在采取集体行动时才能实现和显示”[52]。而个人主义方法论则从微观入手,就个人及其行为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形成由个体到整体、由具体到抽象的分析思路,因此,这两种方法应当是相互结合、相辅相成的。如前所述,环境法融公、私权于一体,所以在环境法学研究中,交错使用这两种方法,对于从不同的视角探讨法律现象,更会起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但是有学者却认为,环境污染、自然资源耗竭、生态破坏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对于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保护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才能达到。“他们相信,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应该限制资本主义对环境的利用和侵蚀,而最大限度的环境保护应该废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并修改宪法中的(个体)自由权利”[53]。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未曾认识个体性环境权利与社会性环境权利的内在逻辑联系所致。其内在逻辑联系表现为:第一,权利之源,根植于人本质上的双重属性:个体性与社会性。而这种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相互妥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私权与社会权、公权之间的边界。第二,法律权利之设置,在于满足人的“私人性”需求与“公共性”需求。其实,在环境保护中,个体利益的内涵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不能狭隘地将个人利益就直接理解为对于那些污染环境、浪费自然资源的个体经济行为的肯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产品的丰富,公众的消费偏好逐步发生变化,包括环境质量在内的生活质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良好的环境被视为人类活动的必要条件,个体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则被视为基本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54]。这种个体利益是有利于环境公益实现的。而且环境法中的公权利有时可以个人主张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主要发生在两类情况下:一是作为集体性权利的公民环境权利在与个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相结合时,可以表现为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二是公民作为社会、集体(如社区)或者某一特定区域的一员,均有权利代表公益对国家、集体或其他成员行使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请求权。[55]
但是,个体主义方法论难于处理不可分公共资源问题,难于处理多功能多价值的资源问题,难于处理经济外部性问题,难于处理环境福利的代际分配等等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整体论的思考,这种整体性应包括所有当事者(影响者与被影响者),应包括人与自然物,应包括当代与未来。也就是说,必须是一种综合型方法论,尤其是在调整客体和调整方式上体现整体环境保护观。从法律调整客体上看,应具有广泛性、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融合环境污染控制、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环境生态保护功能等的统一环境法。从法律调整方式上看,整体环境观指导下的调整方式体现为资源开发、利用和消费全过程的环境保护。但是,必须明确,这里所说的整体利益是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上的,是绝大多数人共同利益的反映;而脱离个体利益的所谓整体利益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整体利益,实质上是某个特殊人物和特殊阶层的特殊利益,不过是一种以普遍利益形式表现出来的特殊利益。如果说这就是整体利益,权利问题的提出就是要对抗这种整体利益。而真正的整体利益则只能是权利高扬的产物。
参考:
[1]欧阳康.研究方法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53.
[2]梁慧星.民法解释学[M].武汉: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80.
[3]See E thridge, Done: Research Methodlolgy in applied Economics, I owa University Press, 1995:24~25.
[4]严平.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评[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18.
[5]约翰·沃特金斯.反对“常规科学”[G]//载伊·拉卡托斯,艾·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32.
[6]刘水林.法学方法论研究[J].法学研究,2001(3).
[7]德怀特·沃尔多.政治学.传统、学科、专业、科学、事业[G]//格林斯坦·波尔斯.政治学手册精选(上)[G]//竺乾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95.
[8]胡玉鸿.法学方法论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180.
[9]B.B.拉扎列夫.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王哲,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16、17.
[10]葛洪义.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3.
[11]安东尼·弗卢.哲学辞典.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79:141.
[12]亚里士多德.颜一,秦典华,译.政治学[G]//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中国大学人民出版社,1994:7.
[13]E·迪尔凯姆.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19.
[14]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2.
[15]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G]//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8.
[16]余谋昌.生态学哲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35~36.
[17]See J.B.Callicott,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 of the Land Ethic, in M. E. Zimmerman et al., e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Prentice~Hall, p. 110~134.
[18]See J.B.Callicott, Animal Liberation: A Triangular Affair, Environmental Ethics (winter , 1980).
[19]李培超.自然的伦理尊严[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13.
[20]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基本主题的再反省与再批评[M].济南:三联书店,1988:153.
[21]葛洪义.探索与对话:法理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7.
[22]韩非子·诡使.
[23]See E. Katz, Organism, Community, and the Substitution Problem, Environmental Ethics (Fall, 1985).
[24]T·Regan,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Routlege ,1984, 1988), pp361~362, p372.
[25]M·Kheel, The Liberation of Nature: A Circular Affair, Environmental Ethics (Summer, 1985).
[26]吕忠梅.环境权力与权利的重构——论民法与环境法的沟通与协调[J].法律科学,2000:(5):77-86.
[27]陈泉生.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43~154.
[28]蔡守秋.环境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39.
[29]蔡守秋.环境政策法律问题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94.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环境立法目的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48.
[30]See John. C. Lilly,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 and Dolphin: The Possibilities of Taking with Other Species. See David S. Favre, Wildlife Cases, Laws and Policy, Associatied Faculty Press, Washington 1983, p237~238.
[31]陶锡良.环境伦理与环境法[J].政治与法律,1996(2):11.
[32]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4-45.
[33]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74~375.
[3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458.
[3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35.
[36]周训芳.环境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36.
[37]H·霍尔茨.自然、技术、生态学[J].柴方国,译.国外社会科学,1989(8):6.
[38]See J. Passmore, 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 Scribner’s, New York, 1974.
[39]托马斯·弗莱纳.人权是什么?(中译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9.
[40]胡玉鸿.法学方法论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188-190.
[41]See Martin Staniland, What is Pohlitioal Economy, A Study of Social Theory and Undere Mplot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6.
[42]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486-487.
[43]郭秋永.政治学方法论研究专集[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126.
[44]迈克尔·H·莱斯诺夫.冯克利,译.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23.
[45]马克斯·韦伯.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7-48.
[46]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M].梁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39.
[47]爱因·兰德.新个体主义伦理观[M].秦裕,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100-101.
[48]姚建宗.法治的生态环境[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171.
[49]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曹玉堂,杨知,译.华夏出版社,1989:141.
[5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99.
[51]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38.
[52]See Collins, D. and Barkdull, J., (1995). Capitalism, Environmentalism, and Mediating Structures: From Adam Smith to Stakeholder Panels, Environmental Ethics, 17(3): p 227-244.
[53]See Waks, Leonard J. , (1996). Environmental Claims and Citizen Rights, Environmental Ethics, 18(2): p 133~148.
[54]赵红梅,于文轩.环境权的法理念解析与法技术构造——一种社会法的解读[J].法商研究,2004(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