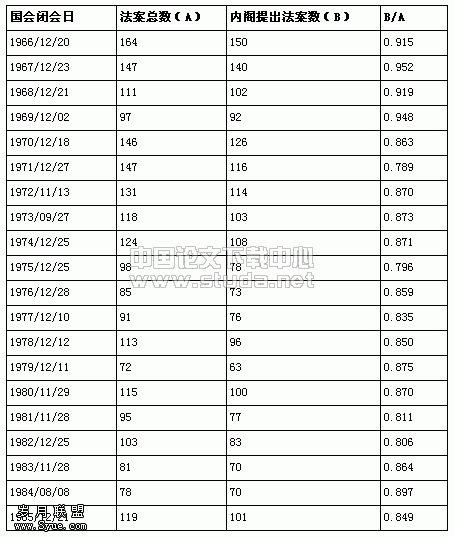道德之剑的熔铸 ——也谈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构筑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7-07
[关键词]职业道德 道德强制 道德教育泛化
在展开本文之初,首先有必要就“道德”这一语词给出个大致明确的定义:所谓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⑴虽然在不同的语境中我们对道德的起源、形成、表现形态等方面尚存有诸多争议,但大家基本能够认同: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⑵。也就是说,道德区别于、党纪政纪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依靠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人们内心信念的力量来保证人们对它的遵守。
在转型的时期的中国,由于旧的社会规范机制正处于变动不居的整合过程中,人们对道德危机的忧虑也日渐深重。而市场的兴起更强化了全社会对诚信等道德规范的呼吁。因而,近几年来,各行各业在各自职业道德的构筑方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关注。正是在这些背景下,同时也因应法官职业特质不断突显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并以其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虽然该准则更多地体现出了对西方法治经验的借鉴和模仿,而殊少对本土传统资源的吸收,但其间昭示的先进司法理念,及其构画出的中国未来法官的大致风范,无疑是令人鼓舞的。一时间也引起了媒体的好评如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整顿清理法官队伍,提升法官群体素质”的制度性功能⑶。
但在笔者看来,《准则》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或仅在于:概括和宣示既有的优秀道德品格,引领法官职业道德的方向,促进对法官职业道德的认知和统一——也就是说,它的功能在于“教化”而非“强制”——其理由就在于本文文首关于道德调整方式的认识。而当前一些关于《准则》的评论和赞誉以及热望,却体现出了关于法官职业道德体系构筑的某些令人不安的倾向。
这些倾向之一就是把法官职业道德混同于法官执业纪律,并试图以法律的或者有关组织的惩戒措施作为其实施的保障,我将其归纳为道德强制的倾向。其二就是单纯强调和依赖道德教育,忽略相关物质、体制、文化等方面配套措施的作用,这里我将它归纳为道德教育泛化的倾向。
以下分析之。
一、防止道德强制。
我在这里之所以使用“道德强制”而不是使用语法上更为精确的“道德强制化”,是为了同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大量存在着的道德法律化现象相区别。必须认识到,那些经由法定程序被赋予强制拘束力的道德规范,它所体现出的已经是法律的或者制度的属性,而不全甚而不主要是道德的力量。因此,无论从形式上抑或从内容上它都已是法律。显然,在就道德与法律的上述分野达成共识后,我们将把一些“执业纪律”、“职业守则”,排除出本文所讨论的职业道德的范围。
在网上我们却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近期,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制定了《干警业外活动行为规范》,其中第二十五条并规定“本规范由院政工科负责检查落实”⑷。而福建泉州市丰泽法院同一时期也出台了《五个不得》规范,并在其中相应制订了一些诸如“黄牌警告”、“给予严厉纪律处分”的处罚措施。⑸这两个规范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均“是根据《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有关要求制订的。”所不同的是,前者赋予规定的是组织保障,后者所仰仗的却是制度方面的力量。
在这里笔者无意于就上述这两个规范内容的妥当性提出质疑,而制订相关纪律条例以管理队伍的作法似亦无可厚非。但是,从行文看来,两个规范显然都具有贯彻实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初衷。也就是说,正如一种观点认为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在实施上还欠缺一些刚性。“《准则》具体规定了法官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但对“不能做”没有制订具体的惩戒措施……这是《准则》的不足”⑹,因而,“为增强《准则》的可操作性,便有必要制定相关惩戒措施”。而在笔者以为,正是这种认识和作法反映出了某种道德强制的危险倾向——如果说它还没有真正犯下道德强制之错误的话。
《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毕竟不同于《行为准则》,虽然其间的很多内容在笔者看来可以且有必要以《行为准则》的方式赋予其强制拘束力。但它同样还有部分内容是着重于内在调整的,无法加以外化或者量化。况且既冠之以“职业道德”之名,就应当局限在道德的范畴中发挥作用。否则有“名不正而言不顺”之嫌。此外,《准则》系由最高人民法院制订,从法理上讲并不具有法规的效力。而如果将《准则》中的规定作为对法官实施惩戒的依据,则会同《法官法》第八条第(三)项之“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处分”规定相抵触,从而导致《准则》本身无效的后果。显然,这在逻辑上亦不足以自洽。
从本质上看,道德是把善的意志作为其要求对象的,它所倡导的实际是人心而非行为。在道德所由立足之处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它在界定了是非善恶而外,却并没有取消人们选择恶的自由,于是善的内心在这种自由的选择中得以彰显。而如果走向道德强制,实质就是以强制手段迫使人们行善,由此将导致道德本身流于形式而与行为人内心意志相脱节,并有可能带来普遍虚伪的产生。故而,“过分地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把它变得如同法律一样威严,不可侵犯,其结果是取消了道德,磨灭了人们的道德意识,把所谓德行变得徒具虚名。”⑺
当然笔者并非对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道德法律化及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竟合的现象视而不见。如前所述,甚至《准则》中亦有许多规定对于法官从业行为是起码的,因而有必要依法定程序使之法律化或制度化。但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毕竟是如此不同,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道德与礼、法上就纠缠不清的国度里,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中国法官比之其他一些地域的同行们本就背负了过多法律之外的承载(例如责任、道义责任),并因此而在一定程序上丧失了其应具的超然地位。那么,如果再加诸内容本就有些漫漶不清的道德强制,会不会使得法官们从此就更加如履薄冰呢?——毕竟,司法改革作为一项综合工程,其主体之一就是法官,因此少不了法官的主观努力以至大胆创新——或者,会不会使得我们本就不甚坚强的法官职业保障和身份保障制度更加流于形式呢?
当然,事实远未严重到这种地步,前景也并非必然如此。但,对这样的可能性保留一点清醒的认识,这在笔者看来却并不能说是杞人忧天。
二、防止道德泛化。
道德着重于对人内心信念的调整,因而道德教育也就成为构筑一定道德体系最为基础性的手段。于是可能会有人认为,随着《准则》的颁布,只要以《准则》内容为纲要在法官群体中不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依靠这种日积月累,一个良好的并能得到严格遵循的法官职业道德体系将会是水到渠成。当然,这种持之以恒的观念灌输其效用不可轻视。但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总是决定于一定的基础,因而“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⑻。在这一意义上说,审判实践和生活实践才是法官职业道德形成的基础。而那种自上而下的观念灌输,在大多数情形下只能让法官们认识到,什么样的职业道德观念是被最高法院所要求的。
那么,怎样保证法官们在自己审判实践和生活实践中累积所得的职业道德观念契合于《准则》的要求(无疑,这是我们构筑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重要目标)?甚至,怎样保证法官们在可能的选择中一体从善,从而将良好的职业道德追求化成自己的内在需要?以及,在不断变迁着的观念冲击下又如何保证法官们的清醒和坚定?
我们可以看到,《准则》在法官的独立性、中立性、超然性和智识素养等方面体现出浓厚的西方法文化背景。某些方面甚至同我们的现行制度实践有所不容。因此我们要移植的就不仅仅是几个关于道德要求的条文,还应包括相关的理论体系,配套制度。比如,捍卫审判独立不仅应是对法官的职业道德要求,而更应当成为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而且,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刚性的职业保障制度使法官们有所倚仗。否则,漠视法官们可能付出的惨痛代价,这既不人道,也势将导致法官们产生对权力(而非权利)无条件的服从意识,并视之为当然的“道德”。比如,在一个习惯于将法律问题道德化、政治化,动辄追问“立场何在”的环境中,法官们优先考虑的将是“立场问题”,“中立性”之缺位乃势所必然。再比如在一个业务经费、收入均与地方利益攸关的社区中,要想法官们有意识保持自己相对的超然地位恐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将法官混同于普通公务员实施管理,尤其是以行政化的思维指导审判工作,将极大弱化审判工作中应有的对法官智识的挑战,在禁锢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亦将无法提升法官的整体智识素养。——在对我们建国以来法治实践的种种反思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文化和制度实践上的种种背离之处,导致了我们的法官普遍的理念?
可以说,单纯的道德甚至不能保证法官们职业道德观念的性。
其次,认识到“什么是道德要求的”并不一定会导致道德的行为,这里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将对良好道德的追求转化为行为人的内在需要。毕竟,道德也只有在行为主体将其内在化时才真正生效。尤其在人们对法官职业提出了比之社会平均道德水平为高的要求之情形下⑼,这一点尤其显得重要。依笔者看来,有两者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高度的职业尊荣感,其二是职业内部的高度同质性。
高度的职业尊荣感将保证法官们精神上的自足,于是与职业相联系的道德追求便成为从业的当然内容。更重要的是,高度的的职业尊荣感必将附带产生致力维护共同职业形象的内在动力,而这正与法官们应具的道德追求不谋而合。但是,职业尊荣感并不能凭空产生,它需要高于平均水平的且稳定的收入以维持体面的生活,需要庄重的办公环境,相对舒适、便利的办公条件,富有挑战的且能给人以成就感的工作内容,社会普遍的对他们职业群体的尊重(当然,这尊重不仅将源于他们手中的赫赫威权,更还将来自于对他们整体学识和能力的景仰,且这种景仰只能依赖严格的职业选任机制来保证)。
职业内部的高度同质性在这里是指法官从业人员的教育背景、知识背景和生活背景的一致。毫无疑问,这种高度同质性将促成从业人员价值观念的同一,从而极大的推动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建构。同时,相似的教育背景和生活背景所带来的知识和能力方面的大体相近,将使得对业内人员高下的评判标准更多的倾向于道德内容,共同的职业团体利益也使同行们更为注重对共同的职业形象的维护。并且,就道德而言,较之外界监督,“来自同事的否定评价才是毁灭性的”⑽
因此,单纯的道德教育同样不能保证良好的道德追求能够当然成为法官们的内在需要。
而法官职业道德在中立性等方面有着与公众道德不同的特点,这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法官职业活动中的道德冲突。例如很多时候公众道德要求我们嫉恶如仇,而法官职业道德却强调对诉讼各方(包括刑事被告)的平等对待⑾。此外,移植于西方的一些制度在很多时候将面临传统道德观念的挑战,且往往“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当挑战因传统道德与职业道德的混淆而演化为对法官个人办案的道德责难,就会动摇法官们依法办案的信念。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越来越多的人将对财富的获取视为个人人生价值的标尺时,如何避免这些观念对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冲击亦是重要课题。在这些方面,我们同样需要社会公众对法官职业特质的尊重和认同,甚至是一定情形下的宽容。同样需要物质、制度和文化诸方面综合的投入。
在上述对道德教育泛化之危险的简单论证中,笔者越来越感觉到它与道德强制之间潜伏的联系。表面看来,二者是各自走向一个极端。但二者其实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根源:即在法官职业道德的构筑中,二者都忽略了法官作为其间主体的作用。事实上,正是怀疑法官在其职业道德追求中的自觉性导致了道德强制,而正是漠视法官在其职业道德构建中的能动作用导致了道德教育的泛化。
危险的根源既已凸现,避免危险的路途便不言自明。
三、对本文的检讨
法官职业道德体系的构筑在时下是一个很流行的话题,要在其间作出有价值的思考确已显得艰难。并且,对道德本身的思考势必要超越道德的境界以寻求新的价值坐标,这在冯友兰老先生看来,就须得深入到哲象的领域了,或许仅此还显得不够。于是在草就本文之际笔者一如从前地痛感到自己理论储备的贪乏。在这里我大胆提出了要避免法官职业道德体系构筑中的两个可能的错误倾向。相比之下,对道德强制的分析更深入,这方面由于有上的若干教训,相信大家会有更多体会。而对道德教育泛化的倾向,在笔者看来,这更多的涉及到的其实只是一些常识,因而对此的展开也并不充分。当然,即使是常识有时也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过去了,所以适当地提及亦有必要。最后关于道德强制和道德教育泛化的认识根源,可说是本文的核心观点,但其引出却略显得突兀 ,这或是本文最重要的缺憾。
法官职业道德的构筑是我们司法改革中的重要课题,其成败也将直接影响到司法改革的成败。确然,《准则》为我们构画了一个的,令人鼓舞的蓝图,但即使有了各方面的投入和努力,这蓝图的实现仍须法官群体付出艰辛,甚至是巨大的牺牲,或许,由于路途的漫长,甚至大部分牺牲亦会显得寂寞。但那样的境界值得去努力。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⑿,笔者不但心向往之,亦深信这样的付出最终会有所回报。
注⑴:《汉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 P259
注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P15
注⑶:可参见http://www.yxfq.com / rsbw /0194.htm
注⑷:见 http://www.hp.gov.cn/hpfy/gzzd/ ywgf.htm.
注⑸:见 http://www.qzweb.com.cn/gb/content/2001-12/26/content--368858.htm .
注⑹:《建立违反法官职业道德的惩戒程序》 黄天优 人民法院报 2002年8月31日第3版。但在笔者看来,最高法院在《准则》中未规定惩戒措施,或正是出于避免道德强制的考虑?
注⑺:《寻求秩序中的和谐》梁治平著 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P273
注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P133
注⑼:这一点从《准则》的内容上可以看出
注⑽:《具体法治》 贺卫方著 出版社 2002年出版 P16
注⑾:见《准则》第十条
注⑿:见《史记· 孔子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