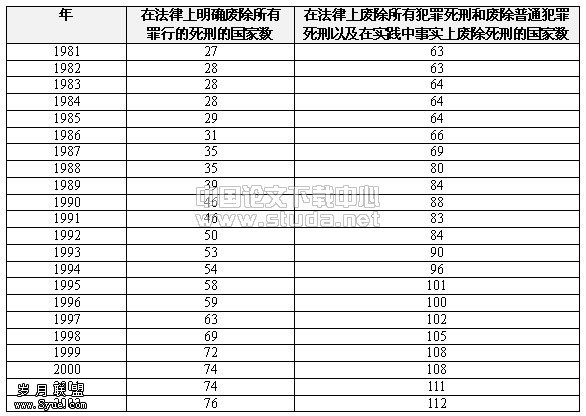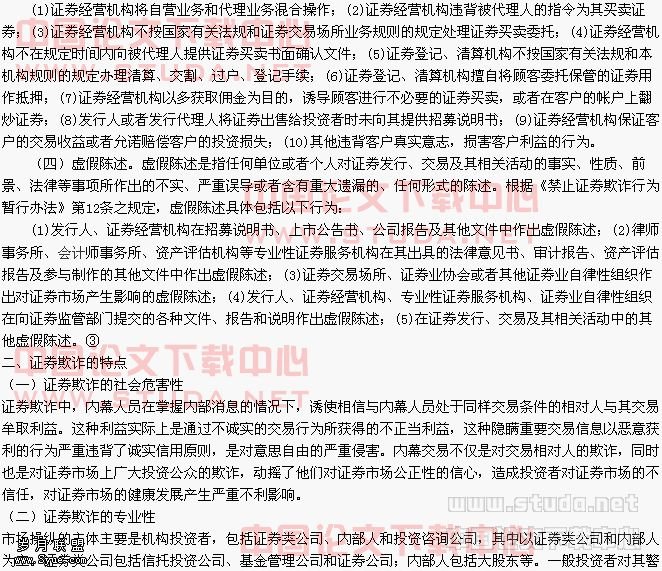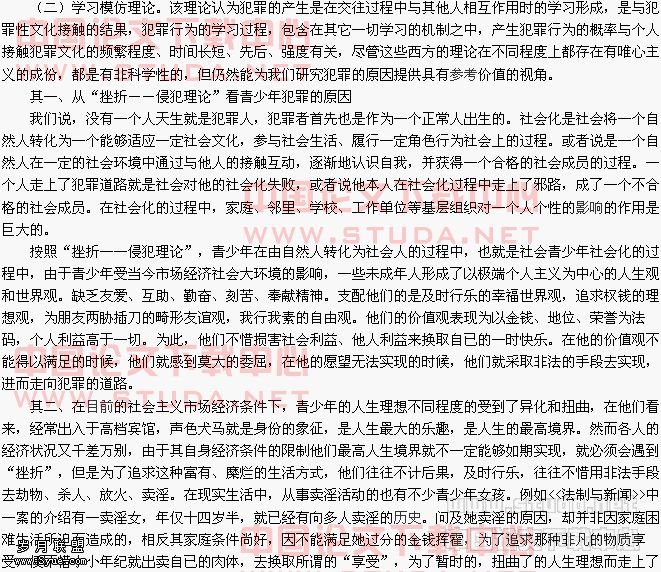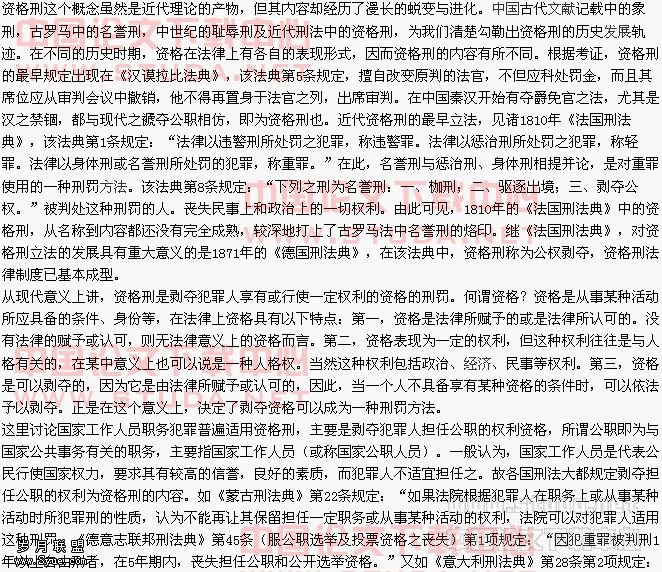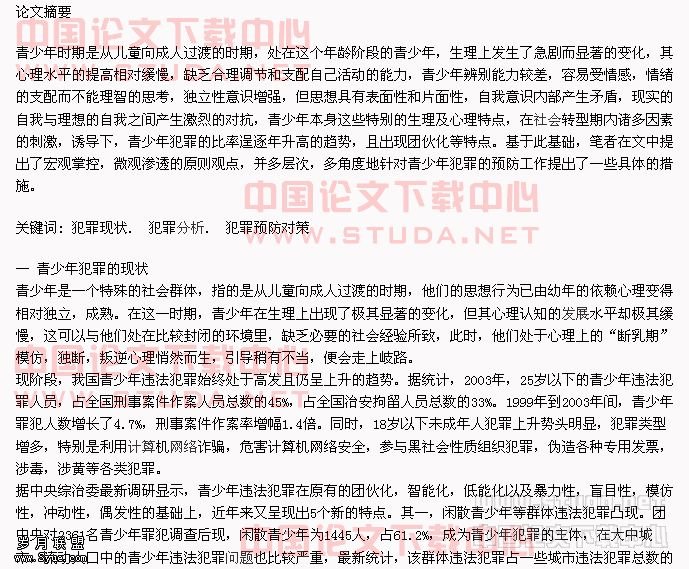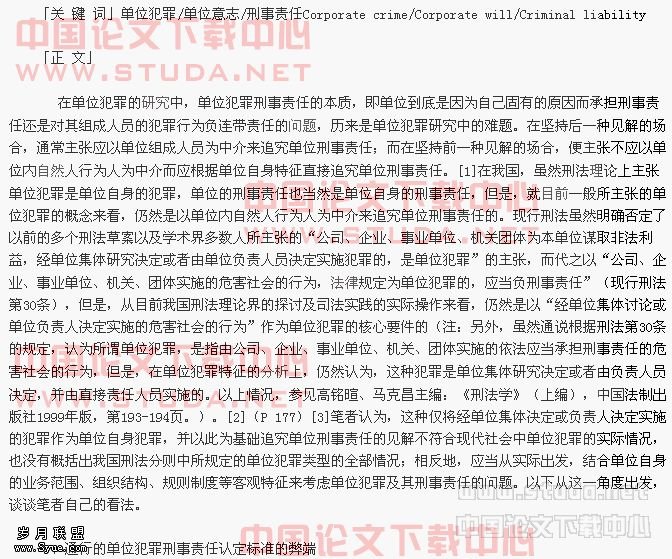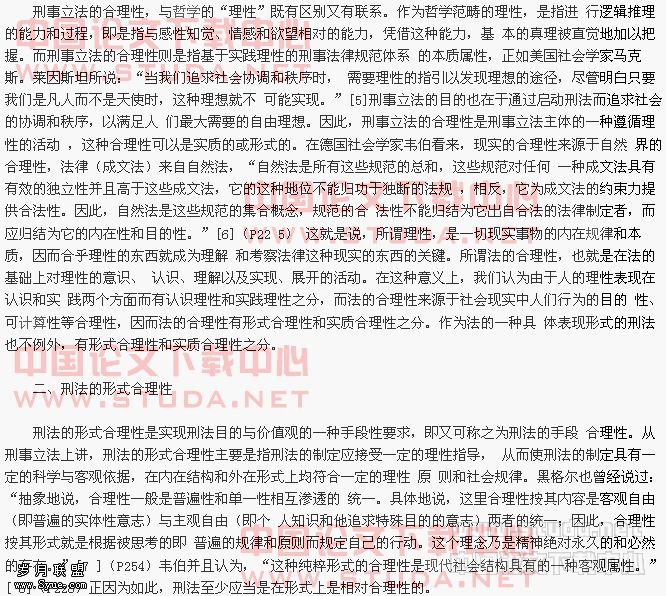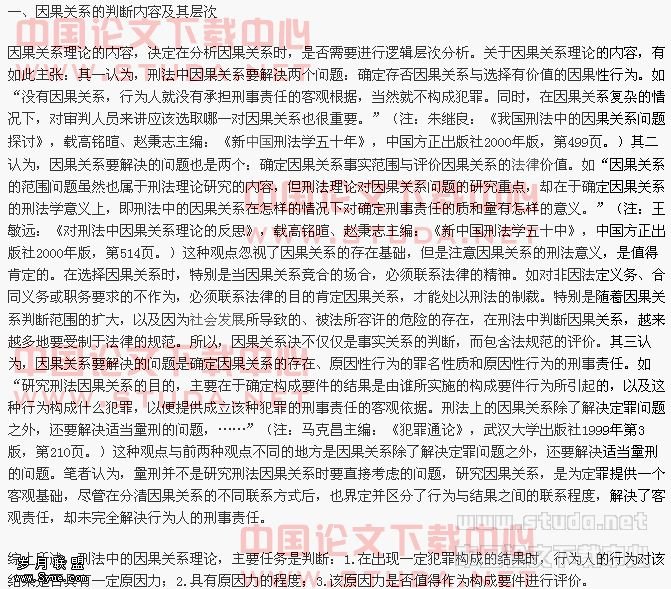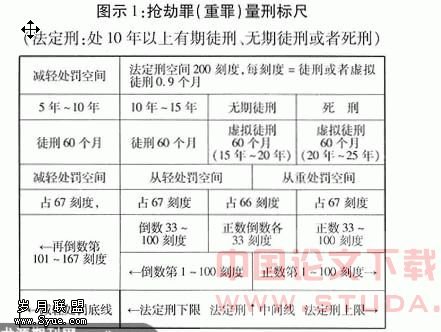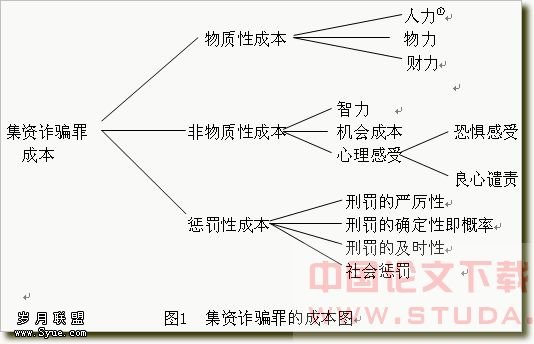论逐步强化刑事审前获得律师帮助权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7-07
[关键词]刑事审前获得律师帮助权;必要性;循序渐进
我国公诉案件刑事审前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获得辩护律师帮助的权利在司法和立法两个方面都得不到重视和保障。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学界讨论热烈。有学者指出要改革证据制度,增加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有学者认为要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还有学者主张要重构刑事审前程序结构。本文拟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一、循序渐进地强化和完善我国刑事审前获得律师帮助权的必要性
(一)循序渐进地强化和完善我国刑事审前获得律师帮助权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保障犯罪嫌疑人真正成为程序主体,实现不纵不枉、既打击犯罪又保护人民的目的
在刑事诉讼中,为了查明案件真相,专门机关在必要的情况下实施拘留、逮捕等项强制措施,来限制一定社会成员的自由权是必需的。但是为了实现公平的目的,被追诉者在自由权受限制的同时,其应当享有必要的程序性权利,尤其是获得律师帮助权。因为在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情况下,很多没犯罪又没有经验的犯罪嫌疑人极易被强大的国家机器吓懵了而不知所措,无法正当、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包括辩护权。于是他就极易被冤枉。这时律师如果能以辩护人的身份有效地介入到所有的诉讼程序包括侦查程序中,以自己专业的知识和超脱于诉讼纠纷的地位,为委托人提供帮助,那么司法机关就更容易发现真实,保障公民的权利,实现正义。
另一方面,即使一个人真的做了坏事,他仍然是人,仍然具有合法权益。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具体而言,我们不能为了发现真实、侦破案件而把人当作手段,用牺牲他的合法权益的方式,如对其肆意进行羁押与对待,来获得证据。况且,在诉讼没有进行完毕,尚未有生效判决确定某人有罪时,任何人都应被推定为无罪。所以在此种情况下,也必须保护这一部分嫌疑人的获得律师帮助权。
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如果犯罪嫌疑人确实是罪犯,那么辩护人在侦查阶段的介入,在事实上会减少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给其以喘息之机,确实会降低突击审讯的效果,给侦查案件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加之律师职业的商业化,律师的诉讼文化和信仰难免沾染功利性,“实现委托人合法利益最大化”的宗旨容易为追逐名利而超越法律底线,“辩护律师,特别是为确实有罪的被告辩护时,他的工作应是用一切合法手段来隐瞒‘全部事实”。正因为如此,我国的公安、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审前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一向持否定态度,予以限制。也正是基于这种不利影响,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享有的律师帮助权应当设置例外,特别是律师的讯问在场权和会见交流权不能一概适用所有的刑事案件,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重大犯罪集团的案件、恐怖活动、黑社会犯罪等重大案件面前,必须作出让步,应当作出例外的规定。总之,在审前程序中,我们不能一下将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权放得过宽,必须循序渐进。
也许有人会说,公安、检察机关内部的法律规章也要求其保障公民的权利,获得律师帮助权会不会多此一举。我们应该看到,在现实生活中,犯罪嫌疑人如果缺乏辩护人的帮助,则处于既缺少法律知识(即使了解法律,作用也不大),又孤立无援的状态。再加上作为“坏人”被羁押,其肆意被对待的可能性就很大,合法权益的保护的需要就很迫切。此时,仅靠公安、检察机关依据法律和纪律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公安、检察机关的职责主要是追究犯罪,当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和追究犯罪的目的发生冲突时,公安、检察机关很地会选择后者,而牺牲犯罪嫌疑人的部分合法权利。所以,要想真正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必须在诉讼一开始就设置另一方力量即律师,从外部制约公安、检察机关的权力,使其在合法的轨道上行使。
(二)循序渐进地强化和完善我国刑事审前获得律师帮助权有助于彻底贯彻无罪推定之原则
无罪推定作为一项思想理论原则是由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提出来的。在《论犯罪与刑罚》中,贝卡里亚抨击了践踏基本人权的刑讯逼供和有罪推定,提出了关于无罪推定的理论框架: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因为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是无罪的人。无罪推定之原则内容包括:(1)法院是可以进行有罪裁判的唯一主体。(2)法院只有通过合法、正当的程序才能作出有罪判决。没有经过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法院不能从法律上判决一个人有罪,即使这个人事实上确实犯有罪行。(3)被追诉者的罪行须经依法证明才能确定。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由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来承担。犯罪嫌疑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当追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判断尚存怀疑时,应作出对其有利的解释。(4)证明有罪的证据必须达到充分的程度,即使法院确信某人有罪而无合理怀疑的程度。否则仍然不能使任何人成为罪犯。(5)被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应拥有为对抗国家追诉权所必备的程序保障。被追诉人在无罪推定原则的保障下,可获得一系列旨在对抗国家追诉权的诉讼特权和程序保障。这些特权和保障旨在确保被追诉者拥有足以与国家追诉机关相对抗的武器,使国家与个人之间天然的力量不平衡状态得到纠正。
只有强化、完善审前获得律师帮助权,才能保证诉讼程序的正当,才能保证证明责任真正由国家追诉机关来承担,才能保证被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拥有对抗国家追诉权所必备的程序保障,才能避免公安、检察机关变成实质上的裁判者、法院成为摆设。这一切的原因就在于:只有真正获得律师的帮助,嫌疑人才可能免于被刑讯或变相刑讯。
为了防止某些犯罪嫌疑人串供、伪造、毁灭证据、逃避、破坏侦查、起诉,危害社会并保证嫌疑人随传随到,也就是为了达到发现真实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而不得已要对其进行羁押。这种羁押状态使得犯罪嫌疑人在形式上与罪犯无异。在审前程序中如果只有追溯方的追诉和羁押,而缺少律师的有效帮助和辩护,这种无罪推定之原则就还只是停留在文本上,至少说是不彻底的。如何解决这种形式有罪而实质上推定为无罪的矛盾,彻底贯彻无罪推定之原则呢?强化、完善犯罪嫌疑人审前获得律师帮助权,设置独立的一方主体为犯罪嫌疑人争取、主张权利,衡平这种形式上的不平衡,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三)循序渐进地强化和完善我国刑事审前获得律师帮助权有助于实现程序正义
刑事诉讼中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有两项要求:一是程序的参与性;二是程序的对等性。前者的核心思想是,权益可能会受到刑事诉讼结局直接影响的主体应有充分的机会并富有意义地参与诉讼结果的制作过程,进而对该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的影响;后者是指控辩双方具有平等的攻击和防御的机会和手段,以及均等的机会提供证据以说服裁判者。
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来说,作为“阶下囚”,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他的诉讼权利很难实现,很难充分参与诉讼。此时,只有由辩护律师介入到审前程序中,弥补他自由上的缺失,嫌疑人才能真正实现其程序权利,成为程序主体,实现程序正义。 二、如何循序渐进地强化、完善刑事审前获得律师帮助权
刑事审前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权不受重视的主观方面的原因在于,我国很多公安、检察等刑事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存有偏见。他们总是认为律师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审前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会见犯罪嫌疑人一定会干扰侦查,破坏诉讼。审前获得律师帮助权不受重视的客观方面的原因在于:第一,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规则的设计方面存在瑕疵。具体而言包括:犯罪嫌疑人缺少不自证己罪的权利;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地位不明确,在审前程序中的权利太少;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则在逻辑结构方面存在缺失;我国刑事审判前程序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第二,我国极少数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存在某些不法的行为。针对现存问题解决方案如下:
(一)补足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则逻辑结构的缺失
众所周知,一个完整的规则应该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个部分。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则逻辑结构中却缺少法律后果的规定。权利人受到侵害后不知道侵权人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也不可以向法院寻求救济。按照权利救济的一般理论,诉讼程序意义上的“救济”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实体性救济”,也就是针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违反法律程序、剥夺律师辩护权利的行为,确立程序性制裁措施;二是“程序性救济”,亦即作为被侵权者的嫌疑人、辩护律师,针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剥夺其辩护权利的行为,获得向法院申请司法裁判的机会,从而促使法院对审判前程序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其中,“实体性救济”作为授权性规则中的“法律后果”要素,具有确定侵权行为之法律责任的功能。没有这一要素,任何权利在遭受侵犯之后就无法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程序性救济”作为一种诉权要素,构成所有权利赖以实现的中介和桥梁,甚至可以被视为诉诸司法机关加以裁判的诉讼权利。没有“程序性救济”,法律即便确立了“违反法律程序行为的法律后果”,这些条款也会形同具文,侵权行为不会受到自动的制裁,被侵权者更不会获得有效的救济。
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应该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这些规则的逻辑结构补足,既要规定“实体性救济”又要规定“程序性救济”。即规定如果公安、检察机关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获得律师帮助权,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可以请求法院认定公安、检察机关程序违法,其由违法行为取得的某些口供应予排除,即达到证据失权的效果,实行程序性制裁。美国曾有学者提议:律师于审讯中必须在场,无律师在场,警察不得讯问被告,否则所取得之自白不得为证据,如此才能有效防制警察对受讯问人心理的强制力。
实行程序性制裁,排除非法证据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作用。早在19世纪,边沁就强调:证据是正义的基石,排除证据就等于排除正义。至20世纪时,知名大法官卡多佐亦言:证据不得任意排除,否则岂不因警察的一时过失而让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可见排除证据对于发现真实、侦破案件非常不利。因此,我们在设定这一制度时必须慎重,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所谓循序渐进的原则有两层含义:一则,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设置应先从犯罪情节轻微的嫌疑人和罪行人手,对于严重危及公民人身安全、国家社会安全的犯罪暂不能适用,到经验丰富、条件成熟时再视情况逐步推广。二则,要同时采取“裁量权排除主义”。即法律只作原则性规定,若警察违法取证,应由法官考虑警察违法的主观意思、违法的严重性、被告所犯的罪行等因素,斟酌个案之公平正义而决定证据应否排除。
(二)逐步赋予犯罪嫌疑人不自证己罪的权利
刑事审前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权不受重视的法律根源在于犯罪嫌疑人有义务自证其罪。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公安、检察机关据此认为逼迫犯罪嫌疑人供述罪行是天经地义的。公安、检察机关之所以要极力限制犯罪嫌疑人的获得律师帮助权,其主要目的是要封锁消息、防止干扰、突击审理,使犯罪嫌疑人处于信息不明且孤立无援的状态,打犯罪嫌疑人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以获取口供。据此,赋予犯罪嫌疑人不自证己罪的权利,有利于实现侦查人员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收集口供以外的证据,减少侦查人员隔离犯罪嫌疑人、逼迫口供甚至刑囚的动机。当然这一规定也必须循序渐进,先从轻罪开始。
(三)重塑我国刑事诉讼的审前程序结构
在侦查、审查起诉程序中,基本上只存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嫌疑人三方主体。犯罪嫌疑人的被追诉地位和国家的追诉者地位是先天性不平衡的。其原因:一是刑事诉讼证明的复杂性要求控诉方要有足够的力量;二是犯罪嫌疑人逃避追诉和审判的倾向使得审前羁押成为必然。因此,国家控诉权常常在事实上高于辩护权,尤其是偏重国家利益忽视个人利益的我国。公安、检察机关作为一个整体——追诉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其权力是绝对的。虽然有党委、人大等的监督,但基本上没有什么主体可以从法律技术的角度对追诉机关的权力运用进行经常性的审查监督。而绝对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那么犯罪嫌疑人的获得律师帮助权经常被侵犯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所以我们要重塑我国的刑事诉讼审前程序结构,将法院的审判权引入到审前程序中去,在审前程序中形成控辩审的基本“诉讼形态”,使法院的审判权可以从法律角度,经常性地、有效地审查制约追诉权。具体而言,也就是当追诉机关侵犯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尤其是获得律师帮助权时,嫌疑人及其律师、亲属可以向法院寻求救济,要求法院保护其权利。法院有权令追诉机关改正。 最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强化律师的职业自律,进一步加强公安、检察人员的思想工作,使广大干警真正认识到保障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和侦破案件是同等重要的。
下一篇:卷宗移送制度改革之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