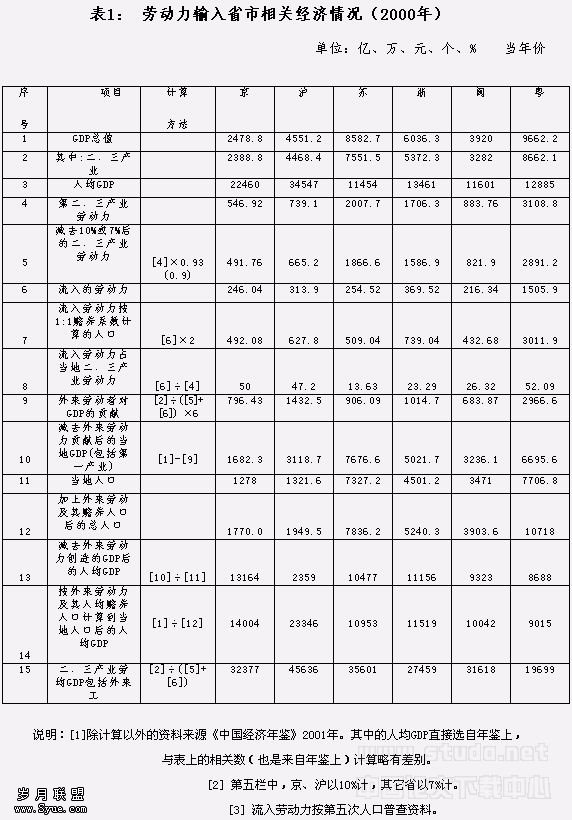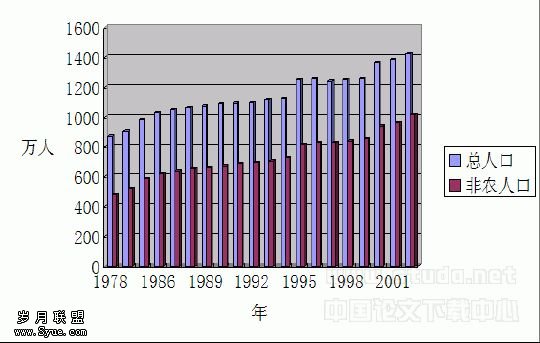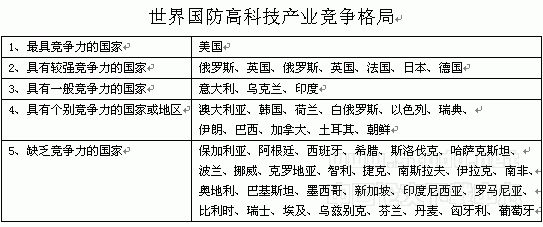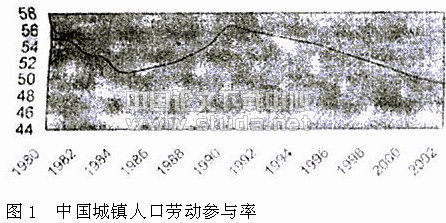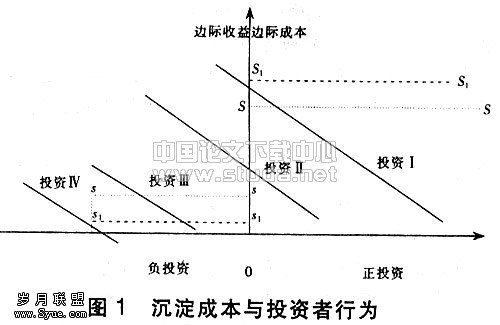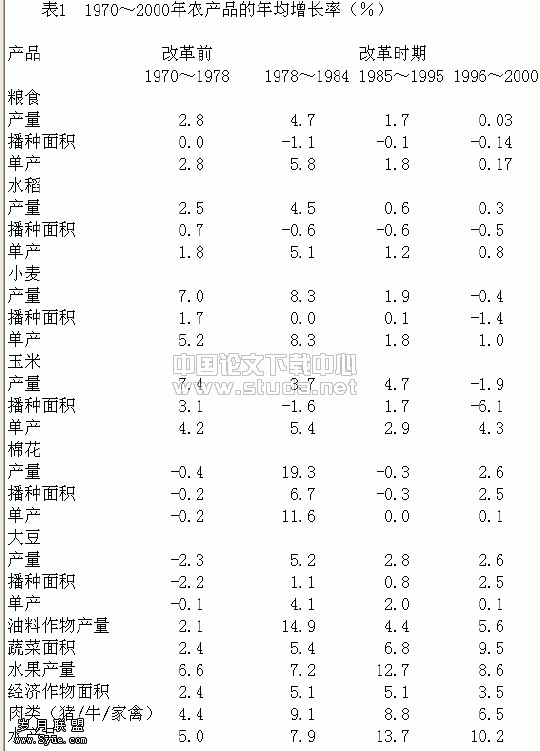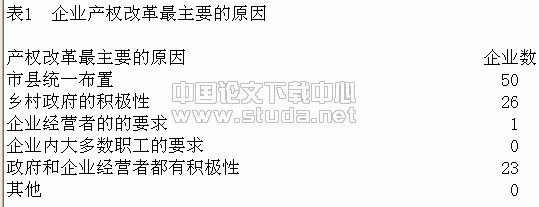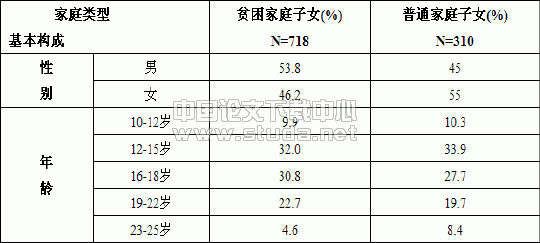沃勒斯坦:真正发现欧洲奇迹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白银资本》的中心议题,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1500年以降就存在着一个单一的全球世界,具有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1998:52;2000:90)①弗兰克在序言的第一句话里就告诉我们,该书的基本宗旨是“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1998:xv;2000:1)。对于读者来说,这里有两个问题。这个中心议题是真实的吗?如果是,弗兰克的著作有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让我们来分别考察这两个问题。
我们必须弄清楚这里所谓中心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按照弗兰克的叙述,它似乎是这样的:从1500年以降,确切地说是从1500年到1800年(因为关于1800年以后的历史研究争议要小得多),全球而不仅是它的某些部分通过一个单一的劳动分工体系而联系在一起。弗兰克还加上一条“和多边贸易”,不过在我看来这纯属画蛇添足。因为如果存在着劳动分工,就必定存在着贸易,而且这种贸易几乎必然是多边的。应该提出的问题恰好相反:如果存在着贸易,是不是必然存在着单一的劳动分工体系?
这种争论和欧洲中心主义有什么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弗兰克也是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的。他希望证明“从一种全球视野来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1998:xiv;2000:2)。弗兰克说是亚洲,但实际上他书中主要谈论的是。或者更确切地说,弗兰克建构了一个重要性的等级结构:中国位于顶端,印度处于中间,欧洲则被打入底层。奥斯曼-阿拉伯地带在他的大部分论述中非常奇怪地消失了。无论如何,弗兰克宣称他一举“摧毁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拉尼、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以及其他许多社会理论家的反历史的、反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根基”(1998:xv-xvi;2000:2)。我是不是应当说一些不胜荣幸或受宠若惊之类的客套话呢?
弗兰克在序言里还提出两个值得分析的问题。一个是“把世界经济或世界体系称作‘资本主义的’究竟意味着什么?”(1998:xv;2000:6)。第二个问题是弗兰克断言“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兴起’来得比较晚,而且比较短暂”(1998:xxiv;2000:13)。
在序言里资本主义还被小心翼翼地描述为某种意义可疑的东西(“如果毕竟有点什么意思的话”),但是到了第15页就变成了“马克思想像的产物”。按照弗兰克的看法,资本主义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如果它毕竟存在的话,也是自从有史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简而言之,资本主义不是在历史时间里某些时刻和某些地域的区别性特征。它既不是一个体系,也不是一种生产方式,更不是一种可以认识的现实。我们应当告诉那些竟然敢于反抗资本家的野蛮暴行的蒙昧无知的人们,资本主义的受害者是不存在的。可怜的弗兰克,他本人曾经不遗余力地投身于这种反抗斗争,今天他似乎对此深表遗憾。
“西方的兴起”成了弗兰克的一个大难题,因为在他所建立的分析框架里根本无法说明西方的兴起,不管它是怎样地姗姗来迟和昙花一现。然而,即便是弗兰克也无法完全抹煞欧洲的财富、军事力量以及对世界的帝国主义统治,至少是在1800年-1950年期间。由于不能给出任何可能的解释,欧洲的霸权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奇迹。这并不是说弗兰克对此完全没有作出解释。他的解释是:“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1998:4-5;2000:26)但是请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暴发户能够“强行分沾”你的市场的好处并且从你的背上往上爬,那么你的支配地位究竟是什么意思?弗兰克使用的另一个隐喻也未能把故事讲得清楚一些:“我的观点是……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车厢座位,然后又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的火车头的位置。”(1998:37;2000:69)这是一个穷人如何发家致富的故事。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从穷光蛋变成阔佬,只有那些工作勤奋、生活节俭而且具有新教伦理的人,才能够享有致富的光荣。不过隐喻已经够多了,还是让我们书归正传罢。
弗兰克是如何证明从1500年到1800年期间(有时候他说1400年-1800年)存在着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而亚洲在这个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二章《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1400年-1800年》以比较审慎的方式开始,但到结束时就相当直率了。最后一节题为《对以为中心的世界的》,认为直至18世纪末这个世界经济(世界和经济之间从来不用连接号,因为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世界经济,不管是同时的还是前后相继的),包括“省际、地区间和构成世界体系性的国际间的经济关系……一直被亚洲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支配着”--这种现实“体现在贸易平衡和货币流向的全球模式中” (1998:126;2000:181-1)。现在我们知道,贸易平衡和货币流向被用来作为单一世界体系的存在和亚洲的主导地位的关键证据。我们是不是应当这样来理解弗兰克呢?他现在终于恢复了他长期以来嗤之以鼻的芝加哥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身份?
他是怎样论证贸易平衡的?他告诉我们,有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的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1998:126-7;2000:181)。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贸易逆差,非洲则靠出口黄金和奴隶弥补逆差。因此,这三个地区都能够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似乎不能生产任何其他地区的其他人所需要的任何商品。于是无能的欧洲人只能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来过日子。照弗兰克这样的描述来看,欧洲人简直连街头吃白相饭的泼皮无赖都不如。
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经济的中心”(1998:127;2000:182),中国比印度又更胜一筹。它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当然是靠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绝对和相对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它们的贸易才能保持“最大的顺差”,尤其是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1998:127;2000:182)。在这里弗兰克提到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关于13世纪世界体系的论述,这个世界体系由八个互相重叠的椭圆形地区特别是其中的三个主要地区构成。阿布-卢格霍德强调各个区域发挥大致相等的作用,但这一点让弗兰克感到不满意。他喜欢另一种区域化的模式,一种“可以表现为同心圆”的模式(1998:129)。他所画的同心圆似乎相当精确:扬子江流域和中国南方处于最中心,接下来的一环是中国的其他地区,然后是滨下武志所描述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然后是亚洲地区圈或亚非地区圈,最后是在这个地带之外的欧洲和美洲。
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前提之上,即贸易顺差是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的标志。然而,弗兰克并不是从来都这样看问题的。在这本书里弗兰克对他以前的思想盟友展开口诛笔伐,对他自己以前所犯的错误表示忏悔,以此证明他在知识上取得的重大突破。我们却很想知道,弗兰克是否认为他在1990年代以前发表的大量著作还值得一读。我希望他不会把它们通通抛弃掉。我认为其中有些是很出色的著作,即使在今天也没有过时。
这里,我要提及1970年代在《欧洲经济史杂志》上发生的一场争论。争论是围绕19世纪末欧洲,尤其是大英帝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展开的。引发争论的是拜罗克(Paul Bairoch)的一篇文章。就经验事实而言,拜罗克和弗兰克不存在分歧。在1880年-1939年间,欧洲的对外商品贸易存在着大约20%的逆差。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1976年秋,弗兰克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批评拜罗克的观点;另一篇文章则致力于阐述他自己的观点,题为《多边商品贸易失调与不平衡的经济》(Frank:1976)。弗兰克断言并证明,“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整个时期,尤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发展中的宗主国(尤其是大英帝国)与“沦为欠发达的殖民地国家”之间存在着商品贸易的失衡。他论证说,这种贸易失衡“在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至关重要(1976:407)。
对谁有利的失衡?弗兰克实际上认为大英帝国与任何国家都既没有出口盈余也没有进口逆差,而欠发达地区的问题恰好相反:它们与任何国家都既没有出口逆差也没有进口盈余。世界上所有其他地区都介于这两者之间。在1976年的文章里,弗兰克由此得出下述结论:
这实际上意味着,即使按照世界市场价格来衡量,世界的欠发达地区由于商品出口超过商品进口,确实在直接间接地为世界所有其他地区提供资金(如果按照实际价值来衡量就更为严重了)。具体而言,欠发达国家的出口盈余(1)支持了欧洲过度的商品消费,表现为后者的商品出口逆差或进口盈余,(2)支持了美国和海外自治领对欧洲的出口盈余,(3)帮助了欧洲的国内投资和,(4)为欧洲在美国和海外自治领的对外投资提供了资金,从而促进了它们的发展,欠发达国家还为对它们自己的“对外”投资提供了大量资金,但这进一步加剧了它们的欠发达(1976:422)。
在这篇文章里,弗兰克似乎极力要证明,大英帝国在19世纪末剥削欠发达国家的方式是,从欠发达国家接受的商品要多于向那里输送的商品。但是现在在其新著中,弗兰克则要证明,在1500年-1800年的比欧洲强大,因为它向欧洲出口的商品远远多于从欧洲进口的商品。我决没有反对弗兰克改变自己观点的意思,即使是把以前的观点颠倒过来。也许他确实认为他以前犯了错误。只有一个问题:他现在是不是愿意在他的新理论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19世纪末欠发达国家要比大英帝国更为强大,因为它们向英国出口的商品多于从英国进口的商品?
第三章的标题是《货币周游世界,推动世界旋转》,讨论从贸易转移到货币。弗兰克告诉我们,货币是一种商品,是由供求法则支配的。按照弗兰克的观点,货币实际上成为最重要的商品。“正是对货币的需求才使市场上供应商品和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成为可能。因此,这种套利兑换的普遍实践本身已经反映了--或者有助于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市场”(1998:137;2000:195-6)。他问道,为什么中国需要这么多的货币?他的回答是,因为“货币支撑和制造着有效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刺激着供给”(1998:138;2000:196)。但是,弗兰克认为,货币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制造出有效需求,只有在已经具备生产能力,因此“有通过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来扩张生产能力的可能性”的地方,货币才能制造有效需求(1998:138;2000:196)。弗兰克说中国有这种能力。兰代斯说大英帝国有这种能力(1998,随处可见)。两个人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
这一章旨在证明世界的白银生产(弗兰克认为它是这一时期事实上的本位货币)的终点是中国,这又反过来证明了中国的经济实力。然而,弗兰克自己的数字并不能支持他的经验论据。我将按照表面价值来对待他的全部数字。在148页(中文版209页),他提供了一张1500年-1800年期间世界白银生产、出口和进口的图表。这张图表说明了什么问题?它表明在16世纪从美洲向欧洲输送了1.7万吨白银,欧洲没有向中国输送任何白银,日本向中国输送2000吨白银。16世纪的情况看来不够理想。但是在17世纪,有2.7万吨白银从美洲运往欧洲,其中的1.3万吨(约占一半)被运往中国,日本向中国输送了7000吨白银。到了18世纪,美洲向欧洲输送了5.4万吨白银,其中有2.6万吨(仍然是大约一半)转运到中国,日本则没有向中国输送白银。另外,还有美洲白银经马尼拉运往中国的传说。之所以说它是一个传说,是因为弗兰克不能肯定究竟有多少白银运往马尼拉,然后又有多少运往中国。他告诉我们,在1600年-1800年期间总数约在3000吨到1万吨上升至2.5万吨。
现在我们来作一下加减法。弗兰克表明在1500年-1800年期间,欧洲从美洲收到9.8万吨白银,其中3.9万吨运往中国,5.9万吨留在欧洲。中国从欧洲收到3.9万吨,从日本收到9000吨,又从美洲经马尼拉收到3000至2.5万吨,总计5.1万至7.7万吨白银。这个数目和留在欧洲的5.9万吨不是相差无几吗?这样看来,根据弗兰克的图表,在这个重要的时期,欧洲和中国同样是白银的“终极秘窖”。但是在这里我们应当把人口数字考虑进来,尤其是因为弗兰克认为人口数字特别重要。大致说来,这一时期欧洲的人口相当于中国的一半,但它保留了与中国相等的世界白银供应。如果按照人均额,欧洲在这个时期得到的白银要比中国多一倍。实际上,弗兰克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认为白银在欧洲引起通货膨胀,而新增的货币“促成了亚洲的生产增长和人口更大的增长”(1998:157;2000:220)。其实,这些数字表明中国和西欧都需要输入白银,区别在于西欧为此付出的成本是动用军事力量掠夺白银的成本,以及后来使用强制劳动开采银矿的成本。中国为了获得白银而付出的成本是必须出口贵重的商品。我觉得西欧为获得白银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只要我们是在谈论人口问题,尽管他引用了上述数字,弗兰克的结论是“亚洲,尤其是和印度的人口增长比欧洲快得多”(1998:171;2000:238)。也许弗兰克使用的是一种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算术,但是我认为他的数字表明,中国人口的增长只比欧洲稍稍快一点。当然,欧洲作为一个范畴包括许多有着不同人口增长率的地区。西北欧人口增长的数字比整个欧洲要多得多,至少和中国的人口增长数字不相上下。令人吃惊的是,从人口增长的这些微不足道的(有争议的)数量差异,如果毕竟还是有差异的话,弗兰克推论(是的,就是推论)出中国在整体生产方面的优势:“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对同一时期(1400年-1800年)世界和地区生产总值的估算数字,但是可以推测,亚洲之所以有如此之高的人口增长,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它的生产也增长得比较快,因此才够支持这种人口增长。”(1998:171;2000:238)
弗兰克的书里充满了这样的推论游戏。“如果说在亚洲许多地区,以生产、生产力和技术为基础的贸易和消费绝对地和相对地处于前列,那么就可以推想,那里也应该相应地有必要的制度‘基础’来促成的。”(1998:205;2000:281)“如果生产和商业的结构和进程确实如本书其他地方所证明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应该问,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是或应该是何种制度组织。”(1998:209;2000:286)然而,对母鹅有好处的不能让公鹅分享。当弗兰克不同意里德(Anthony Reid)关于印度进口的数字时,他指出里德说印度的“进口想必在1650年以后急剧衰落了”,弗兰克评论道:“我突出了句子中的‘想必’一词。很显然,他没有资料来证明这种衰落……”(1998:234;2000:318)这个评论既适用于里德,也适用于弗兰克自己所有的推论性论断,这样的推论在他的全部论证中所起的作用决不是次要的。
第四章题为《全球经济:比较与关系》,其中讨论的一个问题恰恰是分析的单位。弗兰克试图证明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一个单一的世界规模的经济,存在着单一的劳动分工。其他人,例如我,则认为在这个时期同时存在着若干巨大的体系,而且这些体系互相之间的关系与这些体系各自内部的关系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弗兰克在这一章里所做的事情就是假定他是正确的。这样一来他就很容易宣称,其他人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这个时期只存在于地球的某些部分)论述不适用于他的世界规模的单位。但是并没有人说它们是适用的。这纯粹是一个稻草人,根本用不着浪费那么多的篇幅,动那么大的肝火。我们来看看这段文字:
欧洲人能向东方销售的产品很少,因此主要是通过参与亚洲经济本身的“境内贸易”来谋取利润。欧洲的利润主要来自在众多市场之间,尤其是在整个世界经济范围内从事运输业,进行金银、货币和商品的多边贸易。过去,没有一个大国或它的商人能够同时在所有的市场展开活动,或者说能够把自己在这些市场之间的活动组织成这样一种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连贯系统……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欧洲当时不是向世界经济的其他地区出口产品的主要产业中心。(1998:177;2000:245-6)
第一个句子是正确的。欧洲人向东方出售的产品确实微不足道。他们甚至没有这样的企图。西北欧想要做而且做得非常成功的事情,是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出售产品。在这个时期西北欧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而亚洲还不是。弗兰克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的早期著作有大量的这类论述。现在,不是作为一个时期,弗兰克使用了一个逗号,把两个问题连接起来。这里实际上包含着一个不合理的推论。是的,欧洲通过介入印度洋内部的“境内贸易”来谋取利润(但这不是它的主要利润来源)。至少有两代学者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论著。是的,欧洲人的利润来自运输业,没有人反对这一点。是的,我想他们确实可以说是在一个世界规模的中从事贸易,也就是弗兰克所说的“整个世界经济”。那又怎么样呢?他们把从东方获得的利润用于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积累资本,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越来越强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的地区一个一个地纳入到体系中来,从而使后者边缘化。
第二个句子断言欧洲是第一个能够同时在所有市场活动的力量(这显然意味着显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市场,而弗兰克在本书许多地方拒不承认这一点)。这个句子包含着对欧洲很不情愿的赞许。弗兰克没有告诉我们欧洲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如此强大的人不能做到这一点。我引证的最后一个句子说,欧洲不是一个向“世界的其他地区”重要的出口商,但是从来没有人说欧洲在这个时期是重要的出口商。弗兰克在敲一扇开着的门。
这样逐字逐句地分析弗兰克的混乱可能已经使读者感到厌烦了,这里我只是指出这一章里的另一个稻草人。
尽管欧洲人获得美洲的金银并以此买通进入亚洲的世界经济的道路,但是在1500年以后的三个世纪里,他们一直是一个小角色,他们不得不适应--而不是制定!--亚洲的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1998:185;2000:256)。
注意那个戏剧性的感叹号。我斗胆请弗兰克指出一个学者的名字,他曾经说过在这个时期是欧洲人在亚洲制定经济的游戏规则。大部分人所说的,当然也是我所说的,是亚洲在这个时期处于欧洲“规则”占支配地位的区域之外。
第五章致力于论证这样一个命题:“同时性不是巧合。”我同意,至少我同意我们决不应当从假定偶然的巧合开始,而应当首先寻找共通性。这一章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讨论“17世纪的危机”,一个在过去40年里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弗兰克希望证明中国没有发生这场危机。也许有那么一些过分热情的人想要把这场危机扩展到亚洲,尽管我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文章。在我看来,17世纪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部确实发生了危机,但没有任何理由把它扩展到这个体系之外。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弗兰克在这本书(而不仅是在他以前的著作)里继续承认欧洲-大西洋地区存在着“危机”,然后又成功地否认了它在亚洲的存在。我会说它当然不存在。但是,他将如何用本章的标题《横向整合的宏观》来解释这种差异呢?
最后,我们遇到那应当是反题的第六章:《为什么能够西方(暂时地)胜出?》。记住,正是弗兰克告诉我们:
现有的各种关于世界和地区人口、生产和收入的估算以及前面对世界贸易的论述都证明,至少到1800年,与“西方”任何部分或整体相比,亚洲及其各地经济体都具有更大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在全球经济中更拥有不可比拟的分量和影响(1998:174;2000:242)。
似乎只有出现一个奇迹才能使欧洲成为领头羊。谁敢说这是一个“欧洲奇迹”?也许我们应当称之为弗兰克奇迹,他能把自己的分析从他把自己放进去的盒子里带出来。弗兰克是用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来开始这一章的:
一个答案是,亚洲变得衰弱了,另一个答案是,欧洲强大了……这一章要探讨1400年-1800年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在19和20世纪是否与如何转变为自身的劣势和西方的优势(1998:258-9;2000:349-50)。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弗兰克认为“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重要的亚洲经济体”在1450年-1750年期间处于一个漫长的“A”阶段,而欧洲在整个17世纪都是处于B阶段。“在1750年-1800年期间,尤其对于亚洲最核心的经济体来说,大约在1400年开始的这种长周期的‘A’阶段(在据认为是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只有亚洲处于这个阶段)达到了最高转折点,转向继之而来的长时间的‘B’阶段”(1998:263;2000:355)。西方可以利用亚洲进入B阶段这个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地位。这种亚洲的而不是欧洲的B阶段显然至少持续到1970年代,只是在这段时间里西方才“进入一个(暂时的?)主宰时期”,其局势和我们今天所谓的“东亚新兴化经济体(NIEs)”的兴起非常相似(1998:263;2000:355)。
让我们忘掉下述事实,即只要他的论证需要,弗兰克随时可以放弃他关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的虚构。然而,我们还是要问,西方是怎样在中国暂时衰落的时候取代了中国的优势地位?弗兰克借用了阿布-卢格霍德的故事,但至少往后推了三个世纪。弗兰克说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而且正是由于东方的衰落才使西方兴起成为可能。是什么使东方衰落的?印度和中国的统治阶级的市场机遇似乎使他们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在这里可以看到道勃对英格兰封建统治阶级衰落的解释的阴影),而这又加剧了两极分化,“从而也导致了造成经济扩张的那种进程本身的萎缩”(1998:266;2000:359)。实际上,在这个过程背后可能有存心不良的欧洲人在捣鬼。
亚洲内部的和局势之所以愈益紧张,更多地是由于欧洲人的白银供给以及随之而来的在世界经济中、尤其在亚洲的国内和出口市场上购买力、收入和需求的增长。可想而知,这使得收入分配越来越扭曲,从而导致对有效需求的制约以及愈益严重的政治紧张局势(1998:267;2000:359)。
如果我对这段话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下述情况就是可能的:如果人比较有节制,不是那么贪婪,如果它不是出口了那么多有价值的商品换取来欧洲的白银(或者至少没有换取那么多白银),那么他们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都将会继续待在世界的顶端。啊,那些卑劣聪明的欧洲人!如果他们在购买中国商品时少付一点白银(如果中国人有足够的远见,坚持要他们少付一点白银),中国人就有可能永远保持世界领先的地位。
这是对中国衰落的解释。印度又是怎么一回事?著名的欧洲中心主义学者如Amiya Bagchi或Burton Stein认为印度的衰落是在1757年(普拉西)、1800年或1830年以后。弗兰克认为他们全都错了,印度的衰落至少是从1730年代开始的。有“大量的证据”(1998:271;2000:361)表明,在沦为欧洲殖民地之前,印度经济的衰落就已经开始了。至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在18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开始了……”(1998:273;2000:366)。
弗兰克在解释亚洲各国的衰落时拒绝把它归功于欧洲,但他也拒绝谴责欧洲。他所说的仅仅是亚洲的A阶段而然地消耗殆尽,结果是欧洲得以取得优势地位。但欧洲是如何取得优势地位的?他们掠夺了美洲的白银,剥削美洲种植园,从“凯恩斯乘数”获利(1998:278)。现在我们回到原来的弗兰克。但这与反欧洲中心主义有什么关系?我们来读一下这一章的:
在欧洲人从美洲和非洲以及亚洲积聚他们的力量时,亚洲的经济和政治在18世纪日益衰落,最终正如罗兹·墨菲(1977)绘制的曲线图所显示的,两条曲线1815年前后相交了(1998:283;2000:380)。
弗兰克使用这样的措辞显得多么古怪啊--“两条曲线终于相交了”。我原以为从1400年以来,如果不是从公元前2500年以来,它们早就走在同一条惟一的道路上了呢。有的人也许会以为弗兰克是说,它们本来是不同的世界体系,最终进入到同一个有意义的互动竞技场。然而,最奇怪的是,弗兰克还要为欧洲(暂时地?)兴起加上另外一个因素,这就是“革命的技术进展”。这当然是非常独到的非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弗兰克确实告诉我们,它们“不应该被仅仅视为欧洲的成就。更准确地看,它们乃是世界过程的产物,而世界发展过程的空间焦点以前长期在东方徘徊”(1998:285;2000:382)。然而,弗兰克毕竟提出了那个合情合理的问题:
但是,还有未解决的问题:在亚洲人的游戏中,西欧人和美国人后来为什么以及如何能够借助于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战胜亚洲人?这一切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发生的?我们现在可能还得不出一个完全满意的答案……(1998:285;2000:383)
不过弗兰克还是想要给出某种答案。它实际上就是长期以来用于解释美国的经济优势的高工资边疆经济的观点,弗兰克企图把它运用于整个欧洲:
欧洲较低的人口比例以及作为安全阀的向美洲移民这二者所产生的发明机器的刺激要比亚洲人口-资源状况所产生的刺激大得多(1998:286;2000:384)。
这里的问题是,这个观点并不新鲜(毕竟,弗兰克也要引证亚当·斯密来维护自己的观点),而且在本书的前面部分,人口增长据说是中国的一个优势,但在这里欧洲的优势恰恰在于它能够摆脱掉自己的一部分人口,此外我们需要知道“这一切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发生的”。就这个问题弗兰克给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回答,他似乎认为欧洲缺乏白银。
我们能否证明,18世纪中期以后,欧洲获取美洲金银的可能性开始相对下降,从而威胁了欧洲对市场(份额)的渗透?如果是这样,就会刺激欧洲人通过降低自己的生产劳动成本来保护和提高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1998:293;2000:392)。
我承认我是被弗兰克的论证彻底搞糊涂了。仅仅在前几页欧洲的兴起还被归结为和印度的衰落,但在这里欧洲的兴起则被归结为欧洲自己的衰落有可能“威胁欧洲对市场(份额)的渗透”。 也可能糊涂的并不是我。
在对方方面面的论点和论据作了反反复复的概括之后,弗兰克就西方的兴起的问题得出一个简明扼要的结论:
总之,变动中的世界人口--生态形势突然地--大多数人包括亚当·斯密在内都没有料想到--使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投资在经济上变得合理了,也有利可图了(1998:317:2000:421)。
弗兰克的解释的其他部分和所有关于革命的标准教科书没有什么两样。
弗兰克在这里的叙述省略了“1500年:连续还是断裂?”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将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了:连续性。就我所知,对于弗兰克来说,只有连续性而从来没有断裂。当然,在1800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断裂,但到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又恢复了原状,即回复到连续性。应当指出的是,弗兰克对待以1500年划分时期的态度,仿佛是在向某种巨大的习惯势力挑战。实际上,把1500年视为一个断裂点的学者在世界上只是少数。一个半世纪以来,绝大多数社会家一直认为世界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重大的断裂:一次在大约公元前10000年-前8年(农业革命),另一次在大约1800年,或1760年-1840年(工业革命)。弗兰克与这种共识完全一致。
将1500年视为一个断裂这种观点,与其说与西方的兴起有关,不如说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体系的兴起有关。弗兰克否认这种历史分期的目的是要提出他的中国中心说。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不过是马克思想像的产物。资本主义成为一头据说有着极其独特的与众不同的“生产方式”的“神牛”(1998:330;2000:438)。在弗兰克看来,“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更不用说整个世界社会,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所有各种生产关系”(1998:331;2000:439)。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弗兰克论证的方式是把各种因素熔为一炉,仿佛这是这些因素惟一可能的组合方式。让我们以“所有各种生产方式”为例来进行分析。即使对于弗兰克来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产方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可以说具有一种生产方式呢?毫无疑问不是“整个世界社会”,也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把生产方式安置在哪里呢?一个城镇,一个工厂,一个家庭?
在道勃之类的马克思主义者、连接不同生产方式的鼓吹者、调节主义者、世界体系分析学者以及许多其他学者之间激烈的争论已经过去30年了。弗兰克也参与了这次论战,他肯定对每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清二楚:“你把生产方式置于何处”,决定着你的全部历史学。像上述引文以及弗兰克这整本著作那样对于这场争论全然忽略不计,是绝对不能解决问题的。也许面对这个困难而又关键的问题对于弗兰克来说是太艰难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因此,最好是彻底抛弃‘资本主义’这个死结”,并且嘲笑探讨资本主义的起源“无异于炼金术士寻找能够把破铜烂铁变成黄金的点金石”(1998:332;2000:441)。
实际上,炼金术士的努力是摸索实验科学方法的过程的一部分,为后来的物和化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尽管炼金术士的理论最终没有什么用处。当弗兰克说“最好是把它(资本主义的起源)抛在脑后,而去探讨普遍历史的真实情况”(1998:332;2000:441)时,他高高举起经验主义真理的大旗,仿佛这种“真实情况”不是通过某种特殊的理论眼镜观察到的,而他自己戴的也决不是一副茶色眼镜。
在将资本主义的现实忽略不计之后,在证明了中国/亚洲在世界贸易体系中长时期的持续的中心地位之后,他所能说的不过是:
工业革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它发生在欧洲的一部分,是整个世界经济持续不平等的结构和不平衡的进程的一个结果(1998:343;2000:455)。
也许有一些读者,在阅读了350页的煌煌大作之后,对作者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结论感到非常满意:改变了世界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但我可不是这样的人。一方面,所有的事件都是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所有的事件都是可以解释的。弗兰克没有对欧洲“革命”做出任何解释。他拿出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根本无法提出一种合理的解释。这样一来,工业革命就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不仅因为中的行动者没有预见到它,而且因为弗兰克用来阐述世界演化的理论也无法解释它。
我曾经说过弗兰克成为欧洲奇迹的最大的代言人。弗兰克告诉我们,美国现在从全世界获得财富的能力来源于它能够印刷美元,所以它能把西欧人和日本人所生产的东西通通买下。他用非常不屑的口吻说道:
欧洲在1500年-1800年三个世纪所实行的实际上就是(美国今天所实行的)这种无代价战略。差别仅仅在于美元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美国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而欧洲的白银完全是从美洲殖民地榨取的(1998:356;2000:470)。
“至少!”--欧洲人甚至根本没有资格谈论生产力。我们不得不佩服欧洲人那种空手套白狼的本事(trade nothing for something),他们居然能够欺骗有着几千年和文化成就的人、印度人和其他亚洲民族。但是,如果弗兰克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欧洲人是欺骗家,他用得着绕这么大的弯子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向声称欧洲人做出了非常显赫、非常特殊和值得称道的成就,在这部旁征博引的著作里,弗兰克为这个论断提供决定性的证据。这本书是为经济效益而唱的一曲冗长的赞美歌。弗兰克说在1500年-1800年欧洲人在亚洲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对此我完全赞成。另一方面,弗兰克说在1500年-1800年亚洲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我在他的书里没有看到什么可以支持这一论断的证据。在这一时期,亚洲之于欧洲的意义远不能与美洲的意义相提并论,无论我们讨论的是资本积累、结构、价值体系的演变还是历史资本主义的。到头来弗兰克所说的无非是中国在这个时期比欧洲要阔气得多。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应当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在18世纪初的孟加拉有多少中国因素呢?
弗兰克似乎认为他自己是惟一真正的反欧洲中心论者。即使是那些他从正面引证过的作者也被批评为不够彻底。哈比布(Irfan Habib)是印度经济结构的意义的最坚定的维护者,但在弗兰克眼里则不是。对于那些希望摧毁史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人来说,李约瑟是一座不朽的丰碑,但在弗兰克眼里则不是。在他看来,李约瑟从来没有摆脱其欧洲中心主义的根基。
这本书最薄弱的环节是他对西方哪怕仅仅是暂时地胜出所作的解释。这不光是因为弗兰克的心思不在这里,而且因为他给出的解释和他的所有观点相抵触。为了“解释”西方的兴起,他不得不放弃他在前面提出的许多观点。弗兰克一再接过广泛流传的观点,从中抽绎出相反的意义。曾经有一个时候,我们想要弄清楚为什么财富与贫穷在西方和其他地区分布得如此不均衡。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欧洲人更聪明。另外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欧洲人更富有侵略性。这成为世界右派和世界左派的分水岭,弗兰克过去是站在世界左派的阵营里的。但是现在他有了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说这是一个虚假问题,然后就把它置之度外。把这个消息告诉这个世界的贫民区的所有居民,看看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
弗兰克发现在1500年-1800年期间中国和印度是最富裕的地区。还有什么新东西吗?在那个时代,所有的欧洲探险家、商人和统治者一再说的不就是这些吗?说到底,这恰恰是他们到那里去并且掠夺那些地区的主要的正当理由。人们通常不会去掠夺世界上那些一贫如洗的地区,至少不会优先选择这些地区。弗兰克就像电影《奥兹的魔术师》里的多罗希一样踏上了一条康庄大道,但在这条道路的尽头,谁是那个手拿水晶球的魔术师呢?
引用书目:
Frank, Andre Gunder(1976)." Multilateral Merchandise Trade Imbalances and Une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 2 ,Fall, 407-38.
Frank, Andre Gunder (1998).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andes, David (1998).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New York: W. W. Norton.
注释:
①为方便读者起见,文中的引文均标出两个页码,前者为原著页码,Andre Gunder Frank,ReORIE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1998;后者为中译本页码,即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下一篇: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