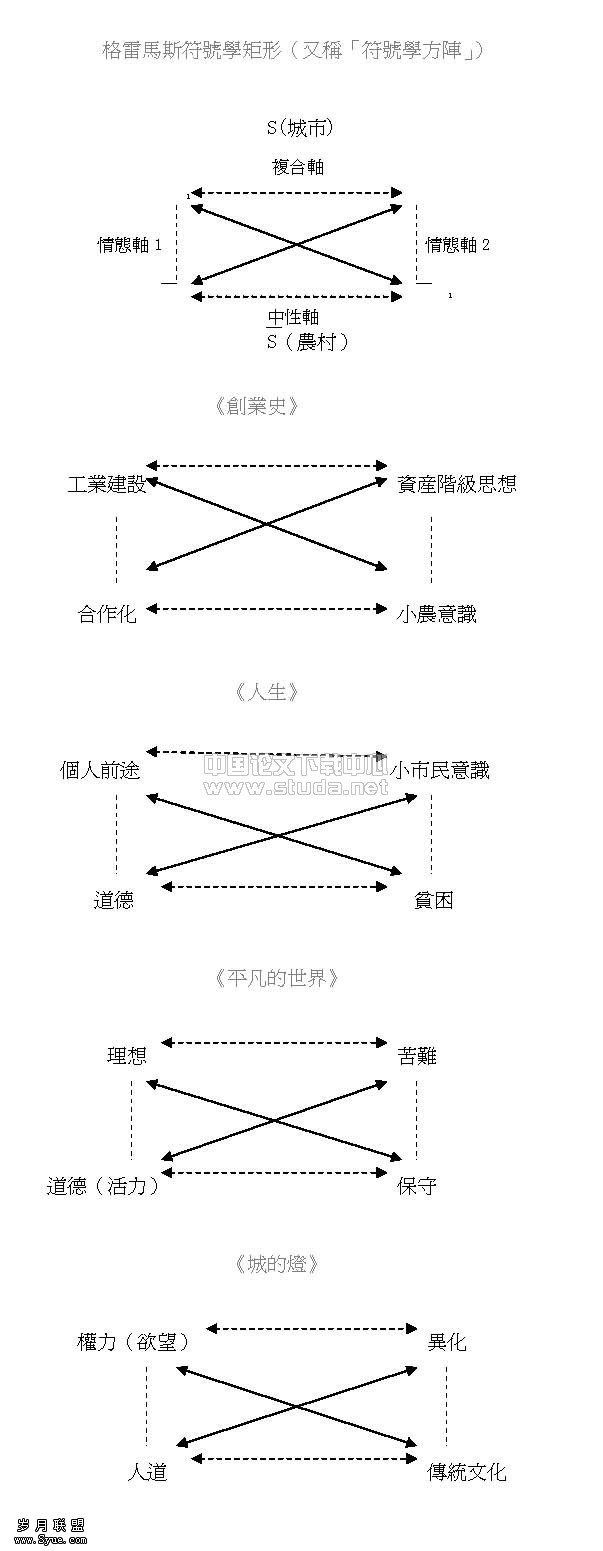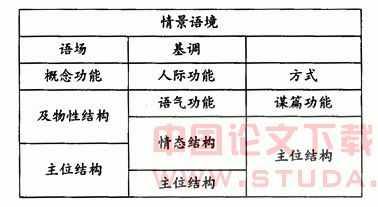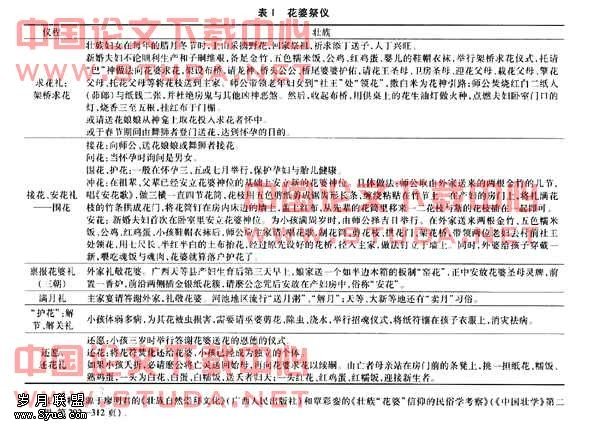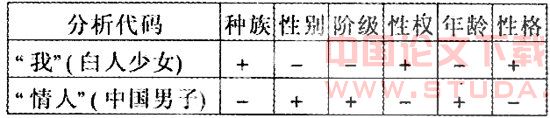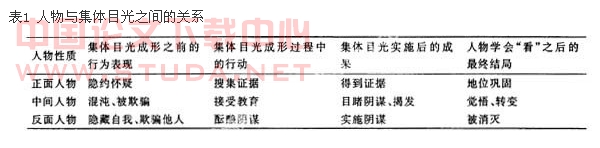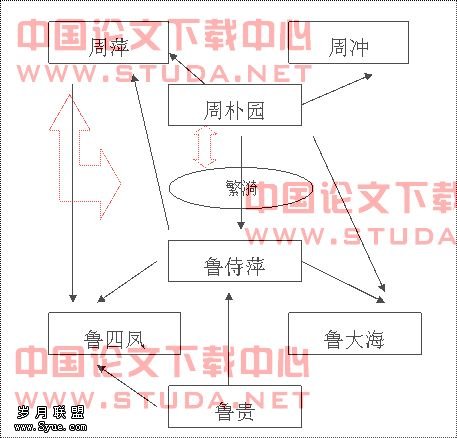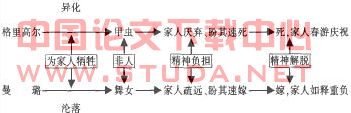文化重复困境中的叙事反思——在《狂人日记》到《长明灯》之间
【内容提要】
本文以《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为中心,考察在作为文化时间范畴的1918年到1925年,鲁迅深陷于文化重复之困境,如何借助于小说叙事进行反思以摆脱这一阴影,从中获得个人经历的反省。本文的讨论从三方面展开:一是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与行动策略的转换;二是从观念性表述到在世俗化生活图景下的深度追问与思考;三是对知识分子先驱者不同的命运、抉择及其意义的认识。本文认为在《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之间不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而且还存在着动态的意义空间。
在鲁迅小说研究中,《狂人日记》的重要性无庸置疑,“短短五千字,……开启了一代作家叙述、重写的契机”①。《长明灯》则不但不为学界所看重,还常被简化为《狂人日记》的一个复本,这样一种认知结果,不仅导致《长明灯》被误读,而且也遮蔽了在《狂人日记》到《长明灯》之间可能存在的有意味的内涵。
《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4月,《长明灯》写于1925年3月,其间相距七年。这七年,如果仅仅从物理的时间去考量,似乎意义不大。但如果同作为文化范畴的时间联系起来,问题就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作家,要在七年后再来作一篇似乎类似的小说表达七年前似乎就已经表达得相当充分的内容,总有其特别的缘由。推想开来,恐怕有两种可能:一是鲁迅陷于文化重复的困境,需要借助于对问题的重新思考摆脱这一阴影;二是在问题反省中个人经验断裂的敞开,即个人对自身经历和遭遇的反省,这种经历和遭遇是在问题意识的背景上被反身观照着。这样一来,《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不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而且在《狂人日记》到《长明灯》之间还存在着动态的意义空间。
1918年到1925年,就中国社会状况而言,仍是处于“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混乱之中,黑暗力量的相互冲突和交替构成了社会关系的主流。就文化环境而言,新思想与旧传统的对立实际上也只囿于部分知识分子的圈子中,并未形成广泛的社会性氛围,正如鲁迅的“铁屋子”理论所言,沉睡的是多数,清醒的是个别。而作为“中国文化史上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文化冲突”的新文化运动,虽然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并开
始了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但也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启蒙性思索的短促”②,从而导致其对彼时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思潮影响的有限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影响力甚至是在多年以后才被人们日益彰显的。
这七年,在鲁迅生命中却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时间段落,人生的大起大落,最辉煌与最绝望一起呈现。梳理这一时间段落,的确耐人寻味:一方面,鲁迅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部的小官员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事业的成功不但成就了鲁迅用文学启蒙救国的人生理想,而且带来了个人地位的急剧提升,使年已38岁的鲁迅从生命的低谷跃至生命的高峰,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其内心仍有所怀疑,但那种“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③的绝望毕竟已被“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④的亢奋所替代,可见鲁迅当时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毫无疑问,这是鲁迅人生的一大转折,此后世事流变,文学活动不仅是鲁迅的生存方式,也是其生命的核心。
但另一方面,鲁迅在这一时期又多次遭受精神重创。其中之一是1921年《新青年》同人的疏离、分手,这对鲁迅的打击尤为沉重。鲁迅在1922年底所作的《〈呐喊〉自序》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又一次陷于“寂寞”、“无聊”、“悲哀”中的绝望感。甚至在事隔十年后,这种“荷戟独彷徨”的悲凉仍未忘怀,1932年,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慨叹当时的情景: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新的战友在那里呢?⑤
渐入晚年的鲁迅,对于“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的精神状态的描述,让我们不难推想其当年内心的巨大创痛。“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的感慨唏嘘,既是对当年社会现实和文化氛围的评价,也是对当年自身处境的评价。
而《写在〈坟〉后面》的一段话,则是更直接地反思新文化运动:
记得初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些人便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前一类早已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后两类是不得已的调和派,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到现在还不少。⑥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伏,对鲁迅而言,又一次强化了他对于历史经验的悲剧性的重复感与循环感。事实上,鲁迅每一次用进化论观照现实生活时,结果却往往是证实了循环论的存在。所以,鲁迅虽然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并由此获得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但传统的循环论观念像幽灵附体,面对表面上风波迭起,骨子里却一切照旧的社会现实,不可避免地深陷文化重复之困境,“历史的演进仿佛不过是一次次的重复、一次次循环构成的,而现实——包括自身所从事的运动——似乎并没有标示历史的进步,倒是陷入了荒谬的轮回”⑦。这种深陷文化重复之困境所引发的内心的绝望感,就其强度和深度而言甚至超过S会馆时期。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为中心,讨论鲁迅在文化重复困境中的叙事反思。
一 从中心到边缘
《狂人日记》和《长明灯》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表达了对封建传统的抨击和否定,都表现了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因为自觉承负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职责,而被庸众视为“异类”,并在与庸众的尖锐对立中处于被囚禁的地位。
但我所发现的一个问题是,从《狂人日记》到《长明灯》,狂人和疯子在文本叙事中“位置”的变化。也就是说,狂人和疯子虽然同是拒斥封建权力话语系统的“精神界之战士”,但在文本叙事中表述为从中心向边缘的位移。
这种变化,就其叙事表征而言,表现在人物言说姿态和心理状态的差异。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把狂人的十三则日记置于小说的主体性位置,作为一种叙事策略,追求最大限度的现场效果,狂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随心所欲地进行着独白式的宣言,张扬启蒙者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献身的激情,其极端的言论充分传达出自我的期待,痛快淋漓的言说几乎淹没了庸众的声音。甚至面对那些“想害我”的眼光,狂人也极自信地认为“他们怕我”:
……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
……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⑧
但是,在《长明灯》中,疯子已经丧失了这一中心地位而趋于边缘化。其断断续续的言说已经难以构成小说的主体,在庸众的杂语喧嚣中,疯子的“熄掉他罢”、“我放火”只是“一种微细沉实的声息”。疯子不但不再是慷慨陈词的英雄,反而成为被戏弄被审判的对象:
……(疯子)短的头发上粘着两片稻草叶,那该是孩子暗暗地从背后给他放上去的,因为他们向他头上一看之后,就都缩了颈子,笑着将舌头很快地一伸。……
“我想:倒不如姑且将他关起来。”
“那倒也是一个妥当的办法。”四爷微微地点一点头。“妥当!”阔亭说。
“那倒,确是,一个妥当的,办法。”老娃说,“我们,现在,就将他,拖到府上来。府上,就赶快,收拾出,一间屋子来。还,准备着,锁。”⑨
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它意味着鲁迅对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现实处境和生存状态的重新审视,对其价值和作用的重新思考,并将这一审视和思考同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探索加以结合。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士为万民之首”,还是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都把知识分子看成社会的栋梁,民众的导师。“五四”一代人深受这些观念的薰陶,当他们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发动新文化运动时,潜意识里难免以救世主自居。鲁迅也是如此⑩。况且做“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本来就是鲁迅的梦想(虽然其多次自认为“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只是这梦想的实现一直未有机会,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客观上所营造的时代氛围,唤醒了那不能忘却的梦,使鲁迅借助于《狂人日记》中的十三则日记完成了书写英雄的欲望。虽然这“英雄”有些荒诞,如王德威所论,鲁迅“让他的狂人写下日记,并以其见证古中国的颓废与恐怖。所有的诗书礼教不过是伪善的门面,所有的伦常纲纪其实是压迫的借口。一场人吃人的盛宴已经开了四千年还散不了席。在死亡的阴影下,狂人不断地写着,妄想用文字铭刻他的发现”11。但狂人毕竟成为鲁迅理想中的“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的“精神界之战士者”,以其“先觉之声”,“破中国之萧条”12。
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现实生活的接连不断的教训,逼着鲁迅质疑知识分子先驱者的中心地位,当他以强烈的自我意识来审视现实问题时,就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高压,使作为个体的知识者以各种方式或自觉或被迫地退至社会边缘。暴力和压制,必然地剥夺知识分子先驱者的言说权,鲁迅对这种“言说的无效”的绝望感是如此强烈,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但是,鲁迅接着又说:“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要反抗,试他一试。”这未一句的“反抗”,鲁迅确认为“是与黑暗捣乱”,而非“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13。如何“与黑暗捣乱”?当“言说”不再有效时,行动是否更有意义。就像《过客》中的“过客”,“向前走”是其唯一的动作和目的。因此,在《长明灯》中,处于被定义、被监护、被规定的边缘化地位的疯子,以“熄掉他罢”为唯一的目的,以“吹熄”、“我放火”为动作。他很清醒,怀疑一切掩饰、粉饰的话语,拒绝乐观,知道灯“熄了也还在”,但仍执着于行动,“我只能这么姑且办。我先来这么办,容易些。我就要吹熄他,自己熄!”小说赋予了人物主体的“动作”实践以一种绝对的意义,使其成为既是思想者,也是践行者。
这样,从《狂人日记》到《长明灯》,不仅表述了个体知识分子从中心到边缘的位移,同时也是从“思想”到“行动”的转化,亦即鲁迅对个体知识者的“知”与“行”的重新审察和重大调整,不仅追求思想的自由,更强调主体的动作、实践的意义。
二 从观念到世俗
这两部小说都具有象喻性,《狂人日记》十三则日记,以“吃人”为象征,《长明灯》以“熄灯”为象征。但在叙事的策略上,各各不同。《狂人日记》对社会文化的探索和批判是主观化、论辩式的,是精神层面的形而上的思辨之直接传达,小说的叙事完全是“由一先导观念统帅”14;《长明灯》则把这种探索和批判化为世俗生活图景,是形而下的叙述,但又不是一般性的叙述,而是通过世俗生活图景,在人的日常生活的场景与细节的背后,对人的存在、人性的存在、人与人的关系进行深度追问与思考,把现实的痛苦和黑暗提升到形而上的层面。在我看来,作为一种诗性活动的小说叙事,《长明灯》对生活的表述更感性、情感更复杂、思考更丰富。
我们不妨选择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加以考察。
首先,在鲁迅小说中,家族血亲关系是鲁迅反省人性的一个重要视角,《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也不例外。不过,《狂人日记》中,被狂人认定为“吃人者”的大哥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相当概念化、脸谱化的人物,小说对他的描写无非是“只是冷笑”、“眼光凶狠起来”、“忽然显出凶相”等等,作为封建礼教、家族制度的功能性符号,简化而直观。而《长明灯》中对四爷(疯子的伯父)的叙述却复杂得多:
(四爷)捋着上唇的花白的鲇鱼须,却悠悠然,仿佛全不在意模样。说,“这也是他父亲的报应呵。……”
“真是拖累煞人!”四爷将手在桌上轻轻一拍,“这种子孙,真该死呵!唉!”
……“我家的六顺,”四爷忽然严肃而且悲哀地说,声音也有些发抖了。“秋天就要娶亲……。你看,他年纪这么大了,单知道发疯,不肯成家立业。舍弟也做了一世人,虽然也不大安分,可是香火总归是绝不得的……。”
“六顺生了儿子,我想第二个就可以过继给他。——但是别人的儿子,可以白要的么?”
“这一间破屋,和我是不相干;六顺也不在乎此。可是,将亲生的孩子白白给人,做母亲的怕不能就这么松爽罢?”
“我是天天盼望他好起来,”四爷在暂时静穆之后,这才缓缓地说,“可是他总不好。也不是不好,是他自己不要好。无法可想,就照这一位所说似的关起来,免得害人,出他父亲的丑,也许倒反好,倒是对得起他的父亲……。”
在我看来,这是鲁迅叙述家族黑暗和血亲关系冷酷的最生动的文字之一,那幸灾乐祸的冷漠,阴毒的诅咒、堂皇的借口下包藏着的居心叵测,贪婪和虚伪,无一不表达着人性的阴暗和卑劣。世俗化的叙事是鲁迅童年记忆的心理积淀,也是对世俗人情的深刻透视,更是对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下人性异化的文化反思。
其次,世俗生活叙述中对“伪士”的批判性反思。鲁迅在《破恶声论》里,曾提出“伪士”的概念。指出“伪士”的主要特点:一是这类人本身为“无信仰之士人”,既为没有信仰的知识分子,但又“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举丧师辱国之罪,悉以归之”,要使出一切手段扼杀别人的信仰,因此常以正统、惟一正确自居,既用“伪信”掩盖自己的无信仰,又以此来垄断信仰。二是本质上“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火”,但又“时势既迁,活身之术随变,……挚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15。“伪士”们最惯用的手法是“瞒”和“骗”。因为善于在迎合权势的同时迎合大众,在迎合传统的同时迎合时髦,所以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占据社会文化的主流地位。在某种意义上,“伪士”正是中国社会文化体制的产物16。《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中,与狂人和疯子形成文化冲突的知识分子正是这样的“伪士”。从《狂人日记》的大哥、何先生到《长明灯》的三角脸、方头、阔亭、庄七光、郭老娃、四爷,他们都被鲁迅一一加以勾画。但在《狂人日记》中,鲁迅似乎来不及对“伪士”作化的构思,因而大哥、何先生的形象显得过于粗疏。《长明灯》中的“伪士”则传神入化。比如四爷之类,表面上以真理阐释者自居,实质是要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三角脸、方头、阔亭、庄七光之流,是典型的既迎合权势又迎合大众,既迎合传统又迎合时髦的“伪士”。这些所谓的“以豁达自居的青年人”,不过是以“不拘禁忌地坐在茶馆里”为时髦,鲁迅不惜笔墨反复描摹他们的世俗画像:
方头和阔亭在几家的大门里穿梭一般出入了一通之后,吉光屯全局顿然扰动了。
阔亭和方头以守护全屯的劳绩,不但第一次走进这一个不易瞻仰的客厅,并且还坐在老娃之下和四爷之上,而且还有茶喝。
面对疯子的行为,他们俨然是“正统”的维护者,先要“除掉他”,再要“送忤逆”,恐吓威胁之余,又施以“瞒”利“骗”:
“你还是回去罢!倘不,你的伯伯会打断你的骨头!灯么,我替你吹。你过几天来看就知道。”……
“的确,该死的。”阔亭抬起头来了,“去年,连各庄就打死一个:这种子孙。大家一齐动手,分不出打第一下的是谁,后来什么事也没有。”
(方头说)“我想:倒不如姑且将他关起来。”
在与封建权力者的合谋中,他们是排斥和压制异己最积极和最阴险者,是“狮子似的凶心,兔子似的怯弱,狐狸似的狡猾”。正如鲁迅所论及,“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17。这类“伪士”形象的创造,是鲁迅进行叙事反思的重要成果,不仅是对进化论的自觉颠覆,也是在小说叙事中对伪知识分子的有效清理。
其实,“伪士”形象在鲁迅其它小说中时有出现,如《阿Q正传》的假洋鬼子、赵秀才等,但都不如《长明灯》中的刻画更丰富、更深刻。
第三,从《狂人日记》“救救孩子”的呼号,到《长明灯》结尾孩子们的歌谣,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关于“救救孩子”,有人认为,它“意味着对含混着地狱和天堂气味的‘中间物'的否定,这种否定同时包涵了对整个传统的最彻底的摒弃和对光明未来的最彻底的欢迎”18。也有人认为“这呼声其实充满反讽”19,鲁迅自己则反思,“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20,还是鲁迅说得彻底,“空洞”。因为只是一种先在的观念传达,而且这观念很容易在文化重复的困境中被不断追问、受到质疑,如何“救”?可能性?可行性?结果?诸如此类。事实上,我们在《长明灯》里,看到“救救孩子”的呼声已化为了一群孩子嘲笑疯子的行动与歌谣:
一 个赤膊孩子擎起他玩弄着的苇子,对他(指疯子——引者注)瞄准着,将樱桃似的小口一张,道:“吧!”
这个细节在小说中几乎是重复地出现了两次,除此,小说还不厌其烦地叙述孩子们将疯子的“我放火”变成“随口编派的歌”“笑吟吟地”“合唱着”,这样的叙述显然意味深长,虽然,孩子们的行为是无目的的,但唯其天然的敌意和凌弱的本性才更可怕,这天真背后的残忍让人不寒而栗。这些正在和将要被封建的文化价值观所同化的孩子们,最终完全可能成为“吉光屯居民”中的一员。这就是社会世俗生活的真实,而这“真实”在小说中的表述,恰恰是鲁迅对“救救孩子”的并不乐观的注释和反思。
三 从放弃到坚守
对“先驱者的命运”的思考几乎贯穿了鲁迅的一生。这一思考主要具有两个指向,一是先驱者所赖以生存的外在的文化环境。鲁迅早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就指出,在“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21的社会里,先驱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22。此后,鲁迅又在很多文章里反复地谈到先驱者“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23的悲剧。因此,知识分子先驱者是始终处于“以众虐独”的文化境遇,承负“独战多数”的宿命。二是先驱者内在的精神世界。也即先驱者在如此黑暗的文化环境中能否坚守个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在与封建传统、权力和庸众意识的旷日持久的绝望反抗中,像旷野里的“过客”,为“永远探索”的声音所召唤,永远在“走”。
应该说,《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亦渗透着鲁迅的这一思考。这两部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意象——囚禁24,即狂人和疯子处于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囚禁之中,这所谓的双重囚禁,前者是指他们的身体或被囚于祖屋或被囚于社庙,后者是指他们精神上的被敌视被围剿被扑杀。鲁迅有意要把人物置于这一境遇中进行叙述,使小说中的象征性意象不但暗示了知识分子先驱者的生存状态,而且使先驱者对自身命运与结局的选择成为某种必然。
我们在这两部小说中看到了选择的结果是不同的。《狂人日记》文言小序所述,狂人的结局是“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通常这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先驱者对封建体制的归附,对政治强权的屈服、对现实生活的调和与妥协而导致自我精神的异化。实际上,这也是对作为先驱者的信仰与责任的“放弃”。这种“放弃”在鲁迅此后的小说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现,比如《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是以“做无聊的事”和“敷敷衍衍”表达了“放弃”,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则是用以毒攻毒的报复表达了“放弃”。在我看来,文言小序中“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并非闲话,鲁迅特别强调了“愈后所题”,他要暗示什么?“愈后”的狂人如何评价狂态时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感?是对狂态的否定,抑或是面对“放弃”的自嘲。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狂人“放弃”前后的心理过程在小说中是一个空白,如果可以作一想象的话,这过程倒是借助于《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进行了补白。
但在《长明灯》里,小说的结尾是,被囚于社庙的疯子“一只手扳着木栅,一只手撕着木皮,其间有两只眼睛闪闪地发亮”,说着“我放火!”这是一种坚守的姿态,鲁迅是把疯子当作了“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25,即便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仍然坚持思想的独立,从而把“无路可走”的境遇中的“绝望反抗”作为个体无可逃脱的历史责任,把义无反顾地执着于现实抗争作为人的生存的内在需要。这种持相当明确的坚守姿态的人物在鲁迅的小说中并不多见。鲁迅在介绍《彷徨》时曾说:“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了不少。”26我尤其注意到鲁迅所谓的“战斗的意气却冷了不少”的自我评价,不管这“战斗的意气”是指启蒙的动机,还是指被“前驱者”所激发的热情,总之,在“冷了不少”的心态下仍能创造出疯子这一形象,其意义和价值非同一般。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完成《长明灯》后仅隔一天,鲁迅就写了《过客》,最末的一句是:“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27再联系写于《长明灯》前后的《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的结尾:“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28“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29这些都与《长明灯》形成了某种呼应,可见鲁迅对这一坚守姿态的不断强化的心理认同。
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写于1918年新文化运动高潮的“呐喊”期的《狂人日记》将狂人送入了放弃信仰,归顺旧体制的行列,而写于1925年鲁迅生命“彷徨”时期的《长明灯》反而出现了不问成败,坚守信仰的疯子?如果说,前者在事实性的希望背后是信念式的绝望,那么后者则在事实性的绝望背后却是信念式的希望,这看起来不合逻辑的生命叙事缘由何在?毕希纳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深渊。因而每个人都将面对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人痛楚与经验。事实上,鲁迅终其一生都在“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与“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之间挣扎。“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这是鲁迅所认定的事实,“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30,这是鲁迅所持有的信念,不过这一信念却是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起伏之后,鲁迅在文化重复的困境中,通过一种历史和个人记忆的延展、深化,达到对现实生活和自我生命的直视和清算,并借此获得有效性的反思的结果。这一结果,标示着鲁迅在现实生存中自觉到别无选择之后的人生选择,从而在重重的矛盾困惑中为自己的人生实践确定了一种出路,以更为坚定的心态和执着的姿态直面现实生存。
注释:
①1119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第3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②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第23、34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③《日记》,《鲁迅全集》第14卷,第2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书信?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4页。⑤26《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56页。
⑥《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285页。
⑦18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第27-28页,第193页,河北出版社2000年版。
⑧《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下所引均同。⑨《彷徨?长明灯》,《鲁迅全集》第2卷。下所引均同。
⑩参见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第9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222《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100页,第79页。
13232530《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74—79,20,32,20—21页。
14郜元宝:《鲁迅六讲》,第109页,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15《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25、28页。
16参见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第1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7《〈二心集〉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191页。
20《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第456页。
21《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8页。
24作为一种对知识分子先驱者生存境遇和生命体验的认识,“囚禁”意象不但在鲁迅小说中多次出现,甚至其为数极少的新诗中也曾出现。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鲁迅发表过一首题为《他》的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知了'不要叫了,/他在房中睡着;/‘知了'叫了,刻刻心头记着。/太阳去了,‘知了'住了,——还没有见他,/待打门叫他,——锈铁链子系着。”
27《野草?过客》,《鲁迅全集》第2卷,第194页。
28《彷徨?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第34页。29《彷徨?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