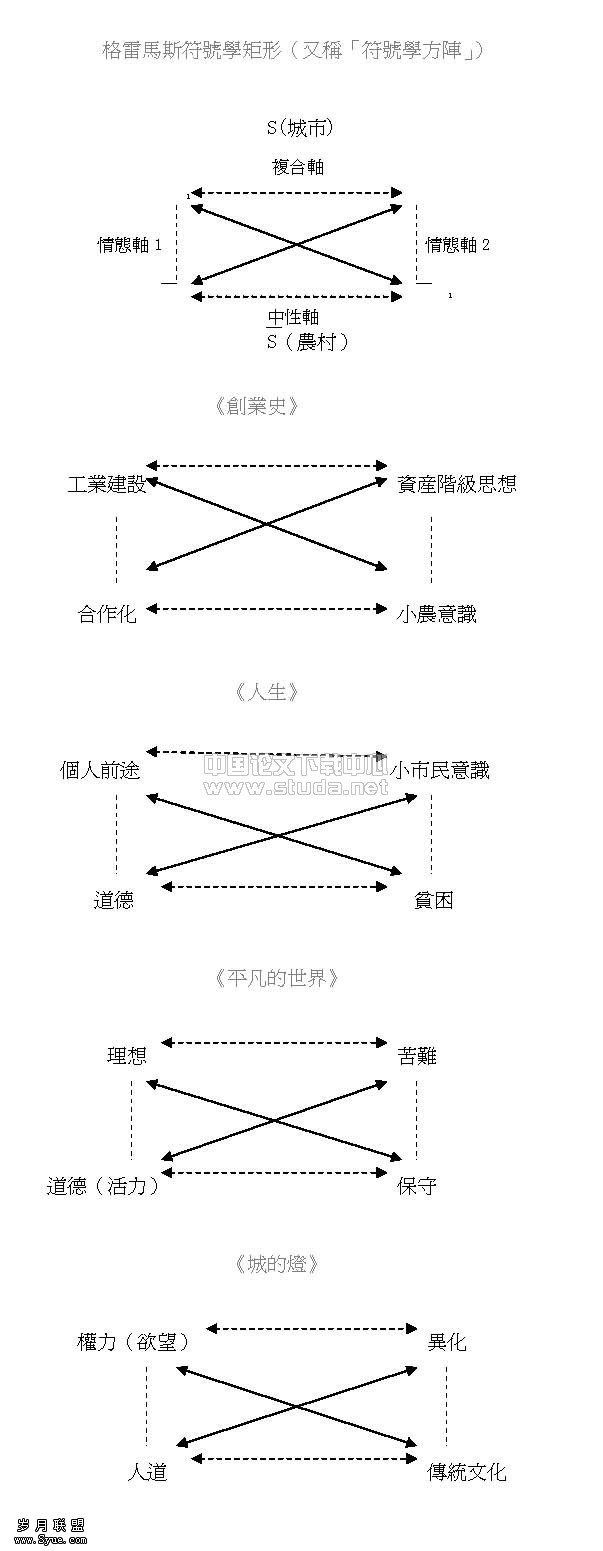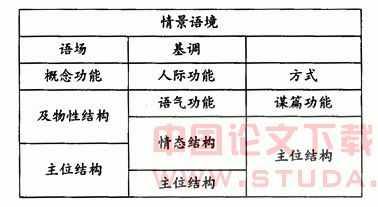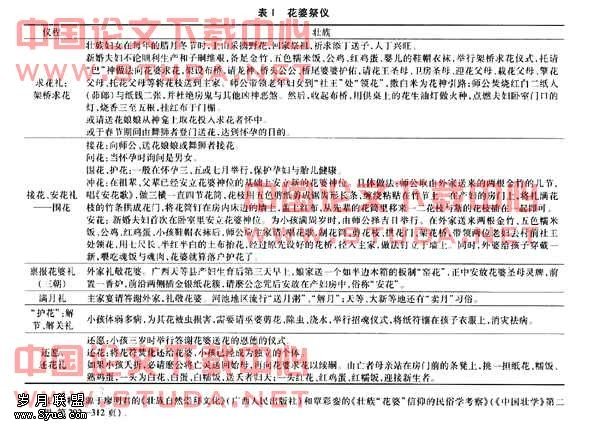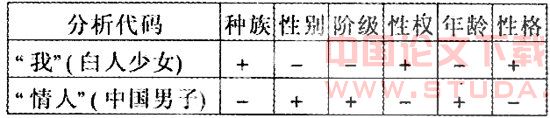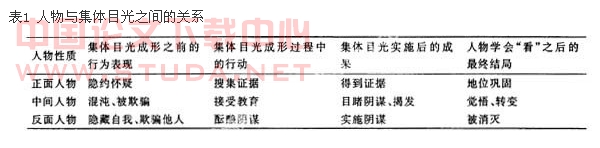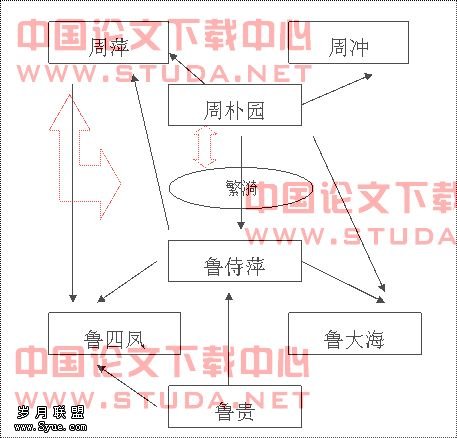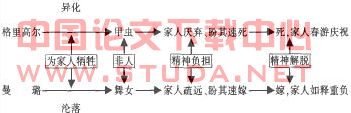左翼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
【内容提要】
30年代“左联”领导的文艺大众化讨论,最终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幻想”层面;40年代延安开展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却成为如火如荼的现实。比较分析可知,政党对文艺直接干预的之力、“大众”诉求基础的转变与对象的明确、知识分子大众化维度的增加,是延安文艺大众化得以实现的决定力量。延安文艺“民族形式”运动为文艺化道路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发挥了重要的转折点作用。
一 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文艺道路的转向
中国文学现代化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和指向的,个人主义是五四新文化最突出的标志。1918年周作人在其《人的文学》中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他同时指明这种“人道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从个人做起”①。这种个人主义的文学倡导,与当时主张全盘西化的文化潮流相一致,与五四对西方“自由”与“民主”启蒙思想的继承、学习相一致。所以说,中国现代文学是标榜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个人主义文学,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道路最初是主张全盘西化、人文主义的道路,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革命斗争以新的形式展开。随着世界无产阶级运动高涨、无产阶级兴起和壮大,新的阶级力量和新的时代都要求表现新的意识形态的文学,于是,文学的阶级性范畴提到首位,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开始登上文学的舞台。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开始号召无产阶级大众文艺。“左联”共组织开展了三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在组织者看来,无产阶级本身就是“大众”、“集体”、“多数”,“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乃至——本质上,就是非为大众而存在不可的东西”②。所以,无产阶级提倡的文艺口号是“大众文艺”,它反对的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文艺即“个人主义文艺”。从“自由人”、“第三种人”与“左翼”的交锋、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艺”与“左翼”“大众文艺”的对峙可以看出,文艺大众化没有成为当时文艺界普遍认同的主流,也就是说,大众文艺并没有动摇五四个人主义文艺的主导地位。几次讨论,实际只是在理论上为文艺大众化做了前期准备。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抗战战争爆发后。1938年,毛泽东提出“民族的形式,国际主义的内容”、“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等主张,标志着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斗争基础上的文艺大众化主张正式形成。1939年初,延安宣传部和文化界领导发起文艺“民族形式”运动。运动发起者陈伯达指出:“民族形式的问题,也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问题。”③因此,文艺“民族形式”运动也就成为在新形势下延安开展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先声。1940年,“民族的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化蓝图,将正在进行的“民族形式”文艺大众化运动进一步推向深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要求,文艺界全面贯彻实践,将文艺大众化运动推向高潮,最终确立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和道路。
二 延安文艺大众化相较“左翼”时期的历史突破
延安时期开始的政党对文艺直接干预的政治之力,“大众”诉求基础的转变与对象的明确,知识分子大众化的全方位策略,是较之于30年代大众化讨论所具有的历史突破点,是延安文艺大众化得以成功实现的决定因素和力量。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在这三个环节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从话语到实践:政党政治之力的影响1930年,鲁迅在文艺大众化讨论时曾说:
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④
“左翼”的文艺大众化设想,终归是纸上谈兵,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设施,其根源也正在于没有凭借到政治之力的帮助。
按照葛兰西的定义:政党是以建立新型国家为明确目标,政党也正是为这一目标合理并合乎历史地建造起来的。⑤因此政党政治意味着支配权力、手段、行动和目的等要素。当政党按照自己建国、建立意识形态的目标对文艺提出要求时,必然会对文艺的每一个发展步骤和环节都进行具体支配和控制,提出具体要求,使文艺担负起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作用。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新形势下,党对文艺提出了配合政治、为政治服务的要求。1939年初,延安宣传部组织发起以创造“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核心的文艺大众化运动。1939年7月,宣传部领导艾思奇在《两年来延安的文艺运动》中对运动的目的作出说明:
抗战文艺运动有两个中心任务:一、动员一切文化力量,推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二、建立中华民族自己的新文艺。……就第二个任务来说,延安建立中华民族文艺的努力,是向着这样的方向走,内容是三民主义的,而形式是民族的。……⑥
由此可知,文艺“民族形式”运动是党为规定文艺道路和制定全国文艺政策所进行的初步探索实践。
1940年初,毛泽东作《新民主主义论》讲演,“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诞生,标志着党的大众文化方向正式确立,这也是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蓝图。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要求,它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具体落实,是文艺大众化实施的具体方案。上述三个文艺运动的环节和步骤,包含着一以贯之的政治之力,不仅显示出政党所要求的大众化的文艺方向和道路的具体形成过程,也揭示了政党政治之力在其中发挥的组织、推动、命令作用。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这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⑦
那么,“左联”领导的文艺大众化讨论没有受到政党政治力量的支配作用吗?笔者认为,“左翼作家联盟”虽然是共产党领导成立的,但其毕竟首先是一个文艺组织,“左翼”提出建立无产阶级的“大众文艺”口号,主要还是从“革命文学”自身的发展方向而来。1928年,后期创造社成员从日本回国,他们带回的“革命的理论”“就是他们在日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看作是‘一种伟大的启蒙'以区别于五四新文学运动那种‘浅薄的启蒙'”⑧。为此,他们揭起与“五四”新文学对立斗争的旗帜。随后,1930年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更进一步提倡无产阶级文学。大众化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核心被着重提出:“大众化'是普罗文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普罗文学,假定没有获得大众的理解和爱护,这是一种很重大的损失。要使普罗文学为大众所理解和爱护,‘大众化'这个问题便非马上提起来不可了”⑨;“文学大众化应当作为怎样的问题而提出呢?第一,这应当作为当前的中国普洛革命文学的最主要的问题,并非在普洛革命文学之外的问题,也非普洛革命文学的附带问题而提出。‘文学大众化'这个任务,应当作为中国普洛革命文学运动当前的最主要的任务而提出”⑩。这样的发起思路表明,“左翼”文艺大众化号召的根源主要是来自马克思主义信仰与无产阶级观念影响,而非政党权力支配结果。
应该说“左联”文艺大众化讨论的初衷是想与政党政治相结合,但事实上不能够实现这一愿望。1931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在决议中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意义进行阐述:“文学大众化问题在目前意义的重大,……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11932年,“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决议指出:“左联应当向着群众,应当努力的实行转变——实行文艺大众化这目前最紧要的任务。……必须和当前的政治任务——反帝、反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联系起来。”12两个决议都表明文艺大众化与政治结合的意图,特别是后一个决议,直接将文艺大众化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相联系,但是,这实际上只能成为一个理论设想——因为“左翼”所在的上海,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不具备推广实施文艺大众化的客观条件。而当时中华苏维埃政权还很薄弱,分散在全国的一些边远地区,不可能也不能够以公开的政党命令、政权组织形式来促使这一目的和意图得到贯彻和实施。所以,文艺大众化的宣传和讨论也就只能成为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准备。这就与延安开展文艺大众化的路径不同。
以文艺“民族形式”运动为开端、经过“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发展,最终由《讲话》指引而达到高潮的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到强有力的政党政权支配之下,纳入到政党建国的方略之下。它们是共产党的宣传机构领导的,而不是文艺人自发组织的,体现出政党政治的要求在前,文艺自身发展的要求在后。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客观上为党推行文艺政策命令,为文艺家具体展开大众化实践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延安三个步骤的文艺大众化运作路线,明显有别于“左联”领导的三次文艺大众化讨论。鲁迅所说的“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精义正在于此——“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终归只有“文艺”一条腿,所以是“文人的聊以自慰”。
多年以后,茅盾在回顾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的文章中,对鲁迅的话表示了深切认同和感触,同时鲜明指出三四十年代两个阶段文艺大众化在“政治”一点上的差别:
在三十年代我们都热心于文艺大众化的宣传和讨论,但所花的力气与所收的效果很不相称。究其原因,也就是一条腿走路的缘故——政治环境太恶劣,而作家们又麇集上海一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艺大众化冲出“文人的聊以自慰”的圈子而真正成为“运动”,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那时,政治上的束缚放松了一些,作家艺术家们也走出了上海的亭子间,投入到大众的海洋;而在广大的敌后根据地中,“在政治之力”的帮助下,大众文艺已不再一条腿走路了。13曾经参加过“左翼”大众化讨论的周扬,对于延安文艺大众化得以实现的政党支配力量亦有深刻感悟:
我们的艺术,文艺运动如果没有和新民主主义政权,和人民的军队,和工农大众密切而且直接地联系,艺术服务政治,就是一句空话。14
可见,政党、军队、政权对延安文艺大众化实现的决定作用。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与政治第一次真正有效结合的运动,是共产党“政治第一、文艺第二”、“文艺从属于政治”路线的实际开端。
(二)大众化诉求基础的转变:“民族—大众化”对“阶级—大众化”的超越
“左翼”文艺大众化理想没有实现,还在于他们“大众”诉求基础的薄弱与对象含糊的局限。“左翼”时期的共产党是单纯主张国际主义的党,普洛大众文艺自然是以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为立足点和指导思想的。相应地,当时的大众化诉求基础就是国际主义,建立在其上的“大众”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劳工大众。这样的“大众”,显然是抽象的,阶级的划分实际上又具有明显局限性,从当时《大众化文艺》上的两篇讨章可见一斑:一是乃超对“大众”的看法:
“大众”或群众,究竟他[它]的内涵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把它规限于被压迫阶级,它仍然能够分开许多阶层。尤其在中国这一阶级中不少意识落后的阶层,要解决他们享受文化恩惠或创造文化的问题,决不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事体,我们现在所谈的大众当然要包括从有意识的工人以至小市民。15一是王独清对“大众”的理解:
这儿所谓的“大众”,并不是“全民”!所谓“大众”,应该是我们的大众,——新兴阶级的大众。若是要把大众解作人类中之多数的话,那也只有新兴阶级才算得大众。因为它的本身便是多数者的社会,它的斗争对象恰是少数的特权者。16二者的观点都显示出当时对“大众”理解的限度:只包括工人,小市民这样的新兴阶级,而不包括广大的农民、知识分子。这说明当时的“大众”观不仅有局限性,而且是抽象、模糊不清的。在大众化的对象“大众”是谁都无法统一认识的情况下,更遑论大众化的创作实践了。
但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共产党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进行有机结合,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统一起来,变成一致的追求,用毛泽东的话解释就是:“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要求在一定的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17“民族主义”维度的增加,使革命的性质和诉求都发生了改变。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毛泽东引用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得出的结论就是:“所谓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18这就使得“大众”的范围突破了以往狭隘的唯阶级论框架,而且“大众”的重心和主体相应发生了改变,即从过去以工人阶级为主,变成了以占全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为主。当然,以农民为主并不是说大众仅指农民,按照毛泽东的概括:“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19“大众”范围的扩大和对象的明确,使“大众化”在这一问题上比“左翼”时期具有明显进步,占有一定优势——获得更多阶层的支持,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支持。
在民族斗争、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延安文艺大众化诉求获得了更多的情感和道义认同。“左翼”时期,在崇尚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那里,无产阶级的普罗大众文艺主张并不能使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作家有更多认同的热情,但是,共产党在经过单纯的国际主义向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相结合的立场转变之后,将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统一调和在一起,这就增加了道德优势——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大众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就有了共同的所属,即与民族、国家的利益一致。“民族”在此时发挥了最强大的凝聚作用——在“民族形式”论争期间,即便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文艺的大众化也是积极支持和认同的,道理就在这里。当代学者指出:“在各大流派之争的背后,隐含着对文化霸权的争夺。而取胜的关键又看谁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民族情绪,整合民族情绪。换句话说,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是中国各思想流派能否取得主流地位之最后决定因素。”20
从文艺“民族形式”论争到《讲话》所主张的文艺大众化,实际上已经不同于30年代“左翼”的大众化诉求,因为二者的立足点不同:一个是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大众化诉求即“阶级—大众化”,一个是以民族论与阶级论统一为基础的大众化诉求即“民族—大众化”;相应地,“大众”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改变——由过去单纯以工人阶级为文艺主体和表现对象扩大到以工、农、兵为文艺主体和表现对象,“大众”基础更为宽泛,对象更加明确,文艺大众化找到了统一的方向和用力目标,在实践上更为可行。
(三)大众化的新维度:知识分子大众化
在30年代“左联”领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中,知识分子普遍是以大众的启蒙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灌输者身份来倡导文艺大众化的。虽然瞿秋白等个别人对此提出批评,指出知识分子高高在上是阻碍大众化真正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但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没有像“旧形式”、“大众语”那样成为当时文艺大众化讨论的专项议题,特别是没有一定的组织命令强制执行,所以知识分子自身的大众化就成为3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缺失。但是延安时期,从文艺“民族形式”运动一开始,知识分子自身的大众化以及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的转换要求就与文艺大众化主张一同被正式提出,并且最终通过政党命令收束一端,要求知识分子全面进行思想改造和身份转换,增加了新的大众化维度和力量,进一步从根本上保证了文艺大众化的全面实施。
陈伯达和艾思奇作为“民族形式”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最初倡导运动的文章中,同时向知识分子发出大众化倡议。陈伯达提示文艺家:“他就需要克服自己高贵的习气,不要以为创作不必要大众能懂,也能千古不朽(事实上,那只是极端片面的真理)。文艺家同时也是家,但是却不要以为自己不必受教育,马克思有句名言;‘教育家本身也要受教育'。你要成为大众化的文艺家来教育大众吗?你首先应当向大众方面去受教育:不但应该去了解他们的实际生活,而且应该了解他们所喜欢的作风,所高兴的格调。”21艾思奇则要求:“我们的文艺人,一方面是民众的教育者;而另一方面却又要同时向民众学习,学习他们的生活,思想,以及言谈。”22由此开始对知识分子提出重新定位的要求。紧接着,毛泽东提出衡量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结合的标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23
如果说,初期对知识分子大众化的要求还是从文艺出发、以对文艺本身的大众化探索为主,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1942年,毛泽东在《讲话》中已经完全将大众化的重心放在知识分子身上:“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24在这一定义中,几乎已经看不到文艺自身的存在。说到底,在毛泽东看来,“一切革命的文学家家……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25。必须要求他们“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26可见,延安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不仅是文艺需要,也是政治需要;知识分子大众化不仅是对大众文艺自身要求的顺应,也是对政党政治命令要求的服从。
周扬在1944年《〈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中曾对3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简单化和表面化有过这样一段反思:
“大众化”,我们过去是怎样认识的呢?我们把“大众化”简单地看作就是创造大众能懂的作品,以为只是一个语言文字的形式问题,而不知道同时更重要、更根本地是思想情绪的内容问题。初期的革命文学者是自以为已经“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那时所理解的“大众化”就是将这“无产阶级意识”用大众容易接受的形式灌输给大众,为的是去改造大众的意识。我们常常讲改造大众的意识,甚至提出过和大众的无知斗争,和大众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斗争的口号;却没有或至少很少提过改造自己的意识。我们没有或至少很少想到过向大众学习。27这段话不仅道出“知识分子大众化”是30年代“左翼”文艺大众化缺乏的维度这一事实,而且揭示“知识分子大众化”是40年代文艺大众化强有力的一翼,是两个不同时期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关键差别所在。
三 文艺“民族形式”运动的历史转折点意义
延安文艺大众化与“左翼”文艺大众化的比较,可以清楚地揭示,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对中国文艺大众化道路的切实转变和实现发挥了历史转折点作用。
首先,文艺“民族形式”运动是毛泽东文艺大众化理想的雏形和实践开端。毛泽东在《讲话》中阐明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一种文艺思想,它有一个形成和的脉络,其雏形和开端应该是1938年提出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命题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创造文艺“民族形式”的大众化运动。经过“民族的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推进和深化,“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具体路线和方针才得以最终形成和落实。可以看出,老百姓—大众—工农兵,是一条线索贯串起来的、逐步成熟和完善的文艺思想,亦即毛泽东的“大众化理想”。
由于全民抗战谋取民族解放的战争背景,使建立在其上的文艺大众化诉求首先具有一定的道义基础。因此,以创造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核心的文艺“民族形式”运动,不仅在延安轰轰烈烈展开,也在重庆、上海等国统区获得文艺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形成一场遍及全国声势浩大的文艺论争思潮。这不仅在理论层面,而且在创作实践上都超越了“五四”个人主义文艺的话语和实践空间,成为“历史合理”、“政治正确”的主张被普遍接受。不论在国统区还是在解放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利用旧形式、民间形式进行通俗化、大众化的文艺创作蔚然成风。这也就为后来接受和贯彻《讲话》思想打下良好基础。如果没有文艺“民族形式”论争长期在思想上、舆论上、地域上、创作上的影响准备,“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单纯靠《讲话》一时之力是不可能很快推广成功的。特别是在作家的思想认识方面,前期论争暴露出的问题,使后来的《讲话》有的放矢,加强了《讲话》的现实针对性,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讲话》作为文艺界整风的指导思想,实质就是针对此前各种论争问题做出的解答,使作家很快解决了论争中存在的分歧,迅速发生思想转变。因此,把《讲话》看成是“民族形式”论争以来引发的各种问题的一个处理结果,是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从《讲话》涉及并解决的“文艺的源泉”、“普及与提高”、“知识分子与大众”、“文艺的对象”等——这些在“民族形式”论争中都曾激烈争论过的问题来看,亦可证明《讲话》和文艺“民族形式”命题的内部同一关系。显然,从“民族形式”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再到《讲话》,是一个完整的文艺思想体系。
其次,文艺“民族形式”问题承担着新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任务,是新中国文艺发展道路与方向的切实开端。文艺“民族形式”命题,是作为未来新中国的文化道路应当走和必须走的理念提出的,它承担着建立中华民族新文艺、新文化的任务。运动发起者周扬说:“民主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新中国文艺之建立,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目标。”28所以,作为后来新中国文艺发展道路与方向的“文艺大众化”的切实开端,实则是文艺“民族形式”命题提出并奠定的。基于这样的立足点就可以说,从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开始,中国文艺现代化开辟的个人主义道路向集体主义道路发生了切实转变。
总之,文艺大众化的真正实现,不仅仅文艺是名称、文艺服务对象以及表现内容的改变,从根本上说体现出文艺所属意识形态的转变,并为意识形态所属的社会基础和性质转变提供了前提基础。归根结底,4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承载着未来民族国家的文化道路和方向,所以,这一转变的意义就非常重大。
注释:
①周作人:《人的文学》,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
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195页。
②沈端先:《所谓大众化的问题》,见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③陈伯达:《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二集“文艺理论”卷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④鲁迅:《文艺的大众化》,同②,第18页。
⑤[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⑥艾思奇:《两年来延安的文艺运动》,《群众》周刊第8、9合期,1939年7月16日,第251页。
⑦1924252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页,第855—856页,第851页,第864页,第857页。
⑧余虹:《革命?审美?解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⑨洪灵菲:《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同②,第24页。⑩洛扬:《学的大众化》,同②,第66页。
1112《“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几次决议(摘要)》,同②,第3页,第4页。
13茅盾:《回顾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同②,第421—422页。
14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90-391页。15乃超:《大众化的问题》,同②,第13页。
16王独清:《要制作大众化的文艺》,同②,第18页。
17182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第692页,第559页。
20欧阳哲生:《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页。
21陈伯达:《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二集“文艺理论”卷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
22艾思奇:《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8页。
27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同14,第460—46l页。
28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同③,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