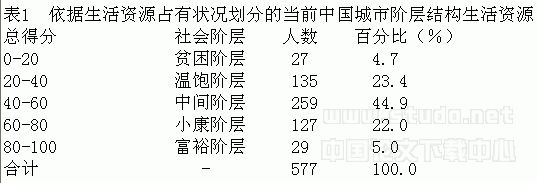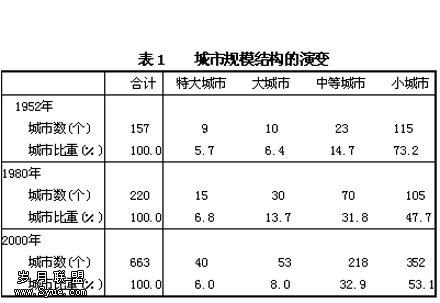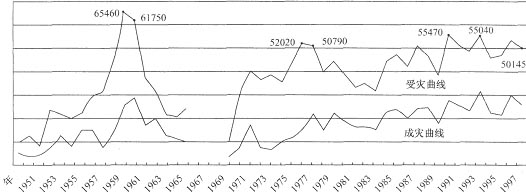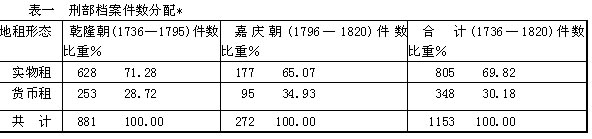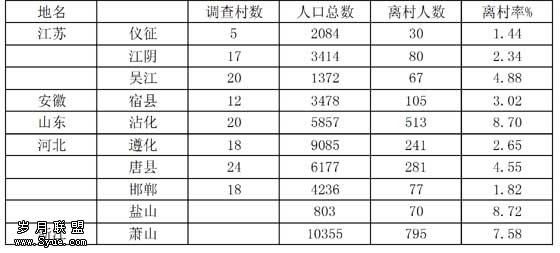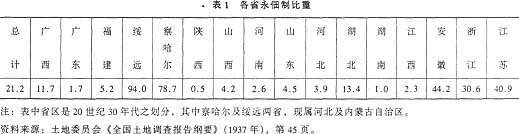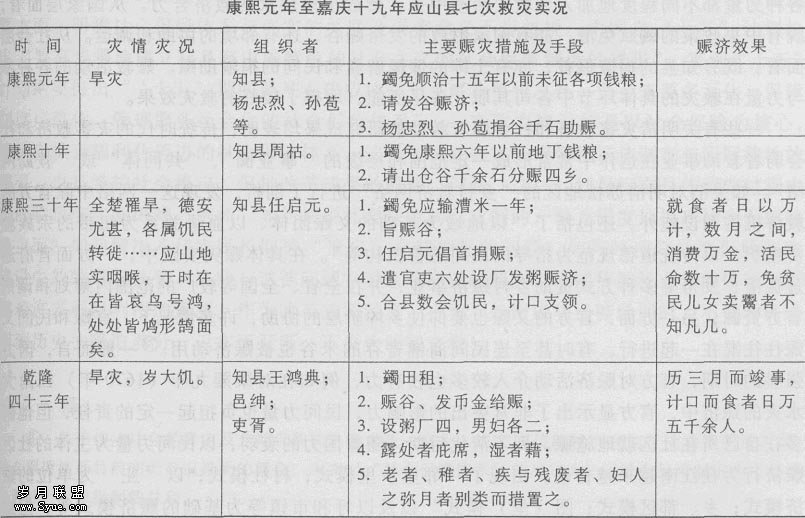台湾社会学的知识–权力游戏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2
Abstract
In Taiwan’s academic circle, sociology is a late comer with a rather small size of population. Among all of the sociologists, American-trained Ph. D. holders occupy an overwhelming amount. As a result, influenced by positivism as the main trend of thought dominated in American sociology, American-trained Taiwanese sociologists, particularly those holding the positions in the major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stitutions, forms as a dominant power-holding ideological clique.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sociology through a mean by controlling the various institutionalized channels of opportunity. To a small-sized academic community just in the beginning stage of promotion like Taiwan sociology, such a power-centralized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ztion will hazard to the future wellness of structure of the entire community if sociology is considered as a discipline desperatedly required to concern with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locality embedded in social phenomena investigated.
Keywords: Taiwan sociology, clique of power-holder, divergent problem, convergent problem
摘要
社会学是一个起步较晚、从业人口迷你短小的学术社群,其中的成员以留学美国、且具有博士学位的居多数。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社会学中居主流地位的实证主义传统,不自主地移植到台湾,成为社会学界潜藏的主流意识,并因而形塑出一个潜在的权力集团。尤其,在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提出「学术研究国际化以追求卓越」的口号,在政府中之学术行政单位极力的配合与鼓动下,台湾地区学术研究更形被「建置化」,这更加有利于各个学门中之权力集团的形成与进行操纵。对学术人口迷你短小的社会学社群而言,尤其,考虑到其研究乃针对着人的「散发性」存在意义,这样一眛地向「国际」倾斜的模式,不免有「揠苗助长」之虞。
关键词:台弯社会学、权力集团、派阀、散发性问题、聚合性问题
壹、前言
在1955年,「台湾省立行政专校」升格为「省立法商学院」,其原有之「社会行政科」合并了「台湾省立行政专修班」的「社会科」改为「社会学系」。{1}
假如我们以此年做为社会学在台湾地区之学院建制内被正式接受而成为一个独立学门开始算起,迄今将近半个世纪了。就一个学门的建置和经营而言,这样的一段时间,说长,并不长,但是,说短,倒也不是很短,回顾起来,还真有一些东西可以写,也可以谈。事实上,在这近半个世纪中,台湾社会学者多有从不同的角度来检讨台湾社会学的发展,写就的文字还真有一些。{2}
考虑到上面所提到的情形,为了避免使得在此的论述与过去已有太多的「事实性」讨论多有重复,在底下,基本上,我将不以引述具体经验数据进行所谓的「事实」描述来做为整个论述的重点。况且,我所要讨论的一些问题,在现阶段,事实上也多有难以找到具体的「经验实征」资料来做为左证的。{3} 话说回来,其实,对一个二、三十年来一直在台湾社会学界里打滚的人来说,有些现象是不需要藉助甚么实际的具体「经验实征」数字数据来支撑,就可以与同仁们分享感知的。此时,所谓「经验实征」数据,说起来,只是犹如一个医生开给神经过敏之无病病人的维他命丸一般,充做心理用的「安慰剂」而已。或者说,它的作用毋宁地更是徒具仪式性质的成份较多,乃用来强化一个没有自信心者的信心、或安稳住一个只相信数据之顽固者一碰到没有数字的情况就会引起的无名焦虑。
总之,在底下,我所要讨论的,甚多只是根据个人的经验认知和感受,提出一些自认为是属于批判性质的意见。尤其,针对着1990年以后台湾社会学的发展(特别是对未来发展的期待),更是我有意思要表示一些个人想法的重点。当然,我承认,这些看法都存有着个人主观定见的成份,未必能够获得同仁们一致认同的。不过,这不打紧,拿来做为,特别对着台湾社会学界的后来新进者,至少应当会有着一定的意义,不是吗?
贰、社会学做为一个学术社群的两个重要人口特质
早在二十世纪初,Simmel即指出,一个社群之成员数目的多寡具有着结构性的意义,它会在社群运作时带动出一些特殊的行为特征(Simmel 1950:87-177)。即使情形是由仅仅的两人添增一个人而成为三人的小社群,这么一个人的添增,就会使得整个社群关系的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譬如,在三个人的社群关系中,即将可能出现了两个人互动的情况所没有的派阀(clique)现象,同时也使得调停者(mediator)这样的角色得以呈现出来(Simmel 1950:145-153)。
当然,一般来说,一个学术团体的成员人数不可能只是三两人而已。再怎么少,至少也得有一、二十个人的数目,才得以成形。根据杨懋春(1976:1)所提供的数据,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台湾的社会学者总数不会超过10个人。当时,其中,除了出身日本东北大学之台籍学者陈绍馨与美籍传教士郝继隆(Albert R. O’Hara)之外,核对孙本文(1982)所列出曾经在大陆登记的名单,就有资料可查者当中,真正受过社会学正规训练出身的大概只有四位,分别是龙冠海、张镜予、谢征孚和郭骥。{4} 即使到了1960年代,加上挂得上边之非社会学本科训练出身的「杂牌军」,在大学任教、且真正从事社会学研究者,顶多应当是在20人之内。发展到1970年代,在国外(特别美国)接受完整专业训练的社会学者返台任教的日渐增加,但是,总地来看,还是不够理想。{5} 直到1980年代的中叶,加上学位非属社会学、但却在社会学系或研究单位任职的,则有40人左右(参看叶启政 1988:202,206)。到了1990年代以后,整个从业的总人数有着显著的增加。根据章英华等人(1996:2)所提供的数据,截至1995年,在各个大学之社会学系或研究所任教的计有85人,若加上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21名研究人员,则有106位。倘若再把分散在非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单位的77位「社会学者」再加进来,就有了183位。再者,根据苏国贤与蔡明璋(2003:3)在其中所提供的资料,截至2002年底,他们所调查的12个与社会学直接有关的研究与教学单位中,共计有131位(包含少数博士学位非属于社会学者)。若把上面所提到截在1995年的77位分散在非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单位的「社会学者」做为最保守的估计值而再加了进来,总计就有了208位。{6}
即使,在台湾这样一个蕞尔小岛上,相对于其它与人文与社会学科有关的学术社群(诸如文学、学、学、学、、学、教育学、甚至传播学或心),有200人左右之专业从业成员的社会学门,都难以相评比,而称得上是「已」具规模的学术团体。依我个人的意见,这顶多只算是「稍具规模」而已。况且,以具这样之成员数目的学术社群来看,扣除一些始终身处「边缘」的不活跃成员不予以,真正对整个社群的「官定」{7}活动有一定参与程度的,以最保守的方式来估算,应当不会超过苏国贤与蔡明璋(2003)所估计的130人上下这个数目吧!总之,不管是200人、130人、或在这之间的任何数目,就成员人口数目来看,台湾社会学界都不能说得上是一个「大」的学术社群。
其次,我要提到的是这些社会学者的训练背景的问题。首先,我要特别提醒的是,前面所提到那些人数甚少的所谓「第一代」的台湾社会学者,基本上都曾至国外(特别是欧美)留学,并获有至少硕士学位。但是,属于接下来的「第二代」,则因种种现实条件的制约,绝大多数不是留学生,而是在学院体制内循梯渐进地从助教(或讲师)一步步往上「爬升」至教授的职位。{8} 但是,到了1970年前后,特别是所谓「第三代」的社会学者,就渐渐以留学生为主体了,而这样的潮流一直延续至今,未见衰退。{9} 根据叶启政(1988:206)的估计,以1970年起算至1984年为止,从国外获有博士学位而返台服务的,至少就有32位。若再加上学位非属社会学,但却在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之研究单位任职的,则有了40人之多。再者,根据1982年教育部对各大学社会学系所进行的评鉴调查资料,萧新煌(1986:275)指出,在总师资人数146人当中,留学外国而获有硕士学位以上的计有94位(占63%),其中获有博士学位的高达60人(占41.1%)。若就留学国别来看,以留学美国的最多,计有76人(占52.1%),而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有52位(占35.6%)。从1982年至今又以过了二十一年,其间,在大学里,添加了一些与社会学有关的新学系与研究所,在要求新进人员必须具备博士学位做为基本要件的情况之下,上述所描绘的情形理当只有更形明显,而不会衰退的。尤其,在这二十一年间因届龄而退休的不在少数,而他们绝大多数是属于未曾留学国外、且是经由助教(或讲师)循梯渐进的「科班」出身者,所以,我扪有理由相信,目前的台湾社会学者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率应当是更高,至少应是有90%,甚至更高。如此一来,留学美国的比率,也就随之更加提高了。{10}
在这样就人口之质与量的双面认定之下,台湾社会学界至少体现出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构特质:(1)归属于每个专业次领域的人数基本上不会太多;(2)一旦所谓(至少是隐性的)派阀产生了,就有了酝酿足以左右着整个社会学之发展趋势的「霸权」机会。底下,让我就此二议题,分别做更进一步的阐述。
参、专业次领域之从业人口的「迷你短小」与其社会意涵
在1970年代的初期,张晓春(1972)曾经回顾当时之台湾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在1949年以后的二十年间,研究重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重要的领域:(1)人口研究、(2)家庭研究、(3)都市研究、与(4)青少年犯罪问题。再过四年,杨懋春(1976)则提出更具多元性的领域划分,他分为11个大类,计有:乡村研究、都市研究、社会变迁、人口问题、青少年问题、小区发展、小区权力、家庭现象、中国国民性、化、以及社会学研究法。当然,倘若比较张晓春与杨懋春所做的分类,我们很难立刻就下结论说,在短短四年(或乃至是整个二十年)之间,台湾社会学界就增加了八个专长领域。我认为,他们两人之分类所以有所不同,主要的理由乃在于两人有着不同的关照点与分类标准。另外,杨懋春是一个乡村社会学家,又是当时台湾大学农业推广学系的系主任,他把乡村研究(甚至小区研究)特别标示出来,自是可以理解。再者,自1970年代初期,当时任职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社会学者文崇一已带领了一个研究团队在台北关渡、万华与桃园龟山等地进行一系列有关社会变迁,特别是所谓「小区权力结构」的研究。{11} 与这同时,台湾大学心理学系(当时也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兼任)的杨国枢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李亦园领导一群学者,正推动有关「现代化」以及所谓「中国人性格」的研究、并召开研讨会,而杨懋春与文崇一两位正是其中被邀请的成员(参看李亦园、杨国枢 1972)。{12} 或许,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杨懋春才特别把小区权力、中国国民性、现代化、乃至社会学研究法标示出来。然而,不管怎么说,这多少自是标明着,杨懋春敏锐地呼应着当时兴起的一些新研究课题。
随着从业人口之绝对数字的增加,特别是这四十年来台湾社会本身历经了相当戏剧性的剧烈变迁,相对应的,社会学者的专业领域更加分殊化,自是可以期待。瞿海源(1998:1)曾经运用「台湾社会学论文摘要文件」索引与章英华(1996)所提供的资料,对台湾社会学者从1963年至1995年共32年之间所撰写之论文中为数最多的17个领域进行分析。无疑的,这份资料为现阶段台湾社会学界之专业分化的梗概,提供了一些更具体的讯息。在此,我不拟把这些专业领域一一列出,因为它们到底是些甚么,并不是在此引用这份资料的用意。不过,既然瞿海源所提供的仅是代表为数最多的社会学者所关注的17个专业领域,因此,事实上应当还有其它的领域存在,只是并不为现有的社会学者们特别关心或引起兴趣而已。尤其,假如我们审视当前台湾社会的变迁状况,其实,不难会同意,在未来台湾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当中,有些目前未被社会学者认定是「重点」的专业领域,将来可能会日渐被看重,而其中有的领域的从业者其实已经是在明显增加之中。总地来说,依我个人的观察,这些领域至少将包含诸如群族关系、女性主义、科技与科学社会学、信息社会学、文化社会学、身体社会学、和休闲研究与消费社会等等。因此,如此林林总总地加在一齐,够得上值得我们严肃加以考虑的专业领域,少说也应当是在30个上下的。{13}
其实,有关「到底台湾社会学社群内部的专业领域可以(或应当)划分成为多少类别、应当是些甚么」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此处关心的课题。在上面,所以花费了一些篇幅来描绘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社会学家为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分类,其实,只是在形式上尽量配合(或谓顺从)时下社会学界强调经验实证数据的一般规范要求,而力求多少有个「实际经验」层次上的依靠,藉此祈求获得同仁们的认同和心安而已。{14} 总之,不管我们可以把当前台湾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区分为10、15、20、30个、或甚至更多,或反过来说,乃至是少于10个,这都不打紧。只是,有一点可以认定、也必须认定的,那是:以台湾会学社群的总人口数来看,即使考虑了一个社会学者的专长领域可以(且往往是)跨越数个的一般现象(尤其是从事学术论文的审查时),一个次领域可以囊括之「够格」的社会学者,平均下来,至多应当不会超过20人,甚至一般是会更少的。{15}
以20人或甚至更少的人口数做为界范一个专业领域之操作的「临界」基数,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迹近「迷你短小」的状况。对我来说,迷你短小乃意味着两个特性:(1)只要是圈内的人产生某种形式的互动,原则上,隐匿性是低的,而警觉性和紧张性(包含正面与负面的)却往往又会是提高。(2)成员彼此之间通常是相互认识,而且甚至是彼此极为熟悉。因此,附加在过去互动所累积之印象中的情感与情绪(不管是正面或负面的)与利益的纠结,往往也就比较容易侵入人们的认知判断之中。换言之,处在这样相互熟悉而隐匿性低的情况下,一般说来,一个人比较容易把自己的整个人格投入,不但考虑是多方,而且,过去互动经验所累积的潜在情绪也较易释放出来,至少在潜意识(甚至是明显意识)中起了影响作用。如此一来,要求保持「客观中立」的「第三者」立场、以「理性」的「部份」自我姿态来呈现自己,说真的,实在并不容易。况且,要求保持所谓「客观中立」与「理性」态度之可能性的本身,本就是可以令人置疑的。
肆、由隐性的学术派阀而至隐性权力集团的形成
在人的社会里,基于利益、情感、喜好、出身背景、身处的团体属性、或接近机会之多寡…等等因素,使得人们彼此之间形成派阀,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因而,若说派阀的存在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社会定律,理应不会是太过分的。
对一个社会的成员来说,派阀的存在可以是被充分感知到,因而产生了明显的群属认同,甚至发展出相当强韧的连带关系。但是,情形也可能是,派阀的界限模糊,成员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跨越,连带关系松散,而致使成员不但没有清楚意识到派阀的存在,相对的,认同也是模糊而暧昧。此时,派阀若有的作用的话,它往往只是以一种隐性潜在、且是游丝一般的方式发酵着。只有在某种特殊的状况(如被挑衅或利益面临严重威胁)之下,派阀感才会以或是暂时且模糊、或是趋向更明显而稳固的姿态浮现出来。
在俗世的现实环境里,派阀的存在通常是依附在、并呼应着社会资源的分配现象,而这即标示着竞争(乃至是冲突)现象必然是存在着。尤有进之的,这更意味着与冲突对反、但总是相随而生的种种合作和妥协形式,也会呈现出来。于是乎,就在竞争、冲突、合作与妥协等等社会互动形式之多重而多元的错综交汇作用之下,人与人之间往往不自主地展露出合纵连横的情形。有人就认为,这样的现实社会生活,虽说是复杂、诡谲,但却是丰富而多采多姿,而乐此不疲地把自己卷入其中。
若说当前的台湾社会学界因有着派阀而导致在诸如利益分配、理念、乃至意识形态等等上面有所分歧,并因而产生了明显冲突,甚至导致不时有着合纵连横的权力运作现象出现,应当是言过其实的。依我个人的观察,在台湾的人文社会学科界当中,社会学界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不受到传统学术界强调年序尊卑、学校出身背景或亲疏远近之门阀观念所左右的学术社群。相对来看,它有着一个比较是属于西方学术传统强调开放、平等、且重视所谓「客观理性」的规范性共识的基本认知模式。就我个人的经验认知来说,这样的情形所以可能生成,似乎是以底下两个条件做为后盾。
首先、相对其他的人文社会学科的专业学门,社会学在台湾是属于晚起的学门。诚如上面提到过的,所谓的第一与第二代的,不但人数不多,而且,在当时的台湾人文社会学科界里,他们更一直无法抢到发言的主导权,甚至连让自己(与社会学)「曝光」的机会,也都一直是处在边陲地带。{16} 尤其,自1960年代起(特别是中后期以后)行政院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国科会」)积极介入学术界本身的运作,扮演起协调、支持(特别是提供研究经费与个人津贴补助)与尔后更为直接「支配」的角色以后,一个学者能否有机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国科会」的业务运作,无形之中成为抢得资源,乃至建立学术「霸权」的关键。在此一权力塑造与争夺战的当中,起步较晚的社会学界显然一开始就是处于落后的位置。{17}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展到第二代为止,台湾社会学界并不像有些学门,有着明显居霸权地位的个别「大老」出现。{18} 如今,第三代、乃至第四代人才辈出,日后? O否会出现手握霸权而足以呼风唤雨地左右整个学门的「大老」,则实有待做进一步的观察的。不过,依我个人的观察,尽管这样掌有「实权」的个别「大老」或许并未见明显呈现,但是,权力集团的雏形却是日益浮现出来。{19} 对此一现象,将在下文中再表示更进一步的意见。
其次,审视西方社会学诞生在西欧社会的历史背景,敏于反思和批判,尤其惯于挑战建制(因而,往往较为左倾,也较为激进)可以说是过去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学(特别是西欧社会学)展现出一种「理性的个人主义」典范。或许,这也正是社会学有别于其它相关领域最为明显的地方吧!{20} 这样的风范施及于1970年代以后的台湾社会学界,影响所及似乎更是明显。
在此,我愿意特别强调的是,依照我个人的认知与从业经验,打从1950年代社会学正式出现在台湾的学术建制之后,分享学术权力资源的特定权威「吻啄」次序(pecking order),{21} 基本上就一直没有明显地在社会学界出现过。观察过去社会学界里较有条件成为所谓「大老」的第一、二代、乃至第三代中较年长者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并没有任何一个人长期拥有足以左右其它人之学术生涯的实质权力资源。{22} 因此,若说台湾社会学界里有所谓的「大老」,那也只不过是徒具象征意义的称呼而已。情形所以会是如此,我个人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五:
(1)在「国科会」以建制的方式介入学术界的资源分配与成就认定之前,除了聘任、升等与「政治思想干预」之外,在早期的台湾?N界里,资深的学者实无太多具体的客观资源条件来约制其它学者的表现。
(2)平心而论,诚如上面提到过的,这些具「大老」之形式条件者,普遍来说,并没有具备足够与其名分对称的学术声望或具体表现。
(3) 其中容或有些人是具有成为掌霸权条件的「大老」,但却因个人的人格特质而不愿经营此种机会,或丧失了经营的契机。
(4) 就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可能是最重要、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莫过于是此处所提到之这种敏于反思和批判的「理性个人主义」典范产生了相当的作用。正因为有了这样之典范的存在,基本上,第三代以降的台湾社会学者,相对地较懂得「自制」,愿意遵行他们所认定之西方学术界定义的「理想」客观规范要求。
(5) 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是:自1980年属第三代的后期者兴起,台湾社会学界人才辈出而开始蓬勃发展。若说这才是台湾社会学真正有所发展的开端的话,那么,这即意味着,台湾社会学界一开始发展,就呈现「群雄并立」的格局,没有谁有条件占有所有(乃至只是大部分)的权力资源,也没有谁可以长期拥有左右一切的条件。正是这样一个「客观」条件的呈现,所以,我才会说,若有霸权出现的话,也只有权力集团。不过,晚近,台湾学术界提出所谓「追求卓越」的口号,努力向西方「先进」国家(实则是美国)看齐,形成了一种强烈自我要求的集体意识,尤其是一种建制性的压力。可以预见的,在此一口号的驱动下,对所谓「学术质量」的规范机制予以建制化的现象日渐明显,而这也因此可能成为推动、且强化权力集团(至少其雏形)日益浮现的基本动力。当然,社会学界理应也会是不例外的。
{1} 后来,与座落在台中市的省立台中农学院合并,改名为中兴大学。如今,它又独立出来,更名为台北大学。
{2} 就我个人所能搜集到的资料,至少有下列的文字是相关的:龙冠海(1963)、张晓春(1972)、杨懋春(1976,1980)、萧新煌(1981,1982,1985,,1986,1987,1995,1996)、萧新煌与张笠云(1982)、萧新煌与章英华(1996)、瞿海源(1982,1986,1996,1998)、叶启政(1982,1988,1995,1996)、黄金麟与谢冷雪(1983)、蔡勇美与萧新煌(1986)、文崇一(1991)、徐正光(1991)、顾忠华与张维安(1991)、林瑞穗(1996)、许嘉猷(1996)、叶秀珍与陈宽政(1998)、陈杏枝(1999)、章英华(1996,2000)、章英华等(1999)、章英华、吕宝静与黄毅志(1999)、章英华、黄毅志与吕宝静(2000)等等。
{3} 有些现象是有所谓的「质性」经验数据做为左证的,但是,诚如底下我要指出的,在台湾社会学界这样一个「迷你短小」的学术社群里,纵然我隐着姓名而只把这些「事实」说出来,事实上,大家立刻即可以相当准确地知道所指何人了。为了避免在同仁之间引起不必要的困扰,我只能舍弃不用。因此,倘若读者们感觉到底下的论说多有无法信服之处,那我只好承担下来,因为,毕竟,「隐短扬长」以臻至「人和」,还是一项值得肯定的美德,我不想扬弃。
{4} 其它如李鸿音和陈国钧很难说是社会学者,应当归类为社会工作、社会行政或社会福利学者。另外,芮逸夫和卫惠林两位实为人类学者。至于杨懋春则是在1958年才由美国来台,距1949年已是九年以后的事了。
{5} 最为大家共同接受的简单指标即是获有所谓的博士学位。
{6} 同时参考叶秀珍、陈宽政(1998:25)与萧新煌(1986:274)。
{7} 指的是,除了负责教学之外,譬如积极参加社会学会的年会、各种研讨会、发表学术论文、以及申请行政院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所提供的研究计划与奖助等等。
{8} 这样的情形也见诸于属于「第三代」的前段者。
{9} 有关对这个趋势的发展的分析,参看叶启政(1988:195-208)。
{10} 我个人认为,只要是在台湾社会学界里渡过二十年以上的人,理当是不必使用统计数字来「实证」一番,单凭着自己平常在台湾社会学界之聚会场合的接触经验,就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的。
{11} 其实,后来,张晓春也参与了文崇一所主持的一些研究计划。有关文崇一所领导之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可参看诸如文崇一(1975,1976)、文崇一、许嘉明、瞿海源与黄顺二(1972,1975)、黄顺二(1975)、徐正光(1976,1977)与瞿海源(1975,1976)等人的研究。
{12} 有关这一段时期的发展的讨论,参看叶启政(1988:208-218)。
{13} 根据苏国贤与蔡明璋(2003:17)调查的131位社会学者,共有34个专业领域,而每个领域乒均要与其它18个领域分享共同的研究人员。易言之,若说台湾社会学里之重要次研究领域大约分别有十几、二十人,那将是一个假象,因为重迭性实在是太高(苏国贤与蔡明璋, 2003:17-18)。
{14} 或谓意识形态,乃至风尚,亦无不可。说来,这样的作为只是一个学院理经常要求的仪式性行为,对整个论述的进行往往并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更未必有任何帮助的。
{15} 参看注13。
{16} 依我个人的观察和意见,譬如在1960年代初期,发生在台湾大学,特别是奉哲学系殷海光教授为龙头领袖的所谓「新启蒙运动」,就未见有社会学者参与。当时,以《文星》杂志为园地,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对台湾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等等进行批判,当中,除了当时在台北之法商学院社会学系任教(后来移居澳洲)的居浩然之外,也是见不到社会学者发声的。即使在更早知识分子以诸如《民主评论》与《自由中国》等杂志发表意见的时代里,基本上,设学者也是阙如的。纵然当时以撰写《从传统到现代》与《现代人的梦魇》二书而名噪一时的社会学者金耀基(1966a,b),也还没到美国修习博士学位。况且,就其在学院的训练背景而言,金耀基从就未在社会学系待过,尽管后来大家公认他是社会学者。再说,纵然我们把焦点摆在所谓的「纯学术」的领域来看,到了1970年代,当以心理学者杨国枢与人类学者李亦园等(等同于社会学界中之第二代)所领导的一连串学术研究风潮(如? {代化、科际整合与中国人性格等等),虽社会学者参与,但是,基本上,他们都不是居主导地位的要角。譬如,在李亦园与杨国枢在年所主导的《中国人性格》研讨会当中,虽有当时任职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文崇一、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的朱岑搂以及台湾大学农业推广学系的杨懋春和吴聪贤等四位一向被定位为社会学家参与,但是,他们并不是主角。况且,当时修习历史学出身的文崇一教授并还没「改宗」做为社会学者,而甚至被归类为人类学者(见李亦园、杨国枢)。至于吴聪贤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的训练基本上是农业推广学,而不是社会学。所以,真正够称得上是社会学者的只有朱岑搂和杨懋春两位。即使今天被定位为社会学者的瞿海源,当时也是以心理学家的身分参与其中的。
{17} 在1978年至1984年之间,笔者曾先以兼任副研究员、尔后以兼任研究员的身分同时任职于「国科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处。当时,个人就发现,虽然社会学被归类为一个独立学门,但是,无论就可能曩括的研究从业人员的数目、研究计划的数目、与使用经费的多寡而言,相对来看,这都是一个业绩「短小」的学门。而且,以当时人文社会学科界之资深学者的的学术成就表现和一般声望排比来说,当时的资深社会学者(甚至包含国科会人文社会科学处所聘之社会学领域的「咨议委员」),平心而论,都是难以与其它领域相评比的。即使与从业人口比社会学还小(或至少是相当)的人类学相比较,情形也是如此的。
{18} 我当然可以把这些「大老」指名道姓地说出来、并加以分析,但是,如此一来,这将会变得过于敏感,引来不必要的争端。再说,对台湾人文社会学科界的「大老」现象进行社会学的解析,并非本文所关心的旨意,因此,在此,我就把「大老」现象存在于某些特殊学门当成是毋庸争议的既成事实,有关的细致举证工夫也就打住不提了。说来,基本上,这是我个人身处台湾人文社会学科界里近三十年来的经验感知。尤其,个人曾经以兼任研究员的身分在「国科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处任职过一阵子,深体会到这种「大老」现象的存在与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19} 在此,必须区分权力集团与影响集团两个概念。前者指的是一群实际掌握了足以左右齐他人之具正当姓的权威机制者。最典型的例子即是如手中握有审查别人之著作的大权、实际参与学术政策的厘订、或决定研究计划的给与等等。至于影响集团指的则是它是以说服的方式来左右别人的行为、感情、认知模式、或思想等等者。体现在学术界中,其最典型的做法即是透过著作或演讲等等的论述方式来进行。大体上,权力集团往往构成为影响集团,但是,影响集团却未必有条件成为权力集团。
{20} 这可以从1960年代风行于欧美的学生运动当中,不论就教授或学生群体来说,在支持学运(尤其左倾思想)的当中,社会学家始终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Marcuse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在运动过程中,社会学(当然,特指马克思主意与批判理论)做为一种启蒙知识。更是重所共见的。其实,这样的情形也见诸于1980年以后发生于台湾社会的社会(特别学生)运动当中。另外,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当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时,蒋介石曾安排飞机把当时留在北京的「名」教授(特别是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两个单位)载至台湾。在撤退到台湾来的这些人文社会学科的「名」教授当中,就是独缺社会学家。在1983年,香港中文大学曾举办了一个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研讨会。这使得自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之人文社会学科学者得以有机会首次面对面开会。在这次的会议中,我有机会碰到中国社会学界的「大老」费孝通先生。当时,我即以「何以不见任何一个出名的社学学家跟随蒋介石? 鴠x湾来」这样一个问题询问他。费先生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都厌恶国民党,而同情共产党,并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在此,我无意争论类似「共产党是否比国民党好」,或「共产党是否真的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样的问题,猺z费先生的话,为的只是表达一个可能的「倾向」:就学门的发展传统而言,社会学家有比较左倾(当然,用于当前这样的所谓「后现代」场景,情形是另当别论)的倾向,同时,批判的思维传统更使得他们比较勇于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而较接受西方启蒙时期以来所揭橥的「理性」态度。
{21} 此乃挪威动物心理学家Schjelderup-Ebbe(1935)所提出之概念。他发现,在一群鸡当中,总是建立起一个相互吻啄的次序。其中会有一只是最具优势,它会吻啄其它的鸡,但是,其它的鸡就是不敢吻啄它。之后,有一只是次强的,只有最强的一只会吻啄它,而其它则不敢。如此类推地发展下去,直到最后,有一只是居最弱势的地位,它不敢啄任何其它的鸡,只有被其它鸡吻啄的份。
{22} 处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台湾社会里,即使到了今天,我还是感觉到难以毫无保留地把心中所认定的「实情」说出来。由于这中间牵涉多位前辈与同仁们的种种「私闻」,基于中国传统所看重的「厚道」美德,我实在无法畅所预言,尤其是形诸于文字,这一点还得商情大家见谅。 伍、社会学界的主流意识型态与其效果意涵
既然,就现实而言,形成派阀(甚至霸权)乃是人之社群所具有的普遍现象,因而,在讨论有关派阀的缺失问题时,现实地来看,整个关键的所在就不应在于消灭派阀,而是如何导引这样的现实现象向着较为良性(至少降低恶性)的方向。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如何使得霸权(或权力集团)的负面作用降到最低程度,于是乎,也就成为促进一个学术社群「向上」发展的前置课题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进一步地使派阀与霸权有着发挥正面作用的条件。在此,我不拟讨论这个关涉「应然」面向的问题,而仅对一个属于「实然」性质的课题提出个人的看法。这个课题是:在前面所指陈的诸多条件下,台湾社会学界到底呈现了一些怎么样的权力集团现象?
从前面提到过的一个现象,即台湾社会学者留学美国的比率居压倒性的优势,我们可以推论:假若美国社会学的训练潜存有一个主流意识传统的话,那么,这个主流意识就会顺理成章地为留美的台湾社会学者们接受下来,除非一个人能够保持高度的自我警觉,一直对自己所学的持有着自我批判的态度,并能够从不同的学术传统吸取另类的经验。那么,到底,美国社会学的主流意识是甚么?这无疑地就成为关键的课题了。
大体来说,西方的精神传统讲究的是,一切的研究都需要有经验实征性的证据做为后盾来支持,否则,都是不足采信的。基本上,这样的实事求是态度是可以接受,甚至也应当予以肯定的,但是,不要忘了,一个对科学认知的基础稍有了解的科学家理当都会同时体认到一项「事实」:任何的科学方法与程序的运用,事实上均内涵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瑕疵」。因此,无论就信度或效度而言,它有着一定的极限。{23} 如此一来,谦虚地不断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同时认识到自己所援用之方式、策略、乃至立论本身的局限性而不越位,更是一个科学家必要具备的基本伦理态度。然而,吊诡的是,这样一个后者的强调,经常却是被自认为「科学家」的一些社会学者们所遗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基本上,这更是一种对社会学做为科学之「源起状态」{24} 的遗忘,其表现在西方社会学传统中者,又是以采取实证主义做为思维与认知模式的表现特别明显,而这恰恰是潜在于美国社会学之知识传统中的主流意识。{25} 准此,一向即极端地向美国社会学倾斜靠拢的台湾社会学家,特别是当前掌握权力机器的第三与第四代,打从一开始,自然是不自主地以这样平面化的经验实证思维和认知模式做为经营社会学知识的基础,而且,甚至也以此当成是确立知识之正当性的不二标竿。{26}
在这儿,我没有意思否定以实证主义之科学观所经营出来的社会学知识,以为它是完全无效、也是无用的。我所不能同意的,是那极端实证主义的信仰者所以为「唯有透过经验实征(甚至是其中更特定)的方式而经营起来的知识,才是科学的,也因此才有价值」这样的主张。换句话说,只要不越位的话,做为一种逼近「社会实在」的进路,所谓经验实征的研究策略还是有着一定的意义与价值。是的,在今天的台湾社会学界里,极端的实证主义信仰者其实并不多见的,但是,在潜意识里,认知上倾向实证主义者却是不在少数。特别,当对别人的研究成果实际进行评审时,潜意识地以实证主义之科学观的立场来操作,依我个人的意见,一直就是主流心态。{27}
对我来说,台湾社会学深受美国(或更扩大来说,整个欧美)社会学知识传统的影响,是远远超过单纯的实证主义的认知模式而已。整个台湾的社会学思考所赖以运作的概念架构,几乎全是由西方「先进」社会移植进来的,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28} 就十九世纪以来东西两种文化不对等的交流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原是沈淀着甚多无可奈何的历史命运际遇,实也无法、更是不应予以太多的厚非的。固然,做为一个非西方的社会学家,我们实有必要对孕生自西方特殊之历史背景与文化传统的社会学概念,以保留的态度不时予以反省批判,但是,在这儿,我认为,我们还是可以再退一步地来接受历史所赋予的现实命运,而以为只要我们一直保持着审慎而批判的态度,运用西方社会学的概念来分析台湾社会,还是具有着一定的恰适性和妥贴性。况且,现实上,这更是无以避免的历史宿命,因为,经过了这一、两百年来西方现代文明不断地洗礼,我们的社会毕竟也与现代西方社会分享着一些极为? @同(至少相似)的结构特征。
情形虽说是如此,然而,在我可以观察到的范围里,对当前台湾社会学界里同仁们所依循的基本操作准则中有一个基准点,我还是深深不能同意。这个基准点是:无论实际进行自己的研究、传递知识、撰写、或对别人的研究和论述进行评论时,一切都以美国(或谓西方)社会学所设下的认知典范做为唯一的归依。说来,这样的认知态度是因为长期以来缺乏属于自己的知识系统与自我意识所孕生之自卑心态的典型表现,而这恰恰在盲目崇拜殖民者的被殖民者身上最经常见得到的。{29} 真碰巧的,在今天的台湾社会学界中不少意气飞扬(尤其年轻一代)的社会学者身上,我们正可以看到这样的心态以不同方式与不同程度发酵着。{30}
处在现代西方科技理性文明一直高居优势地位的时代里,向西方模仿学习,原就是十九世纪以来之非西方社会的人们认为图谋自立生存的必要途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台湾社会学一眛地向世界第一强权–美国的社会学知识建制紧紧地靠拢,
本就有着用来加持、并保证自己的学识能力的潜在作用。遗憾的是,在这样的历史格局里,与一般人相比较,社会学家的智慧似乎并没有显得更加高明,感觉也没有来得更加敏锐。正相反着,专业知识的权威性反而使得社会学家的定见更深,因为唯有把自己所接受的知识体系当成是「真理」的述说而坚实地信仰着,他们的身分和象征地位才得以牢固地被保证着。于是,知识的傲慢变成是确认知识之权威性的一种必要矜持,也往往是最佳的护身。如此一来,学者(当然包含社会学家)往往变得比谁都顽固,但是,他们自己则自认为,这是捍卫真理、或择善固执、或坚持学术良知。其实,说穿了,在本质上,这与初民社会里的巫师因掌握了咒语和巫术的专有权而成为人人崇拜、敬畏的权威,又有甚么不同呢?其间所差者恐怕无几吧!
挟持着科学的名号,专业知识几乎已成为是一种无神的现代信仰,而且为所谓的「学者」所垄断,并同时把他们与芸芸众生轻易地区隔开。那专业论文中诘屈聱牙的陈述和扑朔迷离的概念,总像古代巫师的咒语一般,叫人不寒而栗。{31} 一般的人们更因自己的无知而对它产生了无以名状的敬畏心理,感觉到倍加肃然起敬。于是,在实际的现实情况中,特别是表现在向西方现代文明高度倾斜的非西方边陲社会里,一般人的无知、专家的傲慢、与知识分子的热情使命感,总是交织在一齐,而为科学知识成就出一种难以撼动的无比神圣地位。
总而言之,当以上所陈述如此一般的「科学」态度以潜意识的状态活动在从业人口迷你短小的学圈的时候,一旦其内部自身之权力互动所可能内涵的「暴虐」作用发酵,其效果往往会显得特别明显。情形何以是如此,让我在底下试着提出一些说法来加以申述。
首先,诚如在前面提过的,迷你短小的从业人口容易促使主宰的权力集中在少数资深而被认定是「有成」的「前辈」手中的现象特别明显。尤其,今天的台湾学术界里弥漫着追求所谓「卓越」的风尚,这使得那些(特别是留美)的学术领导阶层以一个美式的基本信念–「不发表则消亡」(publish or perish) 的制式规范–做为评比的基本判准,并进而强调进军国际(实则是美国),因而,一个学者的学术论文能否刊登在国外(特别是被列在美国人所创造之SSCI)的学术专业刊物之中,乃是判定一份研究成果的良寙与界定这位学者的质量的标准。这么一来,界定所谓「学有专精」的有成者,是有着更为「客观」的标准,但是,霸权的形成于焉有了更加具体而稳固的「客观」依靠基础,而且,也更加有机会形塑出少数「学术有成」的「杰出顶尖学者」,他们于是乎成为有条件操纵学术资源的当权者。在一个迷你短小的学术社群里,他们自然而然地是占据了几乎所有可以操控资源(包含诸如自身获得? 媞堛獐?U与荣誉、以及对研究经费、奖助机会、荣誉之给予等等的审查与核定,或种种有关整个学术研究发展与高等之政策的厘订等等)的机会。
其实,资源操控在一些少数「学术有成」的「杰出顶尖学者」的手中,并不是绝无仅有的特殊现象,而且,也不是只见诸于学术界而已,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一般社会现象。然而,对台湾社会学界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因为整个社群的人口过于迷你短小,导致「异类者」企图创造足资具另类(甚至只是另外的仅仅一个)选择机会的「对抗」空间,在现实上都是不可能的。结果是整个资源以及所有的「荣誉」和「成就」几乎都集中在这些少数的「有成」者的身上。
其次,在此,让我特别单就保持审查制度的所谓「公正性」做为例子来做进一步的说明吧!在像台湾社会学这么一个从业人口迷你短小的学圈里,审查时保持匿名与否,其实,往往已不是那么重要。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从业人口的迷你短小,本就使得企图在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匿名性,变得几乎是不可能,只要指头稍稍一扳,就可以猜出是谁审查的。而且,审查者也一样,甚至只要一看文章的题目,顶多,把文章看个几页,就立刻猜得出是谁写的,准确度经常是十不离八九。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要保持完全的客观中立态度,谈何容易?以至于实际的情形往往是,表面上自己以为是保有了客观中立的态度,但是,实则是整个人的情感感受都投入。尤其,在极为关键的时刻(如在「通过」与「不通过」的边缘),情感性因素的介入、对特定认知与思维模式的好恶、甚至派阀的归属认定产生了作用,更往往是无可避免。同时,在这样迷你短小的圈子里,要不,就是专精、且偏好的过于集中(体现在台湾社会学界里的,即如所谓「阶层与社会流动」的研究);要不,就是各有所好、各有所长,甚至南辕北辙,难有搭调的可能(体现在台湾社会学界里的,如所谓的「社会理论」)。不管情况是怎样个样子,结果所呈现的,往往总是两个极端情况:若不是相互包庇奥援,就是相互砍杀凌虐。就现实体现在当前之台湾社会学界中的情况来看,情形则似乎是以后者较为明显。{32} 尤其,倘若审查人又是集中在各个次领域中少数「有成」的学者手中时,那么,自命是高标准、高质量、但实则可能是充满着偏见与「暴虐」的审查意见,无疑地是扼杀了许多研究成果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机会。
陆、对台湾社会学未来发展的一些期待
顺应着时代的潮流,固然我们不能够(或许,也不应该)像过去第一、二代的社会学者一般,以人情关系、身分地位、或辈分等等来决定论文是否可以刊登、或获得升等与奖助的机会,但是,也不应以迹近「过分」严苛的态度来相互折磨,借着制造别人的挫折来证成自己的敬业、用心和学养的恢弘。需知,在这学门刚起步萌芽的阶段,尤其是一个人口的绝对数量尚属不多的学圈里,彼此之间以「超高」标准来相互诘难,只有创造更多的相互挫折与创伤,带来的只会是更多的怨怼与不满。这不但加深了彼此之间的距离,而且平添更多本质上是意气用事之成份较多的情绪性(或利益性)派阀,因而,在整个社群当中孕育了更多的相互疏离氛围。对一个人口数众多的学术社群(如美国社会学会),圈内有着这样的疏离氛围,毋宁地可能对主流产生一些正面而积极的反思冲击作用。但是,对像台湾社会学界这样一个迷你短小的社群来说,纵然这样的疏离氛围大到一个程度,它也不足以形成一股力量来促
使主流霸权进行自我反思。相反的,这只有更加导使权力集团有着更为有利的条件一直霸据着种种资源,进而界定着何种的社会学知识与研究形式才是「正确而正当」,因而,才是「正统」的。{33} 这样的正统性的塑造,对一个正处在起步阶段的迷你短小学术社群而言,情形有点像台湾俗语说的:「还没学会走,就要学跑」,带来的将会是一种过早来临的宰制现象。我深以为,这很不健康。
在我的认知里,一旦怨怼而疏离氛围不是例外而是有着一定的普及性的时候,这样之「早熟」的权力集团的宰制,将只会把权力推到一种看似有权、但实则无力的孤芳自赏境地,而只是在小茶壶里翻腾开水,制造一些小风暴,让权力集团中的少数人在其中干过瘾。是的,这些少数人确实是掌握了「官定」的权力机器(如教育部或国科会里一些具决定性的权力机会,如审查、规划、政策的厘订等等),界定了何种的社会学论述方式与内容才具有着正当性。而在这中间,当然,更是为「有权」的个人带来了一定的名与利上的成就(如荣获杰出人才或院士的头衔、或获得国科会的研究奖金等等)。但是,依我个人的意见,对导引整个学术发展的立场来看,以这样的方式来塑造学术的奖惩规范建制,基本上,类似在制造普洱茶时,以沃堆方式来催化发酵的做法一般,是一种进行揠苗助长的催熟工夫,以至带来了一种不正常的「成熟」假象。对这,说是「早熟」,其实并不对的,因为它根本就从未有过任何之「熟」的成份在。
以揠苗助长的催熟方式而带来的「成熟」假象,看起来,往往像似带来了蓬勃发展的景光,然而,这本质上只是一种无根而虚飘的表象荣景而已,是不踏实的。对整个台湾社会学的长期发展来说,这样的荣景假象,基本上是起不了任何正面而积极的帮助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带来了严重的内伤。所以做这样的说法,有一些理由我认为是重要的,底下,让我就此做说明。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对长期受挫的无力者来说,到头来,他们往往容易与权力中心产生自我疏离的情形。一旦这样的人愈多,权力集团中心实质上的有效「统制」(更恰切来说,应当是影响)辖区,显然就反而变得愈小、也愈显得无效,更不必期待他们会有甚么具挑战性的反思契机了。这情形倒有些像周朝末期的皇权一般,其有效统治范围往往仅及于京畿附近,它有的只是一个「共主」的象征名号而已,而且,一切的荣景仅及于自家的皇宫,任何有心向外发展的企图努力都显得欲振乏力,不可能看得见任何实际成绩的。
总之,诚如在上面已经约略提到的,由于整个的绝对人口数量不够多,这些疏离者又是零星而分散着,他们往往并不足以形成为一个有足够临界人数的次团体,因而,疏离并不足以让这些「边缘者」形成为一股动力,使得他们有机会建立起自己的基地(如办一份较具自我属性的学术刊物),可以形成另类、但却是具对等有效力量的势力来表达抗议。现实上,结构性条件的不利限制,使得他们所能做的只剩下一样的动作;那是:远离权力集团所界定的「官定」游戏,成为一群自我放逐的无声「小众」。当然,在主流权力集团的眼中,这些疏离者往往即是学术质量低下、且甚至是自甘堕落的「失败者」,是应当被遗忘、也可以被忽略的一群。就我个人的立场来说,对一个学术活动正处在起步阶段之迷你短小的学门,一开始,就有意或无意地为论述的基调订有了「正统」,因而把一些未能同调的同仁推挤在外,将会对整体的发展产生了一种自我扼杀的负面效果。结果带来是,在认知与思维态度上型塑了更紧密、更深邃的特定意识型态,而在发展的一开始,事实上就已经把自己导入了死胡同。当然,或许,这些考虑都是多余的,因为主权者总是吃香喝辣的,靠着他们自己所撑出来的「荣景」,早已宣告了社会学的发展是蓬勃、也是成功的。这样的自我界定、自我衍生、自我证成的理路,不正就是整个台湾学术界(当然,也包含了社会学界)早已存在的一种现象吗?然而,当我们说这只是一个自我陶醉的虚拟假象时,也只会被讥笑为是失败者的酸葡萄心理作祟所说出来的托辞罢了!
其次,在上一节中,我曾经特别提到,晚近台湾学术界的领导阶层强调所谓「进军国际」,做为检验提升学术水平的具体指标。在今天这样一个已明显朝向全球化的时代里,现实地来说,实在没有太多的理由让自己怀着「义和团心态」,闭起来门来造车的。尤其,对一个具有进取心的边陲社会来说,所谓「进军国际」,至少向先进国际势力看齐,其实是一种可以理解、也可以预期的「良性」的企图心理。况且,就整个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来说,欲提升学术水平,更是不能不对西方「先进」社会的知识体系有所关照的。{34} 但是,就人文社会学科的诸学门而言,是否应当鼓励以(或其它西方文字)来写作、并发表在西方世界的学术刊物里,尤其是以如此的作为做为判定一个学者的成就,着实是一件可以讨论、甚至是予以质疑的课题。
是的,从十九世纪以来,一向就缺乏自信心、且有强烈自卑潜意识情结之边陲社会的人们,努力学习向西方中心社会认同而靠拢,原本就不是少见的,因此不足为奇。但是,对社会学者来说,倘若绝大部份的人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态,那么,我认为,就相当值得检讨了。
回顾西方社会学发展的历使背景与进程,有一个特点是相当明显,且一直被西方社会学家奉为圭皋。这个特点是,其学术传统甚强调开放性与批判性,而尽管批判指向的是外在的社会现实实在本身,但是,自我反思的批判精神却是一直内涵在整个传统之中的。没错,我深知,只要一提出传统来,不免就有假权威来扣帽子的嫌疑。再说,纵然自我反思的批判精神确实是西方社会学的传统,我们实在也没有非承接下来不可的绝对必要。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主张多元化、去中心、与去权威的「后现代」场景里,诸如漂荡、变动、更易、拼贴等等几乎已成为普世的价值,因此,任何以某种特定的传统做为终极性的标竿以来检讨台湾社会学的现况,若未能普遍获得大家的肯定,原是可以理解,也是必须接受的。毕竟,一切的活动(包含社会学的研究)都可以看成只是一种极具游戏性质的潮流而已,其中本就容不了、也没有必要容纳「真伪」的问题,那太严肃、也太沉重了。
是的,上述这样的说法,是可以说得过去的。这也就是说,坚持以西方社会学的特定传统精神做为评论当前台湾社会学发展的基础,在态度上,兴许是有嫌趋向保守,甚至,可以说是食古不化的。然而,在此,我还是选择这样一个来自西方社会学的传统,做为检讨台湾社会学发展的标竿。所以这么做,其实用意是相当明显的。我认为,发展至今,台湾社会学才勉强算得上是真正开始要进入「起步」奠基的阶段,而在这起步奠基的阶段,自我反思的批判将会是特别有助于整个社会学开展更为多元、开放的发展空间的。尤其,如此才不至于使得整个学们在一开始就立刻被定于一尊,形塑出一个独大的权力集团,而窒息了所有其它之另类的可能性。否则的话,整个社会学思考的想象力将被扼杀,而且,文化感应力也将跟着萎缩。
行文至此,我愿意再特别提出底下的一些意见来与读者分享。首先,我要说的是:假若我们期待社会学的研究有助于人类化解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境遭遇的话,那么,当我们进行社会学的思考时,是否能够发挥想象力与文化感应力,相对地就变得是重要了。然而,如何让社会学的想象力与文化感应力发挥出来呢?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难以三言两语就打发掉的。为了响应这个问题,首先,让我借用Tyrell的说法来做为切入的接口。他曾以散发性的(divergent)和聚合性的(convergent)两个词汇来区分「不可以使用逻辑理由来解决」和「可以使用逻辑理由来解决」的两种问题形式。他指出,生命基本上是由散发性的问题维系着,而这些问题始终是「悬而未解」,或许,只有死亡才能提供解决。但是,聚合性的问题却是人类最有用的发明。做为一种发明,它并不是真正以本有自在的姿态存在着,而是经由一种抽象的程序被人创造出来。准此,一旦问题得以解,解决方案就可以被写下来,并传授给其? L人。如此,往往可以使得接受的人不需再重蹈当初开始寻找解决方案时的心路历程,就马上可以予以运用(引自Schumacher 2000:104)。
Schumacher即指出,诸如物理和数学等等的知识,就是只管着聚合性的问题,而这正是其为何可以不断「进步」,让每个新世代都能承继先人之遗绪,而在百尺竿头上更进一步的缘故。不过,人们所付出的代价往往可是相当沉重,因为只跟聚合性的问题打交道,是不会融入人们的真正生活,有的,只是一再地远离。职是之故,以自然科学认知模式为基架之实证主义的科学态度,基本上就是希望靠着一套「削减」的程序,把所有的散发性问题转化成为聚合性问题。如此发展下来,结果往往是窒碍了足以提升人类生活层次之潜在力量的发展,也使得人类天性中的情绪部份一再沦落(Schumacher 2000:105, 106)。
其实,这样之区分的说法,早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学术界就已经成为讨论的重要议题了。 Max Weber 主张社会学研究的要旨在于对社会行动背后的意义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其实就是呼应着这样之对「现象」分殊特性的认知。对台湾社会学家而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大家没读过Weber的著作,以至于不知道有这样的说法,关键是在于,大家没有充分感知到Weber这样的提法背后所蕴涵之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深刻意义罢了!
对身处文化边陲地区的台湾社会来说,尽管容或社会现象所内涵的散发性问题意识,才是一个具社会责任意识的社会学者真正应当面对的课题,但是,一再地把研究课题「聚合」化,却是台湾社会学者实际操作的基本样态。这正说明着实证主义的思维幽灵一直是盘据着台湾社会学者的心灵,而且是心灵的深底之处。在这样的一般状况之下,整个问题的重点已不是强调「量化/质化」或「理论思辨/经验实征」之两元分殊的课题可以来说明了,因为,在两造的身上,我们看到的都只是实证主义的聚合性思维幽灵。这表现在自认接受了「更完整」(也就是「更良好」、「更优秀」)之西方(特别美国)「科学」社会学训练的社会学者身上,可以说是明显的。他们确实是孜孜勤奋地做着研究,也有论文发表在所谓的「国际」刊物(当然,是SSCI 所列举的),但是,他们对话的参照对象却始终只是一向熟悉之相对应的西方社会学论述,举凡概念、理论架构、研究策略、思维模式一应都是「上国」的,而? o一切与他所生活的台湾社会,尤其周遭之芸芸众生所感知的(特别是有关散发性的)问题,基本上是毫无瓜葛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台湾社会学家们有着各自、且往往平行而不交错的团体。这些参考团体是指向西方的社会学界,其中,当然,美国社会学者是最主要的参考对象。于是,在做学问上面,台湾的社会学者们彼此之间既搭不线,也不想搭上线。{35} 这使得社会学者虽是身体共处在同一个邻近的空间(例如,同一个学系里),但是,他们的心智却是互不来往、也互无影响的可能。他们之心智活动所归属的「隐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s) {36} 是遥远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或乃至日本社会学界,尤其是他(她)过去留学是国时的师承归属。
显而易见的,这样以迹近平行不搭线之自外移植的聚合性认知模式来进行社会学研究(尤其是学术性的互动,特别是评比与审查),不但使得台湾社会学者彼此之间漠视对方的研究成果,而且往往也使得上下代之间的联系变成本质上具短利之功利取向的互动(诸如提供研究助理机会、吸取西方最新的知识、撰写出国留学的推荐函、建立良善的人际等等)。在这样的一般情况下,结果是,原本就已是迷你短小的学术社群,实际上,更加显得是特别的迷你短小,情形几乎是每个社会学者都「自成一家」,在学术研究上,彼此不互相来往。如此一来,整个台湾社会学的研究成果难以形塑集体累积性,这自然也就构成不了实质的「学术传统」了。个人的学术研究于焉成为只是一种炫耀自己熟稔西方知识的概念游戏、或谋生工具、或生涯托体、或谋求名利的道具而已。人在,研究在,人亡,研究亡,所有过去的研究成果终究都化成灰烬,被一再吹进的「新」西风不断地吹走,任何的努力都留不下丝毫的痕迹。{37}
对我来说,倘若台湾的社会学者没有认真地去体认一个社会现象(因而,社会学知识)所内涵的散发性特质,也不知体悟本土之特殊文化传统、社会条件与历史背景等等,对孕育社会学知识乃深具意涵、且为必要的话,他所做的学问将会只是一场文字游戏,也许论述内容四平八稳、中规中矩,对西方的引注十分齐全,而且也紧贴西方社会学的主流概念、理论与议题,深具「国际化」的要件,但是,他所呈现的内容却是缺乏生命力,难以让人们有所感应,也总令人觉得与自己所经验的台湾社会有着距离,甚至是不相干的。然而,吊诡的是,在有着居主流优势之西方(尤其是美国)「先进」之知识体系做为后盾的情形下,居优势地位之那些「学有所成」、且往往自命不凡的留洋社会学者,总又是以他自西方学到的东西做为座架来评断一切。结果,除了眼界高不说外,凡是不合乎他那「优越」知识体系的规矩所界定的(实则,应当是有限且偏狭的)范式,都不足取,也因而在质量上都有问题。在这么的情况下,譬如,本土所训练出来的「土」博士,总因「饲料」不尽完全相同,其所表现不同的地方,自然容易让(至少某些优越感特重的)留洋社会学者觉得,他们样样都是不如的,是社会学界里的「次级品」、或至少是另类的产品。{38}
总之,回头来看所谓西方的古典理论,举凡Marx、 Weber 、Durkheim、或 Simmel等人的论述,那一个不是紧扣着他所的时代与社会的特殊性(最明显的即是资本主义体制)而引生出来的。即使是近代的Parsons、Bourdieu、Habermas、或乃至Luhmann等人,纵然其论述的抽象理论度相当高,表面上看起来,其提出之论点具有超越特殊时空的普遍性,但是,实则还是反映着他们各自所处之社会的种种历史与文化际遇,也与过去既有的一些相关论述对着话。因此,任何社会学的论述,追究到底,都是「本土的」。今天,西方社会学的论述所以看起来、也实际呈现出「普全化」的现象,实乃因西方现代理性文明具有优势性而产生扩散作用所导致的。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中的所谓「结构」基架,基本上朝着西方社会的结构基态而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整个学术界的思维认知模式基本上是「舶来品」,乃呈现出向着西方单面、且亦步亦趋倾斜着的情形。{39} 然而,做为一种本质上具备着散发性特质的学问,台湾的社会学要有其特色(因而,有着特殊精神),尤其,要能对台湾这块土地有所感应、也有所贡献,本土化是必然要走的方向。即使欲求在全世界的社会学之中有一席地位,尤其是对人类整体文明的未来发展有所贡献,本土化更是必经的过程(参看叶启政 2001)。我的意思是:只有先走进西方社会学的深处去掌握其传统的底蕴,并佐以对本土之种种的关照,再回过头来反照西方做深切的反思,才可能为台湾社会学寻找出一条有个性、富创意、且能在全世界当中占一席之地的希望之路来。否则,一眛地跟着西方社会学流行的论述的骥尾走着,学术研究在台湾,将只是一项用来装门面的装饰品而已,相当奢侈。
---------------------------------------------------------------
{23} 在西方学术界里,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可谓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的,现仅顺手列举一些文献为例,如Kuhn(1973)、Lakatos & Musgrave(1970)、Feyersbend(1988)、Latour与Woolgar(1979)、或Latour(1999)等等。以最简单的语言来描绘,基本上,所谓的实证主义者相信,在一套制式的科学研究工具与程序的庇荫下,我们可以根据一些「经验事实证据」把现象「如实地」予以披露出来。这是一种家Rorty(1990)所说的镜像哲学观,它促逼着社会学家认为,只要恰适地使用逻辑以及科学研究方法和程序,即可以经营出一套具普遍真理性质的知识。而这套知识乃运用来描绘(或谓如镜子般地「映出」)「社会实在」的真正面貌。在这样的认知模式的催动下,极端者甚至确认自己即是上帝的代言人,正宣扬着普遍真理呢!这样的思维和认知模式,Giddens(1974:1)管称呼它为一种模仿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而Cassirer(1923)则称之为一种「方法决定论」(methodological determinism)。若借用Wolf(2003)的说法,社会学家则是「没有历史的人」,他们不需要特别关照历史(与文化)的情境的。为了提供更为具体的例证,底下,特别以强调量化之实证社会学使用所谓的「测量」为例来做进一步的说明吧!姑且不论其可行与否的问题,对社会现象施予「测量」时,基本上,其性质与对自然现象进行测量时有着根本的不同。譬如,物里头的「力」(force, F一概念即是以「质量」(mass, M)与「加速度」(acceleration, A)两个可量化测量之概念的关系来定义(即F = M x A)。因此,「力」的概念是由「质量」与「加速度」二概念(也是测量)以特定的关系来衍生界定,其量度是具Coleman(1964:69)所说之「衍生测量」(derivedmeasurement)的性质。但是,在社会学里,绝大多数的概念本身都是属于「基础测量」(fundamentalmeasurement),其概念意涵乃与测量指标相互独立,因而并没有蕴涵任何预先已存的测量(Campbell,1928:14)。譬如,「现代性」一概念的实质内涵并不能直接从用以量度它的「现代性量表」来衍生定义。所谓的「现代性量表」只是做为一种指标,被认为具有足够的信度与效度来「反映」「现代性」的意涵。然而,事实上,这经常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在概念的意义指涉上,其间是有落差,甚至是完全脱离的。更具体来说,它所涉及的「代表定律」(representation theorem)与「独一定律」(uniqueness theorem)经常是不足,也是可疑的(参看Suppes & Zinnes 1963)。倘若我们再把测量尺度的问题考虑进来,那么,在对社会现象进行量化测量的处理过程中(如进行统计母数的工作),所可能牵涉的问题更是严重。譬如,Weitzenhoffer(1971;25)即指出,当Hull(1943)对学习过程进行数学化的运算时,就完全忽视了测量尺度所内涵的基本极限(譬如,某些尺度只能市正整数,不能是副整数,当然,更不能是分数或乃至无理数)。另外一个例子是,当心里学家企图以 I. Q. = k M(M为脑的质量)来表达智力与脑汁大小的关系,其所用公式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倘若测量脑的单位是公克(g)的话,I. Q. 是一个无单位、且无绝对零点的距间尺度(interval scale),因此,k的单位就必须是 1/g,而这是毫无意义的。再者,脑的测量尺度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有单位、且具有绝对零点的比率尺度(ratio scale),如何可以把它与I. Q. 这么一个无单位、且无绝对零点的距间尺度摆在同一个公式之? 尹茠竁F其关系,基本上是可疑,也是毫无意义,更是缺乏正当性的。
{24} 这样的说法是由维柯(Vico)之「新科学」观所衍生的一种思维方式。简单来说,根据Vico的意思,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要留给创造自然界的上帝,但是,对于凡人来说,人类的社会制度世界也可以有科学性的认识,因为这个世界是由我们凡人所创造的,所以,这种世界得以运行的原理或原因,必然可以在人类心灵的种种变化之中找到(Vico 1989:153-154[§331])。同时,这样的一种科学比物理学还完整,比数学还真实,因为正如「几何学在用它的要素构成一种量的世界,或思索那个量的世界时,它就是在为它自己创造出那个量的世界。我们的《新科学》(按:指这本讨论人类各民族文明与社会之制度的源起原则的书)也是如此(它替自己创造出民族世界),但是却比几何学更为真实,因为它涉及处理人类事务的各种制度,比起点、线、面和形体来更为真实」(Vico 1989:165[§349])。以这样的认识模式做基础,Vico认为,新科学是用再创建最初的科学方式来再创造新科学本身,而这最初的科学即占卜术,其它一切科学都是从占卜术衍生出来的(Vico 1989:173-174,191-192,368[§365,391,661])。因此,就其源起状态而言,来自自然状态的人(也就是凡人)都有一种听从自然理性支配和引导的「智慧」能力,而且,这个「智慧」能力本质上是一种具诗性的创造能力(Vico 1989:170-180)。于是,文明起源于「诗性」这样的说法,乃意味着有关人之存有状态的哲学人类学预设是任何有关人与社会之「科学」所不能不关注的基本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一种具感性、且有文化传统做后盾之具「神话」性质的信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做为社会学者,不能被实证主义企图以「去」历史–文化(即「去」时间与空间因素)的方式所蒙骗,自大地以为自己就是替上帝宣扬绝对「真理」的代理人,而忘了自己只是「自然」的仆人,应当以谦虚的态度对待自己所面对的世界。
{25}早在年美国社会学者 C. Wright Mills 已经认定了此一主流趋势、并提出严厉的批评 (同时参看Giddens 1974:1; Levine, Cartar & Gormon 1976; Halfpenny 1982; Ross 1991;叶启政 1982:132-133,1996)。这样的主流精神更是影响到美国社会学家营造「结构」一概念,而形塑了主导整个美国社会学之主流发展的所谓「结构社会学」的思维与认知模式(有关的讨论,参看叶启政 2000:150-163)。尽管有些理论倾向的学者认为实证主义已死,因此,一个社会学者宣称自己是「实证主义者」往往会受到同仁们嘲笑的(Bryant 1992;Gibbs 1994)。但是,Cartrell与Cartrell(2002)以美国两个最具权威性的期刊–美国社会学会之机关刊物《美国社会学评论》和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是美国最老的社会学期刊)的《美国社会学杂志》以及其它期刊为对象,抽取在1966-70年与 1986-90年期间所刊登的论文来分析其研究取径的属性。他们发现,宣称实证主义死亡的说法是被夸张了,因为,事实上,整体看,采取实证主义立场的研究,还是一直位居主流地位,而其中使用统计数字的量化研究更是高居六、七成,它并没有髓时间的迈进而显著减少。同时,即使是理论取向的研究,也多带有实证主义的基本信条的(如采用法则性的命题陈述方式、唯名性的定义或操作定义等等)。只是,Cartrell与Cartrell(2002:653)同意Cole(1992)的说法而一致地认为,如此之实证主义的彰显,其实只是以实证主义做为优势图像(dominant image)而已,社会学者实际操作的,则是更趋向于「实在主义–建构主义」(reqalism-constructionism)。易言之,社会学者体认到社会是被建构的,但是乃受对经验世界的观察所限制。在此,必须附带提到的是,Cartrell与Cartrell发现此种现象也在英国社会学界中看到,只是其风气不若美国那么炽热(按:在英国,持实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立场者似乎是较具显势)。至于台湾的情形,当然,我早已意识到,这些年来,有一些年轻一代的台湾社会学者(特别是留欧回国的)并非实证主义的信徒。他们采取着其它的「科学」研究进路来从事研究工作(包含持实在主义与建? c主义的立场),其中,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反实证」的。但是,在此,我所以还是拿实证主义做为主轴来进行讨论,乃基于一个理由:当前台湾社会学界中的「权力集团」乃为第三、四代所掌握,而这两个世代之社会学者的心态基本上是属于实证主义的。
{26} Cartrell & Cartrell(2002:644)为「实证主义」设下了七个「可操作化」的特点,它们分别是:(1)以法则方式的陈述来连结不同的概念、(2)对概念给予唯名定义、(3)运用操作定义或部份性的诠释、(4)从事假设的推衍以进行经验捡证、(5)以形式语言(逻辑或数学)来表达法则、(6)以经验的方式把变项关联在一齐、和(7)使用统计技术。根据这七个特性,我把在1994年至2003年这十年间发表在台湾社会学界里的两个最主要期刊–台湾社会学社的机关刊物《台湾社会学刊》(包含改名前的《中国社会学刊》以及由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共同发行的《台湾社会学》(包含两个单位合并其刊物前原有的《台湾社会学研究》和《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刊》)中所有的论文(包含〈研究论文〉、〈研究纪要〉与〈研究议题讨论〉)进行「实征」的分析。即使我采取最宽松的标准来认定「非实证」的论文(亦即以最严格的判定标准来界定「实证」的论文),结果显示:在总共166篇论文当中,使用统计数据的有97篇(占58.4%),未使用统计数据、但性质合乎上述标准中至少四项者有25篇(占15.1%),而属于非「实证」的则有44篇(占26.5%)。换言之,前二者加一起,则高达73.5%。假如采取更严格的标准来界定所谓非「实证」的论文(譬如,把其中有些对某个特殊领域之实证经验研究的文章做综合性的介绍与评论、或进行的是总体性的论述、但风格却是不折不扣的「实证」的文章都包含进来),那么,这个数字是会更高的。对我来说,以简单的语言来描绘,这样一个主流意识基本上即是企图把整个西方社会学思维背后所深藏那具特定时空意涵的哲学人类学预设完全予以架空,而以为一切可以如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界时一般来建构社会学的「科学」知识。显然的,如此假设我们可以在完全「清白无暇」的状况下来进行「客观」的理性讨论,应当是大大可以质疑的。
{27} 譬如,总是以Bhaskar(1986)所说之「实际可能性」(real possibility)的实际效果立场来界定「经验」一概念的内涵,因而,不但以为所谓的「经验」必得是以具体可检证之表征化的(量化或质化)数据来左证才算数,而且,也需得是从行为的实际表征结果来「实征」,才是有效的。基本上,他们既不接受Bhaskar所说之「认识可能性」(epistemic possibility)一概念所内涵具演绎性质之「因果力」(causal power)的思维模式是具有正当的,同时,也无法接受「一个研究者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直觉)获得的经验足以做为论述之依据」这样的认识模式。
{28} 参看叶启政(1982)。同时,蔡锦昌(1984,1989,1998,2003)以相当独特而迂回的方式讨论社会学做为一个学门的一些问题,颇有启发性,也有独到之见地,值得参考。
{29} 参看Taussig(1993)传神的论述。
{30}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是,在评审别人的论著时,总是以自己所熟悉的文献来当成评定良寙的标准。譬如,当人家研究的是有关Luhmann论述信赖(trust)的问题时,总是罔顾是否与Luhmann的研究旨趣、研究策略与议题取向有关,而一眛要求人家一定要引述自己所熟悉的某些美国学者的论述,才算有了够水平的「文献回顾」。更严重的是,总是以自己有限的特定知识范畴、尤其是特定的立论立场来月旦别人的论作,而罔顾别人所秉持的论述预设立场与思维进路到底是甚么的问题。换言之,不懂得评论别人论作时,可以(也应当)先以拟情的态度站在别人的立场来看问题,而只知一眛地以自己的特定立场(甚至是不相干的)来做为评论的依据。这么一来,当然,别人的作品都会是一无是处的,而以超高标准来「砍杀」别人的研究成果,于是乎成为审查别人之论文时的「常模」。无怪乎,纵然我们有了上百个以上的专业社会学者孜孜地从事研究工作,但是,台湾社会学社的机关刊物《台湾社会学刊? n却是一直处于稿源不足的状态。虽说情形所以会是如此的可能促因绝不会是单一的,但是,评审者以十足之自我中心、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来对待别人的作品,导使退稿率高,也促使许多人裹足不前,不愿投稿来接受不必要的「凌辱」,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可能、且是重要的因素。说来,这种超高标准的评审,往往只是当事者自己认定的,落在别人的眼中,那可就不一定了。同时,根据个人的观察,我感觉到,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社会学者(其中又以留洋归国的学人为明显)都显得相当有自信,而且眼界高。固然,因自信而眼界高是好,同时,在对别人的论作进行审查或评论时,能够卯足了劲地竭己所能来完成,这样尽责而用心的态度,也是值得激赏。但是,一旦求好心切而执着过多,则往往流于过于严苛,甚至迹近吹毛求疵地百般挑剔,企图在鸡蛋里挑骨头,因此而一眛否定别人的表现,那就令人不免要担心了,因为一眛否定别人的表现只会让自己更自以为是,而锁闭在自己锁经营起来的小王国。况且,这更是会导致一个人不知从别人的长处之中学习到足以令自己成长的经验。凡此种种作为,对刚起步的台湾社会学界来说,都是相当不健康,对未来的发展,更是有着莫大的妨碍。尤其,当一个社会学者一直以个己所习得的有限知识当成是知识的全部之时,他的认真态度与严格设准,在偏狭而无知的傲慢心态驱使下,无疑地将成为一种充满着暴虐性的霸权力量。结果是带来更多彼此相互砍杀与凌虐的情形。
{31} 吊诡的是,这样一个批评施及于本文,可以说也是适用的,不是吗?
{32} 参看注30。
{33} 依我个人的观察,就台湾社会学界的整体而言,这样的权力集团并没有嚣张地以明显的派阀呈现出来,而有着相互斗争的情形。情形毋宁地只是在某些特定场合里不自主地表露出来而已。诸如,一个单位聘任新进人员时经常有所「系统性」的多数偏好(包含正面与负面)、或审查论文时有特定的执着、或考虑同仁之升等时有定型的裁决标准等等。其实,这些现象在学术界中发生,一直就极其常见。
{34} 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参看叶启政(2001)。
{35} 苏国贤与蔡明璋(2003)亦提出类似的发现。
{36} 乃美国社会学者Crane(1972)所提出来的用语。
{37} 同时参看苏国贤与蔡明璋(2003:17-19)。
{38} 我个人最常从留洋之同仁口中听见的是,诸如本土的博士在研究方法上的训练太差、对最新的文献不钩熟悉、写作不够严谨、不够用功等等。总体的情形是否可以如此论断,我个人是相当保留的。
{39} 有关作者对此一议题的讨论,参看叶启政(2001)。 书目
文崇一,1975,〈万华地区的群体与权力结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39:19-56。
文崇一,1976,〈岩村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42:41-47。
文崇一,1991,〈的社会学:国际化或国家化〉。《中国社会学刊》15:1-28 。
文崇一、许嘉明、瞿海源与黄顺二,1972,《台北关渡小区调查研究报告》。台北:中华民国小区研究训练中心。
文崇一、许嘉明、瞿海源与黄顺二,1975,《西河的社会变迁》。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李亦园、杨国枢编,1972,《中国人的性格》。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金耀基,1966a,《从传统到》。台北:商务。
金耀基,1966b,《现代人的梦魇》。台北:商务。
林瑞穗,1996,〈从机构和学生两方面省视国内社会学的发展前景〉。《社会学刊》19:1-7。
徐正光,1976,〈岩村的生态与变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42:1-40。
徐正光,1977,〈工厂工人的工作满足及其相关因素之探讨〉。《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43:23-64。
徐正光,1991,〈一个研究典范的形成与变迁:陈绍馨「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台湾」一文的重探〉。《中国社会学刊》15:29-40。
章英华,1996,〈人文处社会学门规划报告〉。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专题研究成果报告。
章英华,2000,〈学术出版、评审与学术发展:一个社会学家的参与观察〉。《台湾社会学刊》23:1-23。
章英华等,1999,〈社会学专门领域成就与评估〉。全国人文社会会议会前会社会学门分组讨论附录。
章英华、吕宝静与黄毅志,1999,〈国内社会学、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专业期刊排序〉。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专题研究成果报告。
章英华、黄毅志与吕宝静,2000,〈台湾地区社会学、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期刊排序〉。《台湾社会学刊》23:103-139。
许嘉猷,1996,〈台湾的阶级研究〉。页93-102,收录于萧新煌与章英华编,《两岸三地社会学的发展与交流》。台北:台湾社会学社。
陈杏枝,1999,〈台湾宗教社会学研究之回顾〉。《台湾社会学刊》22:173-209。
黄金麟与谢冷雪,1983,〈「社会学在中国:问题与展望」研讨会记录〉。《中国社会学刊》7:293-321。
黄顺二,1975,〈万华地区的都市发展〉。《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39:1-18。
张晓春,1972,〈「二十年来我国行为科学的发展与展望讨论会」〉(发言记录)。
《思与言》10(4):3-14。
杨懋春,1976,〈社会学在台湾地区的发展〉。《中国社会学刊》3:1-48。
杨懋春,1980,〈记台大社会学之创立〉。《台湾大学社会学刊》14:4-10。
叶秀珍与陈宽政,1998,〈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学术研究的现况与发展〉。《台湾社会学刊》21:21-57。
叶启政,1982,〈从中国社会学既有性格论研究中国话的方向与问题〉。页115-152,收录于杨国枢、文崇一编,《社会与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叶启政,1988,〈对四十年来台湾地区社会学发展的反省〉。页193-235,收录于中国编辑委员会,《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发展》。台北:联经。
叶启政,1995,〈社会学门的现况与发展〉。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 会项目计划报告。
叶启政,1996,〈台湾地区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及其潜在问题〉。页17-38,收录于萧新煌与章英华编,《两岸三地社会学的发展与交流》。台北:台湾社会学社。
叶启政,2001,〈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搓揉游戏–论学术研究的「本土化」〉。《社会理论学报》4(1):43-71。
蔡锦昌,1984,〈谈台湾社会学理论教学的一些问题〉。《东吴大学社会学报8:181-192。
蔡锦昌,1989,〈社会学只是个名〉。页191-210,《从中国古代思考方式论较荀子思想之本色》。台北:唐山。
蔡锦昌,1998,〈社会学所学为何?〉。《东吴社会学报》7:271-312。
蔡锦昌,2003,〈还归社会学理论的本来面目〉。《东吴社会学报》14:1-31。
蔡勇美与萧新煌编,1986,《社会学中国化》。台北:巨流。
龙冠海,1963,〈社会学在中国的地位与职务〉。《台湾大学社会学刊》1:1-23。
萧新煌,1981,〈台湾社会问题研究的回顾和反省〉。《中国论坛》129:51- 55。
萧新煌,1982,〈社会学中国化的结构问题:世界体系中的范型分工初探〉。页69-90,收录于杨国枢、文崇一编,《社会与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萧新煌,1985,〈再论社会学中国化的结构问题:台湾的社会学家如是说〉。页287-328,收录于李亦园、杨国枢、文崇一等编,《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台北:桂冠。
萧新煌,1986,〈社会学在台湾:从「传统」的失落到「中国化」的展望〉。页271-310,收录于蔡勇美与萧新煌编,《社会学中国化》。台北:巨流。
萧新煌,1987,〈三十年来台湾的社会学:与结构的探讨〉。页327-390,收录于
赖泽涵编,《三十年来我国人文及社会科学之回顾与展望》。台北:东大。
萧新煌,1995,〈转型的台湾社会学与转型的台湾社会:个人的几点观察〉。《中国社会学刊》18:1-15。
萧新煌,1996,〈转型的台湾社会学与转型的台湾社会:个人的几点观察〉。页3-16,收录于萧新煌与章英华编,《两岸三地社会学的发展与交流》。台北:台湾社会学社。
萧新煌与张苙云,1982,〈对国内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初步反省:现实建构,理论和研究〉。页267-295,收录于瞿海源与萧新煌编,《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萧新煌与章英华编,1996,《两岸三地社会学的发展与交流》。台北:台湾社会学社。
瞿海源,1975,〈万华地区社会态度的变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39:57-84。
瞿海源,1976,〈岩村居民的社会态度〉。《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42:97-118。
瞿海源,1982,〈问卷调查法在国内运用之检讨〉。页209-228,收录于杨国枢、文崇一编,《社会与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瞿海源,1986,〈我国社会学现况分析〉。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专题研究成果报告。
瞿海源,1996,〈台湾社会阶层研究叙介〉。页70-85,收录于萧新煌与章英华编,《两岸三地社会学的发展与交流》。台北:台湾社会学社。
瞿海源,1998,〈社会学课程内容与台湾社会研究〉。《台湾社会学刊》21:1- 20。
苏国贤与蔡明璋,2003,〈台湾社会学者的隐形学群与知识生产〉。宣读于「台湾社会学年会」,台湾社会学会主办,2003年11月30日。
顾忠华与张维安,1991,〈在台湾的中国社会学社〉。《中国社会学刊》15:140-169。
Schumacher, E. F. 着、李华夏译,2000,《小即是美》。台北:立绪。
Vico, Giambattista着、朱光潜译,1989,《新科学》(全两册)。北京:商务。
Wolf, Eric R.着、贾士蘅译,2003,《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台北:麦田。
Bhaskar, Roy, 1986, Scientific Real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 London : Verso.
Bryant, Joseph, 1992, "Positivism Redivivus? A Critique of Recent Uncritical Proposals forReforming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Related Foibles)."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17(91):29-53.
Campbell, Norman R., 1928,An Account of the Principles of Measurements and Calculations. London : Longmans, Green.
Cartrell, C. David & John W. Cartrell, 2002, "Positivism in Sociological Research : USA and UK(1966-1990)."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3(4):839-657.
Cassirer, Ernst, 1923,Substnce and Function and Einsein’s Theory of Relativity.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Cole, Steven, 1992, Making Science.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leman, James S., 1964,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Crane, Dinna, 1972, Invisible College. New York : The Free Press
Feyerabend, Paul, 1988, Against Metho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 Verso.
Gibbs, Jack, 1972, Sociological Theory Construction. Hinsdale, Ill. : Dryden Press.
Giddens, Anthony, 1974, Positivism and Sociology. London : Heinemann.
Halfpenny, Peter, 1982, Positivism and Sociology : Explaining Social Lif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Hull, Carl L., 1943, Principles of Behavior. New York : Appleton-Century Co..
Kuhn, Thomas, 1973,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4th impression)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katos, Imre & Alan Musgrave(eds.), 1970,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runo, 1999, Pandora’s Hope.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runo & Steve Woolgar, 1979, Laboratory Life :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London : Sage.
Leivine, Donald N., E. B. Cartar & E. M. Gormon, 1976, "Simmel’s Influence on American Sociology : 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813-845.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Press.
Rorty, Richard, 1990,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Ross, Dorothy, 1991,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Schjelderup-Ebbe, T., 1935, "Social Behavior of Birds," in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edited by C. Murchison. Worcester, Mass. : Clark University Press.
Simmel, Georg, 1950,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translated,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urt H. Wolff. New York : The Free Press.
Suppes, Patrick & Joseph L. Zinnes, 1963, "Basic Measurement Theory," in Handbook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Vol. I. edited by R. D. Luce, R. R. Bush and E. Galanter.New York : John Wiley & Sons.
Taussig, Michael, 1993, Mimesis and Alterity. London : Routledge.
Weitzenhoffer, Andre M., 1971, "Mathematical Structures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Pp.15-28, in Contemporary Problems in Statistics. edited by Bernhardt Lieberma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上一篇:社会保障私有化及其理论基础
下一篇:马林诺斯基与中国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