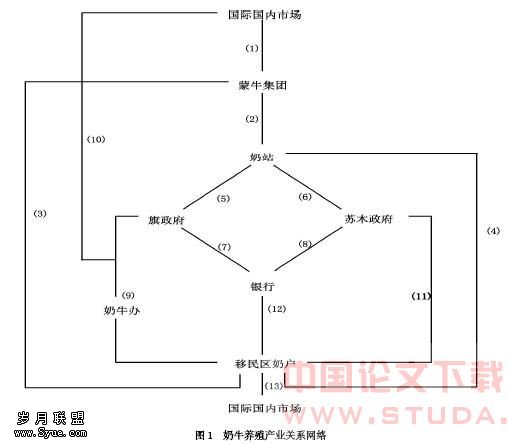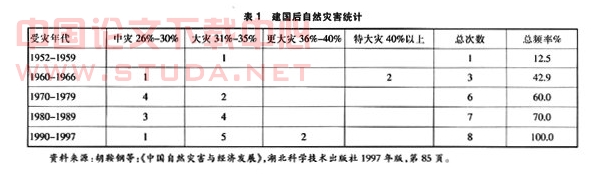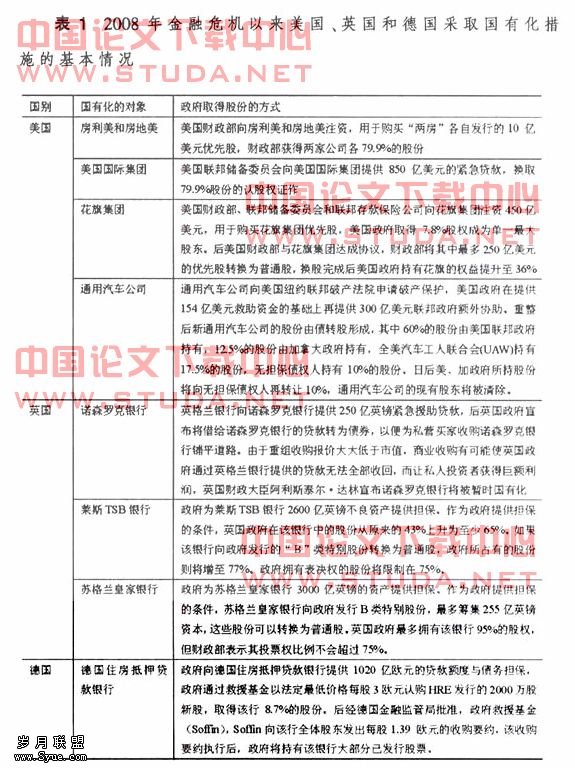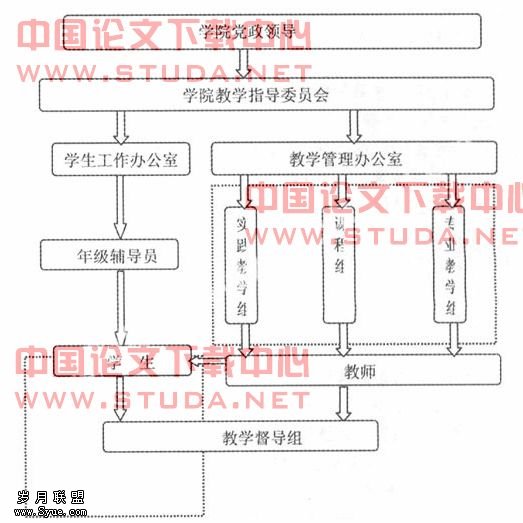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两种路径及其科学整合
[摘要]100多年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们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着“方向性”和“设定性”两种不同的路径。如何处理两种路径的关系是影响社会主义运动成功与曲折交替变化的重要因素。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就是在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方位的基础上,通过对两种路径进行科学整合即按照“方向性”路径的要求赋予“设定性”路径以新的内涵而形成和起来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两种路径;科学整合;中国特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化建设通过改革开放开辟的新道路而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仅使中国人民逐步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100多年来,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们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或趋向;如何处理两种路径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社会主义运动成功与曲折交替变化的重要因素;而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就是在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科学把握中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基础上,通过对两种路径进行科学整合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本文简略梳理两种路径、两种趋向的理论轮廓、发展历程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其进行科学整合后的逻辑框架,以期从一个角度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认识。
1.“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本人那里也许不是个问题。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后继者而言,这却是一个较难把握的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理论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论述和回答,存在着两条不同的逻辑路径。第一条可称之为“方向性”路径。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缜密、深刻研究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提出:(1)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1]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2)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走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2](3)要将社会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就是说要正确理解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不能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而要在实践过程中推进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4],而不能“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不能从头脑中构想出改造社会的方案;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绝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5]。这三个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基本构想,为后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指明了正确方向”[6]。归结起来说,所谓“方向性”路径,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径。
第二条可称之为“设定性”路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剖析旧社会的同时,从“特征”的角度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后来由列宁命名的社会主义社会给出了大致的设定:(1)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上,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7],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2)在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前提下,个人劳动已经直接地作为社会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商品和货币退出经济生活,因此,在社会的经济体制上,社会主义社会将由一个社会中心通过计划来实现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将成为“首要的经济”[8];“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9](3)在分配原则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在对其总产品进行必要的扣除以后,个人消费品按每个人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进行分配。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理论设想,在逻辑上是一个相互规定、相互证明、互为条件的“三位一体”的整体,是一个严密的体系;如果变更其中的任何一项,必然要求和导致其他两个方面随之变更。[10]归结起来说,所谓“设定性”路径,就是按照某种比较理想化的、纯粹的标准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模式的路径。
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两条不同的逻辑路径,给后继者指明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方向,但如果搞得不好,教条式地理解“设定性”路径,也容易造成实践中的偏差。
2.20世纪初,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事实上也存在着前后不同的两种路径。一条可称之为“直接过渡”路径。这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特征性设想以“战时共产主义”的名义进行了大胆的试验。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战时共产主义于1919年初步形成一种特殊的经济体制。这套体制在当时既是为了应付对敌斗争的特殊需要,也是俄共(布)中央组织苏维埃俄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试验,是对马恩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设定性”路径在制度上的“直接复制”。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俄共(布)超越阶段、急于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正如列宁自己后来所说的:“在估计可能发展的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11]所谓“直接过渡”,就是“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但“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2],试验的结果无疑是失败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13]于是列宁转向第二条可称之为“迂回过渡”路径的“新经济政策”路径。
早在1918年,列宁就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个著名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等等=社会主义”[14]。到1920年底实施新经济政策前夕,列宁进一步把建设社会主义与发展大联系起来,以更加简明的语言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15]的公式。列宁的公式包含三大要义:一是强调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国家政权;二是强调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成果;三是强调发展高度的社会生产力。这三大要义在后来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都有进一步的丰富和展开。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和校正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必须根据经验而不是根据书本来讨论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而困难的历史过程,必须及时地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和平的经济文化组织工作上来;必须采取迂回过渡的办法,利用市场、商品和货币关系,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迂回过渡”路径实际上又回到了马恩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性”路径,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于生产力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的重要探索。遗憾的是,随着列宁的过早去世,后一条路径的探索未能继续深入下去。
3.斯大林当政后,在探索、确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相应地也存在着前后不同的两条路径。从1923年10月到1927年12月,斯大林坚持了列宁的迂回过渡路径。其间,以斯大林、布哈林为代表的党中央,先后展开了对托洛茨基反对派和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联合”反对派的党内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建设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斯大林、布哈林多次对反对派的种种错误理论观点给予了深刻而有说服力的批判,捍卫并进一步发挥了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胜利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在坚持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上,布哈林作出了重要贡献。针对反对派认为的新经济政策是“权宜之计”、就其主流来说是个退步、党中央有“富农倾向”等错误观点,布哈林指出,“最能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制度就是最好的经济制度。”[16]“我们在新经济政策中第一次找到了小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事业之间的正确结合。新经济政策不是对无产阶级路线的背叛,而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17]他还特别强调利用市场关系的意义和作用:“过去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一举消灭市场关系。而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18]他后来还强调,“市场关系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这是确定新经济政策实质的最重要标准。”[19]联共(布)中央先后击败“左”倾反对派,使新经济政策得以继续施行,也使从1921年到1927年底这段时期的经济建设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1928年1月至1929年4月,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以斯大林为一方、以布哈林为另一方展开了新的党内斗争。双方以新经济政策的存续为中心,围绕粮食收购、改造小农经济、国家工业化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在这场党内斗争中,斯大林对马恩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两条路径采取了断然的“舍一取一”的选择。斗争的结果是:主张新经济政策是唯一正确政策的布哈林的生命被终结;列宁的迂回过渡路径被斯大林完全丢弃。此后,斯大林全面继承了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路径,并在推进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建设和强制性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使其理论化、制度化了,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或称“苏联模式”)。在所有制方面,实行单一公有制,并认为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故而不断追求将集体所有制升格为全民所有制。在社会的经济体制方面,将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将商品、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胎记”,故而采取极为僵硬的产品交换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分配制度方面,由于无法做到等量劳动取得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便实行以货币为形式、以高度集中统一的等级工资制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按劳分配”。斯大林认为,这种“单一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统一的按劳分配”模式,“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公式”[20]。斯大林还以这个公式为标准,于1936年底宣布苏联一国建成了社会主义。今天看来,以“政府垄断制”为核心的“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一方面说明斯大林脱离实际国情、教条式地理解和照搬了经典作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设定性”路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后来又为俄国民粹主义所强化了的重视军事工业和反商品、反市场关系、反民主的传统。
作为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模式不能不被人们认为是“正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尤其在前苏联以“国际共运中心”名义强力推行数十年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经济制度体系,一度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后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圭臬和样板,并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左”的观念:突破这套体系中的任何一项,就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和否定,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或异端。“斯大林模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原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在谈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长期被困扰的问题时,极其痛苦地说:“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21]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同样存在着两条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这两条不同的路径分别表现为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指导思想上的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另一个是错误的、混乱的、空想的趋向。[22]
所谓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是指从1956年党的八大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里,党在探索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所谓错误的、混乱的、空想的趋向,主要是指从1957年开始,党在探索中逐步形成并在1960年代中期得到系统化、理论化的错误观点和方针政策。
深入研究上述两种趋向,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探索中形成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反映了党遵循了经典作家的“方向性”路径,或者说是遵循经典作家的“方向性”路径进行探索而取得的积极成果。例如,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命题和任务;批评了企图不经过发展经济而在条件不成熟时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跳入共产主义的空想,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论点,[23]提出我国还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以及分“几步走”进行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思想;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首创了包括基本矛盾、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在内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思想以及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依据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提出了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提出了通过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提出了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一系列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等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经典作家关于将社会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将社会主义置于现实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社会要不断改革的“方向性”路径,都是遵循“方向性”路径进行艰辛探索而取得的积极成果。
第三,总体上说,在毛泽东的探索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们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设定性”路径的影响,超过并最终压倒了“方向性”路径的影响。受当时国际、国内局势的影响和经验不足等历史条件的限制,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基本上未能摆脱苏联经验和斯大林模式的窠臼,未能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归根结底未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正如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指出的:“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24]“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反映了我们党和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一样,没有把苏联模式和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区分开来,还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苏联模式;反映了此时的探索重心是放在“建设道路”即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上,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这是改革未能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因此,探索中取得的许多成果,有的还处在萌芽状态,有的还不成熟、不彻底,有的甚至前后矛盾、正确的与错误的趋向相互渗透和交织,有的还没有形成全党的共识,有的即使写进了党的文件也没有最终贯彻到底。因此,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趋向本身没有力量纠正、阻挡错误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到后来反而被错误趋向逐渐压倒、淹没、否定或取代。“文革”的爆发和延续,在事实上否定了发展生产力是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的思想,否定了经过艰辛探索而取得的改革和建设等方面的积极成果。而建国初期基本仿效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包括“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结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则得到进一步强化。由此看来,如何正确处理“两种路径”的关系,是影响社会主义运动成功与曲折交替变化的重要因素。
第四,对于长期处于革命和战争环境中的党和毛泽东而言,在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探索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自然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事业。因此,对于毛泽东这位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中国化、致力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先驱,尽管我们不必为尊者讳,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苛求。相反,毛泽东曾经向视苏联模式为正统、怀疑或“背离”苏联模式即被斥之为修正主义的国际教条主义宣战的创新精神,必将为后人所景仰。而且,无论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还是错误的、混乱的、空想的趋向,无论是正面经验还是反面教训,都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取得和发生的,都是我们进一步探索的宝贵财富。
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并立足于中国国情,同时深刻分析世界各个领域的新变化,通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100多年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两条路径及其经验教训进行科学整合,终于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科学整合”的路径及其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第一,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大历史主题和历史任务。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在改革之初即给全党提出了一个前置性的核心命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作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创改革开放新道路的思想先导;又作为改革实践要探索解决的根本任务。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5];“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26]。他还尖锐地指出,“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27]痛定思痛,“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所谓旧的那一套,就是“过去我们搬用”的“别国的模式”[28]。今天看来,邓小平讲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其全面和革命的意义就在于:要通过改革突破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按照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来创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科学模式,进而开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这表明,我们党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又回到了马恩的“方向性”路径,摒弃了将苏联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唯一模式的认识和做法。
第二,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确地解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对本国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判断正确与否,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事业。由于我国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是在一个未经资本统治充分展开的东方大国里建立起来的,与经典作家设想的全部生产资料实行社会占有因而消灭了阶级、阶级差别、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以及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之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和必须实行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制度体系——属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因此,探索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如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所指出的“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9]一样:首要的和基础性的任务是认清当代中国的国情,即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再认识。邓小平指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前苏联等国之所以既唱了凯歌,又唱了挽歌,根本原因就在于超越阶段“犯了性急的错误”,“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30]因此,“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31]他强调:中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2]党的十三大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据此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作为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立论的基础和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革命性意义在于:(1)科学地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问题,使得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终于从历史发展的阶段上彻底区分开来。(2)科学地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问题,初级阶段理论要求我们非但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还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能是、也必然是按照中国的国情来建设的、切合中国实际的、即置于现实基础之上的、“用脚立地”的社会主义。(3)科学地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用问题,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用来解决我国发展问题、实现强国富民和民族振兴的社会主义,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真正需要的社会主义。(4)归根到底,它提供了既反左又防右、特别是解决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经常“超越阶段”这个老大难问题的理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第三,耦合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设定性”和“方向性”两条路径,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表明: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短暂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它属于共产主义体系,但还远未进入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它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共产”理论在这里是难以完全照搬的。相反,它还面临着自身历史积淀的挑战,还面临着其它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生产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我们只能、也必须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因素。与此同时,“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既要与资本主义交往,充分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竞争比较中赢得优势;又要审慎面对外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张的挑战,避免重新滑向资本主义的“用人头当酒杯”的过程。[33]因此,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之下、在这样一个历史方位之中,就理论体系来说,一方面,还不可能从实践中抽象出一个纯粹、纯洁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需要在一定限度内接受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必需要创造(抽象)出、也只能创造(抽象)出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理论体系。[34]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耦合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设定性”和“方向性”两条路径——以“方向性”路径为指导,探索“设定性”的现实形式;按照“方向性”路径的要求赋予“设定性”路径以新的内涵——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创造性实践中逐步创立和完善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实现了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整体重塑和整体创新。这条新型的、中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在经济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在所有制形式上,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为发展生产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利用非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即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下长期存在。这两条同样是缺一不可、毫不动摇。在经济体制上,既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力,又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既反对借市场化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也反对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之名行维护社会主义传统模式之实。在分配制度上,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又坚持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以促进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的积极性、发展本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在对外开放方面,既实行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历史”,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又在对外开放中坚持以我为主,确保不被“资本主义历史体系”所吞没。在发展观上,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发展视为首要任务、根本任务,又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路子,努力体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在发生变化,“设定性”路径被赋予了切合实际的新的内涵。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即将经典作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性”路径和“设定性”路径进行了科学的整合。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关键所在。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人民出版社,1995(2):101—10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人民出版社,1965(19):451.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人民出版社,1995(4):681,73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人民出版社,1971(37):443.
[6]刘云山.毫不动摇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体会[J].求是,2008(2).
[7][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人民出版社,1972(3):10,44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人民出版社,1979(46上):120.
[10]朱诗柱.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观是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J].扬大税务学院学报,2004(4).
[11][12]列宁全集[C].人民出版社,1987(42):219,176.
[13]列宁全集[C].人民出版社,1987(43):367.
[14]列宁全集[C].人民出版社,1985(34):520.
[15]列宁全集[C].人民出版社,1986(40):156.
[16][17][18]布哈林文选[C].人民出版社,1981(上):358,442,441.
[19]布哈林文选[C].人民出版社,1983(下):392.
[20]斯大林全集[C].人民出版社,1955(13):104.
[21]日夫科夫回忆录[C].吴锡俊、王金柏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28—229.
[22]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418.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C].291.
[24]毛泽东文集[C].人民出版社,1999(7):369—370.
[25][26][27][30][32]邓小平文选[C].人民出版社,1993(3):63,213,267,140,252.
[28][31]邓小平文选[C].人民出版社,1994(2):312,312.
[29]毛泽东选集[C].人民出版社,1991(2):633.
[33]卢周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4).
[34]陈文通.如何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