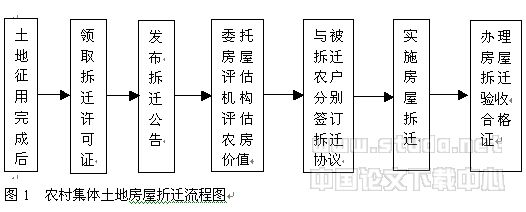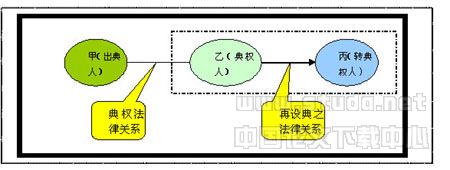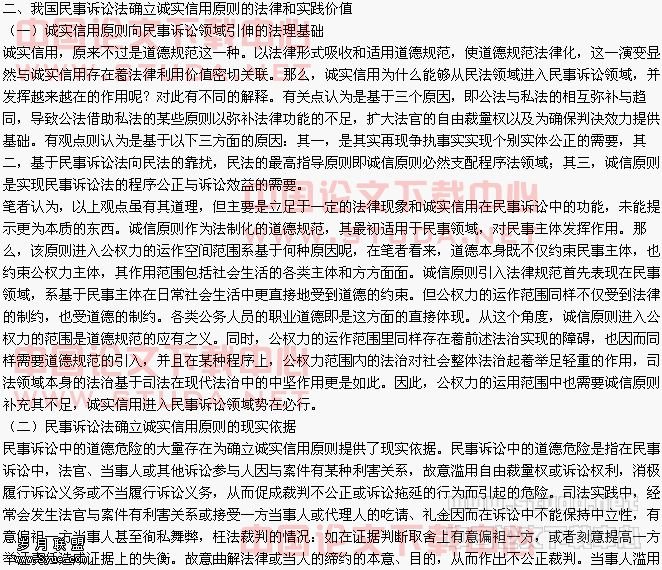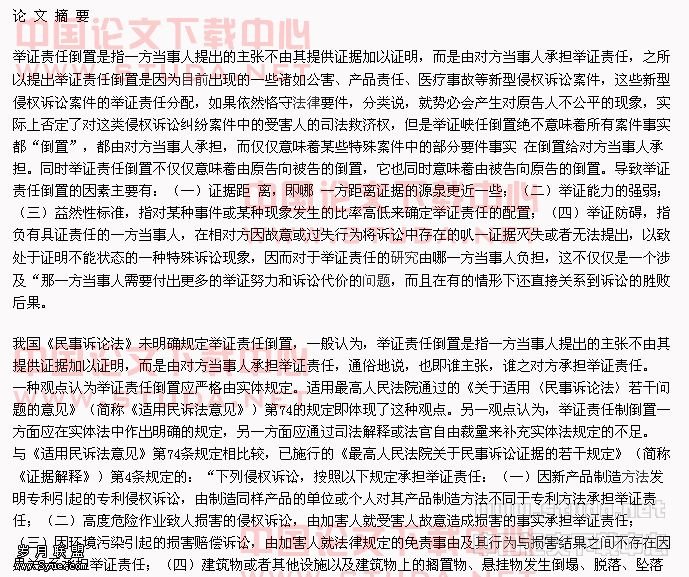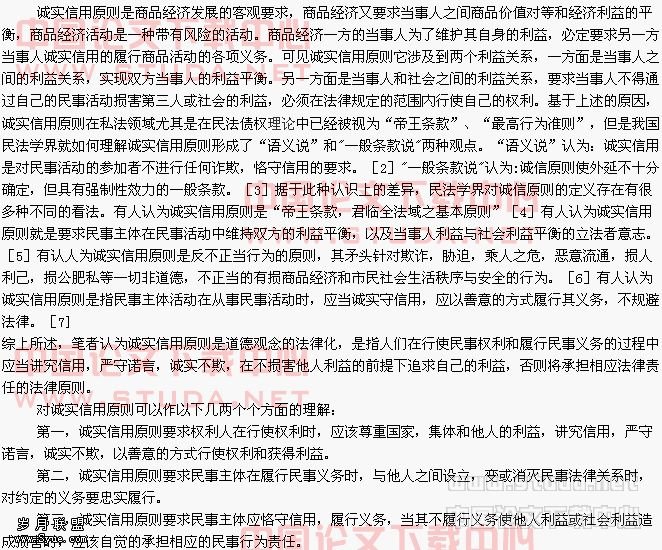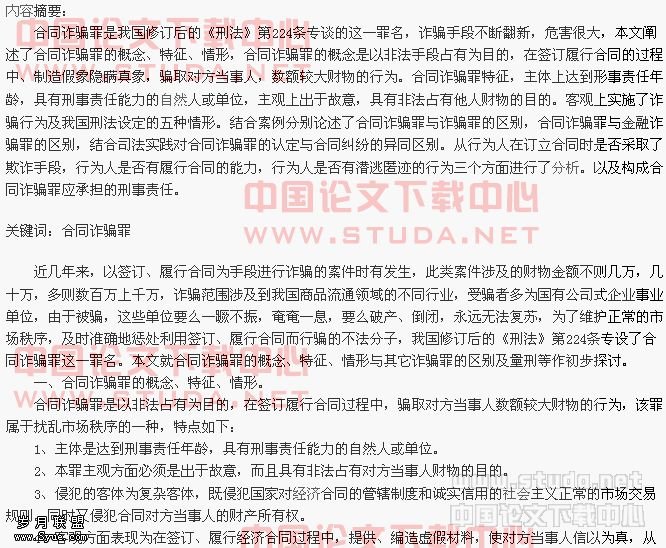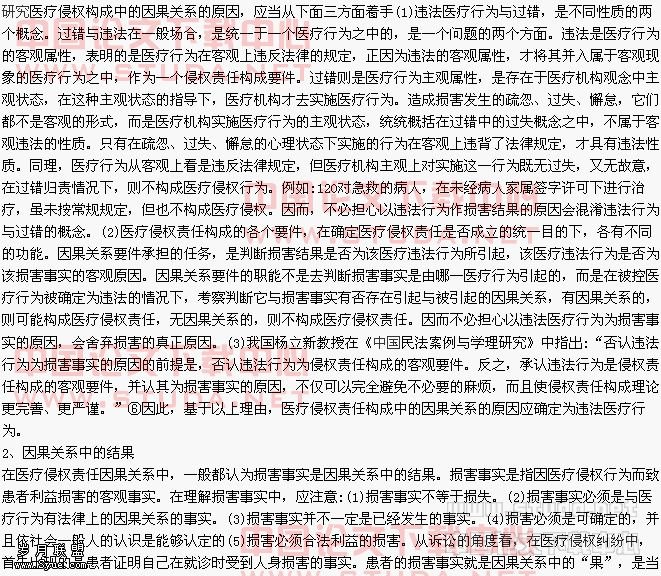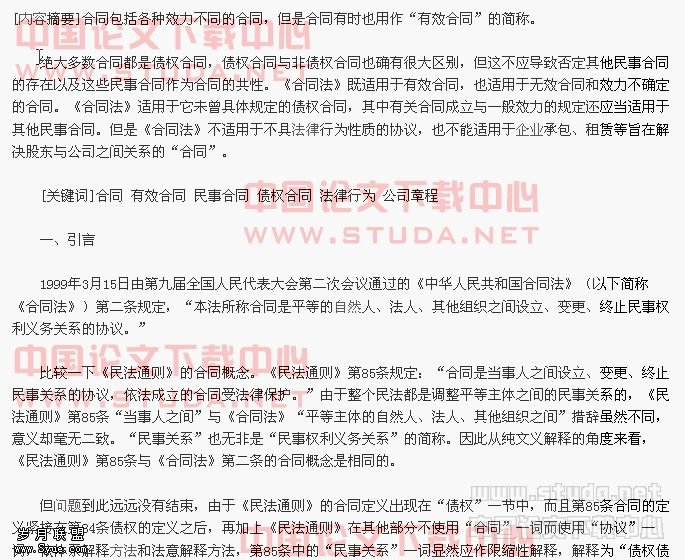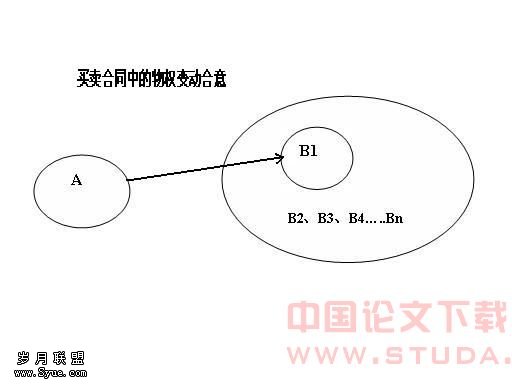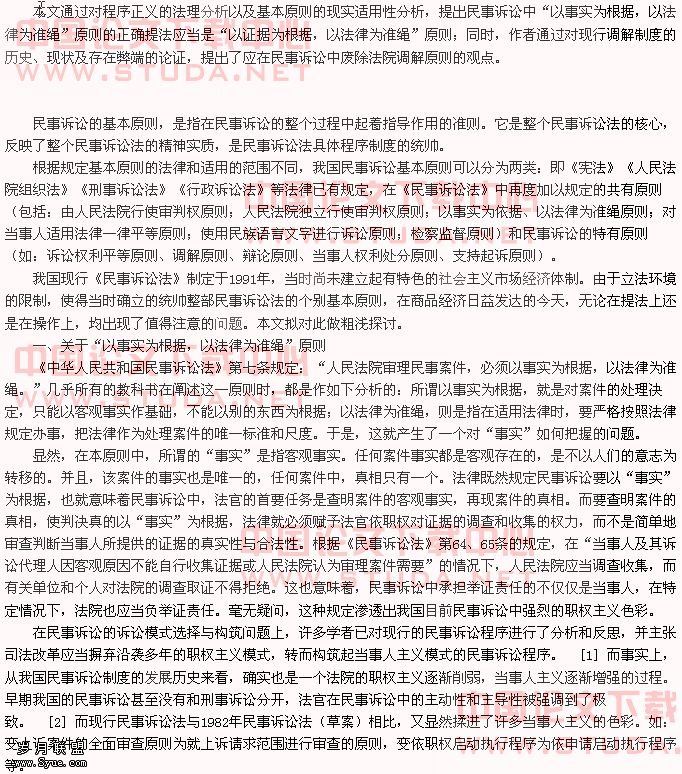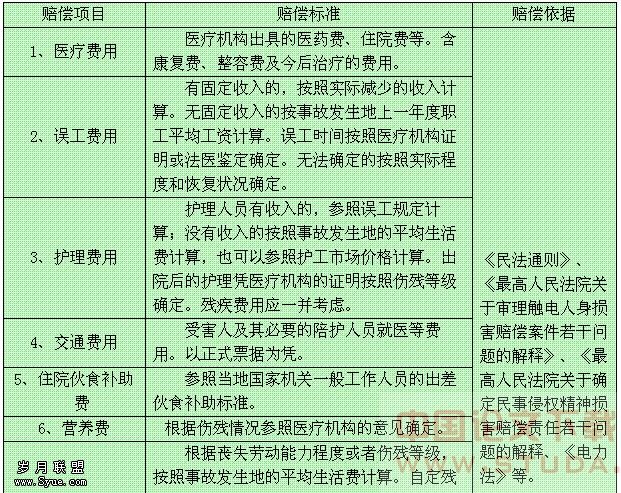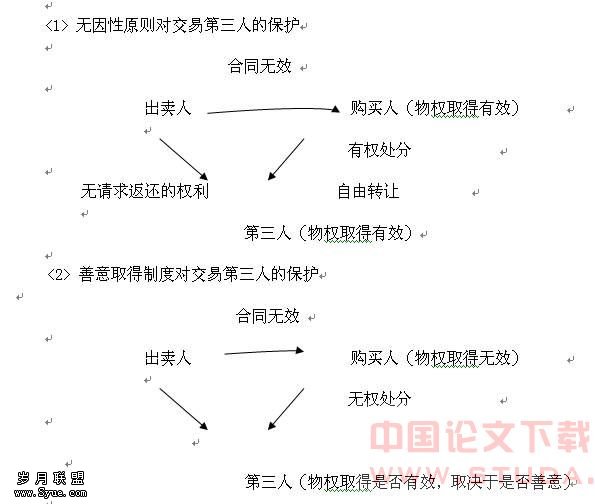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寻求平衡
——以民事诉讼为例
[内容摘要]:对诉讼中追求的真实,有客观真实与真实两种主张。虽然客观真实说存在缺陷,但其作为诉讼的基本理念仍是不可动摇的,我们尽可能地追求客观真实,但所能达到的只能是法律真实。在这个过程中,保持法官的中立和建立正当的程序,是实现两者平衡的路径之一。
[关键词]:客观真实 法律真实 中立 正当程序
诉讼制度被发明之后,其所追求的价值之一——发现真实便成为人们长久讨论的话题。作为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关键环节,它对于诉讼的最终结果和双方当事人各自的利益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而,无论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司法实务上,都是一个核心问题。从更广阔的范围上讲,它具有超越法律体系和法文化的普遍意义,是各国诉讼制度所共同追求的目标。具体到我国的民事诉讼中,我们所追求的究竟是何种真实,客观真实抑或法律真实,法官采取何种方式才能达到追求的目标并获得当事人的认同,这不仅关乎整个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而且涉及到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问题,颇有探讨的价值。笔者在此不避浅陋,以民事诉讼为例对上述问题作一粗浅探讨,试图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中寻求到平衡。
一、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界说
对于诉讼中所追求的真实,向来有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两种主张。客观真实说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原苏联的学者在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民事诉讼中形式真实学说的基础上,作为形式真实的对立物和替代物提出的。后来被原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反映社会主义民事诉讼制度特征的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原则。① 它要求法院采取所能做到的一切方法来确定在客观现实上曾经发生过的案件实际情况,要求法院的判决是以当事人间真正的相互关系为基础而确立。受此影响,我国的民事诉讼理论亦长期认为诉讼中的证明任务是确定案件的客观真实,裁判中认定的事实应当与实际发生的客观事实相吻合。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高度职权化的民事审判方式的重要特征之一即为强调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功能,力图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
然而,客观真实说作为一种理想的价值而存在,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这种主张过于浪漫,脱离了诉讼的实际。相信存在一个完整的客观真实,通过人们的认识活动可以发现这一真实,从而求得对案件的公正判决,被有关法学家称为“事实的乌托邦”,区分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的差异,已逐渐成为共识。②
法律真实说认为,裁判中认定的事实是法律上视为真实的事实,是法官依照诉讼程序,运用证据规则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主要依据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提供的证据和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加以确认的,是经过程序操作而形成的真实。笔者认为法律真实说更接近于民事诉讼过程本身,更符合民事诉讼自身的。首先,民事诉讼中的案件事实是由当事人引入的,事实调查的范围实际上是由当事人控制的,并且法律也承认这种控制具有正当性,那么就等于法律认同民事诉讼是以达到相对真实为满足的。其次,人的认识能力具有相对性。对于不可重现的案件事实,作为审判者的法官只能事后根据证据去推测、判断,但法官的认识能力受制于诸如时间、手段等客观条件,因此,对事实完全客观地把握,实际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再次,民事诉讼要受到诉讼效率与成本的制约。在诉讼过程中,我们不能象家一样对于有疑问的结论无时间限制地研究下去,必须考虑效率问题,另外,发现真实是需要支付成本的,能否发现真实及发现真实程度的高低,往往取决于所支出的费用和花费的时间,鉴于这一成本是全部或主要由当事人负担,在追求真实时考虑当事人的利益和要求是必要的,也符合“司法为民”的理念。
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所能达到的只能是法律真实。但这并非否认客观真实的价值。各国的诉讼和民事证据制度都是以发现客观真实为其重要目标的,很难想象一种对案件真实情况漠不关心的民事诉讼制度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但由于诉讼过程受时间、空间、技术手段、财力等多方面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实现百分之百的客观真实,所以客观真实这个理念不能放弃,但由于具体条件的限制,每个案件在尽可能追求客观真实理念的指导下,最后得到的是法律真实。 ③
二、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寻求平衡的路径
基于上述理念,在裁判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是在寻求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的平衡。如何在达到法律真实的同时,更接近于客观真实,是我们所探求的路径。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裁判者采取何种方式达到发现真实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如何使当事人对法官的判断产生认同。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法官发现真实的过程同时也是当事人对审判产生认同感的过程,法官发现真实的方式、程度直接影响到当事人认同感的大小。其中第二个方面尤为需要重视,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法官作出的裁判能否得到公众的承认。司法的目标是要使判决具有对于社会而言的可理解性和意义性,法律问题不是一个真与假的事实判断问题,而是一个合理与否的价值判断问题。④ 我们过去的诉讼制度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缺陷,所强调的是一种裁判者的职权性和当事人的被动性。这种类似于“家长——子女”的诉讼地位结构导致了败诉的当事人往往将其败诉的原因归责于裁判者,裁判者要证明其判决的正当性并进而赢得当事人以及社会的信赖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裁判者的无与伦比的素质。为走出这种困境,除了遵循证据审查和认定的基本准则外,我们更加强调法官的中立地位和正当程序的建立。
首先,法官要保持中立。法官应当在冲突的当事人之间保持一种超然和不偏不倚的立场及姿态,不能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或者对一方当事人抱有偏见和歧视。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得担任该案件的裁判者;裁判者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能有偏向于一方当事人的主张的言词、行为和态度。只有这样,法官才能成为令当事人信服的公正的裁断者,才能在更大程度上获得当事人的认同。
其次,要建立正当的程序。英国有一句著名的法谚,“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实质性地参加正当的程序,可以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机会参加判决的形成过程,并对判决的形成发生现实的、有效的影响和作用,从而对审判产生认同感。在民事诉讼的过程中,当事人需要提出争议的事实以形成审理的对象,提出证据资料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事实。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应当给予一定的协助,告知当事人有关证据的权利,包括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请求鉴定、勘验,申请延长举证期限,进行质证等权利,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和当事人之间证明责任的分配,告知当事人需要搜集和提供哪些证据,同时保证当事人之间诉讼地位平等,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并且受到法官的同等对待。
这样一来,尽管事实的真伪最终要由法院裁判来认定,但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资料却要由当事人来提供,若当事人未能提出充分的证据来使法院发现真实,他无权指责法院,而要由自己来承担责任。同时,由于当事人在诉讼中已被赋予主张、举证、质证、补充证据、辩论的机会,在司法机关没有出现程序错误的情况下,即使法院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与当事人所经历的实际发生的事实不同,但当事人仍然会认为裁判对事实的认定是正确的,或者至少会理解法院对事实的认定,自行承担判决“实体错误”的风险。这正是程序正义的合理性所在:参与诉讼的当事者接受了即使是自己不满的结果――因为他确信自己在诉讼中依法获得了充分的机会,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法院公正地据此给予审理。
法官的中立和正当程序可以消除合理怀疑和吸收不满。程序可以视为审判的外观形式,是人们评价审判的一种重要视角。当当事人和公众从程序角度来评价判决时,如果法官不能坚持中立,当事人地位不平等,审判不能公开,则审判至少在外观上就已经显得不公正了,如此必然导致当事人及公众对审判的合理怀疑和不满。在判决本身的正确性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这种怀疑和不满将更加强烈。法官中立、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公开审判可以使审判呈现出一种公正的外观,让当事人和公众相信案件是由公正的法官以公正的方式审理的,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他们的合理怀疑并吸收他们的不满。虽然就那部分判决的正确性本身存在争议的案件而言,正当程序并不一定导致当事人和公众对于判决的信服,但是审判通过正当程序呈现出来的公正外观至少可以使其怀疑和不满失去充分和直接的依据,使他们不得不接受判决或者不对判决表示明确的反对。
法官的中立和正当程序有利于当事人和公众理解判决。公开审判对于当事人及公众理解审判过程和判决理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诉讼资料和判决依据的公开、开庭审理的公开进行以及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都可以大大提高审判的透明度和说服力,使判决更加容易为当事人和公众所理解。此外,让当事人实质性参加程序意味着当事人作为程序主体直接置身于程序的运行当中,也便于他们理解审判。⑤
综上所述,法官的中立和正当程序的建立是在客观真实与真实之间实现平衡的路径之一。
①李浩:《论法律中的真实》,载《法制与社会》2004年第3期。
②刘光:《法律真实性和形式合理性》,载《山东公安专校学报》2002年第5期。
③参见:《民事证据法:程序与实体的交汇》
④霍海红:《证明责任:一个“功能”的分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⑤翁晓斌:《关于提高我国民事审判正当性的思考》,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