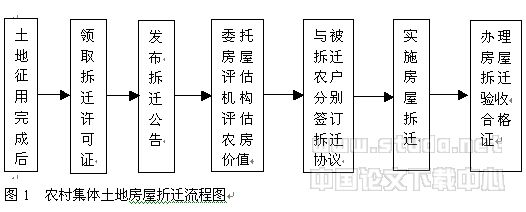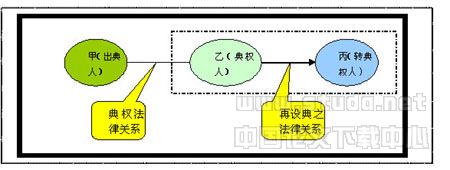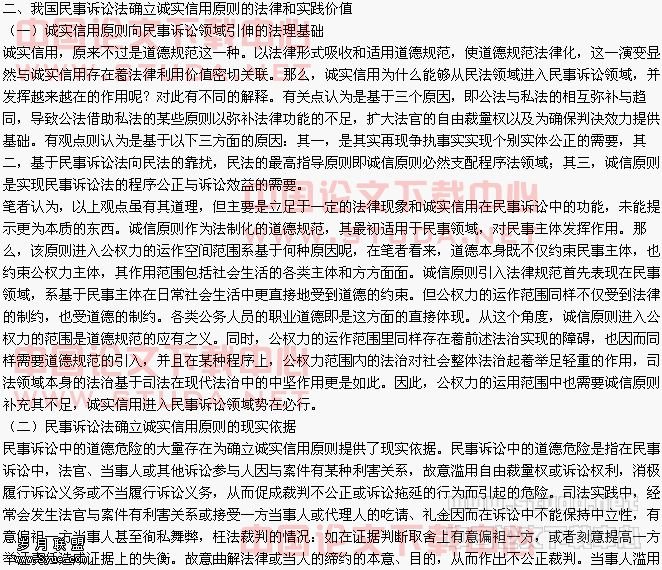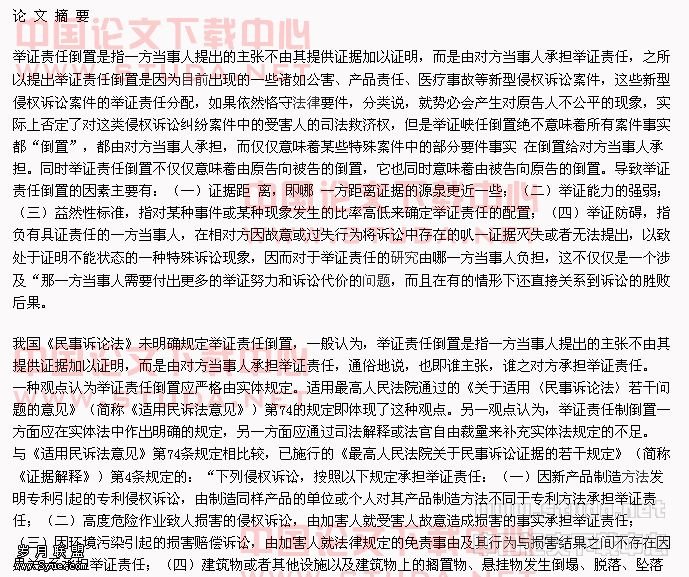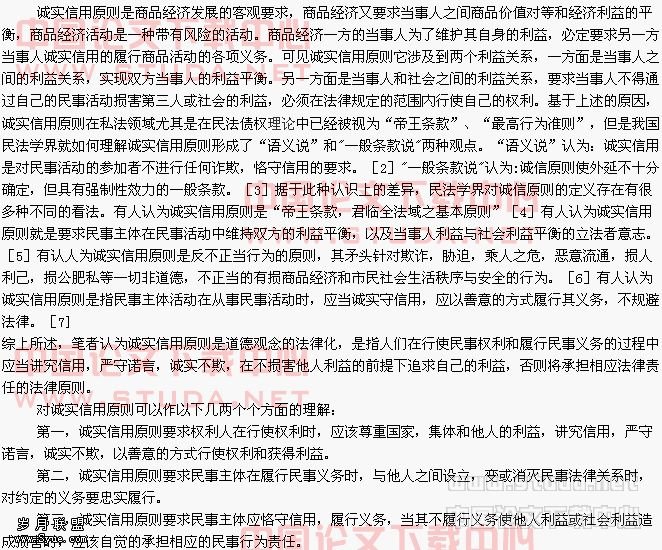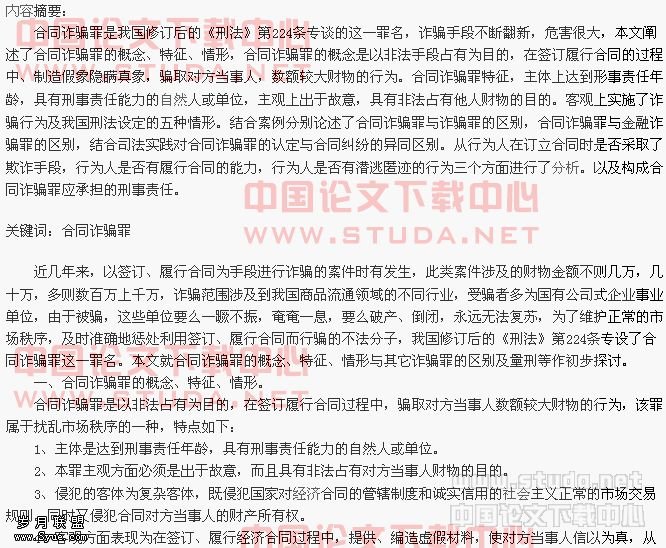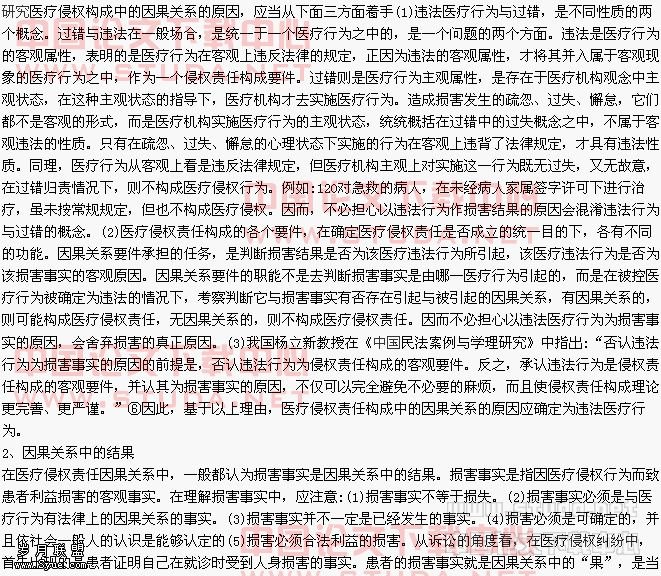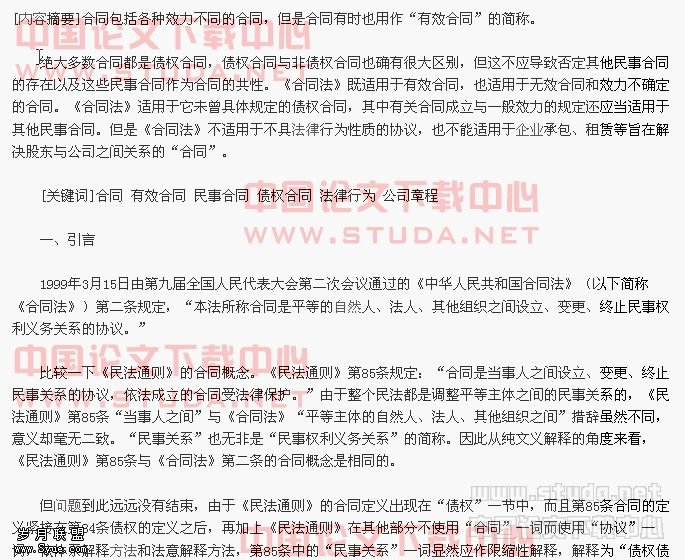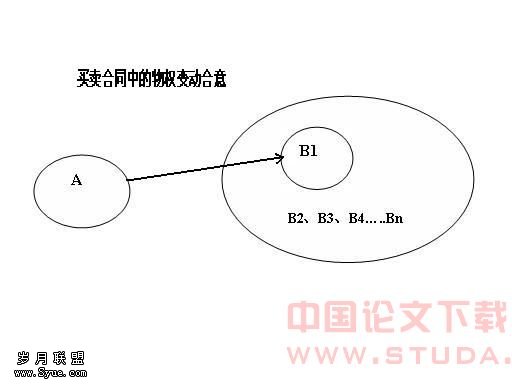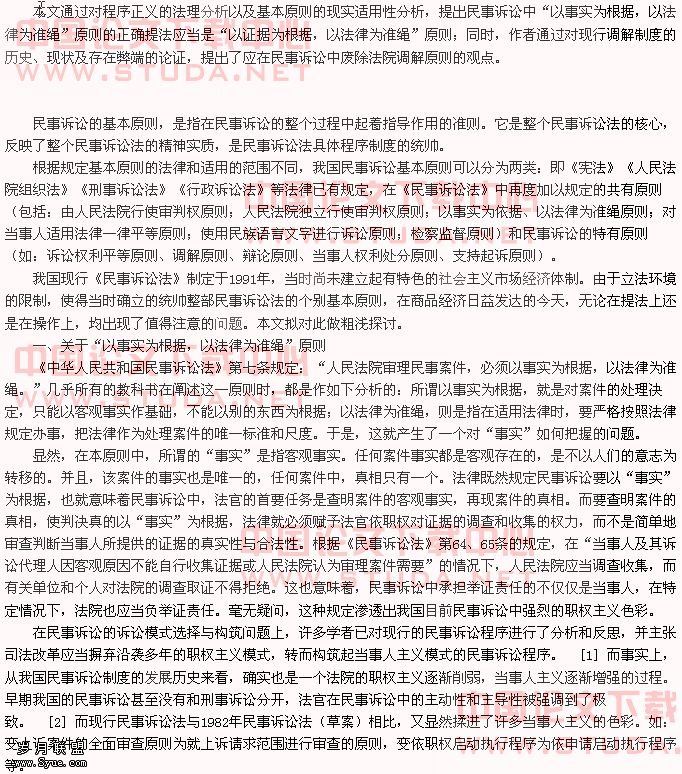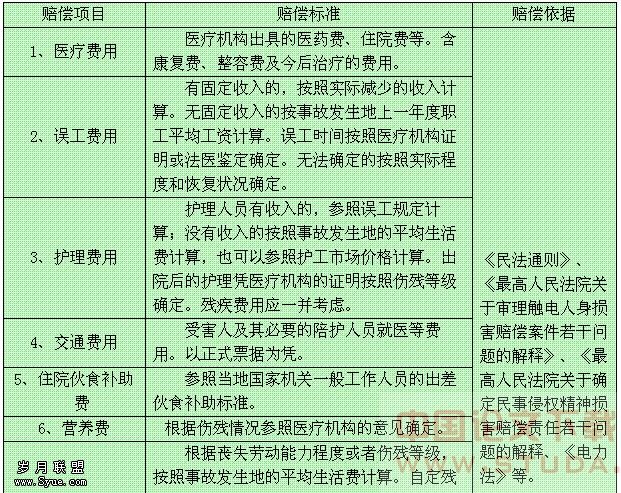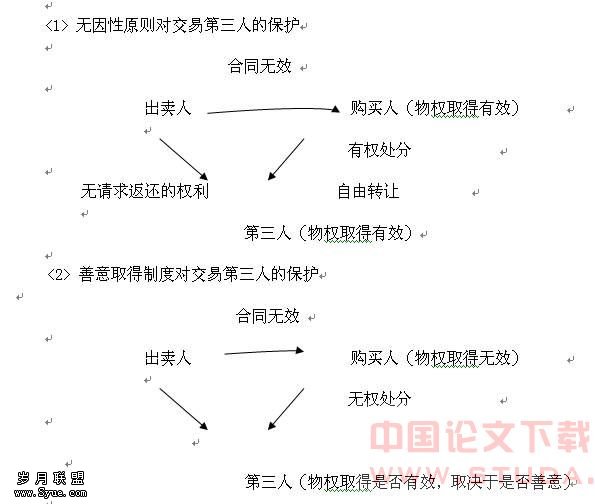我国商标反淡化的现实与理想
内容提要: 我国2001年修正《商标法》增加驰名商标保护规定的目的,在于满足入世的要求,达到TRIPS协定的驰名商标保护水平。由于TRIPS协定没有采纳商标淡化理论,我国《商标法》也没有采纳该理论。商标的魅力在于其吸引力,保护商标权的要旨在于保护商标的吸引力。反淡化和反混淆都是商标吸引力保护体系中并行不悖的双轮,我国应当规定商标反淡化条款。我国在将来修正《商标法》时,应博采美国反淡化模式和欧盟反淡化模式之所长,对商标淡化作出专门规定。
关键词: 商标/淡化/驰名商标/《商标法》第三次修正
我国正在启动《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有关我国《商标法》是否已采纳商标淡化理论,以及应如何规定商标反淡化条款等问题,必将成为其中争议的焦点之一。美国[1]和欧盟[2]的商标保护理论,已经从传统的混淆理论,扩大到了淡化理论,并在立法和司法上得到肯定。淡化理论认为,商标的价值在于其销售力,保护商标就在于保护商标的声誉和显著特征,因此,在不相同也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驰名商标,即使不会导致消费者发生混淆,由于该行为将导致该商标声誉或显著特征的降低,应当被认定构成商标侵害。笔者认为,我国2001年修正《商标法》时,虽然增加了驰名商标保护的条款,但并未采纳商标淡化理论,商标淡化理论具有合理性,建议在合适的时机,借鉴美国和欧盟立法经验,对反淡化作出专门规定。
一、我国尚未采纳商标淡化理论
我国在2001年修改《商标法》时新增加了对驰名商标给予特殊保护的规定,《商标法》第13条规定:“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有些学者可能会认为,该条规定实现了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由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扩大保护到了不相同也不类似的商品上,保护的要求也从明确要求“容易导致混淆”,为“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由于冲淡驰名商标的显著特征和损害驰名商标的声誉,都属于“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内容,而这两种情形都属于商标淡化的基本类型,因此认为我国已采纳了商标淡化理论。
如何解释和使用《商标法》第13条第2款的规定,是商标法理论界和实务界不可回避的问题,但遗憾的是,目前面世的众多专著和教材中,尚未发现对该款中“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作出了明确解释者,似乎也没有对该规定是否具有商标反淡化倾向作出详细分析者。笔者认为,该款规定没有商标反淡化的因子,我国尚未采纳商标淡化理论。
我国增加《商标法》第13条,是为了满足入世的需要,履行《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二和TRIPS协定中对驰名商标给予保护的义务,使我国驰名商标保护制度与世贸规则和巴黎公约的保护形式和原则相一致。[3]《巴黎公约》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建立在混淆理论的基础之上,保护范围限于将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使用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并明确要求以“易于造成混淆”为前提。
TRIPS协定提高了驰名商标的保护水平,但仍然没有采纳商标淡化理论。协定第16条第3款规定:“《巴黎公约》(1967)第六条之二应基本上适用于与已获得商标注册的货物或服务不相似的货物或服务,只要该商标在那些货物或服务上的使用会表明那些货物或服务与该注册商标所有人之间存在着联系(connection),且这种使用有可能损害该注册商标所有人的利益。”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条件是:第一,商标的使用将表明商标使用人与驰名商标所有人之间存在联系,其二,这种使用可能损害注册商标所有人的利益。有些学者提出通过弱化或丑化而丧失商誉,显然属于该款所谓的“损害”,而它们又属于商标淡化的典型类型,因此该款包含了商标反淡化的精神。[4]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因为弱化也好,丑化也罢,这些损害要获得救济都必须以存在联系为前提。为了克服“联系”这一要件对商标淡化的限制,美国最高法院提出,该规定中的“联系”包括了相关公众在后使用人与驰名商标所有人之间存在“精神上的联系(mental association)”。[5]但商标法不是或领域的基础,它仅仅是商业领域的基石。[6]换言之,商标法强调的是“上的联系”,而不关注“精神上的联系”。即便是商标淡化理论,其着眼点也在于商标标识所具有的区别力和标识力是否减弱,商标所代表的商誉是否被不正当利用或者被损害,也与“精神上的联系”无涉。正因为如此,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学者和美国高院对TRIPS协定的解释,并不代表对该协议的权威解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基于寻找各种证明反淡化规定之合理依据而作出的推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曲解,TRIPS协定没有采纳反淡化理论,它与美国《联邦反淡化法》不要求存在混淆可能之规定完全不符。[7]
由于《巴黎公约》和TRIPS协定都没有采纳反淡化理论,我国为达到TRIPS协定驰名商标保护水平而制定的《商标法》第13条,当然也不可能采纳了商标淡化理论。鉴于《商标法》第13条与TRIPS协定第16条第3款之间的渊源关系,我们可以将第13条第2款中的“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解释为“表明那些货物或服务与该注册商标所有人之间存在着(经济上的)联系,且这种使用有可能损害该注册商标所有人的利益”。
二、商标淡化理论之合理性
商标是经营者用来标识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并将该商品或服务区别于其他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标志。由于商标真实地指示了商品的来源,代表了一定的质量水平和经营者的声誉,因而对消费者具有吸引力。商标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赋予了商标以财产的属性,商标也由此荣升为最重要的无形财产之一。
商标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是商标意义之所在,商标保护,应围绕商标吸引力而展开。传统商标法中的商标混淆理论,旨在防止侵权者通过使用他人的商标而将自己的商品伪装成他人的产品,欺骗公众从而侵占商标权人的商誉。[8]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经营者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消费者看到特定商品上使用的商标,可能认为该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与商标权人之间存在控股关系或商标许可关系,但事实上两者之间并没有这种关系,消费者基于对商标权人的信任而相信该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从而使消费者受到与来源混淆相同的损害。对商标权人来说,虽然这种情形并不会导致其客户的分流,但其商誉由于侵权人的劣质产品而丑化,直接威胁导了原告的声誉和商誉。为了保护消费者和商标所有人利益,混淆理论从传统的直接混淆,扩大到间接混淆,只要公众可能相信该产品或服务来源于商标权人,或者来源于与商标权人具有经济联系的经营者,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就可以认定构成侵权。商标直接混淆和间接混淆,都是通过混淆公众视听,误以为这些商品或服务来源于商标所有人或与其有经济上的联系,从而直接利用商标的吸引力。
商标混淆是导致吸引力降低的重要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滥用驰名商标和丑化驰名商标都是重要而常见的形式。将驰名商标使用在根本无关的商品或服务上,消费者不可能相信该商标的使用行为与驰名商标所有人有任何经济上的关系,但由于过多过滥地使用该驰名商标,将会导致消费者的“审美疲劳”,驰名商标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平淡,其吸引力也越来越小。将他人驰名商标使用在色情淫秽等让人产生不良印象的产品或服务上,将直接降低该商标的形象。为了保护商标的吸引力,欧美等国家在防止商标混淆外,还规定了商标反淡化条款。
商标反淡化与商标反混淆,都是为了防止商标吸引力的降低,但路径不完全相同:商标混淆强调消费者是否可能发生混淆,商标淡化则直接以商标的声誉或显著特征是否遭受损害为焦点。由于目标一致而路径不同,两者存在重合之处,但绝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也就不可能用一种来取代另一种。彭学龙博士认为,当商标驰名度上升到极至或者品牌延伸到无所不包的程度,其他只要使用这类商标,就有导致消费者混淆的可能性,反淡化法就失去了用武之地。[9]彭博士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品牌延伸越广,其他企业的商标使用行为,就越可能导致消费者误认为该企业与驰名商标所有人之间存在经济上的联系,就越容易被认定为构成间接混淆,就越没有必要适用商标反淡化的规定。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品牌延伸不可能漫无边际,不管它如何扩张,也必然存在不会导致消费者产生混淆的商标使用行为,例如商标使用人以显眼的方式告知消费者它与驰名商标所有人无关等,对这种可能造成商标权人损害的情形,商标混淆理论鞭长莫及,而这恰恰是商标反淡化条款的用武之地。另外,在丑化驰名商标这种典型的商标淡化情形中,商标混淆理论没有适用的余地,更不可能取代反淡化之适用。因此,品牌延伸可能限制而不能取代商标反淡化的适用,因为反淡化和反混淆,是保护商标吸引力这驾马车上并行不悖的双轮。
(一)采纳商标淡化理论的必备条件
商标淡化理论具有合理性,然而任何理论运用于实践,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商标淡化理论主要针对驰名商标,社会对驰名商标的态度,就成为决定该理论能否适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我国每年通过各种渠道批量生产上百个驰名商标,可能累计起来的驰名商标数量在全世界也名列前茅。对驰名商标的钟爱程度,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获得驰名商标的称号后,不仅将这种“奖牌”专门供奉在办公室的最显眼处,而且还通过各种媒体大肆宣传,大街小巷里悬挂着“热烈祝贺〇〇荣获世界名牌”的红布条,更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道风景线。地方政府也都将驰名商标的数量作为自己的政绩加以炫耀,为了鼓励企业争取被评为驰名商标,许多地方政府不惜斥重金以蛊惑之。由于商标淡化理论具有加强驰名商标保护力度的作用,如果在我国目前加以适用,对疯狂驰名商标情结只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在驰名商标心魔未去,驰名商标的认定尚未回归本来面貌之前,应当无限期推迟商标淡化理论的适用。
即便我国对驰名商标的态度已经回归于理性,也需要论证商标淡化理论的适用,对我国是否起者推动作用。如果真正能够适用商标反淡化条款的驰名商标,大多都属于外国公司,我们就没有必要为迎合外国公司提高商标保护水平的要求,捆绑我国公司的手脚。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考察商标淡化理论是否值得采纳的关键因素。
(二)采纳商标淡化理论的模式选择
将来在采纳商标淡化理论时,需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从目前商标反淡化立法模式来看,主要有美国模式和欧盟模式两种。两种模式主要有以下共同之处:第一,商标反淡化条款都提高了商标权的保护力度,实现了商标保护从以混淆的可能为标准,向不以混淆为要件的飞跃。第二,商标反淡化条款的理念,都以保护驰名商标的独特性和显著性之方式,达到保护驰名商标权人商誉或商标吸引力之目的。第三,对驰名商标的保护,都规定了弱化和丑化两种形式。[10]第四,都将商标淡化作为驳回商标注册申请的理由,都将淡化视为商标侵权情形之一。[11]
商标反淡化条款的美国模式和欧盟模式,也存在一些不同之处,实体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商标淡化类型和商标淡化之例外规定两方面,立法技巧上各有优劣。在商标淡化的类型上,美国除法条明确规定弱化和丑化两种情形外,在实践中还包括了将他人驰名商标退化为通用名称的行为。[12]笔者认为,退化是对驰名商标吸引力最大的损害,应当作为淡化的典型情形看待。欧盟除丑化和弱化外,还将不正当地利用在先商标规定为淡化类型,其目的在于防止在后商标搭在先商标的便车。不正当地利用在先商标需要证明以下内容:在先商标的声誉或显著特征、消费者将两个商标相联系的可能性、商标权人的商标价值或声誉转移到了对方身上、在后商标权人从在先商标权人处获得了重大的利益。笔者认为,这种立法不甚。一方面,商标反淡化条款的目的,在于防止驰名商标的吸引力受到损害,行为人是否获利无关紧要。另一方面,“不正当地利用在先商标”需要以消费者将两个商标相联系,而且导致驰名商标权人的声誉或商标价值转移到对方身上,这些要件恰恰就是商标间接混淆的构成要件,因此“不正当地利用在先商标”这种类型完全可以被间接混淆所涵盖,没有必要迭屋架床式地又在反淡化条款中作出规定。
在商标淡化之例外规定上,欧盟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美国非常重视商标淡化的免责规定,在没有对自由竞争和言论自由等公共利益作出合理的保护时,美国国会宁愿展缓该法的制定,以避免反淡化条款挫伤市场公平竞争或限制言论自由。在对竞争者利益和言论自由作出周全的保护后,美国国会才通过了《1995年美国联邦反淡化法》,此后又在2006年修正该法时进一步完善了商标淡化的例外规定。美国国会对社会公共利益精心呵护的态度,和对制度设置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各国学习。
从立法技巧上来说,两种模式各有优劣。美国立法模式中,将丑化和淡化在条款中作了明确解释,而欧盟的三种淡化情形则不太明朗,经过多年司法实践的摸索后,才逐步确立各种淡化情形的要件。从明确规定淡化的要件方面来说,美国模式更为科学。从商标淡化条款与其他条款的衔接角度来说,欧盟没有专门规定商标反淡化条款,而是将相关内容规定在商标申请要件、商标侵权救济中,整部一气呵成而浑然一体。反观美国《兰哈姆法》,它在专门规定商标反淡化条款的同时,又在商标申请程序、商标侵权救济等部分中再次规定商标反淡化的内容,就有重复罗嗦之嫌。美国商标反淡化法的这种缺陷,与其数次修法的不无关系,美国国会在修正《联邦商标反淡化法》时,将反淡化的内容从一般的权利救济扩大到与商标混淆相同的救济力度,又从实体救济扩大到程序救济,且修法过程中增加和变更条款内容相对容易,删除和合并条款相对比较困难,最终形成了目前这种状况。我国将来增加反淡化内容时,商标反淡化条款在《商标法》中的宏观布局,可以吸收欧盟模式的长处,将反淡化在商标申请程序和商标救济两部分中作出规定,在具体内容的设计上,可以借鉴对丑化和弱化等作出明确解释和规定商标淡化之例外的美国经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和欧盟在商标反淡化条款的规定上,各有优劣,我们应当博采两种模式之所长,制定出更科学的商标反淡化条款。
(三)制定商标反淡化条款的构想
由于商标反淡化条款的设计,涉及驰名商标的保护及其立法表述、商标注册要件及其立法表述等内容,本文在此不便过多展开。笔者认为,我国在商标注册要件中,可以增加如下内容:
第 条 申请注册的商标因在先商标所有人的异议而不得注册:(一)……(三)将任何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志,使用在不相同也不类似的商品上,因可能弱化或丑化而无正当理由地损害该驰名商标的显著特征或声誉。
本法所称弱化,是指由于一个商标或商号与驰名商标类似而产生损害驰名商标显著性的联系。本法所称丑化,是指由于一个商标或商号与驰名商标类似而产生损害驰名商标声誉的联系。
在商标权的保护部分,建议在第52条增加以下内容: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商标权:(一)……
(五)商标驰名后,擅自在商业上使用商标或商号,不管该使用是否具有混淆的可能,将导致该驰名商标可能由于弱化、丑化、退化而淡化的;
(六)给他人的注册商标权造成其他损害的。
下列情形不视为商标淡化:(一)验证和滑稽模仿、讽刺或评论驰名商标所有人或驰名商标所有人之商品或服务的行为,或者为消费者提供比较产品或服务机会的广告或促销活动中,对驰名商标所作的指示性合理使用和描述性合理使用。(二)新闻报道或新闻评论中对驰名商标的使用。(三)对驰名商标的非商业性使用。
注释:
[1] 美国于1995年制定《联邦商标反淡化法》后,经过1999年和2006年两次修订,使该法日臻完善(参见邓宏光:“美国联邦商标反淡化法的制定与修正”,《知识产权》2007年第2期)。
[2] 欧盟为了防止不正当地利用或损害声誉商标的声誉或显著特征,在1988年通过的《欧共体商标指令》和1993年通过的《欧洲共同体商标条例》中,都规定了商标反淡化条款。经过欧洲法院和欧共体商标审查机关数十年的实践,已经使欧盟的商标反淡化规则明确化和具体化(参见邓宏光:“欧盟商标反淡化法”,《电子知识产权》2007年第3期)。
[3] 董葆霖:《商标法律详解》,中国工商出版社2004年版,第66、279页。
[4] Matthew C. Oesterle, It’s as Clear as Mud: a Call to Amend the Federal Trademark Dilution, 81 Chi.-Kent L. Rev. 252, note142. (2006).
[5] Moseley v. V. Secret Catalogue, Inc., 537 U.S. 418, 433 (2003).
[6] Jason K. Levine, Contesting the Incontestable: Reforming Trademark’s Descriptive Mark Protection Scheme, 41 Gonz. L. Rev. 34, (2005).
[7] David S. Welkowitz, Trademark Dilution: Federal,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Inc: Washington DC, 2002, pp. 160-161.
[8] Amoskeag Manufacturing Company v. Spear 2 Sandf (NY)Super 599,605-06(1849).
[9] 彭学龙:“商标法的符号学分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第235页。
[10] 《欧共体商标条例》规定了三种淡化形式:不正当地利用在先商标、不正当地损害在先商标的显著特征,和不正当地损害在先商标的声誉。其中,损害他人在先商标的显著特征即为弱化,损害商誉也经常被称为丑化(参见邓宏光:“欧盟商标反淡化法”,《电子知识产权》2007年第3期)。
[11] 在美国,商标侵权很多时候仅仅指商标混淆的可能性,商标淡化作为反不正当竞争的内容来看待(参见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章和第12章)。但这种分类也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商标保护与反不正当竞争往往是紧密相连的,国外许多商标相关的专著都是以《商标与反不正当竞争》为标,另一方面,一些专著中也将淡化作为商标侵权损害类型看待,如 Mark A. Glick, Lara A. Reymann, Richard Hoffm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mages: Guidelines and Analysis, Wiley &Sons, Inc. 2003.
[12] Ty Inc. v. Perryman 306 F. 3d 509 (7th Cir.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