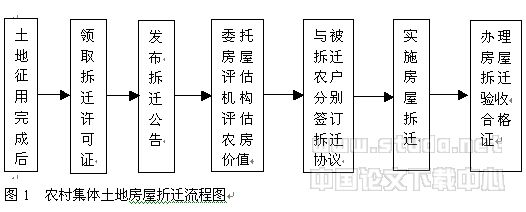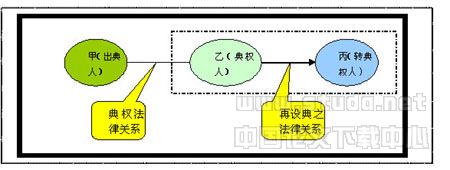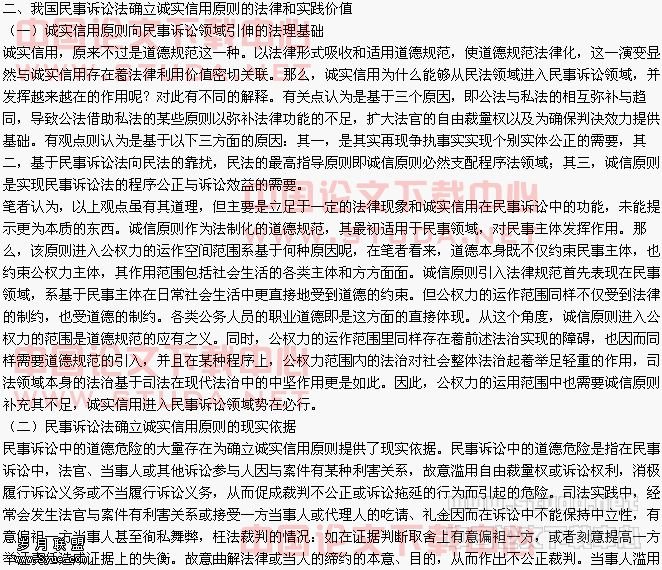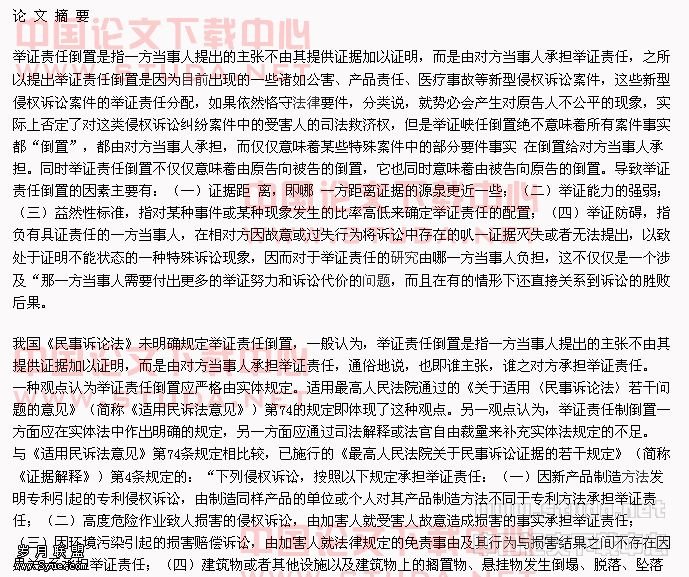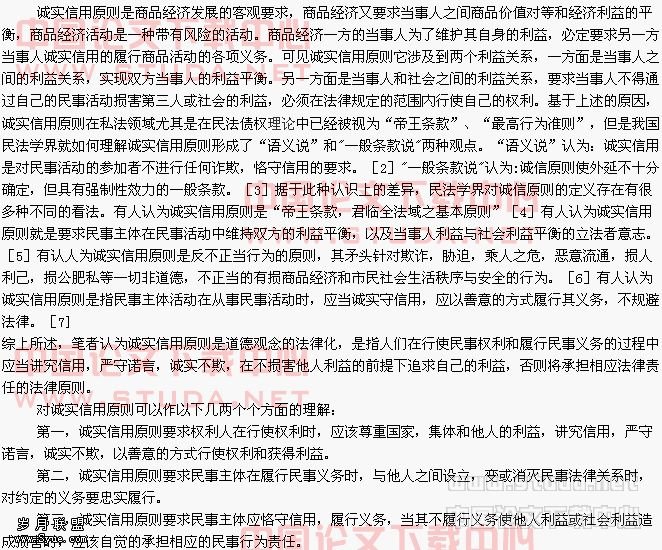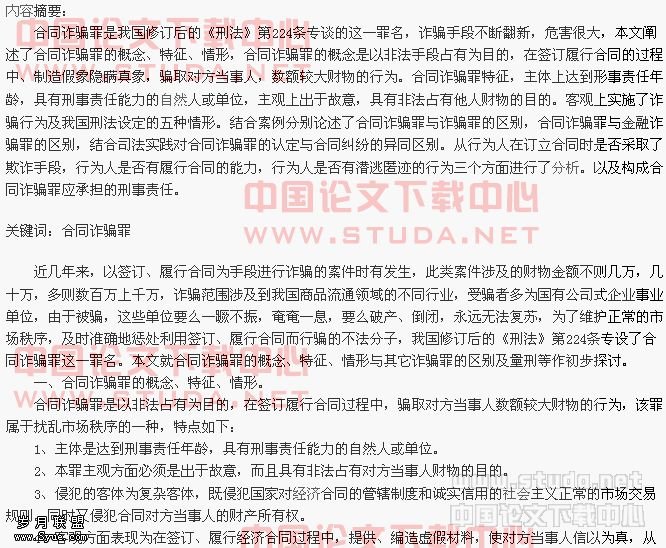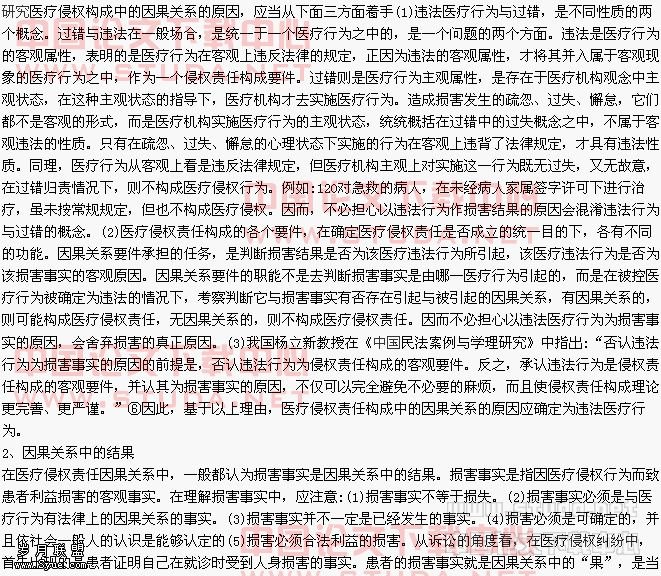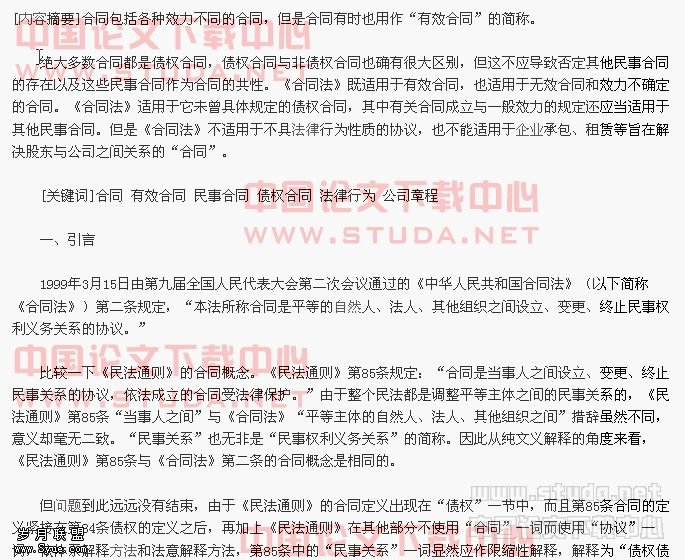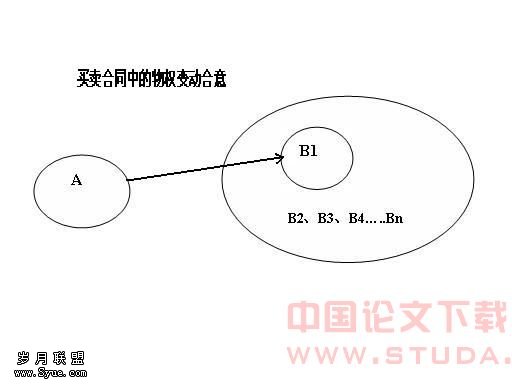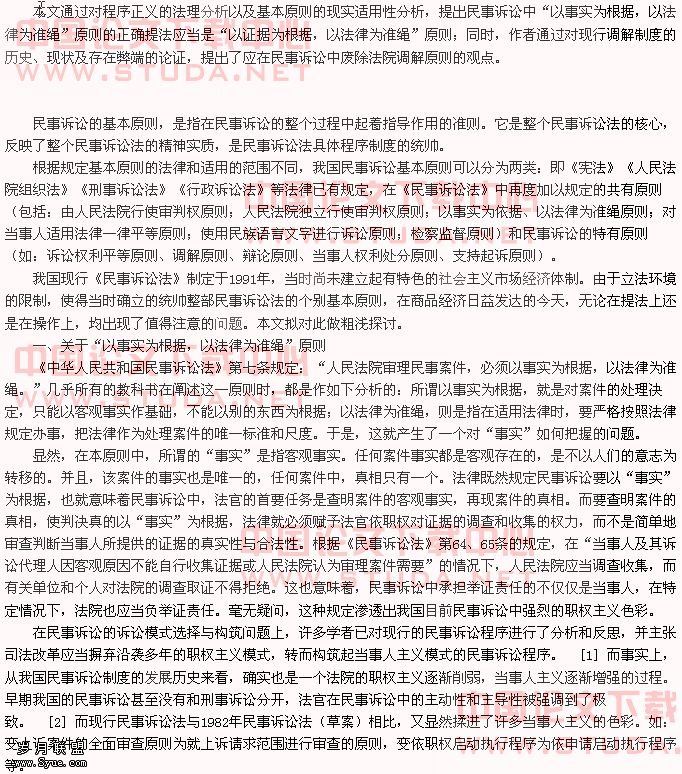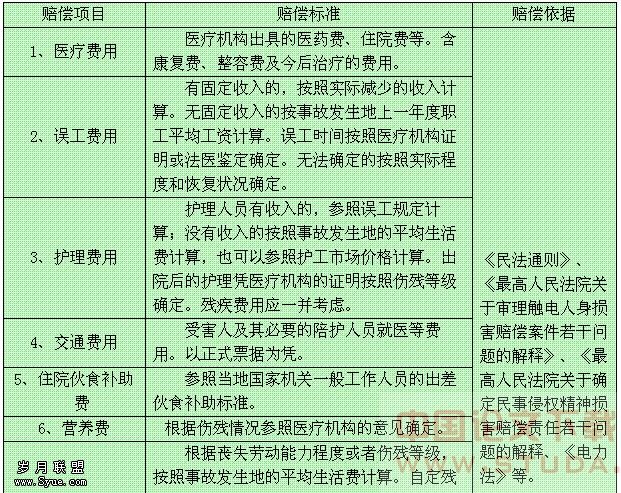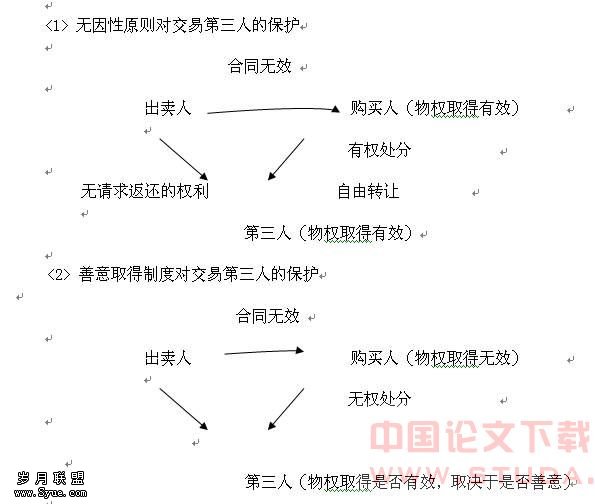住房租赁合同的社会控制(下)
三、住房租赁控制的制度建构
(一)与现状
1.近代史上的租赁控制。自清末民初开始,中国便出现了城市住宅短缺、租金高涨、出租房质量低下等问题。[1]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开始出台文件对租赁关系予以规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解决房荒为目的的房屋救济立法时期(1929-1936年)、以战争为背景的全面租金管制时期(1937-1943年)以及战后租金管制立法的修正与补充时期(1945-1949年)。[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废除了旧法统,但在此后一段时间内维持了旧有的租赁控制规则,直至1956年前后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如多个城市都规定:“可供居住的空闲房屋或超过需要只房屋,遇必要时,得由人民政府限期命所有人或管理出租或出借。”[3]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后,逐步确立了城市公房出租制度。这是一种最极端的租赁控制——国家(多数情况下以企事业单位为媒介)垄断全部的住房供给,全面控制租金水平和租赁合同的内容。1980年,中国启动了公有住房改革,基本思路是“出售公房,调整租金,提倡个人建房买房”。[4]1992年,将房地产业确立为支柱产业,重点扶持。[5]鉴于有大批城市居民既无法“建房买房”,也无法享受租赁公房的福利,面临住房困难,近年来国家开始了廉租房和适用房的建设。[6]
2.住房租赁制度现状。在当下中国,住房租赁有制度包括公房租赁、廉租房和私房租赁几种形式。根据2007年的统计,北京、上海户籍人口中通过租赁公房解决居住需求的分别占总人口的15%和20%。[7]公有住房的租金水平一般比较低。根据2000年的一项统计,公有住房租金水平占双职工家庭平均工资的比重为6%-10%左右。[8]现行廉租房制度的问题主要是覆盖面极小,只针对符合特定条件(双困户)的城市户籍家庭。[9]2008年底,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央政府计划用3年时间,解决近750万户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240万户林区、垦区、煤矿等棚户区居民的住房问题,并积极推进危房改造。[10]但其执行状况仍待观察,另外,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其覆盖面仍然有限。
在私房租赁方面,1990年代以后,建设部和一些省市分别制定了题为“城镇(城市)房屋租赁条例(管理办法)”的地方法规或规章。[11]有些地方的工商局和国土房管局制定了《房屋租赁合同(示范文本)》[12]供签约者。这些法律或范本基本上对住房租赁持自由的态度,如规定:房屋租金由当事人协商确定;租赁期限由当事人协商确定,当事人没有约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随时解除合同;禁止未经所有人同意的转租,否则合同无效等。当前对私有住房租赁合同不多的限制主要集中在治安、税收管理上。如规定租赁合同应备案,[13]个人出租住房所得按1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14]等。实践中,对于治安和税收登记,无论出租人还是承租人都没有充分的动力,因此两项制度都很难执行。
总体来看,公房租赁主要用于解决事业单位的遗留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将慢慢退出市场,廉租房制度则主要着眼于城市低收入家庭,二者适用范围都是比较有限的。相比而言,随着房屋自有率的提高,随着购买第二套、第三套住房人数的增加,私房租赁市场必将日益扩大。虽然城市私房租赁市场也分为多种层次,如城乡结合带的租赁、城中村的租赁与一般城市房屋的租赁等,但只是用途不同而已,需求本身并无差异,因此可一并讨论。
(一) 住房租赁控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对于未来是否应实行一定形式的住房租赁合同控制,宜着眼于不同的租赁控制模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必要性与可行性两个角度加以分析。
1.租金管制模式。首先,如前所述,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租金管制是否必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保护承租人的数量。只有在承租人的数量足够大时,对所有权施加限制才有充分的正当性。[15]在这里,“多数”还是“少数”不再仅仅是量上的差别,而是质的不同。如前所述,从实证数据上看,在实行较强租赁控制的德国、美国纽约、新泽西州等,承租人都占超过50%的比例。这为其租赁控制提供了充分的正当性。相比而言,在中国,因受看重田土房宅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和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目前城市居民房屋自有产权的比例是比较高的。[16]因此,在规模较大的城市,私有住房租赁的比例并不是很高。[17]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度的租赁控制(租金管制)难言正当。
其次,必须要看到,住房问题的解决除租金管制以外还有兴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方式。相比而言,租金管制的长处是在现有住房的基础上解决居住成本的问题。在城市化没有完成之前,城市中居住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有限的住宅总量无法满足源源不断涌入城市的新增人口的居住需求,以北京为例,在当前1633万的城市人口中,有近420万[18]的流动人口[19],城市化的发展意味着要在短时间内解决大多数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因此在商品住宅建设之外兴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也很必要,租金管制至多能限制租金,并不能提升住宅总量。
从可行性看,租金管制的有效运作,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条件:第一,有较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司法裁判系统。在目前中国行政体系和司法体系低效、不透明、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如果实行租金管制制度,行政成本和寻租成本将非常高,若安排不当,很容易产生一个官僚化的强权部门,为规避者提供寻租的温床,甚至可能违反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第二,单一产权住宅楼的比例较大。所谓单一产权的住宅楼,指整栋住宅楼都归一人所有,其将楼中的住宅分别出租给不同的承租人。在进行租金管制时,所有权人虽然可以用将有关房屋出卖的方式规避,但法律可以通过对单一产权住宅楼转为区分所有住宅楼进行限制来加以阻止,而限制区分所有的住宅或独栋住宅的转让是非常困难的。[20]在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单一产权住宅楼的情况下,如果再普遍性地管制转让价格,更将危及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有效运行。第三,有全面的不动产税制度。通常认为不动产税有助于抑制房地产投机和过大的住房需求(税收压力可促使人们选择适当的房屋大小和房屋类型),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21]就租赁控制而言,不动产税可以防止房屋闲置,因而是租金管制制度的重要前提。在中国尚未开征不动产税的背景下,即使规定租金管制,部分所有权人也可以选择将房屋空置而使该制度无法实现其目标。
2.解除权限制模式。德国法上的租赁控制是以市场为中心展开的,因此前述租金管制模式中的两项成本都不显著。其主要收益是降低租赁关系中逆向选择发生的可能性,避免出租人通过策略化行为获益,维护租赁关系的稳定。这对中国目前住房租赁制度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中国住房租赁市场中,租赁期限通常都比较短,多数人对租赁合同缺乏稳定预期。[22]若能修正合同法第232、236条,借鉴德国法的相关制度,限制出租人解除权,引入市场标准作为租金调整的基准,将非常有助于增进中国住房租赁交易的效率。具体可以包括以下安排:(1)借鉴德国法上限制定期租约的制度,规定无正当理由不得签订有期限的住房租赁合同;(2)改变合同法第232条的规定,将不定期租约视为长期租约,除非具有正当理由,不得解除;(3)改变合同法第234条对转租的严格禁止,允许承租人在短期外出时将房屋未经允许临时转租他人(但不得转租牟利);(4)具体建立指导租金体系,为租金上涨提供依据。[23]
在借鉴他国的制度时,还应注意中国各地差异较大的特点。即并不应完全排除未来在某些城市实行纽约模式的租金管制的可能性,尤其在某一地区承租人人口占该区域总人口半数或半数以上比例时,实行较为严格的租金管制,并无不妥。
(三)住房租赁控制制度要点
总体而言,一套行之有效的住房租赁控制制度需要满足五项要求:(1)租金可负担。如前所述,租金管制的程度是两种不同租赁控制模式的最主要差异。在住房紧缺,城市又无从扩张的情况下,适当限制租金水平是必然选择,限制的具体值可以参照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确定,如将租金额控制在每户家庭总收入的30%左右。这一安排除了可确保租金可负担外,也可以“过滤”富有的承租人,让真正需要租赁控制保护的人获得相应的福利。当然,任何控制都应有充分的正当化理由,承租人占多数,住宅租赁市场紧张(如前文纽约市将租金管制与租赁房屋空置率挂钩)是管制租金的必要条件。若欠缺此二者,则应考虑借鉴德国的做法,将管制着眼于合同的解除,而由市场确定租金。(2)房屋适居。纽约州上诉法院法院将租赁视为“栖居处所与服务”的买卖(sale of shelter and service[24]),“所有权人应确保有关房屋适合人类居住,符合当事人关于租屋质量的合理预期,无任何危及承租人生命、健康和安全之处”,可资借鉴。(3)租期稳定。这要求有效限制定期租约的签订,限制出租人的解除权。(4)出租人有合理回报。任何形式的租赁控制,都必须确保租金高于房屋的维护成本,否则必然导致所有人放弃所有权。为此,在制定租金标准时,要专门测算房屋的维护成本。(5)防止承租人滥用法律保护。这需要制定必要的资格审查、限制转租牟利和其他规避行为等规则。
四、结语
住房是一项特殊的商品。其特殊性为对私人之间住房交易进行规制提供了合理性和可能性。第一,住房是必需品。作为“衣食住行”中的一项,住房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这意味着住宅不仅是一项商品,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构成了基本人权——尤其是(政府长期强调的)生存权和权的基础。第二,住房是其他社会生产活动的基础,俗语强调“安居乐业”即是此理。这意味着其关乎社会的安定。第三,住房(土地)是近乎永久存续的耐用品,这意味着对其进行规制是可能的。[25]
就租赁合同社会控制的具体形式而言,目前主要有两种,一是“市场化”的控制,不直接“限制租金数额,主要着眼于限制出租人的解除权,同时为出租人提供市场化的租金参照标准;另一种则以租金管制为中心,配套以解除权限制、强制维修、防规避等规则。在价值判断层面,即使是相对极端的纽约式的租赁控制也有其合理性,不能轻易加以否定。具体到中国,当前阶段,参酌德国的做法适当进行一些“市场化”的住房租赁合同控制,将有助于提高租赁合同的效率,是必要且可行的。未来若一些城市中的承租人比例急剧上升,适当进行租金管制亦是可选之项。
长期以来,笔者对“财产所有权的限制”这一命题的认识一直停留在“权利不得滥用”的观念上。即所有权应与社会利益相协调一致,个人行使所有权应当顾及社会利益。对租赁控制的研究改变了笔者的认识。以上分析表明,所有权的社会限制绝不仅仅是权利不得滥用的问题,而是可以剥夺所有权的某些权能,甚至导致所有权的丧失(如导致房屋所有人抛弃房屋)。在人类社会中,土地与房屋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财产形式,对其的限制可以到这个地步,的确是令人惊讶的。在此,重温耶林的论断会有更深的理解:“世上没有绝对的所有权——没有那种不需要考虑社会利益的所有权,这一观念已随着的发展被内化为人们心中的道德准则。”[26]
注释:
[1] 参见赵津:《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史论(1840-1949)》,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65 页以下。
[2] 参见张群:《民国时期房租管制立法考略——从住宅权的角度》,《政法》2008 年第4 期。
[3] 如《上海市房屋租赁暂行条例(第六次草案)》(1949),第3 条;《天津市私人房屋租赁暂行条例》(1951)第10 条等。转引自张群:《民国时期房租管制立法考略——从住宅权的角度》,《政法论坛》2008 年第4期。
[4] 如《国务院关于印发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1988]11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鼓励职工购买公有旧住房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88]13 号);《国务院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1991 年6 月7 日);《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 号)。
[5] 参见《国务院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国发[1992]61 号)。
[6] 相关规则,如2005 年的《城镇廉租住房租金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5]405 号)和2007 年11 月八部委局及人民银行发布的《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7] 参见《北京统计年鉴》(200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年,第185 页;《上海统计年鉴》(200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年,第374 页。
[8] 参见《国家计委、建设部、财政部印发关于积极稳妥地推进公有住房租金改革的意见的通知》(计价格[2000]954 号)。
[9] 根据一项统计,到2006 年底,全国享受租赁保障的家庭共有54.7 万户,相比全国的庞大承租人群体而言,微乎其微。钱瑛瑛:《上海住房租赁群体租赁保障思路》,《上海房地》2007 年第8 期。
[10]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8]131 号)。
[11] 除《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外,大多数省会和重要城市都有类似规定,如《西安市城市房屋租赁条例》(1997)、《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1999)、《哈尔滨市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2005)、《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2007)等。
[12] 如2004 年发布的《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还有《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合同示范文本(2006 版)》。
[13] 如《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2007)第2 章(第7-11 条)。
[14] 参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适用住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 号)。
[15] 谢哲胜先生亦有同样见解:“房租管制通过与否之决定性因素在于承租人人口之多寡”。谢哲胜:《房租管制法律与政策》,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 年,第190 页。
[16] 根据2000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国72%的城市居民拥有所住房屋的产权。其中,大城市的自有产权比例较低,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大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和珠海),产权私有比例是54%。边燕杰,刘勇利:《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3 期。到2007 年,北京、上海这两大城市中户籍居民自有住宅比例上升到80%。见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统计年鉴》(2007),2008 年,第185 页;《西安统计年鉴》(2006),2007 年,第176 页;《上海统计年鉴》(2007),2008 年,第374 页;广州市统计局:《广州统计年鉴》(2007),2008年,第240 页;《山东统计年鉴》(2007),2008 年,第232 页;《浙江统计年鉴》(2008),第186 页;《河南统计年鉴》(2008),第255 页。
[17] 以2007 与2008 年为例,各省市户籍人口中租赁私房人口所占的比例分别是:北京不足1%,西安1.14%,上海1.6%,广州2.4%;山东、浙江、河南均低于1%。数据出处同上注。这些数据虽然是以户籍人口为基础做出的统计,但即使把流动人口考虑进来(去除农民工、大学生等住集体宿舍的人群),私房租赁的比例也仍不超过30%,因为各省市流动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比例都不超过30%。
[18] 参见朱富言等:《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变动趋势分析》,《西北人口》2008 年第4 期。
[19] 流动人口指没有城市户籍但是在城市居住超过半年的人口,笔者这里假定大部分的流动人口没有房屋所有权,而且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口是农民工,居住在条件很差的临时住宅中。
[20] 美国各州的具体限制方式仍有所差别。其中,纽约市的限制最为严格。如有关法律规定,必须有超过35%以上的承租人愿意购买分拆出售的房屋,出租人才能将有关楼房出卖,否则承租人可以继续租用原住房。关于该制度的具体说明,参见David A. Fine, “The Condominium Conversion Problem: Causes and Solutions,”Duke Law Journal, vol. 1980, no. 2, pp. 320 ff.
[21] 参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物业税改革与地方公共财政》,《经济研究》2006 年第3 期;张再金:《物业税改革的经济影响:一个综述》,《税务与经济》2008 年第1 期;黄茂荣:《不动产税及其对不动产产业的经济指导》,《中国法学》2008 年第4 期。
[22] 在由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主持的一项调查中,天津市住房租赁合同的租期通常为1 年,占所调查租赁合同总数(354 份)的95.8%。见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课题组:《天津市住房租赁抽样调查情况分析报告》,《华北》2006 年第2 期。在福州,63.8%的租赁住房合同租期为12 个月,27.6%的合同租期为6 个月。见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课题组:《2007 年度福州市住房贷款及租赁市场抽样调查分析》,《福建金融》2008 年第4 期。房屋中介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一现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的调查,在问及被调查人“买房前是否考虑过租房”时,81.09%的借款人表示不曾考虑租房。在问及“考虑过租租房,但仍然选择买房的原因”时,57.69%的借款人认为租房没有归属感。很可能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一些城市如北京的租赁市场上,过渡性的一居室供不应求(供需比为1:2.4),而本可用于家庭长久居住的三居室却供大于求(供需比为1.3:1)。数据来源:北京市建委城建研究中心报告。
[23] 在这个问题上,完善现行房地产管理法中地价确定、价格评估和价格申报等制度即可(第32-34 条)。
[24] Park West Management Corp. v. Arthur Mitchell, et al., 47 N.Y. 2d 316, 325 (1979).
[25] Fridrich A. Hayek, The Repercussions of Rent restrictions, in Rent Control: A Popular Paradox: Evidence 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Rent Control, p. 68. 该文是哈耶克1930 年在Königsberg 的演讲辞,原文发表在1930年出版的《社会协会会刊》(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上。注意这里只强调可能性,是否正当或必要是另外的问题,上文已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26] Rudolph von Jhering, Der Geist des Rö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 4.Aufl., 1878, S. 7. 后世的英美法学者如Bruce Ackerman 和Joseph W. Singer 也认为,所有权人应当为承租人提供宜居的环境并索取适当而不是过高的租金,本质上是源于所有权社会责任的义务,是对相关主体在所有权上的信赖利益(reliance interest)的保护。Bruce Ackerman, “Regulation Slum Housing Markets On Behalfof the Poor: Of Housing Codes, Housing Subsidies 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 Policy,” Yale Law Journal, vol. 80,1971, p. 1171; Joseph W. Singer, “The Reliance Interest in Property,”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40, 1988, pp.659-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