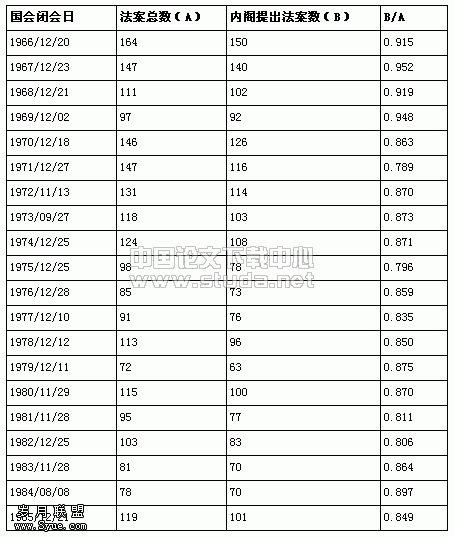反垄断诉讼的价值定位与制度建构(下)
反垄断法中,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和组织往往与政治体制有关。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委员长和局长由总统提名,议会任命,另外,检察长和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也与政治有关。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包括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务部和发改委等也不例外。因而,在反垄断执法、司法中不可能不带有政治偏见。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与立法、执法机关同属于国家机关,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所以其判决不可能不受立法、执法中取得的价值共识的约束,其独立也是有限的。
上述情况决定了任何一方不恰当的代表都可能导致远远超越参与者利益的结果。法院也可能被误导。被提起反垄断诉讼的被告也可能有意无意地以在日后程序中不易修正的方式与受害人群体协调利益。事实上,被告不仅仅是在为自己个人的行为辩护,而且是为相关市场体系中与自己具有相同境遇的所有成员的过去和未来辩护。从这一视角出发,完全依赖于所谓原告和被告的主动性就太荒谬了。法官应当有权确定诉讼参与人,使与案件有关的各类主体的利益都有合适的代表。这一般应经过以下程序:
第一,发布通告并保证能送达或告知那些有可能在诉讼中被代表的人。该通告将解释诉讼的内容并发出使代表完善的参与抗辩的邀请。即使这样,法官也不能完全依赖于通告中提及的主体和内容,而是应给扩张代表的合理要求留有一定的余地,虽然这可能增加对手继续诉讼的成本。
第二,要求特定机构,特别是相关的反垄断执法机关、监管机关和组织(如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参与诉讼,成为顾问。当然,出于裁判可接受性的需要,法院不应将邀请的范围限于那些表示愿意参与或曾有行动的主体。要求特定机构参与诉讼的本意在于获得执法机构、监管机关、行业协会等对判决的认同,以利于对判决的执行提供监督和保证,而完全依赖于受害人的控诉可能导致判决和执行的扭曲,不利于竞争秩序的建构。
第三,在必要时可创设临时的自身机构,如特别主管,以纠正任何代表的不公正。特别主管是一种作用广泛的机构,但他们的重要作用之一是行使代表权。[7]虽为法院所创设,但特别主管作为一方,有时能够表达关于责任和救济等参与者在诉讼中不大可能表达的内容。[8]
(四)救济阶段
从一般救济的角度看,争议解决模式关注的是已经发生了的、既存的事实,如交易或是事件。救济被用于纠正或制止某些孤立的事件,诉讼的重心往往在于作出判决。诉讼严格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戏剧结构:开头、中段和结局。只有在被告顽固不化的案件中,救济阶段才会加长,比如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顽抗者的抵抗在大部分案件开始时都未被考虑为不可缺少的部分。
而反垄断秩序建构诉讼不仅关注已发生的事实,更关注这一事实发生的场域——相关市场及其国内外发展趋向,以及这一事实对相关市场竞争的未来影响。因而救济程序虽有开头,也可能有中段,但几乎没有结尾。它包含了法官、执法机关、监管机关、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长期和持续的关系;它不仅关心已有的救济的执行,而且更重视救济自身的调整。它的任务重心不是明确谁对谁错,也不是计算损害的数量,而是消除威胁理想的有效竞争价值实现的现状。在一些可能解构组织的领域,如在非法合并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中,准许拆分企业可能是可行的选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如限制竞争协议以及我国的行政垄断案件中,这种选择就不可行。这一救济完全建立在法院对国家产业政策、现行市场结构和有效竞争的认识上,其目的在于尽可能消除限制竞争行为对有效竞争价值的威胁,法院的裁判权也随着威胁的存在而持续。
经营者和执法机关对于市场行为认识的局限,以及经营者通过重新建立曾经存在的权利关系以适应干预的能力,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系列的干预—周而复始的辅助改进的循环。长期的监督和监管关系在法院、执法机关、其他公共组织和经营者之间产生。执法、司法必须受到监督,市场竞争行为必须受到监管,并且新的救济方式被用于保证经营者的行为方式在反垄断法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法官为有效实施救济甚至可以设立新的机构,如特别主管,以辅助这些职能的实现。
从特定救济的角度来看,纠纷解决诉讼以特定错误行为为前提,这些救济是回溯性的,或者说是指向过去的,要求针对被告行为造成的既有损害依客观标准作出评价性的判决。然而秩序建构诉讼中的救济有时并不以错误行为为前提,更多的是面向未来,对被告行为对未来市场竞争的不良影响依预期作出评价性判决。因而,在反垄断诉讼最为发达的美国,其救济方式多是禁令,[9]它不需要像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是刑事诉讼中那样对“错误行为作出判决”。禁令是面向未来的。秩序建构诉讼致力于根除现有的对竞争秩序的威胁,而禁令是法院发布指令完成这一任务的正式机制。
五、结论
反垄断法滥觞于19世纪末,勃发于20世纪中,完善于20世纪90年代。在这一时期,科技革命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引起社会分工,社会化不断加深,社会经历着从机械的个体社会向有机整体社会的转化。因而,反垄断法所规制的限制竞争行为,是有机整体社会中的有害行为。这意味着,必须以生物学的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思考这种行为的社会影响。
以有机整体主义的观念来看,行为者直接损害的是其本身处于其中的社会整体—一种所有竞争者与消费者互动所形成的竞争关系状态,其对具体竞争者和消费者造成的损害是限制竞争的结果。这决定了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而不是竞争者及其相关的个人(消费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对竞争的保护也反射性地保护了竞争者和消费者。同时,市场是由众多参与者互动形成的,且是开放的,这决定了垄断行为造成的损害具有主体的不确定性、客体的动态性以及损害的不确定性、可延伸性和不可计量性、非自然性(法定性)、难以补偿性和难以恢复性等特性。可见,垄断行为是一种社会性风险行为。对于风险行为,现代法往往以事前的规制预防为主,反垄断法属于社会经济规制法。
反垄断法作为规制有机整体中限制竞争行为的社会经济规制之法,其基本价值是对竞争秩序的保护,这决定了反垄断诉讼的价值是建构竞争秩序而不是解决纷争,因而反垄断诉讼属于一种新型的诉讼:秩序建构诉讼。对此诉讼不能以既有的以保护个人权利、解决争议为圭臬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争议解决模式来思考,而应借鉴20世纪50年代以来兴起于社会法(环境法、劳动法等)及宪法的、具有整体主义思维的公益诉讼及宪法的结构诉讼所取得的成果,构造反垄断诉讼多方参与的秩序建构诉讼模式,形成在法院积极组织下、由代表社会利益的专门机关及各种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多元参与制度。
注释:
[1]有关司法案例可参见Brunswick Corr. v. Pueblo Bowl-O-Mat,Inc.,429U.5.477(1977);同时参见Cargill,Inc. V. Monfort of Colorado,Inc.,479U.5.104(1986)(对于依据克莱顿法第16条寻求禁令救济的私人案件适用反垄断损害规则);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253F.3d34(D.C.Cir.2001)(将Brunswick案适用于私人垄断案件,但是即使政府也“必须证明垄断者的行为损害了竞争,而不仅仅损害某一竞争者”)。基本理论可参见前引[8],盖尔霍恩等书,第450页。这一观念也被欧洲、日本等许多国家所接受。但对这些国家,这一观念只有理论意义而没有实践价值。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没有多倍赔偿制度,且反垄断诉讼的举证难度远远超过侵权之诉,因而原告更愿意把一些反垄断损害赔偿之诉以侵权之诉提起。
[2]参见我国反垄断法第38条,日本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平交易的法律第45条,加拿大竞争法第9条,韩国规制垄断与公平交易法第49条第2、3款。
[3]这种责任制度源于美国,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也有如此规定,如我国台湾的公平交易法,但多数国家的反垄断法中没有这种规定,我国反垄断法也没有。不过,近年来国际反垄断法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这种责任制度对于促进私人实施反垄断法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主张在反垄断法中设立这一责任制度,但为了防止滥诉,一般不主张美国式的刚性的三倍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这种制度是一种利用私人受害者易于获得违法行为的信息的优势,激励私人提起诉讼维护公共利益的机制。其中私人从诉讼中获得的相当于自身所受损害的部分属于赔偿,而超过损害的部分则是社会对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给予的报酬。
[4]告发人诉讼是英美法国家实行的一种诉讼制度,它允许个人或实体代表政府起诉不法行为人。在提起告发人诉讼后,如果胜诉,则该私人告发人可获得对赔偿额的分配。
[5]在当今由私人提起的反垄断诉讼领域,原告资格的取得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的以已经遭受损害为标准,另一种是德国的以具有受害危险为标准。就司法实践看,美国的标准具有不断放宽的趋势,而德国标准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
[6]目前在私人提起的反垄断诉讼中,还没有哪个国家对私人和解的权利作出限制。美国1974年反托拉斯程序和处罚法(the Antitrust Procedures and Penalties Act of 1974)规定,政府在反垄断诉讼中的和解协议应该向社会公众公布,并由法官决定司法部的和解协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这一法案其实已经意识到让谁以一种权威性的方式代表美国利益发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还是把这一权力授予法官,而法官在决定是否批准和解协议时实际上不受任何既定规范的指导。“公共利益”的标准事实上要求法官在作出决定时考虑那些诸如公众看法和有效分配诉讼资源的非司法性因素。一般认为,执法机关是公共机构,代表公共利益,但政府执事者毕竟不是天使,因而对和解的效力予以司法控制是必要的。而对于具有很强公益诉讼特性的私人反垄断诉讼,笔者认为也应该对和解予以“公共利益限制”,否则可能产生有利于私人受害者而不利于社会的和解协议。
[7]See Geoffrey E. Aronow,The Special Master in School Desegregation Cases:The Evolution of Roles in the Reformation of Public institutions Through Litigation ,7 Hastigs Constitutional Law Quarterly742(1980).
[8] [美]欧文·费斯:《如法所能》,师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9]禁令是商业秘密侵权案中最重要的救济措施。在反垄断法中,由于竞争秩序一旦被破坏就难以恢复,因而美国反垄断诉讼常常使用禁令。签发禁令涉及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法院应在权衡原、被告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