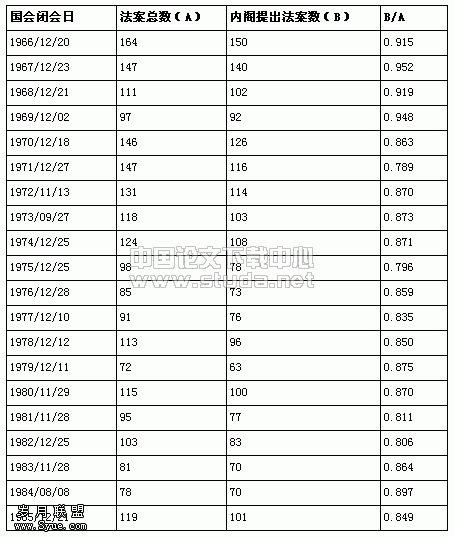论我国《海商法》托运人定义的不足
作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重要的一方,我国《海商法》关于托运人的规定历来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42条给托运人下了定义,即“托运人,是指:1、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2、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 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托运人包括两种人:第一,是指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即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这是托运人本来的含义。托运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可以是本人亲自与承运人订立,也可以委托他人充当自己的代理人,以托运人的名义,或者为托运人,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第二,是指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简言之,指将货物交给承运人的人。因此,托运人也包括并未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而只是将货物交给承运人的实际托运人。根据我国《海商法》第42条第3款的规定,货物买卖合同的卖方基于将货物交给承运人这一行为而成为托运人。同样,实际托运人可以亲自将货物交给承运人,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以其名义或为其将货物交给承运人。
我国《海商法》第42条关于托运人定义的规定,是借鉴了《汉堡规则》的规定,尽管二者在用词上略有不同,但基本含义却并没有什么重大差别。根据我国《海商法》第42条的规定,托运人有两种定义,它们之间用分号分开,给人的印象是:托运人可以是一个,也可以同时有两个,需要在实际业务中加以鉴别。而《汉堡规则》在规定两种托运人定义的条文之间使用了“或者”(or)一词,给人的印象是:托运人只有一个,但需要在每次运输中加以鉴别。《汉堡规则》之所以给托运人下了这样的定义,可能是基于如下考虑:第一,突破传统的合同法理论,将实际交付货物的人纳入托运人的范畴,避免使运输合同或相关被不恰当的规避;第二,通过运输合同之外的其他合同来明确买卖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且买方可通过受让提单而实现其权利,这就解除了承运人为何人履行运输合同的担心,只要交付的货物符合运输合同即可运送;再次,将卖方记载为托运人有利于卖方通过保留货物权利而保护货款请求权,这种服务于贸易的安排会促进贸易的开展;最后,卖方通过提单记载成为由提单所证明的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可以直接承担支付运费、申报货物等义务与责任,有利于承运人权利的保护。但这么规定,在给贸易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了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在FOB价格条件下,买方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而卖方将货物交付承运人,那么到底其中一方是托运人还是双方都应视作托运人?FOB价格条件下,卖方作为托运人,其权利义务如何确定?当FOB卖方实际将货物交予承运人,但其名称却没有载入提单“托运人”一栏,此时其法律地位又将如何确定?由于我国《海商法》基本采纳了《汉堡规则》的托运人的定义和其他相关条款,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法学家早在20年前就预见到的复杂问题。[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正式实施后,因为《合同法》并没有给托运人下定义,根据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在特别法没有作出不同规定时,《合同法》总则与运输合同一章的规定适用于各种运输方式,因此在海上货物运输领域也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以下问题:
1、《合同法》第308条:“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当应当赔偿承运人因此受到的损失。”问题是:此项权利由FOB货物的买方还是卖方享有,如果买卖双方都向承运人提出请求,承运人如何处理?
2、《合同法》第319条:“多式联运经营人收到托运人交付的货物时,应当签发多式联运单据。按照托运人的要求,多式联运单据可以是可转让单据,也可以是不可转让单据。”问题是:在多式联运的情况下,多式联运经营人是否必须将多式联运单据签发给FOB货物的卖方?究竟应该按哪个托运人的要求签发多式联运单据?
3、《合同法》第320条:“因托运人托运货物时的过错造成多式联运经营人损失的,即使托运人已经转让多式联运单据,托运人仍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是:当因为FOB货物的卖方的过错造成多式联运经营人损失的,FOB货物的买方是否需要对此种损失承担责任?
近几年来,我国已发生了多起与托运人概念相关的海事诉讼案,对同类型的案件,国内的司法判决往往差别很大,归根到底在于我国《海商法》关于托运人的定义存在缺陷。
一、 托运人定义的由来
《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中没有关于托运人定义的规定。《海牙规则》第1条定义中规定:“承运人”,包括与托运人订有运输契约的船舶所有人或承租人。《海牙——维斯比规则》没有对承运人的概念做出修改。虽然《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没有给“托运人”下定义,但由于它们规定承运人是指和托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人,因此也可以理解为公约认为托运人是指和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人。
《汉堡规则》是第一个对托运人下定义的公约。在《汉堡规则》中设置托运人的定义的提案是由突尼斯和奥地利提出的,提案提出后引起了激烈的意见冲突。以印度为首的多数家认为,明确限定作为运输合同权利、义务主体的托运人的定义是必不可少的;而日本、挪威等发达国家则认为,由于公约中和以前的《海牙规则》等一样,托运人根据情况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被使用的,设置定义反而会造成实体规定解释的困难。对提案投票的结果是27票赞成,25票反对,4票弃权。决定设置定义的提案虽勉强通过,但具体条文案怎么也得不到半数支持,经过特别工作组反复工作后,才最后通过。
国际公约是一种妥协的产物,《汉堡规则》虽然最后设置了“托运人”的定义,但对定义条文如何解释却留下了很大的余地。如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发运货物既然是两种标准,是同时符合两种标准才能称为托运人,还是只要符合标准之一就能称为托运人?如果是只要符合标准之一就能称为托运人,会不会根据两个标准会有两个托运人?这两个托运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汉堡规则》本身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公约的起草者希望各国根据自己的国内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二、 我国《海商法》托运人定义的不足
笔者认为,根据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国《海商法》关于托运人定义规定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两类托运人之间的关系混乱
《海商法》关于托运人的定义在两者之间并无任何联结词,因此,第42条所定义的两种托运人之间的关系不得而知。国内学者通常认为,《海商法》中有关“托运人”的两个句子为选择关系,即只需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即可视为《海商法》下的托运人[2]。根据这个观点,在CIF和CFR价格条件下,一般只存在一个托运人,而在FOB价格条件下,则同时存在两个托运人。但这样解释,同样面临着如何划分两种托运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的难题。《海商法》所定义的两种托运人,其托运人地位的取得是基于不同的原因——交货或者缔约,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应该有所区别,但《海商法》却不加区分,仅笼统的规定了托运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这样必然导致两类托运人的权利、义务发生重叠,易引起当事人之间的商务纠纷并造成司法审判困难。
2、定义的表达语义重叠,晦涩难懂
《海商法》对托运人下定义时,无论缔约托运人还是实际托运人都规定了三种情况:①本人;②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③委托他人为本人。从角度来看,“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指的就是托运人的代理人的情况,而这种情况从严格意义上讲,本身就包括在托运人的概念中,以托运人的代理人的身份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等同于托运人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其法律后果是相同的,产生的责任也同样由托运人来承担。因此取消“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对托运人或实际托运人的定义并没有什么影响。
如何理解“委托他人为本人”目前仍有争议[3],笔者认为,从字面看,“委托他人为本人”应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从事所受托事项,此时构成直接代理,与托运人定义中的“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构成语义重复。第二种情况是受托人仅表明自己代理人的身份,而没有披露谁是被代理人,此时应构成隐名代理[4],适用《合同法》第402条[5]的规定。在《合同法》实施以前,《民法通则》关于代理的规定仅限于直接代理[6],《合同法》第402条突破了《民法通则》中代理仅限于显名代理的规定,据此规定,隐名代理的效果应该和显名代理的效果一致[7]。第三种情况是受托人直接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所受托的事项,根本不表明自己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托人,此时应适用《合同法》第403条和第414条的规定。《合同法》第403条第1款实际上确立了委托人介入合同的规则,委托人介入的效果,大体上等同于未披露委托人的代理转化为披露委托人的代理,在这种情况下,托运人与实际托运人是确定的,这与《海商法》的立法意图一致;《合同法》第403条第2款的规定实际上确立了第三人的选择权,此时,托运人还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究竟谁是托运人取决于第三人的选择,这与《海商法》的立法本意并不一致。《合同法》第414条的规定[8]仅限于贸易活动的范围之内,而不适用于运输。可见,《海商法》第42条第3款托运人定义中规定的“委托他人为本人”应该仅指《合同法》第402条和第403条第1款规定的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9]尽管最终没有实施,但对于理论探讨来说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第11条规定:“委托他人为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承运人,不管受托人是否以委托人名义办理委托事项,该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托运人均为委托人本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办理委托事项的,受托人与委托人对托运人的义务负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原则上委托人本人是托运人或实际托运人,在受托人以自己名义办理委托事项时,则受托人与委托人对托运人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与《合同法》委托合同的规定略有不同。前已述及,《合同法》第403条第2款实际上确立了第三人的选择权,即此时责任主体是单一的,不存在连带责任。最高院征求意见稿对承运人的保护较《合同法》和《海商法》规定为高。
《海商法》颁布时,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代理仅限于直接代理,对于实践中存在的间接代理问题,则要通过两个合同关系来解决。《海商法》之所以规定了“委托他人为本人”其意图就是想绕过代理人[10],通过法律直接赋予被代理人主体资格来解决承运人与托运人和实际托运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样的规定,在当时的立法背景下具有先进性,但同时也给托运人或实际托运人的识别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合同法》生效后,我国法律对代理制度的规定更加趋于完善。此外,《合同法》第403条第2款的规定也有一定的道理,毕竟相对而言,善意第三人承运人的权利更应受到保护,此时赋予其选择权也是公平合理的。因此,建议取消《海商法》第42条中的“委托他人为本人”。
3、定义用语不规范
“委托”这一用语在《合同法》生效以后有了特定的涵义。《合同法》在第21章对委托合同做出了专门规定。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合同法》委托合同的规定与《海商法》托运人定义中“委托”的内涵并不一致。从《海商法》的立法意图来看,其托运人定义中的“委托”更应该理解为一种广义的代理关系。委托与代理是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11]。因此在《合同法》实施以后,《海商法》在给托运人下定义时,应回避这些用语,以免产生歧义。
4、定义范围涵盖不够完整
《海商法》第42条第三款规定的第二种托运人是“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承运人的人”,实践中存在很多将货物交给实际承运人的情况,超出了托运人概念所涵盖的范畴,此时将货物交给实际承运人的人能否取得托运人的地位则取决于实际承运人是否以承运人的代理人的身份出现。为了保护发货人的利益,建议增加“货物交给实际承运人的,视为交给承运人”的规定或将实际托运人定义为“将货物交给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的人”。
三、 国际上相关立法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作为传统商法之一的海商法也进一步出现国际统一的趋势。纵观国际上关于托运人定义的规定,总体上来说共有以下几种模式:
1、单独式
采取这种立法模式的国际公约或相关国内法,一般没有托运人的定义或仅将托运人定义为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人。
《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中没有关于托运人定义的规定。《海牙规则》第1条定义中规定:“承运人”,包括与托运人订有运输契约的船舶所有人或承租人。虽然《海牙规则》没有给“托运人”下定义,但在实践中一般认为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契约的人为托运人。英国1924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将《海牙规则》作为该法的附件生效。此外还有不少国家或者参加了《海牙规则》,或者将《海牙规则》直接作为国内法的一部分,或者依据《海牙规则》的精神,另行制定相应的国内法。《海牙——维斯比规则》没有对承运人的概念做出修改。至今为止,参加这两个公约或者与采用这两个公约基本一致的立法的国家仍居主流地位[12],可见,在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中,托运人仅限于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人。
《1991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国际商会多式联运单证规则》第2条定义中规定:“托运人”是指与多式联运经营人签订多式联运合同的人。此规定也将托运人限定为缔约托运人,排除了将货物交给承运人的人成为托运人的可能性。
《日本1957年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第2条定义第3款规定:本法律上所谓“托运人”指委托前条运输的租船者及发货人。《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2条定义第(3)项则认为:本法所称“托运人”是指承租人或委托承运人完成前条规定的海上货物运输的人。其发展方向是将托运人限定为与承运人有合同关系的人。
《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第3条第(六)款:“托运人”,是指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人。托运人限定为缔约托运人。
2、并列式
采用这种立法模式的国家主要是。这种立法模式突破了合同相对性的限制,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采用FOB贸易术语的情况下,运输合同将同时存在两类托运人。
中国:《海商法》第42条规定:“托运人”,是指:1、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2、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两类托运人之间没有任何连词,通常认为,《海商法》中有关“托运人”的两个句子为选择关系,即只需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即可视为《海商法》下的托运人[13]。
3、选择式
《汉堡规则》、《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即采用这种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也规定了两类托运人,但这两类托运人不能并存,非此即彼。
《汉堡规则》第1条定义中的第3项规定:“托运人”,是指由其本人或以其名义或代其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契约的任何人,或是由其本人或以其名义或代其将海上货物运输契约所载货物实际提交承运人的任何人。对比我国《海商法》和《汉堡规则》中托运人的定义,二者的区别仅在一个“或”字。日本研究《汉堡规则》的知名专家樱井玲二认为:“本公约中,‘托运人’一词,根据情况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被使用的。在提单实务中,托运人是信用证中的受益人,通常即贸易合同中的卖方。因此,在装货港其与把货物交给承运人的人相一致。另一方面,与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人,在以CIF条件为基础的贸易合同的情况下,无疑是卖方,而在以FOB条件为基础的贸易合同的情况下,便会产生这个人是不是买方的疑问,即这个人是不是在卸货港从承运人那里提取货物的人。结果,在具体的事例中,究竟谁相当于托运人,这除非是在规定托运人责任的条文中(例如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由他们的解释来决定,再无其他办法。”[14]也就是说,这一“或”字,表明了两种托运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对于一项具体的义务,仅存在一个相应的托运人,而具体这一托运人到底是谁,则要结合《汉堡规则》的其他条款来识别。
《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第I部分,第1条定义中规定:“发货人”是指其本人、或以其名义、或其代表同多式联运经营人订立多式联运合同的任何人,或指其本人、或以其名义、或其代表将货物交给多式联运经营人的任何人。尽管采用的术语是“发货人”,但此定义基本与《汉堡规则》中“托运人”定义如出一辙。
4、分立式
《瑞典1994年海商法》和《芬兰海商法》采用了这种模式。这种立法模式将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与将货物交付承运人的人分别定义,并明确了各自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瑞典1994年海商法》在第四部分运输合同第13章件杂货运输的介绍性条文第1条中规定:托运人(sender):指与承运人订立海上杂货运输合同的人;发货人(shipper):指将货物交付运输的人。第14章租船一般规定第1条定义:发货人(shipper):将货物交付装运的人。首创将《汉堡规则》规定的两种托运人分别定义的立法例,权利义务比较清晰,值得借鉴。《芬兰海商法》将《汉堡规则》中的两种托运人分别命名为“合同托运人”和“实际托运人”,并将前者定义为“为海上运输货物与承运人订立合同的任何人”,将后者定义为“提交运输货物的任何人”。《芬兰海商法》的做法与瑞典基本一致。
四、 建议及结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海事立法又趋于活跃。、英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瑞典和我国地区都通过了或修订了本国或本地区的《海商法》或《海上货物运输法》。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在1999年9月24日向参议院提交了《美国1999年海上货物运输法(草案)》;而受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委托,国际海事委员会也于1998年2月提交了《CMI运输法(草案)》以供各国海商法协会讨论,并且几易其稿,在2002年1月8日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与国际海事委员会的联合名义推出了《UNCITRAL/CMI运输法最终框架文件》。
CMI运输法草案第一稿第1.5条规定:托运人,指契约托运人或发货人;第1.6条规定:契约托运人,指和契约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人;第1.7条规定:发货人,指承运人从其手中接受货物的人。即在第一稿中,采取了用托运人概念涵盖了《汉堡规则》所规定的两种情况,然后分别定义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在二者权利义务相同的情况下,用托运人替代,在二者权利义务不同的地方分别定义。无疑,这一立法例对于明晰两种托运人各自的权利义务很有好处,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CMI运输法的第二稿第1.4条中,却将托运人仅限定为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人,而没有定义将货物交给承运人的人即发货人的地位。更富戏剧性的是在CMI运输法最终稿中又分别定义了发货人(consignor)和托运(shipper)。最终稿第1.3条规定:发货人指将货物交给承运人运输的人;第1.19条规定:托运人指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人;第7.7条规定:在一方虽不是第1.19条所称之托运人但为合同条款识别为托运人的情况,如果他接受了运输单证或记录,则此人(a)承担本章和第11.5条规定的托运人的义务与责任,并且(b)有权享受本章和第13章规定的托运人的权利和免责。并且在最终稿条文的说明中,还认为发货人可能包含托运人。从CMI运输法草案三稿的变化来看,尽管要将托运人与发货人各自的权利义务区分开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CMI运输法委员会还是倾向于将《汉堡规则》所定义的两种托运人分别定义,区分其各自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美国1936年COGSA》没有明确规定托运人的含义,但一般认为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人为托运人[15]。《1999年海上货物运输法(草案)》在第2条定义中的第(9)项规定:“托运人”,是指:(A)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与契约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人;和(B)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付给运输合同项下的承运人的人。美国99年COGSA(草案)的规定扩大了托运人的含义,而且该定义的解释与我国《海商法》之相关规定一致,但不同于《汉堡规则》关于托运人之相关规定[16]。
值得注意的是,《CMI运输法最终框架文件》的合作起草者Michael Sturley教授也正是《美国1999年海上货物运输法(草案)》的主要起草者。《CMI运输法框架文件》在托运人定义的问题上几经周折,最终却采用了将合同托运人与发货人分别定义的方式,这也必将对《美国1999年海上货物运输法(草案)》的讨论产生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托运人定义上采用分立式是未来海商法的趋势,将托运人区分为“合同托运人”与“实际托运人”是适当的,这样规定能够更好地弥补因《汉堡规则》规定不完善带来的困境,故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修改我国《海商法》时,可以借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海商法与CMI运输法最终框架文件的做法,将我国《海商法》中明确规定“合同托运人”与“实际托运人”的概念,并在具体条文中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1] 参见郭春风:《论对海商法托运人定义及相关条款的修改》,《中国海商法年刊》1997年。
[2] 参见傅旭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诠释》P74,人民出版社;姚红秀等:论我国《海商法》下“托运人”的认定,《中国海商法年刊1996》P35;另郭春风认为在FOB价格条件下,根据《海商法》就同时出现了两个托运人,可以推出他也认为有关“托运人”的两个句子为选择关系,参见郭春风:论对《中国海商法》托运人定义及其相关条款的修改,《中国海商法年刊1998》P13。
[3] 从傅旭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诠释》第74-75页的写法来看,似乎“委托他人为本人”仅限于直接代理和《合同法》第402条规定的情况。
[4]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订立合同,同时第三人又知道代理关系的存在,这实际上就构成了隐名代理”,参见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第34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 《合同法》第402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与第三人的除外”。
[6] 《民法通则》第63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7] 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第34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8] 《合同法》第414条:“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9] 1994年7月版,当时《合同法》还没出台,《民法通则》对代理的规定仅限于直接代理,即最高院草案的规定已经突破了《民法通则》关于代理的规定。
[10] 此处代理取广义上的含义。
[11] 参见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P338-339,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2] 参见杨良宜著:《提单及其付运单证》第687-68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3] 参见傅旭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诠释》P74,人民出版社;姚红秀等:论我国《海商法》下“托运人”的认定,《海商法年刊1996》P35;另郭春风认为在FOB价格条件下,根据《海商法》就同时出现了两个托运人,可以推出他也认为有关“托运人”的两个句子为选择关系,参见郭春风:论对《中国海商法》托运人定义及其相关条款的修改,《中国海商法年刊1998》P13。
[14]樱井玲二认为,应结合《汉堡规则》第13条和第17条关于托运人的责任的规定来识别在具体的事例中,究竟谁相当于托运人。参见樱井玲二著《汉堡规则的成立及其条款的解释》p268,对外贸易出版社。
[15]参见司玉琢等:《美国99年COGSA的主要变化、影响及我国对策分析》,《中国海商法年刊1999》P376,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16]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