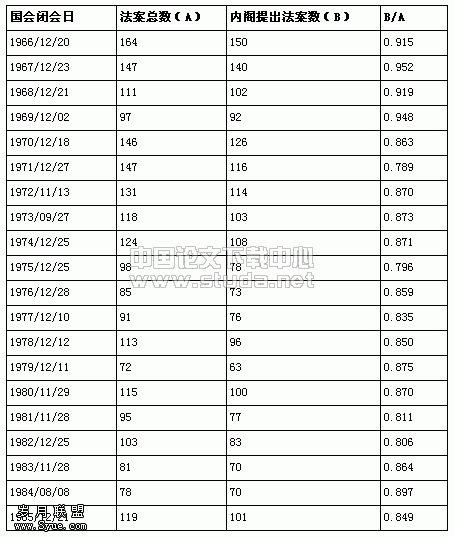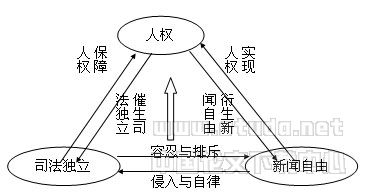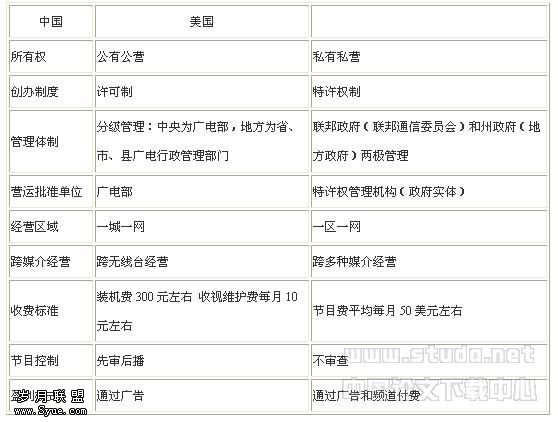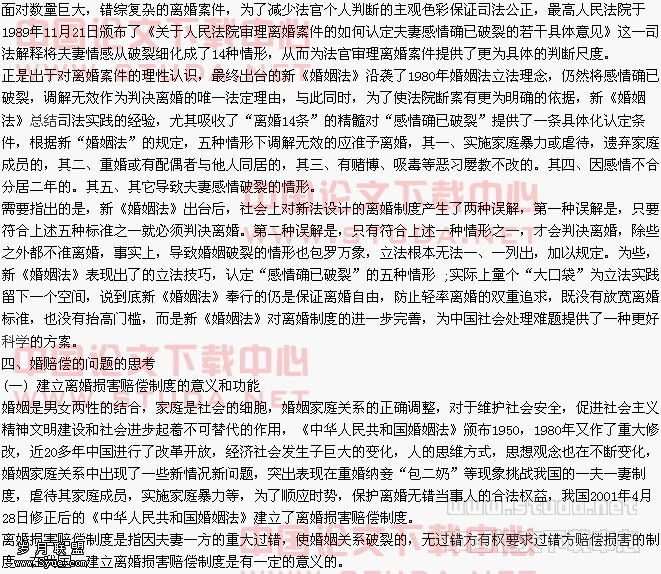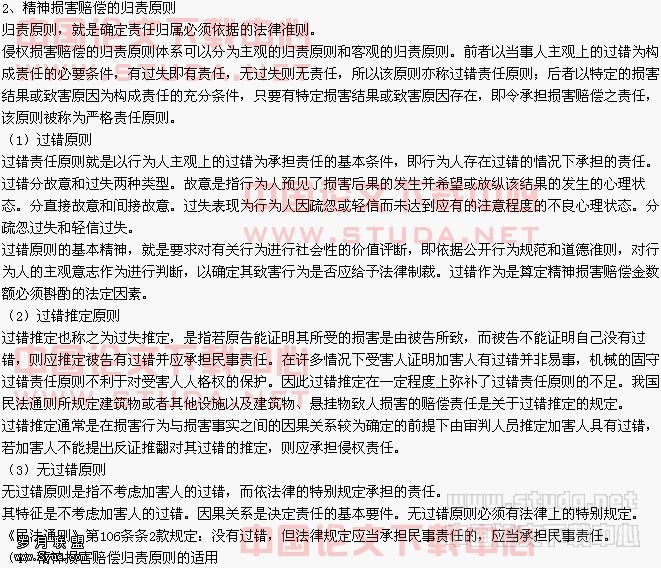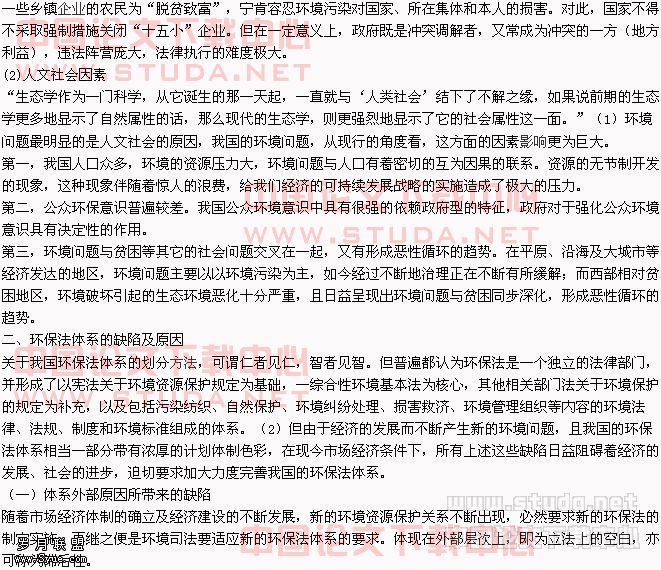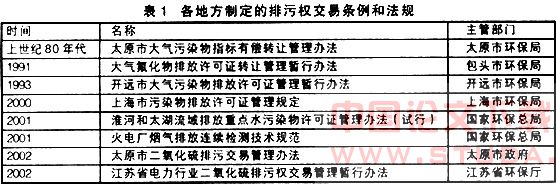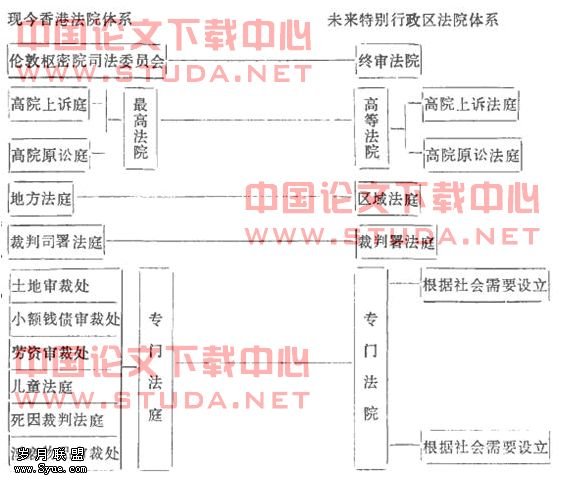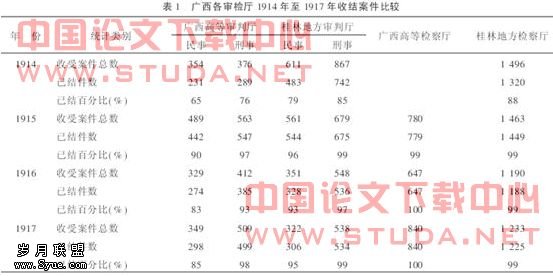行政计划诉讼问题研究
内容摘要:与行政计划相关的诉讼大致可以分为计划的具体内容不服的诉讼、对计划的制定行为不服的诉讼与对计划的变动行为不服的诉讼。对公民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计划不发生诉讼问题,对公民权益发生实际拘束力和直接影响的计划可能涉及诉讼问题;德国与地区确立"集中事权效力"的行政计划裁决,行政计划制定行为可被起诉,大陆尚不具备此制度基础;依据信赖保护原则,计划变动行为可被起诉。
关键词:行政计划 诉讼 实际影响 信赖保护
引言
行政计划很早就作为一种国家管理社会的手段而存在[①],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是在法治社会中,在国家行政活动的范围和内容不断扩大化和多元化的情况下,方才日益突现出来的。现代行政在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建设、文化等众多领域内很大程度上已经依靠有计划地制定各种法规和规划,以实现行政的前瞻性和有序性。"基于行政计划而展开的计划行政,被称为现代行政的重要特色之一。"[②]
毫无疑问,在众多的计划形式中,以城市规划为典型。城市规划所涉及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尤其是有关土地利用和环境保护上。因此,本文所要考察的行政计划诉讼问题将主要以城市规划为背景展开。
行政计划的出现和广泛运用难免会在现实当中引发各种纠纷,通常解决纠纷的渠道有行政机关自我解决,或由权力机关进行处理和由司法机关进行裁决等形式。限于本文的主题,将主要就行政计划的诉讼救济进行介绍。对于行政计划,一般而言,有两种意义上的理解。一种是结果意义上的行政计划,即计划行为所产生的正式书面文件,另一种是行为意义上的行政计划,即与结果意义上的行政计划相关的各种行为的动态的整个过程。根据学者的多数见解,行政计划的行为过程往往分为(1)计划草拟(构想);(2)计划拟定(选定);(3)计划公开(发布);(4)行政确定(核定);(5)计划实施与变更。[③]以产生结果意义上的行政计划这一时点为界,又可以再细分为实施行政计划的制定过程和实施行政计划后的变更过程两个时段。相应地,与行政计划相关的纠纷也可以区分为对计划的具体内容的不服和对计划制定行为的不服和对计划变动(包括中止和变更,两者因为所适用的规则多数情形下是相同的,故本文进行合并讨论)行为的不服等三种类型。三者纠纷的诉讼解决方式各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下试分述之。
一、对行政计划具体内容不服的诉讼救济
行政计划类型纷繁复杂,其具体内容也同样呈现这一特点。因此,对于行政计划具体内容不服的诉讼问题,并不能轻易地下一个简单的结论,而应加以区别处理。
行政计划具体内容有无对人民发生法的拘束力,将在诉讼法上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对相对人不直接产生法的拘束力的行政计划,例如国民发展计划,经济建设计划等政策性计划,或者政府外贸部门公告的外销景气及应对方案之类的建议性(指导性)的行政计划,由于对于人民权益并不产生直接影响,所以一般不能发生诉讼上的问题。而只有那些对公民权益产生实际拘束力和直接影响的行政计划,才有可能引发讼争的问题。
(一)从国外的一起相关案例说起
在日本曾经发生过这样一起案件。该案的被告东京都于1939年间,为在大田区内设置垃圾焚烧场购买了土地,但一直没有着手建设。1957年5月30日,东京都议会通过了可以设置这个垃圾焚烧场的计划案,于同年6月8日,把其内容登载在《政府公报》上。其后,东京都和西松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缔结了建筑工程承包契约。因此,X等(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居民8人)认为,东京都政府选定焚烧垃圾场的位置,从环境卫生来说是最不恰当的地方,违反清扫法6条,以及该法施行令2条1款1项,所以是无效的行政处分。于是,对东京都政府提起请求确认无效的诉讼。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结果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东京都的决议,在东京都公报上登载、被告与西松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工程承包契约等一系列行为,并没有直接以公民为对方,也没有直接影响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因此,这些行为不是作为行政诉讼对象的行政处分。"[④]
(二)对该案例的一种评述
日本法院在本案中体现了其一贯的立场,即认为只有行政处分[⑤]才能提起诉讼。事实上,它也是各国司法制度的共同做法,而对认定行政处分的要件规定一般有三:其一,具有公权力性。即该行为首先必须是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其二,发生具体的法效果。所谓处分,必须是对公民产生法效果的事项。即使在事实上对公民的权益有着重大影响的行为,形式上不具有法效果也不能承认其具有处分性。其三,所发生的纷争具备的成熟性。一项行政行为,只要没有到达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最终决定的所谓终局阶段,就被认为该纷争尚未成熟,不予受理。[⑥]
对照上述三项要件,容易引起对行政计划提起诉讼的障碍的主要是要件二和要件三。因为行政计划在时间上具有动态展开的要素,内容上具有非完结性和留有一定的余地[⑦],所以一般是预定要由后续行为来将权利义务关系具体化。基于上述的特点,抽象的基本计划一般不被认为是对特定个人的具体处分,因而欠缺诉讼的成熟性。[⑧]
但是,对于具体的事业实施计划,则有人认为,实质上它决定着有利害关系者将来的权利关系,并且,若公共事业的实施有非法的地方,早期纠正违法行为,合法地实施有关事业,无论是对于国民来说,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现在多数日本学者认为,也许还不能承认对抽象的基本计划提起诉讼,但当怀疑具体的事业实施计划有违法性质时,应该允许提起诉讼,以谋求阶段性疑问的解除,然后再重新开始公共事业的实施。从这种观点出发,下级法院的判决中,也已经出现了一些承认行政计划可诉性的判决。[⑨]在台湾地区,法院对行政计划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放宽审查标准的过程。
但是纷争成熟性的认定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最早在美国,认定纷争成熟性的标准除内容外,采取了严格的形式标准,即所指控的行政行为必须是"正式的",如正式决定、正式裁决等。如处在非正式行为阶段,则视为司法审查时机不成熟。六十年代以后,成熟原则的要求逐渐放宽,审查标准也改为"对当事人造成了不利影响"。即使行政行为尚未变成正式行为,只要它已经给当事人造成了某种不利影响,[⑩]法院即可受理对这种行为的审查诉讼。可见,所谓的纷争成熟性原则更多的是出于政策上的考虑所作的安排。[11]
(三)我国的相关诉讼实践
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行政程序法或计划法对行政计划内容本身能否提起诉讼,主要还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对"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即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3月8日公布)第3条的规定,它是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而行政计划内容上多数情况下都不是针对特定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所以我国目前还不能针对行政计划行为直接提起撤销之诉。司法实践中针对某项规划不服的,相对人也往往是针对行政机关根据该规划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12]
2002年,温州发生了一起与政府的建设规划有关的行政诉讼。该案的一审原告永嘉县瓯北镇浦西村百余位村民状告瓯北镇人民政府和永嘉县规划建设局违反《城市规划法》,侵犯了他们的通行权。事情的起因是2002年7月,该村的交通干道破土动工,村民们发现即将盖起的大楼,将把双塔路上的控制红线完全占据,把砻坊巷通往双塔路的出口完全堵塞。居住在巷子里的近百户村民,要想到双塔路就必须绕很远的路。村民们多次向镇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未果,遂将瓯北镇人民政府和永嘉县规划建设局告上法庭。而被告永嘉县规划建设局则辩称,他们是依法向瓯北镇政府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符合瓯北镇的总体规划。原告代理律师则认为,瓯北镇人民政府从1990年到现在的12年间,建设规划发生了5次大变动,平均每两年变动一次。处理这样一件涉及老百姓重大利益的公共事务,决策如此轻率随意,不符合群众的根本利益。[13]
这起发生在温州的"百余村民状告规划局讨要通行权"案,一审法院之所以能够受理,就是因为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是撤销规划建设局向镇政府颁发建设工程许可证的行为,而非经过多次变更的建设计划本身的内容。后者常常会被认为属于抽象行政行为,而不在受案范围之列。
二、对行政计划制定行为不服的诉讼救济
有鉴于对行政计划之事后审查可能性不大,而对受行政计划影响的相对人权益之保护又实属必要,所以各国行政法学界已经考虑对行政计划的制定程序进行事先的规范。日本在其1983年制定的《行政手续法要纲案》(此草案即第一次草案)中,特别针对与私人权利利益有直接关系之"土地利用规制计划"(第112条)及"公共事业实施计划"(第1122条)之制定进行程序性的规制。[14]
但是仅有程序上的规制,而没有规定行政相对人行政计划制定行为本身的不服,并不能对相对人提供充分的保护,也不利于督促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有鉴于此,不少国家或地区已经在其司法实践中承认其可诉性。一般认为,计划的制定(广义上理解,包括制定、修改和废止)属于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对计划制定行为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在德国,利害关系人对行政计划的确定行为不服,根据《行政程序法》第74条第一项的规定,适用有关正式行政程序中之决定和撤销的规定,所以相对人行政计划确定行为不服的,可以对其提起撤销之诉。[15]但是计划确定裁决行为以《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3条所规定的正式(听证)程序所作出的,由于该程序的要式形式和因此导致的缜密,对准备程序所提起诉讼是不予受理的。[16]台湾地区1990年的《行政程序法(草案)》第125条规定:"(不服确定计划裁决之救济方法)不服确定计划之裁决者,应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1993年的《行政程序法(草案)》第157条则规定:"不服确定计划之裁决者,得不经诉愿或其它先行程序,径行再诉愿或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德国和台湾都在立法上允许对行政计划制定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与它们在立法上规定了行政计划裁决的"集中事权"效力分不开的。集中事权就是由单一机关统筹依单一程序收件审查,其它机关会同审查,最后由统筹办理之机关核发一张执照,此一执照即为确定计划之裁决书。从德国行政计划裁决之实例来看,裁决书不是像一般行政处分书仅二、三页,而是一本汇整性小册,其中涉及各种许可与相应措施皆在此一裁决书内。[17]简单地说,集中事权效力就是以程序集中的方式处理达到决定集中的效果。
我国现行有关行政计划的法律,如《土地管理法》中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审批、调整、实施及应遵循的原则等作了规定,但这些都是封闭式的内部程序上的规定,基本上是将行政计划作为内部行政行为看待,对行政计划制定行为本身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还处于空白状态。如根据《城市规划法》的规定,行政计划的确定行为是通过上级行政机关的审批程序作出的,而与计划有关的许可程序则是另外进行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也是规划建设局以计划审批程序已经确定的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并对相对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后才作出颁发许可证的决定的。对照德国和台湾地区相应的立法例,具有"集中事权效力"的计划确定裁决实质上就相当于我国计划制定行为和许可行为的合二为一。可见,德国和台湾地区允许对行政计划制定行为提起诉讼的制度是不能单独加以移植的,只有在将来法律对行政计划确定行为赋予"集中事权效力",对计划制定过程作出如公开、听证、咨询等程序上的要求,法院也可以据此对计划制定行为的程序进行合法性审查之后,才可能具备移植行政计划诉讼制度的可行性。
三、对行政计划变动行为不服的诉讼救济
与行政计划相关的纠纷,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于计划的变动(包括变更或中止)所引发的。
计划从拟定到实施的过程常常是经年累月,其间不可避免地会因为、经济形势等发生了变化,而使当初的计划不得不变更或中止,可以说变更、中止是计划的"生理现象"。[18]但是在计划行政的背景之下,民众对自身的行为预期及其相应的安排常常就是以各种行政计划为基础的。例如在行政机关已经作出承诺给予协助完成某项行政计划的相对人以一定优惠待遇时,而相对人亦根据这一计划所提出的内容采取了相应的行为时,如果行政机关事后中止或变更该项行政计划,就会造成私人所投入的资本、劳力等付诸东流的不利后果。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有必要一方面对行政计划的变动施加一定限制,同时也赋予相对人相应的诉讼救济的权利。诉讼法上承认对行政计划变动的情形下相对人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其法理上的依据是现代法治国家所确立的信赖保护原则。"行政机关与人民事务往返之间,往往使人民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持续性产生信赖。当无明显的事由足以证明此信赖与公共利益相违背时,应对其予以适当保护。"[19]信赖保护原则自20世纪50年代在德国行政法中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原则出现以来,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行政法的承认,并加以运用。[20]根据信赖保护原则,对于以行政行为形式作出的行政计划,其中止或变更可以按照行政行为的废止规则进行。亦即因行政计划而受益之人民,对于该行政计划之存续已产生信赖,且于衡量比较废止该行政计划(即中止和变更两种情形,都是终止原行政计划向后的效力)所可维护之公共利益后,其信赖较值得保护时,则该行政计划即不得任意依职权撤销。
对于计划变更的诉讼救济,各国或地区的司法机关过去一直是采取消极否认的态度,只是在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观念确立和加强后才有所放宽。在台湾地区,行政法院1971年判字第738号判决认为,行政官署本于行政权作用,公告实施一种计划,对于一般不特定抽象之规定,而非个别具体之处置,自不得认为行政处分而对之提起诉愿。行政法院1976年裁字第103号裁定重申了这一观点。[21] 但是后来的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解释对这一观点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认为"主管机关变更都市计划,系公法上之单方行政行为,如直接限制一定区域内人民之权利、利益或增加其负担,即具有行政处分之性质,其因而致特定人或可得确定之多数人之权益遭受不当或违法之损害者,自应许其提起诉愿或行政诉讼以资救济"。[22]也就是说,对都市计划的个别变更属于行政处分(具体行政行为),从而相对人可以对其提起行政诉讼。而对都市计划进行通盘检讨后所进行的变更,如果不是涉及该区域内居民之具体权益,而仅涉及政府计划意旨的宣示,则多数学者认为应属于抽象行政行为。只有涉及人民具体权益,例如因土地使用分区管制之划分变更,而影响居民安宁、卫生,或被公共设施保留地,使地价大跌,则可认为是具备处分性。[23]
在德国,立法上所采取的做法虽与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做法有所不同,却也起到了异曲同工之效。具体做法是根据各种行政计划的形式和内容,判断公民的信赖状况,并赋予不同的计划保障给付权。具体包括:计划存续请求权、计划执行请求权、过渡措施和补救措施请求权以及补偿请求权。相对来说,德国的这种做法其涵摄的行政计划变动类型更为全面,对相对人的保护也似乎更为有力。[24]
前述发生在温州的"百余村民状告规划局讨要通行权"案虽已得到诉讼的救济,但笔者认为更为恰当而直接的做法应当是,对这类对于影响特定相对人的行政计划,在计划发生变动,以致其利益受到影响时,也可参照德国的法例区别情形由法律赋予相对人撤销变动或者取得损害赔偿的权利。
结语
行政计划在现代社会得到广泛运用,与人民生活关系至为密切。伴随而来的是众多需要法学家们加以关注的问题,不仅是行政法,尤其是行政作用法上的问题,它在宪法领域内的问题也是相当突出的。行政计划所产生的除了公民自由的限制,[25]还包括公民对计划制定的参与权、计划给付的分配以及对计划实施的信赖等等问题。因此,要真正对行政计划的法治化,避免具有广泛"形成自由"的计划裁量权被滥用,也有必要从宪法原则上加以考量。如合理界分中央与地方、立法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计划制定权,[26]充分保障公民和有关专业团体参与行政计划的制定过程,建立利益反映渠道和对话程序机制等。
事实上,行政计划与其他行政行为一样,其不良运用都会都能产生直接限制相对人呢的权利和利益的法律效果。在我国的行政实践中已经发生了不少因为行政计划引发的诉讼。但是,一方面国内学界对行政计划的法律属性、法律效果及其救济等都尚缺乏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上有关受案范围、起诉条件等方面规定的缺失,[27]造成行政计划相对人利益的诉讼救济相当薄弱。这应当成为寻求行政计划法治化的一个突破口。
Abstract: Therr are three kinds of proceedings relevant to administrative plan: proceedings against specific contents of plan, formulation of plan and change of the plan. Administrative plan without factual influence on rights of the private party can not be sued. Formu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lan can be sued in Germany and Taiwan District in China. Changes of administrative plan should be sued accordings to principle of confidence protecting.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Plan; Proceedings; Factual Influence; Confidence Protecting
[①] 如传统国家就已存在的财政预算,某种意义上讲也可属于行政计划的范畴。
[②] 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64页。
[③] 林明锵:《行政计划》,载翁岳生编:《行政法》,翰芦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676页。
[④] 对该案([日]1964年X等诉东京都案)的案情介绍和评述,参见胡建淼主编:《外国行政法规与案例评述》,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765页以下。
[⑤] 大致相当于我国行政法上所称的具体行政行为。
[⑥] 纷争的成熟性原则即司法审查时机成熟原则,其含义是指被指控的行政行为只有对相对人发生了实际不利影响并适于法院审查时才能接受司法审查。
[⑦] [日]和田英夫:《行政法》,倪健民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⑧] 在日本最高法院看来,基准性计划和行政指导一样,欠缺撤销诉讼的对象性。如不能通过撤销诉讼来攻击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⑨] 例如,日本札幌高等法院1971年12月23日关于土地改良事业计划决定的判决。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72页。
[⑩] 比如如果规章要求立即改变人们的行为规则,不服从规章则予以惩罚,那么受此规章管辖的人一提起诉讼,审查时机就成熟了。
[11] 之所以对行政计划的诉讼资格用成熟性原则加以限制,是出于以下的考虑:(1)成熟原则可以排除法院受理不适于法院解决的有关纯抽象纯理论性的问题的审查请求。(2)避免法院过早干预行政程序,卷入有关政策的理论争论之中。(3)有利于更切实地保障公民权益,对于将因行政行为受到实际的、紧急的、不可弥补的损害的当事人,给予及时的司法救济。参见王名扬主编:《法、英、美、日行政法简明教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
[12] 我国目前虽然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不能提起诉讼,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和不能对之进行审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抽象行政行为被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但是法院可以在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理时对其所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甘文:《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13] 李丰、崔丽:《温州"民告官" 讨要通行权》,《中国青年报》2003年1月8日。
[14] 具体要求有:(1)应听取其它相关行政机关(包含公共团体)之意见;(2)应将计划案提供公众阅览;(3)应给与利害关系人以书面陈述意见之机会;(4)对已提出意见之人应进行听证;(5)应将决定之计划附理由公告之。转引自刘宗德:《现代行政与计划法制》,《政大法学评论》总第45期,1992年6月。
[15] 德国《行政法院法》第40条规定:"一切未经联邦划归为属其它法院管辖的非宪法性质的公法上争议,对之均可提起行政诉讼。"
[16] 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148条规定,以正式行政程序所为之行政处分为标的,提起行政诉讼时,于起诉前,不必另经事前(诉愿)程序之审查。
[17] 董保城:《行政计划》,载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页。德国"确定计划裁决"之范例可见于同书第819-820页。
[18] 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19] 叶俊荣:《行政程序与一般法律原则》,经社研究报告1007,第234页。转引自黄学贤:《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研究》,《法学》2002年第5期。
[20] 黄学贤:《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研究》,《法学》2002年第5期。
[21] 该判决和裁定的出处均为:线上六法全书http://www.6law.idv.tw/aa.htm。
[22] 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156号(裁判日期1979年3月16日)。
[23] 林树埔:《论都市计划与人民权益之保障》,台大法研所硕士(1980年12月),第94页,转引自陈清秀著:《行政计画之制定程序与行政救济》,《宪政时代》第30卷第4期。
[24] 各种计划保障给付对应的行政计划类型和内容介绍请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414―418页;林腾鹞:《行政法总论》,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478-480页。
[25] 近来报章登载的一则新闻,报道了浙江省苍南县卫生局在制定实施区域卫生规划的过程中采取了行政高压手段迫使众多合法的个体医生到山区的乡村卫生室行医,禁止个人行医,就是一个以计划行为侵犯公民选择职业自由的典型案例。详情见《"把个体医生统统赶上山去" 政府该如何行政?》,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9/04/content_1062471.htm,2003年9月4日访问。
[26] 参见戴秀雄:《建立国土综合计划体系中之公权力机关参与机制》,《永续》(析)092-013号。
[27] 如今年杭州发生的一起颇受关注的行政案件--"金喜奎诉杭州市规划局撤销浙江省老年大学建设规划许可证案",就遭遇到由于现行诉讼制度上缺乏公益诉讼或行政公诉机制,而导致违反规划的行为不能得到及时纠正的后果。该案的详情可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03年2月28日做出的(2003)杭西行告字第4号行政裁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