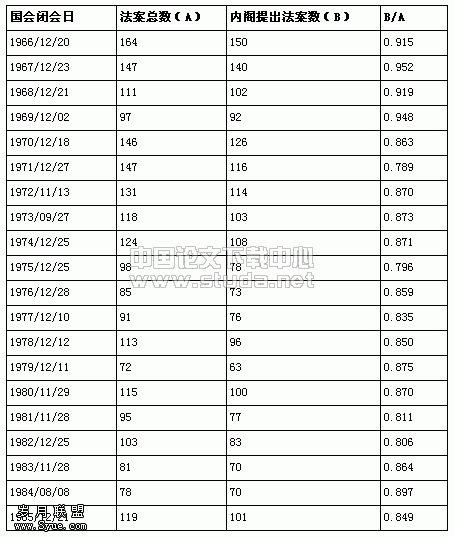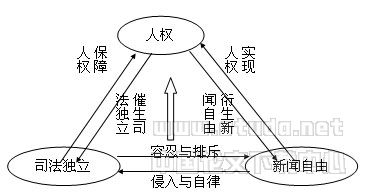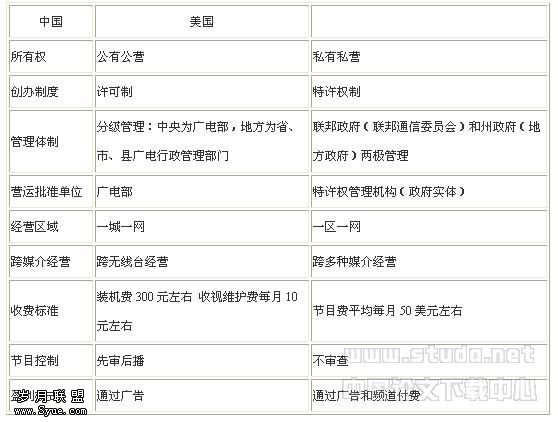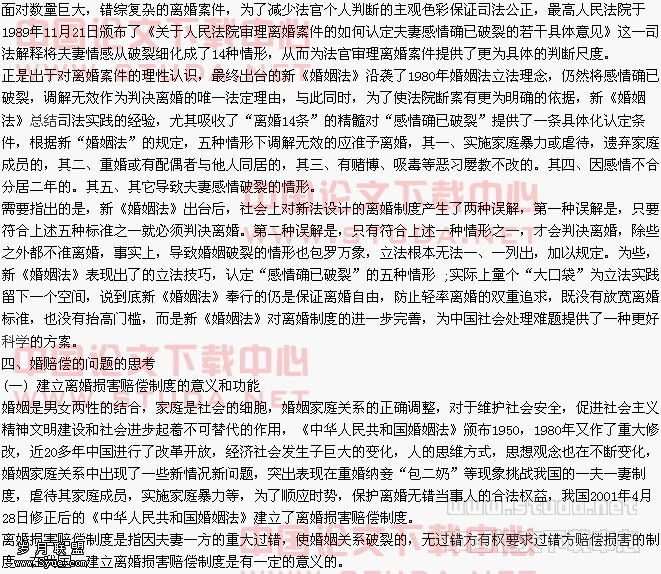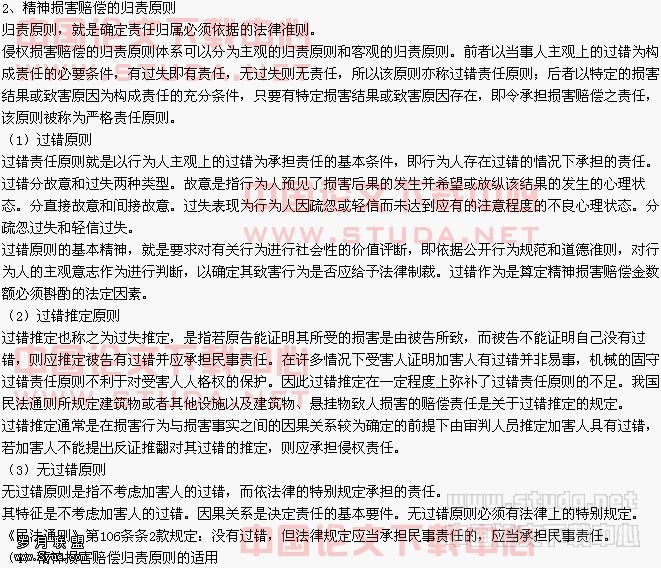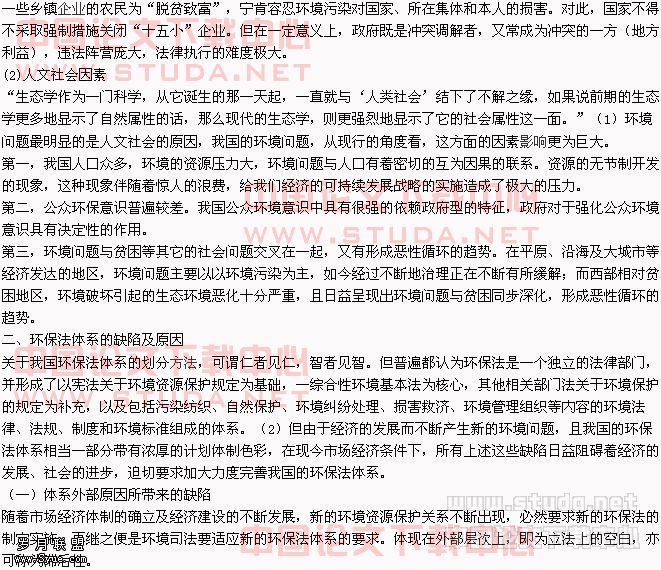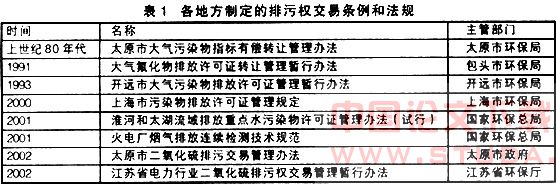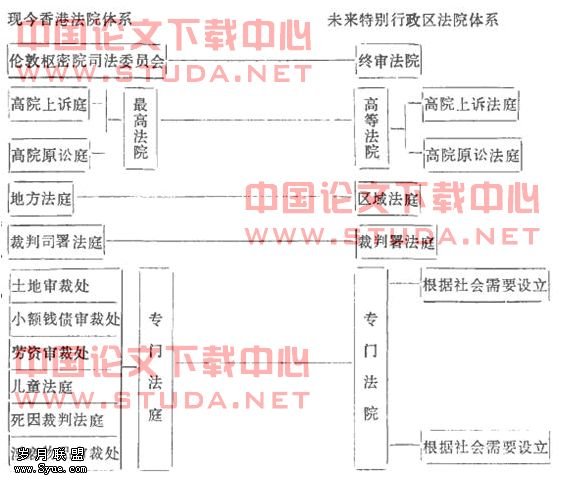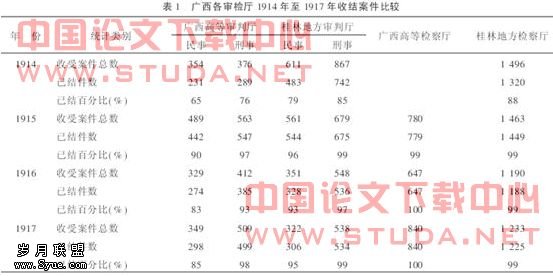论汉代的德主刑辅制度
汉代是我国上一个重要的朝代,是中华民族真正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朝代。汉代之所以能够维持自身的统治数百年之久,与统治者开明的治国思想分不开。汉代从头到尾始终贯穿着重德轻刑的治国方针。本文就是要对汉代的德主刑辅制度作一番探讨。
一、德主刑辅思想产生及确立
汉代的治国思想与秦朝截然不同,秦朝采用了法家的思想,以峻法来治天下,据史书记载,秦朝统治者“收泰斗之赋”,“士民不附,卒录之徒,还为敌仇”。这样的治国方针导致秦王朝后期人民怨声载道,尽管秦朝统一了,还是很快在农民起义的汛潮中崩溃。而汉代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由于连年战乱,生产遭受破坏,调敝,天下饥谨。不仅人民无以为生,四处流亡而且朝迁也是府库空虚,财源枯竭;以至“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面对着这种严峻的形势,新的统治者鉴于赢秦败亡的教训,意识到继续实行秦王朝的那种暴政,自己势必也会被农民起义所推翻。为了恢复经济生产,重建封建秩序,巩固新的政权,西汉初期的统治者,以黄老思想为指导,采取缓和阶级矛盾,休养生息的政策。短短七十余年,西汉便出现史称“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
黄老学派是先秦道家一个别源,“黄”是指传说中的黄帝,“老”是指春秋末期的老聃;尊黄帝为祖,奉老聃为宗,以“黄老之言”作为学派的指导思想,所以被合称“黄老”。经过多年的发展,到了西汉初期,黄老学派的法律思想的基本观点主张“文武并用”,“德刑相济”,已经把“德”抬高到了和“刑”相平行的地位,这与秦代所遵循的法家思想是截然不同的。陆贾向汉高祖刘邦提出了居“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问题;建议他效法商汤、周武物“逆取”、“顺守”,“文武并用”。即要求“德治”,实行“仁义”。文和武,也就是德和刑的两手,各具用途,必须并重,使相济为用。汉初黄老思想对秦代的专任刑罚,持严格的批判态度,但并不否认法律的重要性,也强调“明具法信”,“进退循法”。在刑罚具体运用方面,汉初黄老学说提出“刑不厌轻”,“罚不患薄”,这与先秦法家的重刑学说、尤其是秦代重刑学说更是天壤之别。晁错强调要做到“罪大者罚重,罪小者罚轻”,只有这样,才可称为“平正”。这种思想立足于道家的无为,却和儒家的仁政观点有很多相通之处。可见,黄老思想综合了道家、儒家、法家等多个学派的思想,为两汉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汉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到《汉书•刑法志》列举孝惠、高后时的“衣食滋殖,刑罚用稀”,以及高后及景帝各代的“除肉刑”,“定棰令”等等,就立法者愿意来说,都是要改变秦代暴政,要求宽减刑罚。这正是黄老学派的法律思想不同于秦王朝的法律思想的基本特点之一。它使汉初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黄老思想为同秦王朝的法家法律思想的统治转变为西汉中期及以后儒家法律思想的统治发挥过渡性桥梁作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提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逐步形成了儒学正统思想在法律思想领域的牢固统治。很显然,若不经历汉初的黄老思想的影响,要完成法家思想到儒家思想统治中国这一历史性转变,是十分困难的。黄老思想为中国封建正统儒家思想确立创造了条件。
谈到的封建正统儒家思想,不能不提到董仲舒,他是新儒学的奠基人,他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主张“奉天法占”、兴教化、抑豪强、贵德贱刑、养士办学等等,以巩固中央集权,因而得到汉武帝的重用。他是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地主阶级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逐渐占统治地位,他把天命和群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从理论上加以系统化,提出:“天者一起,百神之大群也”,“王者法天”。“天令之谓命”,“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既然君主是“天”挑选出来的,则名正言顺地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董仲舒还进一步将三纲五常确立为封建法制的基本原则。他提出“天不变道不变”,所以三纲五常成了绝对不变的真理!
董仲舒对“三纲五常”的神化,不仅使它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核心,而且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立法司法的根本指导原则。也就是说,维护“三纲五常”,便是封建法制的根本目的;符合“三纲五常”的言论行动便是“合理”、“合法”,违背“三纲五常”便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罪名要以“三纲五常”为准则,施加刑罚也以触犯“三纲五常”的程度为轻重等等。
怎样维持“天子”的至尊地位?怎样贯彻“三纲五常”原则?其中还有一个统治方法的问题。董仲舒吸取秦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继承孔、孟重德轻刑的思想,提出了德刑相辅、大德小刑的统治方法,并给予神学的解释。
他说:“对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发夏,以罚副凉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异事面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据引认为,对于维护封建统治来说,德、礼与法、刑都是必要的,不能缺少的。但德是主体,刑是辅助:“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而“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以不相顺”,他认识到道德教化和法律强制的“事异而同功”、“其用一也”,即在不同的领域里都起着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但是,二者的关系为“本”、“末”的关系,而德化是刑狱的根本,因而必须特别重视德化。
董仲舒“德”的具体内容,不外是孔、孟提出的省刑罚,薄税敛、去酷吏、兴教化等主张,但在西汉各种矛盾逐渐激化的时期,他的目的在于限制豪强兼并、削弱诸候王势力和全面恢复儒家礼教以缓和阶级矛盾,加强中央集权。所谓:“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威。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它与汉初黄老学派所讲求的不干涉、少干涉主义是迥然不同的。
德刑兼施,任德而不任刑,是西汉的统治阶级前代的统治经验、尤其是吸取了秦亡的深刻教训之后得出的结论。董仲舒肯定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断的正确的同时指出,在汉朝初建之时,就应该坚决革除秦代“法治”之弊,改变统治方策,实行“更化”。所谓:“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这里所指,正是要求用新儒学的德治和礼教取代汉初黄老的“无为”、与贾谊的主张是一致的。他认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从“奉天”的一方面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从“法古”的方面看:“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可见,他是以奉天法古作为“德主刑辅”的理论根据的。
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性三品”的人性论等论述德刑关系,是董仲舒在理论上的创造和特点。
他把封建统治的“大德小刑”原则说成是天意的体现,是房屋持久的最高准则,他说:“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即将人类社会的德、刑与先天的“阴阳之道”机械地比附,然后以之为前提作出论证。比如:他主张德刑兼施,便将它说成是四季运行的要求。所谓“夏主生”,生就表现为德;“冬主杀”,杀就是刑;“冬不可废”,因而刑也不可缺少;“夏不代冬”,因而德也不能代替刑。德、刑二者,缺一不可。“王者法天”,因此君主就应牢牢掌握这两种方法进行统治:“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
他主张任德不任刑,便以“天”“任阳不任阴”来论证:“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生而阴气杀”,“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他主张“先德后刑”、“大德小刑”,便以“天”的阳多阴少、阳先阴后作比附:“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计其多少之分,则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等等。
他还从“人性”的角度来作论证。在他看来,孔孟主张“礼治”,所以提出“性善”论,认为正因为人怀本善才有教化的必要和可能。韩非主张“法治”因而采取“性恶”论,认为人们出于“好利恶害”的本性,无法教化,只有用刑罚强制才能奏效。他自己主张德刑相辅如果沿袭“性善”论,则无法说明刑罚的功能;而若完全照搬“性恶”论,则意味着违背了孔、孟之道。于是,他将孔子与苟况、韩非的人性论调和起来,提出了一种新的折衷的观点:“性三品”说,他认为,善恶二性的表现,又是因人而异的,即分类“圣人之性”、“中人之性”、“斗筲之性”这样“三品”。具有“圣人之性”的人,不经教化便能“善”;而具有“中民之性”的是可能接受教化而为善,又可能不受教化而为恶的人;至于具有“斗筲之性”的,则多属为非作恶者,施予教化也很难为善。他认为,“中民之性”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性,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既用德教,扶植其“仁”质而使之为善,同时又使用刑罚防止和惩戒其“贪”质而使之不为恶。董仲舒就是这样用天命观和人性论为其德主刑辅学说进行辩护。
董仲舒以后,德主刑辅的原则尽管受到不同程度的光战,东汉后期尽管也出现过王符的崇“德”重“法”理论和仲长统的法律“变”、“复”思想但作为两汉指导思想的儒家思想逐步法典化,德主刑辅一直贯穿于整个汉朝,占支配地位。统治者始终将“德”放在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汉代统治者实施的种种政策来看,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担不能对其中的历史进步性视而不见。汉代正式确立德主刑辅法律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以后的封建统治者,都是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法宝承袭下来,无论行动上如何,都对外宣称自己“仁政”,而“重刑轻德”的皇帝通通被后来者视为暴君、昏君。可以说,德主刑辅至少被当成一条衡量封建帝王开明与否的基本方针一代代继承下来。
二、德主刑辅思想的影响和外在表现形式
在德主刑辅的法制思想指导下,汉朝统治者减肉刑,赦天下,发展生产,使汉代居为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第一个高峰期。作为一种对社会起到指导性作用的思想体系,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所影响和体现。本文仅就汉代的若干法制现象来说明汉代统治者是如何贯彻德主刑辅这一基本方针的。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正式设立赦的朝代,也是帝王把赦作为自己的政治手段的开始。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令:“兵不得休八年,万民与苦甚,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八年的战争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天下事毕”正是应该休养生息的时候,刘邦颁布了“其赦天下殊死以下”的赦令。目的何在呢?据史书载,刘邦的这道赦令在公元前202年农历正月发布的。这时项羽已在乌江自刎,刘邦在中原地区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刘邦以汉王的身份发布大赦天下的命令,是向文武官中发出了称帝意向的信息。天下初定,需要安定人心,那些被征服的人口中不少尚存敌意,赦免除死罪以下的犯人正是显示其宽仁的政策,用以怀柔。诸候王也正是在刘邦发布大赦令之后,上表“请尊汉王为皇帝”的。汉王刘邦也就在二月即皇帝位。
登位次年又发布赦诏曰:“天下既安,豪杰有功者封候。新立,未能尽图其功。身居军九年,或未司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怜之,其赦天下。”这次赦令是他计捕韩信之后颁的。这是刘邦削弱跟随他争战多年的将领的势力的开始。韩信功劳最大兵权最盛,是刘邦征讨全国不可缺少的支持者,也是他皇帝宝座的最大威胁。逮捕韩信,削其兵权,但又怕因而引起其它将领的不安,于是曰“天下既安”又赦免了军中犯了法的人犯,以此安定其它文武官员的心理。可见高祖颁赦令,完全是根据政治的需要,而并非出于恤刑与宽仁之心。自高祖开始,赦事已经成为皇帝的重政务;成为重要的政治手段。
汉代的统治者还废除了秦代的种种肉刑,这一点比较秦代是迈出了一大步。汉高祖刘邦入关仅仅约法三章,就是因为他深知农民战争的力量,新生政权还很软弱,人心思安,只有减轻对人民的压迫,人民才会拥护。经历了汉朝初年的休养生息后,到了文帝在位期间,废除了肉刑,更是做了一件万民拥戴的好事。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的评价,许多学者是从着眼,即从破坏还是保存社会生产力的方面加以分析。认为文景之世的刑制改革,明确提出了废除肉刑的具体内容。这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以后,在制度方面所出现的一次重要变革,是刑罚制度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作为奴隶制刑罚制度核心内容的肉刑,是一种残害人的肢体,破坏人的生理机能,使人终身残废的野蛮残酷的刑罚。它通过对一部分劳动力的人身伤害,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健康发展,阻碍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这已不能适应封建个体小农阶层已成长为广泛社会基础,封建个体小农经济已构成为主要经济成分的封建时代的社会要求,不能满足统治阶级日益增长的对劳动力的剥削需要。因此,文景之世废除肉刑的改革,不仅扩大了剥削对象,增加了创造物质财富的社会来源,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与经济的恢复,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而且也使刑罚制度由极端野蛮残酷向相对宽缓人道逐渐过渡,从而消除奴隶制残余在法律制度方面的消极影响,推动封建法律制度向深入发展。
这种观点有它的道理,这是从经济学角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对其评价的,对于废除肉刑客观上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分析较为透彻。但是,这一论点对当时统治者主观上分析较少,要知道限于历史的局限性,汉朝统治阶级不可能站在我们这个高度来思考问题并决策,他们当时的思想出发点是什么?他们不会想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这么一个理由来实施他们的政策。那么,统治者的思想根源到底是什么呢?
文帝改革刑制的时段,似乎不存在所谓的肉刑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情况。在《汉书•刑法志》提到废除肉刑一事之前的一段文字中,班固是这样说的:“及孝文即位,……风流笃厚,禁 罔 疏阔。选张释之为迁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这里谈到一年之中,断狱即刑事审判的案件只有四百。那么被判处肉刑的人是十分有限的,只会占四百个案件中的一部分。从劳动力角度去,这些人和汉代当时已经拥有的几千万人口相比,不能不说是微乎其微的。单纯从劳动力方面讲,保留肉刑也不致出现不能满足统治阶级日益增长的对劳动力的剥削需要。废除肉刑的意义并非在于此。
对肉刑本身的分析,日本学者认为:在中国的上古时代,“受肉刑者已不被看作是社会的一员,任凭他们是死是活都无人关心,与最原始的放逐形态一模一样。刀斧之痛、伤残之苦都不是肉刑的主要目的,肉刑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加之于肉体的毁伤,是社会废人、市民权被终身剥夺的象征。”而让刑人充当贱役,可能是这些被社会抛弃的人难以生存,因此照顾性的给予其度过残生的谋生条件。后来认识到这些人还有一定的利用价值,才逐渐发展出针对刑人的相关制度。认识肉刑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从“驱逐出社会”的角度,一无化地领会死刑、肉刑和放逐刑。判断肉刑属于严重破坏生产力,或者说废除肉刑有扩大剥削对象的意图,似乎分析的都不够到位。如果就事论事,应当承认汉文帝肉刑的本意,还是文帝自己说的,是要实行德政,为罪人开通改行为善之路。
肉刑伴随终身的身份性,应当说对人生的长期伤害是非常重的。因为肉体所遭受的伤痛只是暂时的,甚至并处的劳役刑也不是没有终止之期,伤残有时也是一种外表的畸形化或造成行动的不便。“哀莫大于心死”,只有受过肉刑以后所具有的卑贱的身份,才会让人没有了希望、使人永远丧失改悔从善之机会的关键所在。在分析废除肉刑的意义时,似乎不能忽略这一主要之点。废除肉刑和规定刑期的最大意义,是开辟改过自新之路,使罪人有可能复归社会,使其本人和其后代不致被社会长期歧视。
汉文帝废除肉刑,是一次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的贯彻,是中国封建社会荡涤奴隶社会尘埃的一次重要举措,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中国在西汉初年又向文明的门槛迈进了一步。
三、对德主刑辅的评价
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会采用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来加以倡导和传播,汉代的统治者也不例外。但比较前朝,不能不说汉代的统治者是明君多、昏君少,汉代从建国到出现“文景之治”只有短短几十年,这是与汉初休养生息的政策分不开的。德主刑辅制度把芸芸众生从秦朝的暴政中解放出来,生产力也得到了提高。同时应该看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不会因一时的较为宽松的皇权被儒家思想加以神化后,漫无边沿,成为一种没有任何制约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滥用就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后果。当一位皇帝认为前朝的法制不足以维持他的统治,或者不能满足他的个人喜好,他就可以任意进行更改,这就破坏了法律的连续性稳定性。汉朝也不乏昏君,特别是东汉未年,朝迁腐败,诸候分据,民不聊生,才爆发了黄巾大起义,汉朝的根基被毁,很快就灭亡了。所以,封建社会中人民大众毫无权利可言,天下太平只是全种美好的愿望,统治阶级在一方面宣扬“德”治的同时,不断加大对农民的盘剥,所谓“德”,只是统治阶级对人民大发慈悲,将套在人民脖子上的绳索略微放松一点点;只是封建统治者用来美化自己的一块招牌。
西汉的德主刑辅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以后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一直延续了两千余年,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可谓巨大,只有对其加以深刻的研究和探讨,才能真正把握封建社会法制试制的精髓,才能做到借鉴、继承,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当今的社会主义建设。
:
1、《中国法律思想史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2、《汉文帝除肉刑的再评价》,作者张建国,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3、《试析中国古代的赦》,作者沈厚铎,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在古籍研究所。
4、《机关报编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出版。
5、《中国法制史》群众版社 1995年出版。
6、《新编中国法制史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出版。
7、《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出版。
8、《老子》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