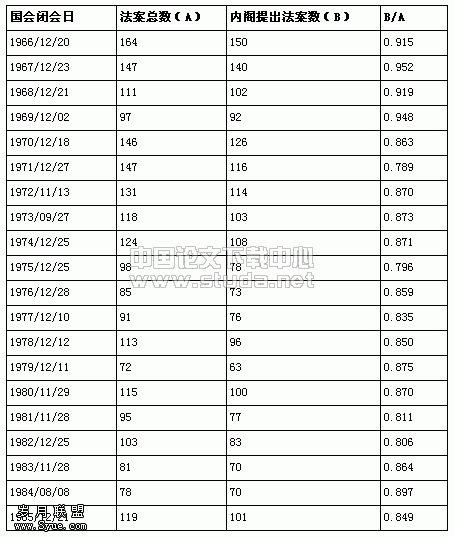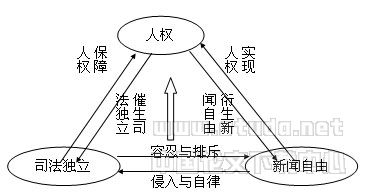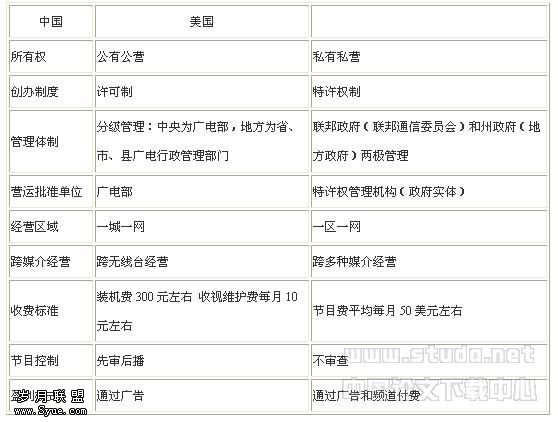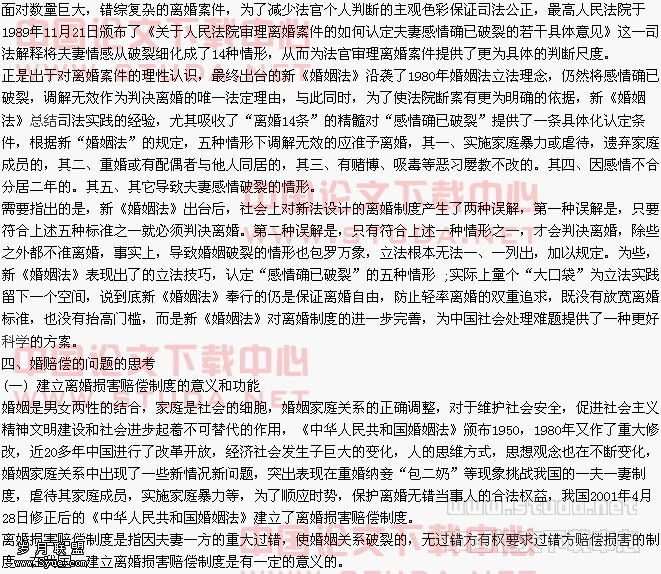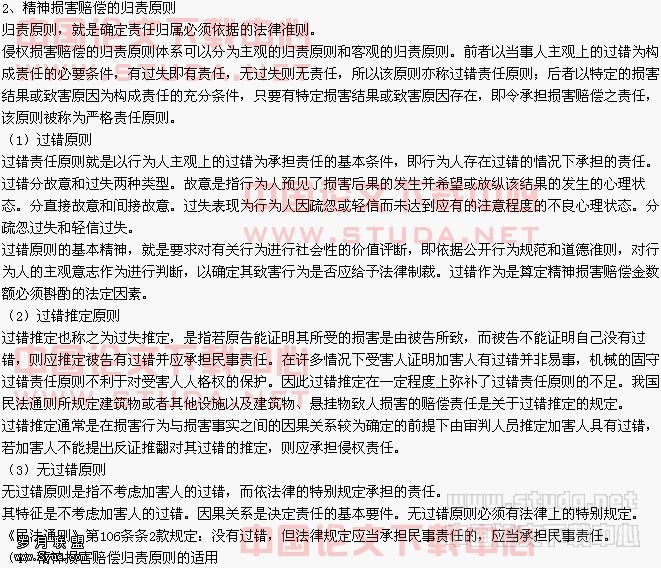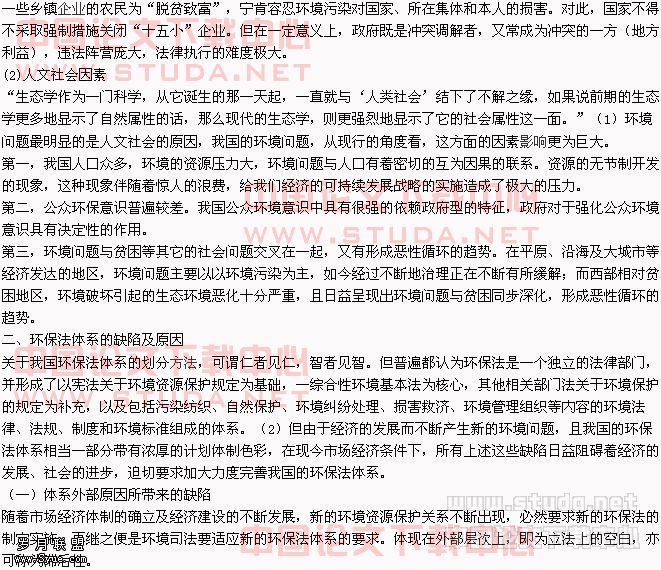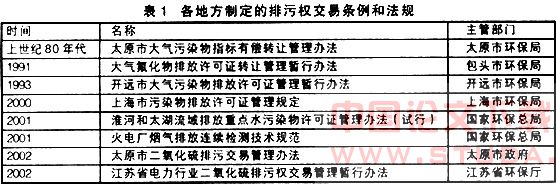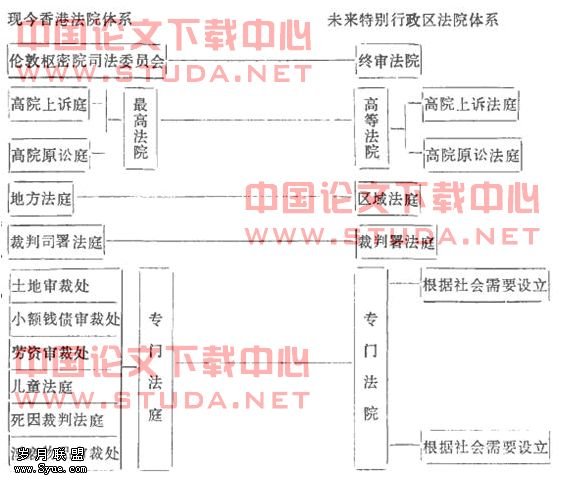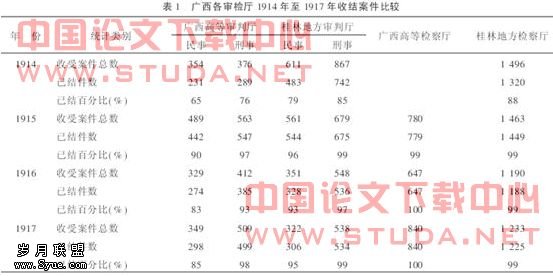论我国“安乐死”的法律制度
内容摘要:
自“安乐死”一词衍生以来,伴随它的争议也不断激烈化。安乐死究竟合不合法,究竟该不该立法,也是众多人口中争议的焦点所在。本文从安乐死的定义、我国的安乐死立法的争议及合理性等几个大方面进行了论述。概括阐述了安乐死的定义、在国家的情况及国际个别国家对安乐死的立法,并针对我国各方面情况对我国的“安乐死”立法作了几点的分析,主要从我国安乐死观念的出现、安乐死立法的争议、安乐死研究的贡献、立法的必要、我国国情、立法条件等方面较具体的阐述了几方面个人的观点。
关键词:安乐死 立法的争议 立法的合理性
一、“安乐死”的定义
安乐死一词原自希腊文Euthanasia,是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所组成。其原意是指舒适、幸福或无痛苦地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
(一)、“安乐死”的学理定义
“安乐死”有广义与狭义,积极与消极之分。广义理解的安乐死,包括一切因为身心原因致死,让其死亡及自杀。狭义理解的安乐死则把其局限于不治之症而又极端痛苦的人,即对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不对他们采取人工干预的办法未延长痛苦的死亡过程,或为了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而采取积极的措施认为的加速其死亡的过程。积极安乐死,也称主动安乐死,是指医生为了解除病危重病人的痛苦而采取某种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消极安乐死,也称被动安乐死,是指停止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病人死亡。
当然,在各个领域,对安乐死的定义也许不尽相同,但都不外乎局限在其本意“无痛苦的死亡”之中。《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安乐死是指在不可救药的患者或者病危患者的要求下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莱克法律字典》对此的释意是从怜悯出发,把身患绝症和极端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和做法.《百科全书,法学》定义为;对于现在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的痛苦,可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
(二)、“安乐死”立法定义的要求
在立法中,“安乐死”的定义必须严谨,细致,有名却的依据与规定,不能莫冷两可、模糊不清。
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三)、立法中“安乐死”定义必须严格要求
“安乐死”不能滥施,只能对有必要的人来实施。立法中的“安乐死”定义更应严格规范,从根本上说,立法中的“安乐死”定义必须先符合以几点要求:
(1)、被施以“安乐死”的人是换不治之症的病人,且在垂危状态下,面临死亡,精神和躯体都极端痛苦。
(2)、“安乐死”必须出于病人自己的主观意愿。在病人已无意识的情况下,可由其家庭成员(配偶、子女其他直系亲属)同意。
(3)、“安乐死”必须使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
安乐死必须符合以上几点要求才能真正的称之为“安乐死”其主要目的是为需要的人解除不必要的痛苦。因此“安乐死”概念绝对不能泛化,不能滥用,否则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危险而令人畏惧的词语。
二、关于我国“安乐死”的概况
(一)、我国“安乐死”观念的萌生
在我国,“安乐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从安乐死的研究,宣传,立法,实施,的全局来看,还有一些基本认识,基本观点需要进一步解决,而这些也造成了众多不同意见的产生了多方面的争议。
(二)、我国“安乐死”观点的发展与现状
“安乐死”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自流传至中国以来,便在中国大地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响。
1986年,陕西省汉中市医生蒲连开因为他人实施安乐死手术,被病人一名家属以故意杀人罪告上法庭。1991、5、17,汉中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蒲连生,王明成为身患绝症的病人(即王明成之母)夏素文注射促进其死亡的药物不构成犯罪。原告不服判决,又提起上诉。1992、6、25汉中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中国首例安乐死杀人案自1986、7、3立案起,经过6年漫长的审理后终于有了结果。2003、6、6,王明成——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主要当事人之一,因胃癌晚期,不堪病痛折磨,提出为自己实施“安乐死”遭拒。7、2,王明成最终没能达成自己安乐死的愿望,在一片争议声中离开人士。
我国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儿童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都是安乐死议案的提案人,他们不仅在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进行着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时也要实施安乐死。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生前也很赞成安乐死。而除了在全国最高权力机关进行呼吁外,有些人士还在民间为安乐死奔走,准备成立纯民间的“自愿安乐死协会”。
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识阶层人士。上海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支持率则高达79.8%;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
三、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思考
(一)、中国关于“安乐死”的争议
1、“安乐死”是否存在违宪问题
马克斯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盛名权力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不仅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死亡的权利是“优死”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鄙人和结果。
2003年,广东省人大文化卫生委员会根据我国《宪法》四十五条:“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又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规定,针对有政协委员在广东省政协及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对无可救治的晚期癌症患者应可以实行‘安乐死’”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违反《宪法》。
此等说法引起极大争议。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色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笔者也认为,从法理上讲,公民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宪法》的这一规定说的是国家保障公民的私权利,并没有限制公民“安乐死”的自由。而且,对公民的私权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公民选择“安乐死”是他们的自由。随着社会的进步,当“优生”的生存观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之后,同样应尊重“优死”的权利,无可救治的绝症患者应当有权利选择有尊严地死去。
2、是否违反刑法“安乐死”不等于“故意杀人”
虽然从刑法上来说“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种种条件,但是从本质上看还有许多不同之处:
第一, 两者出发点和目的不同。“安乐死”已免除特定人群痛苦为出发点;而“故意杀人”却是以报复夺取金钱等为出发点。
第二, 实施者不同。“安乐死”是由合法合格的医护人员操作完成;而“故意杀人”没有特定的人群为实施者。
第三, 运用的手段及方法不同。“安乐死”一般使用药物,采取无痛苦方式终结生命,而“故意杀人”则不管用任何手段、方法强制性剥夺其生命。
第四, 性质不同。“安乐死”是善意的,而“故意杀人”是恶意的
第五, 主动方不同。“安乐死 ”是由被实施人主动提出,是由被实施人的主观意志支配,而“故意杀人”完全由实施者个人主观意志支配
所以,目前不能将“安乐死”列为“故意杀人罪”。
(二)、“安乐死”在我国有立法的必要
实际上,安乐死立法并不象很多人说的那样,是“超前立法”。安乐死立法非但不“超前”反而“滞后”。因为“安乐死”这种社会关系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并且需要以立法加以调整时,立法者行动缓慢以至于使其所进行的立法调整未能及时适应这种社会关系的需要,甚至这种社会关系出现较长时间后才对其加以立法调整“的立法方式——滞后立法。
在2002年,没提关于一位老人在其就九十二岁老母长期昏迷无法至于情况下,请求医院实施安乐死遭拒绝后将其母电死,后被判五年的报道,使政协委员田世宜受到很大震动。政协委员田世宜在其递交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的义愤提案中呼吁,中国队安乐死不应一味回避,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着手研究安乐死相关的法律和立法,首先允许公民在法律严格界定的条件下有权选择安乐死,然后再在操作上做出具体的规定,并运用开发临终关怀服务产业,使人类创造的法律和高科技手段能够有效的服务于人类自生至死的全过程。
由此可见,“安乐死”在我国的确有立法的必要性,只有尽早立法,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法律的发展及完善,才能使类似悲剧不再发生。因此,我国应正确对待国情,正确处理舆论,在大局稳定的基础上,尽快实行对安乐死的立法。
(三)、我国“安乐死”立法必须符合国情
一个社会能够切实尊重保障每个人“安乐死”的权利,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当生命垂危这面对及其低劣的生存环境时,他们应当有权选择体面而又尊严地死去,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地权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
立法要明确规定具有那些特定清醒的病人才享有自愿选择安乐死和授权他人对其实施安乐死的行为的权利。这是“安乐死法”的第一大核心内容。荷兰、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安乐死立法,公用的限制条件主要有:(1)、经确诊,病人患有目前医学证明确实是不治之症;(2)、该不治之症给病人带来无法忍受的极端痛苦;(3)、必须有病人本人亲自提出安乐死的要求。
以上比较了世界一些国家对安乐死的限制条件,而我国虽然要尽快立法,但也不能草率行事。我国安乐死立法。绝不能照抄照搬荷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而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设定更加严格的、更具可操作性、更符合我国国情的限制条件。
第一,“安乐死”要由明确的定义。笔者在本文第一章中已有论述,在此不再多说。
第二,安乐死要有特定的原则。实施安乐死应符合无危害,无痛苦、不违背本人意志的原则。具体为:(1)、医学技术所不能救治的不治之症;(2)、病人的剧烈痛苦无法抑制,且已迫近死亡;(3)、病人有要求安乐死的真诚意愿;(4)、在不违背病人的意愿前提下,由医务人员提供的再无痛苦状态下加快结束或不再延长死亡过程的医疗性服务;(5)、执行安乐死的方法在伦上被认为是正当的;(6)、它时在特定情况下病人利益的最高体现。
第三,要明确安乐死的对象。安乐死的对象应严格控制,通常以下三种认为实施对象;(1)、肉体和精神处于极端痛苦之中的绝症患者;(2)、靠人工维持生命长期昏迷不醒、丧失自我意识的病人;(3)、有严重缺陷的新生儿。
第四,安乐死的形式和方法。合法的安乐死形式既包括被动安乐死,也包括主动安乐死。安乐死的方法应当是快速、无痛的,尽可能表达“安乐”本质,体现出人道主意的精神。安乐死的实施者应为合法的医务人员。
第五,安乐死的实施程序。基本应遵循以下程序:(1)、请求程序。请求必须是病人的仪式清楚的情况下,出自本人的真诚意愿。对于陷入永久性昏迷状态,不能表达意愿的病人,可由其直系亲属请求,但需要得到有关部门和医疗单位的同意方为有效申请。(2)、审查程序。设立有医学专家、法医、医学伦理专家等共同组成安乐死审查委员会,其任务是对安乐死的申请进行严格的医学和司法审查,防止误诊和失控。(3)、操作程序。安乐死申请的到批准后,必须由病人所在两名以上的医务人员按批准的时间、地点等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在实施前病人表示反悔,不同意实施安乐死,应尊重人的选择、不得强迫实施安乐死。
第六,法律责任。(1)、对不符合安乐死条件的病人实施安乐死,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由确切证据证明病人亲属或医务人员时在病人的真诚请求下对病人实施安乐死,但未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的,仍属违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4)、未经病人同意,病人亲属或医务人员对由行为能力的人擅自实行安乐死得,也构成故意杀人罪,应按刑法有关规定承担刑事责任。
四、“安乐死”立法的合理性
(一)、“安乐死”存在着的积极意义
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迅猛着的我国,“安乐死”也早已不是什么新解名词了,许多人都声称到无法医治又承受巨大痛苦,选择安乐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不管安乐死有多么的首任青睐,目前它终究还未被法律允许实施。2003年8月,被称为“中国‘安乐死’之子”的王明成颓然离开人世,留下的是家里拖欠已久的债务,和人们对于安乐死话题更沉重、更深入的思考。
安乐死到底有没有存在的意义?笔者认为答案当然时肯定得:第一,安乐死并没有对其他人造成任何的威胁;第二,安乐死的确帮助了很多生存无望的人结果了无谓得痛苦;第三,安乐第也在促进着人们对生死价值更深一步地理解,通过安乐死,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了死亡,死亡对人们来说虽然是不愉快的事情,但未必是无意义,无价值的事情。
作为安乐死的有限替代品,目前,一般实行两种做法:一个十尽量减轻患者的痛苦,比如,放宽吗啡等麻醉品的使用原则。再一个是放弃出院回家,使患者能够在更的环境中尽量多享受一点做人的乐趣。但无论哪一样都无法从根本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如果病人在清醒且理智的情乱下,慎重的提出“安乐死”对其个人及其家庭也未必部十件好事。
在我国,一般家庭都无法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更何况有很多家庭收入低微。因此,有绝症病人的家庭通常都是心理负担,对家人更是心理及身体的双重负担。而适时,适当的安乐死,对病人个人来说即结束了无休无止的痛苦,也免去了等死的心理压力,更解除对家中亲人的种种愧疚;对病人家庭来说,也不必再承担巨大的身体与精神压力,可以更从容的生活下去。虽然,在精神上要承受一定的痛苦,但这种痛苦是必然的,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家人是必定有心理准备的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病人承受痛苦本身就使家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痛苦,而病人早一日结束痛苦,家人心理也会早日获得轻松的。
综上所述,安乐死的存在的确有着积极的意义,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结合其立法内容可以看到,只要法律在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同时,对“安乐死”的操作程序等做出严格、细致的规范,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学的“安乐死”实施制度,完全可将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而立法者也应当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广泛、深入的理论探讨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立法、司法经验,尽快针对我国的安乐死事例归纳,防止滥用,将重病患者的“安乐死”权利落到实处。
在此特别感谢在本人撰写期间,对本人做出了无私帮助的老师和同学,并希望他们都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
[1] 载 新华报讯 2002年5月20日
[2] 艾文波 《应尊重 “安乐死“的权利”》 2003年7月23日出版
[3]秦平 《危险的“安乐死”概念泛化》 2003年11月14日出版
[4]夏敏 《媒体呼吁安乐死早日进入立法程序》2003年8月19日出版
[5]张毅 《安乐死立法当慎行》 2003年7月28 日出版
[6]王利明 《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7]李强 《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2003年12月3日出版
[8]周泽 《“死于安乐”有多难 在中国为何难以合法化》2003年10月22日出版
[9]载 南方日报《我国首例“安乐死”案解密》 2001年5月20日
[10]王晓辉 《无被害人“犯罪”的视角转换:安乐死之非犯罪化》 2003年2月25日
[11]王作富 黄京平《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2002年9月第6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