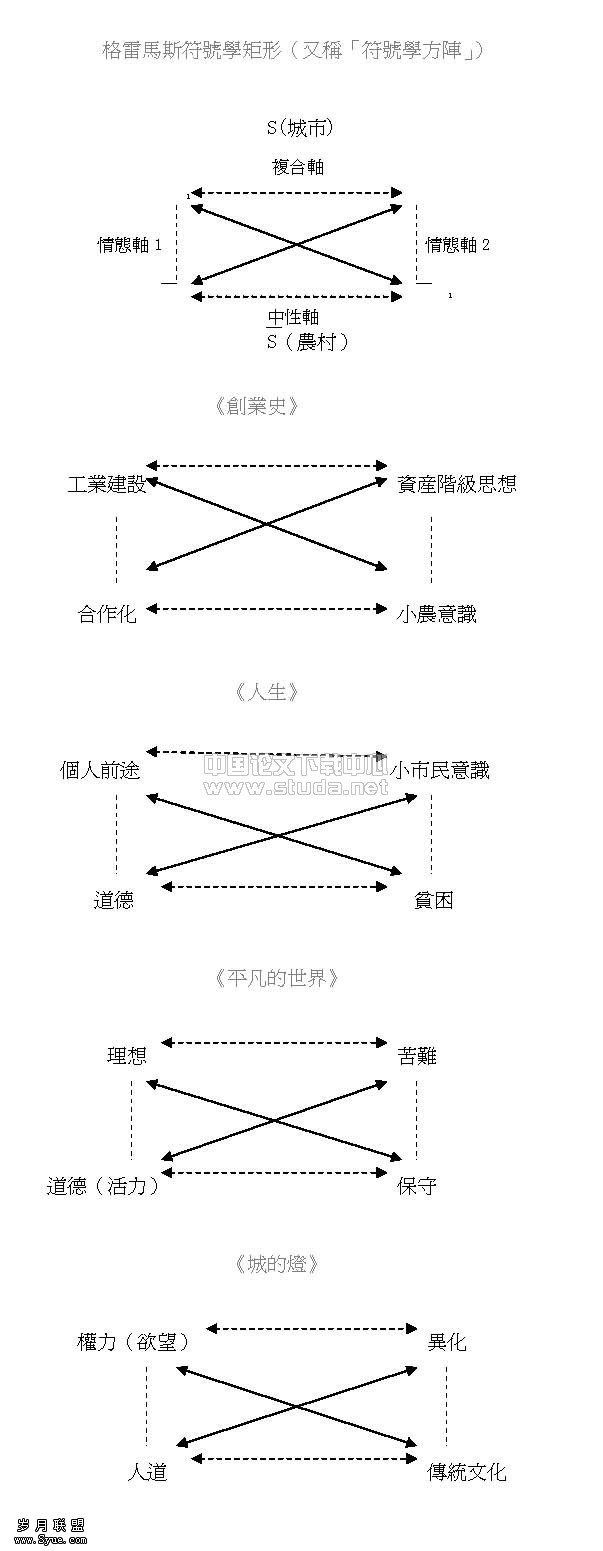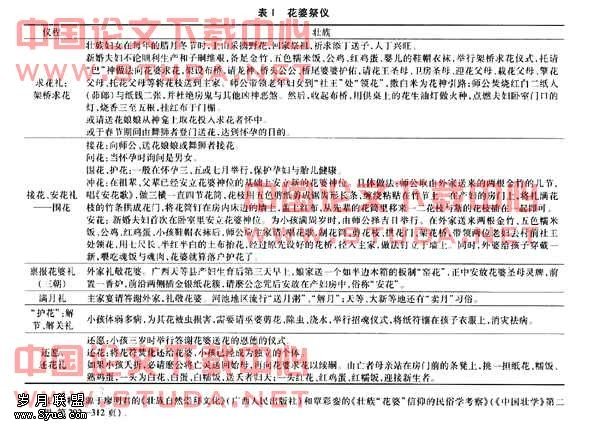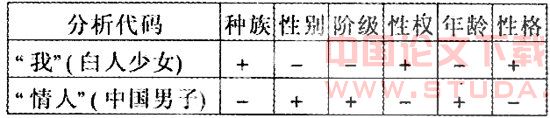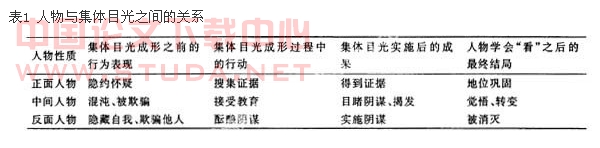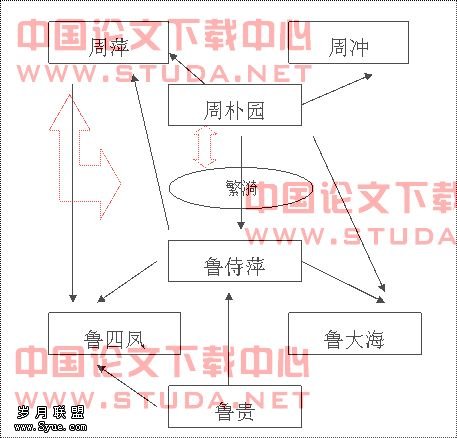“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3
关键词 新启蒙主义 审美问题 人性启蒙 自由意志
一、前提与根据:时代呼唤“新启蒙主义”
经常有朋友见面寒暄时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你还在搞‘启蒙’吗?”“你的‘启蒙’还没搞完么?”这样的“关心”听多了,不能不引起心中隐隐的不安。显然,在有些人看来,启蒙问题即使“没有过时”,也至少不是一个新鲜话题,而且是应该“搞”一段时间就得结束的,就像文学研究者研究完了一个作家需要换另一个作家来研究一样。然而,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尤其是将启蒙作为进入文化、文学和思想研究对象的途径的工作,是值得任何一个学者付出毕生精力的,更何况常说常新、“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本就是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对上面的疑问我有时只好这样自我解嘲:连福柯都说启蒙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我怎么就能“搞完”呢?
今天为什么要重提启蒙问题,而且还冠之以“新主义”的名号?这绝非为新而新,笔者关于“新启蒙主义”的所有努力其实都可以归结于将启蒙这样一个老话题刷新为一个面对时代与未来的新课题,并最终使其上升到“主义”的高度。“新启蒙主义”之“新”及其存在的必要性都隐含在世纪之交以来文化转型纷乱现象背后的深层需求之中,蕴涵着充分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内涵。首先,从历史的要求来看,它是对鸦片战争以来时断时续的历次启蒙运动的一种呼应和超越。以“新民”为核心的近代启蒙运动由于缺乏充分的性吸收与孕育,如先天不足、后天又少合理营养与膳食结构的婴孩一样,其质素与肌理的僵化也就不足为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启蒙准备了一份不无完整的启蒙谱系版图,但是其与民主的外在要求与伦理革命的内在要求之间发生了抵牾,并没有同步深入,也过早地发生了转向。30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扬弃”与综合创造的任务,反而从文化启蒙转向救亡运动,并最终转向反启蒙。80年代的“新启蒙”在“回归五四”的旗帜下对历次启蒙运动包括“五四”运动做出了深刻反思,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毋庸讳言,其侧重于民主与理性的文化批判与“外在扩张”,缺少人性建构与内在超越的缺憾也隐含着自身的危机。而且这时的“新启蒙”远没有像“五四”那样渗透至文学审美潮流之中,形成文化与文学、思想与审美“联手作战”的局面。因此,总起来说,上述几场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时”,向外的趋向均大于向内的趋向,社会启蒙的成分大于“人”的自身启蒙的成分,缺乏信仰纬度的呵护与标高,因此上述“新启蒙”必然会蜕变为“旧”的。
其次,从理论的要求看,自90年代以来,“现代性”、“全球化”成为研究界最热门的理论视域,而后启蒙、后现代、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等成为思想界的重要思潮和热门话题,这些热点固然有其深刻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必然性,也系学术上“与国际接轨”的潮流之所向。然而它们却蛮横地遮蔽了一些具有根本价值的本土问题,尤其是现代性取代启蒙成为人们的思想中心后,现代性的“家族性”、多元性、内在价值悖论在解构启蒙“元叙事”的同时,也驱逐了启蒙的内在价值与永恒意义。而且一般把启蒙现代性引申为现代性,或者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视为现代性自身相互矛盾、相互斗争、彼此反驳的两个方面,这样就更导致了启蒙问题的狭隘化和边缘化。这一个趋向至今没有引起学界充分的警惕。在这样的前提下,新启蒙主义力求恢复被现代性理论所扭曲的启蒙的尊严,从理论上将其从现代性混杂的内涵中独立出来。
再次,更重要的是,新启蒙主义体现了对现实的深层需求的回应。在形形色色的理论视野中,对中国当下文化、国民心态的描述和阐释与其对象一样,多元共生、良莠并存、泥沙俱下、五彩缤纷,莫不带上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等等的文化幻象,却掩盖了中国当下文化最严峻的现实性问题。在笔者看来,当下文化表象背后的真实面目是———愚昧和偏见。其实,常常令人们怨声载道的价值迷乱、道德沦丧的文化现实与道德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消费主义等理论思潮或生活潮流之间,只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方式,后者并不能对前者进行切实的考察和诊断,二者之间亦不能构成本质性的和逻辑性的关联,其症结与渊薮在于国人的人性现状充满了愚昧与偏见。如果说愚昧是一种封建主义式的无知,拒绝人格独立与人性的解放;那么偏见则是滥用了人性解放的条件,成为为新的习俗、时尚所裹挟的人性迷乱状态。尤为令人痛心的是,充满了“傲慢和偏见”的现代人自以为自己的人性解放了,自以为可以“看透”社会与人生的方方面面,但其实,他也许已经陷入人性的迷障而不能自拔。在此,贝尔的反思就颇有代表性,他说:“现代人的傲慢就表现在拒不承认有限性,坚持不断的扩张;现代世界也就为自己规定了一种永远超越的命运———超越道德、超越悲剧、超越文化。”①比如以“自我实现”的名义不断破除宗教、道德、、等对人的“束缚”,疯狂地追逐毫无边界的所谓“自由”,———而这种自由在经典启蒙家看来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不自由”。如果说,从“五四”时期到七、八十年代中国启蒙的主题是与愚昧作斗争,通过“祛魅”促进解放;那么,当下启蒙则不仅要剔除愚昧,更要与形形色色的偏见做斗争。如果说,愚昧是一张白纸,一旦理性开窍就有希望在上面画上美丽的蓝图;那么偏见则是满纸涂鸦,更何况其在当下充斥于各个阶层,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恢复清明难乎其难。正如卡西勒所指出的,“人们喋喋不休地指责启蒙时代自命(比其它时代)‘知之更多’那股傲慢劲,从这种指责中又产生出大量偏见,这些偏见时至今日仍是人们公正地研究和评价启蒙哲学的障碍。”②一言以蔽之,启蒙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而是当务之急,其必要性、针对性、艰巨性尤甚于前。新的课题催生“新启蒙主义”。
二、方法与途径:作为审美问题的“人性启蒙”
如上所述,当下思想界流行的现代性理论以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对抗为研究范式,这一范式从理论出发点上就将启蒙问题与审美问题割裂开来,同时更遮蔽了启蒙命题与人的全面解放的内在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启蒙主义”正是为了弥补这种缺憾,重新从方法论上开掘通往启蒙的途径,即将作为审美问题的“人性启蒙”从纷乱的理论话语中突出出来。
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在康德的时代,康德做了回答;在二百年后的当代,福柯做了回答。当然,从康德之前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到其后的黑格尔、马克思、卡西尔、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做过精辟的论述。但从启蒙的本体论上,即从何为启蒙,而不是如何展开启蒙、如何反思启蒙等方面来说,康德与福柯的命题应该说最有代表性。
就启蒙这个概念或者启蒙运动本身来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历史性的过程或“事件”,它既是个体的自我启蒙的问题,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性的启蒙问题,如福柯所说,启蒙“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它涉及到地球上所有人的政治和社会的存在。”3也如康德所指出的,“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4根据福柯的理解,既然当人只是为使用理性而推理时,当人作为具有理性的人(不是作为机器上的零件)而推理时,当人作为有理性的人类中的成员而推理时,那时,理性的使用是自由的和公共的,那么“启蒙”便“因此不仅是个人用来保证自己思想自由的过程”。只有“当对理性的普遍使用、自由使用和公共使用相互重叠时”,才有“启蒙”。然而“怎样去保障理性的公共使用呢”?于是“我们看到,‘启蒙’不应当仅仅被设想为影响着整个人类的总过程,不应当仅仅被设想为个人应尽的义务,它已显示为政治问题。”5如此一来,启蒙囊括了从个体精神解放到人类精神上升,从宗教事务改革到政治革命与社会实践的几乎所有领域。
但是,当我们将启蒙与审美联系起来,问题就有所不同了。由美学的本质及其边界所决定,它只能分担启蒙的一部分任务(或康德所谓的“神圣权利”),就像文学主要是一种“人学”而非社会学,也像审美是一种形式而非政治精神的传声筒一样。换言之,启蒙主义文学精神承担的只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层面、某种领域。这就意味着,当我们将启蒙作为一种审美精神时,就需要转移一下启蒙思想的重心,即从整体性的事件转移至与审美相关的精神领域。而另一方面,当我们将启蒙作为考察文学的一种精神视野即研究角度而非研究对象时,尤其需要抓住其“人学”的核心,即人性解放的层面与个体哲学的维度。或者说,这时我们要强调启蒙的生存论、伦等与个体“自我承担”相关的内在思想维度,而非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相对于个体自身来说那些外在性的思想维度。由于启蒙在康德及其以后许多启蒙思想家那里是一个综合性的命题,因此当我们将启蒙作为一个审美问题,并试图从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吸取思想资源时,就需要适当地有所取舍。而这种取舍显然恰恰可以避免受康德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明显断裂的二元论的影响,也就少了纯粹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之间某些纠缠不清的话题。
尽管康德意识到最终抵达启蒙需要个体与社会的共同才能完成,但他思想的重心仍然放在个体性的实现上,而这个个体在根本上是人类的而非某个群体的一员。尽管每个人都像卢梭说的那样“人天赋自由,然而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启蒙永远无法完成或者说启蒙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理由至少有这样几层:其一,人的不自由的不成熟状态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并不是别人或者社会或者制度强加给一个人的。其二,即使处于不成熟状态的人也并非是愚不可及的,他们有着自由的天性,有着理性的潜在力量,只是因某些原因而被压抑在无意识之中,连自己都察觉不到了。比如他强调说,“一个人确实可以为了他本人并且也只是在一段时间之内,推迟对自己有义务加以认识的事物的启蒙;然而迳行放弃它,那就无论是对他本人,而更其是对于后代,都可以说是违反而且践踏人类的神圣权利了。”6显然,在他看来,启蒙不仅是个体自身的权利,而且是对人类的义务的担待。一个人有权利展开自我启蒙,但同时更没有权利拒绝自我启蒙,况且人天生具有懒惰的本性,这种本性常常会阻碍人们进行自我启蒙的勇气与韧性。
那么对于一个个体来说(而不是从人体与社会的关系来说),怎样才算是进入了启蒙的过程?———这句话已广为人所征引:“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7据笔者理解,这里包含着层层递进的三重内涵:其一,启蒙既是一个个体脱离“不成熟状态”的过程,同时又是走向(注意是“走向”而不是“达到”)“成熟状态”的过程。“因而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其二,这个过程虽然需要被启蒙的引导,但这种引导仅仅是一个开始,仅仅是启蒙的入口。一旦进入这个入口,被启蒙者就不再需要引导者即启蒙者的理智,而完全靠自身的理智了。因此从本质上说,启蒙的过程是一个主动的或自动的过程。其三,启蒙既然是一个主动的自我启蒙的过程,因此它的主体必然要经受来自各种各样的非启蒙因素、反启蒙因素的干扰、阻挠甚至迫害。于是自我进行启蒙的主体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仍然会在某个上升的环节上退缩而中止启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康德更担心的不是一个人理智的缺少,而是勇气的缺席。因此他宣布说:“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综此三个层面,如果一个人始终停留在“未成年的状态”,那只能由他自身负责。
那么什么样的状态是“启蒙了的”“成熟状态”呢?或许可以表述为:什么样的人性状态堪称实现了“人性的最高阶段”8了呢?按照福柯对康德启蒙论的阐释,人类成为成年之日并非是无需再服从命令之时,而是有人告知“唯命是从,但你可以尽情推理”的时候。(这里的razonieren,即为推理而推理,而不是为了某种实用的目的,比如“纳税,但可以尽情地对税收大加议论”,这便是成年状态的特征。)因此,福柯精辟地指出,在这里“启蒙”是由意愿、权威、理性之使用这三者的原有关系的变化所确定的。显然这一理解涉及的主要是人的一种生存态度与生命姿态,而未从人性的内在规定性方面着眼。其实,康德在关于启蒙的论述中也没有专门对此做出规定,但他在讨论人的理性与意志的关系等哲学命题时涉及到这一问题,在他看来,从一个粗糙的人达到“真正成为人”的状态需要满足这样的基本条件,即人的意志只有不顾欲望、爱好和外界的支配,完全依照理性的先天道德原理,做到自律,即真正的自由或独立自主时,才有道德性,而人也才真正成为人。显然,在这里,理性的最高目的不是知识、科学、必然性,而是使意志实现自由,成为一个自由的、道德的、善的意志,这也就是人类理性的整个使命或天职。康德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可以视为康德在人性解放层面上对启蒙下定义的总统摄性的观点。
康德揭示人性的最高境界时用了一个关键的概念,即“自由意志”,这里所谓自由意志与一般人所理解的“意志的放任”以及顾名思义的“意志的自由”绝不相同。一方面这种意志是自由的、独立不倚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又是自律的、具有道德性的和善的意志。这就意味着其自由性从哲学上划出了明确的边界,即意志只有既不受来自身体的欲望,又不受来自外界的支配时,它才是自由的。以黑格尔的说法,“当意志并不欲望任何另外的、外在的、陌生的东西(因为当它这样欲望的时候,它是依赖的),而只欲望它自己的时候———欲望那意志的时候,‘意志’才是自由的。”绝对的“意志”就是欲望成为自由的意志。自己欲望自己的“意志”,乃是一切“权利和义务”的基础。它自身是绝对的、在自己为自己的、永恒的“权利”,在和其他各种专门的权利相比较的时候是“最高的权利”。靠了这种最高的权利,“人类”成为“人类”,所以它是“精神”的基本的原则。9
无论是康德从人之“真正成为人”的前提,还是黑格尔从“最高的权利”或人类精神的基本原则等角度来讨论自由意志,都有一个共同的人性论的价值学预设,即自由意志是人性上升的“阿基米德支点”。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把地球推动。无独有偶,康拉德也有一句名言:给我相当的字,正确的字,我可以移动世界。可以说,“阿基米德支点”是人追求超越性也是人之实现超越性的惟一动力支点。当然这里说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如果从人性自身的范畴内看自由意志,它正相当于这一实现自我超越性的支点。没有这个支点,人性就只能沉沦于动物性或者“未成年状态”之中,有了这一支点,人性的潜能———诸如人的先验道德律等———就被激发出来,通往“人性的最高阶段”。
自由意志作为人性启蒙的“阿基米德支点”,还意味着它必然被置于一种动态的人性上升的链条上,它本身主要作为一种动力而存在,尚不能囊括人性至高之境界的全部因素与启蒙人格结构。正如卡西尔论述启蒙时强调的:“启蒙思想的真正性质,从它的最纯粹、最鲜明的形式上是看不清楚的,因为在这种形式中,启蒙思想被归纳为种种特殊的学说、公理和定理。因此,只有着眼于它的过程,着眼于它的怀疑和追求、破坏和建设,才能搞清它的真正性质。”10同样,要搞清楚自由意志的真正性质就需要考察它的先在来源与前趋方向。联系康德及其他启蒙思想家的相关论述可知,“自由意志”往前追溯应为“理性意志”,往上提升则为“道德意志”,是人的低级存在状态向人的高级存在状态的过渡地带。以下拟进一步从这一动态的链条上追踪意志的来龙去脉。
在康德看来,自由意志是通过大胆地公开地运用“自身的理性”而得来的,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也就是一种理性意志的在场。而理性意志又是针对非理性意志而言的。斯宾诺莎指出,人的自由受着两大束缚,即屈从于自己的情绪和对必然性缺乏认识。他说的必然性,就是指实体存在的必然性,也就是界普遍的秩序、,或曰宇宙真理。为此他提出了“理智拯救”论的命题,即试图将人类理智从屈从于自己情绪奴役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而使理智认识必然性为生活的宗旨,为至高的道德和至上的幸福。这样经过理智拯救的情感已经不是被动情感,而是主动性的情感,或曰理性情感,是认识必然性或真理的情感,因而是神圣情感;而被动情感是被奴役的,是非理性和不自由的。11这样的主动情感即具有了“意志力”,从而促使被动的非理性意志上升为“理性意志”。
自由意志的进一步提升则意味着道德意志的确立。据伯林在《反启蒙运动》中对康德的理解,只有那些主动行动而不是被迫行动,那些在自愿接受的原则指引下根据道德意志的决定采取行动,并在必要时进行抵制,而不是出于不受他们驾驭的因素———不管它是物质的、生理的还是心理的(例如:情绪、欲望和习惯)———无法摆脱的因果压力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被恰当地认为是自由的,或者才能说他们是道德的行动者。康德由此引起了一种对道德自律的崇拜。这也就意味着,意志的自由在本质上将是意志的自律,是道德意志的生成。在自由意志的范畴内,解决的是“为意志而意志”的问题,而在道德意志的层面上,则产生出“为道德而道德”的命题。康德指出:“我们是有理性的存在物,我们的内心道德律使我们独立于动物性,甚至独立于感性世界,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摆脱尘世的限制,向往无限的自由世界。这才真正体现了我们作为人类的价值和尊严。”12无论在什么时代还是哪个民族,也无论是人类还是个人,都需要以一种“道德律”作为精神支柱以维护自身的价值与尊严,而这一道德律又必须是形而上的。此乃人类理性的自然趋向之所在,所以康德还强调:“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13在这种“为道德而道德”的形而上层面上,人格、信仰、上帝等终极性的人性超越性因素得以进入自我启蒙的内涵结构之中,成为人实现最高本质的标志。启蒙神学家莱辛所推崇的形而上的“信仰”就蕴涵着这样一种认识:“世界归根结底是作为自己核心的理性的表现形式,而且人们可以,也应当以道德之身生活在这个世界上。”14“真理必定使人类走向道德的完善。”15换言之,道德意志要求人性自身最终抵达启蒙人格的完成。人性启蒙的过程于是成为自由与自律相统一,理性与信仰相统一,欲望与意志的统一的过程。完成了这一过程,人就不复是单纯由欲望决定的人,即“欲望的人”,不复是单纯由情感决定的“情感的人”,也不复是单纯由理性决定的人“理性的人”或“单面的人”,而是真正成为人的、启蒙了的、道德的和自由的人。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福柯将启蒙具体发展或者说修正为一种“我们自身的批判的本体论”,并试图“对我们是什么的批判,既是对我们之被确定的界限作性分析,也是对超越这界限的可能性作一种检验”时,特别指出,“我们自身的批判的本体论,绝不应被视为一种理论、一种学说,也不应被视为积累中的知识的永久载体。它应被看作是态度、‘气质’、哲学生活。”16显然,启蒙无论作为一种“态度”、一种“气质”,还是作为一种“哲学生活”,必然是由个人自行负责的,此时它与人的生存环境、人的身份等暂时失去了必然的关联。于是,启蒙在本质上成为一种“人性启蒙”,成为一个哲学问题,一个伦与本体论的问题。进言之,从康德的“以人为目的”和对道德自律的崇拜,到黑格尔的“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的判断,都暗含着对启蒙主义最终目的的思考。启蒙在此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纯粹的审美问题。
三、问题与描述:“人性启蒙”的审美演绎
基于上述判断,以下试图将人性启蒙还原为审美问题,通过文学史上的审美行为进行一次简略的描述。审美上的人性启蒙是一个人性被拯救与自我拯救的过程,一个被塑造与自我塑造的过程。它应该包括:人性解放—人性上升—人格完成,这样的一个“三部曲”联贯合成起来才算是真正走上启蒙之途。
真正的“启蒙了的”人性是怎样的呢?它意味着一个个体关于人与自然,关于自我的欲望是什么,是否应该实现和追求某种欲望,以及活着的意义在哪里等等问题都有一种充分的“自知之明”,达到了一种哲学上称之为“澄明”的人生境界。而这种境界与个体的身份无关,如果没有启蒙的人格,一个腰缠万贯的人过得不如一个穷人更有意义,更幸福,也可能一个人的才能、金钱、地位恰恰成为主人的灾难。因为,这些东西从根本上讲系“身外之物”,只有它符合人性要求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启蒙既然侧重于“人性启蒙”,那就与社会启蒙、政治启蒙等有所区别。
第一步“人性解放”,主要指欲望、本能的解放。祥林嫂就没有跨出这一步,她花费“巨资”捐的门槛恰恰成为她永远跨不出去的象征。谁跨出去了呢?莫言《红高粱》中戴凤莲的“野合”,刘恒《菊豆》中菊豆的“乱伦”,郁达夫《沉沦》主人公为性而苦闷,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主人公渴望被灵魂肮脏的凌吉士亲吻,舒婷的《神女峰》高呼“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的神圣,这些审美形象便将人呼唤到本真的存在中来。如果没有这第一步,就谈不上反对封建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张贤亮的《习惯死亡》中有一句话,说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一个大的修道院,什么时候中国变成一个大的妓院了,中国就进步了。———这句话至少说对了一半,因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7不过还有一半不对,因为它拒绝探讨人性由此上升的问题。
第二步“人性上升”,又包括三个方面,也可以说是三个小步骤。其一,从欲望中生发出情感来,在情感中上升。所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所谓“愤怒出诗人”,都是将被压抑与扼杀的欲望转化为审美的情感。其二,从欲望与情感生发出理性来,并在理性中上升。这就意味着欲望是全面的,是“人”的,而不仅仅是动物的欲望。其三,情感与理性在现实中往往是矛盾的,怎么办?那就需要进入第三个小步骤:在情感与理性的“相互激荡”中上升,而不是在情感与理性的矛盾中沉落。如《沉沦》的主人公到妓院去得到的不是欲望的发泄,反而被激发出自怜与自爱的复杂情感与理性,以及强烈的人格自尊。可以说,这个小说的意义恰恰在于他拒绝沉沦。但卫慧的《上海宝贝》就没进入“人性上升”的第二层。《乌鸦———我的另类留学生活》的作者九丹更甚,非但如此,九丹还笑话卫慧“虚伪”,说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开始还算接近一个女人的本质,后来林白就“穿上花衣裳”了。她的理由是一种赤裸裸的欲望逻辑:“你们都说我是妓女作家,可是你能肯定人们更爱看淑女写的东西吗?”而同样是涉性描写,《廊桥遗梦》就通往人性上升之途。《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也相似,性在这里不但是美的,而且与文明对人的异化想对抗,以人的本能、情感与理性的相互激荡抵抗人性的麻木与社会生活的机械化、官僚化。正如拉康所说的:“欲望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性欲或其他生理性的欲望,而是所有欲望和需要———从食欲、性欲到审美需要和伦理要求———的渊源和本体。”18在这里,人的本能的东西在上升,在往一种超越境界升腾。
第三步“人格完成”则指在前二者的基础之上,个体自我塑造出了一种自由意志,有了自由意志(理性意志),也就标志着一个个体的人格通达一种启蒙人格,进入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自由意志由于是经过了前两步的启蒙过程而完成的,所以不是一般人理解的“随心所欲”,不是阿Q说的“我想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意志已从人性的欲望、本能层面超拔出来,从而取得康德所谓“不顾欲望”或黑格尔所谓“为意志而意志”的自由状态,并最终达到一种可称为“道德形而上主义”19的人性存在状态。
需要强调的是人性启蒙“三部曲”的“联贯性”问题,第一,只有其中的一步不是真正的启蒙;第二,缺少了其中的一步也不是真正的启蒙;第三,把这个过程的顺序打乱了或者颠倒了也不是启蒙。祥林嫂的问题就在于一出生,她的“人格”就完成了,意志就定型了。这是启蒙的颠倒。当下流行的下半身写作、妓女文学,则是仅仅停留在第一步。“上海宝贝”除了性,就是与性相关的莫明其妙的情绪,这种“人性”即使得到了,也是一场空虚,一种自欺欺人的虚假的自由。
那么一个个体怎样才能实现这个“三部曲”呢?这就一定要解决“被启蒙”与“自我启蒙”的关系问题。正如福柯指出的:“他(康德)在文章一开始就要读者注意,人自身要对所处的未成年状态负责。应该认为,人只有自己对自身进行改变才能摆脱这个状态。”20启蒙的完成最终是靠自我启蒙与自我拯救来完成的,是自我提升的过程。接受前人与先知的与启发是必要的,但这种被启蒙仅仅是一种外力。如果仅仅靠外力,仅仅是接受来自灵魂以外的培养、灌输、导引,很难保证个体的启蒙之途能够沿着人性上升之途演进。而且如果让外力转化为一个人的灵魂的最终归宿、最终极的道德诉求,那就会非常危险地“将自由牺牲于它物”,成为信仰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活人献祭”21。作为审美问题的“人性启蒙”的最高境界,主要限定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与道德形而上主义之“自我为自我立法”的追求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一个生命的个体没有达到这种境界,那罪责在个体,因为他没有进行充分而艰难的自我启蒙与自我拯救,始终处于“偏见”状态。也因此,对于现实中的人来说,千万不要将自我的失落统统归咎于他人或社会,迁怒于一切外在条件,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尤其如此。由之,“新启蒙主义”也就包含了“自我新启蒙”的意味。
注释:①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96页。②卡西勒:《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页。
3福柯:《何为启蒙》,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531页。
4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4页。
5福柯:《何为启蒙》,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532页。
6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7-28页。
7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2页。
8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3页。
9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454-455页。
10卡西尔:《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页。
11冯玉珍:《理性的悲哀与欢乐》,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0页。
12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64页。
13康德:《形而上学专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63页。
14维塞尔:《莱辛思想再释———对启蒙运动内在问题的探讨》,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65页。
15维塞尔:《莱辛思想再释———对启蒙运动内在问题的探讨》,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
16福柯:《何为启蒙》,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54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18引自王杰:《审美幻象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1页。
19参见拙文《道德形而上主义的三重境界》,《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
20福柯:《何为启蒙》,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530页。
21赫尔岑:《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37页。
上一篇: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下一篇: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论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