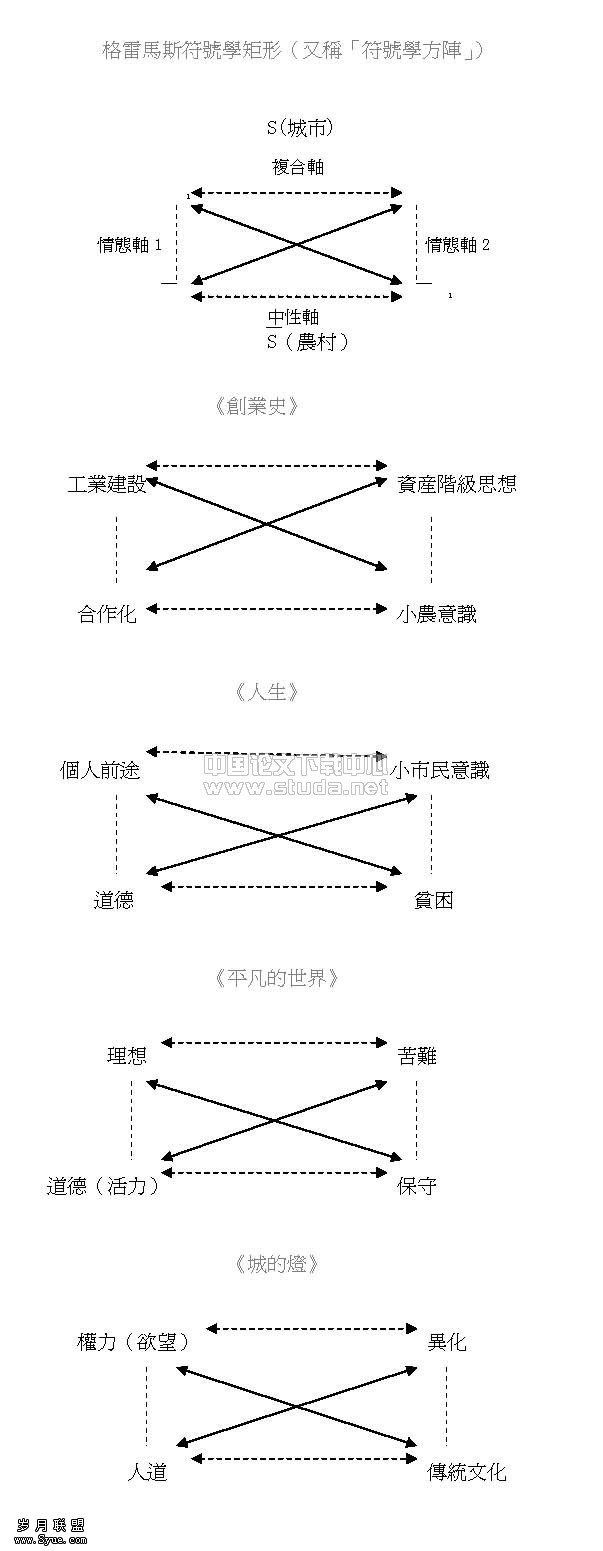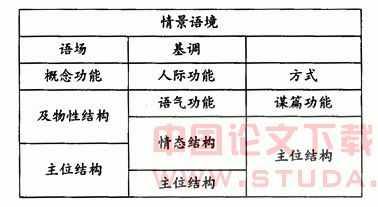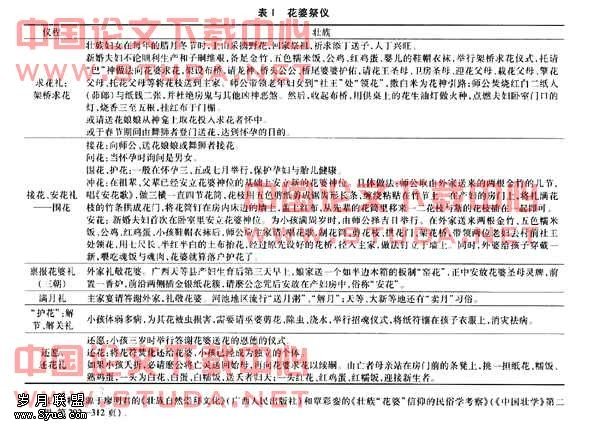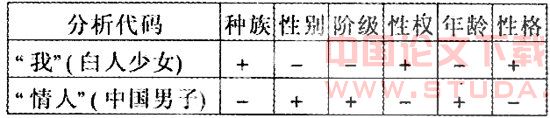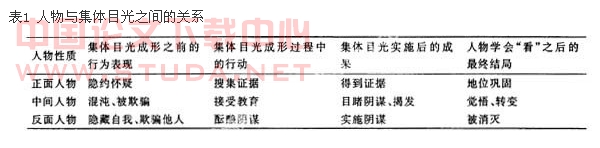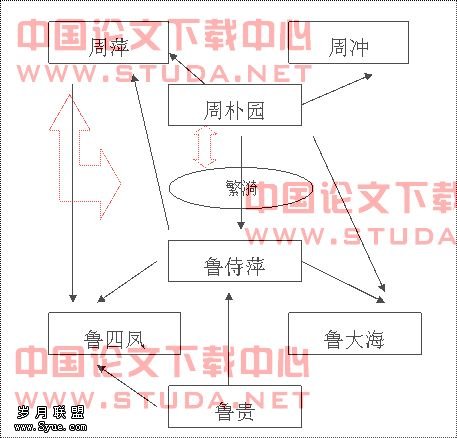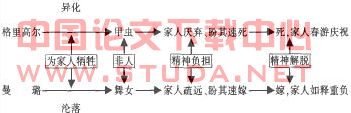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那么应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它到底有何特征呢?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其特征在于,从人的本能欲望之发掘与提升到人的自由意志之塑造并进而实现创造性的自我,从逻辑上说这是一条线性结构,但在这一线性结构的中心环节又有一个由理性与情感的动态激荡而形成的面式结构。②它的介入使整个启蒙过程成为一种复式结构:其一是从本能欲望——理性——自由意志——创造自我;其二是从欲望——情感——自由意志——创造自我,二者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一复式结构的特点在于前者与后者之间互为前提互为保证,缺一不可。换言之,理性通过对情感的作用保证后一结构的完成,而情感通过对理性的作用又赋予前一结构以合法性。如果将其置于启蒙主义的文化动力系统之中,二者的交互作用共同指向自由意志的塑造,也标示了逻辑统一性完成;而从美学范畴来说,这一动力系统中的理、情、意分别表现为真、美、善,真与美的互动地指向善,而“自律的创造的生命自我”之形成也就标志着通往真善美相统一的最高境界。对此郁达夫的说法极有代表性:“小说在艺术上的价值,可以以真和美的两条件来决定。若一本小说写得真,写得美,那这小说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社会的价值,及伦理的价值,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尽可以不管。不过事实上凡真的美的作品,它的社会价值,也一定是高的。”但是这种效果是“间接的影响”,不能是有意识的,因为“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品,既具备了美、真两条件,它的结果也必会影响到善上去。”③由此就决定了其启蒙叙事既不是纯理性主义的,也不是纯感情主义的;既不是纯自然主义的,也不是纯浪漫主义的。这两种叙事可称之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理性主义叙事”。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可以重新解释为什么在“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思潮与浪漫主义思潮同时成为文学上的热点,为什么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几乎同时崛起于文坛,其“对立互补”正蕴含着上述必然性与合理性。扩而大之,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的启蒙叙事之所以以“理性浪漫主义”与“情感理性主义”为特点,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
二
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其特点在于虽然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有关情感、情绪的来源、内涵、力度与价值指向等等莫不与理性相关,在它的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早在清末民初时期的言情小说,尤其是苏曼殊等人的创作中就以其新旧过渡时代所特有的情思方式展现出黎明前的清新气息。到了“五四”时期,以爱情为核心的情感表现更成为文坛的最辉煌的景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启蒙者不但把情爱婚姻问题视为反封建思想的突破口,而且还将其视为囊括新道德与新理性的象征。“对解放的普遍心理都把爱情和自由融为一体,意即通过恋爱并激发个人的热情和能力,他就能变成一个完美和自由的人”;爱情“还被视作一种违抗和真诚的行为,即敢于冲破伪善社会种种人为束缚,而寻求真正的自我”。④对爱情婚恋的专注所表现的不但是作家的一种新的人生观、道德观,更是时代的一种价值观。爱情作为文化转型期的最为敏感的一大焦点问题,其象征性和启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自称“为爱情而爱情”的湖畔诗虽然并不注重以情爱婚恋去反映社会问题,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从世俗观念和封建礼教禁锢中解放出来的直率与喜悦,表现了青年人自己“真的声音”。在冯雪峰的《山里的小诗》、应修人的《悔煞》、 汪静之的《过伊家门外》、潘漠华的《寻新生命》等诗作中,他们怀着青春稚气歌咏爱情的欢欣,怀着天真痴情歌咏爱情的坚贞,满怀热烈的向往歌咏爱情的大胆,怀着热恋的心态歌咏爱情的令人颤抖的神秘力量,怀着对未来的执著向往歌咏爱情给诗人带来的“崭新生命”。诗中的爱情主人公形象以其天性的纯洁、真挚和对爱情甘苦本身的执着追求,针对封建旧道德、“伪道德”发出了独特而叛逆的宣言。正如周作人在反击封建卫道士斥责这批情诗“轻薄”、“堕落”时所说,“这旧道德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⑤它指向了崭新时代和人的觉醒所必需的道德理性。
“五四”的时代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自立、创造、朝气勃勃的青春精神。一代青年作家感应了时代的脉搏,以自己的青春心态和全新创造跃到了这场时代洪流的波峰。此时暮气沉沉的中华大地正需要他们。保守、中庸而不乏温情脉脉的传统文化心理,正需要、也只能靠一种狂暴的、不重经验的(甚至必然是偏激的)叛道的一代人来冲决。郭沫若那首被誉为“唱出了个性解放的最强音”的《天狗》便典型地表现了这代叛逆者横空出世,睥睨一切,扩张自我,创造“新我”的决绝姿态。这个“新我”是“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我的心肝”,彻底与“旧我”决绝之后更生的,“新我”不相信“还有位什么父亲”(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郭沫若《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在这个“自我”的面前,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切上下尊卑的封建伦理、封建权威,都被踏倒,都被毁坏。叛逆者的“新我”汇集了“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具有无穷的力量,可以“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郭沫若《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这个“新我”按捺不住从恶梦中醒来的惊喜与热情:“我的灵魂是琴声似的跳动,我的脚步是江水一般的奔跑,我向着一切欢呼,我向着一切拥护。”(冯至《月下欢歌》)总起来看,这个“新我”形象虽是浪漫主义者个性的表现,却综合了“五四”文学理性探索精神的的方方面面,成为“五四”人道主义灵魂的典型的最强有力的化身,成为一种主客体相互渗透,超越了族界乃至国界的精神象征。
美籍学者李欧梵曾注意到,西方浪漫主义的两种典型形象——维特型(消极的感伤)和普罗米修士型(充满活力的英雄),深刻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文学的两类浪漫主义,这就是以郁达夫为代表的“消极浪漫主义者”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者”。⑥如果说上述“新我”形象极为接近“凭他的个性来影响世界,改造世界——甚至是创造一个世界成为一个新的普罗米修士形象”,那么在郁达夫等带有感伤色彩的浪漫主义作家笔下,则塑造了一批“带有普遍性的忧郁症”的维特型形象。⑦这是一批发现了自我,但无力“忠实地守住这自我,彻底地主张下去,扩充下去”的“零余人”、“漂泊者”形象。尽管这类形象所表现的并非先觉者对他们由愚昧走向觉悟,由沉默走向思考,或追求个性解放,或追求独立意志等觉醒因素的理智性的肯定和赞美,作家也无意于对其作理性的剖析,而是一任自身情感情绪起伏奔涌,但这里的情感却莫不是觉醒者——也只有觉醒者才会有的“性的苦闷”、“生的苦闷”。觉醒者对理想的追求和爱情愿望,无论是在视中国人与狗等同的岛国日本,还是在军阀混战、政治黑暗的20年代中国社会,都是无法实现的。当他们闻到了“真的人生”的气息之后再也不愿回到从前“奴隶”的位置,于是苦闷、孤独、徘徊、痛苦、忧郁、悲观、绝望纷纷袭来,像“一只迷途的鸟”,“漠漠寒潭里的孤舟”,“任着狂风苦雨的飘零”,“任着舟子的流浪”(林如稷《流霰》)。但在他们表面的伤感、悲痛后面潜藏的是一颗剧烈跳动的愤世嫉俗的反抗心灵。冯沅君《隔绝》的女主人公宣言“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并最终以死殉情,对封建礼教做了彻底的叛逆。总之,在这批既是作者“自我”又是与“自我”同病相怜的以“苦闷”为特征的知识分子形象身上,所表现出的最终价值仍在于与“五四”启蒙人道主义潮流的内在契合,在于对“人”的主体自我意识的表现。而这种自我意识基本上是在以下两个指向上展开的:一是同社会处于对立状态的主体意识的,迫切要求自我生存方式的确立和自我价值在现实中的实现;一是与封建意识形态相对立的自我本能的觉醒,迫切要求冲破封建伦理体系使自我的感性生命欲求得以实现。二者所表现出的社会主题与文化精神共同加入了启蒙主义文学以“立人”为核心的理性协奏曲之中。
正如郭沫若所说,诗人虽是感情的宠儿,他也有他的理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在审美上的情感化从不拒绝理性的底蕴与理性的理想,只不过这种理性的宇宙观不具备审美创造的本体价值,而是在情感的发现和创造性中自然而然体现出来的。这意味着启蒙主义的情感在本质上具有引发人的理性思考、理性探索的能力。就人类的情感体验来说,无论是社会的物质现状还是意识形态(包括社会制度、文化思想、社会舆论等等)都会对它有直接的影响。当这种影响是引起情感向着不满足、受压抑乃至痛苦不安的方向活动时,主体必然会重新思考审视社会、人生及其与自身的关系,产生改变现状从而满足情感需求的愿望及行动的趋向。这样情感的需求也就逐步转化、上升为理性的需求。由于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外在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往往不能满足个体的情感需求(这种对立基本上是越往前追溯越尖锐),因而对情感的肯定、情感的发现总是促使文化向着进步的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的发现也就是情感的解放,而情感的解放也就是发现人本身,从而促进理性的觉醒和解放。同时它的意义与价值还表现在,理性作为一种相对远离感觉、心灵、体验的东西,它的指向、深度、价值是不是符合人性的与进化的标准,单靠它自身是无法证明和检验的。这与西方理性主义不同,在康德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体系之中,理性自身就具有实践能力,而它何以有这种自我完善的运行机制是不言自明的。因而启蒙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在他那里就只剩下理性如何实践自身的问题。中国的启蒙主义者不相信存在着这样的纯粹理性,他们在崇拜理性的同时,还需要通过人的真实情感进行检验或者修正。这样的理性观与启蒙观导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可谓是势所必然。
30年代前后,上述理性浪漫主义叙事逐渐分化为这样几种形态:一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叙事”,包括概念化与革命情绪皆强的某些革命文学创作、为政治服务的歌颂性文学等。有人把中国20世纪从《新中国未来记》、创造社的创作到革命浪漫主义、“高大全”、“三突出”的文学再到张承志小说等等,统称为“启蒙浪漫主义”文学思潮,⑧这样做实有眉毛胡子一把抓之嫌。应该说,某些政治性的浪漫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在本质上背离了启蒙主义的范畴,因为其情感不是源于自由理性而产生的,它自身也不具备促进理性的觉醒与解放的启蒙动力,因而在论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时这类文学创作不具备代表性。二是“道德的浪漫主义叙事”,这一叙事特点在于用浓厚的抒情性方法,通过对内心情感体验的表现,集中对道德理性与实践理性进行挖掘和探索,如沈从文小说、巴金小说等等,在理性问题上表现出对于道德的困惑、道德的探索、道德的建构与道德的理想。这一叙事较完整地继承并发扬了“五四”启蒙主义的这一叙事传统。三是“人性的浪漫主义叙事”,此种叙事在艺术表现上更具有个人体验的色彩,侧重于人的被动情感而非主动情感的探索,诸如人的莫名其妙的情绪冲动、隐密的心理状态、变态的心理倾向以及宗教式的神秘体验等更加非理性化的东西。“五四”启蒙主义叙事传统中的“理性”,在此被置换为对人性中超然性与神秘性方面的普遍性进行心与哲理的审视。这又以张爱玲、“新浪漫派”等为代表。
三
由于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源于人的态度体验的非理性因素,具有自发性、个体性等特点,因而它对人的理性觉醒的促进作用总起来说是渐进的、自发的,缺乏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对人类群体进行启蒙的作用方式常常表现出短暂性、突发性。而理性的觉醒则往往能够较大幅度地引发情感的解放,不但有时表现为爆发、突变的方式,而且具有持久性和逻辑力量。周作人在解释到底什么是平民文学时曾指出,所谓“平民文学”,并非只是专做给平民看,专讲平民生平或平民自己做的文学,也“决不单是通俗文学”,更不是指那“慈善主义的文学”,而主要是指那种以平民派的观念“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这就要求作家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而描写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时,其正确的态度应是“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浑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便我的事。”⑨这里需要注意两点:其一,周作人用“研究”一词来说明作家应持的写作态度;其二,他强调作家主体应以人类为本,也就是作为其中的一个“单体”体验人性的普遍性。两个方面都意味着以一种理性的姿态进入艺术世界的建构之中。深受“五四”影响的苏雪林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正是那时的启蒙思想在她的心灵种下了理性的种子,她反复声称自己“是一个平日喜以唯理主义‘五四人’自命者”,“我们心龛里供奉着一尊尊严无比仪态万方的神明——理性”,那么在她心中这是一种怎样的理性呢?1994年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五四以前,对‘我’的认识不明确;五四后对‘我’有深刻的了解,认为‘我’应该有独立的人格与权利,可以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⑩之所以援引这几番话,是因为它是从一个“世纪老人”,一个深有体会也最有发言权的作家那里发出的声音,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苏雪林仿佛更为深情的回忆起正是那时理性给人们带来了无以伦比的情感的新生。这种理性的崇拜表现于艺术叙事范畴就是情感理性主义叙事。
从艺术表现的主体而言,情感理性主义叙事表现为如马克思所说的以“思维着的悟性”衡量一切价值,评判一切现象。基于国民性对启蒙主义理想的严重阻害,叙事者通过深刻的笔触与典型化不遗余力地“攻打病根”,“撕去假面”,揭出国民的愚昧、保守、迷信、麻木、苟且、孱弱等痼疾,“活画出一个个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闰土的麻木,华老栓的迷信,孔乙已的迂腐、穷酸,单四嫂子的孤独与空虚,沛君的自私自不必说,在《离婚》中连乡绅地主慰老爷也不放在眼里的敢于反抗夫权、族权的爱姑在七大人一声“来……兮”的威严下突然偃旗息鼓,表现出了她刚强泼辣的外壳下深藏着的灵魂的软弱以及对封建政权抱有幻想的麻木心理。鲁迅的启蒙小说不仅展现了中国国民精神上的麻木病态,更重要的还在于展现了这种国民性弱点和病根之所在。人们自己被封建主义吞吃不作反抗,却又以封建伦理道德标准论理处事,律己衡人。这种国民性弱点不仅使他们成为“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且常常成为“吃人”者无意识的“帮凶”。“无意识的杀入团”几乎成为鲁迅所有小说中的一个永恒的艺术环境。通过对这不见血的虐杀的揭示,“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切中了中国积贫积弱的要害。
从表现对象来说,情感理性主义叙事则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理性的觉醒起着肯定情感、发现情感、升华情感、锻铸意志、培养信仰等作用。无论在的封建社会还是西方黑暗的中世纪,人总是匍匐在上帝或皇权的脚下,人的正常的情感需求被否定和遏制,当人们从神学、礼教的愚昧中走出来,确立了人自身的价值,被压抑、否定的情感便在这种启蒙主义思潮所蕴含的理性精神的照耀下得到了确认和肯定。而另一方面,人类的情感是丰富多采的,同时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又是千差万别的,在发现人与发现世界的理性探索过程中,那些微妙的、曾经被压抑的或存在于潜意识之中的情感形式会不断得到发掘,从而使人的情感日益丰富充盈。像“五四”时期问题小说、问题戏剧中的小知识青年形象,作为从“铁屋子”里被先驱者“嚷起来”的“较为清醒”的少数者,随着新思潮的广泛传播,他们开始睁眼看社会现实,重新思索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劳工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家庭问题,到国民性改造问题,一直到人生目的的问题,等等。他们的苦闷、彷徨、失望、求索,莫不源于新的理性精神。冰心《一个忧郁的青年》的主人公彬君便道出了一番典型的反映这类青年的心理状态的自白:从前“我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但现在,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比如:“为什么有我?"“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念书?”下至穿衣、吃饭、说话、做事,都成了问题。从前是不求甚解,浑浑噩噩的过去,现在是要明白人生的意义,要创造我的人生观,要解决一切的问题。胡适小说《一个问题》中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主人公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象我这样养老婆、喂孩子,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吗?"这正是鲁迅笔下的狂人所发出的“从来如此,便对吗?"的疑问,在这些重新思索、重新行动的人物形象身上表现出了理性给人带来的新的情感体验。正如穆勒告诫人们的,“宁愿成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却不要成为踌躇满志的猪。”11如果说这里充满了悲哀,那也是可贵的悲哀,新时代的悲哀,因为它蕴含的是新的理性精神,绝不如有人所指责的是激情压倒了理性。
第二,理性的觉醒既扩大了情感的幅度,又改变了人们情感的强度和方向。喜、怒、哀、乐本是人之常情,但人在理性并未得到充分解放的阶段,因价值理性的缺限而使情感的表现趋向于中和,少走向极端,传统的“中庸”之道、“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等即与此有关。而当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通过理性的觉醒并产生明确而笃信的价值观念、价值准则时,情感的表现也就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方向和强度,从而获得新生。曹禺《日出》中的陈白露在与方达生重逢之前,其理性被掩盖于纸醉金迷的情感天地中,在与方达生的思想交流与交锋中,她一度追求的个性解放思想重被唤醒,理性的介入终于使她对那种“妓女不像妓女,姨太太不像姨太太”的生活方式以及周围的环境,产生了厌恶的强烈感情。虽然她的理性觉醒的程度尚不能使其重新获得新生的勇气,但足以使她产生了“与黑暗同归与尽”的意志。她的死告诉人们要真正实现自我必须进一步追求理性的力量。《北京人》中的愫方深深地爱着曾文清,为了使他实现“人成为人”的真正生活,她自己情愿留在曾家这个封建牢狱中忍爱着无穷无尽的精神折磨。对文清的希望成为她情感世界的惟一的太阳,这种情感的寄托使她进一步形成了甘愿自我牺牲的意志。我们可以想见,如果曾文清终生不回,她也就将会在这种“又凄凉又甜美”的情感体验中生活一辈子,因为没有理性的力量使她改变这种被动情感与非理性意志,她的一切价值观念尚囿于传统道德的范畴。是曾的失败为她“换出一个‘明白’”,使她拥有了自己的理性,而正是这种理性的觉醒否定了她自己过去的情感体验与意志,使她完成了从寄希望于他人的复活到决意自身复活的飞跃,毅然决然地“逃出快要压上盖子的棺材”。
对于理性与情感的关系,大卫·贝斯特曾结合艺术欣赏作过十分精僻的论述:理性对于欣赏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为适当的反映提供理解力。此外,在一定的范围内,一种新的解释的理性可以改变对象,即改变人们对作品的概念,因而改变情感的特征。扩而大之,“理性能够改变人们的概念,并进而改变人的情感。”由此他特别提醒说:“我们应该认识到,精神、理性同情感是一致的;情感——尤其是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的情感——与认识能力是无法分开的。”12大卫·贝斯特还进一步将审美活动中理性对情感的作用概括为这样几点:一是提供理解力的理性和改变艺术作品的概念能够决定于艺术作品的情感变化。二是情感介入艺术需要理解力。三是扩大理解力的理性提供了扩大情感范围的可能性,这就使通过艺术进行情感培养有了意义。13为此,他还以莎士比亚名作《奥赛罗》为例加以证明:起初,奥赛罗对狄斯德蒙娜的爱大概是基于他把她当作贞洁的化身。埃古为他提供了把她看作不洁的理性,由于接受了这种改变了的观念,奥赛罗的感情变得醋意大发,以致于杀死了她。后来,爱米利亚为他提供了理性,使他认识到怪罪狄斯德蒙娜不贞是错误的,于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情感,即悔恨。这个例子表明,理性的觉醒对于情感解放具有极关键的意义。我们再看陈白露与愫方,一个走向死亡,一个走向新生,就同样表现了理性的觉醒对于情感的决定性力量;而同是“离家出走”,愫方又与子君不同,子君大胆的反封建行为仅仅是源于一个从启蒙者那里发出的理性观念,而愫方的行为却是源于自我的觉醒,所以一个重新回到家庭,一个获得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子君到愫方,表现了由他者启蒙到自我启蒙、由非理性意志到自由意志的深刻转变,也说明只有通过理性的不断觉醒,才能真正实现个人自我的解放与自律的创造的生命。这种启蒙叙事作其所蕴含的独特价值在巴金、老舍、路翎等的作品中都不难发现。
四
作为一种对现实的对象和现象是否适合人的需要和社会需求而产生的体验,情感和其他心理过程一样,是人在实践中产生的。情感过程又是通过态度体验来反映客观事物与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的,并伴随着比较明显的机体变化;而理性是指“人的意识和思维”,作为主体的人,是有意识、能思维的存在物,在人的精神中,存在着概念、推理等理性因素和理性活动。这些理性因素和理性活动都表现为有目的有意识的,并遵循着一定的逻辑规则和逻辑程序而进行的自觉过程。但人的精神属性和精神世界中除了理性因素外,还有无意识、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及活动,也具有在人类活动和人类生活中不可低估的作用。人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的因素的统一构成了人的完整的认知结构和人性结构,没有理性的和没有非理性的人,都不是现实的和完整的人。现实的和完整的人都是理性和非理性、肉体和灵魂、理智和情感的统一。马克思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14这里的“完整的人”,应该就是一个感性、理性和非理性相统一的人。
人的理性总是伴随着情感的过程,二者虽然是人的精神世界中两个不同的范畴,却总是发生着联系,根据我们对情感的认识,会发现二者之间发生着关联的关键点在于主体所持有的价值观。因为一方面价值正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或客体满足主体需要与否的性质及其程度,不同的价值导致不同的态度趋向,而不同的态度决定了情感的体验方式(包括情感的方向及强度等等);另一方面,价值观直接导源于价值理性,而价值理性正是实践理性、道德理性的主要组成部分。价值观属于一种评价活动,这一活动由三种认识活动构成:其一是对客体事物的事实确认;其二是对主体自我需要的认识;其三是对客体与主体关系的认识。三个认识活动均离不开理性因素,没有理性活动就不能认识客体是什么和主体有什么样的需要,从而也就不能作出客体是否能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判断。比如祥林嫂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情感的悲剧。她死于麻木、绝望,死于灵魂的自我放逐、自我摧残,这些都是以她独特的情感体验、反映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而且这种情感正源于她在价值理性上的愚昧无知,或者应该说她只有价值而没有价值理性。或者说是因为她的价值不是来自理性,而是来自非理性的先验信仰——即贞节观念。由此可见,情感的解放最终取决于理性的解放,没有理性的觉醒也就谈不上情感的解放,从而也就谈不上“人的解放”。如此以来,价值理性就与情感过程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再比如同样是受到丈夫的虐待,古典型妇女可以逆来顺受、自我排解或“认命”,并无必然的绝望、忿怒、痛苦的情感的体验;而型妇女则会产生愤慨、不平、反抗等情感体验。这正是由于“男女平等”作为一种价值理性准则已进入现代妇女的心理结构之中的缘故。
随着社会进入异化阶段,情感与理性作为一种矛盾始终伴随着人类。由于情与理产生的根源、二者的运动、其向度与目标等等都具有重大的差异,因而在情感与理性的矛盾结构中,其相互和谐的统一关系仅仅是矛盾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有条件的和暂时的;而二者的对立关系是更为永恒持久和无条件的,它们永远存在着相互抵牾、彼此消涨的关系,这也是痛苦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根源。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文学创作既扎根于时代现实的土壤之中,又具有对人的觉醒与解放的深层次关怀,在文化学、哲学与形而上层面上体现着浓厚的人学理想与超越精神。它认识到人的情感要求与理性要求都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之所在,而且都是不可或缺的方面,同时人的情感、理性需求的不断丰富、、变化又是人类精神不断进步的主要标志;但二者并不是平行发展的,尤其当它以人的存在方式展现于具体时代现实生活之中时,情与理的冲突与矛盾更为复杂与剧烈。这一矛盾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根除的,但在艺术世界中则可以以某种审美境界来实现。席勒曾指出,人有三种冲动:感性冲动是生命,涉及人的本能;形式冲动是理性的道德法则。前者是内在的,后者是外在的,两者都体现为强制。第三种是游戏冲动,即审美,它是弥合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中介。“感性冲动由自己的主体中排除了一切依从性和一切受动。……两种冲动都是强制精神。前者通过规律,后者通过理性的法则。在游戏冲动中两种冲动的作用结合在一起,它同时在道德上和自然上强制精神,因为它排除了一切偶然性,从而也就排除了一切强制,使人在物质方面和道德方面都达到了自由。”15这就是说,在审美中,由于处于规范(理性、道德)和需要(本能、情感)恰到好处的中点,因而摆脱了强制而达到自由。度勒指出了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审美活动是主体对生命与道德理性的自由体认;换言之,审美将道德规范内化为想像力的游戏。启蒙美学家几乎皆注重道德法则在审美观念照中愉悦地内化。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审美功能通过某一种基本冲动即消遣冲动而发生作用,它将消除强制,使人获得身心自由。它将使感觉与情感同理性的观念和谐一致,消除理性的规律的道德强制性,并使理性的观念与感性的兴趣相调和。”16中国近现代的启蒙叙事之所以以理性浪漫主义叙事与情感理性主义叙事为特点,正是为了在真善美的艺术营造中对上述宿命般的存在悖论进行广泛的探求与顽强的抵抗,从而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
① 参见包亚明:《在语言与现实之间》第25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5月版。
② 关于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建构,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③ 郁达夫:《小说论》,《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16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④ 李欧梵:《浪漫主义思潮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第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⑤ 周作人:《情诗》,《晨报·副刊》1922年10月12日。
⑥ 参见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第85-8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⑦ 参见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第85-86页。
⑧ 如郑波光:《20世纪中国启蒙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文艺争鸣》1998年第2期。
⑨ 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19日。
⑩ 转引自沈晖:《论苏雪林与五四新文学》,《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第85页。
11 转引自H.P.里克曼:《理性的探险》第13页。
12 大卫·贝斯特《艺术·情感·理性》第151页,工人出版社1988年8月版。
13 大卫·贝斯特《艺术·情感·理性》第16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124页。
15 席勒:《美育书简》,中译本,第8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
16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