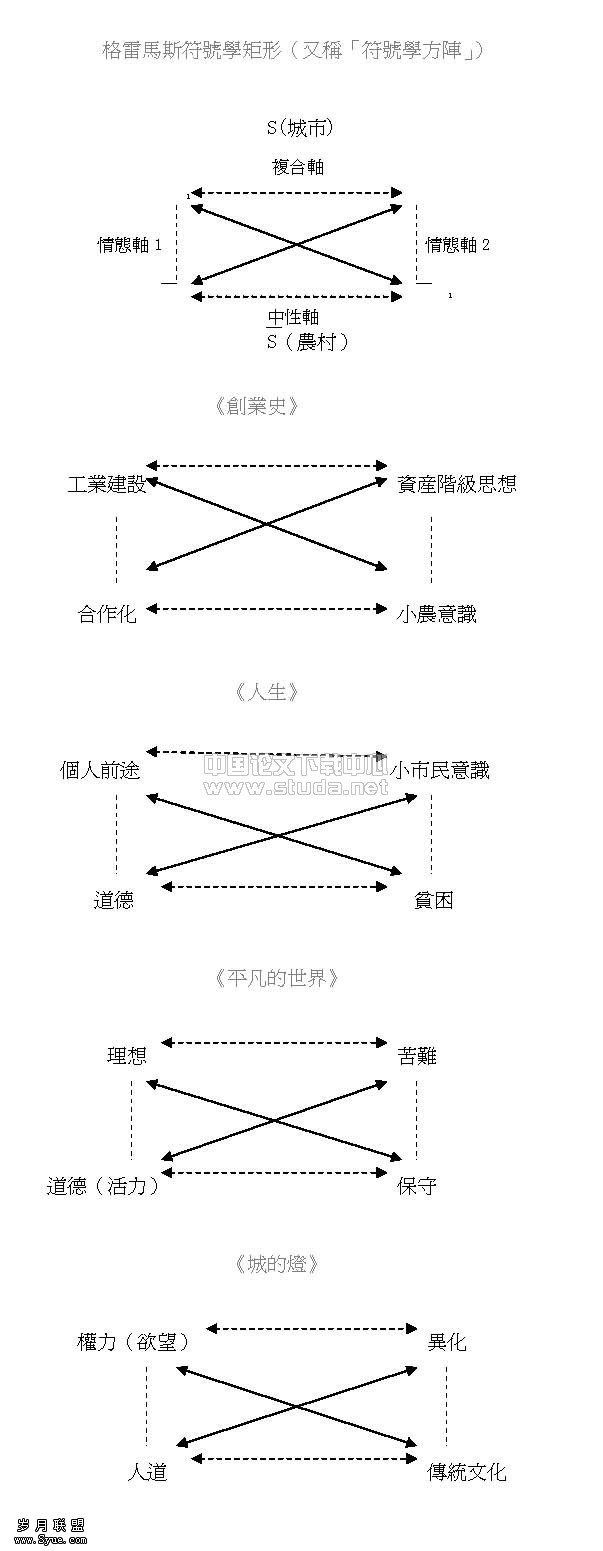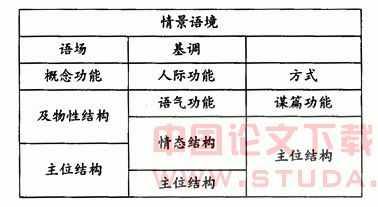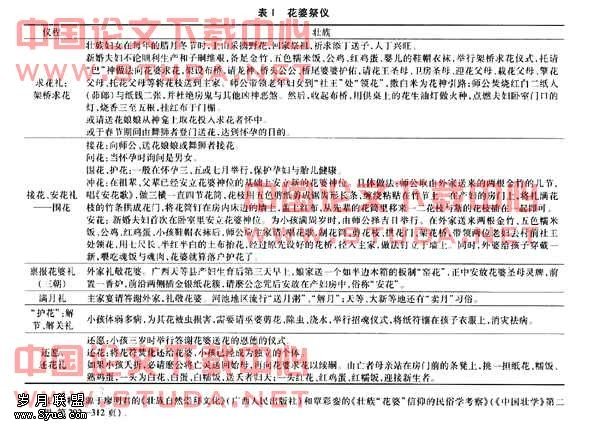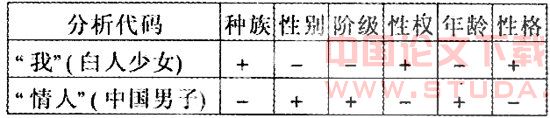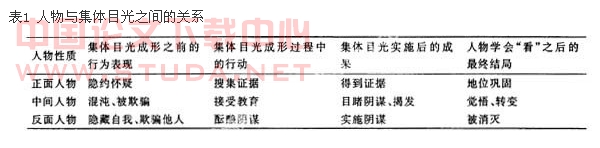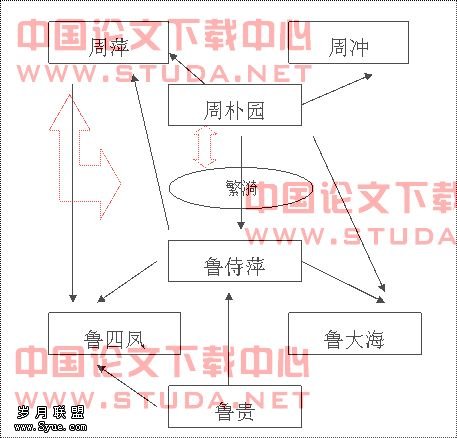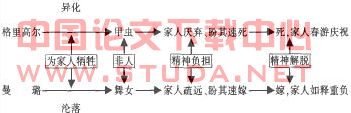施蛰存《将军底头》的「内在性」问题
一、绪论
柄谷行人在他富有启发性的著作《日本文学的起源》中曾提到「内在性」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观察日本文学现代性形构的一个坐标。根据柄谷行人的说法,所谓「内在性」(interiority),是指内在自我(inner self)、内在意识(inner consciousness)的存在,它随着人听到自己的声音,并意识到其存在而展开。[1] 借着考察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现代文学的整个趋势,柄谷行人提出日本现代文学内在性的形构跟当时的言文一致运动、语音中心语言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2] 他并认为,「内在性」并非早已存在,而是通过各种物质形式(例如言文一致运动、私小说的告白形式)的调解(mediation)而构成。[3] 换言之,「内在性」是一种论述效应(discursive effect),由一套特定论述方式所产生。
就笔者看来,柄谷行人关于「内在性」的重要观点,对我们重塑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形成与发展极有价值。若果承认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已逐步走向现代之路,那么,有关「现代性」的问题即不能回避。汪晖在〈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一文中,在唐弢的基础上提出了几个思考「现代性」的进路。汪晖指出,直线向前进行的时间观、语言上的变革、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个人与外界之间的冲突,以至叙事形式的变迁等各个方面,都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特征。[4] 汪晖的文章,提纲挈领地为我们指点了追寻现代步履的线索。近年学者更继续深化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探讨它的多元面向,例如王德威就认为,「现代性的生成不能化约为单一进化论,也无从预示其终极结果」,而由于走向现代性之路有着极多变量,「即使重新排列组合某一种现代性的生成因素,也不能想象完满的再现」。[5] 循此,王氏进一步提出「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个概念,试图挖掘在不断进步的进化论观念以外所存在着的另一种现代性。[6]
在王德威的讨论中,晚清的科幻小说和狭邪小说、鸳鸯蝴蝶派,以至后来的新感觉派、沈从文、张爱玲的创作,都是外于当时写实主义主流以外的写作尝试,带着某种「被压抑的现代性」。那么,一般被视为「新感觉派」一员的施蛰存,他的小说所体现的现代性,又是怎样的呢?若加入柄谷行人的观点作为参照,我们又是否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当然,「内在性」并非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唯一进路,但从这一角度切入,应有助加深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并把握施蛰存小说现代性的其中一个侧面。[7]
若细心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它在五四之初,早已触碰到有关「内在自我」 / 「内在意识」的问题。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倡用白话文写作,反对继续使用不能「上口」的、已经「死去」了的文言文作为现代人的书面语。这个颠覆传统的观点背后,假设了在传统形式写作中 ,「言」与「文」存在着极大的分裂。正是从这个假设出发,新文学运动的提倡者才能高呼「我手写我口」的口号,发起中国本土的「言文一致运动」。提倡白话文、汉语拼音化,甚至废弃方块字,这些举措都反映了他们意欲将「言」和「文」重新结合。透过使言文一致,他们认为人们就可以脱离旧文学形式的约制,用靠近日常生活语言的文字,直接抒写内心所感,从而达到解放思想的目标。
事实上,新文学运动「我手写我口」这个口号的意义是双重的:它除了反映着重新结合日常语言与文字的时代要求,更意味着一个具有表达需要的现代「自我」经已在白话文运动中逐渐形成。众所周知,「表现自我」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从这个主题出发,五四作家创作了不少意在「表现自我」、抒发个人情感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徐志摩「浓得化不开」的新诗、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还是朱自清「意在表现自己」的散文,都是五四张扬个性、「表现自我」主题的产物。正如前文指出,意识到「自我」声音的存在,是「内在性」出现的标记。在作者发现自己心中有话要说,并把它写出来的一刻,「内在自我」经已成形。故此,就这点来说,中国现代文学「表现自我」的主题与其「内在性」形构,是一体两面的。不过,基于文体性质不同,考察小说、散文、诗歌的内在性时,或需要有不同的方式。散文和诗历来被认为是作者的个性的直接表现,其内在性比较容易在文本层面上观察得到,至于小说方面的问题则比较复杂。由于小说以情节和人物构成,作者不能直抒胸臆,谈小说的内在性或要从人物入手。
现代小说的其中一个特征,是着重人物心理的刻划,而非追求情节的曲折。这个特征与「内在性」的出现是紧密连系着的。欧洲十九世纪的心理小说,一般被视为「现代意义的小说」,它不像以往的小说那样,把心理描写当作故事情节的陪补,而是成为了与情节的展开密切相关的内在成分,甚至是情节发展的依据。[8] 因为受到西方小说的影响,大部份五四小说对人物心理的刻划甚为注重。甫发表即轰动现代文坛的鲁迅小说〈狂人日记〉,整篇小说的推进都倚赖于人物心理的描写。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伪源头,[9] 〈狂人日记〉开启了一个独特的写作形式,并首次体现了现代自我的特征。利用白话文及日记体,小说中的狂人,写作并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省悟到自身独异的存在,恰当地体现了柄谷行人所指的「内在性」。
另一方面,郁达夫自叙传抒情小说的主人公,亦集中地显示了作家对现代自我的形构。郁达夫的小说,一方面接受了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文艺活动;另方面吸收了日本「私小说」的手法,着意在文学作品中暴露作家自己的心境。[10] 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不追求曲折的情节和周致的构思,致力写出自己个人的情绪和心理变化,其中最常用的手法是直抒胸臆,即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去描写主人公所经历的生活情景,作坦率的自我解剖,甚至采用长篇独白的形式去直接抒发内心感受。由于想「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以求「世人能了解我内心的苦闷」,[11] 故此他的小说无论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写成,主人公都带有作家浓厚的影子。与日本的「私小说」相似,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透过「告白」的文学形式,创出一个饱受内心灵肉冲突和苦闷煎熬的主人公,在小说中传达那「零余者」(某程度是他的自我写照)内在的声音,而这最终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小说「内在性」的萌芽。
从鲁迅和郁达夫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里,现代小说的「内在性」已经逐渐发展成形。那么,到了三十年代,「内在性」的发展又会否有一新局面?这个问题,笔者以为可以从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中得到答案。
施蛰存,被誉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意识地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写作心理分析小说的作家。[12] 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若以题材来区分,大约可分故事和现代都市生活两类,分别以《将军底头》及《梅雨之夕》为代表。[13] 两者虽各自展现出不同的形态,但同样致力于表现「内在现实」(inside reality)。[14] 一九九九年,李欧梵在他名作《上海摩登》中,对施蛰存小说创作的价值,作出了以下的评价:
作为一个有创意的作家,施蛰存是一个先锋和领路人,冒险进入人类心理中崭新的内在领域,勇于一瞥非理性的力量。他可能是第一个有意识地运用弗洛伊德理论,于小说的现实和「超现实」景观上去带出性欲暗流的中国现代作家。[15]
李欧梵在这里,恰如其份地给了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一个历史的评价。施蛰存在部份小说如《将军底头》中,放弃了直接抒发内心感受的写法,实验以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来描写内心的可能性。透过引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及采用相应的叙事策略,他尝试为其主人公构作一复杂隐秘的心理迷宫。那么,这种对内心的发现与探索,会否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在性」(interiority)的拓展具有特别意义?尤有兴味的是,如果施蛰存的小说,真的揭示了「人类心理中崭新的内在领域」,那么,这个领域是如何在文本中被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条件促使他能够将主人公的内心置于读者的眼前?又或者,文本中这些所谓「内在」都不过是由叙事机制所制造出来的效果?
借鉴柄谷行人对日本文学内在性的研究,本文尝试以施蛰存代表作品《将军底头》为例,探讨其心理分析手法与小说「内在性」的关系。[16] 选择以「故事新编」切入「内在性」问题,一方面是由于「旧题新写」往往能见作者新作跟传统经典之乖离,另方面是为了在新与旧的比较中,凸显作者形构人物「内在自我」的努力。除了《红楼梦》外,传统小说一般较重视情节的铺排,对人物心理刻划常有不足;虽然不少现代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等都曾以现代小说的形式重写传统题材,但这些「故事新编」在展现人物心理方面却未见特别成功。[17] 然而,这些原本很可能是离「内在性」问题最远的旧小说,竟在施蛰存的打造下成为专务展现「内在」的现代心理分析小说。在这些故事新编中,我们将会看到施蛰存的小说是如何借用传统小说暧昧的「先天性缺陷」,塑造出一个个充满张力的内在自我,从而创造出跟传统小说迥然不同的小说主人公;而我们亦将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内在性的发展经已在不知不觉中在施蛰存的手上趋向成熟。
以下首先简介《将军底头》及说明「故事新编」的文类性质;其次借着考察鲁迅、郭沫若等同期作家「故事新编」的特点,尝试为施蛰存小说重构一个较具体的历史语境;然后就施蛰存「故事新编」的心理分析手法与「内在性」问题作一探讨,以期照见《将军底头》的独特之处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某个侧面。
二、作为「故事新编」的《将军底头》
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本节首先简介关于《将军底头》的背景资料,并对本文采用「故事新编」(而非「历史小说」)来命名《将军底头》的文类性质的原因加以说明。
《将军底头》,一九三二年由上海新中国书店出版,内收四篇小说,依次为〈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石秀〉和〈阿褴公主〉。这四篇小说约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间写成,并曾于文艺刊物上单独发表。[1] 根据施蛰存的回忆,这种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心理分析小说,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尝试:
我在创刊号(按:指《新文艺》)上发表了《鸠摩罗什》,同时《小说月报》发表了我的《将军底头》,这两篇都是运用历史故事写的侧重心理分析的小说,在当时,国内作家中还没有人采取这种创作方法,因而也获得一时的好评。[2]
〈鸠摩罗什〉的发表,标志着施蛰存小说写作的转向。施蛰存在上海文坛成名甚早,自一九二九年八月出版「真正的第一本新文学创作集」《上元灯》后,[3] 他的短篇小说便获得了文坛的注意,如沈从文就曾发表过有关这本小说集的评论。[4] 由于受到读者的好评,于是「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5] 施蛰存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心理分析手法去写小说,先后完成了〈鸠摩罗什〉等一系列心理分析小说,并于一九三二年结集出版。
施蛰存的《将军底头》,论者对它有不同的分类,或谓「历史小说」,[6] 或谓「历史心理小说」,[7] 或谓「历史题材小说」,[8] 或谓「历史题材的故事新编」,[9] 而施蛰存本人则称之为「历史故事」。[10] 其中较为通用的是「历史小说」。[11] 然而由于「历史小说」一词所引起的各种疑问和混淆,在此我将以「故事新编」一词代替「历史小说」来命名《将军底头》所属的文类。
正如不少我们常用的概念一样,「历史小说」其实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我们不妨先看看「历史小说」一词的定义。一九二六年,郁达夫曾对「历史小说」下了定义:
现在所说的历史小说,是指由我们一般所承认的历史中取出题材来,以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为骨子,而配以历史的背景的一类小说。[12]
骤眼看来,这定义似乎是再清晰不过的了。然而甚么是「一般所承认的历史」?「历史」、「小说」在事实和虚构之间的平衡,有没有一定的准则?要有多少「历史」作为「骨子」或背景才可算作历史小说?关于这些问题,胡适早已于一九一八年在〈论短篇小说〉尝试处理,认为「最好是能于历史事实之外,造成一些『似历史而非历史』的事实,写到结果却又不违背历史的事实」。[13] 不过,胡适的说法其实亦非常含混,没有真正解决「历史小说」概念所造成的疑问。究竟,怎样才可在「历史事实之外」,另造与之不相违背、「似历史而非历史」的事实?而我们又如何得知所谓历史的「真实」记载,没有丝毫虚构的成分?于是,「历史小说」内蕴的悖论:「虚构∕纪实」的混淆,[14] 始终停留在原地打转。
若以这些定义去量度《将军底头》,我们会发现它并不尽符合以上的「标准」。《将军底头》共有四个主人公:鸠摩罗什、花惊定、石秀、阿褴公主,所采的故事原型并不尽数来自「历史」。《水浒传》的石秀究竟是否「历史人物」?〈将军底头〉末段,将军的头与身体分开后仍能流泪,是否「违背」了历史的「事实」?似乎,若持「历史小说」去量度《将军底头》,只会产生更多的混乱。其实,与其纠缠于「历史小说」虚构 / 纪实混淆的瓜葛中,不如退一步以「故事新编」来命名《将军底头》的文类性质。「故事新编」的重点在于旧题「新」写,作者把故事(不论是真是假)重新编造,量度的重点在写作手法(形式),相对于「历史小说」采用「题材」(内容)作准则,实在较为清晰。
此外,以「故事新编」来命名《将军底头》所属的文类,亦更能贴合施蛰存创作这类小说的用意。施蛰存自言在写〈鸠摩罗什〉时抱有「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的想法,[15] 而这种创新的手法,正是以心理分析的手法,「应用旧材料而为新作品」。[16] 跟同期的作家不同,施蛰存写作这类小说,其意不在满足历史的考据癖,亦不为宣传新思想,而是旨在「旧」题上翻出「新」花样,重在形式上的实验。[17] 以此一来,小说的重点在于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而非在于历史∕小说虚实的比重之上。故此,以「故事新编」来命名《将军底头》,应是比「历史小说」较好的选择。以下为论述上的方便,其它作家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小说,亦一概称之为「故事新编」。
三、中国现代「故事新编」的发展方向
施蛰存运用心理分析手法写作「故事新编」虽为新尝试,但并不表示当时没有其它作家在利用历史故事来旧题新写。三十年代前后,采用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小说其实甚为盛行。当时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茅盾等人都或多或少地写过这类小说。若要了解施蛰存的《将军底头》在中国现代「故事新编」的独特之处,必须将之放回当时脉络以作参照。以下即尝试借本雅明有关故事和小说的讨论,以鲁迅和郭沫若为例,对中国现代「故事新编」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作一简单的梳理。
谈到中国现代文学上的故事新编,鲁迅和郭沫若是常常被相提并论的。中国现代的第一篇的「故事新编」,其中一个说法是鲁迅一九二二年完成的〈不周山〉(后改名〈补天〉)。[18] 姑勿论「故事新编」是否鲁迅首创,他的《故事新编》,实为五四以来同类小说中最重要的成果。[19] 同样,郭沫若亦创作了不少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故事新编,在鲁迅完成〈不周山〉后的一、两年间,郭沫若先后发表了〈鹓雏〉、〈函谷关〉等故事新编,在鲁迅《故事新编》出版后九个月,他又以同样规模出版了「历史小说集」《豕蹄》。[20]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一九三六年发表的〈讲故事的人〉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小说与所有这类文体(按:指故事)的差异在于,它既不来自口语也不参与其中。这使小说与讲故事尤其不同。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21]
本雅明认为,「小说」和「故事」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文体。故事拥有口口相传的传统,产生于群体之中,注重的是「讲」故事的技艺、「听」的过程。说故事者在讲演故事时,往往涉入甚深,将自己的经验与口头流传的故事结合起来,夹叙夹议地传授给听故事者。小说则相反,人们可以独自写作,闭门造车。由于倚赖书本作传播工具,不需要现场听众,小说倾向于表达那些不能作口头讲授的经验。
正因为文体性质不同,「小说家」和「讲故事的人」亦有着不同的关注点:
小说家需要的持续记忆与讲故事的人的短期记忆形成对照。前者致力于一个英雄,一段历程,一场战役;而后者则描述众多散漫的事端。[22]
小说家苦心经营,说故事者随意散漫,本雅明笔下这两种不同的写作人,恰恰点明了鲁迅和郭沫若故事新编的相异之处。事实上,鲁迅的故事新编可说是本雅明所谓的「故事」文体,至于郭沫若所写的故事新编,则属所谓「小说」文体。透过考察两人作品的特点,我们将能把握到中国现代故事新编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向。
鲁迅「说故事式」的故事新编,与本雅明所谓的「故事」十分相似。他《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都比较自由散漫,不追求宏大的架构,枝节较多,虽也博采,却用古今杂陈、插科打诨的写法,将现代生活细节和语言注入历史故事当中。关于《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鲁迅在〈故事新编.序〉曾有说明:
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23]
正如鲁迅所言,「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24] 其《故事新编》的创作是相当「随意」的。鲁迅利用拼凑的写法,把旧事乃至新事(如高长虹事、顾颉刚事),毫不顾忌地编织进小说中。[25] 他自如游刃于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兴之所至,更将各种从身边拈来的新闻、传闻轶事、闲话俗话、流行物品和语汇等现代事物,如「莎士比亚」、「OK!」、「幼儿园」、「为而艺术」、「警笛」、「警棍」等,连接到由古书翻译过来的古代故事中,做成一个古今杂陈的奇特混合体。[26]
事实上,所谓「故事新编」,实际上就是「现代人将古代事讲给现代人听」,在性质上来说,本来就是一种「讲故事」的文体。在写作者通过自己的叙述,再现 / 重组一些早已存在的传统故事题材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一个「现代」的叙述者(narrator),问题只在于其位置是「显」还是「隐」。而鲁迅,则正正承袭了一直以来「讲故事」文体的传统,并把它的叙事策略延续到现代小说的写作上。
刘玉凯认为,鲁迅「油滑」的叙事方式,实际上源于民间说书技巧,与说书人的插科打诨、边说边评的「说故事技艺」有密切的关系。[27] 他将鲁迅这种叙事方式称为「间离叙事法」:
间离的叙事主要从讲唱文学发展而来。它不像西方现代小说主要……再现人物的容貌。而是凭讲故事人的叙述评说,让听者(读者)若即若离地感受人物,理解人物。在叙述语言中时而进入角色,作者代替角色说话,时而又跳出来,把角色的秘密告诉给我们读者(或听众);讲述故事的人总的来说是评说的地位,与听众处在同一时空之下,有共同的语汇和观点。他经常用今人今调述说古人古调本来也就理所当然了。[28]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透过今人今调的叙事语言及叙述者的不断介入,彰显叙述者的位置,从而拉远叙述者与故事的距离,制造出某种疏离效果,让读者对故事重新加以思考。[29] 就此而言,这种叙述手法实在与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史诗式剧场(epic theatre)有着相通之处。
不过,这样一来,内在性的形构就被堵塞了。「间离叙事法」所产生的疏离效果,使叙述者与故事人物分离,即使他进入角色,代替他说话,依然未能与之认同,合而为一。《故事新编》的叙述者,就好比一名戴上面具的演员,在众人面前扮演故事人物,无论如何努力,始终都不能做出「逼真」的效果。然而,这种「逼真」(亦即维持小说的「假定性」),[30] 却恰恰是建构故事人物「内在自我」的基础。因为演员要真正地成为角色,人物才能「逼真」,才能有所谓「内心」的声音。正是基于这一理由,鲁迅《故事新编》那些由说书人扮演的、今人今调的「古人」,实在难以有「内在性」可言。
至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小说式」故事新编,则与鲁迅的写法迥然不同。郭沫若尝试将性质本属「说故事」的故事新编转化为「小说式」的格局,放弃散漫的写法,透过不断向内挖掘,致力再现「一个英雄,一段历程,一场战役」,并透过大量独白,为主人公建构一个丰富的内心,展现他的情绪或想法。
黄修己认为,郭沫若的故事新编,具有以下的特色:
他的这些小说同样注重对现实的讽喻,都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因而也把这些小说称为「速写」。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郭沫若的小说也「注重在史料的解释」,「对于历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释或翻案」。而且往往将历史人物影射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对象。[31]
事实上,当时大多数写作故事新编的作家,例如茅盾、郑振铎、郁达夫等人,都采取这种写法。他们一方面接受具体历史文献的约制,其角色造型、对话以至场景的设定,声言忠于故事发生的时代;另方面借人物之口传作家之言,批评现实或寄托个人心志。这种故事新编,正好与鲁迅的小说形成一个对比。若果说鲁迅「讲故事」式的故事新编中不避现代的词语,有意暴露出当中现代人的意识,那么这种「小说式」故事新编则将现代人意识隐藏在「现实主义」幻象之下。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答案是那些大段的独白。郭沫若故事新编的一大特征,是为主人公加插大段的自白。无论是寄托或讽喻,几乎全是通过登场人物之口说出来的。[33] 独白作为展现人物内在自我的方式,在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中使用得非常成功。然而,若直接用在假设了作者与人物必须分离的故事新编上,便会出现问题。由于郭沫若为人物安排过多的独白,使本是「讲故事」的故事新编,成为了自叙传小说。这样一来,就能够明白为何他的故事新编的人物,总给人一种很「虚假」的感觉,因为作者的声音替代了人物的内在声音,也就是说,人物的内在,早被作者侵占了。
鲁迅和郭沫若的故事新编,显示了二、三十年代的故事新编正循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一端是继承说书人的插科打诨,采取今人今调的手法,揭示说故事的人与历史的距离;另一端是使用现实主义的写法,虽也渗入作者的现代观点,却选择维持小说的假定性。两者在「内在性」的形构上,都不太成功。那么,在这样的脉络中,施蛰存《将军底头》的出现又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走上了怎样的道路?
四、《将军底头》与故事新编的「内在性」问题
在鲁迅和郭沫若等人的故事新编之间,施蛰存的《将军底头》是个独异的存在。它虽像鲁迅「讲故事式」的故事新编一样,拥有一个说书人模样的叙述者,但却承接了「小说式」故事新编的传统,在叙事中致力维持小说的假定性。然而,它却没有出现郭沫若那种「用强加的当代意识杀死古人」的情况,反而在不知不觉间把古人的声音置换成现代人的声音,将「现代人的意识」更深地植入「古人的意识」当中。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郁达夫和郭沫若的小说,在五四时期已经呈现出某种「内在性」的特征,不过,他们那些直抒胸臆的表现手法,在嫁接到故事新编这种形式时,却出现了种种问题。不过,到了施蛰存的手上,说书人的故事新编终透过与心理分析手法结合,完成整个过渡到现代小说的过程。
在笔者看来,施蛰存故事新编之所以能在重塑人物方面突破同期「小说式」故事新编的困局,其关键在于心理分析理论和相应叙述策略之引入。心理分析作为一种「新编」的手法,一方面让作者可以「忠于原著」,但另方面又扩阔了他想象的余地,让他可以就着传统故事人物「不为人知的内在心理」大造文章。透过引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以及采用相应的叙述手法,施蛰存成功地将以情节为中心的传统故事重新打造成以人物心理活动为核心的现代小说,并进一步营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潜意识」内在空间,开拓了中国现代故事新编的「内在性」。以下即分三部份就施蛰存《将军底头》「内在性」的建构及其相关问题加以探讨。
1. 「内」、「外」的划分与联结
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施蛰存《将军底头》是他小说写作的转折点。事实上,这种转变跟他接触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施蛰存自言:
《上元灯》里的大多数作品,都显现了一些浮浅的感慨,题材虽然都是社会现实,但刻划得并不深。《将军的头》忽然倾向于写历史故事,而且学会了一些弗罗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这条路子,当时给人以新颖的感觉,但是我知道,它是走不长久的。[1]
不论这种手法能否作长期的尝试,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在施蛰存重新编写旧故事的过程中,占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如果缺少了心理分析方法的引入,施蛰存的小说风格,未必会产生这样激烈的转变。
刘禾曾经指出:「弗洛伊德理论给施蛰存提供了一系列的词语,使他能够把中国古典志怪小说翻译成中国超现实小说。」[2] 事实上,刘禾的说法亦可用于对施蛰存《将军底头》的分析之上。不过,这里所谓「词语」,似乎应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施蛰存固然在《将军底头》中不时运用如「二重人格」之类的心理分析理论术语,但若只停留在作品中找寻心理分析用语的话,则似乎未能捉到要害。必须注意的是,弗洛伊德的理论不但是一系列的词语,更是一套用以组织人类内心世界的论述方式。
施蛰存曾对自己这几篇小说的「主旨」有这样的说明:
〈鸠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底头〉却写种族和爱的冲突了。至于〈石秀〉一篇,我是只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的心理,而最后的〈阿褴公主〉,则目的只简单地在乎把一个美丽的故事复活在我们眼前。[3]
从施蛰存的自述可清楚看出,他在写作〈鸠摩罗什〉等小说时,是企图把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作为支撑整个故事的轴心。旧故事所注重的是情节,对人物的内心少有刻划,于是施蛰存为主人公设想了「过去不为人知」的内心,并透过各种冲突、场景将之曲折地呈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冲突中,爱 / 性欲望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这明显是受弗洛伊德性心理理论的影响,因为在他的理论中,性是一切行为、心理冲突的源头。
以〈石秀〉为例,它虽根据《水浒传》第四十四至四十五回写成,但重点却从石秀怂恿杨雄杀嫂的经过,转移为行为背后的内心活动。在施蛰存的版本中,石秀其实一直暗恋着义兄杨雄的妻子潘巧云,但碍于兄弟之谊,不便勾引,于是陷于性的苦闷之中。后来石秀发现潘巧云与和尚私通,妒忌不已,遂向杨雄告发,并怂恿他把潘巧云杀掉,自己在旁以虐待狂的心态欣赏行刑的过程。整篇故事的重点,乃在石秀对潘巧云的性欲心理之上:写其由爱到恨以至要杀死她,但却又在观赏她受刑的过程中得到快感的整个过程。如此一来,整个关于道义、贞节的故事,就被扭转为一个交织着嫉妒、爱欲、血腥复仇的情欲小说。当中各种心理因素不断互相拉锯,加强了小说的内在张力,而文本终成了人物潜意识冲突的战场。
这种采用内心冲突作为改写的中轴,并将新编的部份限制在人物心理活动的写法,使施蛰存的故事新编产生出一种微妙的叙事效果。由于主人公的潜意识成为描述的重点,施蛰存的故事新编显示出一种对「内在」高度的关注,亦因此造成了小说对人物「内」与「外」的严格区分。他笔下的人物通常都具有二重人格,表里不一,「内」与「外」有着极大的分歧。例如鸠摩罗什表面是得道高僧,内里却是一名贪恋色欲的凡人;石秀表面上是正义的好兄弟,但其实是因爱成恨的嗜血者。从表面上来看,施蛰存小说之所以能够开展,是基于这种人物「内」「外」互相对立的深层结构,但事实上,他的心理分析小说背后最基本的假设,却正是「内」与「外」的相互诠释的合法性。
柄谷行人曾经指出,中世纪并没有「无限空间」(infinite space)的概念,亦没有对于「内」「外」的明确划分。中世纪的人视世界为一「层级式的世界」(stratified world),为他们来说,「这里」(here)和「那里」(there)有着「质」的不同,故此不同空间的连结问题并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4] 然而,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现代和心的兴起,开始出现「内在」与「外在」的分野。[5] 弗洛伊德的《梦的解释》,指出梦是人潜意识的流露,它作为一种符号系统,与潜意识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弗洛伊德的理论,为「内心」在外在世界找到相应的对应物,从而把内在与外在世界重构为隶属于同一逻辑的同质空间,打破了内外诠释的界限,使中世纪的层级式世界,转变为具有同质感的空间(homogeneous sense of space)。而亦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才可以成立。
施蛰存曾有所谓「内在现实」(inside reality)之说,指「人的内部,社会的内部,不是outside是inside」。[6] 林耀德将这种「内在现实」理解为:
内在投射出去后,外在的客观世界就被改造出一种心灵空间,是意识的投射面,产生一种崭新的现实,……您(指施蛰存)的小说不是主观的变形而是客观现实中的变形了。[7]
由于局限在「客观」和「主观」的框架之中,林耀德似乎未能足分把握到所谓「内在现实」的意义。固然,施蛰存的小说可以说是一种折光,[8] 但这种折光是立足于现实世界的。由于潜意识为意识所看守,不能直接到达意识的层面,于是我们只好利用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情景来描绘这个不可知的东西,这就好比基督徒利用鸽子的形象代表圣灵一样。当我们一旦利用可知的事物描绘不可知的东西时,即假设该种不可知的事物,与我们所知的事物是可以互相比拟的,亦即假设两者有着相同的逻辑。施蛰存的小说,正是由于背后假设了内与外有着相同的逻辑,才可以借着外在世界谈所谓「内在现实」。而这样的一种处理手法,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内与外的浑然一体。
如此一来,〈将军底头〉末尾所描写的奇幻场景,就变得可以解释了。在小说的结尾,将军的头被吐蕃将士砍了下来,并被吐蕃将士拿在手中,但他的身体依然骑着马回去村庄寻访少女。后来少女见到他,对他加以嘲笑侮辱,于是将军的身体倒了下来,同时他在远处的头也流下了眼泪。这个结局,被不少论者视为「超现实主义式」的处理,其实不妨将之解释为作者运用写实手法描写内心的结果。在此,「内心」与「外在」事实上都处于同一性质的空间,并不能清楚地划分,所以我们应该将之视为内在与外在于同一空间里相互移位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手法只可以在「现代」出现,因为这些小说的前设,正是内在与外部世界的同质化。
2. 建构潜意识的内在空间
以上考察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在施蛰存旧题新写时所产生的作用,并就《将军底头》的深层结构及其背后逻辑作一分析。在紧接着的这一节里,我们将会看到,在「内」与「外」可以相互诠释的前设下,施蛰存是如何在他的小说文本中,建构出一个属于潜意识的内在空间,把古代主人公隐秘的内心,呈现于读者眼前。
柄谷行人曾以名画「蒙罗莉萨」作为例子,阐释「内在性」建构的问题:
我们必须留意那个寻找「蒙罗莉萨」微笑的意义的问题。我们不能将这看成是表达着(expressing)某种内在性。在此,同样地,情况跟我们所假设的相反。这是因为从蒙罗莉萨裸露的面孔(naked face)──不是作为所指的面孔──第一次出现起,这张面孔就不断地被假定为表达着某种内在的意义。在此,内在性不是被表达出来的,而是那张突然揭穿了的裸露面孔,开始指涉内在性。[9]
换句话说,柄谷认为「内在」并非是「表达」出来的,而是一种论述效果,一种幻觉(illusion)。正是「表达」的概念本身,建构出所谓「内在」和「意义」。长久以来,人们都不断讨论蒙罗莉萨那微笑背后的意义,但实情正是基于这种假设,那张面才会正在表达着什么。在此,面孔成为了能指,指涉着有待诠释的内在。
同样地,施蛰存小说文本中的「内在」,某程度上是小说叙事机制制造出来的效果。施蛰存小说以巧妙的叙述策略,建构出主人公的「内心」,并制造出「再现」(represent)内心的幻象,让读者产生误识,以为文本是故事主人公内心的真实写照。那么,在施蛰存的小说,担当指涉「内在」的能指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小说中那一系列的梦、口误和幻觉。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将军底头〉中作者对花惊定将军的描写找到证明。
〈将军底头〉的内容是写大唐将军花惊定被派往征伐吐蕃,然而由于将军流着吐蕃勇士的血,以及大唐兵士的恶劣行为,使他产生了忠于种族还是忠于职守的内心矛盾。到了边境,发生了骑兵企图侵犯汉族少女的事件,将军按军法判处犯事的骑兵斩首之刑。可是,将军在不知不觉间也爱上了这位少女,于是堕入了多重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意欲投奔祖国,却又爱上了汉族的少女;另方面自己严格执行军法,却对少女起了欲念。自此,将军就开始不断为幻觉所缠扰。例如,有一次,将军被邀往少女家作客,在回军营的路上见到那个被自己判处死刑的兵士的首级,就出现了一些幻觉:
当走过那挂着一个首级的树下的时候,不觉得通身打了个寒噤,在将军自己的手中,被杀了的人也不算得少,将军从来没有一天能从记忆中想起他们的面貌来的。而这一回,将军觉得有些异样了。自在橙黄的灯光下,与那好客的武士及其妹妹一同坐下来用着清静的晚餐的一时间起,将军就恍惚眼前继续地在浮动着那个被刑的骑兵的狞笑的脸。[10]
这个突兀地出现的头,指涉了将军的内心声音。将军之所以会在幻觉中看见被刑骑兵狞笑的脸,不单是因为内心不安,更是因为他对少女产生了爱欲。若果连将军自己都对少女有爱恋之心,他又有何资格去判决骑兵的罪呢?正因为这样,他才会在潜意识中产生被骑兵嘲笑的幻觉。这个头的出现,暗示了在将军正义的表面背后正存在着些什么,如此一来,一个「隐藏着的内在自我」便在文本中被建构出来。
后来作者又再次安排将军在朦胧的月光下出现另一次幻觉。这一次,将军在幻觉中目睹骑兵当日企图所做的事都付诸实行,正在咬牙切齿地痛恨着那个骑兵之际,将军忽然发现那正在肆意侮辱着少女的人竟是他自己:
将军通身感觉到一阵热气,完全自己忘却了自己。原来将军骤然觉到侮辱那少女的人竟绝对不是别人,是的,决不是别人……而是将军自己。自己的手正在抚摩着那少女的肌肤,自己的嘴唇正压在少女的脸上,而自己所突然感到的热也就是从这个少女的裸着的肉体上传过来的……[11]
与上面的例子一样,这个侵犯的场面同样是一个能指,代表着将军的内心。在此,将军的形象与骑兵的形象重迭起来,表现出将军潜意识中对少女的欲望。现实中因军法的关系,将军极力压抑自己对少女的欲念,但这种本能的冲动,却透过投射作用,在幻觉中以骑兵的形象得到满足。透过这种幻觉,懂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读者,就会发现藏在将军看似荒诞的幻觉背后的欲望。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施蛰存在小说中所安插的口误、幻觉、梦,其实担当着能指的作用。在故事中,借着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框架的引入,这些标记在解读人物内在心理的脉络中获得了意义。这一系列突兀标记,就如安装在文本表层的一个个玻璃窗户,它们的出现打破了单一的现实空间,开辟通往另一内在空间的路径。如此一来,施蛰存在小说中添加了一种内在的深度和立体感,建构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潜意识内在空间,使一种有别于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内在性得以成形。
3. 叙述者角色的转换与内在声音的形成
以上集中讨论了施蛰存《将军底头》如何透过梦、幻觉等标记之设置,在文本之内建构出一个内在空间。余下来的问题是,施蛰存是如何维持小说的假定性,使读者感到古人的内在声音是真实可感的?
Dorrit Cohnm曾经指出,现代人对自己「内心」的解释和把握,与现存的叙事文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 刘禾亦认为:
小说叙事文体对心理描写策略的运用,并不是作品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某种真实的反映(这种镜象式的反映不过是小说刻意追求的幻象而已),而应该倒过来看,即这种文体是叙述语言对内心世界的幻想(捕捉不到,故求助于幻想),亦是小说语言对人的自我认识极限的突破。[2]
从刘禾的角度出发,施蛰存〈将军底头〉等小说所「描述」的主人公波澜起伏的「内心」,也不过是叙事文体所形成的效果。值得追问的是,何以施蛰存小说的读者,并不察觉所谓内心声音只不过是幻象,而总感到自己能真实地看穿主人公的内心呢?
笔者认为,施蛰存之所以能够将主人公的内心置于读者的眼前,其叙述者角色的转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施蛰存《将军底头》虽以其完全不同的结构相异于「讲故事式」的故事新编,但它却同样拥有一个说书人模样的叙述者,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施蛰存《将军底头》的四篇小说,皆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并以非聚焦作为小说的基本叙述视角。这个故事新编的叙述者,有时候会以一个说书人的形象出现。例如〈将军底头〉的开首,就出现了这样的句子:
这是在唐朝广德元年呢,还是广德二年?那可记不起了。[3]
这个语调完全是属于说书人的。又如:
但是,究竟这将军是谁呢?对于这样的询问,我们这样地讲着,是谁也不会猜想得到的,因为时代已经把我们对于他的记忆洗荡掉了。但如果在当时,巴蜀之间――哎!岂止巴蜀之间呢!自从讨平了段子璋以后,简直是遍天下了!我这样地一提起,谁不会肯定地说:「唵,这不是花惊定将军吗?」[4]
依然是说书人模样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不过,这个说书人模样的叙述者,并不像鲁迅《故事新编》的叙述者般,有意打破读者的幻觉,惊醒他们对故事作深思熟虑的批判。跟郭沫若故事新编相似,施蛰存的故事新编,着意维持小说的假定性,暗暗地把现代人的意识包装为古代人的意识。小说里事件的发展,都被叙述者从一个固定的角度加以回溯式的观照。这种观照形成了一种线性的时间感,使整个故事被框限在单一叙述视角之下。这种手法就如单点透视法般,加强了将叙述者中性化的效果,从而达到一种客观叙述效果。这种做法最终将叙述者置放于文本的后设层面(meta-level),有助营造一种现实的感觉。[5]
那么,第三人称的叙述者,如何传递主人公内心所想呢?李欧梵认为,施蛰存的小说技巧可归纳为主观叙述,即如何把角色的主体声音和视角放进叙述的框架中,置换成叙述人的声音。[6] 在此,自由转述体(free indirect style)的运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所谓自由转述体,是指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中,不加标记地直接引入第一人称的叙述。叙述人可以不必借助直接引语,但依旧能用人物的口吻说话。由于自由转述体模糊了叙述人语言和人物语言之间原有的文体界限,取消了直接引语或间接报导的文体标记,如引号或「想到」等,使主人公的内心叙事变得格外透明,真实可信。[7] 正如刘禾所言:
自由转述体一边制造内心叙事的幻像,一边积极抹去使这一幻像得以形成的文体痕迹。仅这一点,它就比别的叙事模式更容易达到心理写实主义所预期的效果。[8]
透过自由转述体,主观的人物语言注入客观的叙述者语言之中,内在与外在的空间都能纳入同一个叙述框架之中,于是透明的、可信的内心声音亦得以出现。
举例来说,〈鸠摩罗什〉中对鸠摩罗什思考过程的描写,是以这样一种手法来写的:
他仿佛记起日间当他讲经完毕,出了草堂寺的山门登舆的时候,曾看见一侍卫趁着纷乱之际挤着一个女人,而她曾撒着娇痛骂着,那个侍卫可不是他吗?至于那个被挤的女人,是谁呢?仿佛也是熟识似的。他沉思着,他忽然害怕起来,那个女人好像是自己的亡妻﹗没有的事!噢,想起来了,好像是那些在前排坐着的宫女中的一个呢。但为什么会想着了亡妻,这却不可解。[9]
被标示着的句子,原应使用第一人称表述,现在却混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中间。这种写法使鸠摩罗什的内心活动的过程被展示出来,让读者彷佛跟主人公同步思考,参与他的思考过程。这样一来,内心真实可感的幻象,便成功地被建构出来。
借着采用单一叙述视角和自由转述体,施蛰存成功地改造了「讲故事式」的叙述者,把「小说」文体引入故事新编的写作之中。《将军底头》的叙述者,虽有着说书人的模样,但却不采取介入式的评述。在此,叙述者一方面作为一个全知旁述,另方面又像一个沉默的心理分析师,聆听人物的内在声音,并担当其记录者和代言人。如此一来,施蛰存成功建立了一个属于人物的可被不断发掘的内在空间。若要谈《将军底头》在中国现代小说 / 故事新编「内在性」拓展上的意义,或者就正在这一点吧。
五、结语
施蛰存《将军底头》的出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是重要的一页。透过心理分析理论与写实的叙述手法,施蛰存在他的故事新编中建构了一个可以容纳「内在自我」的空间,拓展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在性。施蛰存以写实手法为起点,以其小说叙述机制企图形构出无法「写实」的内在,并将不透明的内心,很「透明」地表述出来,在文本的层面上创造出主人公的内在自我和内在意识。这些看似荒谬的行为,亦正正是整个小说叙事文体的吊诡之处。
51. 施蛰存,〈施蛰存.序〉,《施蛰存(中国现代作家选集)》,页2。
52. Liu, Lydia H.,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P, 1995) 135-136.
53. 施蛰存,〈将军底头.自序〉,《十年创作集:文学创作编.小说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6),页793。
54. Karatani Koji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62-63.
55. Ibid., 61-65.
56. 郑明娳、林耀德专访,〈中国现代主义的曙光:与新感觉派大师施蛰存对谈〉,《联合文学》,第6卷第9期,页141。
57. 同上。
58. 同上。
59. Karatani Koji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62.
60. 施蛰存,〈将军底头〉,《十年创作集上.石秀之恋》(北京:人民文学,1991),页157。
61. 同上,页160。
62. Cohnm, Dorrit, Transparent minds: Narrative Modes for Presenting Consciousness in Fi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78) 11.
63.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香港:天地,1997),页102。
64. 施蛰存,〈将军底头〉,《十年创作集上.石秀之恋》,页137。
65. 同上,页138。
66. 参见Karatani Koji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72-73.
67.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页159。
68. 参见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页104-106,112。
69. 同上,页112。
70. 施蛰存,〈鸠摩罗什〉,《十年创作集上.石秀之恋》,页126。着重点为笔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