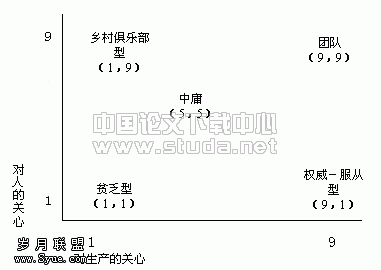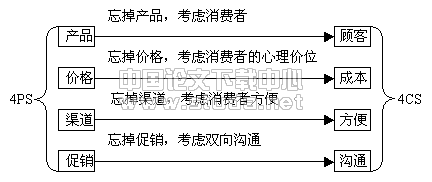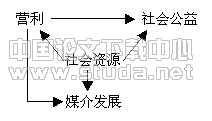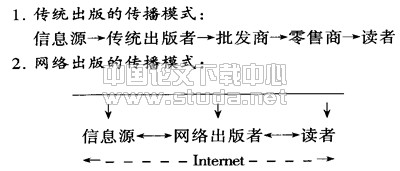我国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
[摘要] 我国传播学研究起步迅速,但缓慢,从总体上讲,我国传播学尚处在引进介绍和引进式研究阶段。主张全面而有重点地翻译西方传播学著作,多介绍一些批判学派的著作,重视出版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译著。认为现在是加强中观研究的时候,应多出版一些结合传播实际和研究成果,来介绍西方传播学分支学科和重要理论的专题性著作。要使我国传播学成果打入国际传播学界,必须加强原创性研究。原创造性研究必须重视学术规范,讲究研究方法,与国际接轨。中国古代传播研究如能加以改进,就可以向传播学贡献新原理发现的成果。我国传播学研究是一种追赶式研究,需要加强组织、协调。
[ABSTRACTS] The research of communication as a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has been quickened its step but developed slowly. As a whole, communication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stage of introduction and bring-in research. I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advocates that western works of communication be translated comprehensively with focal points, such as works from the school of criticism, as well as work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organize communication. The author also considers that it's now the time we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medium angle. More works which introduce subdivision subjects of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special works introduce important theories, combining the realities of the communication in China and achievements of research, should be published. In order to let the achievement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known by international circles of communication, original and regional study of communication must be reinforced, while academic standards and research method must be paid attention to. If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communication is improved, we may contribute to communication the achievements of more new theories. The research of communication in China is in its pursuing stage, thus it should be organized with greater efforts.
[关键词] 传播学研究 学术规范 研究方法 中观研究 原创性研究 学术引进 古代传播研究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传播学,至今已21年了。在世纪末之际,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明确传播学研究该向何处去,是很有必要的。
笔者在传播学研究上建树甚少,但很关心和留心观察这项研究。现在不揣冒昧,说些近乎外行的话,目的是抛砖引玉,促进讨论,探讨传播学发展之良策。
一、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定位
这21年来,传播学研究在我国很是红火,取得的成绩是肯定的。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几十本,发表的论文数以百计,由中国社会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先后与各有关单位主持召开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到今年11月已有5次。30多所院校开设了传播学课程。我国传播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存在问题也不少。我国翻译的西方传播学著作数量很少,且很不全面。我国学者最早的传播学著作,要算戴元光等写的《传播理论与实务》,出版于1988年。已出的传播学著作大都是在教材的基础上丰富、整理出版的,其中《传播学引论》(李彬著)、《传播学导论》(董天策著)等若干著作架构合理,逻辑严密,论述流畅,对于普及传播学知识很有意义。但超出教科书的研究专著比较罕见。传播学研究有不少是在浅层次上重复,原创性研究不多。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对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历来不够重视,更谈不上与国际接轨。现在几乎还没有看到,我国学者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原理和方法被国外权威刊物或著作所引用。所有这些说明,我国传播学研究起步快,但发展缓慢。
对于这20多年来的传播学研究,有人划分为几个阶段。但我认为,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在总体上是追赶式研究,只能在个别领域上或许可以说是赶超型的研究。追赶式研究,是说我们的研究仍处在引进式介绍和引进式研究阶段。作这种定位,比较能够反映实际。这样定位并不是低估成绩,更不会妨碍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而恰恰能有利于认识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二、引进介绍应力求全面一些
1981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我们对待西方传播学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后两句话今天看来似乎说大了点,但其意思大体还是可以肯定的。可是究其实际,我们到现在连“系统了解”也还没有能够做到。
传播学基本上包括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大部分,如果加上包含前二者在内的组织传播,也可说是三大部分。(有人说,还有一种“自我传播”,但我认为,传播学研究的传播都是社会传播,所谓“自我传播”不应包括在内,它应属于心范畴)。可是长期以来,我国传播学界翻译介绍和研究的均属大众传播范围,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译著一本都还没见到。
从学派来讲,我国介绍的大量是美国的经验学派,欧洲批判学派是传播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派,它的某些观点更容易在中国引起共鸣。但是我们对它的译介很少,几乎一本译著都还没有出过。只有王怡红、李彬等写了一些介绍文章。缺少这一大块,对于我们研究传播与、和社会发展,研究传播大众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等诸多重大课题,都会缺乏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方法论的启示。陈力丹在1995年曾撰文,主张“更多地借鉴欧洲传播学派的方法、观点”,他认为,“他们的理性思维,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有较深刻的分析。在方法论上,他们更多地从整体上考察传媒,更多地采用的、文化的、的、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注意传播过程及其每个环节所起的作用。同时,并不排斥用经验学派常用的一些具体方法。”①但陈力丹所倡导的迄今并无进展,我国传播学界接触批判学派仍然很少。幸得李瞻教授出面张罗,为大陆十几个院校赠送了一些新闻传播学的书籍,可从中得到一些帮助。
至于从国外浩如烟海的传播学论文中挑选精品翻译发表,同样极为罕见。
我国传播学研究者,可能多数外文都不很过关,看原著有困难,而且由于研究经费有限,购买外文原著也是难事,何况从为数众多的外国著作中去精选,对于每个研究者个人来说,都是难度不小的事。所以组织挑选和翻译若干外文传播学原著,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1997年,潘忠党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发起了翻译出版“媒介、文化、与社会译丛”的计划,该计划认为,“我国目前市场上涉及这个学科(传播学科)的书籍极少,仅有的少数也大多处于‘概述’和‘初级介绍’的水平,缺乏超出教科书的专著”,“要在我国学者近20年努力的基础上,将传播学的介绍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必须翻译介绍“一些学术专著和研究范例型的著作”。
这一计划列出了24本专著,包括了文化/批判学派、社会行为学派等各学派的有代表性重点著作。现将这24本书的作者、书名、出版年份转列如下:
1、维·沃萨德:《传播的生态:控制的文化形式》(1995)
2、班纳迪克·安德森:《想象的社区: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扩散之回想》(1991)
3、奥利弗·巴瑞特·波德、克里斯·纽波德(合编):《研究媒介的途径》(1995)
4、丹尼尔·戴岩、艾利休·凯茨:《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1992)
5、约翰·费思克:《理解流行文化》(1989)
6、荷伯特·甘斯:《决定什么是新闻:对于CBS晚间新闻、NBC每夜新闻、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的研究》(1980)
7、德·吉特林:《打开黄金时段》(1994)
拉斯苟大学媒介研究小组、:获取资讯:新闻、真理、与权力》(1993)
德·戈丁:《媒介的政治经济学》(1997)
10、贤托·阿岩伽、当那德·金德:《事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公众舆论》(1987)
11、塔码·李伯思、艾利休·凯茨:《意义的外销:对于〈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1993)
12、索尼亚·莉文斯通:《理解电视:受众解读的心理学》(1990)
13、约翰·麦克马内斯:《市场导向新闻学:公民应否警觉?》(1994)
14、保罗·玛萨瑞斯:《视觉说服:形象在广告中的作用》(1997)
15、约史华·玛雅维茨:《失去的空间感:媒介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1985)
16、戴维·墨利:《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1992)
17、迪姆·欧苏勒文等(合编):《传播与文化研究中的关键概念》(1994)
18、埃夫瑞特·罗杰斯:《创新的扩散》(1995)
19、麦克尔·刹德荪:《广告,艰难的说服及对于美国社会疑虑丛生之影响》(1986)
20、盖·塔克曼:《制作新闻:对于现实构筑的研究》(1978)
21、约瑟辅·特若:《媒介产业:新闻与娱乐之生产》(1984)
22、特云·凡·戴克:《新闻作为话语》(1988)
23、威廉·雷蒙德:《文化社会学》(1981)
24、威廉·雷蒙德:《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语汇》(1981)
这个丛书还成立了由李金铨、朱立、陈世敏、李瞻、郭庆光、喻国明、张国良、李良荣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提供咨询、建议。上述著作原计划分批翻译出版,到2000年上半年出齐,后来由于某些原因,计划搁浅,甚为可惜。但所选的书目无疑很有意义,即使不是每一本都很合适。望有能力承担此书出版者,能够挑起重担。
上面所列书目学术性大都很强,对于研究者帮助很大,我们也需要翻译出版一些教科书类型的专题著作,以利教学和普及。据了解,北京广播学院已在作这方面的努力,已有5部书稿译出。
三、中观研究及与我国传播实际相结合
传播学研究在美国实际上是经历着从微观到宏观的观程。开始是研究演讲和修辞的技巧,后来研究预测总统选举中选民投票的意向和美国人对重大事件的意见,研究战争时期宣传的效果,然后到威尔伯 施拉姆,集前人研究成果之大成,出版了《传播学概论》(《Men, Message, Media—A Look of Human Communication》)之力作,标志着传播学的创立。当然,这种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是反复进行的。现在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无数课题,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都是微观的、具体的。《传播》刊登了陆晔、潇湘写的《传播学的多元视角与多维框架——’99年国际传播学第49届年会述评》,这次年会是1999年5月在美国旧金山湾举行的,其主题是“传播与对立:通过对话接受差异”。但另外还有300多场专题报告,涵盖了17个方面,每个专题下面都有很多微观的、具体的研究课题。②西方科学界都重视原创性研究,而原创性研究必然是从微观入手。相信到一定时候,还会出现施拉姆式的大师,把前入的成果进行系统归纳,使传播学的构架体系跃入一个新的层次。
我国传播学研究的路程则不同,是从引进开始的,首先是从翻译介绍施拉姆《传播学概论》、德弗勒等人的《大众传播通论》等宏观著作开始的。我国已经出版的很多传播学著作也都是概论性宏观著作(大多是以上两本书的某一种的构架作些变化,或以上两本书的构架综合起来作些变化,来确定自己的篇章结构)。一些学人是在领会这些传播学著作原理和粗通一些传播研究方法以后,才去着手进行带有原创性的研究的。所以,是一种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
鉴于我国进行出版的宏观性著作已经不少,而微观的原创性研究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一时难以有大的发展,我在这里提出加强中观研究。所谓中观研究,就是要求以专著的形式,系统介绍西方传播学关于某一学术领域(或某一分支学科,或某一基本理论等)的源流发展、基本内容(包括原理、规则、方法以及目前正在研究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还包括发展趋势),并结合中国的传播实际和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我认为,作为追赶式研究,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
本人以为,在未来几年,如果能够出版以下中观研究的著作,对于传播学研究的深化和传播学知识的进一步普及,都会起很大作用。
(1)传播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理解传播、说服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传播心理学、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传播、文化传播等。
(2)传播的一些基本原理:批判理论、沉默螺旋理论、两级传播理论、媒介理论等。
(3)传播的一些基本方法:议程设置、传播控制等。
(4)传播学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如经验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传播学许多常用的研究方法(如实地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控制实验法、个案研究法等)。
上面所谈的中观研究领域,其实国内出的传播学概论性著作都有所涉及,但是由于大家都浅尝辄止,谈的人再多,信息量和知识含量也没有增加多少。所以,让概论和教科书中的一章一节,成为一本书,该是时候了。诚然,有些中观研究的课题,我国已经有人做过,如邵培仁教授等主编过传播学、传播学等,堪称很有意义的一次尝试;陈力丹著的《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倒是一个难得的收获。四川社科院新闻所研究生宋昭勋写了一本《非言语传播学概论》,填补了一个空白。但我以为,一个课题出两三本书,应算正常,有有比较,才会有佳作出现。
顺便说一点,我倒不认为中观研究课题后都得加一个“学”字,如“对外传播学”、“新闻学”。我常纳闷:这个“学”,是“学科”(Field of Studies),还是“”(Science)?但无论作为学科,还是作为科学,总得有一些本学科特有的原理和特有的术语,如果暂时还做不到,就不忙加“学”字,等到以后有了再加不迟。之所以提及这个问题,是担心学界的一种华而不实的学风会不会刮到新兴的传播学园地。
中观研究贵在与我国传播实际相结合。这个结合主要表现在两点:首先,要尽可能紧密联系的传播实际,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研究,而是国外传播学知识的专题介绍了。那种介绍,即使有些个人见解,也只能是微量的研究成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当然,结合中国实际,不是要求西方传播学都服从中国的习惯提法,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其或相同或相近之处,充分展示能为人们提供启示的地方。其次,尽可能运用中国人熟悉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不能生吞活剥,让著述充满外国人的现成话或欧化的句子,使人读了若明若暗,不得要领。
四、原创性研究与规范和方法
我国传播研究者要想对传播学作出真正的贡献,还在于扎扎实实地进行原创性研究。所谓原创性研究,就是研究前人没有研究过的课题(或者虽然研究过但没有得出应有结论的课题),得出前人没有得出过的结论。像喻国明关于测度新闻媒介传播内容极其结构的传通效果的指标体系的研究③,林之达关于作为传播致效的中介的心理能的研究④,我认为都是具有原创性的。原创性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它能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那种主要是综合、整合前人的成果,稍加一点自己的分析的研究,不能称为原创性研究。传播学中那些里程碑性的成果,无不是原创性研究的硕果。凡是提到那些成果,人们就会同时想起取得这项成果的著名学者。
我国传播学界要搞好原创性研究,有两点是必须加以重视的。
首先,原创性研究强调规范。一项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原创性,必须以学术规范来检验。学术规范也是个很大的话题,大到学术道德和秩序,小到引证规则都在其内,此处无法详述。我觉得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我们的一些研究往往在学术信息不足的情况下进行。一项研究开始,没有检讨或文献回顾,没有尽可能把前人所作的相关文献加以分析,研计其得失,从而说明自己所作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让人明确这项研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而做不到这一点,就有可能进行一次重复研究,去发现前人已经发现的结论。
其次,原创性研究讲究研究方法。不少,都象随感录,或者夹叙夹议的散文。有的运用思辩方法的论文,对自己的基本的研究对象不使用定义法加以明确,看得出其概念的含义在游蛇般地走动。有的例证选择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十几年来,实证研究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从无到有,逐步有所发展。但有些研究,没有严格按照方法的要求操作,论文中没有充分证明样本的科学性,历次获得的资料也缺乏可比性,因此读者对结论的可靠性信心不足。诸如此类的成果都称不上严肃的科研成果。这种状况不改变,我们的成果就很难打入国际传播学界。在科学研究中,任何一个学者提出自认为有理由的观点,如果没有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充分的论证,那仅仅是提出了假说。一篇论文中对于诸多问题都是蜻蜓点水,未经充分论证,就成为“假说连篇”;倘若假说也是别人说过的话,连假说都算不上,那就更无新意了。⑤一句话,原创性研究必须是有板有眼的、扎扎实实的。
五、中国古代传播研究及如何对传播学作贡献
澳洲传播学者奥斯本(Dr. Graeme Osborne)说:“对一个没有特殊传播理论的国家来说,一个最有效的、有力的开端是认真研究本国的传播史,尤其是本国传播政策形成的过程,从中发掘本国传播的目的、目标和原则。”系统的传播理论虽然不产生于中国,但中国几千年的上有丰富的传播资源,从历史到制度,从思想到技巧,有取之不竭的资料可供研究。二十多年来,海峡两岸有不少学者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的研究,不计大量论文,已经出版的著作就有朱传誉著《宋代新闻史》(196?)、张玉法著《先秦的传播活动》(1983)、尹韵公著《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0)、关绍箕著《中国传播理论》(1997)、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1997)、李彬著《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1999)等书。余也鲁教授等主持的“五史六论”(五部传播断代史,六部传播理论探索论文)的研究,正在进行中,有的已经成稿。
进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研究,不但需要新闻传播学者、文史学者参加,还需要吸引、政治、语言、文化、人类等各学科的学者参加。
如何使中国古代传播研究对世界传播学做出贡献,有三个环节必须抓住:
首先,必须在传播原理、传播方面发现、有所。这方面的东西一旦有了就能成为全人类的。要把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理论升华再升华,不要仅仅停留在历史的描述上,要把它们提炼成原理,有的争取再提炼成术语。我在《华夏传播论》一书的《政治传播》中试图总结决策圈与信息圈的关系对政治的影响(二者重合,政治就清明;二者分离,就会出现阴谋政治,政治就腐败);在《科学传播》中试图说明逆向传播的道理(一个社会中,逆向传播不能存在,只能作“借经立言”式的传播,科学就不可能发展)⑥,就是这种努力。黄星明教授正在研究的“风草论“,我认为也比西方的‘魔弹论”贴切得多。(“风草”一说出自《论语》中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风行草偃”讲的是德教化民的道理,是说君子的德教传播,如风掠过,老百姓接受,会产生象草应风匍匐一样的效果。那么,要想让老百姓能顺应你的意向,信息就得源源不断地送过来,才能使他们一直处于接受的状态。)
其次,要用正确的方法、规范的论证和表述方式,来论证和推演你根据大量史料得出来的论点。这一点很重要。比如上面所谈到的信息圈与决策关系的政治传播原理,逆向传播的科技传播原理,我也都是在长篇论述中提到而已。由于种种原因,事后也未能重新来做,殊为可惜。所以,我所提出的还只能算假说,而不是科学结论。我最近读到古代传播研究方面的一部书稿,文中许多地方迸发出真知灼见,有的的确能上升为原理,可都是匆匆带过。如果以某一灼见作为理论假设,重新组织材料,进行充分论证,就可能出原理发现上的重要成果。
著名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能给人们这方面的启示。它是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 内尔-纽曼教授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提出的: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因为害怕孤立,他便不太愿意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其实,这种认识几乎是东西方“人人心中所有”(亲身经历过“文革”造势的中国人对此尤有体会),只是“人人笔下所无”。但内尔·纽曼教授抓住这一现象不放,并且推演出一系列的论点。比如,占支配地位的或日益得到支持的意见就会愈加得势,另一方则越来越失去支持的声音。这样,一方表述而另一方沉默的倾向便开始了一个螺旋过程,这个过程不断把一种意见确立为主要意见。又推出,如果这个过程有大众媒介参与,螺旋往往形成得更快、也更明显。还推出,各种受者的声音又作为媒介的声音的和声进而影响更多的人。⑦所有这些论点,都被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加以证实,从而完成由假设到科学论断的飞跃。这位教授的“秘诀”在于:抓住它,展开它,用科学的方法证实它。
其三,要用改写或翻译既有原理发现,又符合国际通用的学术规范的学术成果,并在国传播学刊物上发表。
六、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我国传播研究,由于财力不足,在翻译引进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人力资源占有优势,我们有大量的新闻传播学术人才可以依靠,还有不少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可以借用,一些从事国际研究、文化研究的机构和学人现在也在进行传播研究,且成绩斐然。某些研究如中国古代传播研究方面,资料也相当丰富。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研究经费特别是各种研究基金都在增加。很明显,有利条件在增多,不利条件在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有意识地加强组织、协调,就会使我国传播学的研究发展得更快、更好。这种协调,最好是能成立中国传播学研究会。如果一时办不到,也可以通过两年一度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进行。因为我国传播学研究,当前从主体上看,还是一种追赶式研究,合理使用人力、经费,就可以使重点课题得到保障,同时避免低水平重复。
学术研究的协调,不是“计划经济”式的指令,而主要是通过过信息交流、咨询建议来实现。其实现方式主要是:
(1)拟出近期、中期可供翻译介绍的国外重要传播学著作(包括一些重要论文)目录。为此,可以成立顾问委员会,由中外学者组成(要有一定数量的海外华人学者),请他们推荐。现在,国外传播学研究有日益庞杂之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这样做。
(2)向某些研究者建议需要研究的课题,需要撰写的中观研究的书籍。
(3)向社科基金或其他基金提出关于需要招标资助的课题的建议。
(4)回答各地研究者关于哪些课题已有人研究之类的询问。(或定期在有关刊物上公布正在进行研究的课题名称、主持人姓名,以及尚未有人研究的项目)
(5)联系社会捐助者,资助传播学研究课题。
前面已经提到,组织协调并不意味着指令、指派。传播学者可以在极其广阔的范围内,自由选择题目进行研究。传播学研究在中国还属于“跑马占地”的阶段,没开垦的土地还多得很。各人发挥自己特长,有的可以沿着西方传播学研究的路子走,跟踪国外研究成果同时自己也进行研究;国学基础好的,可以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宝藏。外语条件好的,可以多做些翻译介绍国外传播学著述的工作。总之,不能强求一律,更不能互相指责对方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谁的建树,都是传播学园地上的收获。
注释:
① 陈力丹《对我国传播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现代传播》1995年第4期第27页。
② 陆晔、潇湘《传播学的多元视角与多维框架—’99年国际传播学第49届年会述评》,《现代传播》1999年第4期第19页。
③ 林之达《论传播致效的中介——心理能》,打印稿。
④ 喻国明《从传—受互动方格看亚运会报道》,《体坛纵横》1986年第1期。
⑤ 孙旭培《学术规范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新闻大学》1999年春季号第14页。
⑥ 孙旭培《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⑦ 参见任湘怡、陈思吉力《科索沃的螺旋》,《现代传播》1999年第4期第33页。